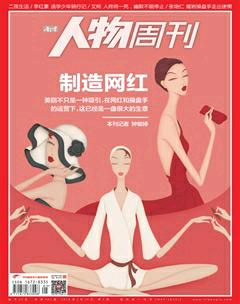絕對會失敗的人生計劃,定還是不定?
當年申請研究生院,每人得交一篇“個人陳述”,套路大致是先吹噓一下自己的過去,再羅列一下現在,最后展望一下未來——5年后,你會在哪里?做什么?
可愁死我了。
我討厭計劃,因為我的計劃總不靠譜。幾年后不小心翻出來,恨不得把時間倒撥幾秒,免得記起自己身在井底時立下的志向——先滅少林,再滅武當……別人覺得你蠢無所謂,最痛心的是自己都覺得自己蠢。
那就定個“腳踏實地”的計劃?做起來才發覺意外頻出——每個讀過博、結過婚、創過業的人,誰不曾在長夜涕下而太息——當初我怎會定了這么個狗計劃?
索性放棄一切計劃,車到山前必有路,且走一步看一步。王陽明兵法曰,“此心不動,隨機而動。”我這么想著,這么做了。結果呢?心也亂動,身也亂動,頭破血流,只好在南墻根下,躺倒不動。
假如你的計劃注定會失敗,定,還是不定?
哈佛商學院的克萊頓·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建議,人生計劃必須有,但須換個思路,像企業定戰略那樣去制定。
傳統的計劃方式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它基于幾個假設:①我已經掌握了足夠詳盡、足夠準確的信息;②我能根據這些信息預見未來;③我所定的計劃適用于我所預見的未來;④我定能堅持到底,贏得勝利!
很遺憾,這些假設統統不成立。93%的成功企業曾“轉換過戰略”,換言之,就是“一開始的計劃行不通”——這還是成功者的數據。失敗者則不必說了,100%。
在不確定性越來越多的今天,更可能的狀況是:①掌握的信息不足或者不準確;②黑天鵝意外頻出,預測的未來完全錯誤;③盡管正確地預見了未來,但計劃卻不適用;④未來全中,計劃合宜,但執行崩了……成功雖在望,壯士已斷腕。
所以,當失敗幾率非常大時,你需要制定一個“受發現不斷驅動的計劃”(discovery-driven plan),簡稱DDP計劃。
沃頓商學院的伊恩·麥克米蘭(Ian MacMillan)和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的麗塔 ·麥格拉思(Rita McGrath)認為,要制定一個DDP計劃,必須自問如下問題:
我這個計劃背后,存在哪些假設?
我需要證實哪些假設,來說明這個計劃是可能成功的?
在“代價越小越好,速度越快越好”的前提下,我如何一一檢驗這些假設?
收集到什么樣的數據時,我可以對這個計劃追加投入?
收集到什么樣的數據時,說明這個計劃完全失敗,我必須中止計劃?
他們建議,把計劃定成“走一步看三步”,事先定好3個“檢查點(checkpoint)”。你的資源(精力、人脈、財富)必須分批投入,一開始投入的資源只夠抵達第一個“檢查點”,到達后,根據收集到的反饋,修正計劃,重新設定未來的3個“檢查點”,再投入部分資源……如此不斷反復循環。
一個人要像一家公司,一段人生要像一連串創業,一次創業要像一場科研。而每天,都是人生科研的實驗直播。
你要有實驗目的,要仔細研究你的假說,要定出走一步看三步的實驗計劃……最后,假如收集的數據跟你的假說不符,不要畏懼改變假說,不要畏懼推倒重來……人生啊,最糟糕的不是計劃失敗,而是明知計劃失敗,你卻咬牙堅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