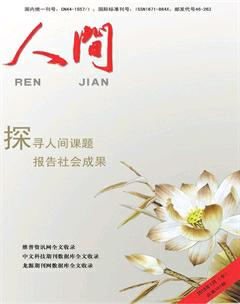論《紅巖》中革命英雄主義者與個(gè)人英雄主義者的家庭觀念
趙靚 汪俊 孫櫻之(浙江師范大學(xué),浙江 金華 321000)
?
論《紅巖》中革命英雄主義者與個(gè)人英雄主義者的家庭觀念
趙靚 汪俊 孫櫻之
(浙江師范大學(xué),浙江 金華 321000)
摘要:《紅巖》中,革命英雄事跡可歌可泣。江姐、許云峰、雙槍老太婆等,為祖國(guó)的命運(yùn),走出家庭,舍小家為大家。比起傳統(tǒng)小說(shuō),《紅巖》并沒(méi)把家庭與愛(ài)情作為作品靈魂。這從四對(duì)愛(ài)人:江姐與彭松濤、雙槍老太婆與華子良、劉思揚(yáng)與孫明霞、華為與成瑤的身上可看出一共同點(diǎn),即為了革命而戰(zhàn)勝苦難,經(jīng)歷坎坷,同時(shí),也抵御住“家”與“愛(ài)情”的誘惑,這便是《紅巖》中正面人物即革命英雄主義者的家庭觀念。當(dāng)然,作品中的甫志高是作為一個(gè)反面人物,為了成全“小家”幸福,犧牲“大家”利益,背叛戰(zhàn)友,這便是《紅巖》中反面人物即個(gè)人英雄主義者的家庭觀念。
關(guān)鍵詞:革命英雄主義;個(gè)人英雄主義;家庭觀念
一、前言
《紅巖》創(chuàng)造了一系列不再具有真實(shí)人性的普通人,而是具有高度的歷史使命和堅(jiān)定的革命意志的英雄。同時(shí),很大程度上也變成了作者筆下,在特定年代中的意識(shí)形態(tài)化的符號(hào)。本文,立足于《紅巖》中典型革命英雄人物的家庭觀念來(lái)論述革命與家的關(guān)系,并對(duì)“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對(duì)于“真實(shí)人性”的篡改這一文學(xué)現(xiàn)象作一番分析。
二、革命英雄主義者“豁達(dá)”的家庭觀念
(一)革命英雄主義者“豁達(dá)”的家庭觀來(lái)源于他們對(duì)于“共產(chǎn)主義”的執(zhí)著追求。在充滿炮火的年代,他們不僅目睹了自己的同志被國(guó)民黨反動(dòng)派或秘密或公開(kāi)的迫害,而且他們自己也生活在白色恐怖中。革命形式的嚴(yán)峻與生活環(huán)境的惡劣,使得他們更加堅(jiān)定了對(duì)共產(chǎn)主義的信仰,也讓他們逐漸拋棄了“狹隘”的家庭觀念,主動(dòng)先服從“大家”、靠近“大家”、服務(wù)于“大家”。如:劉思揚(yáng)與妻子孫明霞一直負(fù)責(zé)共產(chǎn)黨《挺進(jìn)報(bào)》的抄錄,由于甫志高的背叛,最后被捕。劉思揚(yáng)作為資產(chǎn)階級(jí)出生的少爺,并沒(méi)有像其他同志一樣被嚴(yán)刑拷打。但這一特殊的優(yōu)待反而讓他很痛苦。“他覺(jué)得自己的衣著太好,又沒(méi)有受刑,難免要引起別人對(duì)他的懷疑,甚至遭到歧視。”于是,他在獄中主動(dòng)要求去做一些苦役,用監(jiān)獄中的肉體鍛煉來(lái)消除自己出生于剝削者“資產(chǎn)階段家庭”的罪惡。當(dāng)他的哥哥把他從監(jiān)獄里解救回“小家”之后,他卻千方百計(jì)地想回到監(jiān)獄,回到戰(zhàn)友的身邊,與革命“大家”中的戰(zhàn)友們患難與共、同生共死。
(二)革命英雄主義者不排斥小家庭的存在,但能做到無(wú)日常生活的情感。對(duì)于江姐與彭松濤、雙槍老太婆與華子良、劉思揚(yáng)與孫明霞、華為與成瑤四對(duì)愛(ài)人,當(dāng)“小家”與“大家”產(chǎn)生沖突時(shí),他們?yōu)榱恕按蠹摇保闳粵Q然地選擇舍棄“小家”。他們總是能夠很巧妙地處理好“小家”與“大家”的關(guān)系,最終贏得同志們的尊敬與愛(ài)戴。一般而言,丈夫犧牲是對(duì)作為女人、作為妻子的婦女的最大挑戰(zhàn),也是“永世難忘的痛苦”。并且,從這一刻開(kāi)始,江姐心中那馬克思與燕妮式的“小家”徹底破滅,只剩下了“大家”,“前仆后繼”的革命理想成為了她活下去戰(zhàn)斗的唯一力量與信念,使她在極大的打擊之時(shí)壓住內(nèi)心極大的痛苦,方寸不亂。令人難以想象的是,在革命英雄的眼里,另一半永遠(yuǎn)是先戰(zhàn)友,后同志,最后才是丈夫。正因如此,他們?cè)凇靶〖摇北黄茐闹螅芤宰羁斓乃俣绕綇?fù)悲傷的心情,重拾繼續(xù)戰(zhàn)斗與革命的力量。在他們身上,黨性和階級(jí)性遠(yuǎn)遠(yuǎn)得大于“真實(shí)的人性”。這就是革命英雄主義的體現(xiàn)。革命英雄主義者之所以與個(gè)人英雄主義者不同,與凡人不同,并不是因?yàn)樗麄儧](méi)有最正常的那般情感,而是因?yàn)樗麄兡軌蚩朔€(gè)人的情感,包括對(duì)于家庭與愛(ài)情的渴望與追求。在革命面前,個(gè)人的“小家”幸福與個(gè)人的喜怒哀樂(lè)讓步于“政治”,讓步于“大家”。
(三)革命英雄主義者在意志上、思想上都折射出階級(jí)性和黨性。《紅巖》這部作品中,作為共產(chǎn)黨員的革命英雄們,接受著“馬克思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的熏陶。對(duì)于“馬克思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馬克思,他們視其為楷模。他們學(xué)習(xí)著“馬克思主義”,同時(shí)也向往著馬克思與燕妮的那種家庭,既美好又能在革命事業(yè)上相互促進(jìn)、相互鼓勵(lì)、相互扶持。如:“江姐的情緒,被華為牽動(dòng)了。她想象著華為的媽媽?zhuān)肽钪湍怯⑿劾咸艖?zhàn)斗在一起的自己的丈夫彭松濤。分別一年了,今天就可以重逢,就可以見(jiàn)到他,而且在一起過(guò)著新的戰(zhàn)斗生活。這怎能不使她興奮激動(dòng)啊!”這段話很好的印證了《紅巖》中,以江姐為代表的革命英雄們的一種家庭觀念,在他們看來(lái),家人不僅僅是日常生活中的伴侶,更是精神層面和革命戰(zhàn)斗生活中的戰(zhàn)友、同志。
三、個(gè)人英雄主義者“狹隘”的家庭觀念
甫志高開(kāi)始是負(fù)責(zé)黨內(nèi)經(jīng)費(fèi)運(yùn)轉(zhuǎn)的重要人物,曾是一個(gè)比較稱(chēng)職的小負(fù)責(zé)人。但在紛繁復(fù)雜的革命斗爭(zhēng)中,他漸漸迷失,革命英雄主義漸漸消退,個(gè)人英雄主義逐漸上升。從甫志高叛變一事,可以分析出以他為代表的“個(gè)人英雄主義者”的“狹隘”的家庭觀念。
(一)對(duì)個(gè)人“小家”權(quán)力的追求。甫志高對(duì)于權(quán)利的追求體現(xiàn)了“封妻蔭子“的思想。他要求更多工作,執(zhí)意擴(kuò)建書(shū)店,悉心發(fā)展陳松林和鄭克昌,都是為了追求更大的權(quán)力而“封妻蔭子”,是一種貪婪的欲望。
(二)對(duì)以往成績(jī)的自滿,造就自我封閉。甫志高曾是一個(gè)負(fù)責(zé)黨內(nèi)經(jīng)費(fèi)運(yùn)轉(zhuǎn)的重要人物,也曾得到了組織上的認(rèn)可。于是,他便固守自己以前取得成績(jī)所用的工作方法,不知與時(shí)俱進(jìn),也不知繼續(xù)學(xué)習(xí),甚至是自我封閉,于是對(duì)江姐、老許的批評(píng)與建議置之不理,甚至覺(jué)得可笑。
(三)思想意志的薄弱,虛榮心容易得到滿足。在徐鵬飛的嚴(yán)刑拷打之下,在特務(wù)們的物質(zhì)誘惑之下,甫志高投降了。但最重要的是,甫志高自身的思想意志相當(dāng)薄弱,無(wú)堅(jiān)定的信念,黨性也不夠強(qiáng)大,導(dǎo)致虛偽又虛榮。最終,因?yàn)橐粋€(gè)甫志高的出賣(mài),無(wú)數(shù)同志受到牽連。在他的身上,無(wú)“大家”大局意識(shí),有的只有為己的自私與虛榮。這里頭,就有他“狹隘”的家庭觀念在作怪。
四、結(jié)語(yǔ)
《紅巖》是一部17年文學(xué)中的一部過(guò)渡性作品,但是在這部作品中,革命與家的關(guān)系的得到了高度、成熟的體現(xiàn)。體現(xiàn)了“英雄無(wú)家”這一主題,選擇革命“大家”還是選擇個(gè)人“小家”,這就決定了在文學(xué)作品中最終是英雄形象還是反面形象。江姐的挽聯(lián)“是七尺男兒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還家”便是那個(gè)充滿炮火的年代里革命英雄們最好的寫(xiě)照。
參考文獻(xiàn):
[1]周澤.論《紅巖》中的家庭觀念[A].長(zhǎng)江大學(xué)文學(xué)院,2010,(04)
[2]羅廣斌、楊益言.紅巖[M].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2
中圖分類(lèi)號(hào):G205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671-864X(2016)01-00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