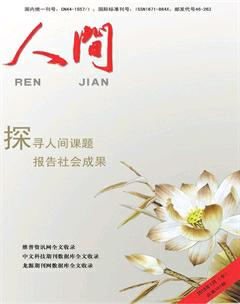徐冰作品《天書》研究
石瑞
(華南師范大學(xué),廣東 廣州 510631)
?
徐冰作品《天書》研究
石瑞
(華南師范大學(xué),廣東 廣州 510631)
摘要:徐冰是85美術(shù)新潮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觀念藝術(shù)家。徐冰的作品《天書》,激發(fā)了國(guó)人對(duì)于觀念藝術(shù)的進(jìn)一步了解。本文通過對(duì)徐冰作品《天書》的分析和解構(gòu),意圖揭示《天書》和其創(chuàng)作理念。本文立足于前人對(duì)于《天書》的研究基礎(chǔ)之上,加之自己的一些想法,亦可謂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完成了這篇論文。在這里,謹(jǐn)向藝術(shù)界的前輩致敬!
關(guān)鍵詞:觀念藝術(shù);天書;徐冰;文字;意義
一、《天書》的簡(jiǎn)介
《天書》的制作始于1987年,當(dāng)時(shí)他在央美的一個(gè)10多平的小房間里開展自己的創(chuàng)作。這些都及其需要耐心和毅力,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情。這些字讀不出來,在我們的傳統(tǒng)思維中,讀不出來的字就是無意義的字。但當(dāng)徐冰將這些字用雕版印刷印出來并裝幀成線裝書之后,就立刻呈現(xiàn)出它了的當(dāng)代性。它有著無可挑剔的形式,它詮釋了作者的內(nèi)心,但是它無法與人們交流。這件藝術(shù)品就是《天書》。這部作品第一次開始參展后就一直是熱烈討論的對(duì)象。據(jù)說有位老藝術(shù)家去看了這部書,卻沒有一個(gè)字能辨認(rèn),“這讓他很惱火”。有讀者說:“這部作品是他對(duì)文化依賴的警告。” 徐冰自己評(píng)價(jià)《天書》說:“這是一個(gè)比較完備的作品,它的完備是因?yàn)樗裁炊紱]說,十分嚴(yán)肅、認(rèn)真,又荒誕模糊,充滿矛盾。”
(一)《天書》的背景。
徐冰創(chuàng)作天書有其特有的歷史背景。隨著1976年“文革”的結(jié)束,全國(guó)的政治空氣開始緩和起來,“人的覺醒”也在藝術(shù)領(lǐng)域有著不同以往的表現(xiàn)。西單民主墻的出現(xiàn),藝術(shù)界中“星星畫會(huì)”的成立及其不同于以往的展覽形式,這些都讓我們感受到了自由和解放。盡管“星星畫會(huì)”的藝術(shù)家大多都不是專業(yè)的人才,但在當(dāng)時(shí)也引起了不小的轟動(dòng)。盡管如此,從總體上講,1976至1978年是“造神”運(yùn)動(dòng)的延續(xù),藝術(shù)家們打破長(zhǎng)期以來的固定藝術(shù)思維模式難度很大,思想鉗制對(duì)他們的影響太大,英雄式的表現(xiàn)形式還是主流,這一現(xiàn)象在中年藝術(shù)家中更為常見。他們很想改變現(xiàn)狀,很想跟隨潮流,但是又沒有好的例子可以參考,所以他們?cè)谒囆g(shù)上的解放之路走的也頗為艱難,很大程度上還是皈依于傳統(tǒng)和本土。
隨著國(guó)門的打開,中國(guó)與西方國(guó)家的交流增多,尤其在文化藝術(shù)方面表現(xiàn)尤為活躍。青年學(xué)生總是最先對(duì)新鮮事物產(chǎn)生好奇的群體,他們的敏感度相當(dāng)高。80年代前半期,各個(gè)地區(qū)各個(gè)院校的青年學(xué)生都迅速成長(zhǎng)起來,他們強(qiáng)烈要求自由和個(gè)性的解放,當(dāng)代藝術(shù)的現(xiàn)狀已經(jīng)無法滿足社會(huì)的需求,亟待進(jìn)步。這時(shí)期,西方印象派與現(xiàn)代派藝術(shù)的書籍和畫冊(cè)、各類西方哲學(xué)和文學(xué)藝術(shù)理論著作開始被大量翻譯進(jìn)來,形成了一股“文化熱”潮流。西方現(xiàn)代拋棄了以往的創(chuàng)作樣式,不再拘泥于寫實(shí),給了正處于尋找和釋放自我個(gè)性的中國(guó)年輕藝術(shù)家以指引,又加之“文革”時(shí)期的文化沙漠導(dǎo)致的無書可讀的遺憾,此時(shí)的知識(shí)分子陷入了一種“瘋狂”的狀態(tài),什么書都要讀上一讀,這也是特別的時(shí)期造就了特別的現(xiàn)象。
這些書籍給人們帶來反思和疑惑,書中講到的觀念藝術(shù),對(duì)國(guó)人來說是一個(gè)全新的領(lǐng)域,好像發(fā)現(xiàn)了新大陸,突然覺得原來還可以這樣去表現(xiàn)藝術(shù),表現(xiàn)自我。1985年是一個(gè)特別的時(shí)期,中國(guó)當(dāng)代美術(shù)界風(fēng)起云涌,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全國(guó)各地突然涌現(xiàn)出的一百多個(gè)藝術(shù)家群體,他們辦展覽、發(fā)宣言,倡導(dǎo)中國(guó)現(xiàn)代藝術(shù),正是這些群體的思想和活動(dòng)構(gòu)成了“85美術(shù)運(yùn)動(dòng)”,在社會(huì)和藝術(shù)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和爭(zhēng)議。在這股轟轟烈烈的新潮運(yùn)動(dòng)中,出現(xiàn)了很多標(biāo)新立異的藝術(shù)家,他們給中國(guó)藝術(shù)界帶來一股生機(jī)和活力。不少人開始以文字為媒介進(jìn)行創(chuàng)作,之所以選擇這一媒介是因?yàn)闀ㄊ侵袊?guó)的傳統(tǒng)藝術(shù),他們想要?jiǎng)?chuàng)新,但是創(chuàng)新也需要依據(jù),需要基礎(chǔ),這個(gè)時(shí)候中國(guó)的傳統(tǒng)藝術(shù)就發(fā)揮了它們的光和熱。在書法中加上全新的藝術(shù)觀念就是一件新的藝術(shù)作品,或者直接用現(xiàn)成的書籍和印刷字體作為材料進(jìn)行創(chuàng)作。這既與中國(guó)傳統(tǒng)的強(qiáng)大慣性有關(guān),又受到了當(dāng)時(shí)涌進(jìn)的西方現(xiàn)代藝術(shù)思潮和大眾文化媒介形式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在當(dāng)時(shí)新潮藝術(shù)家主張徹底拋棄或者對(duì)傳統(tǒng)藝術(shù)進(jìn)行改造,這一趨勢(shì)迫在眉睫,藝術(shù)家們開始向西方現(xiàn)代派學(xué)習(xí),與此同時(shí),一些刊物在藝術(shù)運(yùn)動(dòng)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美術(shù)》、《中國(guó)美術(shù)報(bào)》、《江蘇畫刊》、《美術(shù)思潮》等,成為許多新潮思想的發(fā)生場(chǎng)和傳播場(chǎng)。而在這股激烈和熱情的浪潮中,徐冰又做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他發(fā)表了一篇文章——《版畫要精美》。那時(shí)新潮藝術(shù)家關(guān)注點(diǎn)已經(jīng)變了,觀念上的銳意革新才是一件藝術(shù)品的靈魂,相反,對(duì)技法的要求已經(jīng)不那么嚴(yán)格。所以徐冰的這篇論文很突兀。他笑稱自己走的是一條“愚昧”的路線,并且,這種“愚昧”也成為其作品的養(yǎng)料。每個(gè)人的成長(zhǎng)都是和自己的家庭環(huán)境密不可分的,這將會(huì)對(duì)自己的性格和行為產(chǎn)生極大的影響,徐冰也不例外。
徐冰出身書香門第,也許是對(duì)書本天生的渴求,一有機(jī)會(huì)他就讀書,1984年徐冰在考取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碩士的這段時(shí)間里讀了很多書。
對(duì)于自己的創(chuàng)造才能徐冰非常看重,也很珍惜。下鄉(xiāng)插隊(duì)的經(jīng)歷也在徐冰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起著或隱或顯的影響,他小時(shí)候在北大的圖書館時(shí)期就培養(yǎng)了自己對(duì)書籍和文字的敏感度,這一經(jīng)歷使他對(duì)書籍和文字特別感性,這一特質(zhì)在他下鄉(xiāng)插隊(duì)時(shí)期也有表現(xiàn)。1975年,徐冰作為知青,插隊(duì)到北京郊區(qū)的農(nóng)村,做一些相關(guān)的文藝工作,包括宣傳,或者在黑板上畫畫,做大字報(bào)。這些工作越來越熟練之后,徐冰也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yàn),他和其他知青還有當(dāng)?shù)剞r(nóng)民一起做了一個(gè)刊物,叫做《山花爛漫》,各自都有不同的分工,徐冰做其中的美工。這些都給他創(chuàng)作《天書》打下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這在后面的創(chuàng)作過程中都會(huì)一一體現(xiàn)出來。美工需要做的工作很多,當(dāng)時(shí)的徐冰除了負(fù)責(zé)插圖、刻印,還要對(duì)字體的不同風(fēng)格、樣式進(jìn)行研究,徐冰每天都沉浸在對(duì)不同報(bào)紙、雜志等刊物的字體差別、變化的鉆研中,這些都是以后進(jìn)行創(chuàng)作的資料,是基礎(chǔ)。而參與創(chuàng)制《爛漫山花》還有更大的意義,《爛漫山花》已被視為徐冰早期的代表作,被視為版畫和刻印技巧的精美制作典范。
另外,文革中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并沒有因文革的結(jié)束而消散。80年代前衛(wèi)藝術(shù)中的“禪宗熱”好像是它的繼續(xù)。這一思想也確實(shí)極大地沖擊了保守的藝術(shù)觀念。
(二)對(duì)《天書》的分析和解構(gòu)。
《天書》這件作品,在材料的運(yùn)用上選擇了“文字”為主體物,這里的文字按其自身語言,我們可以分為三類:一種是我們?nèi)粘I钪锌梢杂|及的,手寫體,電腦體,以及中國(guó)印刷術(shù)的印刷文字,我們統(tǒng)稱它們?yōu)槲淖值耐庠谡J(rèn)知性;另一種是文字材料與社會(huì)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第三類即文字材料。《天書》之所以很成功,這三種文字材料起了很大作用,是關(guān)鍵所在。《天書》的成功還在于它的空間布置上。
徐冰所制作《天書》所用的媒材是繁體字,繁體字具有象形文字的功能,但又不像象形文字那么生動(dòng),它的象征性質(zhì)更多一些,是一種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在文字的選擇上,徐冰用的是最簡(jiǎn)單的宋體,他希望作品一出現(xiàn)在觀眾面前,大家感受到的是熟悉的感覺,下意識(shí)的會(huì)去讀這些文字,會(huì)以為這就是繁體字,是可以釋讀的。但是真要去細(xì)細(xì)品味的話,又發(fā)現(xiàn)每個(gè)字都不認(rèn)識(shí),只是一些字的偏旁部首胡亂的組合在一起,阻隔了文字與人之間的交流,每一個(gè)文字感覺都無法參透。在我們的觀念中,文字就是要表達(dá)意思的,在這種原則上,對(duì)徐冰的文字出現(xiàn)了無法閱讀,但又無法否定其存在意義的兩難境地,文字失去了原本的溝通和交流的功能,就成了一個(gè)錯(cuò)亂的系統(tǒng),切斷了人們正常理解和交流的方式,觀眾就迫不及待的想找出一種新的可以去解讀它們的方法。而徐冰正是希望觀眾產(chǎn)生這樣一種心理反應(yīng),自己參與到作品中去,猜測(cè)其中的含義,這樣每個(gè)人感受的東西都會(huì)不一樣。這就是他對(duì)《天書》中文字材料選擇的用意所在,既能表達(dá)文字的外在認(rèn)識(shí),又打破了其社會(huì)普遍認(rèn)知度。在這樣一個(gè)80年代的文化熱時(shí)期,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處于從文革中的文化冷漠到文革后的文化狂熱時(shí)期,人們對(duì)于生活、對(duì)于文化有太多的爭(zhēng)論,徐冰就是用這本《天書》表達(dá)了他對(duì)當(dāng)時(shí)文化熱看法的冷靜對(duì)待。
1989年,徐冰的“天書”第一次展出,就在藝術(shù)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藝術(shù)家和評(píng)論家等都在對(duì)此作品議論紛紛,重說紛紜。老一輩的學(xué)者和藝術(shù)家大多還是很肯定天書的積極意義的,這部作品有一定的突破性,打破常規(guī),其創(chuàng)作理念與西方觀念藝術(shù)不謀而合。同時(shí),前輩們也給了徐冰一些善意的建議。
《天書》爭(zhēng)議最大的部分集中在作品的“內(nèi)容”上。一說到字的內(nèi)容,人們很容易就聯(lián)想到字所表述的含義,但是徐冰的“字”都是一些無法辨認(rèn),偏旁部首隨機(jī)組合的無法解讀的“偽漢字”,人們站在巨大的篇幅面前會(huì)產(chǎn)生一種深深的無力感,會(huì)很懊惱,無法起到文字溝通和交流的作用。
從“天書”的內(nèi)容上對(duì)其進(jìn)行否定,是站在把“天書”跟漢字混為一談的角度了,這樣是不正確的。我們應(yīng)該清楚的明白,“天書”是一個(gè)完整的作品,它是由四千多個(gè)“漢字”構(gòu)成的,可以說“天書”這件作品的內(nèi)容就是這四千多個(gè)“漢字”。《天書》中“漢字”作為單獨(dú)的個(gè)體,其內(nèi)容是被抽空的,在表達(dá)內(nèi)容和承載信息這方面它是無效的。即便是這樣,也不能說“天書”沒有內(nèi)容,正因?yàn)檫@些一個(gè)個(gè)的“偽漢字”失去了特定的含義,變的不確定和模糊,無數(shù)這樣的字體組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的篇幅,對(duì)人的震撼是極大的,其形成了一股強(qiáng)大的力量——鋪天蓋地的形似漢字的“偽漢字”同時(shí)涌入腦墻,卻沒有任何一個(gè)“字”是能夠傳達(dá)給你信息。人們慣性思維是看文字一定要看意思,當(dāng)沒有意義可解讀的時(shí)候,觀眾會(huì)對(duì)此作品產(chǎn)生懷疑。同時(shí),也會(huì)對(duì)自身產(chǎn)生懷疑,“見到文字就要讀”和“見到作品就要解讀”的思維慣性真的好嗎?
因此,從這個(gè)角度看,徐冰做的很好,他把漢字的內(nèi)容抽空之后反而更賦予了其無限的內(nèi)容。徐冰的意圖就是使作品內(nèi)容針對(duì)人們的一種慣性。“天書既是對(duì)具有弱點(diǎn)和局限的語言的一種政治性揭示,同時(shí)又是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書寫規(guī)范的皈依。”
二、《天書》的意義
“天書”的意義從形式語言之中就能一目了然,具體來講形式語言就是版式、字體,以及作品的展示方式。在制版技術(shù)上,徐冰選擇了宋代的活字印刷技術(shù),這一印刷術(shù)有它不足的地方,制作大批量的印刷和字?jǐn)?shù)多的書籍等類似作品,這種印刷術(shù)就明顯不行了,所以很快被淘汰,但這種制版技術(shù)的確是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一部分。在“天書”的版式上,每頁有多少行,每行有多少字,字的大小選擇,還有“天頭”、“地角”、“魚尾”等都有嚴(yán)格的要求,是按照古籍善本的方式制作的,再結(jié)合字體的選擇,最終徐冰選擇了“明體”的裝訂和印制形式。“天書”使用的是宋體字,但宋體字并不是宋代使用的字體,而是隨著印刷術(shù)的不斷發(fā)展,直到明代,刻工們找到的一種比較簡(jiǎn)易的刻字方法,幾刀就可以刻完一個(gè)字,但字的形式橫平豎直,也就是后來的宋體字,在臺(tái)灣被稱為“明體字”。宋體字的字形并不是由某個(gè)人發(fā)明的,而是在不斷刻書的過程中,刻工們對(duì)比不同的字體選擇的一種最便利雕刻的字體風(fēng)格,它是集體創(chuàng)造的結(jié)果,作為最常用的印刷字體就要求筆劃形式的規(guī)范,因此,宋體字摒棄了更多的個(gè)性色彩,是最沒有個(gè)性的一種字體,而對(duì)于筆觸、筆劃等個(gè)性的摒棄即是對(duì)指向性和內(nèi)容的拋棄,這樣的“天書”就只剩下被抽空內(nèi)容的形式。另外,宋體字后來發(fā)展成為中國(guó)大陸的官方印刷字體,所有正式的公文、書信等的書寫也都一般用此字體,代表著權(quán)威和嚴(yán)肅。因?yàn)樾毂趯?duì)宋體字的選擇上特別的注重,以及對(duì)善本版本也十分考究。這樣一來,雖然作品充滿了荒誕和戲謔,卻不會(huì)讓人覺得胡鬧,他很嚴(yán)肅、鄭重并且認(rèn)真的對(duì)待這件作品。每一個(gè)步驟,在技術(shù)上越傳統(tǒng),概念上就越現(xiàn)代,越嚴(yán)格就越荒誕,對(duì)讀者越拒絕就越具有吸引力,越是把文化擺在一個(gè)輝煌的祭壇中,對(duì)它的質(zhì)疑就越強(qiáng)。
“天書”是一件有意義的作品,它的獨(dú)到之處是不可否認(rèn)的,這是一種觀念藝術(shù),它的意義不僅表現(xiàn)在嚴(yán)肅考究的形式語言所制造的巨大荒誕性上,其表現(xiàn)出的高度學(xué)術(shù)性也使其區(qū)別于同時(shí)期的其他新潮藝術(shù)作品和現(xiàn)代藝術(shù)作品。尹吉男指出,新潮美術(shù)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探索性,但是普遍來講學(xué)術(shù)性不足,徐冰的展覽最大的特點(diǎn)體現(xiàn)在學(xué)術(shù)性上。新潮美術(shù)時(shí)期觀念主義盛行,人文熱情高漲,很多作品出現(xiàn)了過分注重觀念性而忽視其形式和內(nèi)容的現(xiàn)象,王廣義最先提出對(duì)清理人文熱情必要性的強(qiáng)調(diào)。這種人文熱情的高漲與當(dāng)時(shí)盛行的“禪宗熱”也有一定的關(guān)系。
三、結(jié)論
本章主要講了天書的創(chuàng)作背景、對(duì)天書的解構(gòu)和分析以及天書的意義。文革的結(jié)束、國(guó)門的打開,徐冰下鄉(xiāng)的經(jīng)歷以及他的家庭環(huán)境等都與他創(chuàng)作天書有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對(duì)《天書》的具體分析能更清楚的了解這一作品,更好的去闡釋其與觀念藝術(shù)的聯(lián)系,本文第二章已經(jīng)清楚的講述了觀念藝術(shù),在了解了《天書》的相關(guān)信息以后,它們的聯(lián)系已經(jīng)顯而易見;至于《天書》是否有意義,這又是一個(gè)主觀性的問題,每個(gè)人的想法都不盡相同。
參考文獻(xiàn):
[1]徐冰.析世鑒——世紀(jì)末卷.北京:中國(guó)美術(shù)館,1989
[2]鄒躍進(jìn).新中國(guó)美術(shù)史1949-2000.湖南: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2005
[3]張慧.文字何以成為圖像-徐冰文字藝術(shù)研究.北京: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2014
[4]李燕楠.感受徐冰的裝置作品.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2011
[5]潘冀,周軍.淺析徐冰的文字藝術(shù).絲綢之路,2009
[6]費(fèi)大為.85新潮-中國(guó)第一次當(dāng)代藝術(shù)運(yùn)動(dòn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7]徐金.觀念藝術(shù).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04
[8]王杰泓.中國(guó)當(dāng)代觀念藝術(shù)研究.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12
[9]陳鵬軍.徐冰的四重奏.山西:山西青年,2012
[10]解玉斌.觀念藝術(shù)存在論.貴州:貴州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4
指導(dǎo)教師:王金玲。
作者簡(jiǎn)介:姓名:石瑞,出生年份:1990年,性別:女,民族:漢,籍貫:河北邯鄲,學(xué)校:華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位:碩士,研究方向:美術(shù)學(xué)(中西美術(shù)比較研究)。
中圖分類號(hào):J292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671-864X(2016)01-022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