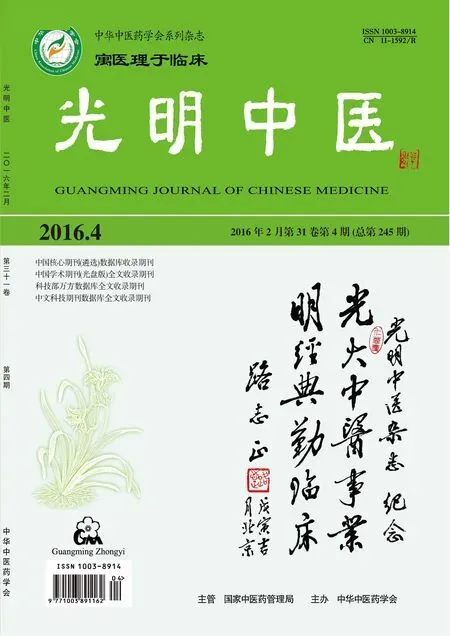試論中醫的科學屬性與發展方向(下)
尹亞東
?
試論中醫的科學屬性與發展方向(下)
尹亞東
河南省舞陽縣人民醫院中醫科(舞陽 462400)
摘要:目的討論中醫的學科屬性和發展方向。方法通過“科學”“非科學”“偽科學”定義及界定標準的溯源,以及中西醫學不同文化基礎、哲學基礎、認識方法、研究方法的討論,確定中醫的學科屬性和研究方向。結果認為構建在經驗總結、演繹推理等“形而上”研究方法上的中醫理論體系是不同于建立在“實證”“實驗”基礎上西醫“科學”理論體系的“非科學”理論體系。所以沒有必要討論中醫的“科學性”,更不需刻意證實其“科學性”。無論以“偽科學”為由對中醫惡意的攻擊或迫害,還是以“科學化”名義對中醫的善意改造或研究,其實都脫離了中醫理論體系的基本屬性,都是對中醫的傷害,都是不可取的。結論中醫是不同于西醫“科學”體系的“非科學”體系。中醫必須在自己特有的文化基礎上,堅持自身獨具的研究方法以保證確切的臨床效果,才能夠存續、發展。
關鍵詞:中醫;西醫;科學;非科學;偽科學;哲學;形而上;形而下
(上接第3期)
4 不能以“科學”的名義認識、研究中醫
法國哲學家保羅·薩特曾經說“他者是自我的墳墓”。因為研究對象和研究目的的相同性,所以對于中醫而言,西醫東漸伊始就成了揮之不去的“他者”[11]。而如果中醫對于自身以及西醫這個“他者”缺乏理性且清醒的認識,不從哲學基礎提供的不同研究方法的特異性上認識彼此,加上西醫“科學”的認識研究方法更簡捷直觀從而讓人更容易接受,那么在這個“他者”的注視之下,中醫肯定就會方寸大亂,就會自覺不自覺的以“他者”(西醫)的思維方法、研究方法來思考、研究中醫,就會直接導致中醫固有的思維和研究方法弱化,進而導致中醫臨床治療效果全面下降,“中醫存在主體性消失的危險”(陸廣莘)也就是當然的結果,最終會導致中醫存在的必要性受到懷疑。
隨著西學東漸尤其西醫的傳入和迅速發展壯大,相對而下是中醫這樣那樣的原因日漸式微。所以為中醫“科學性”的辯護以及把中醫列為“科學”體系的努力,—個多世紀以來,幾乎成了中醫同仁們的首要任務。發展至當前,中醫的教育體系、評價體系、傳承方法、研究方法甚至連思維方法,幾乎都有意無意沿襲了西醫的“科學”模式,還美其名曰“中醫的現代化”,實質其實就是中醫“西化”。中醫包括思維方式、概念、范疇的西化(筆者在《過敏性紫癜對應中醫病名辨析--<中醫外科學>“葡萄疫”命名商榷》一文中討論過此現象[12],后專文討論),已經脫離了中醫賴以生存發展的自身基礎即中國傳統文化,帶來的只能是中醫理論的異化和臨床療效的急劇下降。而確切的療效,恰恰是中醫數千年薪傳不熄的最根本原因。因為醫學,無論科學或非科學體系,祛病延年才是最根本的追求。如果療效再不足以讓受眾信任期待,那么中醫就真的離滅亡不遠了。
但是以此為方向的探索研究目前仍然蓬勃,此處僅舉代表性一例。
有人[13]在政府基金資助之下研究 “中醫藥與時俱進發展路徑”,認為中醫藥日漸式微有四方面原因:中醫學術理論迄今仍停留在陰陽五行階段,是中醫未能超越醫易相通困局的要害;中醫臨床診斷停留在望聞問切、辨證陰陽的經驗醫學層面,是中醫難有發展的癥結;中藥治病原理徘徊在四性五味、升降浮沉和歸經的架構上,是中藥不能長足發展的軟肋;中醫藥時常被究竟是否科學的弱智問題糾纏,是中醫藥事業舉步維艱的根源。
中醫的基礎理論到今天仍然是陰陽五行是事實,但估計很難改變,中醫的基礎理論想越過“醫易相通”也基本不可期待。因為如果抽去了中醫理論中“陰陽五行”的哲學內核,放棄了“形而上”的研究方法,“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不知道中醫理論中可以保留的東西還能有多少,也不知道“失魂落魄”而沒有了自我特質的“四不像”中醫還能不能稱為中醫;臨床上中醫的診斷方法仍然是望聞問切,臨證處方靠辨證陰陽,也是客觀事實。但這些存在是否就是中醫不能發展的癥結所在,就頗值得商榷。就在西醫傳入中國的前夜,堅持“形而上”研究方法的中醫學,在中國醫史上還出現了一個甚至不比目前西醫學治療水平低的、“溫病四大家”治療發熱性傳染病的學術高峰。至于今天中醫醫生診療水平的急劇下降,究竟是被望聞問切、辨證陰陽所禁錮,還是因為沒有了中國文化靈魂的支撐、中醫知識技能的掌握欠火候,已經不能夠真正的辨證施治,卻自覺不自覺在以西醫的思維和研究方法“使用”中藥,因為不倫不類所以才療效退化,值得中醫界同仁們思考;中藥的四性五味、升降浮沉和歸經,包括中醫的經穴認知,筆者至今都深信不疑和“內證”有關。因為無論如何“形而上”的格致推理,基本上不可能得出如此玄妙細致且頗成體系同時在臨床實際施用時又切實可靠的認識。不要因為目前不能“證實”“內證”這種說法就武斷的說是“偽科學”,因為雖然你我不能體驗“內證”,也不能說“內證”就一定不存在。就如無論有沒有“日心說”或“地心說”,太陽和地球其實就在那里自然運轉,認識水平有高低而已。另外,用研究單一化學成分西藥的方法來認識研究成分相當復雜的中藥,是不是就科學?是不是非要研究到分子水平才算科學?而如果非要研究到分子水平,窮一人一生之力能否研究透徹哪怕一種草藥?更何況即使相對簡單的方劑也有相當繁復的藥物組合類型,煎煮之下又有多少不為人知的潛在新物質生成?這種研究方法可以移植來研究中藥嗎?這樣做豈不是沒事找事先把自己搞暈再得出一些莫名其妙的研究結論然后回過頭懷疑否定甚至攻擊中醫中藥理論?如作者所言:是否科學的弱智問題糾纏,是中醫藥事業舉步維艱的根源。但其實,作者此論的基礎仍然是認為中醫屬于“科學”體系,認為中醫需要科學的改造而又不知該如何科學改造的糾結,才是以上四點看法的精神實質。
中醫界尤其不愿認可中醫的“非科學”屬性,仿佛“非科學”就一定是“偽科學”、就是封建迷信。而事實上,被文化自卑所束縛、糾結于中醫是否“科學”的中醫界同仁的心魔,正是中醫發展的真正大敵。因為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如果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都不再被自己認可而想改造,還能奢求體系以外其他人的尊重嗎?所以,中醫百年來不能發展的原因,是否因為外部以“科學”的名義對中醫進行學術壓榨甚至滅絕,以及中醫界自身越來越沉重的文化自卑導致自發的以發展的名義、現代化的名義“閹割”中醫理論的復合作用所導致,尤其值得中醫界深思。
5 走自己的發展道路中醫才有未來
隨著國家社會的快速發展進步及三十多年來西醫學在中國充分發展應用以后所暴露出的局限和不足,中國文化的自尊在回歸,所以中醫存在的必要性已不容置疑。越來越多的國人也在進一步冷靜思考中醫應該的發展方向。中醫當下科學化、現代化和標準化的研究好像代表了中醫目前以及將來發展的主要方向,但這些研究思路均是基于中醫屬于“科學”體系基礎之上的,如果顛覆了這個值得商榷的認識基礎,如此的所謂發展方向就很值得探討。從20世紀50年代我國就開始了所謂的中醫“科學化”進程,歷時數十年,目前的結果卻是中醫虛火不退、病態繁榮。隊伍日漸龐大但真正的名醫大家越來越少。而無論出發點如何,這種“西化”的研究非但沒有贏得“科學”體系西醫的尊重,不倫不類的所謂研究成果恰恰又給了以“科學”為名攻擊中醫者更多口實。實質上就是“努力把中醫偽科學化”的過程。以至于延續至今,國人甚至中醫人自己,在潛意識里就認定中醫是落后的,認為中醫學必然會慢慢消亡,西醫學逐漸成熟壯大,就是醫學科學發展的終極趨勢[14]。
正如楊振寧所說,中醫基礎理論確實是沿襲了《易經》“形而上”的哲學思路,而不是近代科學化實驗或實證的“形而下”的研究思路和手段[15]。相較于屬于“科學”體系的西醫,中醫“非科學”的屬性特征是明顯的。相對于注重“實證”“實驗”的西醫科學體系,中醫“形而上”的經驗總結,雖不能為西醫理解、認識、接受,但在功能性疾病以及所謂亞健康狀態(所謂“亞健康狀態”,在中醫其實已經可以辨證陰陽、處方施藥以糾正、調整。中西醫學此方面的不同看法另文專論)、耐藥性病原微生物的治療等等西醫學頗受局限的諸多領域,都逐步顯現出了自身獨特的優勢。臨床實踐的有效性,決定了中醫存在的必然性。所以,延續百年以“科學”的名義滅絕中醫的目的,是不可能達成的。中醫屬于“非科學”的范疇,肯定存在有科學的成分,那也只看科學的西醫是不是愿意去研究、去借鑒;而如果可以提高中醫的療效而有中西醫結合的可能,當然也不妨自自然然結合。但中醫界絕不必去刻意逢迎。這其實就是兄弟學科之間的交叉、交流而已,不應該有高低貴賤之分,也不需要去證明什么、解釋什么。所以與學習中醫、研究中醫,尤其是與做中醫,實在不應該有太大的關聯[16]。依靠卓然療效自尊自信的站立,終究強過削足適履、卑躬屈膝去祈求別人的認可。但是目前許多所謂的以現代化的名義對中醫的研究,不但造成了醫療以及科研資源的巨大浪費,客觀上導致了人們對中醫的信任感逐漸喪失,使中醫的發展嚴重偏離了應該遵循的道路和方法。所以中醫不但沒有讓人接受為“科學”,偽科學的質疑卻此起彼伏,中醫萎縮和消失的趨勢反倒在加劇、加速[17]。
另外需要著重說明的是,“非科學”不是“偽科學”,但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轉化為“偽科學”的,而且僅當它冒充“科學”的時候[1]。既然中醫的屬性是“非科學”,那么真的就沒有必要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以及金錢,以所謂的中醫現代化、科學化、標準化的“西化”研究方法,來證明中醫的“科學性”。而且因為方法論與研究主體的不適應,所謂“科學化”的中醫研究結果往往得不到西醫的認可和尊重,所以這樣做的客觀結果,恰恰是把中醫從“非科學”的范疇推到了“偽科學”的境地。而反之,如果認同了中醫“非科學”屬性的正確定位,反而可能與“科學”體系的西醫學形成優勢互補,倒更有可能為衛生事業帶來福音[4]。所以鐘南山院士才會說“這幾十年提出說要中西醫結合,我本人不太贊成。中醫和西醫各有各的方法,還是應該二者齊頭并進、取長補短、共同進步”。鐘院士此論是否受到“非典”中醫藥療效的影響不得而知,但對比中醫業界的文化自卑、道路迷茫,以及某些所謂精英專家們丑化中醫、消滅中醫,不知能否看出底蘊單薄或無知無畏。
綜上所述,中醫是不同于西醫“科學”體系的“非科學”體系。所以某些人以“科學”的名義,武斷的認定中醫是“偽科學”而口誅筆伐、必欲滅之而后快的做法可以休矣。因為“科學”的定義和界定均未明確,且自己都不了解“科學”為何物,所以不必拿無知衍生出的“無畏”,以所謂“科學”的標準來丈量“非科學”體系的中醫;中醫同仁也應該知道中醫究竟是什么、需要怎么發展傳承。千萬不要以現代化的名義、以“西化”的研究方法,盡心竭力對中醫的“科學性”進行證明,卻實實在在是“偽科學”化中醫。以上兩種做法實際上都是對中醫的巨大傷害。作為實用性很強的醫學學科,療效應該是評判其存在合理性的唯一標準。通過扎實學習中國傳統文化打好中醫基礎,通過大量誦讀歷代經典充分掌握中醫理法方藥理論,通過跟師以及不懈的臨床實踐提高中醫藥療效,才是中醫傳承發展的必然途徑。中醫既然是幾千年來獨具體系的客觀存在,中醫的產生和延續又獨具自身特點,那么中醫的發展必然要遵循自身獨具的規律。科學體系不過區區幾百年歷史,通過科學的方法去研究已存在數十億年的生命尤其生命最高形式的人,其實就如讓一個剛出生幾秒鐘的嬰兒去理解、認識一個年富力強學養深厚的成年人,任之重道之遠幾乎不可想象。所以即便幾千年歷史的中醫在無邊無際的生命課題面前同樣也很幼稚,但中醫以“非科學”的方法研究、呵護生命,客觀上是另辟蹊徑,畢竟也多了一種道路選擇。既然中醫西醫都非盡善盡美,而且各有所長、不可替代,我們是否更應該以平和、理性的態度支持中醫體系的存在并努力完善、發展呢?莊子說:井蛙不可以語海者,拘于虛也;夏蟲不可以語冰者,篤于時也;曲士不可以語道者,束于教也(《莊子·秋水》)。真心希望醫界同仁們(包括西醫、中醫)都能于專業技術之外學習一些文化知識、了解一些哲學常識,不要瞎子摸象認識中醫,更不要盲人瞎馬發展中醫,總歸不要再以“科學”的名義繼續傷害甚至毀滅中醫!因為中醫不僅僅屬于中醫人,她還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因為不是哲學專業出身,中醫藥學又博大精深、堂奧難窺,所以粗疏舛錯之處在所難免。以“試論”命題,意在拋磚引玉,歡迎老師們批評指正!
參考文獻
[1]魏屹東.科學、非科學及偽科學的界定[J].自然辨證法研究,1998,14(6):19-20.
[2]馮契.哲學大辭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958-959,963.
[3]李建華.科學哲學[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4:184-191.
[4]陳斌.關于中醫非科學的思考[J].醫學與哲學,2013,34(11A):73-74.
[5]羅素.西方哲學史(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1.
[6]曾仰如.形上學[M].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5:1.
[7]華崗.辨證唯物論大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1,18.
[8]尹亞東,劉書紅.《黃帝內經》與《道德經》養生思想淵源初探[J].河南中醫,2002,22(3):71-72.
[9]鄭志堅,孟慶云,孫濤,等.哲學、科學及中醫的劃分[J].中醫臨床雜志,2011,23(10):914-915
[10]陳治維.影響世界的哲學家[M].臺中:好讀出版有限公司,2003:322.
[11]李明,高穎,李敏.西醫,中醫揮之不去的他者[J].醫學與哲學,2006,27(4A):18-19,42.
[12]邵啟峰,尹亞東,劉書紅.過敏性紫癜對應中醫病名辨析——《中醫外科學》“葡萄疫”命名商榷[J].中醫臨床研究,2014,6(12):89-90,92.
[13]吳紅娟,張效峰.醫易相通的哲學反思[J].醫學與哲學,2013, 34(4A):11-13.
[15]黃利興.對中醫的科學性與未來走向的思考[J].醫學與哲學:人文社會醫學版,2011,32(11):66-67.
[14]楊振寧.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科技發展的影響[N].中國中醫藥報,2005-01-24(3).
[16]張瑞萍,黃超平,尹亞東,等.從腎病治療看中西醫結合[J].中國中醫急癥,2014,23(3):467-468.
[17]張春麗.科學、非科學和偽科學劃界與中醫學的生存與發展[J].醫學與社會,2011,24(4):35-37.
doi:10.3969/j.issn.1003-8914.2016.04.004
文章編號:1003-8914(2016)-04-0463-03
收稿日期:(本文校對:楊建國2015-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