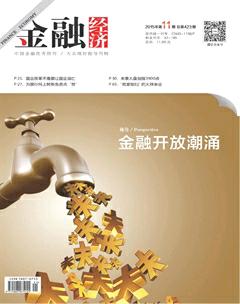通過深層次改革邁向全球金融價值鏈高端
章玉貴

新常態下,中國要在全球頂尖層面的貨幣與金融分工中擁有一席之地并切實維護本國核心利益,就必須盡快筑起“經濟與金融高邊疆”。
新常態下的金融改革開放,其目標指向是在清除金融業發展沉疴的基礎上,前瞻性分析全球金融競爭與產業變遷的趨勢,以銀行業深層次改革、資本市場的新一輪整體設計與配套改革為契機,結合人民幣國際化,以戰略金融人才的培育為牽引,積極參與并爭取主導全球金融產品定價,鍛造中國金融資本力。
深化金融改革,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十二五”即將收官,作為全球超級新興經濟體的中國,在過去五年間的金融改革與發展,既取得了具有指標意義的進步,亦存在著諸多不足之處。而這些不足,恰恰為后續的改革提供了新的行為空間。
眾所周知,金融作為現代市場經濟的核心,本質而言,是基于定價與交易規則的財富分配轉換器,而所謂金融創新,按照筆者的理解,是產業資本創造的剩余價值通過金融資本的轉換創造更大的收益預期。因此,任何層面的金融創新,均離不開實體經濟的效率改進。金融作為最高層面的分工形式,其內生性的創新動力來自于服務實體經濟的匹配度,以及給到市場參與主體的收益預期。
而今,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已經取代美歐日本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引擎,世界經濟力量重心東移的趨勢也日漸明顯。中國順勢推出的一系列具有開發性新特征的金融公共產品也成為最近幾年全球經濟秩序變遷的一大亮點。不過應當看到,中國盡管是迄今為止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之一,中國經濟在過去十年里取得的成就足以令優越感一向強烈的美日等國羨慕,但中國畢竟不是天外來客,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邏輯框架下,2008年的全球危機來臨時沒有任何一個開放經濟體可以置身事外,中國本身也是那場危機的重要受害者之一。中國當時啟動的反危機策略在今天看來的確有值得檢討之處,不過,歷史從來不能假設,在一個巨型經濟體出現增長休克跡象時,手持政策手術刀的操盤手想得最多的,恐怕是如何搶救,之后才會考慮如何治理后遺癥。
如此看來,中國在反危機過程中真正值得檢討的,應該是在經濟企穩之后,及時清理經濟發展沉疴,盡早告別債務驅動型發展模式,將經濟增長軌道切換到依靠內生性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和有效需求驅動的發展軌道上來。但是對各地各級政府而言,要告別長期以來養成的增長偏好一般會無比痛苦。而對新的增長路徑的探索,不僅需要付出難以預料的成本,而且還可能伴隨巨大的不確定,且在既有政績考核機制尚未真正轉變之前,“理性”的地方政府官員們一般不會拿增長的不確定性做政治賭注。因此,盡管最高決策層一直強調要切實轉變經濟發展模式,但落實到具體的執行層面,往往出現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的非合作性博弈局面。
中國經濟在告別低風險發展階段之后,今后要取得新的具有指標意義的發展成就,其所付出的經濟成本以及需要克服的經濟風險都有可能較以往時期的為大。毋庸置疑,中國的投資效率并不高,全要素生產率一直未有實質性提升,經濟增長的邊際成本這些年來一直在加大。而隨著中國幣值的升值、人口紅利的逐漸喪失以及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上升,中國制造業的成本正大幅上升,假如不能通過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的提升來推動中國制造業的整體升級,將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中國實體經濟的競爭力。而一旦新一輪產業和技術革命在美國完成,進而掀起全球范圍內的新一輪分工大洗牌,中國將在失去比較優勢的同時又將失去競爭優勢。誰都知道,中國的王牌是制造業,中國擴充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影響主要依靠的是遍布全球的貿易觸角,假如沒有強大的制造業和貿易價值鏈的全面提升,中國將很快失去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有效支撐。而保持本國貨幣幣值的相對靈活性是中國經濟保持活力的內生性要求。中國當然不能成為國際產業和金融資本低成本獲益的樂園,更不可自縛手腳。只有掌握本國貨幣的定價權,才能保持本國經濟政策的相對獨立性。而這,對于新興經濟體來說是邁向產業與金融強國的基本前提。但是,中國和所有新興經濟體一樣,都面臨著本國金融體系發育不成熟,高端金融專才欠缺的局面,而建設強大的資本市場絕非靠一流的硬件和軟件系統就能達成的;另一方面,盡管中國央行在資產方面早已成為全球首席央行,但央行迄今為止所推出的貨幣政策,并非都匹配中國實際。假如沒有更具前瞻性的發展思維,單單依靠貨幣政策的調整,本身并不能防范金融風險。
盡快構筑“經濟與金融高邊疆”
未來一段時期,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可能不是增長乏力遲滯深層次經濟與社會矛盾的解決,而是在金融深化過程中由于金融直覺不足、監管的遲鈍或缺位導致金融風險敞口在短期內被急速放大,直接引爆系統性經濟與金融風險。宏觀經濟政策的下一步,既要鞏固來之不易的經濟發展成果,更要著力打造資本市場良序,始終將金融的穩健發展建立在對實體經濟有效增長的預期反映上。對于一個沒有太多金融基因且市場與法治尚不健全的中國資本市場,真實世界中的巨大不確定,異常兇險。事實上,A股在今年六七月份遭遇的斷崖式下挫,其對市場信心的摧毀力不啻于金融海嘯的來臨。而從系統性風險的特征來看,由于出現千股跌停,投資者無法及時止損,在這個時間段爆發的風險根本不可能通過分散投資相互抵消或者消除,形成不可分散風險。從經濟學角度而言,意味著股市進入全面市場失靈階段。在此危亡時刻,為了防止市場信心大面積喪失引致全面金融恐慌,唯有央行通過注入流動性履行最后貸款人的職責,這是避免股市崩潰的唯一手段。
過去,中國和廣大新興經濟體異常擔心的國際金融資本在本國制造金融危機,那是因為中國和新興經濟體的經濟與金融漏洞為國際資本制造金融危機提供了可能條件。中國長期施行的金融政策又在逐步強化人民幣和美元之間的無風險套利機制,并允許外資在此機制下自由流動,尋求套利空間。隨著外資不斷涌入及成效不彰的金融產品創新,央行從緊的貨幣政策勢必加劇生產領域中貨幣緊縮和流通領域中貨幣過剩的流動性二元化現象。而金融調控的空間和手段有限以及央行沖銷成本的日益增加、資產價格的膨脹和巨額熱錢流入等已經顯著增加了中短期的金融風險。顯見,國際過剩投機資本大量流入我國,既是規避國際金融市場動蕩的風險,也是對人民幣套匯套利的驅動。如果人民幣匯率持續大幅度升值和資本流動逆轉風險,資產價格大幅波動則從匯率和熱錢問題中衍生出來,倘若沒有金融資本市場銳意進取和創新成功,則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乃至大規模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劇增。
作為經濟規模超過10萬億美元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要在全球頂尖層面的分工中擁有一席之地并切實維護本國核心利益,就必須鍛造中國“金融資本力”。而從提升中國在全球金融業價值鏈獲益程度的角度來說,中國亟需培育可與匯豐、高盛匹敵的超級金融資本。有了這些金融力量工具,才有可能利用其對全球金融定價和金融系統穩定的影響力有效維護國家利益。新常態下,中國要在全球頂尖層面的貨幣與金融分工中擁有一席之地并切實維護本國核心利益,就必須盡快筑起“經濟與金融高邊疆”:建設強大的資本市場、世界級的銀行與保險體系,培育比肩美元的國際貨幣本位幣,打造能與紐約、倫敦抗衡的國際金融中心以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新興產業群,以此擺脫在全球經濟發展與戰略博弈中受制于人的被動局面。
面對全球金融的競爭態勢,中國必須構筑能夠全方位參與金融分工的種子選手,迫切需要總結以往金融發展的經驗,鏡鑒美歐金融業教訓,前瞻性地分析全球金融競爭的未來生態,以制度創新和人才培育為牽引,以深層次改革為牽引,切實推進公司治理改革,加強制度文化建設,提高風險管理水平,加快業務創新和國際化能力建設,并穩步提升對國內投資者和消費者的利益回報和服務品質;形成以國內市場為主體,海外市場與多邊國際金融機構為依托的“一體兩翼”經營格局,力爭培育出一大批真正適應國際化競爭的世界級金融企業,占據全球金融價值鏈的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