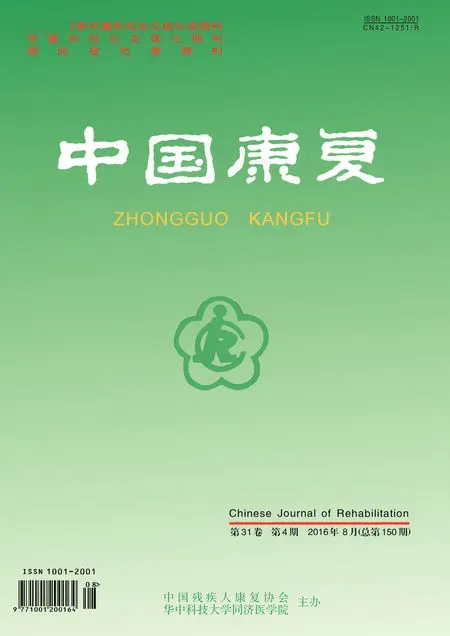焦點解決短期療法聯(lián)合舍曲林治療腦卒中后抑郁的臨床研究
萬其容,汪志宏,胡亞榮,易軍
腦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 depression, PSD)是腦血管病最常見的情緒障礙之一,會影響卒中患者的治療依從性,損害其言語及認知功能,增加致殘率、卒中復發(fā)以及死亡風險[1]。另外,PSD還會給家庭成員帶來經(jīng)濟和心理負擔[2-4],增加社會開支[5-6]。因此,安全、有效、快速、經(jīng)濟的治療方案對PSD患者非常重要。焦點解決短期療法(solution-focused brief therapy, SFBT) 是近20年逐步發(fā)展成熟的心理治療手段,它改變傳統(tǒng)的以“問題為中心”的治療模式,將治療重點放在幫助患者尋求問題的解決模式上,讓患者成為自己行為改變的主導者。SFBT在國內(nèi)很少用于卒中后抑郁患者的治療。本研究采用SFBT對卒中后抑郁患者進行心理干預,觀察PSD患者的情緒狀態(tài)及神經(jīng)功能恢復程度。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3年1月~2014年3月在我院神經(jīng)內(nèi)科、老年病科住院治療的78例腦卒中后抑郁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入選標準:均符合2005年版《中國腦血管病防治指南》關于腦卒中的診斷標準[7],并經(jīng)頭顱CT或MRI檢查確診;符合美國精神障礙診斷與統(tǒng)計手冊第4版(Diagnostic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Ⅵ)抑郁癥的診斷標準[8];抑郁程度采用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24項版本評定[9];自愿參與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書,無溝通障礙。隨機將78例患者分為2組,①對照組40例:男22例,女18例;年齡(69.01±6.13)歲;病程(23.06±5.62)d;腦梗死30例,腦出血10例;大專及以上學歷12例,中等及以下28例;已婚34例,喪偶或離異者6例。②觀察組38例:男25例,女13例;年齡(70.61±3.54)歲;病程(24.81±4.23)d;腦梗死31例,腦出血7例;大專及以上學歷14例,中等及以下24例;已婚31例,喪偶或離異7例。2組患者一般資料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
1.2 方法 2組患者急性期均接受內(nèi)科常規(guī)治療,腦出血患者采用脫水、降顱壓、腦保護劑、對癥支持治療等,腦梗死患者給予改善循環(huán)、抗血小板聚集、溶栓、神經(jīng)保護劑等治療。在內(nèi)科常規(guī)治療基礎上加用抗抑郁藥鹽酸舍曲林片(左洛復)口服,起始劑量為每晚25mg,若無不適第2天可立即加量至50mg/d,1周內(nèi)加至 100mg/d。若有睡眠困難者,給予右佐匹克隆片(商品名:文飛)1~3mg口服。觀察組在常規(guī)治療和舍曲林治療的基礎上,予以焦點解決短期療法,每周1次,每次30min,療程為8周。由一名經(jīng)過SFBT培訓的心理治療師進行,并且心理治療師有督導師。書面記錄每次會晤的治療過程,具體治療過程包括建構解決的對話階段(開場,陳述癥狀,討論例外,奇跡提問,使用量表)、休息階段、正向回饋階段(贊賞)。對話階段引導患者說出困擾,明確問題及目標,要求患者和醫(yī)生共同尋求解決的辦法,治療師記錄患者的問題,此階段目的是喚起患者戰(zhàn)勝疾病的信心和勇氣,不要執(zhí)著于糟糕的癥狀,而是如何更好地改善現(xiàn)狀,獲得正面反饋;休息階段對上一階段中的問題、解決方法和途徑進行回顧,同時治療師根據(jù)患者的問題分析;再次對話進入正向回饋階段,治療師給予肯定和認同。SFBT治療理論假設與治療目標構架簡介如下[9]:①強調(diào)正向積極改變,認同每個人都有力量與潛力去改變;②循序漸進,從小改變起步,卒中患者常對自己的未來喪失信心,認為一旦“偏癱”便成為家庭負擔,若從容易達成的小改變開始,則給他們帶來了成功的信心,愿意繼續(xù)努力,故小改變將帶來大改變,③例外構架,尋找正向的“例外”,例如詢問患者是否有不依賴他人自我處理問題的時候。 ④建構有效解決模式,不糾纏于疾病的預后,積極尋找康復方法;⑤假設解決構架,奇跡問句,水晶球問句等。如:“假如問題都不存在了,你會干些什么”,“假如有一個水晶球能預知未來,你希望看到自己發(fā)生了什么改變?”等引導卒中患者積極行動;⑥評分式問句,類似此類提問“假如10分代表你想要達成的目標,而1分表示最不滿意的狀況,你目前可打幾分?”,“怎樣做才能提高1分?”等,將抽象的目標轉化成具體操作的小步驟,從而引發(fā)下一步的有效行動;⑦家庭作業(yè)。患者在治療期間均進行血、尿常規(guī)、肝腎功能及心電圖檢查,并記錄不良事件。
1.3 評定標準 2組患者在治療前、治療4周和8周后分別進行漢密爾頓抑郁量表、神經(jīng)功能以及日常生活能力評估。①采用HAMD 24項版本評定抑郁程度[10],HAMD總分<8分為無抑郁,8~16分為輕度抑郁,17~23分為中度抑郁,≥24分為重度抑郁。②采用美國國立衛(wèi)生院神經(jīng)功能缺損評分(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11]評定患者的神經(jīng)功能,其包括15項條目:意識情況、眼外肌運動、視野、面肌功能、肢體運動、感覺、共濟失調(diào)、語言功能、構音障礙和偏側忽略等項目。③日常生活能力評定:采用改良Barthel指數(shù)(modified Barthel index,MBI)[12]評定,滿分為100分,評分越高,表示日常生活活動能力越強。

2 結果
治療4周及8周后,2組HAMD及NHISS評分較治療前均持續(xù)顯著下降(P<0.01);治療4周及8周后,觀察組HAMD及NHISS評分更低于對照組(P<0.05)。治療4周和8周后2組MBI評分較治療前均持續(xù)顯著提高(P<0.01);治療4周及8周后,觀察組MBI評分更高于對照組(P<0.01)。見表1。
患者在治療過程中,血、尿常規(guī),肝、腎功能及心電圖均沒有發(fā)現(xiàn)明顯異常,其中觀察組1例出現(xiàn)惡心;對照組1例患者出現(xiàn)惡心,2例出現(xiàn)口干。

表1 2組患者干預前后HAMD、 NHISS及MBI評分比較 分,
與治療前比較,aP<0.01;與治療4周后比較,bP<0.01;與對照組比較,cP<0.05,dP<0.01
3 討論
PSD是腦卒中的重要并發(fā)癥之一,其發(fā)生率約為25%~75%[13]。目前,PSD的發(fā)病機制尚存在爭議。大部分學者認同PSD是神經(jīng)生物學機制與社會心理學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神經(jīng)生物學機制提出5-羥色胺能和去甲腎上腺素能環(huán)路在卒中后抑郁的發(fā)病中起了重要作用。舍曲林是一種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能增加神經(jīng)突觸間隙5-羥色胺的濃度,改善抑郁癥狀,從而提高患者的情緒動力和治療積極性。腦卒中對象多為中老年患者,伴發(fā)的軀體疾病復雜,合并用藥多,已有研究證實舍曲林對P450酶影響小,藥物之間相互作用少,具有高等級的心血管安全性循證證據(jù)[14]。同時有研究證實舍曲林能提高卒中患者的認知功能[15]。本研究結果顯示,2組患者在舍曲林治療4周和8周后抑郁情緒明顯改善,神經(jīng)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也有顯著提高。因此,舍曲林治療PSD患者效果顯著,且耐受性好、安全性高,能促進卒中患者神經(jīng)功能的康復。
針對社會心理學機制,很多學者提出了卒中后抑郁的非藥物治療方法,如高壓氧、針灸、心理治療等。我們認為PSD患者回歸社會最科學經(jīng)濟的方法是抗抑郁藥物治療聯(lián)合心理治療,能從根本上幫助患者恢復身心健康,但我們的臨床工作中往往忽視了心理治療這一點。SFBT是一種操作簡單、起效快、療程短的心理治療方法,已被廣泛應用于抑郁癥、強迫癥、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等心理疾病的臨床治療[16-17],與傳統(tǒng)的心理治療模式不同,SFBT治療重點是幫助患者成為解決自身問題的專家,建立健康的個人保護機制,患者是治療的主導者,起效更快,效果更明顯。
發(fā)掘患者的積極能動性和正性力量,強調(diào)患者疾病中可以改變的可能性,不把注意力放在疾病表現(xiàn)和預后上,由易于做到的微小改變開始。本研究發(fā)現(xiàn),SFBT能更快速、更有效地改善PSD患者的抑郁情緒,改善神經(jīng)功能的恢復。卒中后患者因為軀體功能障礙和經(jīng)濟地位、家庭社會角色的突然改變,常常會出現(xiàn)強烈的心理落差,如果治療效果起效太慢會降低患者的治療依從性,增加致殘、自殺等意外風險。而起效慢是當前抗抑郁藥的最大缺陷,一般需要3~4周才開始發(fā)揮抗抑郁作用,這必然會導致部分患者在治療初期因主觀感覺治療無效而中斷治療[17]。因此,心理治療起到了很好的增效作用。
綜上所述,焦點解決短期療法聯(lián)合抗抑郁藥舍曲林可以快速、安全、有效、全面的改善抑郁癥狀,降低殘疾或自殺風險,促進患者神經(jīng)功能的康復,提高生活質(zhì)量,同時可縮短住院時間,減輕家庭的經(jīng)濟負擔,改善患者的遠期預后。
[1] Ramos-Perdigués S, Mané-Santacana A, Pintor-Pérez L. Prevalence and associated factors of anger post stroke: a systematic review[J]. Rev Neurol,2015,60(11):481-489.
[2] Mores G, Whiteman R, Knobl P, et al. Pilot evaluation of the family informal caregiver stroke self-management program[J].Can J Neurosci Nurs, 2013,35(2):18-26.
[3] Denno MS, Gillard PJ, Graham GD, et 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ssociated with caregiver burden in caregivers of stroke survivors with spasticity[J]. Arch Phys Med Re habil, 2013,94(9):1731-1736.
[4] Quinn K, Murray C, Malone C. Spousal experiences of coping with and adapting to caregiving for a partner who has a stroke: a meta-synthesi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J]. Disabil Rehabil, 2014, 36(3):185-198.
[5] Allan LM, Rowan EN, Thomas AJ,et al. Long-term incidence of depression and predictor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older strokesurvivors[J]. Br J Psychiatry, 2013, 203(6):453-460.
[6] Jeong BO, Kang HJ, Bae KY, et al. Determinants of quality of life in the acute stage following stroke[J].Psychiatry Investig, 2012, 9(2): 127-133.
[7] 饒明俐.中國腦血管病防治指南摘要[J].中風與神經(jīng)疾病雜志, 2005, 22(6):388-393.
[8] 賈繼敏,徐俊冕.抑郁癥診斷分類的臨床研究[J].臨床精神醫(yī)學雜志, 2001,11(2):95-96.
[9] 許維素.焦點解決短期心理治療的應用[M].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9,3-6.
[10]胡契.心理治療效果的評價及其影響因素[J].中國康復醫(yī)學雜志, 2006,21(3):263-264.
[11]侯東哲,張穎,巫嘉陵,等.中文版美國國立衛(wèi)生院腦卒中量表的信度與效度研究[J].中華物理與康復醫(yī)學雜志, 2012, 34(5):372-374.
[12]李奎成,唐丹,劉曉艷,等.國內(nèi)Barthel指數(shù)和改良Barthel指數(shù)應用的回顧性研究[J].中國康復醫(yī)學雜志, 2009, 24(8): 737-740.
[13]Arseniou S,Arvaniti A,Samakouri M.Post stroke depression:recognitio-hand treatment interrenfions[J].Psychiatrike, 2011, 22(3):240-248.
[14]Karaiskos D, Tzavellas E, Spengos K,et al.Duloxetine versus citalopram and sertraline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stroke depression, anxiety, and fatigue[J].J Neuropsychiatry Clin Neurosci, 2012,24(3):349-353.
[15]Jorge RE, Acion L, Moser D, et al. Escitalopram and Enhancement of Cognitive Recovery Following Stroke[J]. Arch Gen Psychiatry, 2010, 67(2): 187-196.
[16]Boseart VM.A communication intervention for nursing staff in chronic care[J].J Adv Nurs, 2009, 65(9):1823-1832.
[17]陳琛, 王小平.抗抑郁藥的快速起效[J].中華精神科雜志,2012, 45(2):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