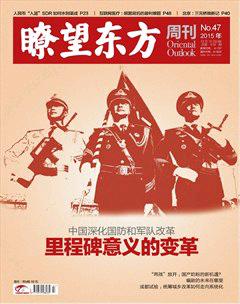404 Not Found
404 Not Found
互聯(lián)網(wǎng)醫(yī)療:喧囂背后的盈利難題
劉硯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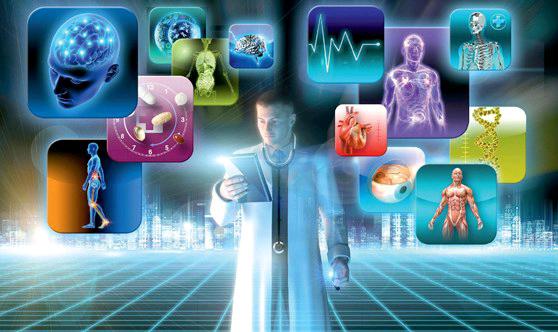
2015年第四季度以來,互聯(lián)網(wǎng)醫(yī)療行業(yè)的商業(yè)合作密集展開:
10月18日,阿里健康和滴滴出行、名醫(yī)主刀三家公司在多個(gè)城市推出“一鍵呼叫醫(yī)生,隨車上門咨詢”服務(wù);
11月18日,人保財(cái)險(xiǎn)與春雨醫(yī)生簽訂戰(zhàn)略合作協(xié)議,雙方將在健康險(xiǎn)等領(lǐng)域展開深度合作;
11月20日,騰訊、丁香園與眾安保險(xiǎn)宣布推出基于大數(shù)據(jù)的“互聯(lián)網(wǎng) + 醫(yī)療金融”創(chuàng)新合作模式;
11月30日夜,復(fù)星醫(yī)藥發(fā)布公告披露,旗下全資子公司已與掛號(hào)網(wǎng)簽訂E輪認(rèn)購(gòu)協(xié)議,出資6500萬美元認(rèn)購(gòu)后者3966萬股。
盡管動(dòng)作頻繁,但互聯(lián)網(wǎng)醫(yī)療真的像看上去這般美好嗎?
或許并非如此。
就在2015年10月中旬,擁有9200萬用戶的春雨醫(yī)生陷入了一場(chǎng)“被倒掉”的輿論狂潮;
11月初,北大人民醫(yī)院院長(zhǎng)王杉更是在一場(chǎng)公開活動(dòng)上直言:根據(jù)中國(guó)現(xiàn)行的醫(yī)療管理辦法,醫(yī)務(wù)工作者必須在醫(yī)療機(jī)構(gòu)執(zhí)業(yè),而所謂遠(yuǎn)程問診的行為,嚴(yán)格來說就是違法。在王杉看來,醫(yī)患雙方僅通過手機(jī)交流的方式極不安全:“一個(gè)人上腹部不適,網(wǎng)絡(luò)另一端的醫(yī)生如何判定這是簡(jiǎn)單病還是復(fù)雜病?”
伴隨著對(duì)其模式的質(zhì)疑,互聯(lián)網(wǎng)醫(yī)療還要面對(duì)盈利難題。
優(yōu)化而非取代醫(yī)療體系
創(chuàng)立于2011年的春雨醫(yī)生靠“輕問診”起家,一直以來都有不少人質(zhì)疑“輕問診”這個(gè)概念就是在打遠(yuǎn)程問診的擦邊球。
“輕問診就是遠(yuǎn)程問診,我也不認(rèn)為面對(duì)面是醫(yī)療診斷的唯一合法動(dòng)作。” 站在輿論的風(fēng)口浪尖上,春雨醫(yī)生創(chuàng)始人兼CEO張銳對(duì)《瞭望東方周刊》表明了他的態(tài)度。
在張銳看來,春雨醫(yī)生的本質(zhì)就是一家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而這樣一群起初并不懂醫(yī)療的人,殺入這個(gè)傳統(tǒng)行業(yè),肯定會(huì)給圈子帶來一些不適。
盡管國(guó)家衛(wèi)計(jì)委曾明確表示互聯(lián)網(wǎng)上只能進(jìn)行健康咨詢,不能開展涉及醫(yī)學(xué)診斷的治療,但如今“健康中國(guó)”已正式升級(jí)至國(guó)家戰(zhàn)略,“互聯(lián)網(wǎng)+醫(yī)療”產(chǎn)業(yè)也受到了國(guó)家政策的大力支持。
2015年9月,國(guó)務(wù)院發(fā)布《關(guān)于推進(jìn)分級(jí)診療建設(shè)的指導(dǎo)意見》,強(qiáng)調(diào)提升遠(yuǎn)程醫(yī)療服務(wù)能力,利用信息化手段促進(jìn)醫(yī)療資源縱向流動(dòng)。
國(guó)家衛(wèi)計(jì)委法制司司長(zhǎng)張春曾在公開場(chǎng)合表示,相關(guān)部門正在加緊制定互聯(lián)網(wǎng)醫(yī)療的相關(guān)政策與標(biāo)準(zhǔn),包括明確互聯(lián)網(wǎng)醫(yī)療有關(guān)標(biāo)準(zhǔn)和各方職能、制定互聯(lián)網(wǎng)醫(yī)療針對(duì)性鼓勵(lì)政策、完善相關(guān)法規(guī)政策,等等。其中是否允許非醫(yī)療機(jī)構(gòu)從事具有一定邊界、可控的服務(wù)恰是政府部門正在研究的問題。
張銳在采訪中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互聯(lián)網(wǎng)醫(yī)療的目的不是取代醫(yī)院,而是希望借用互聯(lián)網(wǎng)的技術(shù)手段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優(yōu)化資源配置。
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鵬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國(guó)家之所以沒有叫停諸如春雨醫(yī)生一類的互聯(lián)網(wǎng)問診平臺(tái),也是在觀察它們到底會(huì)有怎樣的發(fā)展。
“很多人認(rèn)為醫(yī)療關(guān)乎生死,其實(shí)醫(yī)療的最終結(jié)果是偶爾實(shí)現(xiàn)治愈,通常都是緩解,主要是種安慰。”朱恒鵬對(duì)本刊記者表示,除疑難雜癥和危急重癥必須交給醫(yī)院來做之外,相當(dāng)一部分普通門診和慢病管理都可以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進(jìn)行。

2015 年10 月19 日, 上海某醫(yī)院一名即將上門為市民問診的“滴滴醫(yī)生”在整理藥箱
他認(rèn)為,慢病管理的核心在于提高患者的依從性,讓大家按時(shí)吃藥,而這項(xiàng)工作只要受過醫(yī)療培訓(xùn)的人都可以勝任,根本不需要在醫(yī)院實(shí)現(xiàn)。
“一個(gè)項(xiàng)目只要能夠起到改進(jìn)作用,就算得上好方案。”朱恒鵬特別強(qiáng)調(diào),改革不能理想化,不能指望由互聯(lián)網(wǎng)醫(yī)療去解決那些連醫(yī)院自己都不能保證的質(zhì)量問題。
脫離線下商機(jī)難尋
實(shí)際上,互聯(lián)網(wǎng)醫(yī)療在中國(guó)真正興起也不過是最近兩年。
因?yàn)轭^頂“顛覆醫(yī)療”的光環(huán),這一領(lǐng)域里始終不乏熱錢。波士頓咨詢公司2015年9月發(fā)布的《中國(guó)數(shù)字化醫(yī)療市場(chǎng)變革》估算,2014年已披露的中國(guó)數(shù)字化醫(yī)療領(lǐng)域的融資規(guī)模為45億元人民幣,這一數(shù)字是前三年投資總和的2.5倍。
盡管項(xiàng)目一個(gè)接著一個(gè),投資一筆高過一筆,除了被指“不夠安全”之外,互聯(lián)網(wǎng)醫(yī)療還在盈利模式上備受懷疑。
2015年10月,醫(yī)療圈被一篇名為《論春雨醫(yī)生的倒掉》的文章刷屏,作者直言:醫(yī)療服務(wù)不可能以盈利為目的,春雨醫(yī)生的商業(yè)模式和發(fā)展計(jì)劃注定只是空談,公司在花光所有投資后勢(shì)必關(guān)門。
“投資互聯(lián)網(wǎng)醫(yī)療的風(fēng)險(xiǎn)不亞于買股票。”王杉認(rèn)為,在現(xiàn)階段中國(guó)醫(yī)保和醫(yī)藥政策都不完善的背景下,互聯(lián)網(wǎng)醫(yī)療不可能得到長(zhǎng)足發(fā)展。
“互聯(lián)網(wǎng)醫(yī)療對(duì)每個(gè)人來說都是全新的,沒有任何可以學(xué)習(xí)或模仿的對(duì)象,所以大家只能在摸索中嘗試各種可行性。”張銳承認(rèn)自己走過彎路,春雨醫(yī)生曾嘗試對(duì)用戶收費(fèi),由于已經(jīng)習(xí)慣免費(fèi)咨詢,付費(fèi)制度推出之后,用戶活躍度大幅降低,而且這些用戶在線上獲得免費(fèi)服務(wù)后,他們的錢還是會(huì)流向醫(yī)院或藥店。
“應(yīng)該說,脫離線下的互聯(lián)網(wǎng)醫(yī)療確實(shí)很難找到商業(yè)模式。”丁香園創(chuàng)始人李天天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時(shí)表示,目前單靠互聯(lián)網(wǎng)醫(yī)療積累出來的數(shù)據(jù)厚度很難在治療領(lǐng)域給患者帶來有效幫助。
他認(rèn)為,相比其他行業(yè),醫(yī)療行業(yè)的商業(yè)鏈條更長(zhǎng),互聯(lián)網(wǎng)主要是在掛號(hào)、問診、檢驗(yàn)、治療、護(hù)理和康復(fù)過程中起銜接作用,很難脫離整體,自創(chuàng)商機(jī)。
為打造相對(duì)完整的商業(yè)鏈條,包括春雨醫(yī)生和丁香園在內(nèi)的互聯(lián)網(wǎng)醫(yī)療企業(yè)紛紛從線上走回線下,開辦診所服務(wù)。與傳統(tǒng)醫(yī)療機(jī)構(gòu)不同的是,因?yàn)樽詭Щヂ?lián)網(wǎng)基因,他們的診所運(yùn)營(yíng)思路也頗具互聯(lián)網(wǎng)特色。
“雖然醫(yī)患的面對(duì)面問診不可能被網(wǎng)絡(luò)取代,但我們也只聚焦在患者照護(hù)這個(gè)環(huán)節(jié)。”李天天告訴記者,丁香園除了把診前預(yù)約、診中支付和診后隨訪都交給微信之外,還將藥品供應(yīng)和醫(yī)學(xué)檢測(cè)全部外包。
瞄準(zhǔn)保險(xiǎn)這筆生意
互聯(lián)網(wǎng)醫(yī)療何時(shí)才能從輸血狀態(tài)進(jìn)入造血階段?
面對(duì)這個(gè)問題,多位業(yè)內(nèi)人士表示:無論是哪個(gè)細(xì)分領(lǐng)域的互聯(lián)網(wǎng)醫(yī)療,最終付費(fèi)方一定是保險(xiǎn)公司。
2015年11月18日,人保財(cái)險(xiǎn)與春雨醫(yī)生簽訂戰(zhàn)略合作協(xié)議。根據(jù)協(xié)議,春雨醫(yī)生將為人保財(cái)險(xiǎn)客戶提供基于線上健康咨詢、春雨診所和權(quán)威醫(yī)療機(jī)構(gòu)的分級(jí)診療服務(wù)。
“保險(xiǎn)公司是以控費(fèi)為前提的。中國(guó)之所以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健康險(xiǎn),是因?yàn)楸kU(xiǎn)公司不能控制醫(yī)生的醫(yī)療行為。”張銳指出,互聯(lián)網(wǎng)醫(yī)療對(duì)于保險(xiǎn)公司最大的價(jià)值在于,它不但可以幫助那些不需要去醫(yī)院的人不去醫(yī)院,還可以讓那些需要去醫(yī)院治療的患者及時(shí)就醫(yī),從而降低重大疾病的發(fā)生幾率。
從國(guó)外經(jīng)驗(yàn)來看,健康險(xiǎn)的確是互聯(lián)網(wǎng)醫(yī)療機(jī)構(gòu)的重要利潤(rùn)來源。歐美不少保險(xiǎn)公司都將可穿戴醫(yī)療設(shè)備免費(fèi)贈(zèng)給客戶,通過長(zhǎng)期監(jiān)控健康數(shù)據(jù),以達(dá)到減少客戶入院幾率,從而降低賠付成本。
中國(guó)也在復(fù)制類似的方式。2015年11月19日,在騰訊糖大夫智能血糖儀2.0版發(fā)布會(huì)上,騰訊、丁香園和眾安保險(xiǎn)聯(lián)合推出“糖小貝計(jì)劃”,為一萬份血糖儀提供配套的保障。
本刊記者了解到,用戶如能堅(jiān)持按要求測(cè)量血糖,即可領(lǐng)取一定數(shù)額的保費(fèi),將來一旦出現(xiàn)糖尿病并發(fā)癥,可獲得最高2萬元的醫(yī)療保障。
盯準(zhǔn)保險(xiǎn)這塊生意的還有掛號(hào)網(wǎng)。其創(chuàng)始人兼CEO廖杰遠(yuǎn)對(duì)《瞭望東方周刊》表示,掛號(hào)網(wǎng)的目標(biāo)是要做中國(guó)的凱撒醫(yī)療集團(tuán)。
凱撒醫(yī)療集團(tuán)是美國(guó)最典型的HMO組織。HMO即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又稱健康維護(hù)組織,旨在通過協(xié)調(diào)各類醫(yī)療資源,在避免所有不必要或不當(dāng)服務(wù)的前提下,幫助預(yù)付少量費(fèi)用的患者獲得適當(dāng)?shù)慕】底o(hù)理。
廖杰遠(yuǎn)說,HMO的最大特點(diǎn)是預(yù)付費(fèi)、用戶自費(fèi)比例低和具有成熟的轉(zhuǎn)診制度。而掛號(hào)網(wǎng)要做的,就是以家庭為單位為用戶提供HMO式服務(wù)。
不以快慢論英雄
盡管每家互聯(lián)網(wǎng)醫(yī)療企業(yè)都宣稱要打造“以患者為中心”的服務(wù)模式,但中國(guó)絕大多數(shù)患者還是會(huì)一邊吐槽,一邊熬夜在公立醫(yī)院排隊(duì)。畢竟三甲醫(yī)院里不但有名醫(yī)大腕,更有醫(yī)保報(bào)銷。
如果醫(yī)保可以對(duì)互聯(lián)網(wǎng)醫(yī)療放開,分級(jí)診療是不是會(huì)更容易實(shí)現(xiàn)?
面對(duì)互聯(lián)網(wǎng)醫(yī)療對(duì)接醫(yī)保的巨大呼聲,人社部醫(yī)保司醫(yī)保管理處處長(zhǎng)黃心宇對(duì)《瞭望東方周刊》表示,醫(yī)保基金雖然總體結(jié)余,但仍面臨一些現(xiàn)實(shí)困境:全國(guó)醫(yī)保基金結(jié)余的40%都集中在山東、廣東、江蘇和浙江四省,不少省區(qū)的醫(yī)保基金已經(jīng)穿底;老百姓對(duì)大病、康復(fù)、護(hù)理有較高報(bào)銷需求;兒童、老人、殘疾人、困難人群等特殊人群需要考慮照顧……
“中國(guó)的經(jīng)濟(jì)水平和醫(yī)保現(xiàn)狀決定了醫(yī)保基金還是要以疾病治療為主。”黃心宇指出,醫(yī)保基金不是產(chǎn)業(yè)支持基金,但如果創(chuàng)新的結(jié)果能夠給醫(yī)保基金和參保人帶來好處,那么購(gòu)買服務(wù)是沒有問題的。
在現(xiàn)階段醫(yī)保不放開的情況下,互聯(lián)網(wǎng)醫(yī)療單靠商業(yè)保險(xiǎn)吸引用戶的做法能夠長(zhǎng)期維持嗎?
“我們的首要任務(wù)是把服務(wù)設(shè)計(jì)好,而非想辦法讓保險(xiǎn)公司埋單。”在李天天看來,互聯(lián)網(wǎng)醫(yī)療到底可以幫患者節(jié)約多少醫(yī)療成本、帶來怎樣的價(jià)值,這些都需要十分詳細(xì)的設(shè)計(jì)體系,照搬線下控費(fèi)機(jī)制這條路一定行不通。
中國(guó)醫(yī)保基金的控費(fèi)狀況究竟如何?黃心宇直言,中國(guó)醫(yī)保基金雖整體結(jié)余,但結(jié)余率卻在逐年降低,其中醫(yī)療費(fèi)用快速增長(zhǎng)是加大醫(yī)保基金壓力的主要原因。以2013年為例,中國(guó)藥品費(fèi)用上漲16%,檢查費(fèi)用增長(zhǎng)近40%,耗材費(fèi)用增長(zhǎng)也達(dá)32%。
“保險(xiǎn)的控費(fèi)流程可以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來規(guī)范,但我們不能指望通過技術(shù)手段解決體制問題。”李天天對(duì)記者表示,與其盼望健康險(xiǎn)來救互聯(lián)網(wǎng)醫(yī)療,不如讓互聯(lián)網(wǎng)醫(yī)療設(shè)計(jì)出一套合理的服務(wù)模式來反哺健康險(xiǎn)。
“互聯(lián)網(wǎng)醫(yī)療企業(yè)不應(yīng)過分關(guān)注投資人,而是要想清楚自己到底能給醫(yī)生和患者帶來哪些好處。”李天天再三強(qiáng)調(diào),醫(yī)療是一個(gè)嚴(yán)肅漫長(zhǎng)的過程,這個(gè)行業(yè)不能簡(jiǎn)單地以快慢論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