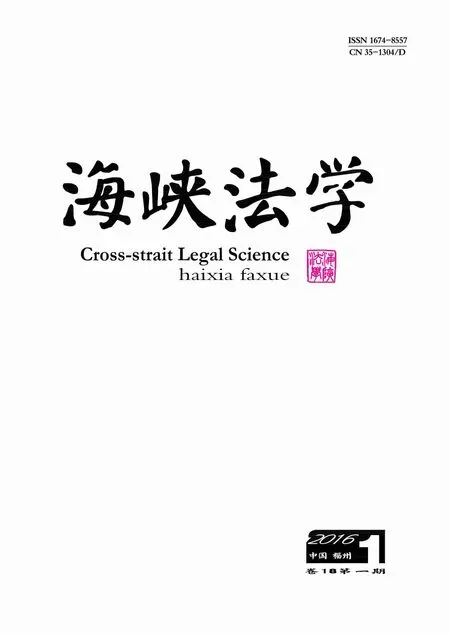我國(guó)民法典中的合伙立法模式之選擇
陳 鵬
?
我國(guó)民法典中的合伙立法模式之選擇
陳鵬
摘要:我國(guó)合伙制度的立法規(guī)制以民商合一為基本立法邏輯,但隨著《合伙企業(yè)法》的頒布,司法實(shí)踐中合伙規(guī)制邏輯從民商合一轉(zhuǎn)向了民商分立。民商關(guān)系之爭(zhēng)導(dǎo)致民法法典化進(jìn)程中對(duì)合伙制度的定位出現(xiàn)偏差,民商事合伙區(qū)分標(biāo)準(zhǔn)的可非議性使得民商事合伙本身的識(shí)別產(chǎn)生困難。在我國(guó)民法法典化的進(jìn)程中應(yīng)當(dāng)借鑒英美國(guó)家的登記制度構(gòu)建民商合一邏輯下的統(tǒng)一合伙規(guī)制模式,即以登記作為界分點(diǎn),當(dāng)事人申請(qǐng)登記為有限合伙的,適用民法典有限合伙之規(guī)定。未登記的,統(tǒng)一適用民法典普通合伙之規(guī)定。
關(guān)鍵詞:民商合一;民商分立;識(shí)別;登記;統(tǒng)一規(guī)制模式
我國(guó)《民法通則》和《合同法》將合伙作為主體形態(tài)進(jìn)行規(guī)制,近來(lái)的《民法典·建議稿》也采取此觀點(diǎn)。同時(shí),隨著民商分立之觀點(diǎn)的逐步盛行,我國(guó)商事領(lǐng)域逐步確立了商事合伙制度。立法界和學(xué)術(shù)界就合伙制度如何構(gòu)造,是形成單純的民事主體,還是作為商事主體,抑或是形成民商分立的二元制主體,并未形成統(tǒng)一觀點(diǎn)。從我國(guó)目前立法邏輯來(lái)看合伙制度的規(guī)制依然堅(jiān)持民商合一的立法體例,但在司法實(shí)踐中卻轉(zhuǎn)變?yōu)槊裆谭至⒍坪匣镆?guī)制模式。然而,民商事合伙相并立的二元制模式亦再次表現(xiàn)出立法目的的落空與法律識(shí)別之難等問(wèn)題。故而在未來(lái)民法典中,如何選擇合伙規(guī)制模式不僅關(guān)乎合伙制度的有效運(yùn)行,更關(guān)乎法典體系之合理性。
一、我國(guó)現(xiàn)行合伙規(guī)制模式之反思
馬克思主義法學(xué)認(rèn)為法是經(jīng)濟(jì)基礎(chǔ)的反映,同時(shí)任何社會(huì)制度總與經(jīng)濟(jì)基礎(chǔ)相牽連,合伙制度概莫能外。目前我國(guó)民商分立下的二元制合伙規(guī)制模式雖然為合伙制度的運(yùn)行提供了制度支撐,但是在司法實(shí)務(wù)界和法典化進(jìn)程中卻誘發(fā)了諸多問(wèn)題,值得反思。
(一)民商關(guān)系爭(zhēng)議下合伙制度定位之偏差
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在學(xué)界的爭(zhēng)議由來(lái)已久,相關(guān)研究已臻成熟,筆者于此無(wú)贅述之必要。堅(jiān)持民商合一的學(xué)者認(rèn)為在安排合伙制度時(shí),并不能完全否認(rèn)商事合伙之存在,因此建議在民法典總則部分抽象設(shè)置所有合伙制度的共同性規(guī)則,在其他單行法中單獨(dú)規(guī)定合伙制度具體規(guī)則或者規(guī)定商事合伙等特殊規(guī)則,①王利明:《民商合一體例下我國(guó)民法典總則的制定》,載《法商研究》2015年第4期,第8~9頁(yè)。對(duì)此新近《民法典·建議稿》中采取了此種模式。②中國(guó)法學(xué)會(huì)民法典編纂項(xiàng)目領(lǐng)導(dǎo)小組:《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民法典·民法總則專(zhuān)家建議稿(征求意見(jiàn)稿)》,http://www.civillaw.com.cn/zt/t/?29169,下載日期:2015年10月6日。堅(jiān)持民商分立的學(xué)者認(rèn)為合伙根據(jù)某一標(biāo)準(zhǔn)——“是否營(yíng)利”、“是否為組織體”、或“是否進(jìn)行了商事登記”——分為民商事合伙制度。但在上述模糊標(biāo)準(zhǔn)之下認(rèn)為民事合伙不具備營(yíng)利性、未取得商事登記,且以契約形態(tài)存在而適用債法規(guī)則;商事合伙則具備前述特征,適用商事特別規(guī)則。同時(shí),在規(guī)則適用上商事合伙優(yōu)先適用商事特別法規(guī)則,只有當(dāng)民商事合伙在各自領(lǐng)域出現(xiàn)適用空白時(shí),方可互為缺省性適用。③方流芳:《關(guān)于制定合伙法的幾點(diǎn)意見(jiàn)》,載《中國(guó)工商管理研究》1995年第6期,第14頁(yè)。郭峰:《民商分立與民商合一的理論評(píng)析》,載《中國(guó)法學(xué)》1996年第5期,第43頁(yè)。可見(jiàn),上述爭(zhēng)論之本質(zhì)在于前者折射出的是德國(guó)潘德克頓“總——分”式的、縱向性的立法思維模式,并且無(wú)論是合伙主體資格之賦予,抑或是規(guī)則的司法適用均是如此;后者折射出僅是技術(shù)性規(guī)則的便捷適用,是一種并列式、橫向性的立法思維模式,是僅從形式的角度區(qū)分法律規(guī)則的適用范圍。
從現(xiàn)行法遵從的形式邏輯來(lái)看,我國(guó)在合伙制度立法上堅(jiān)持的是民商合一的體例,隨著《合同法》的頒布、實(shí)施,使得《民法通則》確定的民事合伙具備了主體資格,《行政許可法》與《合伙企業(yè)法》的相關(guān)規(guī)定④《行政許可法》第12條第5項(xiàng)規(guī)定:“企業(yè)或者其他組織的設(shè)立等,需要確定主體資格的事項(xiàng)”。《合伙企業(yè)法》第11條:合伙企業(yè)的營(yíng)業(yè)執(zhí)照簽發(fā)日期,為合伙企業(yè)成立日期。合伙企業(yè)領(lǐng)取營(yíng)業(yè)執(zhí)照前,合伙人不得以合伙企業(yè)名義從事合伙業(yè)務(wù)。亦使得商事領(lǐng)域中的商事合伙具備了主體資格。《合伙企業(yè)法》看似是民商合一邏輯下具體單行法彌補(bǔ)共同規(guī)則之手段,但《合伙企業(yè)法》中的規(guī)則卻偏離了《民法通則》,并且兩者之間形成了張力——《民法通則》中的合伙規(guī)則并非是對(duì)所有合伙類(lèi)型的抽象,《合伙企業(yè)法》中某些條文也并不對(duì)《民法通則》中的民事合伙產(chǎn)生效力。故此與學(xué)界主張的我國(guó)合伙立法是民商合一之體例邏輯相悖。正因上述張力之存在使得《合伙企業(yè)法》確定的民商事合伙區(qū)分標(biāo)準(zhǔn)——登記——被司法機(jī)關(guān)間接或直接運(yùn)用,⑤在司法實(shí)踐中,法官在裁判合伙糾紛時(shí)認(rèn)為合伙企業(yè)和個(gè)人合伙最大的區(qū)別在于是否進(jìn)行了商事企業(yè)登記、是否取得了商事人格——認(rèn)為合伙企業(yè)具有人格字號(hào),而個(gè)人合伙沒(méi)有人格外在之表現(xiàn)的字號(hào)。參見(jiàn):“應(yīng)榮富與沈明強(qiáng)合伙企業(yè)財(cái)產(chǎn)份額轉(zhuǎn)讓糾紛上訴案:(2009)湖吳商初字第1931號(hào)二審;(2010)浙湖商終字第218號(hào)”;“王聰訴許曉峰等合伙企業(yè)糾紛案:河南省洛陽(yáng)市中級(jí)人民法院,(2015)洛民終字第2410號(hào)。“張宏娟訴鐘貽鴻合伙企業(yè)糾紛案:貴州省從江縣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shū),(2015)從民初字第412號(hào)”。即在當(dāng)下司法裁判中出現(xiàn)合伙糾紛并非按照學(xué)界所主張的民商合一之立法體例邏輯進(jìn)行裁判,而是偏向民商分立的合伙立法體例邏輯進(jìn)行裁判——以是否取得商事登記,從而選擇裁判依據(jù)。進(jìn)而導(dǎo)致在合伙制度定位上,從立法上的民商合一偏向了司法上的民商分立,出現(xiàn)了法律制度屬性上的定位偏差。
(二)登記界分民商分立的目的落空
依前述,目前我國(guó)合伙制度的前提邏輯已從民商合一轉(zhuǎn)向了民商分立,且在民商分立體制之下我國(guó)立法及司法實(shí)踐中均以登記區(qū)分民商事合伙。然,傳統(tǒng)立法技術(shù)確定的登記之目的在面對(duì)實(shí)踐時(shí)出現(xiàn)無(wú)法自洽性。詳言之:
現(xiàn)行《合伙企業(yè)法》第9條、第10條、第11條及《民法通則》第30條⑥《合伙企業(yè)法》第9條:申請(qǐng)?jiān)O(shè)立合伙企業(yè),應(yīng)當(dāng)向企業(yè)登記機(jī)關(guān)提交登記申請(qǐng)書(shū)、合伙協(xié)議書(shū)、合伙人身份證明等文件。合伙企業(yè)的經(jīng)營(yíng)范圍中有屬于法律、行政法規(guī)規(guī)定在登記前須經(jīng)批準(zhǔn)的項(xiàng)目的,該項(xiàng)經(jīng)營(yíng)業(yè)務(wù)應(yīng)當(dāng)依法經(jīng)過(guò)批準(zhǔn),并在登記時(shí)提交批準(zhǔn)文件。《合伙企業(yè)法》第10條:申請(qǐng)人提交的登記申請(qǐng)材料齊全、符合法定形式,企業(yè)登記機(jī)關(guān)能夠當(dāng)場(chǎng)登記的,應(yīng)予當(dāng)場(chǎng)登記,發(fā)給營(yíng)業(yè)執(zhí)照。除前款規(guī)定情形外,企業(yè)登記機(jī)關(guān)應(yīng)當(dāng)自受理申請(qǐng)之日起二十日內(nèi),作出是否登記的決定。予以登記的,發(fā)給營(yíng)業(yè)執(zhí)照;不予登記的,應(yīng)當(dāng)給予書(shū)面答復(fù),并說(shuō)明理由。《合伙企業(yè)法》第11條:合伙企業(yè)的營(yíng)業(yè)執(zhí)照簽發(fā)日期,為合伙企業(yè)成立日期。合伙企業(yè)領(lǐng)取營(yíng)業(yè)執(zhí)照前,合伙人不得以合伙企業(yè)名義從事合伙業(yè)務(wù)。《民法通則》第30條:個(gè)人合伙是指兩個(gè)以上公民按照協(xié)議,各自提供資金、實(shí)物、技術(shù)等,合伙經(jīng)營(yíng)、共同勞動(dòng)。認(rèn)為劃分民商事合伙的標(biāo)準(zhǔn)是“企業(yè)登記機(jī)關(guān)的登記”。即我國(guó)民商事合伙的區(qū)分是以企業(yè)登記機(jī)關(guān)的登記為界分點(diǎn),但關(guān)于商事登記的性質(zhì)目前在學(xué)界主要存在三種爭(zhēng)議:“公法行為說(shuō)”、“私法行為說(shuō)”及“混合行為說(shuō)”。①“公法行為說(shuō)”認(rèn)為商事登記是國(guó)家出于監(jiān)管目的需要的行政行為。“私法行為說(shuō)”認(rèn)為商事登記是一種民事法律行為。“混合行為說(shuō)”則認(rèn)為,一方面商事登記是登記主管機(jī)關(guān)代表國(guó)家意志,以公權(quán)力對(duì)商事私法行為及其營(yíng)業(yè)狀態(tài)、主體地位的法律確認(rèn);另一方面,在商事登記過(guò)程中當(dāng)事人對(duì)營(yíng)業(yè)種類(lèi)、經(jīng)營(yíng)范疇、投資方式、營(yíng)業(yè)期限等事項(xiàng)可以按照自身的意愿享有選擇的自由。 當(dāng)然,目前對(duì)商事登記的性質(zhì)的認(rèn)為是私法屬性的觀點(diǎn)亦有很多。參見(jiàn)趙萬(wàn)一、王蘭:《私法視域下商事登記的重新解讀》,載《河北法學(xué)》2009年第6期,第66頁(yè)。鄒小琴:《商事登記制度的屬性反思及制度重構(gòu)》,載《法學(xué)雜志》2014年第1期,第50頁(yè)。結(jié)合我國(guó)《行政許可法》第12條②《行政許可法》第12條第5項(xiàng)規(guī)定:“企業(yè)或者其他組織的設(shè)立等,需要確定主體資格的事項(xiàng)”。可知,合伙的成立屬行政許可的范疇,其實(shí)質(zhì)為公權(quán)力法律部門(mén)確認(rèn)合伙主體資格、管理市場(chǎng)主體的公法性手段,且《合伙企業(yè)法》第11條亦明文要求合伙企業(yè)未得營(yíng)業(yè)執(zhí)照之前禁止以合伙企業(yè)名義進(jìn)行交易。可見(jiàn),《行政許可法》下的“許可”與《合伙企業(yè)法》中的“企業(yè)登記”均為公法性,且就《合伙企業(yè)法》中的“登記”而言,兼具公法的“門(mén)檻性”與私法的“主體資格取得性”之雙重功效。同時(shí),無(wú)形之中還具有區(qū)分民商事合伙之功能。而傳統(tǒng)立法經(jīng)驗(yàn)認(rèn)為《合伙企業(yè)法》之所以要求登記,是因登記可達(dá)到主體信息公示、降低交易風(fēng)險(xiǎn)、維護(hù)交易安全。③鄒小琴:《商事登記制度的屬性反思及制度重構(gòu)》,載《法學(xué)雜志》2014年第1期,第50頁(yè)。葛聲波:《企業(yè)登記:功能定位與制度完善》,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0年第5期,第130頁(yè)。然,筆者意為此目的并未達(dá)致,此因在合伙這一特殊主體模式下,即使對(duì)合伙進(jìn)行了商事登記,抑或?qū)⒑匣锏南嚓P(guān)信息進(jìn)行了交易前的公開(kāi),但實(shí)踐中影響交易相對(duì)人行為選擇之可能性的仍然是合伙人的風(fēng)險(xiǎn)承受能力,而非合伙是否登記、合伙信息是否公開(kāi)。所以,筆者意為立法確定登記作為區(qū)分民商事合伙二元制的優(yōu)勢(shì)與目的并未實(shí)現(xiàn)、維護(hù)交易安全之功能亦不存在。
概而言之,筆者認(rèn)為登記本身所區(qū)分出的民商事合伙也僅成為一種人為的區(qū)分,登記的根本目的是公法對(duì)團(tuán)體屬性在私法領(lǐng)域的政治性預(yù)防,故而立法才以要求登記為必要,且此種立法慣性從我國(guó)二十世紀(jì)五十年代的合伙立法中業(yè)已出現(xiàn),并延續(xù)至今。④我國(guó)在1956年聯(lián)營(yíng)[合伙]契約討論稿中將其規(guī)制于債法分則之中,同時(shí)對(duì)合伙的成立不僅需要章程,還需經(jīng)主管機(jī)關(guān)批準(zhǔn)或許可方可成立,可見(jiàn)對(duì)私法法律關(guān)系的成立公法干預(yù)較多,而這種公法的政治性預(yù)防亦存在歷史慣性,并延續(xù)至《合伙企業(yè)法》之中。參見(jiàn)何勤華、李秀清、陳頤編:《新中國(guó)民法典草案總覽(中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436~438頁(yè)。
(三)民商事合伙分立模式下的法律識(shí)別之難
我國(guó)合伙制度民商分立的實(shí)質(zhì)性基礎(chǔ)導(dǎo)致對(duì)民商事合伙本身的界定與區(qū)分上產(chǎn)生巨大爭(zhēng)議。有學(xué)者提出民事合伙側(cè)重契約形式存在,商事合伙側(cè)重主體性、組織體形式存在。⑤席書(shū)旗:《商合伙的主體法律地位與責(zé)任承擔(dān)規(guī)則》,載《山東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7年第4期,第158頁(yè)。董翠香、祖良軍:《合伙主體的層次與合伙立法研究》,載《煙臺(tái)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7年第3期,第36頁(yè)。有學(xué)者認(rèn)為民商事合伙的區(qū)別在于合伙人或合伙本身是否存在營(yíng)利目的,民事合伙人或者合伙本身不一定存在營(yíng)利目的,商事合伙人或合伙具有營(yíng)利目的。⑥高在敏、楊森:《民商事合伙區(qū)分與合伙的法律地位》,載《經(jīng)濟(jì)論壇》1996年4月,第75頁(yè)。有學(xué)者提出商事合伙具有從事?tīng)I(yíng)利活動(dòng)、組織連續(xù)性(表現(xiàn)為具有字號(hào))等特點(diǎn),民事合伙未具之。⑦韓文苑:《商事合伙主體地位辨析》,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2006年碩士學(xué)位論文,第3頁(yè)。筆者以為上述標(biāo)準(zhǔn)均不構(gòu)成對(duì)民商事合伙的實(shí)質(zhì)性劃分,如此龐雜的標(biāo)準(zhǔn)只會(huì)導(dǎo)致司法裁判中法律規(guī)則的識(shí)別之難,亦會(huì)導(dǎo)致裁判依據(jù)的多元化與裁判結(jié)果的不統(tǒng)一性。具體言之:
首先,組織體并不能作為劃分民商事合伙的依據(jù)。組織體并非法律概念,何為“組織體”?哲學(xué)的定義與社會(huì)勞動(dòng)關(guān)系學(xué)的定義基本類(lèi)似,兩者均要求“組織”具備目的性與結(jié)構(gòu)性(系統(tǒng)內(nèi)各部分要分工合作),①哲學(xué)含義上的組織需具備如下要素:(一)一定數(shù)量的成員。這是組織生存的先決條件。每個(gè)成員都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和履行一定的手續(xù),在組織中承擔(dān)一定的責(zé)任與義務(wù)。(二)特定的活動(dòng)目標(biāo)。任何社會(huì)組織都是為了實(shí)現(xiàn)一定的社會(huì)目標(biāo)、執(zhí)行特定的社會(huì)職能而建立起來(lái)的。(三)明確的行動(dòng)規(guī)范。為了實(shí)現(xiàn)組織目標(biāo),必須對(duì)成員制定嚴(yán)格的組織規(guī)范,對(duì)成員的行為作出明確規(guī)定,以保證各成員行動(dòng)的順利銜接和密切配合。(四)嚴(yán)謹(jǐn)?shù)臋?quán)力結(jié)構(gòu)。在社會(huì)組織內(nèi)部有著一個(gè)自上而下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網(wǎng)絡(luò),各級(jí)權(quán)力有嚴(yán)格的責(zé)任范圍和制度,以控制成員的行為和指導(dǎo)組織的活動(dòng)。(五)一定的技術(shù)設(shè)施。用以作為組織活動(dòng)的場(chǎng)所及內(nèi)部的物質(zhì)設(shè)備和工具。而社會(huì)勞動(dòng)關(guān)系學(xué)意義上的組織需具有以下特征:(一)開(kāi)放性。不斷地同外界發(fā)生物質(zhì)、信息、能源的交換。(二)系統(tǒng)性。組織內(nèi)人們互相協(xié)作,將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財(cái)力有效地轉(zhuǎn)變?yōu)楫a(chǎn)品,實(shí)現(xiàn)生產(chǎn)目的,這就形成了許多子系統(tǒng),各個(gè)子系統(tǒng)之間相輔相成,結(jié)構(gòu)嚴(yán)密。(三)目的性。組織都有其共同的目標(biāo)。(四)結(jié)構(gòu)性。在組織內(nèi)部,各部分要分工合作。現(xiàn)代管理學(xué)家認(rèn)為,任何組織都有六個(gè)要素:人員、職位、職責(zé)、職權(quán)、關(guān)系、信息。作為一個(gè)健全的組織,就要具有:清晰的職位層次順序,流暢的意見(jiàn)溝通渠道,有效的協(xié)調(diào)合作。參見(jiàn)《馬克思主義百科要覽(下卷)》,人民日?qǐng)?bào)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3367頁(yè)。苑茜著:《現(xiàn)代勞動(dòng)關(guān)系詞典》,中國(guó)勞動(dòng)社會(huì)保障出版社2000年版,第874頁(yè)。而此特性恰好被法學(xué)所采納。筆者認(rèn)為無(wú)論是民事合伙還是商事合伙本身都具有目的性和結(jié)構(gòu)性,而民商事合伙本身(或稱(chēng)之為民事合伙組織)在實(shí)現(xiàn)目的與形成結(jié)構(gòu)時(shí),契約關(guān)系僅是隱性的因子,僅是組織實(shí)現(xiàn)目的與結(jié)構(gòu)的基礎(chǔ)性要素。況且關(guān)于組織本身的理解與界定存在主觀性,我們?cè)诶碚撋纤斫獠^(qū)分的商事合伙的組織性與民事合伙所具備的組織性差距到底有多大,值得懷疑。因此,筆者以為以是否為組織體或是否為契約形式來(lái)區(qū)分民商事合伙并不科學(xué)。
其次,“營(yíng)利”在釋義學(xué)上和實(shí)踐理性上存在無(wú)法逾越的障礙。就“營(yíng)利”而言,何為“營(yíng)利”?從《當(dāng)代漢語(yǔ)詞典》查知:營(yíng)利,是指做生意謀求利潤(rùn);從《現(xiàn)代漢語(yǔ)分類(lèi)大詞典》查知:營(yíng)利,是指謀求利潤(rùn)。從《辭海》查知:營(yíng)利,一指,謀求私利;謀求利潤(rùn)。二指,贏利。從該詞上述釋解來(lái)源詳查,營(yíng)利是指謀取利潤(rùn),當(dāng)然此處的利潤(rùn)為廣義,筆者意為理解為好處、有利等未嘗不可。然在市民社會(huì)中每個(gè)民事主體均為理性人、經(jīng)濟(jì)人,都從自身的理性出發(fā)不斷的謀取利益最優(yōu),且檢索市民社會(huì)的交易主體,無(wú)論是自然人、法人抑或是民商事合伙,其所有交易活動(dòng)均以謀取“好處”為目的。當(dāng)然,也有學(xué)者指出區(qū)分民商事合伙的標(biāo)準(zhǔn)歷來(lái)是模糊不清的。從理論上來(lái)說(shuō),商事合伙具有營(yíng)利性,民事合伙則否,但這是一種以偏概全的說(shuō)法。民事合伙完全可以具有盈利的性質(zhì),只是它的目標(biāo)事業(yè)不屬于傳統(tǒng)的“商業(yè)”范疇而已。②方流芳:《關(guān)于制定合伙法的幾點(diǎn)意見(jiàn)》,載《中國(guó)工商管理研究》1995年第6期,第14頁(yè)。故而,在筆者看來(lái)方流芳先生認(rèn)為民事合伙所具有的營(yíng)利性質(zhì)只是與傳統(tǒng)商法所確定的營(yíng)利性質(zhì)不一致,但不否認(rèn)其營(yíng)利性。因此,從釋義學(xué)和實(shí)踐理性角度而言,以“營(yíng)利”為標(biāo)準(zhǔn)區(qū)分民事合伙與商事合伙并非無(wú)懈可擊。
再次,就學(xué)者提出的民商事合伙之別為組織連續(xù)性(具有名稱(chēng)、字號(hào))問(wèn)題,筆者意為此主張亦難成立。名稱(chēng)、字號(hào)僅是組織人格的外化或表現(xiàn),無(wú)論是民事合伙還是商事合伙都是在承認(rèn)合伙這一主體地位之下的再分類(lèi)。我國(guó)《民法通則》第33條、《合伙企業(yè)法》第18條均在承認(rèn)合伙名稱(chēng)與字號(hào),③當(dāng)然字號(hào)與名稱(chēng)之間的差別是存在的,有學(xué)者指出字號(hào)和商號(hào)等同適用,且兩者作為主體名稱(chēng)的有機(jī)組成部分。參見(jiàn)柳建閩、楊曉丹:《字號(hào)、商號(hào)、商業(yè)名稱(chēng)之辨析》,載《福建農(nóng)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9年第3期,第43頁(yè)。可見(jiàn)此觀點(diǎn)并不構(gòu)成對(duì)合伙之實(shí)質(zhì)性分野。故而,筆者認(rèn)為目前在民商分立體制下所建構(gòu)的民商事合伙二元理論,由于兩者分類(lèi)上存在難以自洽的理論矛盾,所以勢(shì)必導(dǎo)致發(fā)生合伙糾紛時(shí)法官在法律規(guī)則的識(shí)別與選擇上出現(xiàn)困難。
二、合伙困境解決之維的域外法找尋
我國(guó)作為法典化進(jìn)程較慢的國(guó)家,在民法典合伙制度構(gòu)造中面臨的問(wèn)題在域外各國(guó)法典進(jìn)程中亦曾存在。因此,對(duì)域外法制中的合伙規(guī)制模式進(jìn)行梳理,可為我國(guó)民法法典化進(jìn)程中的困境提供文本性借鑒。
(一)大陸法系中之合伙規(guī)制模式梳理
1. 法國(guó)法律變遷中民商分立邏輯的實(shí)質(zhì)性轉(zhuǎn)變
法國(guó)資產(chǎn)階級(jí)革命勝利之后,采取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在民商分立體例指導(dǎo)下的《法國(guó)民法典》中規(guī)定了民事合伙(民事合伙被分為包括合伙①包括合伙:參見(jiàn)《法國(guó)民法典》第1837條:現(xiàn)有全部財(cái)產(chǎn)的包括合伙為合伙人將其現(xiàn)有全部動(dòng)產(chǎn)及不動(dòng)產(chǎn):以及此種財(cái)產(chǎn)可能產(chǎn)生的利益,均歸屬于合伙。此種合伙亦得包括其他種類(lèi)的利益,但繼承、贈(zèng)與或遺贈(zèng)所取得的財(cái)產(chǎn),只能以其收益作為合伙財(cái)產(chǎn):如將其所有權(quán)約定作為合伙財(cái)產(chǎn)時(shí),除夫婦間并依有關(guān)規(guī)定辦理外,應(yīng)禁止之。第1838條:收入的包括合伙為合伙人在合伙存續(xù)期間,不論何種原因,由勞力所得的任何利益,均歸屬于合伙:合伙人在合伙契約成立當(dāng)時(shí)所有的動(dòng)產(chǎn)亦包括于上述收入之內(nèi);但不動(dòng)產(chǎn)則僅以其收益為限。與特別合伙②特別合伙:參見(jiàn)《法國(guó)民法典》第1841條:特別合伙為僅以特定財(cái)產(chǎn)的使用或其所產(chǎn)生的利益所成立的合伙。第1842條:數(shù)人為特定的企業(yè)或經(jīng)營(yíng)某種工藝或職業(yè)而締結(jié)合伙契約者,亦為特別合伙。);商法典中規(guī)定了商事合伙,兩種合伙制度分屬不同法典形成不同法律規(guī)則體系。民事合伙置于民法典合同制度之下,以契約形態(tài)進(jìn)行對(duì)待③張千帆:《<法國(guó)民法典>的歷史演變》,載《比較法研究》1999年第2期,第252頁(yè)。;商事合伙(商事合伙為商業(yè)公司一種)置于商法典商事總則部分以無(wú)限公司、兩合公司形式對(duì)待④1807年《法國(guó)商法典》規(guī)定了商事合伙,但以無(wú)限公司、兩合公司之名行商事合伙之實(shí)。無(wú)限公司是股份公司的一種類(lèi)型,無(wú)限公司就是全體股東對(duì)公司債務(wù)承擔(dān)連帶無(wú)限責(zé)任的公司。兩合公司(KG),是以共同商號(hào)進(jìn)行商業(yè)活動(dòng)的公司,其股東的一人或數(shù)人以其一定的出資財(cái)產(chǎn)數(shù)額而對(duì)公司的債務(wù)負(fù)責(zé)任(有限責(zé)任股東),其他股東負(fù)無(wú)限責(zé)任。可見(jiàn),無(wú)論是兩合公司還是無(wú)限公司,最終的責(zé)任承擔(dān)均由股東(或稱(chēng)之為合伙人)來(lái)承擔(dān),所謂的兩合公司與無(wú)限公司本身的主體性責(zé)任能力并未彰顯。參見(jiàn)王樂(lè)宇:《大陸法系國(guó)家關(guān)于合伙的立法沿革及發(fā)展趨勢(shì)》,載《現(xiàn)代營(yíng)銷(xiāo)(學(xué)苑版)》2012年第6期,第174頁(yè)。,但是不具有法人資格。但法國(guó)民商分立體制下的合伙制度在主體地位問(wèn)題上出現(xiàn)了障礙,因此,直至1966年《法國(guó)商事企業(yè)法》承認(rèn)了合伙在內(nèi)的一切商事企業(yè)自登記時(shí)的法人資格⑤方流芳:《合伙的法律地位及其比較法分析》,載《中國(guó)法學(xué)》1986年第3期,第30頁(yè)。,并且將合伙以公司性質(zhì)進(jìn)行對(duì)待。同時(shí)法國(guó)在公司立法過(guò)程中將民法典合伙編作為公司法的總則部分⑥羅結(jié)珍譯:《法國(guó)公司法典(上)》,中國(guó)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4頁(yè)。羅結(jié)珍譯:《法國(guó)民法典》,中國(guó)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412頁(yè)。,無(wú)形之中使得民商事合伙適用的規(guī)則基本一致,如此便合理解決了民商分立體制之下的法律識(shí)別之難,也保證了民商事合伙定位的邏輯統(tǒng)一性。隨后1978年的民法典修訂最終承認(rèn)了除隱名合伙外的合伙自登記之日起開(kāi)始享有法人資格。登記之前,適用契約關(guān)系規(guī)制當(dāng)事人之間的權(quán)利義務(wù)⑦王樂(lè)宇:《大陸法系國(guó)家關(guān)于合伙的立法沿革及發(fā)展趨勢(shì)》,載《現(xiàn)代營(yíng)銷(xiāo)(學(xué)苑版)》2012年第6期,第174頁(yè)。,即適用民法典之規(guī)則。
簡(jiǎn)言之,法國(guó)后期的法律改革雖以“行政管理性質(zhì)的登記”區(qū)分民事合伙與商事合伙,以此形成技術(shù)性的民商事規(guī)則的區(qū)別適用。從形式角度而言,法國(guó)合伙立法繼續(xù)追求民商分立的立法邏輯,但是承認(rèn)合伙的統(tǒng)一法人資格、公司法立法對(duì)民事合伙規(guī)則的全盤(pán)移植等表明合伙立法邏輯在實(shí)質(zhì)上已經(jīng)開(kāi)始轉(zhuǎn)向了民商合一。
2. 德國(guó)合伙主體資格欠缺下的內(nèi)在性統(tǒng)一
1900年的德國(guó)合伙立法“以是否進(jìn)行了商事登記”⑧[德] C.W.卡納里斯著:《德國(guó)商法》,楊繼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頁(yè)。將合伙二分為民事合伙與商事合伙。若合伙未登記,構(gòu)成《德國(guó)民法典》中的民事合伙,以契約關(guān)系對(duì)待。若合伙進(jìn)行了登記,且合伙人之間訂立的合伙合同必須“以經(jīng)營(yíng)商事?tīng)I(yíng)利事業(yè)”為目的,滿(mǎn)足此兩項(xiàng)要素才可構(gòu)成商事合伙,方可適用商事法律規(guī)范,①杜景林:《<德國(guó)商法典>中的商人》,載《德國(guó)研究》2011年第1期,第16頁(yè)。否則適用民事合伙之規(guī)定。同時(shí)在《德國(guó)商法典》中將商事合伙以無(wú)限公司、兩合公司模式進(jìn)行規(guī)制,且適用全部商事法律規(guī)范。可見(jiàn),德國(guó)在合伙立法模式上以“是否申請(qǐng)商事登記”為基礎(chǔ)區(qū)分民事合伙與商事合伙,登記成為適用不同法典之標(biāo)準(zhǔn)——且民法典與商法典關(guān)于合伙之規(guī)定亦是不同。之后在登記區(qū)分出民商事主體之后,以“是否具備法人資格(著重體現(xiàn)在能否獨(dú)立承擔(dān)責(zé)任上)”將團(tuán)體形態(tài)進(jìn)一步劃分為資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zé)任公司具有法人資格)與人合公司(無(wú)限公司、兩合公司不具有法人資格)兩種形態(tài),②趙吟:《公司法律形態(tài)研究》,西南政法大學(xué)2014年博士學(xué)位論文,第91頁(yè)。且兩種公司形態(tài)在適用統(tǒng)一公司規(guī)則之下(其與法國(guó)《公司法》收錄民法典合伙編之做法完全不同,此公司統(tǒng)一規(guī)則僅是商法框架下的規(guī)則,與民法典的合伙制度是相剝離的),亦分別適用各自特殊規(guī)則。當(dāng)出現(xiàn)規(guī)則缺漏時(shí),可為互補(bǔ)性適用。③參見(jiàn)《德國(guó)商法典》第105條第3款:對(duì)于無(wú)限公司,以本章無(wú)其他規(guī)定為限,適用《民法典》關(guān)于合伙的規(guī)定。《德國(guó)民法典》第736條:關(guān)于合伙人退伙的,其后續(xù)責(zé)任準(zhǔn)用商事合伙之規(guī)定。
概而言之,德國(guó)合伙立法從形式上貫徹了徹底的民商分立邏輯,但是卻蘊(yùn)含了一個(gè)前提——德國(guó)法并沒(méi)有承認(rèn)民商事合伙的主體地位。因此,民商事兩種合伙只是在不同法典中對(duì)合伙這種非主體形態(tài)的再劃分而已,其并未失同一性。同時(shí)從微觀角度而言,由于民商事合伙兩者在主體資格、責(zé)任承擔(dān)上的同質(zhì)性使得即使在司法實(shí)踐中涉及民商事合伙之認(rèn)定亦不構(gòu)成任何實(shí)質(zhì)性障礙,以此便無(wú)形之中弱化了民商事合伙的法律識(shí)別之難,使合伙的制度定位始終處于無(wú)權(quán)利能力社團(tuán)這一統(tǒng)一邏輯之下。對(duì)此,德國(guó)合伙法之適用規(guī)則——各自適用之時(shí)又可為互補(bǔ)性適用——亦是明證。
(二)英美法系中的合伙制度安排
目前規(guī)制英國(guó)合伙制度的法律主要有三部:1890年的《英國(guó)合伙法》、1907年《英國(guó)有限合伙法》和2000年的《有限責(zé)任合伙法》。④吳會(huì)仙:《英國(guó)合伙制度的起源與發(fā)展》,載《法制與社會(huì)》2011年第17期,第32頁(yè)。在1907年的《英國(guó)有限合伙法》中根據(jù)合伙是否登記區(qū)分為普通合伙與有限合伙,⑤同上。但英國(guó)法中普通合伙與有限合伙卻均不是法人。⑥王樂(lè)宇:《英美法系代表國(guó)家關(guān)于合伙的立法沿革及發(fā)展趨勢(shì)》,載《現(xiàn)代營(yíng)銷(xiāo)(學(xué)苑版)》2012年第9期,第194頁(yè)。登記僅是合伙人承擔(dān)有限責(zé)任之依據(jù),否則歸為普通合伙接受《英國(guó)合伙法》調(diào)整。2000年底,英國(guó)在法律修訂過(guò)程中對(duì)特殊行業(yè)形成的合伙通過(guò)頒布《有限責(zé)任合伙法》加以規(guī)制,且對(duì)此種“有限責(zé)任合伙”賦予了法人資格,由有限責(zé)任合伙對(duì)外作為獨(dú)立實(shí)體承擔(dān)責(zé)任,合伙人不再承擔(dān)個(gè)人責(zé)任,且有限責(zé)任合伙中的相關(guān)制度可適用公司法之規(guī)定。⑦在有限責(zé)任合伙的登記設(shè)立、財(cái)務(wù)信息披露、合伙成員資格、清算以及外部監(jiān)管等方面,《公司法》的有關(guān)規(guī)定都適用于有限責(zé)任合伙。它們主要包括:(1)有限責(zé)任合伙必須按照“真實(shí)與公允反映”的原則編制財(cái)務(wù)報(bào)表,接受注冊(cè)會(huì)計(jì)師審計(jì);審計(jì)人員的任免適用成員大會(huì)批準(zhǔn)程序; 經(jīng)審計(jì)的合伙賬目和財(cái)務(wù)報(bào)表需報(bào)公司登記機(jī)關(guān)備案,并提交合伙成員以及持有合伙所發(fā)行債券的債權(quán)人。(2)有限責(zé)任合伙成員執(zhí)行合伙事務(wù)的行為,適用《公司法》關(guān)于董事行為和董事資格的規(guī)定;不符合合伙成員法定條件的,法院可以剝奪其作為成員的資格。(3)有限責(zé)任合伙因違法行為而受處罰,有關(guān)政府部門(mén)可以像對(duì)公司事務(wù)進(jìn)行調(diào)查一樣,對(duì)合伙的違法行為進(jìn)行調(diào)查;(4)合伙的破產(chǎn)、清算事宜準(zhǔn)用公司破產(chǎn)清算的規(guī)則,合伙清算人可以行使資產(chǎn)取回權(quán)。參見(jiàn)劉燕:《職業(yè)利益籠罩下的法律制度創(chuàng)新——對(duì)英國(guó)《有限責(zé)任合伙法》的評(píng)述》,載《環(huán)球法學(xué)評(píng)論》2005年第2期,第208頁(yè)。吳會(huì)仙:《英國(guó)合伙制度的起源與發(fā)展》,載《法制與社會(huì)》2011年第17期,第32頁(yè)。當(dāng)然有限責(zé)任合伙人在獲得公司法保護(hù)的同時(shí),也作出了利益讓步。⑧有學(xué)者指出有限責(zé)任合伙以法人形式存在,合伙人不承擔(dān)個(gè)人責(zé)任。但在賬目公開(kāi)、接受審計(jì)以及在清算時(shí)適用“資產(chǎn)取回”規(guī)則。此外,普通合伙中為專(zhuān)業(yè)人士所崇尚的組織價(jià)值——靈活性、非程式性以及非公開(kāi)性,在有限責(zé)任合伙中都將受到很大程度地制約。詳見(jiàn)王樂(lè)宇:《英美法系代表國(guó)家關(guān)于合伙的立法沿革及發(fā)展趨勢(shì)》,載《現(xiàn)代營(yíng)銷(xiāo)(學(xué)苑版)》2012年第9期,第194~195頁(yè)。
美國(guó)合伙制度源于英國(guó),具體制度基本與英國(guó)相似但較為復(fù)雜。囿于美國(guó)的聯(lián)邦制政權(quán)體系,使得各州形成了不同的合伙制度。①美國(guó)作為聯(lián)邦制國(guó)家,其關(guān)于企業(yè)主體(包括但不限于合伙)的立法權(quán)限屬于各州的立法機(jī)關(guān)。因此,由“美國(guó)統(tǒng)一州法全國(guó)委員會(huì)”制定有關(guān)合伙性質(zhì)企業(yè)的“統(tǒng)一法”,但本身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而是作為示范法的意義存在,以便為各州提供立法范本。詳見(jiàn)沈四寶、郭丹:《美國(guó)合伙制企業(yè)法比較評(píng)析及對(duì)中國(guó)法的借鑒》,載《甘肅政法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6年第2期,第18~19頁(yè)。目前美國(guó)以合伙是否申報(bào)登記將合伙分為兩大類(lèi)四種類(lèi)型合伙:普通合伙(而有限責(zé)任合伙為普通合伙之特殊形態(tài)②美國(guó)的普通合伙與有限責(zé)任合伙實(shí)質(zhì)上均為普通合伙,其分別可對(duì)應(yīng)我國(guó)普通合伙和特殊普通合伙制度,與我國(guó)相關(guān)制度差異不大。)與有限合伙(而有限責(zé)任有限合伙為有限合伙之特殊形態(tài)③美國(guó)有限合伙與我國(guó)有限合伙企業(yè)類(lèi)似,其頗具特色的為有限責(zé)任有限合伙。有限責(zé)任有限合伙將有限合伙與有限責(zé)任合伙(即我國(guó)的特殊普通合伙)的優(yōu)勢(shì)相結(jié)合,依有限責(zé)任有限合伙組織形式的風(fēng)險(xiǎn)投資基金為例,不僅作為有限合伙人的出資人受有限責(zé)任的保護(hù),作為普通合伙人的基金管理人(自然人)也享有有限責(zé)任合伙中普通合伙人有條件的有限責(zé)任的保護(hù)。即普通合伙人只對(duì)自己的過(guò)失給風(fēng)險(xiǎn)投資企業(yè)造成的損失承擔(dān)無(wú)限責(zé)任,而對(duì)其他普通合伙人在管理風(fēng)險(xiǎn)投資基金過(guò)程中產(chǎn)生的過(guò)失不承擔(dān)連帶責(zé)任。詳見(jiàn)沈四寶、郭丹:《美國(guó)合伙制企業(yè)法比較評(píng)析及對(duì)中國(guó)法的借鑒》,載《甘肅政法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6年第2期,第24頁(yè)。)。就普通合伙的構(gòu)成而言,僅需以營(yíng)利為目的,無(wú)需履行任何公法程序即可成立普通合伙(如此以來(lái),則無(wú)需在立法按是否營(yíng)利去區(qū)分其是民事合伙還是商事合伙),但有限合伙必須申報(bào)登記,否則為普通合伙。同時(shí)根據(jù)是否登記,普通合伙與有限合伙之間適用法律依據(jù)有所不同,即普通合伙和有限責(zé)任合伙適用1914年《統(tǒng)一合伙法》與1994年《修訂統(tǒng)一合伙法》;有限合伙和有限責(zé)任有限合伙適用1916年《統(tǒng)一有限合伙法)》與1985年《修訂統(tǒng)一有限合伙法》。④騰威著:《合伙法理論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頁(yè)。
從英美國(guó)家合伙立法模式來(lái)看,不同的合伙制度以不同單行法規(guī)制。不論普通合伙、有限合伙,抑或是有限責(zé)任合伙,不再以是否營(yíng)利、是否為組織體等去區(qū)分其是否為民事合伙,還是商事合伙,而是將登記作為區(qū)分合伙類(lèi)型、合伙人責(zé)任及適用具體單行法技術(shù)性規(guī)則,從而簡(jiǎn)化了法律識(shí)別過(guò)程中的困擾,亦使傳統(tǒng)合伙立法技術(shù)下登記所攜帶的法律父愛(ài)主義因子被剔除,登記僅演化為合伙人自愿選擇是否改變自身風(fēng)險(xiǎn)狀態(tài)的一種手段。故而,筆者以為英美法此種便捷的技術(shù)性規(guī)則可為我國(guó)合伙主體規(guī)制模式提供借鑒思路。
三、民法典構(gòu)造中的統(tǒng)一合伙規(guī)制模式之選擇
目前我國(guó)民法典相關(guān)草案已經(jīng)公布,合理選擇合伙規(guī)制模式不僅關(guān)系到民法典體系之合理性,同時(shí)亦關(guān)系到市民生活之有序推進(jìn)。民法典是調(diào)整市民生活之總綱,是市民主體行為之可選擇范圍,且從法律工具主義理念出發(fā),法律本身在于社會(huì)生活之便利解決、行為性質(zhì)之厘清,而不應(yīng)脫離生活淪為高深的部門(mén)法哲學(xué)。⑤在民法典制定過(guò)程中,江平教授提出關(guān)于財(cái)產(chǎn)法的制定上,我們不應(yīng)該采用物權(quán)這樣的概念——一則老百姓不懂,二則領(lǐng)導(dǎo)人也不懂。應(yīng)該直接像英美國(guó)家一樣,制定一個(gè)財(cái)產(chǎn)法,在財(cái)產(chǎn)法之下,再分有形財(cái)產(chǎn)、無(wú)形財(cái)產(chǎn)。債權(quán)概念我們也不要用,就直接用合同和侵權(quán)行為之概念。筆者認(rèn)為在合伙法律制定時(shí)理應(yīng)采取此種立法理念。詳見(jiàn):中外法學(xué)編輯部、北京大學(xué)第22屆研究生會(huì)編:《中國(guó)民法百年回顧與前瞻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文集》,法律出版社2003版,第415頁(yè)。通過(guò)反思我國(guó)現(xiàn)行合伙規(guī)制模式和檢索域外法,筆者意為在我國(guó)民法典制定過(guò)程中必須堅(jiān)持民商合一體例下的合伙制度構(gòu)造,唯此才能破除現(xiàn)行法體例下的諸多問(wèn)題。
(一)構(gòu)建統(tǒng)一合伙規(guī)制模式的可行性說(shuō)明
誠(chéng)如上析,目前我國(guó)合伙規(guī)制模式存在難以自洽的矛盾,而域外各國(guó)在解決曾與我國(guó)相同立法之困局時(shí),無(wú)論是從形式還是從實(shí)質(zhì)都在試圖構(gòu)建統(tǒng)一的合伙規(guī)制模式。故,筆者意為我國(guó)在民法法典化的進(jìn)程中也應(yīng)借鑒域外法之成功經(jīng)驗(yàn)以統(tǒng)一的合伙規(guī)制模式重構(gòu)我國(guó)合伙制度。筆者認(rèn)為所謂統(tǒng)一合伙規(guī)制模式是指引入英美國(guó)家登記區(qū)分規(guī)則,對(duì)合伙不再區(qū)分是民事合伙,還是商事合伙,僅將登記作為區(qū)分合伙類(lèi)型(有限合伙和普通合伙)和合伙人責(zé)任的一種規(guī)制模式。當(dāng)然,筆者之所以認(rèn)為可在我國(guó)構(gòu)建統(tǒng)一的合伙規(guī)制模式有其可行性依據(jù),具體理由如下:
首先,統(tǒng)一合伙規(guī)制模式符合市民生活的本旨。我國(guó)歷史演進(jìn)中的數(shù)次法典(草案)對(duì)合伙制度的定性與分類(lèi)基本是圍繞合伙的階級(jí)性與合伙人行為的主觀性而展開(kāi)的。如在二十世紀(jì)五十年代囿于當(dāng)時(shí)政治環(huán)境影響,對(duì)合伙制度的研究尚處初級(jí)階段——當(dāng)時(shí)立法中還存在私人之間有沒(méi)有合伙經(jīng)營(yíng)買(mǎi)賣(mài)和其他事業(yè)之疑問(wèn);①在1956年左右專(zhuān)門(mén)發(fā)布《關(guān)于合伙、聯(lián)營(yíng)問(wèn)題調(diào)查提綱》,其中關(guān)于合伙主要涉及兩個(gè)問(wèn)題:一是,目前私人間有沒(méi)有合伙經(jīng)營(yíng)買(mǎi)賣(mài)或其他事業(yè)的情況;二是,社會(huì)主義組織間(機(jī)關(guān)、企業(yè)、合作社、社會(huì)團(tuán)體)有沒(méi)有共同經(jīng)營(yíng)某種事業(yè)的情況。詳見(jiàn):何勤華、李秀清、陳頤編:《新中國(guó)民法典草案總覽(中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36頁(yè)。關(guān)于合伙性質(zhì)之認(rèn)識(shí)仍處于“資”與“社”的階級(jí)屬性劃分之中。②全國(guó)人民代表大會(huì)常務(wù)委員會(huì)辦公廳研究室于1957年1月21日發(fā)布了《債權(quán)篇聯(lián)營(yíng)(合伙)參考資料》,其中總結(jié)了北京市12個(gè)聯(lián)營(yíng)章程,以此作為草擬聯(lián)誼(合伙)條文的參考資料。其中就聯(lián)營(yíng)的性質(zhì)而言認(rèn)為是“在國(guó)家有關(guān)業(yè)務(wù)部門(mén)的領(lǐng)導(dǎo)下,小商、小販、小手工業(yè)者,自愿組織起來(lái),實(shí)行資金入股、共同勞動(dòng)、統(tǒng)一經(jīng)營(yíng)、統(tǒng)一核算、共負(fù)盈虧的半社會(huì)主義性質(zhì)的商業(yè)組織”。詳見(jiàn):何勤華、李秀清、陳頤編:《新中國(guó)民法典草案總覽(中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438頁(yè)。后隨著民商分立理論的出現(xiàn),以合伙人行為之主觀性——營(yíng)利——區(qū)分民商事合伙的理論也在立法中逐漸被承認(rèn)。然而,筆者以為合伙僅是私主體降低風(fēng)險(xiǎn)的結(jié)合體,并不摻雜任何公法性因素。同時(shí),市民社會(huì)中主體的趨利避害性是民法經(jīng)濟(jì)人、理性人假設(shè)的基本前提,市民主體的所有行為均具趨利性。因此,筆者認(rèn)為對(duì)合伙進(jìn)行的階級(jí)性劃分和對(duì)合伙人行為的主觀性考察并不符合市民生活之本旨,而統(tǒng)一合伙規(guī)制模式僅要求對(duì)民事主體的行為從實(shí)踐角度定性,僅從行為的外觀性出發(fā)而并不討論主體行為的階級(jí)性與主觀性,故此不僅符合法律是對(duì)行為進(jìn)行的外部性評(píng)價(jià)這一特征,同時(shí)也符合市民合伙生活的實(shí)踐理性。
其次,統(tǒng)一合伙規(guī)制模式符合民法典編纂體例之要求。誠(chéng)如前文所析,我國(guó)現(xiàn)行合伙立法在形式上基本堅(jiān)持民商合一的編纂體例要求,但在具體立法操作中卻改變?yōu)槊裆谭至ⅰ9P者意為民商合一的統(tǒng)一合伙規(guī)制模式的構(gòu)建不但可以防止法典體系內(nèi)部邏輯的分裂,而且可對(duì)司法裁判形成統(tǒng)一的裁判準(zhǔn)據(jù)。當(dāng)然,目前學(xué)界有學(xué)者提出若將單獨(dú)立法融入民法典會(huì)使法典整體的概念體系、自洽性遭致破壞。③趙紅梅:《私法社會(huì)化的反思與批判——社會(huì)法學(xué)的視角》,載《中國(guó)法學(xué)》2008年第6期,第178頁(yè)。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單獨(dú)立法進(jìn)入民法典,不但會(huì)使民法典的體例雜亂無(wú)章,更可能導(dǎo)致法典內(nèi)容因過(guò)于龐雜而不堪重負(fù)。④趙萬(wàn)一:《中國(guó)究竟需要一部什么樣的民法典——兼談民法典中如何處理與商法的關(guān)系》,載《現(xiàn)代法學(xué)》2015年第6期,第52頁(yè)。然筆者認(rèn)為上述觀點(diǎn)并不必然成立,此因法典體例之合理性并不在于形式上的條文之多少,同樣是民事主體之構(gòu)成,尤其自然人主體部分的條文依然很多,緣何成為法典體例科學(xué)之典范,而合伙制度卻成為反面之典型,顯然存有邏輯之悖。所以,筆者認(rèn)為統(tǒng)一合伙規(guī)制模式的選擇正是民法法典化進(jìn)程中民商合一邏輯的充分展開(kāi),正是對(duì)法典概念體系合伙合理性的證成,其并不構(gòu)成對(duì)法典體系之沖突,符合民法典編纂體例之要求。
最后,統(tǒng)一合伙規(guī)制模式之構(gòu)建可簡(jiǎn)化法律識(shí)別,方便司法裁判。目前司法實(shí)踐中由于我國(guó)區(qū)分民商事合伙標(biāo)準(zhǔn)的多元性,使得裁判合伙糾紛時(shí)在識(shí)別合伙類(lèi)型上出現(xiàn)司法實(shí)踐的不統(tǒng)一性,此不僅導(dǎo)致法官法律識(shí)別之難,亦導(dǎo)致案件的“同案不同判”。筆者意為由于合伙規(guī)則本身具有制度內(nèi)部的高度契合性,所以在民法典制定過(guò)程中應(yīng)當(dāng)整合現(xiàn)行合伙制度——將《民法通則》與《合伙企業(yè)法》之性質(zhì)相契合的制度進(jìn)行統(tǒng)一化處理——形成統(tǒng)一的合伙規(guī)制模式,如此便可不必再重重證成民商事合伙之區(qū)分,保證合伙制度的立法與司法邏輯之統(tǒng)一,同時(shí)將簡(jiǎn)化民商事合伙的法律識(shí)別、方便司法裁判。
(二)統(tǒng)一合伙規(guī)制模式之構(gòu)建
在合伙制度的法典化的進(jìn)程中,有學(xué)者提出在堅(jiān)持民商合一體例之下將合伙進(jìn)行二元制規(guī)制,在《合同法》領(lǐng)域確立合伙合同制度,在《公司法》領(lǐng)域修改并確立無(wú)限公司和兩合公司以此廢除《合伙企業(yè)法》實(shí)現(xiàn)對(duì)合伙制度的雙重規(guī)制。①馮躍芳:《中國(guó)合伙制度立法模式論》,西南政法大學(xué)2007年碩士學(xué)位論文,第33頁(yè)。筆者以為上述觀點(diǎn)有其可取之處,但仍是在堅(jiān)持契約型合伙與組織體型合伙之劃分的前提之下進(jìn)行的制度建構(gòu),且此觀點(diǎn)與現(xiàn)行法將合伙(無(wú)論契約型合伙,抑或是組織體型合伙)確定為主體而非債之法律關(guān)系的立法明顯相左。并且筆者認(rèn)為以無(wú)限公司與兩合公司的路徑重構(gòu)合伙制度已然不妥,此因以無(wú)限公司和兩合公司形態(tài)重構(gòu)合伙制度無(wú)形之中需要再次界定契約型合伙與組織體型合伙。如此,會(huì)陷入概念的重重證成之中,而目前我國(guó)合伙規(guī)制模式的重構(gòu)要避免的正是概念的重重論證,慎防陷入明希豪森困境之中。②“明希豪森”困境理論包括三種:第一,無(wú)限倒退(無(wú)窮地遞歸)。即A命題需要B命題支持和證明,B命題又需要C命題支持,C命題需要D命題支持,無(wú)限后退。由于理論上任何運(yùn)動(dòng)的東西都需要被另一個(gè)東西推動(dòng),這種論證方式的確定性需要建立在一個(gè)能夠證明其他命題而本身又是不證自明的公理之上,而在人文社會(huì)領(lǐng)域這種不證自明的命題又不存在,所以,必然陷入一種無(wú)限倒退的境地,以至無(wú)法確立任何論證的根基;第二,循環(huán)論證。即用B證明A;用C證明B,用A證明C,命題之間互相證明;第三,武斷地終止論證。在論證過(guò)程中,將某個(gè)特殊的理由和依據(jù)(例如某個(gè)教條、道德或宗教信條等)作為不證自明的東西,斷然地終止論證。例如通過(guò)宗教信條、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或其他方式的"教義"來(lái)結(jié)束論證的鏈條。同時(shí),也有學(xué)者提出制定統(tǒng)一合伙法之構(gòu)想,③方流芳:《關(guān)于制定合伙法的幾點(diǎn)意見(jiàn)》,載《中國(guó)工商管理研究》1995年第6期,第17頁(yè)。但并未言明具體如何構(gòu)建。筆者意為統(tǒng)一合伙規(guī)制模式的建構(gòu)應(yīng)從如下幾點(diǎn)進(jìn)行:
首先,轉(zhuǎn)變登記之性質(zhì),將登記與責(zé)任掛鉤,登記僅是合伙人責(zé)任承擔(dān)的區(qū)分依據(jù)。在統(tǒng)一合伙規(guī)制模式構(gòu)建中必須轉(zhuǎn)變登記作為法律父愛(ài)主義下政治性預(yù)防的這一屬性,將其轉(zhuǎn)變?yōu)楹匣锶顺袚?dān)責(zé)任——有限責(zé)任或連帶責(zé)任——之依據(jù),而非合伙本身成立之標(biāo)準(zhǔn)。歷史上我國(guó)曾在1956年討論聯(lián)營(yíng)[合伙]契約時(shí),就合伙的成立不僅需要章程,還需經(jīng)主管機(jī)關(guān)批準(zhǔn)或許可方可成立。④何勤華、李秀清、陳頤編:《新中國(guó)民法典草案總覽(中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33頁(yè)。現(xiàn)行《合伙企業(yè)法》第10條、第11條⑤《合伙企業(yè)法》第10條:申請(qǐng)人提交的登記申請(qǐng)材料齊全、符合法定形式,企業(yè)登記機(jī)關(guān)能夠當(dāng)場(chǎng)登記的,應(yīng)予當(dāng)場(chǎng)登記,發(fā)給營(yíng)業(yè)執(zhí)照。除前款規(guī)定情形外,企業(yè)登記機(jī)關(guān)應(yīng)當(dāng)自受理申請(qǐng)之日起二十日內(nèi),作出是否登記的決定。予以登記的,發(fā)給營(yíng)業(yè)執(zhí)照;不予登記的,應(yīng)當(dāng)給予書(shū)面答復(fù),并說(shuō)明理由。第11條:合伙企業(yè)的營(yíng)業(yè)執(zhí)照簽發(fā)日期,為合伙企業(yè)成立日期。針對(duì)合伙的設(shè)立上仍堅(jiān)持準(zhǔn)則主義設(shè)立模式,仍然將合伙的設(shè)立交由國(guó)家機(jī)關(guān)的公權(quán)力進(jìn)行管控。所以,筆者認(rèn)為合伙在設(shè)立與運(yùn)行的過(guò)程中,只要其在法律允許范圍之內(nèi),不應(yīng)以行政強(qiáng)制的手段限制私權(quán)利本身之運(yùn)行,而登記的行政屬性也應(yīng)轉(zhuǎn)變?yōu)槊袷滤椒▽傩浴?/p>
其次,以登記為合伙人責(zé)任承擔(dān)之界分點(diǎn)構(gòu)建統(tǒng)一合伙規(guī)制模式。基于商事領(lǐng)域內(nèi)普通合伙的責(zé)任連帶性與民事領(lǐng)域內(nèi)民事合伙的責(zé)任連帶性之性質(zhì)相重合,筆者認(rèn)為可將《民法通則》、《民通意見(jiàn)》中的合伙規(guī)定與現(xiàn)行《合伙企業(yè)法》中的普通合伙制度(包括特殊普通合伙)、有限合伙制度相整合,并置于民法典主體一編。在具體的體例安排上,民法典合伙編分為合伙的一般性規(guī)定、普通合伙、有限合伙與合伙的其他規(guī)定四節(jié)即可。在整合中,不再要求合伙是否采取組織體形式或者是否營(yíng)利,僅從責(zé)任意義上區(qū)分為有限合伙與普通合伙,即以登記作為界分點(diǎn),當(dāng)事人申請(qǐng)登記為有限合伙的,適用民法典有限合伙之規(guī)定;未登記的,統(tǒng)一適用民法典普通合伙之規(guī)定。
最后,統(tǒng)一合伙規(guī)制模式的建構(gòu)需維護(hù)合伙制度本身的獨(dú)立性。目前學(xué)界在構(gòu)造合伙制度時(shí)有意無(wú)意的在向自然人或者法人制度靠近,導(dǎo)致建構(gòu)的合伙制度無(wú)形之中帶有自然人或者法人制度的影子。筆者意為既然立法已經(jīng)賦予了合伙獨(dú)立的民事主體地位,故而在合伙制度構(gòu)成層面無(wú)需刻意靠近自然人或者法人制度,合伙僅是一種民事主體謀求利益的手段,其與自然人、法人制度沒(méi)有任何不同。故而,在構(gòu)建合伙制度時(shí)也無(wú)需考慮合伙制度形成之后在組織形式上到底如何選擇,是模擬自然人的日常形態(tài),還是按照法人一樣形成一定的組織機(jī)構(gòu),筆者以為此完全在于民事主體的意思自治,無(wú)需在立法層面強(qiáng)制性的要求合伙必須具備像法人一樣的某些要素。①我國(guó)《合伙企業(yè)法》第14條中要求合伙的成立必須具備某些要件——有自己的經(jīng)營(yíng)場(chǎng)所、組織機(jī)構(gòu)等,此無(wú)形之中是在模仿法人成立之要件。
四、結(jié)語(yǔ)
在市民生活中,民眾在謀取利益時(shí)無(wú)論其以自然人身份,還是法人身份,抑或是合伙形式,對(duì)于他們而言關(guān)注的僅是風(fēng)險(xiǎn)的存在與責(zé)任的承擔(dān),而對(duì)于學(xué)界和司法界所主張的民商事合伙之分并未有絲毫的留意。所以正如江平先生所言,民法典的制定必須為民眾生活之便,而非高深的部門(mén)法哲學(xué)。因此,筆者以為我們的立法必須符合市民社會(huì)最基本的生活邏輯,以市民生活的合理、方便解決為基本滿(mǎn)足點(diǎn),而以登記為工具所形成的責(zé)任區(qū)分意義上的統(tǒng)一合伙規(guī)制模式正是對(duì)市民主體所關(guān)注的對(duì)象和市民主體行為之客觀性的基本回應(yīng)。
(責(zé)任編輯:常琳)
【作者簡(jiǎn)介】陳鵬(1986-),男,甘肅慶陽(yáng)人,甘肅政法學(xué)院民商經(jīng)濟(jì)法學(xué)院教師。
【基金項(xiàng)目】本文系2015年甘肅省高等學(xué)校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重點(diǎn)研究基地——甘肅省經(jīng)濟(jì)法制研究中心科研資助項(xiàng)目《合伙主體資格研究》階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6-01-20
中圖分類(lèi)號(hào):D923.1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674-8557(2016)01-005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