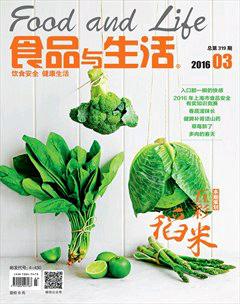糟缽頭 最“上海”(一)
周彤
老上海人沒人不知道杜月笙的,這位當年的流氓大亨既販過鴉片、開過賭場、鎮壓過工人運動,也行過慈善、抗過東洋、辦過紅十字會。
上海解放前,老謀深算的杜月笙既沒有聽國民黨的,也沒有聽共產黨的;既沒逃去臺灣,也沒留在上海,1949年4月,他獨自去了香港,這是他心目中最安全的避風港。
此時的杜月笙已是60歲開外的老人了,他聽不懂粵語,也沒有多少朋友,于是,只能和大多數上了年歲的人一樣,躺在寬大的搖椅里一遍又一遍地在回憶中思念故鄉。
對于獨處異鄉的人來說,老家的味道是思鄉之情最好的載體,但是香港沒有這種上海味道。其實,即使是在上海,他也只認定一家的風味,那就是百年老店“德興館”,家里的廚子無論如何都是做不出這種風味來的。那種綿長而幽雅的味道曾經那么親近,但此刻又那么遙遠。

這種思念像蜘蛛網一樣纏繞著他,終于,他決定不管花多大的代價,也要請上海的師傅到香港來一趟,他再也不能忍受沒有這種味道的日子了。
于是他便讓他的原總賬房黃國棟再次回到上海,找到了“德興館”。當時,由于美國的海上封鎖,上海的船只不能直達香港,于是黃國棟手持杜月笙的親筆信找到了時任上海市副市長的潘漢年,由潘漢年想辦法,安排“德興館”的兩位廚師經由第三國繞道去香港。
那么,讓杜月笙如此念念不忘的,到底是道什么樣的菜肴呢?這種勾魂的味道到底又是一種什么樣的風韻呢?
這道菜就是糟缽頭!
對生于上海川沙的杜月笙來說,糟缽頭的味道本身就是上海的化身。而這道很不怎么起眼的菜,可以說是本幫菜中資格最老的,差不多已經有210多年的歷史了。
本幫菜的基本成形是在清朝末期的同治、光緒年間,而它的孕育過程顯然要漫長得多。在咸豐年代以前,也就是中國還沒有與外國簽過什么“不平等條約”的時候,上海菜基本上都是些家常而平民的江南菜式,比如爛糊肉絲、紅燒大腸、腌篤鮮等,這些登不上大雅之堂的菜式往往取用的是些普通、廉價的原料,從這個角度也可以管窺一下,當時的上海還是一個“很不怎么樣的”小城市。
糟缽頭也是如此,這道菜最早差不多就是豬下水的一鍋大雜燴。與如今這個世道所不同的是,在明清那會兒,豬肉很值錢,而內臟下水卻不大值錢,這些耳、腦、舌、肺、肝、肚等內臟往往是殺完豬以后窮人的“殺饞”之物。而這些“殺饞”之物的做法也極其簡單,那就是一鍋亂燉,上海話稱之為“篤”。
如果大家都這么簡簡單單地“篤”下去,那么那種市井風情也許只有地方史研究者才會有點興趣。但這道菜“篤”到清朝嘉慶年間時,有個叫徐三的本地廚師,換了一種“篤”的方法。于是,糟缽頭這道名菜便誕生了。
徐三是上海浦東三林塘人。過去農村按地域的不同,往往都會像“世襲”一樣地傳承某種謀生的技能,比如蘇州東山的木匠、揚州杭集的玉工、歙縣鄭村的磚雕匠等。三林塘這個地方歷來是個廚師輩出的地方,學做菜是當地人除了種地以外最重要的謀生手藝,后世的本幫名廚大多祖籍出自浦東三林塘,故而三林塘有著“本幫菜搖籃”的說法。而徐三就是當時靠做菜小手藝謀生的“農民工”。
那么,當年徐三的“篤”法到底做了什么樣的革命性改良呢?據《淞南樂府》記載:“徐三善煮梅霜豬腳。邇年肆中以缽貯糟,入以豬耳、腦、舌及肝、肺、腸、胃等曰‘糟缽頭,邑人咸稱美味。”
這道美味到底美到了什么程度呢?有詩為證:“淞南好,風味舊曾諳。羊胛開尊朝戴九,豚蹄登席夜徐三,食品最江南。”
在清朝時的江南,吃羊肉就像今天吃燕鮑翅一樣,是極其尊貴的,因為江南本不產羊,這種奢侈的吃法要上溯到北宋變成南宋的那會兒,開封的那幫達官貴人們從北方河南帶過來的一種飲食癖好(同時帶來的另一種飲食癖好是以甜為雅,這同樣是不產甘蔗和甜菜的江南比較奢侈的)。
徐三的這道菜不僅能夠“登席”,而且還能夠和做羊肉的那位戴九老兄齊名,可見當年的文人對徐三和徐三的糟缽頭是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的。
不過中國美食史的記錄者們往往有一個大同小異的壞毛病,那就是所謂的“君子遠庖廚”,那時候的文人大多是不屑于記錄下廚師到底是怎么做出菜來的,這就是中國美食林中往往傳說很多,詩詞很多,但信史卻很少的原因之一。
說了半天,這道糟缽頭的美味到底是怎么回事,還是等于沒說,畢竟形容詞是堆不出美味來的。
糟缽頭這道菜傳到民國年間的時候,“德興館”等本幫菜館已經把它研究得相當透徹,并且已經達到從不失手的境界了。這道菜傳到今天,最有發言權的,當數本幫菜泰斗李伯榮大師。
徐三善煮梅霜豬腳。邇年肆中以缽貯糟,入以豬耳、腦、舌及肝、肺、腸、胃等曰‘糟缽頭,邑人咸稱美味。
——《淞南樂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