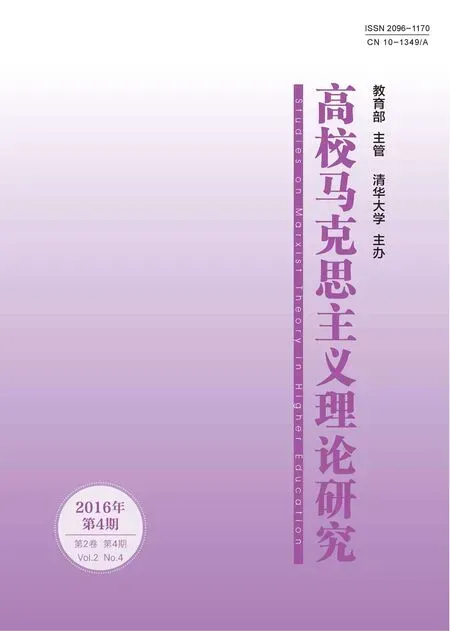《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立場性與人學理論建構*
劉臨達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立場性與人學理論建構*
劉臨達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簡稱《手稿》)是馬克思思想走向成熟過程中的重要著作,其中蘊含強烈的立場性與理論建構的訴求。《手稿》展現的是馬克思對不同理論的選用與揚棄,反映的是馬克思力求建構一種工人人學理論的努力過程。馬克思出于其工人立場的需要,引入異化勞動理論,否定了國民經濟學的私欲邏輯。《手稿》中的人本主義價值體系并非“價值懸設”,而是因引入異化勞動理論帶來的、必須完成的“價值建設”。對思辨哲學進行批判,否定精神的主體性地位,代之以感性實踐性的人的主體地位,同樣是出于建構工人人學的立場性需要。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工人立場;人學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的最大特點就在于其在馬克思思想發展歷程中所具有的過渡性。正是這種過渡性,使其具有了高度的混合性與駁雜性:“馬克思思想體系中的諸多組成部分在《手稿》中都能找到原生態基因。”[1]29無論是費爾巴哈哲學的舊痕跡、黑格爾哲學的影子,還是后期經濟學的萌芽跡象,都能在《手稿》中找到“藏身之處”。正是這種混合性,給《手稿》的解讀帶來了巨大的困難。這種混合性,給對其進行單純定性留以巨大的空間,如將《手稿》簡單地界定為歷史唯物主義誕生的標志,抑或舊人本主義的“價值懸設”。而筆者認為,這種混合性應從“立場性寫作”與理論建構的角度來理解。《手稿》應理解為馬克思出于建構一個為工人的理論的總意向所作的一次關于工人人學的建構嘗試。
在《手稿》中,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的一個最大的理論努力方向,那就是否定私欲與貪欲,而私欲與貪欲正是舊國民經濟學為馬克思指引的思考方向。因為為了否定私欲與貪欲,馬克思才要引入異化勞動理論。而正是因為引入了異化勞動理論,馬克思才要改造并超越舊思辨哲學的辯證法——因為賦予勞動以非私欲的解釋,依賴的正是辯證法的邏輯正當性。這一切都應從理論建構的角度理解,正是這種建構,也使《手稿》不是單純的“價值懸設”,而是一種“價值建設”。
一、辯證法對私欲的否定
《手稿》的第一部分,充斥著大量的經濟學摘抄。而對于這些摘抄,馬克思最終轉向一種強烈的批判。究其原因,應當歸結為國民經濟學的私欲假設違背了馬克思的工人立場。按照這種私欲邏輯,工人的勞動動因在于私利:“工資的提高在工人身上激起資本家那樣的致富欲望。”[2]121言下之意,在國民經濟學的邏輯里,無論是工人還是資本家,都是趨利的動物,一切經濟的運轉都從私欲開始,最終,私欲建立起了一座經濟大廈。工人于是就在這個私欲對自身的建構過程中,趨向毀滅:“首先,工資的提高引起工人的過度勞動。他們越想多掙幾個錢,他們就越不得不犧牲自己的時間,并且完全放棄一切自由,在掙錢欲望的驅使下從事奴隸勞動。這就縮短了工人的壽命。”[2]119在工人趨向毀滅的同時,資本完成了積累,并反過來加劇工人的毀滅:“資本的積累擴大分工,而分工則增加工人的人數;反過來,工人人數的增加擴大分工,而分工又增加資本的積累。”[2]120
這在國民經濟學的思維看來是合理的,但是馬克思卻必須將其否定掉,探索更加深刻的理論來分析和批判現實。為什么?因為這種“合理性”和馬克思的工人立場相悖,即工人不應該是私欲驅動的動物。在當時的馬克思看來,工人一定是有其另外的更為深邃的本質的,即人的本質。馬克思在《手稿》中必須完成的一個任務,就是建構為工人的人學理論,為工人的勞動做“非私欲”闡發。如果承認國民經濟學基于私欲所作的推演,則工人出于私欲而自我毀滅也就具有了“合理性”。所以,立場性決定了馬克思理論建構的努力方向。于是,為了以“科學性”維護自身立場,馬克思必須尋找新的批判理論作為借鑒。出于這種需要,哲學再次登場。是立場性導致馬克思暫時告別經濟學,回步哲學,拾起了異化——復歸的理論模型。在“貪欲以及貪欲者之間的戰爭即競爭”[2]120一句之后,馬克思還刪去了一句話:“我們必須回顧上述財產的物質運動的本質。”[2]120雖然這句話被刪掉了,但我們卻可以通過這句話以及兩句話中被加粗的文字,探觸到馬克思深層次的思維意圖。實際上,馬克思為了否定國民經濟學的膚淺性,而意欲將國民經濟學歸入“現象”。所以,馬克思這里的言下之意是:對現實的理解,并不應按國民經濟學那種膚淺的現象級的理論來進行,在這之下,一定有什么本質層面的實質意義未被探究。馬克思之所以要發出這樣的論證,實際上還是為了引入更為“本質”的理論來對現實問題作新的解釋,以新的、本質層面的理論,以理論層級上的優越性,否定國民經濟學架設在私欲之上的“合理”推演。
在發現了私欲邏輯這一國民經濟學的核心假設后,馬克思的理論建構即已啟程。在當時的馬克思看來,辯證法的本質邏輯正是可以對抗私欲邏輯的有力武器。在辯證法的邏輯之中,主體的勞動應該是對主體自身的本質的實現。主體通過勞動,應該滿足的是主體的本質,而非私欲。在引入異化勞動理論時,馬克思實際上是將工人對對象的占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架設在了辯證法的邏輯模式之上。辯證法是一種“內容邏輯,或者說是內涵邏輯”[3],工人對對象的占有的正義性,就存在于辯證法邏輯所包含的主體對客體、對對立面有要求的邏輯之中。異化的非正義性,以及復歸的正義性,都包含在辯證法的這種邏輯設定之中。
然而,辯證法和異化勞動理論的引入,帶來了兩個問題,即兩個理論任務:第一,人既然是主體,且人的本質不是作為本體的精神,那么人的本質是什么?所以,馬克思還要對人的本質作“非自我意識”的建構。所以,《手稿》的人本主義并不是一種“價值懸設”,而是一種“價值建設”。第二,改造思辨哲學的辯證法。因為以辯證法論述人,則辯證法不能再是精神的辯證法,而應當是人的辯證法、實踐的辯證法、人化自然的辯證法。
二、“價值建設”而非“價值懸設”
整個《手稿》所呈現出來的人學思想,都應該歸結為一種力求解釋人的本質的“價值建設”。這是否定和替代私欲邏輯的必要任務。正是為了完成這一任務,舊人本主義和思辨哲學都成了馬克思運用和改造的理論資源。總的來說,《手稿》中的人學思想包括以下幾個方面:①消除分工帶來的工人的發展的片面性,實現人的發展的豐富性;②消除貪欲造成的占有,消除基于權力的對立性社會關系;③人作為類存在,具有改造自然、人化自然的能力;④人是自然性和社會性統一的對象性存在物,人的本質在對象性活動的過程中體現。詳細檢視《手稿》中的人學理論,我們即可判斷其是否為“價值懸設”。實際上,上述①和②方面,是馬克思深入經濟學研究后,經過繼承與批判所獲得的思想成果;③和④方面,是馬克思借鑒費爾巴哈和思辨哲學的相關思想的理論重構。
一方面,馬克思闡述了克服工人處于分工體系中的發展片面性的思想。“工人”和“人”是馬克思特意進行區分的兩個概念。在《手稿》的語境里,人,應當是全面發展的、不囿于某一單調的分工工作之中的人。比如,馬克思說:“在分工有很大發展的情況下,工人要把自己的勞動轉用于其他方面是極為困難的。”[2]116以及類似“分工使工人越來越片面化和越來越有依賴性;分工不僅導致人的競爭,而且導致機器的競爭。因為工人被貶低為機器,所以機器就能作為競爭者與他相對抗”[2]121的論述。這里不能一一列舉,總的來看,馬克思關于人的發展的豐富性,克服人作為分工生產線上的工人的片面性,是馬克思人學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那么,這種人學思想是不是一種“價值懸設”?筆者認為,這不是一種“價值懸設”,相反,這是馬克思在經濟學研究過程中,在繼承與批判中獲得的價值取向。我們從馬克思所摘錄的舒爾茨的《生產運動》中的某些段落,便能找到一些與之相類似的論述:“‘從復合的手工勞動向下一階段過渡,首先要將這種手工勞動分解為若干簡單的操作。但是,最初只有一部分單調的重復的操作由機器來承擔,而另一部分由人來承擔。根據事物的本性和一致的經驗,這種連續不斷的單調的活動無論對于精神還是肉體都同樣有害。’(舒爾茨《生產運動》第69頁)。”[2]126同時,另一段從舒爾茨那里得來的摘抄是:“他們(工人)首先必須有能夠進行精神創造和精神享受的時間。”[2]125從馬克思的這種摘抄來看,即使馬克思自己沒有在經濟學研究中得出要克服人在分工中的片面性的結論,也一定能從舒爾茨的有關論述中獲得一定啟發。
另一方面,馬克思的人學建構中,存在著對貪欲、占有、權力的強烈否定。馬克思《手稿》中的人學思想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克服貪欲,消除基于貪欲的占有,消除權力性的對抗關系。所以,在馬克思的人學價值體系中,必然要包含這樣一個部分,即論述一種占有——非貪欲,非私欲——合乎人的本質占有。關于貪欲和占有的人學思想,出現在馬克思關于共產主義的論述中:出于貪欲來對勞動產品進行占有的共產主義,就是“物質的直接地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2]183的共產主義,在這種共產主義中,“工人這個規定并沒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廣到一切人身上”[2]183。在這里,“工人”和“占有”都被加粗,即馬克思要否定的私欲邏輯下的工人和占有。私欲邏輯下的工人在馬克思的人學思想中,是需要被超越的片面性的人的發展階段,所以,馬克思否定直接地占有。這種占有,只不過是把個人出于貪欲的排他式的占有,推廣到一切人身上的出于貪欲的占有。馬克思總結道:“這個用普遍的私有財產來反對私有財產的運動是以一種動物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用公妻制來反對婚姻。”[2]183這里,“公妻制”和“婚姻”作為加粗字體,都表示一種比喻。“公妻制”表示全體人共同出于貪欲占有私有財產,“婚姻”表示個人出于貪欲占有私有財產。
同時,若不消除基于貪欲的占有,人與人將一直處在一種權力關系之中:“普遍的和作為權力而形成的忌妒,是貪欲所采取的并且只是用另一種方式使自己得到滿足的隱蔽形式。任何私有財產本身所產生的思想,至少對于比自己更富足的私有財產都含有忌妒和平均主義欲望,這種忌妒和平均主義欲望甚至構成競爭的本質。”[2]184可見,馬克思對人學價值體系的建構,包含著一個克服私欲、克服權力關系的平等維度,這一維度很難說是一種“價值懸設”。在馬克思對貪欲、權力關系的批判中,我們可以看到其中包含的深刻的對經濟現象的批判,所以這是從經濟事實出發所進行的批判得來的人學價值維度,這是馬克思意欲主動建構的人學價值體系的重要部分。馬克思最后對其力求主動建構的人學理論中的“占有”總結道:“我們已經看到,在被積極揚棄了的私有財產的前提下,人如何生產人——他自己和別人;直接體現他的個性的對象如何是他自己為別人的存在,同時是這個別人的存在,而且也是這個別人為他的存在。”[2]187這段論述集中體現了馬克思對平權式社會關系的呼喚。而這種平權思想很難說是來自黑格爾還是來自費爾巴哈,更多地還是應該歸結為馬克思自己的社會直觀和理論探究。
以上兩個方面的人學理論,是馬克思從經濟事實出發進行批判得來的;而另外兩個本節開篇提到的人學理論的維度,則是馬克思借鑒了費爾巴哈和思辨哲學的邏輯模式所闡發的更為宏觀的人學思想。
馬克思首先闡發了人化自然的類思想。《手稿》從費爾巴哈處借鑒而來的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就是費爾巴哈的類思想。在馬克思看來,人因為作為類存在物而具有了強大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是,馬克思借鑒的只是費爾巴哈類思想的邏輯模型,而在此邏輯模型下輸出的卻是馬克思自主建構的類思想。在費爾巴哈那里,類思想是一種宗教心理發生學的類思想。費爾巴哈認為,人總是會感覺到自身作為個體的局限性,從而希求一種超越。人希求的這種超越,其實是把人作為類的存在當成了自己想象力的對象。人將上帝賦予人格式的想象形式時,其實是將人作為類存在的能力賦形為一個人格式的象征——上帝。費爾巴哈說:“上帝起源于缺乏感。”[4]115比如,個體的人總是要死的,但個體卻有超越個體局限的期望,有不死的想象需求。而在自身無法達到不死的境界之時,人便利用想象力將不死的期望對象化到人格性的上帝之上。“人格上帝之所以必要,乃是由于人格式的人只有在人格性中才適得其所,只有在人格性之中,才找到‘自己’。本體、純粹的精神、單單的理性滿足不了他,對他來說,這些東西太抽象了,因為這些東西并不表現他自己。”[4]145“在上帝之人格性中,人贊美他自己的人格性之超自然、不死、不依賴和無限制。”[4]145“上帝的本質不是別的,只是擺脫了自然限制的人的本質。”[5]37所以,人格性的上帝,其實就是作為類的形式存在于想象力之中的對象。這就是費爾巴哈在其宗教心理發生學中闡釋的類思想,即人利用想象力,借助對類的想象,超越自身意識到的局限。這種類思想無疑被馬克思借鑒了過來,但是馬克思卻將之加以改造。在馬克思那里,人同樣是借類來超越自身的,但是不同的是,卻不是利用想象力,而是利用實踐能力。人以類的方式存在,其作為類的強大的實踐能力,使人能夠從事人化自然的實踐。馬克思說:“人把自身當作現有的、有生命的類來對待,因為人把自身當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來對待。”[2]161“人和動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賴以生活的無機界的范圍就越廣闊。”[2]161“在實踐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現為這樣的普遍性,它把整個自然界——首先作為人的直接的生活資料,其次作為人的生命活動的對象(材料)和工具——變成人的無機的身體。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體而言,是人的無機的身體。”[2]161
可以看出,在費爾巴哈那里,人的普遍性、類性是想象力的普遍性。而在馬克思這里,人的普遍性、類性是實踐能力的普遍性、類性。所以,筆者認為,馬克思從費爾巴哈那里借鑒而來的,只是一種類思想的舊邏輯模式,而輸出的卻是一種全新的實踐意義上的人學理論——人化自然。
其次,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是自然性與社會性統一的對象性能力。費爾巴哈的人本學思想,在主客體統一的層面是一種屬性化統一的理論。從認識論的層面講,費爾巴哈對主客體的認識是一種直觀式的認識,主體在對象中顯現其本質,是一種基于感性確定性的直觀顯現。而馬克思從費爾巴哈那里借鑒而來的,只是主體于對象中顯現其本質的思維架構,而在此架構之中,馬克思卻將其人學思想轉化為一種在歷史性、過程性之中主客體實現統一的實踐人學。“自由自覺的勞動”是人的本質,并非一種“價值懸設”,而是一種馬克思主動建構的人學理論維度。
為了對抗近代形而上學從主體中去除感性屬性、抽象出絕對實體的做法,費爾巴哈特別強調主體是具有自然特性、感性屬性的存在,主體的本質中包含各種屬性。即使是思維,也只是一種人的自然屬性:“思維是人的本質的一個必然的結果和屬性。”[5]76在費爾巴哈的對象性理論中,主體在客體中顯現的,是主體本質中的某種屬性化的質。費爾巴哈雖然也談到了某些實踐的內容,如“誰耕種土地,誰就是農夫;誰以打獵為生,誰就是獵人;誰捕魚,誰就是漁夫,諸如此類”[5]8,但在費爾巴哈看來,主體的質是主體固有的屬性,通過某種對象性活動,主體的質以某種屬性化的形式展現出來。一個人,他是漁夫,另一個人,他是農夫,原因就在于打魚、種田都是不同的人擁有的不同屬性。費爾巴哈沒有從實踐的維度來理解這些屬性,而只是把這些屬性當作人固有的感性確定性接受下來。不同的主體具有不同的屬性化的質,通過考察主體所面對的對象,能夠反推主體的屬性化的質。比如,費爾巴哈說:“草食動物的對象是植物,而由于這樣的對象,這種動物的本質,就與其他動物有所不同。又如眼的對象是光而不是聲音,不是氣味,而眼的本質就在眼的對象中向我顯現出來。”[5]8可見,費爾巴哈所闡述的主客體的統一,是一種先驗統一,不是一種在經驗的過程中的社會歷史性的生成式統一,也就是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所批評的:“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2]499
費爾巴哈的這種局限性,其來源就在于其直觀式的認識論方法,這也與他要反對思辨哲學的歷史任務有關。一言以蔽之,費爾巴哈在反對思辨哲學的同時,也把思辨哲學所體現出來的主客體辯證統一的主體能動性取消了。“為謀與抽象理智的對抗,特別是為謀與思辨推理的對抗,一句話,為謀與近代形而上學對抗計,費爾巴哈乃訴諸感性,訴諸對象性;而訴諸感性——對象性,對于費爾巴哈來說,同時意味著訴諸直觀,亦即訴諸感性直觀或對象性直觀(直觀的感性或對象性)。”[6]
然而對于馬克思來說,他因為要否定私欲邏輯,所以要保留辯證法的邏輯架構,這是馬克思與費爾巴哈人學的根本差異。與費爾巴哈不同,馬克思語境里的人的屬性,是一種社會歷史性的屬性,是一種在現實的勞動實踐生成歷史的過程中一起發展的屬性。由于這一切屬性都是帶有社會歷史性的屬性,所以其不可能是人的本質,這些屬性應該是來自于一種能夠生成這些屬性的本質。于是,馬克思將能夠從事“自由自覺的勞動”作為人的本質,加入其力求建構的人學理論當中。馬克思所說的人的本質是勞動本身,而不同于費爾巴哈所說的固有的屬性。在《手稿》的語境里,人和對象都統一在社會歷史的生成之中,而非直接的靜止式顯現。本質是一種能力,因為這種能力,對象才是一本打開的關于主體的“書”。誠然,馬克思當時還無法說明人為什么具有這種本質,但是這不能當作一種“懸設”來理解,而應當理解為馬克思意欲建構的努力方向。也正是因為它是一種建構方向,才有了后面對辯證法的唯物主義改造。
三、第三對象理論對黑格爾哲學的瓦解
正如前文提到過的,為了維護其立場性,馬克思引入異化勞動理論來否定國民經濟學,于是這遺留下一個重要的理論任務,即否定精神的主體性地位,而確立感性存在的實踐者的主體性地位。為實現這一轉變,馬克思闡發了有關第三對象的理論。
在黑格爾的思辨哲學里,實體即主體,精神作為主體,以“理性的狡黠”體現其能動性,完成創造活動。作為這種思辨哲學里的人,其能動性是作為自我意識的能動性。馬克思總結道:“自我意識的外化設定物性。因為人=自我意識,所以人的外化的、對象性的本質即物性(對他來說是對象的那個東西……)=外化的自我意識,而物性是由這種外化設定的。”[2]208所以人是一種精神性的存在,人的能動性在于精神的外化。但是馬克思要維護的立場,要為之發聲的工人,絕不能是在“理性的狡黠”的統攝下的精神性存在。如果工人是自我意識所驅動的,則馬克思只是和布魯諾·鮑威爾趨同。所以,馬克思要否定自我意識的作用。而要否定自我意識的主體性,就要提高第三對象的地位,使之不再是純粹被動的可以被精神以泛神論的方式融化進自身的異在,而是具有感性實在性的客觀存在。
有關第三對象理論,學界曾一度認為“馬克思的這些話確實有些令人費解”[7]。在筆者看來,所謂“第一對象”,就是意識自身。在黑格爾那里,意識可以是為意識的意識,意識能夠“走過一條經驗的序列”而認識自身,即“經過這樣發展而知道其自己是精神的這種精神”。[8]意識可以成為一種對自身進行反思的意識,所以意識自身是第一對象。所謂的“第二對象”,就是外化后的意識,如自我意識外化設定的物性。所謂的“第三對象”,則應當被理解為具有感性確定性的感性客體(在馬克思哲學語境下)。第三對象是具有感性確定性的對象,這就是為什么馬克思要提高第三對象的地位的原因。因為要否定精神作為主體的地位,就要提高感性客體的地位,使其不再是精神的泛神論統攝下的對象。所以,面對這樣的對象,人的實踐也就不再是作為精神的主體的實踐,而是實實在在的被“受動性”制約著的實踐。人的實踐,必須是一種對抗受動性的感性力量。關于這種“受動性”,馬克思說:“它(作為自我意識的人)所以創造或設定對象,只是因為它是被對象設定的,因為它本來就是自然界。”[2]209即人是自然界的人,而非自我意識的人。所以,“只要我有一個對象,這個對象就以我作為對象”[2]210-211。所以人是以自然界為前提的人,人的實踐能力也是在受動性制約下的改造自然界的現實感性力量。所以,在馬克思建構的人學中,人的實踐能力不再是作為主體的精神所帶來的,于是“激情、熱情是人強烈追求自己的對象的本質力量”[2]211。
關于“激情”“熱情”,學界的一種觀點將之稱為“激情本體論”[1]27。確實,馬克思的這種理論建構也可以被稱為一種“非科學的價值評判邏輯”[9]。但筆者認為,恰恰是在這種“非科學”之中,我們應該看到馬克思力求建構一種理論所付出的艱苦努力以及不懈探索。在這種理論建構的背后,恰恰是馬克思為工人的立場性所迸發出的對理論“徹底性”的強烈渴望。馬克思并非單純地要借某種理論來瓦解黑格爾哲學以實現哲學批判的某種哲學史任務。馬克思真正的意圖在于建構一種為工人的理論、一種工人人學,以實現對工人立場的維護。在“激情”“熱情”這種非科學的范疇被推出之際,我們也看到了馬克思在為工人的立場性驅動之下,在理論建構之路上的無奈與彷徨。在最終將黑格爾拉下神壇之際,我們也恰恰領會到了為什么這是“哲學獲得空前的理論勝利,而這一勝利也是哲學的失敗”[10]。因為單純地以科學性維護立場性的理論建構,無法找到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案。對時代問題的解答,無法通過人學理論的建構來完成。異化勞動理論和《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以及《資本論》雖然有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11],但馬克思之所以很少再提及異化勞動理論的真實原因,筆者認為就在于其在《手稿》中進行人學理論建構所產生的挫敗感與無奈。
四、小結
《手稿》是一次立場性寫作,是一次馬克思力求以理論的科學性來維護其為工人的立場性的人學理論建構嘗試。馬克思帶著為工人的立場性,試圖追求理論的“徹底性”,開啟了國民經濟學研究。但陷入當時國民經濟學重私欲的膚淺性邏輯之中,馬克思讀出的工人為私欲而勞動的結論,直接打擊了馬克思的為工人的立場。馬克思由此開啟了由立場性驅動的建立一種為工人的理論的探索。在引入了異化勞動理論來為工人的勞動進行“非私欲”的闡釋后,馬克思面臨兩大理論任務,即否定精神的主體性以及建構合理化的工人人學。由此,馬克思帶著深入經濟學研究所獲得的有益成果,借鑒費爾巴哈哲學的舊邏輯,輸出了關于工人的人學理論的新價值。同時,馬克思在其建構人學理論時,還借鑒了思辨哲學所發展了的主體能動性,克服了費爾巴哈哲學的直觀方法,從而將其人學理論建構成一種帶有生成性的社會歷史實踐論人學。最后,馬克思還借第三對象理論,瓦解了思辨哲學的唯心主義體系。
從立場性與理論建構的角度來解讀《手稿》,其最大的意義在于能夠避免對《手稿》進行簡單的諸如“價值懸設”等單純定性。混合性的最大意義就在于它是對過程與探索的體現。透過這個過程,我們能夠真切地體會到一種理論努力方向的成果與無奈,也能夠更加深刻地領會馬克思后期理論轉向的內在動因。《手稿》的探索,以激情和熱情為最終基石,顯然凸顯了這種理論建構的蒼白與無奈。由此,馬克思轉向“科學”,轉向《資本論》的寫作,在此視域下便顯得尤其生動!
[1] 王東,劉軍.馬克思哲學革命的源頭活水和思想基因——《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新解讀[J].理論學刊,2003(3).
[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交融與交鋒:關于馬克思與德國古典哲學的對話[J].哲學動態,2013(1):9.
[4] 費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M].榮振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5] 費爾巴哈.未來哲學原理[M].洪謙,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
[6] 吳曉明.形而上學的沒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66.
[7] 趙家祥.《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的地位[J].學習與探索, 2012(6):4.
[8] 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上卷)[M].賀麟,王玖興,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66.
[9] 張一兵.青年馬克思的批判的經濟哲學——《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第二、三筆記研究[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1999(1):11.
[10] 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M].顧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150.
[11] 孫熙國,尉浩.論馬克思異化勞動理論與資本批判理論的統一——《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與《資本論》比較研究[J].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4(4):16-26,157.
(編輯:蔡萬煥)
劉臨達,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 本文系清華大學自主科研計劃(文科專項項目)“馬克思早期哲學思考的雙重邏輯分析”(項目編號:2015THZWYX10)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