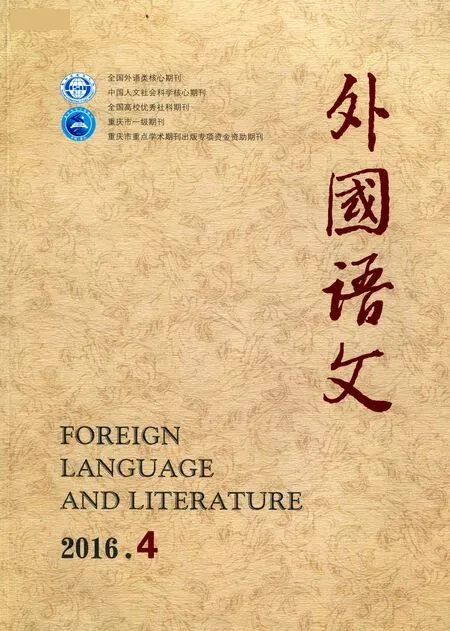論薩義德“理論旅行”①的批評實踐觀
黃麗娟 陶家俊
(1.北京外國語大學 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089;2.北京外國語大學 英語學院,北京 100089)
?
論薩義德“理論旅行”①的批評實踐觀
黃麗娟1陶家俊2
(1.北京外國語大學 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089;2.北京外國語大學 英語學院,北京 100089)
在《理論旅行》(1983)和《再議理論旅行》(1994)這兩篇文章中,美國后殖民思想家愛德華·薩義德從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喬治·盧卡奇的理論入手,考察理論在穿越歷史時間和地理空間時,如何遭遇不同社會的政治文化而分別降調(diào)弱化和激進強化的過程。本文在美國的批評理論譜系下從元理論層面剖析這兩篇文章中“旅行”所征兆的批評理論與批判意識時空觀,說明跨界性、轉(zhuǎn)化性和開放性是薩義德撰文所強調(diào)的“理論旅行”的動態(tài)運作機制。薩義德這一“理論旅行”的批評實踐觀為比較文學和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方法指導。
薩義德;理論旅行;批評實踐觀
在《理論旅行》(1983)和《再議理論旅行》(1994)這兩篇文章中,美國后殖民思想家愛德華·薩義德以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喬治·盧卡奇的理論為起點,論證了理論在穿越歷史時間和地理空間時,如何受到具體社會的政治文化影響而分別降調(diào)弱化和激進強化的過程,提出理論跨界旅行的批評實踐觀。這兩篇文章雖然篇幅不長,卻體現(xiàn)了薩義德批判思想的精髓,受到國內(nèi)外學者的廣泛關注。比爾·阿什克羅夫特認為:“理論旅行是威廉姆斯多個思想路線的延續(xù)拓展。”(Ashcroft,2001: 60)阿里·阿哈邁德(Ali Ahmad)指出,薩義德已拋開國家、階級和經(jīng)濟基礎等馬克思主義概念,主要立場已從馬克思主義轉(zhuǎn)變?yōu)楹蟋F(xiàn)代相關主義,更傾向于或在喚起后殖民思想驗證(Abbinnett,2009: 28)。還有學者認為薩義德在呼吁用跨界的思維方式,打破身份為中心的政治(Rooney,2009: 40)。甚至有人指出理論旅行體現(xiàn)了薩義德的悲觀思想(Veeser,2011: 122)。中國學界對薩義德“理論旅行”的評述出現(xiàn)在21世紀初,趙一凡在《西方文論講稿續(xù)編》一書中專門討論了薩義德“旅行理論的由來”(趙一凡,2009:497)。同年,趙建紅(2008:21)指出,旅行理論“是對具體的政治和社會情境的回應”,陶家俊撰文分析了薩義德理論旅行的“復調(diào)式”(陶家俊,2008:292)。現(xiàn)今,理論“旅行”已然成為國內(nèi)外學界研究理論在不同語境下變異的套語。但筆者發(fā)現(xiàn),還沒有研究從“旅行”的機制揭示這兩篇文章中薩義德的批評實踐觀。美國著名文化學者、歷史學家詹姆斯·克利福德認為旅行有著更寬廣的含義,“這一術語包含多種經(jīng)驗的轉(zhuǎn)化,比如‘離散’‘邊界’‘移民’‘旅游’‘朝圣’‘流放’…… 考慮到轉(zhuǎn)化具有歷史變數(shù),它沒有一個完整的比較視野下的穩(wěn)固之所” (Clifford,1997: 11)。本文在美國的批評理論譜系下從元理論層面考察這兩篇文章中“旅行”所征兆的批評理論與批判意識時空觀,說明跨界性、轉(zhuǎn)化性和開放性是薩義德所強調(diào)的“理論旅行”的動態(tài)運作機制。
首先,“旅行”隱指批評理論具有學科間的跨界性,而不局限于文學研究內(nèi)部。在《世界、文本和批評家》一書的開篇,薩義德以批評家的立場勾勒美國文學批評實踐現(xiàn)狀,他認為文學理論在美國是一個相對較新的學科,起步較晚,無法與歐洲媲美,因為早在20世紀初期,歐洲就有像沃爾特·本杰明和盧卡奇這樣涉足理論、頗有建樹的巨匠。在薩義德看來,美國理論界真正步入正軌是在20世紀70年代,而且是受到歐洲思想界的催發(fā)。二戰(zhàn)后,結(jié)構主義、符號學、解構主義等思潮紛紛登陸北美大學,這些粉墨登場的歐洲文學或批評理論的特點是在思想上大都具有反抗力,與社會實踐和人類行為緊密相連,這令薩義德非常贊賞:“干預的矛頭直指傳統(tǒng)守舊的大學模式、決定主義和實證主義所處的霸權地位、資產(chǎn)階級人文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物化現(xiàn)象以及學科專業(yè)上的刻板界限,出現(xiàn)了大量像索緒爾、盧卡奇、列維-施特勞斯、弗洛伊德、尼采、馬克思等思想家。”(Said,1983: 3)
然而,這場打破專業(yè)界限、勇敢卓絕的理論干預社會現(xiàn)實的運動卻在美國70年代末風向逆轉(zhuǎn),文學理論退到了后現(xiàn)代“文本化”(texuality)的怪圈和迷宮中,排斥歷史性,主題思想不再具有世事關懷,不再情境化。文學研究轉(zhuǎn)而成為精英行為和高雅文化實踐,人們將文學與人文學科一同視為罩在文化這一精美外表之下的唯美花瓶,主要任務是“保衛(wèi)經(jīng)典、自由教育的美德以及文學寶貴的愉悅性”(Said 1983: 2),完全脫離了社會現(xiàn)實語境。薩義德以一個人文學者的社會使命感尖銳地指出,這一與社會政治隔絕的文學理論“文本化”事實上脫離了“賴以發(fā)生和作為人類行為能理解的情境、事件和實際感覺”(Said,1983: 4)。
在《理論旅行》中,薩義德指出文學研究的領域并非封閉,理論的“旅行”要跨越原有的學科疆界和局限:“思想和理論就像人和批評流派一樣,經(jīng)歷從人到人、從地點到地點、從情境到情境、從時段到時段的旅行,使文化和知識生活在思想的循環(huán)下得到滋潤和營養(yǎng)……”(Said,1983: 226)“若要詳細闡釋理論如何從一種情境旅行到另一種情境,就會發(fā)現(xiàn)界定或限制任何理論所屬的領域,有著很大的不確定性。”(Said,1983: 227)。薩義德指出文學專業(yè)學生在進行“理論”或者“批評”時,僅僅專注于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依然不夠,因為文學研究的領域與其他學科間的界限已經(jīng)模糊,文學不再像從前那樣僅僅模仿現(xiàn)實、傳遞善意和人文精神。與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緊密相關的思想史和比較文學學科已經(jīng)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有很多斷裂、分散和不規(guī)則,原有的同質(zhì)空間已被打破,人們正放棄或在不完全借助從前那種“傳奇式的整齊合一、連貫完善”(Said,1983: 227)的專業(yè)領域。在這種情況下,文學顯然失去了既定的疆域界限,當代文學批評家也失去了界限分明的權威正統(tǒng)的研究疆域。究其原因,薩義德認為,知識專業(yè)化令人們對整個文學領域在內(nèi)部進行了切分式理解,與此同時,一些如符號學、后結(jié)構和拉康精神分析等外部話語介入文學話語,充斥文學批評領域。因此,僅僅停留在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學文本的內(nèi)在文學性已顯不足。除了關注文學性,人們已經(jīng)開始而且應該借鑒精神分析學、社會學或語言學等學科領域的知識。也就是說,批評領域排斥封閉固定,文學批評具有“孤單松散、引人憐憫和游戲性”(Said,1983: 229)。但這并不意味著出現(xiàn)了某種新方法或新技術,能起到主導作用,相反,有了“對各種無限闡釋的爭論,有了各種對文學或人文學科的永久主導價值的意識認識,有了各種宣稱能夠完成無須事實驗證的任務體系”(Said,1983:230)。薩義德引用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的觀點,認為當代批評實踐充滿張力和擺動,是一場無與倫比的語言運動。他認為可以用多元化稱這種跨界性,“一個機會,令人具有質(zhì)疑精神和批判性,既不屈服于教條主義,又不讓步于悲傷憂郁”(Said,1983: 230)。也就是說,人文領域如文學或思想史等不再有內(nèi)在界定的范圍,再也沒有任何一種理論能夠凌駕在異質(zhì)開放的書寫或文本闡釋之上,一定的理論或批評僅適用于特定的歷史情境。那么,一種理論在不同的社會和不同的歷史情境下會發(fā)生什么?
薩義德用“旅行”隱指理論具有隨地緣政治而變動調(diào)適的轉(zhuǎn)化性。在提到理論的轉(zhuǎn)化機制時,薩義德關注某種理論的形成與“出走”,指出“旅行”從來不是所向披靡、毫無阻攔地進入新環(huán)境,必然經(jīng)歷“與起點不同的重新表征與制度化的過程”(Said,1983: 226)。他將思想理論的“旅行”分4個階段:第一,思想形成,開始進入話語;第二,思想形成后穿行一定距離,指的是理論會受不同語境影響,從原點穿行到另一時間地點,得以發(fā)展;第三,異地接受或抵抗理論,具有一定條件;第四,理論在新的地點和時間,經(jīng)調(diào)試后被轉(zhuǎn)化。在這4個必要條件作用下,理論會進行相應轉(zhuǎn)化。在《理論旅行》一文中,薩義德描繪了一幅理論弱化降調(diào)的轉(zhuǎn)化圖景,而他似乎感覺意猶未盡,于是在時隔11年后,他又撰寫《再議理論旅行》,增補了強化激進的轉(zhuǎn)化圖景,足見他對一種理論隨不同社會的文化語境而產(chǎn)生多種轉(zhuǎn)化形式的思考。
薩義德深刻地剖析了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1923)中表述的物化-總體性思想的深邃內(nèi)涵及其革命性。在思想史上,笛卡爾、黑格爾、馬克思等哲學家對主客體之間的二律悖反關系均做過不同闡釋,盧卡奇在這些思想之上,進一步揭示資本主義社會拜物教對人的物化,還充滿信心而又預見性地提出無產(chǎn)階級意識的超越性。他從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結(jié)構入手,指出普遍的物化現(xiàn)象下,“主體”陷入僵局,逐漸與現(xiàn)代的工業(yè)生活割裂開來。但是,在危機時刻,以質(zhì)的形式存在的事物(如情感、激情、機遇等混亂的非理性)令大腦或主體透過事物的表面看到實質(zhì),戰(zhàn)勝僵化的客觀形式和物化厄運,獲取意識。“主體被動默觀的意識能夠轉(zhuǎn)變?yōu)橹鲃优械囊庾R,也就是說意識能從物的世界上升到理論的世界,形成主觀批判和思維能力,進而挑戰(zhàn)、塑造和改變未來。”(Said,1983: 233)無產(chǎn)階級反抗資本主義的物化世界,對其進行批判和反抗,會產(chǎn)生批判意識,也就是無產(chǎn)階級意識,由此盧卡奇揭露的是主客體對峙關系中主體意識獲理論的超越性和反抗性。
盧卡奇這一革命思想的火種旅行到20世紀的歐洲內(nèi)陸,經(jīng)歷了兩次降調(diào)弱化。第一次從匈牙利穿越歐陸山川到了50年代的法國,由盧西安·戈德曼完成轉(zhuǎn)化。戈德曼在自己的博士論文《隱蔽的上帝》(1955)中,將革命的理論意識降調(diào)成“世界視野”,認為精英作家的文本是“世界視野”的窗口,具有可感知的集體意識。他分析了17世紀巴斯卡爾和拉辛的作品,認為文本表達著對世界的認識,這種對世界的認識來自一定階層的整個思想和社會生活,表達了一定階層的思想和感受。如果說盧卡奇關注社會政治和生活領域的激進主客體對峙關系,那么戈德曼則將視角轉(zhuǎn)向?qū)W術研究領域中的個體作家作品與所推測世界之間結(jié)構上的對等關系。革命性的自我意識轉(zhuǎn)化為經(jīng)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性影響,總體性階級意識轉(zhuǎn)化為“世界視野”,是有成就的作家從階層的主導政治和經(jīng)濟氛圍中獲取,并在作品中表達的集體意識。在戈德曼那里,理論就是研究人員將不相關的事物以完美的對等關系聯(lián)系到一起。
到了70年代,盧卡奇的物化-總體性理論又一次穿過英吉利海峽到達英國劍橋,在年輕的雷蒙·威廉姆斯那里經(jīng)歷了第二次降調(diào)弱化。威廉姆斯曾聆聽戈德曼到劍橋的兩次講座,受到極大的啟發(fā)。他立足于利維斯和瑞查茲為代表的英國劍橋?qū)W術傳統(tǒng),認為總體性理論過于極端,要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采用不同的理論和批判意識理解物化變形,“總體性在那時是準確地批判這種變形的一種有力武器,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但是這種優(yōu)越其他價值的宣稱并不完善。相反,對特定經(jīng)濟狀況的歷史分析可以從根本上了解變形,克服戰(zhàn)勝它并不在于個別的見證者和獨立的行為,而是在于在實際中以更人性的、政治的和經(jīng)濟的方式,找到和創(chuàng)建更人性的社會。”(Williams,1980:21)他從盧卡奇和戈德曼兩者身上借鑒和摸索到更為細微復雜的理論意識,主張將文學與社會聯(lián)系一起。他撰寫的《鄉(xiāng)村與城市》一書就記錄了控制占有的局限以及反對控制占有的積極方法,認為:“無論一個社會體制多么占主導地位,控制占有僅是行動家設定的局限與選擇,因此它并不能窮盡和覆蓋所有的社會實踐,也就是說,總會有他種行為和他種目的,雖然他們并不在社會體制或建設中發(fā)聲。”(Williams,1979: 252)因此,威廉姆斯降低了物化對人們的完全占有和控制,認為它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充滿縫隙,可以抵抗控制。
如果說盧卡奇的物化-總體性理論的革命性經(jīng)過戈德曼和威廉姆斯的闡釋不斷弱化降調(diào)地轉(zhuǎn)化的話,《再議理論旅行》一文則增補了另外一種轉(zhuǎn)化方式——激進強化。同樣以盧卡奇革命總體性思想的源頭為靶,他討論的是不同美學形式與其產(chǎn)生或回應的特定歷史經(jīng)驗之間的關系。盧卡奇曾在《小說理論》(1920)中指出,小說是再現(xiàn)現(xiàn)代性的一種藝術形式,理論話語可以表征或揭示小說涵蓋的范疇以及主人公的命運,可以表達形式的基本諷刺意義,表現(xiàn)為解決主客體關系的無產(chǎn)階級階級意識(Said,1994: 254)。也就是說,在盧卡奇看來,主客體關系和現(xiàn)代性的反諷可以用敘事形式清楚地體現(xiàn)。
盧卡奇這一文藝理論旅行到40年代的德國和70年代非洲的阿爾及利亞。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西奧多·阿多諾在《新音樂哲學》(1948)中激進地將主客體之間轉(zhuǎn)化為不可調(diào)和性,闡釋了新音樂如何藝術地表現(xiàn)現(xiàn)代性無可挽回的墮落。在阿多諾看來,調(diào)性相當于封閉的商業(yè)資本主義社會體制,20世紀新音樂家勛伯格(Schoenberg)、貝爾格(Berg)*(1885—1935)奧地利作曲家。、韋伯恩(Webern)*(1883—1945)奧地利作曲家、指揮。等已經(jīng)超越前輩貝多芬、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俄國出生的作曲家、指揮家、鋼琴家和作家。(Stravinsky )和巴托克貝拉(Bartok)的封閉調(diào)性音樂傳統(tǒng),以非常邊緣、罕見、特殊的12音技法的藝術形式表達出對社會的拒絕與反抗(Said,1994: 255)。12音技法是勛伯格試圖發(fā)展無調(diào)性音樂所創(chuàng)作的新音樂形式,由半音節(jié)的12個音自由組成一個序列,它所表達的是音樂主體與客體世界之間的抗衡關系,以完全具有挑戰(zhàn)性的藝術模式拒絕附和討好聽眾。如果說盧卡奇以小說這種藝術形式表達了主客體關系的調(diào)和,代表著中間道路,一種綜合,那么12音技法新音樂理論則告訴人們綜合的不可能,主客體之間是絕對地抵制和抗衡。
第二次激進強化則發(fā)生在70年代的阿爾及利亞,知識分子弗朗茲·法農(nóng)分析種族主義中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的主客體對峙分離關系,意識到主客體之間辯證關系的活力,同時也注意到它的局限性。他指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是互相排斥,永不妥協(xié)和讓步的關系。前者侵吞劫掠,后者伺機報復(Said,1994: 261-262)。因此,法農(nóng)對殘酷的殖民主義開的解藥是暴力,沒有暴力就沒有解放。法農(nóng)似乎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系上復制盧卡奇的主客體關系,但在民族主義層面更超越盧卡奇。即:殖民與被殖民兩者之間是國家層面的對立敵視,是一方占有另一方、阻止另一方獨立而又相互依存的二律悖反關系,完全不可調(diào)和。這樣,盧卡奇的文藝理論經(jīng)過阿多諾和法農(nóng)的闡釋轉(zhuǎn)化,更加激進沖突。
再次,“旅行”隱指理論跨時空轉(zhuǎn)化過程中的開放性,強調(diào)批評理論與社會政治之間的積極互動關系,反對僵滯固化地將理論運用于社會實踐。在分析理論的兩次降調(diào)弱化和兩次激進強化旅行過程中,薩義德雖然沒有具體分析不同的社會語境,但顯而易見的是理論隨地緣政治的變化而開放地轉(zhuǎn)化。那么,轉(zhuǎn)化變動背后的歷史根源是什么?西方學者不難知曉,盧卡奇生活在20年代的布達佩斯,受俄國十月革命的熱潮影響,他對無產(chǎn)階級革命和未來充滿信心,洞見性地揮灑革命性的總體性理論,“理論對他而言就是由意識產(chǎn)生的,不是躲避現(xiàn)實而是投身于世事和周遭變化的革命意志”(Said,1983: 234)。到了20年代末和30年代,西方工業(yè)國家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不但沒有取得進展,法西斯主義反而肆虐猖獗。40年代中期冷戰(zhàn)開始,社會主義共和思想逐漸減弱,無產(chǎn)階級的未來越來越渺茫。50年代,隨著兩次世界大戰(zhàn)和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主義的揭露和批判,西方國家大批知識分子陷入困惑與思索。難怪法國的戈德曼和英國的威廉姆斯從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減弱了盧卡奇理論的革命性。另外,戰(zhàn)后科學技術飛速發(fā)展,異化現(xiàn)象日趨嚴重。到了60年代,隨著各國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興起和1968年爆發(fā)的“五月風暴”,抵抗和對峙資本主義發(fā)展與國家霸權主義的社會批判理論日益成風。德國的法蘭克福派學者阿多諾和法農(nóng)的激進思想也是風云變幻的時代癥候體現(xiàn)。
理論穿越地緣政治轉(zhuǎn)化時,所具的開放性不僅體現(xiàn)在理論家受時代癥候影響上,還體現(xiàn)在開放性地運用理論上,薩義德警示人們要杜絕全盤化,避免在現(xiàn)實社會中僵化保守地運用理論。他將矛頭指向法國著名思想家和理論家米歇爾·福柯最為有名的理論——知識/權力說。一方面,薩義德充分肯定福柯對改變?nèi)藗冇^念的貢獻,認為福柯的一系列作品從瘋癲或醫(yī)院等的檔案譜系著手,逐漸深入到權力世界和體制內(nèi)部,試圖從西方現(xiàn)代性內(nèi)部解釋權力運行的限制性體制,不斷地在思想上叩問和揭露工具話語的運作規(guī)律。福柯的權力理論還指出,體制的運作同樣依賴于體制的連續(xù)性以及體制合理性工具意識的彌散。福柯的理論無疑是對非歷史的形式主義的重要宣戰(zhàn),現(xiàn)身說法地向人們揭示,專業(yè)知識分子能夠掀起挑戰(zhàn)壓制性體制的小規(guī)模的游擊戰(zhàn),而不是“無聲和隱匿”。
但另一方面,薩義德認為即使福柯這樣透徹的開創(chuàng)性理論也會陷入自身的方法論陷阱,容易陷入簡單而封閉、脫離社會實踐的牢籠。他指出“權力”一詞在《知識考古學》一書之后開始頻繁出現(xiàn),甚至在《性史》中甚至表達出“權力無處不在”這樣簡單化的思想,屬于將理論過于整體化和全盤化,沒有考慮到歷史的特殊性,沒有考慮到目的、抵抗、努力或者沖突。相比之下,薩義德更加贊成喬姆斯基,喬姆斯基雖然與福柯一樣反對壓制,但他的理論更加具有社會政治性,具有活力與積極性。因此,薩義德認為福柯的歷史觀是文本化的或者情境化的。“在人類社會歷史中總有超越主導體制的事情發(fā)聲,無論主導體制貫穿社會多么深厚,這能產(chǎn)生變化,限制福柯意義上的權力,克服那種權力理論。” (Said,1983: 247)薩義德呼吁避免落入理論全盤化和單向度的陷阱僵局,“要認識到?jīng)]有理論能夠覆蓋、適用和預測所有的社會情境”(Said,1983: 241),也就是強調(diào)理論在旅行過程中的開放性。
綜上所述,薩義德用“旅行”隱喻理論的跨界性、轉(zhuǎn)化性和開放性,這種批評實踐觀與他所倡導的“世事性”“現(xiàn)世批評”“連接”(filiation)與“親緣”(affiliation)這類術語有異曲同工之處,均強調(diào)批評理論與社會政治兩者之間不可分割、相互貫通的動態(tài)機制,反對理論教條與保守主義。難能可貴的是薩義德還在這里為批評家和人文學者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即:要具備獨特而超越的批判意識。薩義德認為,既然理論表達的是超越物化世界的自我意識,受一個社會語境旅行到另一個社會語境的影響,會跨界、轉(zhuǎn)化而且開放,那么批評者在借鑒理論時一定要真正地考慮到理論的“旅行”特質(zhì)。沒有理論是完整不變而普適的,作為評論家或者理論家要具備社會實踐的批判意識。他主張將理論與批判意識區(qū)分開,具有批判意識意味著空間意義上具有更為寬廣的超越意識:“后者是空間意義,是一種定位理論的衡量功能,這意味著要根據(jù)理論出現(xiàn)的地點和實踐去掌握它,它只是那個實踐的一部分,在那個時間中或為那個時間運行,是對那個時間的回應。因此,第一個產(chǎn)生理論的地點要與接下來的地點對照比較,才能使用。具有批判意識意味著要了解環(huán)境差異,了解沒有什么體制或理論能夠窮盡或覆蓋它出現(xiàn)或要抑制的環(huán)境。總之,批判意識是抵抗理論的意識,對具體經(jīng)驗或矛盾闡釋進行抵抗的反應。”(Said,1983: 242)
進一步而言,評論家的任務就是要對理論進行有距離地審視,也就是薩義德所言評論家要具備“抵抗理論的意識”,不是機械地局限于學科界限、不是固守理論產(chǎn)生的合理性而一成不變地套用和泛用某種理論,而是關注每個理論得以產(chǎn)生的歷史和現(xiàn)實維度、社會維度、個人需求和利益維度,考察每種理論闡釋之外、理論產(chǎn)生之前和之后的具體日常現(xiàn)實和社會條件。薩義德“理論旅行”批判時間觀對國內(nèi)學界具有參考價值,也就是說,文學研究者既不能沒有理論指引,也不能將某種理論奉為圭臬,而要考慮到理論的“旅行”機制,錘煉批判意識。近年來,比較文學領域很多研究探討西方某某理論在中國的“旅行”,如:接受美學在中國的“旅行”、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中國旅行等,弄清楚薩義德所主張的理論跨時空“旅行”機制,對中國語境下比較文學和外國文學的跨文化研究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Abbinnett, Ross.2009. Fellow Travellers and Homeless Souls [G]∥ Ranjan Ghosh.EdwardSaidandtheLiterary,Social,andthePoliticalWorld. New York: Routledge.Ashroft, Bill and Hussein Kadhim.2001.EdwardSaidandthePost-Colonial[M].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Clifford, James. 1997.Routes:TravelandTranslationintheLateTwentiethCentury[M].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Rooney, Caroline. 2009. Derrida and Said: Ships that Pass in the Night [G]∥ Ranjan Ghosh.Edward Said and the Literary, Social, and the Political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Said, Edward.1983.Traveling Theory[G]∥TheWorld,TheText,andtheCritic. Harvard UP.
Said, Edward. 1994. Traveling Theory Reconsidered [G]∥ Robert M. Polhemus & B.Goger Henkle.CriticalReconstructions:TheRelationshipofFictionandLif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Veeser, H. Aram. 2011.Edward Said: The Charisma of Criticism[M]. New York: Routlege.
Williams, Raymond.1980.ProblemsinMaterialismandCulture[M]. London: Verso.
Williams,Raymond. 1979.PoliticsandLetters:InterviewswithNewLeftReview[M]. London: New Left Books.
陶家俊. 2008.薩義德“旅行理論”觀的啟示[J]. 英美文學研究論叢(1): 292-305.
趙建紅.2008.賽義德的“理論旅行與越界”說初探[J].當代外國文學(1) : 20-25.
趙一凡.2009.西方文論講稿續(xù)編[M].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責任編校:路小明
Critique and Praxis in Edward Said’s “Travelling Theory”
HUANGLijuanTAOJiajun
In two of his theses “Travelling Theory” (1983) and “Travelling Theory Revisited” (1994), Edward Said, American postcolonial theorist, uses the theory of George Ardorno, a western Marxist,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to explore the process of how theory undergoes upgrading and degrading when it travels spatial-temporally to different political, social situations. This thesis locates Said’s critique and praxis in the genealogy of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to analyze what “travel” meta-theoretically indicates and exemplifies, that is, boundary-crossing, translating and openness. This dynamic mechanism of Said’s travelling theory is a crucial methodology for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ross-cultural issues.
Edward Said; Travelling Theory ; critique and praxis
2016-04-16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yè)務費專項資金項目“現(xiàn)代旅行文學的中國敘事研究”(2016jj021)的階段性成果
黃麗娟,女,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英語小說、西方批評理論、比較文學和跨文化研究。
I712.074
A
1674-6414(2016)04-0005-05
陶家俊,男,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英語文學、后殖民研究、跨文化研究與批評理論研究。
① 英文題目為TravellingTheory,本文采用朱小敏博士發(fā)表在《術語與翻譯》2011年第5期的文章《旅行理論還是理論旅行——Traveling Theory中文譯名的思考》中的結(jié)論——“理論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