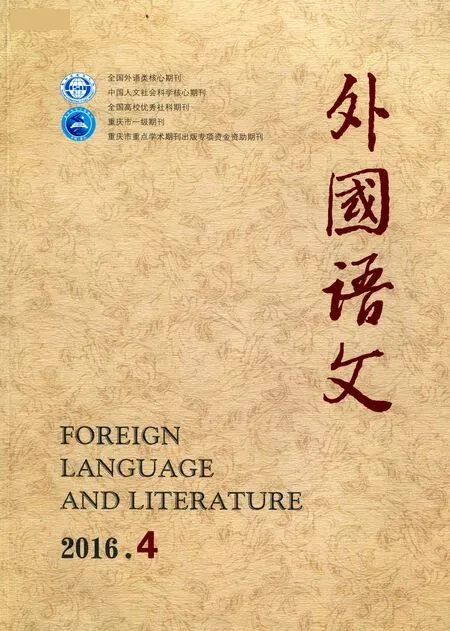克萊斯特《洪堡親王》劇中的不可知論
萬燦紅
(華東理工大學 外國語學院,上海 200237)
?
克萊斯特《洪堡親王》劇中的不可知論
萬燦紅
(華東理工大學 外國語學院,上海 200237)
康德的不可知論認為“物自體”在時空之外,所謂的真理并不是完全可靠的, 世界也并不是完全可以認知的。這種認知危機對克萊斯特的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亦成為其創作的源泉之一和作品的特色。本文即著眼于《洪堡親王》一劇,從主人公不可知的命運,亦虛亦實的夢來論述康德的不可知論對克萊斯特創作影響來剖析該劇的特點,從而得出克萊斯特對康德不可知論這一哲學論點的闡釋是基于他對該理論的親身體驗。這種體驗在他劇本中表現在:人無法完全認識外部世界,人的命運和人生發展都是不可預知的,無法掌控的,人無法按照自己事先設想的道路去生活。
康德;不可知論;克萊斯特;《洪堡親王》
0 引言
海因里希·馮·克萊斯特 (Heinrich von Kleist, 1777—1811)是德國劇作家、小說家和詩人,并且在他歷經的魏瑪古典時期和浪漫主義時期都被視作為“經典陣營中的隔岸人、局外人”(Wolfgang Beutin usw., 1994:188)。《法蘭克福評論報》專欄劇評人、編輯彼得·米查爾奇克說: “克萊斯特是一個難以接近、固執的人,同時他又是一個在動蕩、戰爭和革新的時代敏捷的人。” (Peter Michalzik,2011:Ⅰ)他的性格和人生選擇讓人捉摸不透,他的作品充斥著大量的幻覺、無意識、情節荒誕、不可預測、懷疑和壓抑。這些特點使克萊斯特及其作品研究有了各種推測的可能性。要對克萊斯特進行研究,便不可忽視他生命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即所謂的“康德危機”。
1800年,克萊斯特在柏林開始研究康德哲學。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指出,人只具備有限的認知能力,而“物自體”在時空之外,人們只能看到現象,而不能認識客觀對象的本質。康德認為世界并不是完全可以認識的,所謂的真理并不是完全可靠的。“人雖有知識的能動性,為自然界立法,但人也不是像神靈一樣全知的,而是有所知有所不知;所知者可以認識,所不知者可以思想,但認識和思想畢竟有區別。”(范進,1996:107-108)這種不可知論直接導致克萊斯特的世界觀發生根本的改變,因為深受啟蒙時代思想影響的他堅信理性的火炬能夠讓他認知知識的世界,然而這種樂觀主義在他接觸康德哲學后戛然而止。他在1801年給他的未婚妻威廉米娜·封·曾俄說:“不久前我了解到了新的所謂的康德哲學……我們不能確定,我們所說的真實是否是真的真實,還是這只是我們覺得是這樣的……我唯一的、最高的目標沉沒了,我現在沒有任何目標,自從我的內心充滿了這種信念:在這個世界上無法找到真實,我就再也沒有碰過書啦。” (Klaus Müller-Salget, Stefan Ortmanns(Hrsg.),1997: 205)恩斯特·卡西爾指出了康德哲學對克萊斯特藝術創作的意義,“沒有人比海因里希·馮·克萊斯特更深刻地、更內在地體驗過康德學說的含義,克萊斯特越是用盡所有的力量和熱情,所有本性中的個人能量去抵制它,越是受到他的侵襲”(Ernst Cassirer,1919:4f)。克萊斯特認為人的認知能力以及世界的可推測性被設定了界限,無法找到真實;同時他也將這種不可知論的觀點帶入他的創作之中,在他的作品里面探討認知的可能性和界限,有序的世界以及求真等主題。所以這種認知危機成為其創作源泉之一,亦成為他作品的特色。《弗里德里希·封·洪堡親王》(Friedrich von Homburg)(以下文中簡稱為《洪堡親王》)是克萊斯特1810年創作的劇本,也是克萊斯特最后的作品,講述了洪堡親王在戰爭中因為“夢”而遭遇的一系列事件。《洪堡親王》的故事情節可謂是跌宕起伏,一方面,克萊斯特沿承了一貫的偶然性、突發性的風格,這種突發性在常人眼里非常突兀,缺乏邏輯性和合理性,常讓人無法接受和理解;另一方面,全劇以“夢”為線索貫穿始終,洪堡親王的命運因為選帝侯隨意戲弄的“夢”而走上另一條軌道,而克萊斯特通過“夢”營造出一種似虛似真的交錯感,進一步加深了這種不確定性和偶然性。
1 不可知的命運
全劇故事情節荒誕離奇,匪夷所思。在1675年的費白林戰役中,洪堡親王、選帝侯、公主、選帝侯夫人、伯爵等系列貴族成員輪番登場。大戰前夕,洪堡親王沒有聽從選帝侯的指令隨騎兵部隊出發,而是在一棵大樹底下半夢半醒,手中拿著由桂樹葉編織的桂冠往自己頭上戴。選帝侯半是生氣半是戲弄一把奪過親王的桂冠,把它遞給納塔麗公主,迷糊中的親王好似清醒了,心急地站起來,順手去抓,結果只抓住了公主的一只手套。這時選帝侯等人快速地離開了現場。醒后因為手套而患上相思病的親王始終想入非非,在元帥安排作戰部署時,洪堡親王手拿記事板,定睛看著選帝侯夫人和納塔麗,充耳不聞元帥的命令,以至于在戰爭中違反軍令提前向敵人發起進攻,卻歪打正著贏得戰機,并取得了戰爭最后的勝利。滿心歡喜的親王以為就此可以功成名就,抱得美人歸。當他興高采烈等著邀功時,不料晴天霹靂:選帝侯因其嚴重違反軍令而要把他送上軍事法庭,處之以死刑!這一切的轉變是如此之快,僅在一夜之間,親王從英雄變成了階下囚。在親王所認知的世界里,他堅信選帝侯不會殺他。甚至到了軍事法庭上,親王依舊相信他從小愛戴的選帝侯不會將他處死:“他制造烏云滿天的黑暗,只是為了驅散它,使我的頭頂上空像太陽一樣大放光明。”(克萊斯特,1985:11)而最后的結果證明,這一切親王的“已認知”不過是他自己的臆想,現實情況實為親王的“不可知”。最后,當親王面對鐵一般的現實——選帝侯已經在親王的死刑判決書簽字,面對這種“不可知”無奈、痛苦的親王只得發出“天啊,我的希望!”(345)這樣的感慨。
親王得知自己的死訊,又看到為自己所挖的墳墓后陷入極端的恐懼,驚慌失措地去向選帝侯夫人求情: “如果我犯有錯誤,那就用別種方式來懲罰我,為什么一定要用槍彈的?免去我的職務,罷我的官;如果法律要這樣做,那就開除我的軍籍。我只想活下去,請不要問,那種生活是否體面!”(349)這時候的親王對于他與納塔莉的愛情,已經完全不顧:“在我心里,對她的溫情都已熄滅,假如瑞典國王卡爾·古斯塔夫要娶她,她完全可以委身于他,我會祝賀她的。”(350)他頓時變成了一個小丑,惶恐,膽怯,完全沒有了尊嚴。而下一幕,當他手握納塔麗從選帝侯那里求來的有條件的赦免令的時候,又開始思考其在選帝侯面前的尊嚴:“他在我面前是那么威嚴,我不想在他面前成為一個沒有尊嚴的人!只有我認識到自己身負重罪,他才肯寬恕我,要是這樣,我寧肯不要他的寬恕。”(363)前一秒親王不求“體面”只求活下去,后一秒又開始因為想要“尊嚴”寧愿接受法律的制裁。這一情節的前后似乎非常矛盾,又因為不符合普魯士軍人的正面形象,暴露出洪堡親王貪生怕死懦弱的缺點,所以該劇上演時,洪堡親王面臨死亡的恐懼這一情節常常刪除,因為人們不明白這一情節到底要說明什么。其實這是一種求生的本能,是感性的沖動,是對異化世界的抗爭,而軍規是異化世界的產物。他的感性已經超越了理性,這個世界無法認識和理解。洪堡親王不能依靠理智去認識這個世界,而是任憑求生的欲望去做那些有失尊嚴的事情。他詆毀理智,認為起決定作用的是本能的情欲(馮至,等,1958:187)。而當要求他親自承認自己的錯誤,他又選擇保持尊嚴。他用這種獨特的手法與理性抗衡,演繹自己對異化社會的抗爭,感性和理性的對抗成為克萊斯特作品的主題(趙雷蓮,2010:90)。正如康德所說,世界的認識是受到“心靈”影響,那么這顆多愁善感的心也不似“理性”那般一成不變,而是隨著時間空間不斷變化。
當親王萬念俱灰,坐等死亡來臨的時候,選帝侯又因為公主的幾句求情的話而簽下了赦免令,劇情陡變,生的希望再次點燃,生殺大權竟變得如此兒戲,這無疑是對命運的一種諷刺。洪堡親王的生死只取決于選帝侯的一道旨意,對于命運的不可知與事件發生的突兀性在本劇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如果我們把選帝侯看成是“上帝”或所說的“命運”,那么洪堡親王就是掙扎于這個社會上千千萬萬的“平凡人物”, “平凡人物”自以為參透了“命運”,可實際上“命運”在克萊斯特筆下是不可知的,你永遠也不會知道下一秒“命運”會對你做出何種選擇,是痛苦,是喜悅,是成功,乃至死亡?親王面對這個變化多端的世界毫無對抗的辦法,只能任由其擺布,人在不可知的命運面前是軟弱無力的。如康德所認為的那樣:物自體向我們展現它,但是我們總是受到自身心靈的影響而無法完全認識它。親王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尚且搞不清楚,又如何掌握自己的命運和人生,更別提是猜測別人的思想。人的命運和人生發展都是不可預知的,無法掌控的,人無法按照自己事先設想的道路去生活。
克萊斯特還將這種認知的困難性表現在劇中另一角色選帝侯的命運中。當費白林一戰勝利后,人們卻得知選帝侯犧牲的噩耗,正當所有人都悲痛欲絕,贊頌選帝侯為這個國家如何鞠躬盡瘁時,消息又傳來選帝侯還活著,說是選帝侯的坐騎受驚,司廄史費羅本和他交換了坐騎準備去馴服那匹選帝侯的白馬,誰料敵人誤以為那是選帝侯便將其射殺,選帝侯陰差陽錯地逃過了一劫。這一插曲著實讓讀者的情緒經歷了一次大的波動。世界是不可知的,你眼中看到的未必就是真實的,克萊斯特以突如其來的大轉折強調事件難以看透的特點,以此來表現命運的不可知的特征。該劇中逆轉生死的情節讓人覺得撲朔迷離,這并不是克萊斯特故弄玄虛,因為文學創作本來是要扣人心弦、出奇制勝,受不可知論的影響使得克萊斯特在這方面充分將偶發性、不可預知性注入到了情節安排中,增強了劇本的文學性和吸引力。有了不可知論,他可以更加大膽地發揮與安排情節的突發性和不可預知性,也讓突兀的情節有了合理的解釋。
2 夢——亦虛亦實的媒介
懷疑世界不可知使克萊斯特加入了浪漫主義運動的隊伍,他晚期的作品充滿了直覺、道德上的經驗、詩人的靈感、夢、陷入無意識(Heinrich v. Kleist und die Feinde Brandenburgs,1951:4)。夢是虛幻的、真假難辨的、難以捉摸的象征。克萊斯特將他所認為不能完全認識清楚的不確定因素巧妙地轉移到夢上,讓洪堡親王始終被夢左右,他的命運高低起伏,似乎都是夢做的主。克萊斯特用這一點很清晰地告訴讀者未來的不可知性,一切將要發生的事誰都不能做出準確的預測。夢成為劇本中亦虛亦實的媒介,洪堡親王出場便是一種半夢半醒的夢游狀態,給讀者一種混沌未明、不知真假的錯覺。夢中的洪堡給自己編織一個桂冠,這暗示著他最終的勝利,但正因為這是在夢中,這種勝利顯得虛無縹緲,也許更像是一種臆想:“我(洪堡)做了一個非常奇怪的夢!我夢見自己披金戴銀,一座王家宮殿的大門訇然中開,那些我所深愛的人:選帝侯和夫人……我也跟了上來,那丹墀卻無限擴展,直接天國大門,我東抓一把,西抓一把,令人駭異的是我一下子抓住了一位貴人,桂冠沒有抓到,宮殿的大門突然洞開,從殿內發出的一道閃電將她吞噬。大門又呼的一聲關了起來,在追逐中我從那甜蜜倩影的手上奮力掠下了一只手套,那些全能的神祗啊!我醒來后,手里還抓著這只手套。”(312-313)醒來后的洪堡親王不知自己所經歷的一切是真是假?亦如莊周夢蝶般,陷入混沌之中,整個夢中場景虛實相生,“披金戴銀”“閃電”等這些意象象征著夢的“虛”,而“選帝侯和夫人”、“手套”卻又是如此真實,更加離奇的是,這既是親王自以為的夢,卻又是真實發生的夢游事件。通過“夢”這種媒介手段,克萊斯特巧妙地把“可知”與“不可知”結合起來。對于洪堡親王而言,夢是“不可知”,他不知道自己“所知的”是否是真實發生的,還是只是自己腦海里的一種臆想;對于其他見證了親王夢游的人而言,他們自以為知道了“可知”,可是他們是真的知道嗎?所以當霍亨索倫伯爵嘲笑親王“你這全是癡人說夢!說不定你是在幽會,清醒地享受了肉體的快樂,結果是一只手套落在你的手里!”(313)時,親王毫不客氣地反駁他“什么話!落在我的手里,在我溫存的時刻!”(313)正是這種對于認知的差異,造成了“可知”與“不可知”的矛盾,而不同人從不同的角度來看,每個人的“可知”都是不同的,因為每個人所經歷的“時間”和“空間”是不同的。換言之,每個人都不可能知道別人的“可知”,這本身就是一種“不可知”。 人和人之間是不可能完全能相互了解的,彼此之間不同的認知也是對方無法了解的。同樣一個夢,對于親王來說“溫存時刻”,而對于霍亨索倫來說是“癡人說夢”,因為他們二人對于世界的認識是不同的。也即可以說,每個人從不同的認知看待同一個問題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而手套作為貫穿夢與現實的線索,把“虛”與“實”貫穿起來。在夢游中,親王獲得一只手套,醒來后,正是因為這只手套是真實存在,他陷入混亂之中,我真的是在做夢嗎?第二天在選帝侯頒布命令的時候,恰巧公主四處尋找手套,這又讓親王困惑,難道這只手套是公主的?亦夢幻亦真實,可知與不可知,在親王的世界引起一片混亂,這片混亂讓他在聽元帥的作戰計劃時仍魂不守舍,根本沒有聽清楚作戰計劃,夢境對現實產生致命的影響。對納塔麗的幻想進而又使他在陣地上一度陷入夢幻之中,促使他不顧一切,違令而行。康德認為,我們的心靈由于通過時間和空間來認識世界而帶有直觀形式,故而我們認識的世界不可避免地帶有主觀性,不是一個本真的世界。世界一分為二:本體世界和現象世界。本體世界對應于物本身或者物自身,是不可知的;現象世界對應于表象,是我們正在經歷的,能夠認識的。而人的認識能力不能超出感覺經驗或現象的范圍,不能認識事物的本質及發展規律;只能認識感覺現象世界,不能認識世界的本質。直至文章的最后,霍亨索倫伯爵道出了一切的真相,在讀者看來也頗似“上帝”戲弄“百姓”:“有天夜里,我們看到親王沉睡于花園的懸鈴木下,他手持桂冠,可能在夢想來日的勝利。您大概想了解他心里在想什么,于是便從他手中拿下了花冠,并把您胸前佩戴的項鏈微笑著纏繞與桂冠之上;然后您就把花冠和項鏈,他們互相交錯著,交給您高貴的甥女,公主小姐之手。親王站起身來,在這奇妙的情景中滿面通紅,他想從那么可愛的手中抓取那么美妙的東西。而您將公主拉到了一邊,便匆匆離他而去。您進了門,女郎、項鏈、桂冠也都倏而不見,孤零零的只有一只手套在手,從誰人的手中抓來的,這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又沉睡于午夜的懷抱之中。”(372-373)如果伯爵所說的是一個本真的世界,那這個世界便是客觀存在的。可正是這個本真的世界超越親王的認知界限,使親王產生了錯覺。他的理解是有限的,他不能完全認識這個世界,身為凡人的洪堡親王抓住僅有的一點線索——手套,試圖努力去還原真實,去認知物自體,但是最終他什么也無法確定,因為物自體是實在的對象,存在于人類認知之外,是不能直觀感知認識的,他所認知的世界便是劇本開頭,一個似夢非夢的世界。這個世界是不可知的,我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表象,人是無法認識外部世界的。
夢這個意象被克萊斯特運用得神乎其神,他將夢作為一種媒介,夢這個意象貫穿了整個劇本,夢境和現實交織在一起,給人一種撲朔迷離的難以認知的感覺,著力刻畫了一種虛實交錯的意境,這反映出創作者本身的虛實結合的心理活動。在洪堡親王這里,他的夢(夢游)則更加詭異,在腦海中好似發生過,可又沒有發生過。是真是假?在親王的腦海里,他已經無法分辨清楚。洪堡親王處于夢境狀態的言語在劇本里一再出現,如當選帝侯下令逮捕洪堡親王時,洪堡說:“我是在做夢?我是醒著,我還活著嗎?我還是沒有知覺。”(339-340)當納塔麗將選帝侯的赦免信交給洪堡時,洪堡說:“這不可能,不,這是在做夢!”(360) 在選帝侯的安排下,項鏈、桂冠、女郎再次回到醒著的洪堡身邊,面對突如其來的幸福洪堡卻暈過去了。被大炮驚醒后,他的第一句話是“不,請告訴我,這是不是一場夢?”(381)而科特維茨上校的回答“不是夢是什么呢?”(381)使得洪堡親王再次陷入夢的幻境。克萊斯特在劇本里總是出現“這是一場夢”等等之類的話,這種現實和夢境的混合真可謂是:亦真亦幻夢非夢,真真假假真非真。是否克萊斯特自己也陷入了如親王一般的迷茫、困惑之中呢?最終劇中發出這樣的回答“不是夢是什么呢?”(381)克萊斯特在這里設置令人費解的事實,創造一個充滿矛盾和謎團的環境,吸引讀者進入特定的“故事世界”中。這里的“夢”已不單純指實際上的存在于腦海中的“夢”,而是指那種虛無縹渺的、不為人所認知的現實與未來。洪堡所經歷的一切到底是真是假?克萊斯特沒有給出確切的答案,或許,這也是克萊斯特本人一直苦苦糾結卻沒有找到答案的地方。借助于夢游這一元素,使得整個劇本那些突兀的情節都顯得合情合理,且這種虛實結合的手段也提升該劇的藝術性。
3 結論
《洪堡親王》在很多研究中都被認為是作者在探討“統治者和他的軍官之間的軍法服從職責的必要性和它的界限”(11)。亦被稱為國家主義的劇作,宣揚為了國家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孫宜學,2001:26)。無疑對該劇可以做這樣的釋讀。但是細看劇中,可以看出不少主人公不太完美的非國家主義形象,但更深入的問題在背后,主人公的不服從、任性只是問題的一面,另一面主人公也表現出為了軍法的尊嚴不惜以身相擁的態度,可以說二者矛盾。但恰是這個矛盾烘托出了全劇的主題:生命的矛盾與不可知。反視克萊斯特的個人經歷,同樣如此。自己的藝術創作得到的卻只有冷眼,他的一腔熱情并沒有得到當局的賞識和接受,他的作品亦未得到同時代人的認可,克萊斯特的作品飽受歌德等人的批評:“即使是在決意表示真誠同情的時候,這位作家仍總是讓我感到戰栗和嫌惡,就像看到一幅原本天生美麗的肌體患了不治之癥……”(Müller-Seidel, Walter(Hesg.),1980:459-460)”克萊斯特面對自己不可預知的現實生活,他把自己心中的體驗表達出來并加以藝術升華,這也是克萊斯特深刻地、內在地表達過康德學說的含義。君特·布勒克爾曾指出:“克萊斯特的主人公生活在謎團中,這是作家在康德危機之后為他們,也為自己指明的生存空間。”(Günter Bl?cker,1960: 124)親王大膽追求榮譽和愛情,面對死亡的單純恐懼,以死維護法律的尊嚴獨特的性格,這是克萊斯特對人生、對世界的思考體悟,也是主人公道德精神的凈化和美化。克萊斯特面對自己殘酷的現實生活,感到了現實和理想的不確定性,不可知性,他認為一切都是不可知的,并把這一觀念融入他的創作中,在《洪堡親王》中則體現為:人無法認識外部世界,人的命運和人生都是不可知的,無法把握的,人無法按照自己事先設想的道路去生活。于是就出現了《洪堡親王》中讓人難以理解的突兀的情節以及洪堡親王不顧尊嚴求生的行為。克萊斯特在他充滿不確定和疑惑的世界里拼命掙扎,飽嘗痛苦的他沒有放棄過希望,時時都在渴望抓住一點確定性,所以他給融合了自己諸多特性的洪堡一個美好的結局,也許在他的潛意識里也曾默默希望自己可以和洪堡一樣以喜劇收場。但現實,不可知的現實,從沒讓他如愿以償。雖然該劇在1881年9月份轉交給了普魯士公主瑪麗安娜,但由于劇中洪堡親王對于死亡的恐懼的描繪引起普魯士王室的不悅,所以該劇在克萊斯特在世時一直沒有得到出版和上演;法國脅迫普魯士簽訂普法聯盟條約政治局勢的發展,他精神上的希望也完全破滅。面對自己的人生和命運不可知,加上經濟上的困窘,克萊斯特最終在1811年11月選擇飲彈自盡。一部戲劇,表面上敘說著“洪堡親王”的故事,實際上深深映現著作家個人的生活體驗:生命的混沌,亦虛亦實,因此不可知。或許生命本來就是如此,或東或西,雖然矛盾,但都是合理的。面對如此的生命,要么抗爭或妥協,像劇中的洪堡親王;要么放棄,像生活中的克萊斯特。生活中的克萊斯特雖然最終選擇放棄,但《洪堡親王》中的他卻無疑在尋找著在不可知世界中的生存,這或許是該劇的意義所在。
Anon. 1951.Heinrichv.KleistunddieFeindeBrandenburgs[N]. aus Die Zeit Nr. 35 vom 30 August 4.
Ernst Cassirer. 1960.Heinrich von Kleist und die Kantische Philisophie[M],Beilin: Verlag von Teuther & Reichard, 1919: S4f Günter Bl?cker: Heinrich von Kleist oder Das absolute Ich. Berlin: Argon Verlag.
Klaus Müller-Salget, Stefan Ortmanns(Hrsg.). 1997.HeinrichvonKleist:Brief.∥HeinrichvonKleist,S?mtlicheWerkeundBriefeinvierB?nden, Bd. 4. [G]. Frankfurt am Main: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Kleist, Heinrich von. 1995.WerkeundBriefe[M]. Herausgegeben von Siegfried Streller in Zusammenarbeit mit Peter Goldammer und Wolfgang Barthel, Anita Golz, Rudolf Loch. Berlin: Aufbau Verlag, 4. Auflage:24-25.
Müller-Seidel, Walter(Hesg.) 1980.HeinrichvonKleist,Aufs?tzeundEssays[M].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459-460.
Peter Michalzik. 2011.Kleist.Dichter,Krieger,Seelensucher[M], Berlin: Propyl?en Verlag, Ⅰ.Wolfgang Beutin, Klaus Ehlert, Wolfgang Emmerich, Helmut Hoffacker, Bernd Lutz, Volker Meid, Ralf Schnell, Peter Stein und Inge Stephan. 1994.DeutscheLiteraturgeschichte.VondenAnf?ngenbiszurGegenwart[M]. Fünfte, überarb. Auflage. Stuttgart, Weimar: Metzler.
鄧曉芒.2010.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釋義[M].北京:人民出版社.
范進.1996.康德文化哲學[M].北京:社會科學文化出版社,107-108.
馮至,等.1958.德國文學簡史:上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康德.2009.康德三大批判合集[M].鄧曉芒,譯.北京:人民出版社.
康德.2011.純粹理性批判(注釋本)[M].李秋林,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克萊斯特.1985.克萊斯特小說戲劇選[M].商章孫,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孫宜學.2001.論克萊斯特劇作《破甕記》的結構和戲劇藝術[J].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6-30.
趙蕾蓮.2014.論克萊斯特戲劇的現代性[M]. 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趙蕾蓮.2010.論克萊斯特中篇小說的現代性[J].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89-98.趙薇微.2009.與傳統和現實的抗爭——論德國作家克萊斯特的思想及其創作[J].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1):56-60.
責任編校:肖 誼
On Agnosticism in Kleist’sHumboldtPrince
WANCanhong
According to Kant’s agnosticism, “things-in itself” is beyond time and space. The world can’t be fully recognized and the truth is not completely reliable. These points of view have become one of the sources for his creative works and the unique style of his works and have a huge impact on his creative works as wel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knowable fate of the protagonist and virtual or real dreams,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reflection of Kant’s agnosticism on Kleist’sHumboldtPrinceand the features of this drama. It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at Kleist’s interpretation of Kant ’s philosophy is based on hands-on experience that the outside world can’t be fully understood by human and human’s fate and life are unpredictable and beyond control. What’s more, human cannot live a life like what was pre-planned.
Kant; agnosticism; Kleist;HumboldtPrince
2016-02-28
萬燦紅,女,華東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碩士,主要從事德語語言文學研究。
I516.074
A
1674-6414(2016)04-003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