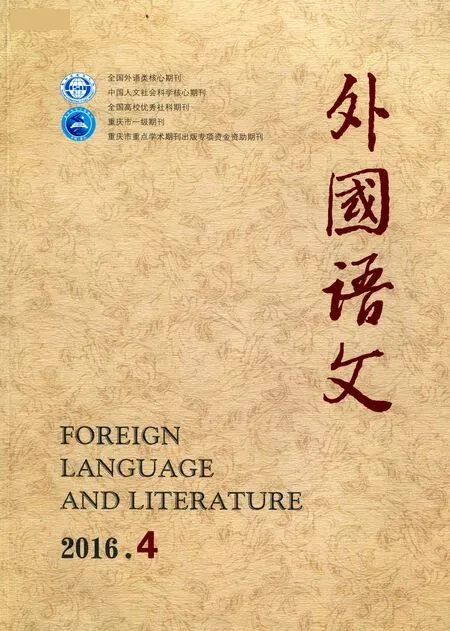域眾:人群活化與歷史還原
——動漫儀式性語境敘述分析
馬笑春
(重慶電子工程職業學院,重慶 301331)
?
域眾:人群活化與歷史還原
——動漫儀式性語境敘述分析
馬笑春
(重慶電子工程職業學院,重慶 301331)
族群、儀式、群體事件是動漫文學的基本要素。依據這個要素需要挖掘族群的內涵,探索文學反映生活需要進行文化還原,體現出大眾形象的語境意義。動漫域眾意向是歷史與大眾的還原,也是現代文化復興戰略發展策略的依據。
文化復興;族群回歸;域眾文學
1 動漫域眾研究背景及其族群問題提出
1.1 域眾文學的現代社會學以及人類學屬性
域眾,作為動漫術語,特指動漫中的族群。動漫吸引人的美學依據就是域眾作為一種族群現象,它很好地演示了社會族群制度的非封閉性特質,因此,動漫作品或者動漫游戲設計都具有意向性根由追尋的美學傾向。后現代文學域眾主題進行了形式到內容的改造,試圖將文學進行風俗再造。現代世界日益呈現出一體化的趨勢,現代化浪潮也如洶涌洪流席卷著整個世界,沖擊著全球的每一個角落。但是,“民族化”和“本土化”也在進一步強化,即各個民族的民族意識似乎也在空前高漲,其民族文化有著更加顯著的呈現和強烈的表達愿望,也呈現出強烈的族群認同傾向。在人類21世紀新的處境下,大眾以一種全新的眼光重新深入全面地考察和思索族群本體,即在“小人物——生存——歷史”的基本群體法則中獲得歷史的確認。
我們需要了解目前中國文化建設的域眾主題,就要首先恢復族群關愛、村落關愛、部族關愛。“語境場域”系由維特根斯坦提出,是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中的一個核心概念。它強調了語言活動的意義,旨在通過語言的使用過程研究語言。維特根斯坦將日常語言活動稱為“敘述”,指由語言和行動(指與語言交織在一起的那些行動)所組成的整體,即我們的語言是按照一定的規則在一定的場合中使用的活動,語言、規則和使用的活動就是它的基本要素。維特根斯坦的“語言”觀將話語理解視為一種建設性和持續性的活動,而決非僅是將話語所包含的信息輸入聽者大腦中的簡單過程,即話語理解乃是聽者在接收到話語信息后根據內容、觀點和場景的各種關系而進行系統闡釋的過程。任何一個詞語概念的含義或意義并不僅僅包含在其所意指的對象中,而是包含在其依據一定的規則與其他的詞語的組合方式中。
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指出,互動話語的意義體現在使用中,且意義的提取是多層次、自動化和共時加工的過程,要確定意義,聽者須依據內容場景等諸多因素對話語進行系統的解釋和闡述(鮑剛,2011:128)。馬歇爾·麥克盧漢曾指出:“人類心靈生活的戲劇模式……使我們能夠分享自己內心最深層的幻想”,其研究令人信服地證明了“人群語言敘述”通常以作為構成人類基礎文化的重要因素而發揮作用。我們有必要全面梳理儒家的人群禮儀儀式的域眾解讀,把人群活化、復原,全面構建中華文化體系。動漫文學尤其以域眾建構現代大眾的“現實-歷史”論域,摸索新的當代大眾公共論域中的人群傳統、族群與社會重建、語境中的人群敘述——這就是動漫語境的“場域倫理”以及大眾意向敘述。
1.2 現代人群回歸與禮儀敘述語境
人類學、歷史學一直在探索人類族群的命題。人類社會性的基礎依舊是族群,回歸族群是人類文化的語境歸因。隨著近代哲學到現代哲學再到后現代的過渡,身體問題、語言問題、他者等哲學基本問題都發生了演化和變遷。這些漸進或突變不僅擴大了“主體”外延和廣度,同時也逐步掏空了近代“社會主體”的內涵和深度,最終導致了主體形而上學的解體(楊大春,2002:79-86)。例如,阿佩爾的“交往共同體”取代了傳統的先驗意識的概念,認為主體不僅是指主動進行認識的人類,而且也包括認識者進行認知的情境,即在交往之中有兩個以上的主體自我存在,而不是一個獨我的主體和被看作純粹的認知客體的其他對象的共存(張今杰,林艷,2011:127-132)。如是一來,傳統的“主-客”對立模式隨之發生轉化:那些無生命的或無意識的傳統“主-客”思維模式中的物或客體,則借由觀察態度的轉變而充滿活力,以及那些隱藏于客觀世界背后的他者也就具有了主體資格而與傳統的主體進行互動(張世英,2002:220)。因此,儀式參與人必須表現為某個意義整體,其在自由的活動中以體驗的方式展現了某種意義,但這種意義不是表現給參與者自己的,而是表現給一個人群模式——語境;如果沒有人群儀式,語言表現的意義就沒有得到顯現,這個意義實際上就沒存在過,它沒有進入公共領域。因為,“通向觀眾的公在共同構成了游戲的封閉性。只有觀眾才實現了游戲作為游戲的東西”。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人群問題一再成為研究的核心問題。專家檢索出來的有關家庭史的相關成果,包括著作70余部,論文近200余篇*王立華.20世紀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家庭史研究述評(課題報告). 參見:http:∥bbs.jlu.edu.cn/cgi-bin /bbsanc?path=/groups/GROUP_7/CH/D97E7ACB6/D93A0560F/DA786CCEB/M.1078937681.A。但是,研究者根據文化歷史唯物觀的看法,認為族群在歷史上所依托的傳統教育制度、政治制度、家族制度等在20世紀已全面解體,作為族群的異化,現代社會制度異化了民族性格。文學研究一直堅持自己的族群宗旨,族群宿命在當代現實生活中,在大眾、知識分子、政治家內心存活著的憂患意識、大眾精神、奉獻精神中,不斷敘述著基本人群的“文化遺存”。黑格爾(2004:7)說過:“我們之所以是我們,乃是由于我們有歷史。或者說得更正確些,正如在思想史的領域里,過去的東西只是一方面,所以構成我們現在的,那個有共同性和永久性的成分,與我們的歷史性也是不可分離地結合著的。”甚至他還認為,現實“活動以一個現成的材料為前提,它針對著這些材料而活動,并且它并不僅是增加一些瑣碎的材料,而主要的是予以加工和改造”(李澤厚,1985:9)。
同樣,西方的族群意向主要建立在域眾法則上,這樣形成了不同城堡域眾的基本政治、經濟模式,因此,族群也是西方文化歸因的基本命題。西方文學也是圍繞不同的族群建立域眾,其構建法則并不亞于東方系統的宗族、氏族、部族體系。在現代西方社會科學中,西方學者普遍關注的社會資本、社會網絡、社會習俗究竟以何種邏輯在“看不見”地運行,其實無非是在社會習俗的范圍內實現良好的族群交往抑或社會治理,無非是在加重責任的群體負擔之余,加強群體內部的自我監督和管理,以實現在信息不全條件下的激勵問題。因此,對詞源學上族群的描述有很多大眾化的外延界域。我們中國歷來有方域的界定,西方戲劇演出以及宮廷議院則有更多域眾的開放特征。中西方“域眾”的內涵在歷史源頭上確實有不同的起源,從而導致后來的發展具有不同的大眾形態。今天,隨著多民族國家的日益普遍,民族國家不再強調自身的“族裔”上的單一性,改變了僅從“民族”這一視角看待國家,從而有利于多民族國家的和諧發展。殊途同歸,我們要研究域眾內涵對全球化大眾觀的影響,我們就需要構建一個開放的體系,也需要基本蓄養的穩定,還需要整體民族特性的弘揚。只要我們確定了族群宿命的前提,不同的域眾研究路徑將會為我們突破全球化域眾的瓶頸問題指明方向。
因此,族群宿命是各個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無孔不入地滲透在人們的觀念、行為、習俗、信仰、思維方式、情感狀態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人們處理各種事務、關系和生活的指導原則和基本方針,亦即構成了這個民族的某種共同的心理狀態和性格特征。值得重視的是,它的思想理論已轉化為一種文化心理結構,不管你喜歡或不喜歡,這已經是一種歷史和現實的存在。”(李澤厚,1985:9)全球化以來,族群宿命具有的“相當強固的承續力量、持久功能和相對獨立的性質”,“已經全面演化出直接間接地、自覺不自覺地影響、支配甚至主宰著今天的”(黑格爾,2004:297)全球族群戰略。當今各個國家都重視族群戰略,但是,從族群文化內容到族群宿命演化,從族群道德、族群觀念到族群模式、族群交往等等,都沒有進行全球化的重構,也缺乏持久的、延續的、活的、深層的研究。
1.3 族群文化復興與新域眾關懷
“語境禮儀”不僅僅是動漫的一種去主人公的敘述形式,動漫被稱為文學還不限于此,“敘述禮儀”意味著歷史形態與現實形態的文化轉換中對文化回歸的族群價值繼承,這個繼承不是適度利用而是回歸古代語境的重新發現。“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不同族群文化復興的提出,直接顯示了新的民族域眾主義的傾向成為人類未來的最大“儀式”。語言文學這個概念和禮儀敘述規則緊密相連,維特根斯坦將語言活動比作語言游戲, 就是為了突出強調兩者在遵守規則這一點上的相似性(劉劃民,2004:34-36)。所謂規則,“并不是超越語言之外的絕對裁定性手段,而是語言游戲本身,因為具體的游戲規則必須在具體的語言游戲中才能被制定、被習慣、被遵守……規則被建立在理解的一致性和使用的一致性上。”(蔡曙山,2007)通常,人們把游戲看作是一種“無目的”的活動,因而也是“無功利的”“自由的”活動(皮柏,1991:10)。但實際上,游戲的“無目的性”只是人們從游戲的外部對游戲考察的結果;而從游戲自身的存在來看,游戲具有內在的目的性,語言使用往往受制于使用者在不同場合下的意圖、需要等因素(涂紀亮,2005:23)。因此,禮儀儀式敘述乃是朝向某一內在目的、在規則約束下的一種有序運動,并非是一個“自由王國”或“非理性的活動”(胡伊青加,1998:4),而是目的性統轄下的秩序世界。正是基于這種內在的目的性和秩序性,游戲者須認真對待游戲:沒有規則就沒有游戲。這“在涉及游戲規則的地方不可能有懷疑主義的余地……是一種不可動搖的真理……因一旦規則遭到破壞,整個游戲世界便會坍塌”(胡伊青加,1998:14)。因此,任何人要想成為人群禮儀的儀式參與者,必須服從和遵守儀式規則,即動漫敘述并不能隨心所欲、無拘無束地“自由地”游戲,而須首先自己遵循游戲的規則,無條件地聽從規則的命令。其實,域眾的原意乃是一種“被動式而含有主動性的意義”(伽達默爾,1999:133),即隨著儀式本身升格為人群的主體,從事人群禮儀的主體的人不再是主宰人群的因素,它在儀式中成了被動者,因為在儀式中主體必須遵守游戲規則,方能使儀式具有特殊的感染力,形成一種獨特的境域。正是最初的文學語境的 “立法”活動對儀式規則的在先性的“賦予”或“認定”,儀式本身的權威性才得以確立(董志強,2002:82-88)。
動漫人群敘述規則必須滿足哪些要求呢?阿佩爾、庫恩與哈貝馬斯等人認為,任何語言主體必須滿足領會的可能性、談論的真誠性、陳述的真理性以及行為的合法性等規則要求(張今杰,林艷,2011:127-132),這就為意義的確定奠定了基礎。我們今天還在描述歷經災難的人類族群文化所形成的民族文學以及藝術形態,成為族群宿命的承續范本。但是,回歸傳統的禮儀——《詩經》與《楚辭》,卻需要建立新的族群體系,因此,“文化保護-文化繼承-文化族群”的策略成為全球化各個國家的核心策略。英國保持歐共體之外的族群政策,歐盟恢復歐洲族群的一體化,俄羅斯族群的崛起意識,美國族群的開放與介入模式,中國族群的回歸全民族的振興和全球包容性,等等,都顯示了族群核心的智慧所在。盡管全球發展的氛圍已經大大緩解,回歸族群傳統文化似乎頗有氣候,然而,“這并不等于說深刻把握現代性問題”(李澤厚,1985:9),透徹認識族群傳統在新的處境下,對于重新發現中國文學思想與當代中國發展等等大問題,中國學術界亟須以一種全新的眼光予以深入全面地考察和思索。
2 族群儀式與域眾文學
2.1 傳播開放與歷史再造:所有“在場”和“不在場”的游戲主體或參與者各司其職
“在場”(presence)這一概念乃是由后結構主義哲學家德里達提出的,用以指代他所說的“絕對詞義”,即所謂超乎語言應用之外的一個絕對的語義基礎(艾布拉姆斯,1990:69)。由于現實的瞬間本身已經包含了“不在場”,即某個存在本身必然與過去和未來相聯系,故而不能將“在場”理解為不在場的反面或對立面,而應認識到“在場”與“不在場”均是一種存在的表現形式,“在場”意義具有“不在場”的性質,二者其實是相互轉化的。要實現陳述的忠實、準確、真實、一致,譯員應充分調動在場和不在場的游戲參與者,并讓其各司其職。
域眾文學,即在本文中所特指的動漫文學,在一開始就確立了自己的族群觀念,全新闡釋了人類族群法則的所在——儀式性“在場”,產生了全新的文學社會以及人文的族群效應;同樣,在嚴肅的社會文學領域,動漫還是缺乏深刻的主題認可以及社會學體系下的主題建構。動漫研究的理論體系還是處在一個新神話模式的狀態。如果要確立一個回歸族群的動漫文學的現實主義定義,或者浪漫主義的揭示,我們必須建立域眾研究這個基石。維特根斯坦在“遵守規則”和“認為自己在遵守規則”之間做了嚴格的區分,認為人們不可能“私人地”遵守規則,即反對私人語言的存在。由于語言是一種互動的語言、交際的語言,需要兩個以上或多個主體來同時完成,一個人的語言沒有意義,因為沒人能夠理解。由此說明了語言的意義不僅來自使用,更來自彼此之間信息的交換和理解。這里也強調了語言的主體間性及其實用功能。因此,在人群儀式語境下,各敘述主體需互相合作,同時既是禮儀者也是規則的監督者和維護者,在遵守規則的同時亦及時制止其他主體違反規則的行為,以維護禮儀的嚴肅性,最終確保陳述的忠實、準確、真實、一致,具有可理解性。總之,意義是在互動的語境中產生的,是一種主體間事物,不能再簡單地把主體和客體、客體之間或是主體之間簡單地分立開來。
“族群”概念早期具有人類學概念內涵,后來擴展為社會學概念。但是,現代以來,美國好萊塢藝術進行了美國文化族群的擴張,各類大眾域眾文化發展為社會論域,比如電影、街頭藝術、邊緣化、少數人等,逐漸改變了原來民族學的族群概念。今天,“族群”泛指社會上因為群體事件產生的相互認同的結合或者群體行為。“它可以用來指社會階級、都市和工業社會中的種族群體或少數民族群體,也可以用來區分土著居民中的不同文化和社會集團。”(劉泓,2003)但是,族群的內涵本質上不屬于國家或者民族的主流范疇,相反,構成族群的不同群體具有民間融合的再造機制,因此,中國文化中的社會風俗很好地表現了“五里不同風,十里不同俗”的族群形態,形成了具有宗族體系、氏族風俗、部族精神的傳統文化底蘊。長江、黃河流域孕育了各自的域眾文化以及文化關懷的模式,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表述的域眾風氣體現了現代族群儀式的具體語境,給族群以一種信心、一種理念、一種渴望。
族群是依據群體道德建立起來的,它是民族文化的核心,也是民族模式的基礎。域眾,作為承載族群宿命的文化人,沒有通過族群認同上升為主流文學或者精英文學,這是不能歸咎于消費文化或者大眾文化體系,根本上是目前人類族群宿命與社會歷史整體轉換中如何確立域眾主題的社會學、歷史學內涵,而這些內涵又不是以個人的歷史故事演繹的古代英雄神話或者好萊塢的當代神話來確立,而是現代大眾的全球化普世法則域眾改造,因此,“域眾”在動漫文學研究中是一個嚴肅的現代大眾群體命題。動漫從其產生之初就開始了與其他文化、亞文化的應和、包容和偏離,它不是一種自閉的存在,而是一種與外部環境、其他文化形式相互滲透發展同時又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的藝術形式。動漫美學文化就是在動漫作品的影響下,以動漫及其產品為載體,傳達出來的審美思想、社會認知和生活方式(郭海濤,郝萌,2010:70-71)。但由于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獨特地理環境、經濟生活、文化傳統和心理素質,故而產生了審美意識的民族性差異,而這種差異是不能隨意改變和加以忽視的。因此,中國動漫如果要取得自己的成績,必須回到自己的族群模式來建構,而不是重復或復制別人的商業模式。
2.2 群體認同與禮俗風氣
儀式語言層面的在場,從闡釋學的視角看來,由于語言乃是一個歷史性的存在,也是一個文化事件,源語中的文化歷史境遇本身屬于“不在場”范疇(劉宓慶,2006:59)。動漫文學通過解讀源語這種參與行為,調動自己的歷史和文化體驗來對源語進行加工和處理,從而通過自己及翻譯行為這種“在場”,將源語中的文化歷史境遇這種本身并不在場的因素,在目的語中體現為一種文化與歷史的“在場”,最終有助于新文本的生成與理解,畢竟話語本身及其包含的歷史文化因素是不能自動展示出來的。“域眾”的命題來自群體認同,這個認同由文化的儀式來獲得。顯然。群體認同的開放性需要一個族群文化的特定原則和標準,沒有族群的文化意向,認同就沒有一個共有的歸屬。
因此,族群意向認同的模型具有“典型形象”的屬性,它來自歷史背景以及文化傳統在域眾的現實演繹并加以確認和重建,這是馬克思主義典型理論在歷史高度對文學人物的精辟認識。歷史造就階級,證明了歷史在族群演化上逐漸形成以階級為背景的域眾,即是文學的典型。因此,在開人文之風氣上,文學起了很大的作用。“風氣”,是一個很中國化的說法,類似風氣、風俗、風尚,都是對“大眾文化”的命題,從人類學理論解釋看,就是一個“族群”概念,無論在中文詞典還是希臘史詩、希臘戲劇里,我們都可以看到大眾的基本族群屬性,族群智慧、族群財富、族群權利基本上顯示了不同族群的生存形態下不同族群獲得文化模式的不同域眾特征,歸根到底,都只是族群演化的開放性如何獲得保護和維持。
也就是說,域眾開放包括了豐富的社會內涵。我們在解讀《詩經》愛情主題的詩歌時,幾家注釋的分歧都在對愛情的評價上,都沒有回歸文學性(史忠義,2010:1)的域眾內涵。這樣我們在《葛覃》一詩中,對采摘葛葉的族中婦女在“那個葛樹窩”采摘,在溪潭里浸泡的因勞動而起興就缺乏一個勞動族群的共鳴,對族群之鳥——“黃鳥”*“黃鳥于飛”,在《詩經》中多次出現,都與宗族、部落英雄相關。成群呼應的“于飛”,想到自己部族和族人一起勞動的情景,然后托付黃鳥告訴族人的“師氏”頭人,自己想回來歸寧。她激動的心情忐忑不安,想到家人按照族規迎接女兒,想到留在族群眾自己的臥房以及穿著的衣物,想到家中灑掃庭除,想到家中為她的歸寧洗洗曬曬。這些女性文學的域眾主題,體現了當時對女子族群的文化關愛。《關雎》《靜女》《君子偕老》都是不同風俗域眾下對女性的內涵的升華;如此,動漫文學也會對傳統觀念顛覆或升華。以一部集北歐神話之大成的作品《魔偵探洛基》為例,在北歐神話中,洛基是冰霜巨人的后代,邪惡刁鉆,喜歡為非作歹,但又法力強大,一貫以負面形象出現。但在動漫《魔偵探洛基》當中,洛基被主神奧丁貶到人間,卻以偵探的身份做起了正義的主角,而在北歐神話中一向以光輝形象出現的雷神、陽光之神、愛與美之女神、虹橋的守護神等眾神,在該動漫中卻紛紛下界以各樣的方式追殺洛基,這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傳統神話中各自的形象而豐富了其社會內涵。故詩中或域眾文學中的詩歌詞語或人物形象的解析,都會因不同的主題進行各自的體會或解讀。
因此,在族群相互蓄養關系中,我們會發現族群的相互關愛形成的域眾文化體系。儒家形成了禮儀儀式,道家形成的自然道德,佛教的普度眾生,都完全是依據了這個域眾體系描述的,理論體系是后人為了繼承這個族群意向而予以整理形成的,因此,復原族群是重新解讀古文的前提,而古文語境的回歸同時也使得后人建立實事求是的社會實踐觀。
在動漫族群的域眾描述上,我們會看到不同種類的關懷主題,都會揭示族群意向的原初本性的回歸。例如,美國迪士尼公司善于從周圍的文化中尋找創意的源泉,而后用自己的獨特風格對各地的文化進行包裝,進而將這些混合作品變成了富含迪士尼自己文化的動漫作品,包括《獅子王》、以中國民間故事而打造的《花木蘭》等。在美國的動漫中,總有一個勇敢、堅強、拯救人類的英雄形象,讓人產生一種崇高感、一種征服的喜悅感;此外,源于北歐神話的日本動漫《魔偵探洛基》和《銀河英雄傳》及其本土動漫《神偵探柯南》,還有源于我國神話的中國動漫《華山救母》《葫蘆娃》《哪吒傳奇》等,無一不體現出對正義的追求和對英雄的崇拜,從而凸顯出強烈的群體認同感。
目前,各地都在挖掘本地文化,發現了域眾傳承的很多現象,但文化挖掘還非常淺陋,距離中華文化的復興還有待進一步確立中華域眾文化的整體發現,因此,動漫給了我們群體認同的文學樣式,各個區域如何形成自己的風格就是中國動漫的著力點。
2.3 族群融合與人群制度
語言的使用是運用符號的儀式,語言儀式可以通過規則來建構社會現實。人們所面對的世界是通過語言展示建構出來的,人類的全部精神財富都是通過語言并以語言的形式保存下來,語言因此從簡單的工具地位被提升到了本體地位,而一旦語言具有本體作用,語言就理應成為一個研究重點,就需要考察語言實踐中的大量的具體案例,研究語言在具體語境下的具體使用(涂紀亮,2005:3)。
在中國古籍里我們可以看到重視族群與域眾的歷史沿革,在中國古籍中,“族”“民”“人”“種”“部”“類”是一種公共論域的用語,一般在正式的公文中用于區分政治差異,而在政治管理體系里卻是突出域眾。《尚書·周書·牧誓》記載“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的域眾形態,可以看到方域觀念的“民”是“族”的蓄養關系的基礎,“多族一域”或者“一族多域”造成聯姻以及融合,民歌有了跨界的空間,部族有了越界的文化交融,那是族群比較早的形態。“族群”比較符合中華民族農業文明的基本形態,因為族群文化中,作為權利的領域范圍是依據管理對象而論,權利的領眾就依據一方水土一方人,藏風于民,聯姻于族,血親族緣,立宗傳家,構成了文化的歷史形態以及經學體系。這一點,西方城堡孤立分割的自我系統建立的市民族群,其族群宿命就具有悲劇色彩。一個不斷被封閉的族群勢必須要建立民眾的論域,在此基礎上,建立個人與族群的賦權就是城堡的核心文化。
自古以來,人類維護公共生活秩序的手段多種多樣,其中道德和法律是基本的手段。《周易》中與男女宗族乃至家族有關的卦就有《咸卦》《恒卦》《姤卦》《家人卦》,整個《易經》基本都是圍繞家、國體系構建,因此,有關的爻辭充斥全篇。《周易·家人卦》“初九”描述了家人的作用:“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這個意思就是說,一個君子擁有宗族,可以開宗立祖,那么一個男人就會沒有遺憾,因為,承擔責任才會使人成熟。“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這里描述了宗族之家的各自使命使得宗族之家目標得以成為群體共識。“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也許這里才是對《君子偕老》中貴夫人的“失家節”的解釋。這里寫出了各人個性的尺度,宗族為氏族耕作才會有家,只有勞動,才是古代文明的基本內涵。
這一點作為文學“域眾”的民歌,在許多研究文學的理論中,“勞者歌其事,饑者歌其食”,文學在社會壓力需要節度每個人的行為上采取的是域眾的基本道德。其次,集體勞動與群居時代存在相互的宗族競爭以及外族擴張,因此,宗族穩定十分重要。宗族穩定的基礎就是“六四”所揭示的“富家,大吉”。動漫的族群宿命是否有現實主義的依據呢,《周易》與《詩經》的研究告訴我們,氏族的“富家”是一種原始公共體系的族群概念,在這個組群里面,人人均有,老人不需要“負”,也不要“戴”就可以專門奉養;外嫁的女子依舊保留她的居室,可以歸寧居住,離異也可以歸家;歸寧父母還要言告部族的師氏,大家小家都居公共體系之中。后人從歷史宿命的角度,對歷史進行了唯物主義或者唯心主義的解釋,但是,這種解釋忽略了人類學的基本法則以及社會學的平面視角。正如“九五”提示我們的那樣,宗族的問題是人類的根本問題,歷史確實是演繹了家族戰勝宗族的一幕,但是,“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依舊是今天人類學的基本結論。從社會學角度而言,“上九”也談到了宗族的公共養蓄體系,“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公共生活領域越擴大,公共秩序就越復雜,道德和法律的作用就越突出。假如沒有這樣的自然形態的社會群體制度,怎么會產生女性文學的《關雎》《靜女》《君子偕老》這樣的婚姻審美觀念呢?《詩經》以現實主義的態度表現了人類文學的基本主題,這一點在儒釋道的思想體系中都有高度的認同。
3 域眾傳承與人群宿命
3.1 人群宿命與域眾意向
隨著近代哲學到現代哲學再到后現代的過渡,禮儀儀式語境的轉變充滿活力,使得那些隱藏于客觀世界背后的他者具有了主體資格而與傳統的主體進行互動(張世英,2002:220)。動漫文學運用儀式語境乃是一種特殊的人群交際行為,動漫域眾各方并不直接發生信息的傳遞,而是通過儀式這個信道才進行交流。傳統文化規則在這個儀式中起著詮釋者或傳達者的作用。畢竟規則可建構人群、決定意義、賦予行為體身份及物質和行動以特殊的意義;儀式語境調動其在場的禮儀參與者,包括字、詞、句、語篇等言語信息,包括域眾知識、人群文化,讓所有的參與者恪守自己應否在場的儀式規則,使“在場”與“不在場”的參與者始終處于動態變化中,以創造性地建構新的文學閱讀語境、擴大文學共享、實現交際效果的最大化,最終實現域眾的目的。
動漫文學傳承了族群宿命的開放性主題。域眾作為文學的敘述主體,直接構建了族群文化的基本模式作為自己的故事載體。其實,日、美動漫在選題方向有重合之處,即故事選題具有全球意義,也符合類型影視理論的商業原則,從而明確商業產品的目的性,滿足消費需求,實現利益最大化的表現,市場化運作帶來了大眾化市場評判標準,創作者逐漸摸索出不同年齡職業區間觀眾的共有欣賞趣味,不需要行政性導向刻意安排,而是市場發展、商業化運作的必然結果,創作者會自動摒棄或避開嘗試過分個人化的創作手段和形式;而文本上的模式化特征體現在動畫作品的內容上,就是元素不斷復制出現,同一具體題材中故事情節、敘事結構、人物形象語言的相似性,從而使得其文本內容上的模式化創作套路逐漸清晰直至成型。作為開放性的中國類型動畫的創作也應該向這些方向轉移,從這些經過全球市場和觀眾篩選的題材創作類型中構建本國動畫的類型庫,這才是中國動畫創作真正的商業化轉型。如果沒有開放的域眾意向,族群內涵就會失去意向活力。因此,動漫文學顯示其社會價值在于文學確定了一條還原真實的路徑,建立了文學類似百科全書的大眾社會語境,使得域眾獲得政治、社會的精英認同以及主流身份。域眾往往是承擔族群宿命的小人物群體,族群的回歸是小人物群體成了群體認同所關注的域眾,因此,域眾關注作為文學形態產生了古代的神話人物、民間英雄、行吟詩人以及域眾文學相應的文體。我們姑且不去爭論孔子創立的儒學是否與他主持祭祀有關,但是,胡適先生關于儒家域眾理論的視野是《詩經》文學形式的最好解讀。
因此,動漫文學正在積極發展自己的域眾語境,形成各個民族體系下的族群范式。考量中國的宗族信仰、長城的國家信仰與埃及金字塔族權信仰,乃至佛教的塔信仰,都是解決大眾意向開放問題的很好的傳統。大乘佛教最為精深的“普度眾生而眾生實無可度”,就是解決個人意向的修行與菩薩修行之間的“論域間性”。這個問題儒家和道家都沒有解決。儒家“禮教”和“仁學”試圖建立一個中庸的大眾體系,道家強調小國寡民的大眾化路徑,他們都試圖建立宗族信仰和自然信仰體系下的問題歸因,有了一個公共話語的語境歸因,社會論域就會自動協調各自的話題規范,形成語境族群的文化存在范式。域眾文化的形成,集中體現了族群的智慧,但是,族群的開放性,使得族群文化要大于域眾的論域范圍,因此,域眾形態往往會發展為一種高雅文化、精英文化,或者演化為消費文化,而文學演示的域眾主題以及域眾人物,體現了文學特有的人文經驗以及特有的文學意向——這就是我們說的族群宿命,所以,族群宿命的回歸才是域眾主題確立的原則。
3.2 族群儀式與域眾形態
語言學的轉向使得文學研究的批評話語轉向域眾意向發現。文學還原原初的語境意義確定了人類科學全新的發展路徑,此路徑一次次產生了中國文化的回歸民眾的原初形態,這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一次次的回歸古文的運動。我們發現,秦漢以后對儒家進行脫離民眾的家族政治移寫,最大的失真導致對古代眾域主體的全面擠壓,這與先秦文化向民間移寫的眾域模式截然相反。一般意義上講,不同民族之間的戰爭將會強化異族文化排斥,在秦國之后的異族入侵出于對漢族意識的壓制,也會同時禁止域眾主題出現在民間文藝中,因此,戰爭導致秦把中國文化的域眾主題所直接承載的開放性轉化為封閉的為家族綱常儀式,家域主題的封閉導致故步自封的專職,先秦文化開始全面解體,族群文化中民間民俗缺失,這就是非物質文化或者物質文化成為遺產的根本原因。
文學的尋根性自古就有。魯迅是現代唯一一位具有族群眼光的文學大師、文化大師,他的雜文作為中華民族文學傳承,顯示了現代中華民族的域眾鋒芒。族群的吶喊、域眾的彷徨構建起來了且介亭的批判心境,以及南腔北調的域眾面目。文學的“國民性”顯示了魯迅身上的族群自信。魯迅熱愛生活,關心大眾,在魯迅的筆下許多小生命、小動物、小人物充滿了欣喜、慈藹、悲壯。對域眾的發現,魯迅曾贊美道:“我以為紹興有兩種特色的鬼,一種是表現對于死的無可奈何,而且隨隨便便的‘無常’”;另一種則是“帶復仇性的,比別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強的鬼魂。這就是‘女吊’。”(魯迅,2005:637)魯迅之所以稱得上是中華現代文化的大師,就在于他建立的文學與民眾的眾域體系都是無法被人們忽略的社會核心論域。因此,動漫文學不應當限于兒童文學、新神話文學的界定,應當屬于新人類族群的文學傳播,這也解決了詩人、作家、作者與讀者、受眾、傳播的體例、身份、承續的語境問題。
而動漫的族群也不外乎就是域眾回歸的尋根。例如,“廣西少數民族民間故事動畫系列片”項目負責人就曾指出,隨著社會發展,民間故事在當今少年兒童中的傳播力和影響力嚴重下降,面臨傳播鏈斷裂和消失的危險。為繼承和弘揚民族文化,動畫片是一獨特的表現形式。無論是由廣西電視臺制作的“廣西少數民族民間故事動畫系列片”(取材于壯、瑤、苗、侗等12個民族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創造的《劉三姐》《媽勒訪天邊》《布洛陀》等家喻戶曉的少數民族民間故事),還是廣西千年傳說動漫影視有限公司制作的26集動畫連續劇《阿米蘿之歌海奇緣》和《阿米蘿之空中大陸》,抑或是取材于“體操王子”李寧而根植于壯族經典傳說《媽勒訪天邊》、采用由木偶、真人和3D多媒體影像共同完成的動漫《跟斗小子》,均反映出廣西原創動漫以實際行動尋根本土民族文化。
目前,擺在中華族群文化面前的是建立中華文學的族群語境。中華文化的族群意象與域眾主題需要建立一種開放的研究、教育、創作格局,這樣才能發揮社會主義文學的“下基層”“回民間”“到村寨”的主流優勢。文化的定義雖然無法窮盡,但是,基本上的法則首先是生存方式的開放性以及普世法則的自在性,我們要進一步發現民間的部族文明、氏族關愛、宗族教育。儒家把這個自在用《詩》來建立,道家用莊子的逍遙游以及莊周化蝶來超然物外,佛教用眾生來闡述佛性,所有這些使得我們感受到了文化之邦中國的域眾文明的價值。解決人類根本問題還是文化的堅韌、民眾的族群、認同理解等文化品格的承載,只有在族群的體系中,域眾才會如同乾卦那樣自強不息,好比坤卦那樣厚德載物。域眾在動漫藝術表現為那些眾生的族類,其內涵恰恰是我們文化精神的“化蝶”,我們民眾精神的“化身”,我們自然法則的“化現”。
3.3 文化身份主題與族群儀式回歸
中國文學具有百科全書的屬性,屬地風俗、宗族交往、琴棋書畫、武學醫術、建筑風水、油鹽居家、茶酒俗尚,可以說天文、地理、人文都是族群主題的核心構建;正是這種族群關愛,在同處一方的互相認同,對血親家族的互相包容,對衣食父母的互相體諒,對語言文化的敬重崇拜,對立宗開祖的生機擴張,才有了“民族”的內涵揭示。1971年聯合國“人與生物圈計劃”也在探索回歸傳統建立域眾主題。由于對文化的族群認同,產生了街頭文化、好萊塢文化、讀圖文化、商業文化等等。后現代的域眾主題從文化荒原走向底層文化,文學場域轉化為具體的大眾傳媒體系。大眾域眾主題開始進行去政治化、種族化的族群回歸。
中西方動漫文學發展淵源、歷史脈絡、文化語境各不相同,或者說中西方動漫文學的差異必然會導致它們各自的儀式敘述和主題訴求的差異。那么如何來協調這種張力?或者面對這種差異時如何確立相同或相似的族群宿命呢?正如安德森在其《想象的共同體:民族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所指出的,動漫文學在新的技術傳播下,可以挪用傳統符號構建新的“想象的共同體”,因傳播技術的革新會促進或加強族群觀念和身份認同,而挪用新傳統符號,輔之以域眾尋根,必然會有助于復興傳統文化。須注意的是,具有悠久歷史的東西方文化并不是都像美國那樣可以任意開放域眾意向,也不是前蘇聯試圖以族群替代掉民族問題導致民族解體,而是文化的融合與認同。全世界都面臨著民族族群的回歸以及文化復興,從而引發了全球化的民族族群的現代性改造。我們遠不必對族群進行市民、族民、氏民、宗民乃至國民的界定,我們可能需要的是“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的域眾功德,“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的宗族分工,“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的部族認同,“旅力方剛,經營四方”的域眾自由,因此,只有文學才可能承載這個體系。現代域眾的覺醒締造了新的后現代文化模式,文化族群復興促進了域眾文學動漫全球化、大眾化的進程。因此,動漫文學中洋溢的現代群體精神是人類大眾的全新面貌(亨廷頓,1996:46,58;詹明信,1997:430;湯林森,1999:16)。馬克思預言了人類族群下域眾的“自由個性”的辯證歷史過程(馬克思,1979:104)的前提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1972:273)。因此,文學要發展為現代民眾的一種符合我們的自由方式中獲得感悟,體現了價值保護與精神弘揚,民眾生存與全球關愛,語境交流與民風維護的價值,還有很多的問題需要解決。起碼,動漫文學在這個方面有了自己的獨到視角,并且已經在影院模式、電視劇模式、紀實模式上都有了相當的規模,因此,給予理論升華也是我們希望看到的。
艾布拉姆斯.1990.歐美文學術語詞典[M].朱金鵬,朱荔,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鮑剛.2005.口譯理論概述[M].北京: 中國對外翻譯公司.
蔡曙山.2007.語言、邏輯與認知[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董志強.2002.析伽達默爾的游戲觀——兼論游戲的本質[J].學術月刊(12):82-88.
郭海濤,郝萌.2010.動漫美學文化的影響力[J].電影文學(23):70-71.
黑格爾.2004.哲學史講演錄:第1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
亨廷頓.1996.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華出版社.
胡伊青加.1998.人:游戲者——對文化中游戲因素的研究[M].成窮,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伽達默爾.1999.真理與方法[M].洪漢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劉泓.2003.解讀族群(一) [N].學習時報,2003-12-22.
劉劃民.2004.維特根斯坦語言游戲說探析[J].廣西社會科學(7):34-36.
劉宓慶.2006.口筆譯理論研究[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李澤厚.1985.中國古代思想史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
魯迅.2005.且介亭雜文末編·女吊[M]∥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馬克思.197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馬克思.197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皮柏.1991.節慶、休閑與文化[M].黃藿,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史忠義.2010.關于“文學性”定義的思考.《問題與觀點——20世紀文學理論綜論》序[M]. 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湯林森.1999.文化帝國主義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涂紀亮.2005.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思想研究[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楊大春.2002.主體形而上學解體的三個維度——從20 世紀法國哲學看[J].文史哲(6):79-86.
張今杰,林艷.2011.“范式”與 “語言游戲規則”——庫恩科學革命理論與卡爾-奧托·阿佩爾先驗語用學比較研究[J].北方論叢 (4):127-132.
詹明信.1997.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張世英.2002.哲學導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責任編校:路小明
商務英語研究專欄 主持人語:
今年是商務英語專業成立十周年,即將召開第十二屆全國商務英語學術研討會,也是教育部新的《高等學校商務英語專業本科教學質量國家標準》頒布之年,總結和回顧商務英語專業和學科的十年成就,完善商務英語學科體系,加強商務英語專業建設,提高商務英語人才培養質量,推動商務英語學術研究,思考和展望商務英語的未來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當前,制約商務英語學科發展的兩個關鍵因素是學科理論研究和師資隊伍建設。本期我們圍繞商務英語學科理論建設和商務英語師資發展兩個重要主題,推出五篇論文。王立非、翁鳳翔、段玲琍三位教授探討商務英語學科與理論建設,嘗試構建商務話語語言學的理論體系,探討商務英語語用學的核心問題,涉及言語行為研究、禮貌和面子理論研究和語用能力研究等方面,從宏觀視角論證商務英語學科命名、學科屬性、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等。
葉興國和郭桂杭教授分別從教學能力和自主能力探討商務英語的教師發展,以第六屆全國英語專業教學大賽商務英語組總決賽為題,探討商務英語教學創新、教師教學自主和教學質量標準之間、知識模塊和能力模塊之間以及各教學環節之間的辯證關系,指出高校商務英語教學自主能力應當引起關注,并就如何改進提出建議和對策。本期的論文相信對商務英語教學改革會提供有益的啟示。
王立非
Ethnic Community Activation and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Narrative Analysis of Ceremonial Context of Animation
MAXiaochun
Ethnic community, ceremony and community activity are the basic elements of animation literature. As required by these elements, the connotation meaning of ethnic community in animation shall be studied to reflect life and the context meaning of public images. The intent of the ethnic community in animation is to achieve the historical and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which is also the found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tactics of the modern cultural renaissance strategies.
cultural renaissance; return of ethnic community; literature on ethnic community
2015-11-20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大清律例》英譯比較研究”(13BYY030)的階段性成果
馬笑春,女,重慶電子工程職業學院講師,碩士,主要從事英美文學和翻譯學研究。
I109.9
A
1674-6414(2016)04-003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