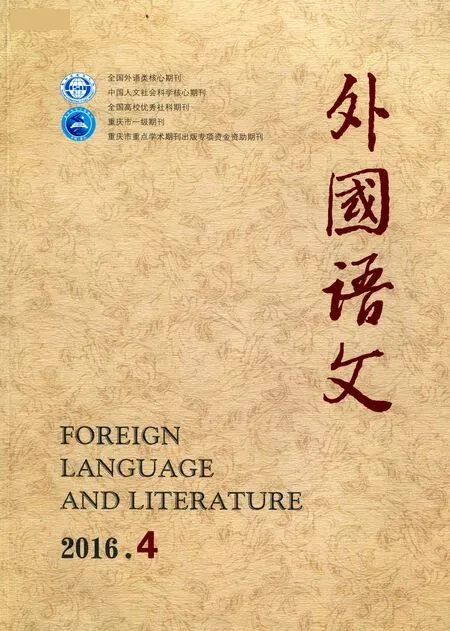“忠實性叛逆”:沙博理之文學翻譯觀
黃 勤 劉紅華
(華中科技大學 外國語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
?
“忠實性叛逆”:沙博理之文學翻譯觀
黃 勤 劉紅華
(華中科技大學 外國語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
作為一位向西方國家介紹了大量中國文學作品的華籍美裔譯者,沙博理對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做出了卓越貢獻。沙博理在文學翻譯實踐中,既踐行忠實原則,又對“翻譯者即叛逆者”這一意大利戲言感同身受,本文因此將沙博理的文學翻譯觀界定為“忠實性叛逆”,認為叛逆是為了達到更大程度的忠實。即兩個“忠實”與兩個“叛逆”:忠于原文思想和譯文讀者,逆于原文的部分內容和形式。通過對《新兒女英雄傳》英譯本具體翻譯策略和方法的仔細分析,對這一“忠實性叛逆”文學翻譯觀進行解讀,以期有助于探尋中國文學作品英譯之可行方法。
沙博理;《新兒女英雄傳》;英譯;“忠實性叛逆”翻譯觀
0 引言
“翻譯者即叛逆者”之說法由來已久,可追溯至尼可羅·馬基亞維利時期意大利的一句諺語“Trattutore é tratitore”——“翻譯者即叛逆者”*“Trattutore é Tratitore” 在國內有兩種譯法,一種是錢鍾書(1984:697)先生的譯法 “翻譯者即反逆者”,此譯法體現了原句詞首書寫形態相同的詩學特征, “反逆”雖也有反叛的意思,卻是一個生僻詞,大多數漢語字典里都未曾收錄;第二種譯法是 “翻譯者即叛逆者”,雖在形式的保留上有失偏頗,卻準確傳達了原意,而且譯界大多使用此譯法,因此本文選取第二種譯法,即“翻譯者即叛逆者”。。國內譯界關注“叛逆”的研究者眾多,但大多聚焦于“創造性叛逆”*孫致禮(2001:18)將“叛逆”劃分為:無意性叛逆、權宜性叛逆、策略性叛逆、關照性叛逆和創造性叛逆,創造性叛逆只是其中一種。,且褒貶不一,有極力贊成者(謝天振,2012;許鈞,1997;孫致禮,2001等),也有全力反對者(江楓,2006)。依筆者之見,兩種觀點各有道理,只是對“創造性叛逆”內涵的解讀不同而已。贊成派看到了其積極的一面,認為叛逆是在追求忠實的前提下不得已而為之,叛逆是為了更好地忠實,是翻譯活動本質上的局限(許鈞,1997:41-42);反對派則認為“叛逆”是相對于“忠實”的胡譯、亂譯,是王向遠(2014:141)所提到的“破壞性叛逆”的層面,即“叛逆”的消極面或負面。筆者更傾向贊同積極與正面的理解。錢鍾書先生(1984:697)曾論述,由于兩國文字之間的距離、原文作者與譯者的距離、譯者理解與其表達的距離,譯文難免會失真和走樣,即“訛”,也就是本文討論的“叛逆”。由此看來,“翻譯要做到絕對忠實是不可能的,因而叛逆是不可避免的”(孫致禮,2001:18)。語言與文化的差異構成了譯者忠實的局限,叛逆與忠實只是現實與理想的差距而已,忠實是譯者理想的追求,而叛逆則是在具體翻譯實踐中的無奈之舉。 概言之,翻譯實踐中的大多數叛逆都是由于翻譯活動的特殊性導致譯者為了追求更大程度的忠實而不得已所做出的各種程度的背離,“表現在形式上就是翻譯中的刪減、添加和意譯”(廖鴻鈞, 1987:103)。本文所探討的叛逆絕非顛覆翻譯本質的胡譯亂譯,而是在忠實的基礎上對形式和內容進行不同程度的調整,因此本文以“忠實性叛逆”命名此翻譯觀。
鑒于“忠實”這一概念內涵豐富,譯界對其仍爭論不休,此處有必要界定其在本文中的含義。中外傳統譯論一直將忠實奉為圭臬,即便是在大興解構之風的當前譯界,忠實也得以在被無數次解構之后幸存。譯界對忠實與否的爭論焦點不在于是否需要忠實,而在于“如何定義忠實”(Berman,1992: 17),即“應該忠于什么”。魯迅的“寧信而不順” 與韋努蒂(Lawrence Venuti)的“異化翻譯”(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傾向于對原文表達方式的忠實;而奈達的“動態對等”(dynamic equivalence)則傾向于對譯文在目的語中的交際效果的忠實。玄奘的“既須求真,又須喻俗”、嚴復的“信、達、雅”和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的翻譯三原則*(1)譯文應完全復寫出原作的思想(the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2)譯文的風格和筆調應與原文的性質相同(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3)譯文應與原作同樣流暢(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original composition)(Tytler, 1978:16)。,更是注重對原文思想、風格、目的語語言規范等多方面的忠實。本文所探討的忠實是指對原作思想(意義)、目的語語言規范和目的語交際效果的忠實。
1 “忠實性叛逆”:沙博理之文學翻譯觀
作為將新中國社會發展和中國文學介紹給世界的國際傳播使者,華籍美裔翻譯家沙博理(Sidney Shapiro)先生半個世紀筆耕不輟,沙博理共完成著作176部,其中專著4部、編譯3部、譯著169部,譯著題材豐富,包括小說、散文、詩歌、戲劇等,其中15部長篇小說(包括長篇回憶錄)、125部中短篇小說(包括短篇小說集、短篇回憶錄和游記)、14首詩歌、7篇散文(包括評論)、4篇報道、1部戲劇、1部連環畫、1個動畫片場景、1個相聲。這些譯作中出版了單行本的有15部,在《中國文學》(英文版)雜志上發表的譯文共計155篇,涉及原作141部,涉及作者104位(包括4位匿名作者),包括茅盾、趙樹理、劉白羽、孫犁、杜鵬程、徐懷中、瑪拉沁夫、柳青、端木蕻良、袁水拍、敖德斯爾等。其《新兒女英雄傳》的英譯本DaughtersandSons是在美國出版的第一部中國紅色小說、其《水滸傳》英譯本OutlawsoftheMarsh被《大中華文庫》收錄、其茅盾英譯作品集SpringSilkwormsandOtherStories被《熊貓叢書》收錄、其編譯作品JewsinOldChina:StudiesbyChineseScholars等被譯成多國語言,受全世界關注。因此先后獲得了“中美文化交流獎”(1994)、“彩虹翻譯獎”(1995)、“國際傳播終身榮譽獎”(2009)、“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2010)、“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獎”(2011)等榮譽,足以見其對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性。
在其50余年的漢譯英實踐中,沙博理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翻譯觀,其對文學翻譯的見解主要體現在其所撰的《中國文學的英文翻譯》(沙博理,1991:3-4)一文中,還有些散見于其自傳《我的中國》(沙博理,1998)、譯序《水滸新英譯本前言及翻譯前后》(沙博理,1985: 404-414)、訪談(洪捷,2012:62-64)和書信(張經浩、陳可培,2005:321)中。 沙博理在其中多次借用意大利戲言“Traduttore é traditore”(“翻譯者即叛逆者”)表達自己在文學翻譯中對原作進行結構的調整、內容的增刪等叛逆行為。但這種叛逆都是在忠實的基礎上不得已而為之。沙博理認為,翻譯既要考慮對原作的忠實,盡可能傳達原作的精神,又要考慮譯文讀者的接受,符合目的語讀者的接受習慣。沙博理將翻譯比喻成“走鋼絲”,倒向作者不行,倒向讀者也不行,因此只能對雙方進行適度的叛逆來做到最大程度地忠實于原文作者兼譯文讀者(洪捷,2012:63)。依沙博理之見,叛逆是為了獲得更大程度的忠實。這種見解極大地肯定了翻譯中叛逆行為的合理性與價值。在談到文學作品內容和風格的翻譯時,沙博理表示:“意大利人戲言,‘Traduttore é traditore’——‘譯者即逆者’。要做到忠實,不致背離正在翻譯的作品,我們就得用英文創作一個短篇或一部長篇,讀來同樣好懂,具有與中文原作相同或相當的文學特點。”(沙博理,1991:3)可見,沙博理始終將忠實作為文學翻譯的規范和標準,要在目的語中忠實傳達原作的思想,譯文是否“好懂”是關鍵。因此,譯者就要盡量遵守目的語的語言文學規范,“用我們的英語把我們的中文意思傳達出來”(沙博理,1991:4),但是由于中英兩種語言、文化間的差異,就不得已在某種程度上背離中文的語言文學規范。
綜上所述,沙博理的“忠實性叛逆”文學翻譯觀是指譯者在忠實于原文思想的基礎上,為了最大限度地忠實于為讀者服務的翻譯目的而不得已對原文的部分內容和形式進行叛逆的翻譯觀,即兩個“忠實”和兩個“叛逆”:忠于原文思想和譯文讀者,逆于原文的部分內容和形式。當然,后者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而為之。忠于原文的思想就不得不背叛原文的形式,因為“要忠實翻譯原文的意義,譯文的表達方式往往會偏離原文”(泰特勒,2000:15);忠于譯文讀者的接受效果就不得已要背叛原文的表達方式而采取目的語的表達習慣,因為后者更易于讓讀者接受。鑒于此,沙博理主張采用以歸化為主,異化為輔的翻譯策略,認為要“用我們的英語把我們的中文意思傳達出來”(沙博理,1991:4),具體方法如下:一方面,可以進行適當刪減與壓縮,即刪減重復累贅或與作品主題脫離的內容和一些泄露文章內容的快板、民謠;另一方面,可以增加一些有助于讀者理解的文內釋義、注釋等,還可插進句子把話說明;再者,可以改變詞序與句序(沙博理,1991:4)。概之,在沙博理看來,為了忠實于原作的思想,實現易于讀者接受的目標,譯者可以對原作進行內容的適度增刪和結構的適當調整。
2 “忠實性叛逆”文學翻譯觀在《新兒女英雄傳》英譯中之體現
《新兒女英雄傳》是沙博理英譯中國文學作品的第一次嘗試。初到北平,沙博理閑來無事,正好一位朋友送了他一本新出版的小說《新兒女英雄傳》,“這本書對我很有吸引力,我開始翻譯它,希望能打入美國市場” (沙博理,1998:88)。可見,沙博理選擇翻譯此小說主要是源于個人愛好。雖然其任職于外文社期間仍在繼續翻譯《新兒女英雄傳》,但沙博理當時只負責審譯英文新聞,并未被分配翻譯小說的任務,因此《新兒女英雄傳》的英譯應該看作是沙博理的個人行為。小說譯成之后,沙博理自己做主將其譯作刊登在《中國文學》雜志上,并自己聯系了紐約的自由圖書俱樂部將其在美國出版(洪捷,2012:63-64 )。因此,《新兒女英雄傳》的譯本選材、翻譯過程、出版發行等方面受當時新中國的主導詩學、贊助人、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較少,最能反映其作為譯者的本真翻譯觀。以下我們將具體分析《新兒女英雄傳》的英譯本,以此來解讀其中所體現出的沙博理的“忠實性叛逆”文學翻譯觀。
袁靜、孔厥(2002)*沙博理翻譯《新兒女英雄傳》是在1949年,可推斷他是參照此小說的第一個版本,即海燕出版社1949年版。但此版是繁體字。經對比,筆者發現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版雖插圖與1949版不同,文字內容無異,因此筆者在此選擇了2002年版作為研究對象。合著的長篇小說《新兒女英雄傳》講述了抗戰時期,冀中白洋淀地區以牛大水為代表的廣大勞動人民在共產黨員黑老蔡等的領導下,進行抗日自衛斗爭的英雄故事。小說在內容方面,章與章之間的情節有些缺乏連貫;在形式方面, 保留了章回體小說的回目,但舍棄了刻板的對子,代之以民歌、民謠、民諺、新詩、俗語等,大都暗示了本章的主要內容;風格方面,樸素自然,通俗易懂。
通讀譯文,我們發現沙博理在《新兒女英雄傳》的英譯中是使用“自上而下”(top to bottom)*Newmark(1991:126-128)提出了兩種翻譯方法(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and to translating):由下至上(bottom to top)及由上至下(top to bottom)。的翻譯方法,以語篇為翻譯單位,再到段落、句子、詞。在不同層面的翻譯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忠實性叛逆。因篇幅所限,本文僅分析譯文在語篇層面的叛逆,以探索沙博理的“忠實性叛逆”文學翻譯觀,其他層面筆者將另著文分析。
“語篇指任何不完全受句子語法約束的在一定語境下表示完整語義的自然語言。”(胡壯麟,1994:1)大到一部小說,小到一個詞組甚至是一個詞都可以是語篇。本文所探討的語篇包括這篇小說及其章節與段落。對比原文本和譯文本,筆者發現沙博理對語篇的叛逆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刪除全部20回的所有回目;(2)省譯累贅的段落;(3)重組每一章*本文用“章”表示章回體小說中的“回”。的結構和內容;(4)在段內增添合適的句子。下面舉例說明。
2.1 回目的刪除
回目是章回體小說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本章內容的概括,因此刪除回目雖未損失原作內容,卻背叛了章回體小說的表現形式。這部小說中每一章開頭都以民歌、民謠、新詩、俗語等概括該章的主要內容,旨在引起讀者興趣。但沙博理認為:“很多故事本身就很好了,但還沒有到重要的情節之前就有快板、民謠等先泄露了文章內容,這些快板等我就可能刪減不譯。”(洪捷,2012:63)從中我們不難體會到,為了忠實于目的語讀者崇尚簡潔暢達的閱讀習慣,沙老在翻譯中不得已叛逆了原著章回體小說的表現形式。
2.2 累贅段落的省譯
與小說原文本對比,我們不難發現,英譯本中,每一章節中都省譯了幾個句子,甚至幾個段落。對此,沙博理(1991:3)解釋:“如果原文重復太多,啰里啰唆,我以為可以允許壓縮。這些做法對形式會稍有改動,不致改動根本的內容,有助于外國讀者更加清楚地理解原意。” 沙博理認為應該通過壓縮內容的方法使讀者更加清楚地理解原意,即內容的刪減非但不會損害原文的意義,還能將其在目的語中更好地傳達出來。我們以沙博理對原小說段落的省譯這一對原文部分內容與形式的叛逆策略為例來驗證其英譯中體現的兩個“忠實”,即對目的語讀者的忠實和對原作思想的忠實,以進一步闡釋其“忠實性叛逆”文學翻譯觀的真正內涵。
教師在講解《文化生活》相關內容時應提升文化素養并擴充文化知識積累。教材中很多知識點舉例對學生來說有距離感的原因就在于課前學生對相關概念缺乏了解,僅停留在片面化與碎片化的名詞解釋。書本上選取的實例背后往往隱藏著真實的歷史價值,例如書中“傳統建筑”下列舉的北京菊兒胡同和每一個古老的北京胡同一樣,曾為官宦人家的宅邸,承擔著日常生活中的多種功能,但是在講解之前,部分教師內心由于缺乏一定程度的認可與了解,低估其獨特的歷史價值,因而無法使學生產生信服的感覺。所以,教師在講解知識點前應明確書中涉及案例背后的真實價值,領略文化實體的特殊魅力,對文化產生認可和自信心,進而有足夠的底氣向學生傳遞正確的文化觀念。
例1 何世熊家里養著一條狼狗。這年冬天,各村都來了個打狗運動,為了游擊隊活動方便,把大大小小的狗都打死了。只有何家這條狗,說是多少多少銀子買來的,不叫打。村干部不敢惹他們,狼狗就留下了。(袁靜、 孔厥,2002:99)
此段為第五章中第一節的第一段。原文旨在解釋在村里狗都被打死了的情況下,何世雄家里為何還養著一條狗。沙博理省譯此段應該有以下兩個原因:(1)原文與主題不相關,破壞了前后文的話題連貫。第四章以“找不著何世雄和何狗皮”的話題結束,按照正常的行文邏輯,第五章應該是解釋為何找不到這倆人——因為狗報信了。原文作者卻在“狗報信”話題之前利用一個自然段為狗的出現做鋪墊,殊不知這段描寫非但沒有達到澄清話題的目的,反而破壞了第四章與第五章之間話題的連貫,因此將其刪除便顯得順理成章、自然貼切。(2)原文與目的語讀者認知語境相悖。西方讀者將狗視為寵物,因而可能會認為“將大大小小的狗都打死”這種行為著實殘忍,這種理解會加大目的語讀者對原作中所述游擊隊作為英雄人物形象的誤解。對原文的刪減處理雖然在內容和形式上有悖于原文,卻達到了兩方面的忠實:一方面保證了譯文的話題連貫和閱讀的流暢性,忠實于目的語讀者的接受;另一方面避免了讀者對原作中英雄人物的誤解,從而忠實于原作思想的傳達。
2.3 章內結構和內容的重組
整篇小說的英譯都是以“章”作為翻譯單位,其中每章內不乏段落間順序的調整和內容的重組。此種譯法既非刪減內容的節譯,也非胡亂增添的編譯,而是保持原文意義不變、重組行文邏輯的意譯方法,前兩者是屬于“破壞性叛逆”的層面,而后者是屬于“忠實性叛逆”的層面。另外,有別于傳統以句子為單位的意譯,沙博理是以篇章為單位,以篇章為單位進行翻譯“可以不拘泥于原文的句次和句型,可以按照譯文的語篇結構習慣,重新組織和調整,使譯文更加流暢、更富有條理性和邏輯性”(奚兆炎,1996:2-5)。
原小說中第一章第一節的前四段,原文主要包含了兩大內容:介紹牛大水的基本情況和談及牛大水他爹想給他娶媳婦的事,重心在后者。英文的語篇規范是先說主位,即說話的出發點,后說述位,即圍繞主位逐步展開的實際內容。原文的主位是牛大水,述位是圍繞牛大水所展開的“娶媳婦”這一事件。原文中對男主人公牛大水的基本情況介紹主要包括以下信息:申家村人(第四段),喪母,與爹和一個弟弟相依為命(第二段),負債,靠種著五畝地為生(第三段)。從括號中可以看出,這些介紹牛大水的信息都散落在不同的段落當中,缺乏整體性。譯者經過顛倒句次、重新組合以后,將散落的信息都集中在第一段,完成了對牛大水的全面介紹,再用三個段落展開對牛大水“娶媳婦”這一事件的敘述,眉目更加清楚,邏輯性更強,也更加符合英語小說的文體特征。譯文采用了典型的英文篇章的模式,先說主位,即介紹牛大水,后說述位,即牛大水他爹想給他娶媳婦這件事,從而關照了目的語讀者的閱讀習慣。
2.4 段內句子的增添
上文提到,沙博理主張歸化為主的翻譯策略,因此《新兒女英雄傳》英譯本中不乏釋義、注釋、詞句的增添等增譯策略的運用。因本文僅限于篇章層面的探討,所以在此只分析句子的增添這一增譯策略。沙博理主張用英文表達中文原作中的思想,而英文很注重語篇的銜接與連貫。鑒于此,沙博理在《新兒女英雄傳》的英譯中通過添加過渡句以及適當補充譯文讀者匱乏的外部世界的知識來保證譯文語篇的銜接與連貫,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例子當中:
例2 小梅在地里碰見秀女兒了。兩個人見了面,又是難受又是歡喜,就在一塊兒跑。餓了就向人要口餑餑吃。有個伴兒還好一點,可是又遭遇了敵人,兩個人又跑散了。(袁靜、 孔厥,2002:107)
Refugees in great number wandered aimlessly. Once Mei ran into her friend Niu-erh, and the two girls clung to one another crying happily. They managed to stay together for a while, begging food when they were hungry. Then they lost each other again when they stumbled upon a party of Japanese and fled pell-mell.(Sidney Shapiro, 1979:119)
例3 大水在地里胡混了幾天,心里想:“老這么東跑西顛的,也不是個事兒,找‘堡壘戶’鉆個洞試試看吧。”(袁靜、 孔厥,2002:118)
After wandering in the country for a few days, Ta-shui realized he couldn’t accomplish anything alone. He decided to spend some time in one of the underground “forts”. The “forts” were places of concealment in the homes or fields of peasants who where also members of the underground. At the height of the Japanese “mopping-up” campaign, the “forts” provided places of refuge and rest, and a means of keeping contact with other members of the organization.(Sidney Shapiro, 1979:132)
此例摘自第九章第二節,同樣是對“五一大掃蕩”這一主題所展開的實際內容。大水因在外閑逛多日,覺得單憑一己之力無法抗日,于是就想找個“堡壘戶”看是否能聯絡到其他共產黨員。此處的“堡壘戶”是指在抗日戰爭時期斗爭環境極端殘酷的情況下,覺悟群眾舍生忘死、隱藏保護共產黨干部和人民子弟兵的住房關系戶,是保護和積蓄抗戰力量的基地。這一中國特色文化詞形成于抗戰時期,普通的西方讀者不具備了解這一文化詞的背景知識,因此無法僅憑“underground ‘forts’”就能領會其深層含義。譯文通過對“堡壘戶”進行釋義,補充目的語讀者匱乏的背景知識,來保證譯文的語義連貫,忠實傳達了原作的思想。
3 結語
“叛逆”是翻譯的宿命。“忠實性叛逆”卻是不愿接受宿命的譯者們孜孜不倦的追求。沙博理就是這樣的眾多譯者中的一位。通過對沙博理“忠實性叛逆”文學翻譯觀進行解讀,筆者嘗試得出如下結論:(1)翻譯研究中“忠實”與“叛逆”兩個維度的研究都不可或缺,人為裁剪和割裂翻譯全貌以及翻譯學研究對象,更不利于譯學研究全面發展。但切記不可籠統對待文學翻譯中的“叛逆”行為,要區分“忠實性叛逆”與“破壞性叛逆”,并判斷如何對其進行取舍。前者以忠實為前提,叛逆是為了達到更大程度的忠實,保持原文意義不變、重組行文邏輯的意譯方法就屬此類;后者包括誤譯、編譯、節譯、竄譯、改譯等,造成這種后果的原因眾多,不一而足,如譯者力所不及,在對原文的理解與譯文的表達上不夠準確,或者是譯者因個人興趣愛好或贊助人的要求對原文進行大量增刪等。(2)沙博理的“忠實性叛逆”文學翻譯觀具有一定的理論高度與實踐深度。理論上,這一翻譯觀跳出了傳統的“忠實”觀與“叛逆”觀對立的瓶頸,認為文學翻譯是“忠實”與“叛逆”的對立統一,把握了“忠實”的客觀性與“叛逆”的主觀性,達到了辯證法的哲學高度。再者,筆者認為這種文學翻譯觀對非文學翻譯同樣適用,是對現有翻譯理論的補充和完善。實踐上,其以歸化為主、異化為輔的翻譯策略與以意譯為主、直譯為輔的翻譯方法對中國文學乃至非文學的英譯有切實的指導作用。
眾所周知,沙博理的中國文學英譯事業為中國文化對外傳播做出了巨大貢獻。因此,對其翻譯觀進行解讀能為中國文學作品的對外翻譯提供一些可行性指導,對中國文化“走出去”之譯介模式的構建也有一定的啟示。
Berman, Antoine. 1992.TheExperienceoftheForeign:CultureandTranslationinRomanticGermany[M]. S. Heyvaert (tran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hapiro, Sidney (trans.). 1979.DaughtersandSon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Tytler A. F. 1978.EssayonthePrinciplesofTranslation[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B. V.
洪捷. 2012. 五十年心血譯中國——翻譯大家沙博理先生訪談錄[J]. 中國翻譯(4):62-64.
胡壯麟. 1994. 語篇的銜接與連貫[M].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江楓. 2006. 江楓翻譯評論自選集[M].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廖鴻鈞. 1987. 中西比較文學手冊[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錢鐘書. 1984. 林紓的翻譯[G] ∥ 羅新璋編. 翻譯論集. 北京:商務印書館.
沙博理. 1991. 中國文學的英文翻譯[J]. 中國翻譯(2): 3-4.
沙博理. 1998. 我的中國[M].宋蜀碧,譯. 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沙博理.1985. 水滸新英譯本前言及翻譯前后[J]. 李士釗, 妙齡譯. 水滸爭鳴(4): 404-414.
孫致禮. 2001. 翻譯與叛逆[J]. 中國翻譯(4):18-22.
王向遠. 2014. “創造性叛逆”還是 “破壞性叛逆”?——近年來譯學界 “叛逆派”、“忠實派”之爭的偏頗與問題[J]. 廣東社會科學(3):141-148.
奚兆炎. 1996. 在高于句子的層次上翻譯[J]. 中國翻譯(2):2-5.
謝天振. 2012. 創造性叛逆:爭論、實質與意義[J]. 中國比較文學(2):33-40.
許鈞. 1997. 我和翻譯[G] ∥ 戴立泉, 楊懷宇. 江蘇學人隨筆.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亞歷山大.泰特勒著. 2000. 論翻譯原則[G] ∥ 潘慧儀,譯.陳德鴻, 張南峰. 西方翻譯理論精選.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197-210.
袁靜, 孔厥. 2002. 新兒女英雄傳[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張經浩, 陳可培. 2005. 名家名論名譯[M].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責任編校:陳 寧
“Faithful Treason”: Sidney Shapiro’s Literary Translation View
HUANGQinLIUHonghua
Sidney Shapiro, an American Chinese translator who introduced numerous Chinese literary works to western countries, made a huge contribu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culture. When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ry works into English, Shapiro adhered to the principle of faithfulness as well as offered empathy of the Italian saying “Trattutore é tratitore”, thus we define his translation view as “faithful treason” which means treason is for the sake of greater faithfulness, that is, be faithful to the target readers and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 betray part of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the original work. Through a detailed analysis of Shapiro’s specific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adopted in his English translation ofSonsandDaughters, this paper conducted an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faithful treason” translation view in order to look for feasibl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Sidney Shapiro;SonsandDaughters; English translation; “faithful treason” translation view
2016-03-10
黃勤,女,華中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翻譯理論與實踐、文學翻譯研究。
H315.9
A
1674-6414(2016)04-0111-05
劉紅華,女,華中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翻譯理論與實踐、文學翻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