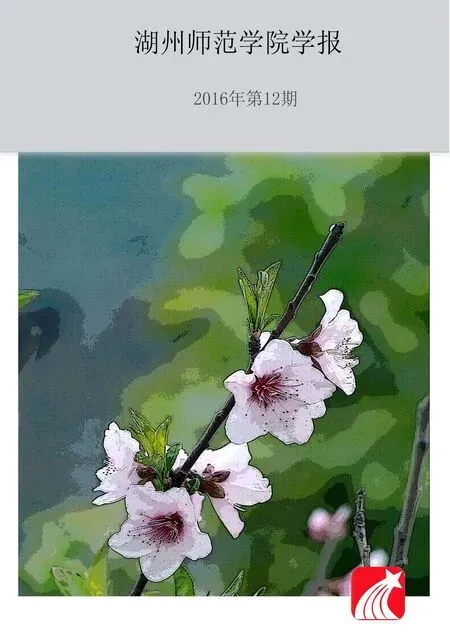師范教育的國家化路徑
——以浙江省立第一師范為例
鄭煒君
(華南師范大學 教育科學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1)
師范教育的國家化路徑
——以浙江省立第一師范為例
鄭煒君
(華南師范大學 教育科學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1)
相較于其他國家,中國近代師范教育在創辦之初,就被歷史賦予了一種獨特的地位:在地方精英控制了初等教育的背景下,各級政府必須要找到一條新的出路來統一全國的教育,掌控學生的思想,最終,它們將目光聚焦到師范教育上。民國初期,教育國家化在師范學校那里體現得尤為深刻,而師范學校也對此給予了積極回應。本文擬就以1897年(中國第一所師范學校成立)到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這三十年為期,梳理師范學校在中國的發展脈絡及其獨特性,并以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為個案,嘗試探討普通中等師范教育在民族-國家建設中所承載的歷史使命。
師范教育;國家化;獨特性;一師
師范教育在我國近現代教育史中有其特殊的地位,百年的發展中也經歷種種周折、起伏。從“癸卯學制”的仿日,到“壬戌學制”的習美,中國近代學制自它誕生之日起,就被貼上了“舶來品”的標簽,但是,即便是“舶來品”,也并非全盤照抄,其中,師范學校的變遷歷史恰恰折射出近現代教育在中國的本土化探索。在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進程中,教育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其中,師范學校又成為重中之重。本文擬就以1897年(中國第一所師范學校成立)到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這三十年為期,梳理師范學校在中國的發展脈絡及歷史賦予其的獨特地位,并以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為個案,嘗試探討普通中等師范教育在民族-國家建設中所承載的歷史使命。
一、獨立師范教育系統之濫觴
戊戌變法期間,一批有識之士看到了教育在現代國家建構中所具有的“開民智”之功效,提出要向西方學習,普及大眾教育,由此,興辦師范學堂以培養師資被提上日程。1896年10月,梁啟超在《時務報》上發表《變法通議·論師范》,認為“師范學校立,而群學之基悉定”。他在這篇文章中對當時洋務教育的現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同文館、水師學堂等新式學堂雖然聘請了外國教師,但存在“語言不通、教法不通、教師對中國文化一無所知、用不同語言練兵造成困惑,以及薪水遠高于華人”等問題,歸根結底,中國應培養自己的教師,“故欲革舊習,興智學,必以立師范學堂為第一義”。[1]如何辦師范學堂呢?梁文詳細介紹了日本的成功范例,通過對日本學制和師范學堂設置的模仿,對中國的師范教育做出具體規劃。
1898年《籌集商捐開辦南洋公學折》中,盛宣懷提到自己創辦南洋公學最先是從師范院開始的,“上中兩院之教習,皆出于師范院”。上海南洋公學師范院是公認的第一所中國師范學校,可惜在經歷變法失敗和庚子事變后,于1903年關閉。1898年《籌議京師大學堂章程》中,專門提出要“別立一師范齋以養教習之才”,因當年爆發“戊戌政變”,師范齋未能真正開辦,直到1902年《欽定學堂章程》頒布后,京師大學堂附設仕學館與師范館,師范館首先招生,并于當年12月17日正式開學,由此拉開我國高等師范教育之帷幕。
現代國家中,沒有哪個國家,不通過教育立法,完成教育國家化,實現國家壟斷,發展國家知識生產力,使知識國家化。[2]中國自然不例外,在民族-國家建設進程中,通過教育立法實現了國家對教育的收歸統一。其中,師范教育自成系統,顯得尤為重要,“壬寅”“癸卯”以及“壬子癸丑”學制,見證了近代師范教育體系從無到有的獨立過程。
《欽定學堂章程》又稱“壬寅學制”,是中國近代第一個系統完備的新教育制度。該學制雖然沒有得到施行,但卻初步規定師范教育分師范館與師范學堂,不過二者分別附設在各學堂內,換言之,此時的師范教育尚未形成獨立的組織系統。1904年頒布的“癸卯學制”更進一步,規定師范教育自成系統,獨立設置。作為《奏定學堂章程》總綱的《學務綱要》提出“師范學堂,意在使全國中小學堂各有師資,此為各項學堂之本源,興學入手之第一義。”[3]各省城應即按照現定初級師范學堂、優級師范學堂及簡易師范科、師范傳習所各章程辦法迅速舉行。因為初級師范學堂是小學教育普及的基礎,限定每州、縣至少要辦一所,“學堂經費,當就各地籌款暫備用,師范學生無庸納費。”[1](P14)考慮到操作的現實困難,允許由省城暫設一所,等到以后各省城優級師范學堂有畢業生后,州、縣一級再考慮以次添設。在優級師范學堂方面,規定“京師及各省城宜各設一所”,“省城優級師范學堂初辦時,可與初級師范學堂并置一處,俟以后首縣及外州縣全設有初級師范學堂,將省城初級師范學堂增高其程度,并入于優級師范學堂。”[1](P29-30)《師范學堂章程》還詳細規定了各級師范學校的學科設置、分科教法、考錄入學、畢業效力、教員管理等,至此,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師范教育體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07年《奏定女子師范學堂章程》正式頒布,而在1904年的《奏定初級師范學堂章程》中,還提到雖然外國在設立男子師范學堂之余,還有女子師范學堂,“但中外禮俗不同,未便于公所地方設立女學,止可申明教女關系緊要之義于家庭教育之中”。[1](P15)雖然當時女性接受教育的目的還只限于“培養賢妻良母”,但畢竟女子教育由此走向了社會,這既是時代發展的需求,也是“癸卯學制”中設立蒙養院所帶來的“意外驚喜”,為中國女性日后爭取男女平等打下基礎。
中華民國成立之初,師范教育的獨立系統得以保持,同時,對清末帶有封建痕跡的師范教育體制所進行的改革,則是從教育宗旨、辦學內容開始的。師范教育的宗旨由原來的“尊君親親”“孔孟為中國立教之宗”變為“愛國家,遵法憲”“國民教育,趨重實際”。1912-1913年,“壬子癸丑學制”頒布,其中涉及師范教育的章程包括《師范教育令》《師范學校規程》《高等師范學校規程》《女子高等師范學校規程》等。規定初級師范學堂改稱師范學校,師范學校的設置以省立為原則,私人或私法人亦得呈請設立師范學校;優級師范學堂改稱高等師范學校,以國立為原則。在管理方面,明確將女子師范教育納入師范教育系統,指出“專教女子之師范學校稱女子師范學校,以造就小學校教員及蒙養院保姆為目的。”“女子高等師范學校以造就女子中學校、女子師范學校教員為目的。”[1](P156)而且廢除了以往對女子師范學校那些基于封建禮教而制定的管理條規。在課程設置方面,“讀經講經”“經學大義”等科目被刪除,取而代之的是與資本主義相關的法制、經濟等課程。另外,教科書都重新編寫,在教學內容上進行了較為徹底的改革。此學制一直沿用到1922年,被“壬戌學制”所取代。
1920年代初的那場教育改革,有學者認為其實是地方自治運動與中央權力長期博弈的一個結果。[4](P18)師范教育系統的獨立性受到了嚴重沖擊,從另一個層面上看,意味著中央想要通過師范教育來掌控全國教育的企圖遭到了地方的抵制。
1922年,北洋政府以大總統令公布了《學校系統改革案》,史稱“壬戌學制”,其確定的“六三三”框架,對中國現行學制意義重大。和“壬子癸丑學制”所體現出的集中性、統一性不同,“壬戌學制”受美國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影響,相對突出分散性和地方性。新學制“七項標準”中的最后一項就是,多留各地方伸縮余地。在改革中學學制的基礎上,新學制力圖提高師范教育的辦學靈活性,設置了6年制的師范學校、3年制的師范學校、高級中學內的師范科、短期師范講習所、2年制師范專修科和師范大學等多種教育機構,提出由普通中學、大學與原來的師范學校一起承擔培養教師的職責。尤其是“高級中學分普通、農、工、商、師范、家事等科,但得酌量地方情形,單設一科或兼設數科”這一規定,直接導致“師、中合并運動”的產生,師范教育從一個單獨的體系被逐漸納入進普通中等教育中。浙江率先動作,將省立中學與師范學校合并,改名為省立中學,女子師范學校改名為女子中學。 其后,廣東、湖北、福建、江蘇等省相繼將師范學校并入省立中學,成為高中師范科,師范生的公費待遇不得保障,結果造成師范學校及師范學生數量驟減,教育質量下降。中師遭遇“寒冬”,高等師范學校也沒能幸免。“高師改大”運動期間,大多數高師相繼重組改革,成為綜合性大學。1921年,郭秉文擔任南京高師校長時,將南京高師改為東南大學。1922年,沈陽高師緊隨其后,改為東北大學。接著是武漢高師、廣東高師、成都高師等,到1931年前后,原來的7所高師僅剩下北平師范大學和北平女子師范院兩所,二者也在1931年進行了合并。
當然,這個階段的師范教育也并非一片冰天雪地,中等師范教育地位降低、高等師范教育削弱,鄉村師范教育卻在此時蓬勃興起。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團體和教育改革家以師范學校作為改造鄉村社會的工具,試圖為落后地區創造出一種新型發展模式,將鄉村社會帶入現代[4](p18)。鄉村師范教育在這里顯示出其“地方性”的一面。 1919年,余家菊在《中華教育界》上發表《鄉村教育之危機》,翌年又在同一刊物上發表《鄉村教育運動的涵義和方向》,倡導鄉村教育運動。這一運動的方向首先就是“向師范學校去運動”,具體言之就是在師范學校各科教授中著眼于鄉村,設置鄉村教育學科,創立鄉村試驗學校,并養成師范生服務于鄉村社會的精神。1919年,山西太原成立了以培養鄉村小學教師為宗旨的國民師范學校,被不少人認為是我國鄉村師范教育的先聲。1925年陶行知在《師范教育下鄉運動》中指出,“鄉村師范學校負有訓練鄉村教師改造鄉村生活的使命。……我們要想每一個鄉村師范畢業生將來能負改造一個鄉村之責任,就須當他未畢業以前教他運用各種學識去作改造鄉村之實習。這個實習的場所,就是眼面前的鄉村,師范所在地的鄉村。”[5]1927年,他身體力行,在南京北郊創辦了我國第一所試驗鄉村師范學校,即著名的曉莊師范。
二、“以收統一之效”的師范教育
(一) 師范學校
18、19世紀,歐美各國的師范教育制度陸續完善,如18世紀,德國的師范院已遍及各地,經過費希特的提倡和洪堡的改革,師資訓練制度基本確立;法國從1833年起,各省獨自或聯合興辦培養小學教師的師范學校,招生、培養等有關規定逐步統一;英國有組織的培訓師資開始是與導生制結合在一起,1870年初等教育法頒布后對師范教育提出新的要求,1888年克羅斯委員會提議大學建立走讀師范學院以培養小學教師;美國自1823年霍爾在康科特創辦第一所私立的中等師范學校后,經過多年的發展,中等師范教育體系至19世紀末基本形成。 從上述幾個國家師范教育形成的背景來看,彌補師資之不足,為社會各級各類學校培養教師,是各國成立師范學校的初衷,在這一點上,中國并沒有不同。只是,清末興辦兩級師范學堂之時,正直廢除科舉制度之際,中國的師范學校除了擔負培訓師資之職責外,還多出了一項在廢除科舉后解決廣大寒儒身份的功能,這,形成了中國師范教育鮮明的獨特性。
1904年,張之洞等人在《管學大臣等奏請試辦遞減科舉注重學堂折》中,為那些在科舉中未能考中進士的人做出安排,讓他們可以轉任當地新學校的教師。在他們的安排中,那些有初級功名,年齡在30歲以上者可以在速成師范學校畢業,50歲以上者需要通過政府的特殊考試后,安排政府輔助之職,那些終身舉業而不中又年滿60者可安排較低的教學職務,那些有功名而又年齡偏大者可以成為教師或考試官。[4](P60)1905年,范祎在《師范學堂與仕學館之亟宜設立》一文中提出,“處置舊時科舉之士及科舉之官”,可以有兩條路,一是豢養之以遂其愿,二是栽培之以收其用,莫若廣設師范學堂與仕學館二種。
從癸卯學制中也可以一窺當時改革者對師范學堂的定位,即師范血統在新學制中的地位非常類似科舉制下的官學體系,從招生到畢業以及學銜授予、職位分派都與官學類似,受到政府控制。如《欽定中學堂章程》中就規定,中學堂附設之師范學堂,“擬招貢生、監生、廩生、增生、附生等入堂肆業”。師范學堂畢業后,生員根據考列成績被授予功名。“優級師范學堂考列最優等者,作為舉人,以國子監博士盡先選用,并加五品銜,令充中學堂及初級師范學堂教員”“初級師范學堂考列最優等者,作為拔貢,以教授盡先選用,并加六品銜,令充高等小學堂教員”[6]。尤其在早期,各地師范學堂的招生對象主要以有功名者為優先,對畢業生也頒發功名,這些都說明了當時的師范學校作為改革的緩沖器,為舊式文人的轉型提供了一個渠道,同時,也通過師范教育為地方士紳、精英分子安排去處這樣的舉措,構架起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橋梁,增強了政府對地方的管控。
在教學內容方面,獨立的師范學堂與普通中學堂相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增加了一門教育學。比如附設在中學堂里的師范科,使用的是同一張課表,只是“每星期減去外國文三小時,加教育學、教授法三小時”。與國外師范學校的課程相比,清末的中等師范教育(初級師范學堂)更多傾向于倫理、修身、讀經等,注重師范生的品行教育。最早在對“壬寅”學制的修訂中,就透漏出了政府對師范生品德質素的重視:“師范教育務須恪遵經訓,闡發要義,萬不可稍悖其旨,創為異說”“必須常以忠孝大義訓勉各生,使其趣向端正,心性純良。”[7]為何如此注重師范生的思想和品行,《學部奏定師范獎勵義務章程折》中提到,“竊維振興教育,以養成師范為始基,故師范一途,關系至為重要。”正因為“師范為各種學堂之根源“,國家的有用之才,都是老師教出來的,正本清源,故而對師范生的品德要求自然要比其他學生高出一些,當然,獎勵也會更優厚一些,“優級師范學堂程度與高等學堂同而略勝,初級師范學堂程度與中學堂同而略勝。”
無論是學生生源、畢業待遇,還是課程設置、興學力度,師范學堂在開辦之初,就彰顯出中國師范教育特殊的重要性,即政府希望通過掌控師范教育來主導整個國民教育體系,進一步為國家培養有用之才。1904年1月頒布的《奏定學務綱要》中提到,“查開通國民知識,普施教育,以小學堂為最要,則是初級師范學堂造就教小學之師范生,尤為辦學堂者入手第一義。特是各省城多有已設中學堂、高等學堂者,勢不能聽其自出心裁,致誤將來成材之學生,則優級師范學堂在中國今日情形亦為最要,并宜接續速辦。”[8]可見,當時的政府能看到小學堂對提高國民素質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各地經費支絀,在官方沒有能力舉辦更多小學堂時,將簡易師范科或師范傳習所培養出來的師范生,充任到由地方鄉紳、家族主辦的小學堂,不可不為一捷徑。1906年,學部要求各省推廣師范生名額,“現在請以全力注重師范,五個月內本部當派視學官分省巡視。”[4](P573)
(二) 師范區制度
有一種觀點認為,當莊嚴的統治大權從幼小的滿族皇帝手中正式交到袁世凱之日起,中國失去了具有兩千年歷史的強有力的政治統一象征的君主政體,從此,占據國家中央地位的,是一個既無政綱,又無帝王權威的反動、無恥軍閥。[9]不論這種觀點正確與否,辛亥革命后,地方分權自治卻是在與中央集權的對抗中日漸膨脹。中央政府在將國家權力的觸角深入地方時,注意到了“以教育收統一之效”。歷史上,近代學校均有幫助國家實行政治上的統一、灌輸國民意識、創造民族身份認同的功能。[4](P17)而在中國,民國時期各種政府不約而同地把這種功能賦予了師范學校,利用師范學校來管理地方教育的職責,通過對教師的培養、管理和支配,確保各級各類學校能協助國家政權控制地方社會。
教育部認為“近來國家多故,對內急于對外,故定教育行政之方針,尤應以力圖統一為第一義”。“高等師范學校為師范學校教員所出,又為教育根本之根本。惟有將高等師范學校定為國立,由中央直轄,悉以國家之精神為精神,以國家之主義為主義,以收統一之效。”[7](P485)民國初年,孫中山以大總統的名義令教育部通知各省優級師范學堂一并開學;教育部公布的《師范教育令》規定:凡師范教育學校為省立學校,高等師范學校為國立學校。這一系列舉措大大提升了師范學校的地位。
袁世凱稱大總統時,也不希望看到地方獨大的局面出現,為了擴充兵力,他縮減財政開支,唯獨對教育非常慷慨,不僅廣興學校,更設置全國性師范區,試圖通過教育的統一改善中央權力軟弱的狀況。教育如何統一?袁世凱首先做的是收回教育權,改變分散辦學的情況,由中央統一規劃,并通過高等師范來統攝全國的教育。1913年,時任教育總長的范源濂提議設立“六大師范區制”,得到了袁的認可。1914年,《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中提到,師范學校校長除了擔任教育科目的教員之外,“每年課余有視察本區內教育情況之義務,歸時有提出報告開會研究之義務。”高等師范學校的設置采集中主義,即國立原則;師范學校的設置采分立主義,由各省自行辦理。校長要由部委派,科目編制教授等均由部考核。1915年頒布的《教育綱要》,將全國大部分地區分為六個大師范區,以六所國立高等師范學校為中心,每區下轄數省,各省中等師范以府道區進一步劃為師范學區。六所高師按規定有責任協助本地區的教育行政機關,辦好中等教育,高師校長除管理好本校行政與教學外,還要視察本地區的中等學校。 1916年初教育部制定了一個更為詳細的計劃,將全國分為八大師范區:直隸區以北京高師為中心;東三省區以沈陽高師為中心;湖北區以武昌高師為中心;四川區以成都高師為中心;廣東區以廣州高師為中心;江蘇區以南京高師為中心;蒙古區含蒙古、西藏和青海;新疆區則包括新疆和伊犁,當然,后二者并沒有高等師范學校作為依托,所以難免有“紙上談兵”之嫌。 同年,袁世凱病逝,教育部既無經費也無能力落實全國師范區的規劃,此后的北洋政府時期,中央權力不斷瓦解,地方政府又不配合,使該制度幾乎成為“一紙空文”。雖然在國家級層面,這個計劃被無限擱置,但在省一級層面,它部分得到了實現。有資料表明,1914-1918年,大部分省劃定了省內的師范區,并著手為每一區建立地方師范,到20世紀20年代初中央政權癱瘓時,這些師范區依然在部分地區運作,在這些師范區內,師范學校是教育行政的中心,擔負考察、指導本學區小學教育的職責。1919年,“五四”運動吹來民主與科學之風,杜威來華進一步傳播了美國實用主義教育思想,1922年在留美學生主持下的第七屆全國教育聯合會的倡導下,“壬戌學制”出臺,新學制突破了師范學校分區設立的框框,提出各地可按照自身情況酌設相當年限的師范學校或師范講習所,“中、師合并運動”中,師范學校進一步失去其獨立性,成為普通中學的附庸,師范學區制因此不廢而廢。[4](P100)
師范區制度,是當時的政府迫于現實而采取的一種手段。該制度下的各區的師范學校,對本區各級各類學校需要承擔起掌握情況、聯絡統一、提供決策的職責,其實就是在替政府機關行使一種教育行政權。師范學校該如何行使這一職責呢?除了各校校長親自考察本學區的學務狀況之外,各師范學校也聯合了起來,一時間,諸如師范教育研究會、師范學校聯合會等團體紛紛涌現,對當時教育政策、法規制度的出臺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1915年,陳寶泉在北京創辦全國師范教育研究會。同年,《全國師范校長會議規程》又規定定期召開由教育總長主持的全國師范學校校長會議。1918年,成立國立高等師范學校聯合會。此外,從1915年起每年召開一次的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在當時也是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團體,師范教育成為他們每次開會都無法回避的重要議題。全國師范學校校長會議和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的召開,不僅促進了師范教育自身的改革,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它們實際上代替教育行政部門行使了部分權力,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為國家最終形成教育法規建言獻策。
比如,在統一語言方面。探討教育與國家的關系命題,有這樣一種表述:“切實的知識系統和健全的語言政策,能夠加強社會整合,鞏固民主法治,維護國內、國際的合理秩序。從教育方面說,應該在國家的、地區的和全球的層次上,推究知識政策和語言政策的極端政治性。”[10]語言的統一是民族-國家建設的必經之路。而在中國,國語運動的興起得益于兩個因素,一是新文化運動領導者所倡導的白話運動;二是全國教育會在1917年提出教育部應要求所有師范學校必須大力宣傳并推行國語。1918年,教育部接受高師校長會議的建議,命令所有高師設國語科,1919年,全國教育會第五屆會議促請教育部采取五項措施推進國語,其中第一項就是在所有師范學校增加國語課程。[4](P103-104)
師范區制度是中國近代師范教育發展的新事物。 其設立的主要目的有兩個,一是在財政有限的情況下,以國家控制師范學校,然后通過將師范學校作為區域教育行政中心的方式謀求全國教育的統一; 二是以此推動全國師范教育尤其是高等師范的平衡發展和促進教師教育質量的提高。雖然師范區制度的設置時間并不長,且由于軍閥割據等現實,也沒有達其初衷,但是師范區制度卻是教育對當時政治、社會環境的一種回應,體現了師范教育在那個時期所承擔的重要作用。從中我們可以總結出兩點,一是在當時,師范學校所扮演的社會角色,除了培養廣大中小學教員之外,還肩負著區域內的教育監督、社會教育之責;二是在大學較少的情況下,國立高等師范學校在一定時期內實際上承擔了大學的社會功能,成為各區的學術文化乃至教育行政中心。
三、以浙江省立第一師范為個案
地處吳根越角的杭嘉湖平原,自古就是魚米之鄉、富庶之地。自唐宋以降,更是被賦予了濃重的詩書禮儀之鄉的色彩,到明清時期,已是名儒輩出。晚清的社會變革,尤其是科舉制度的廢除,對當地的精英產生了巨大沖擊,幸運的是,這群人并沒有因此頹廢不振,而是借人文、地理、經濟等各種優勢,開風氣之先,或遠涉重洋學習西方先進理念,或創辦新式學堂培養經世人才,成為具有新學背景的新式知識分子。1906年,浙江兩級師范學堂*辛亥革命后,為響應教育部提出的集中高師以統一全國教育的號召,該學堂將優級公共科的學生送往北高師,于1913年更名為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專事中等師范教育。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創辦的。鄭曉滄在《浙江兩級師范和第一師范校史志要》中提到,雖然當時創辦高等學校,必須經由督撫向朝廷奏準,但是絕不能認為建校的動機“純起于當時的巡撫”,而應是起于地方的若干所謂“士紳”并得到了巡撫的支持。此外,學堂以省城貢院舊址改建,這也是富有意義的一件事。在科舉制度下,各省均有一個貢院,浙江的貢院大概有一萬余個“考棚”,每三四年會聚各府州縣的生員廩貢前來考試,約舉一百人,所謂“舉人”,得向京師“會試”。在貢院的舊址上新建師范學堂,鄭曉滄認為這標志著一個教育史的轉折點,即“科舉已被決定廢止了的,代之而起的乃是學校”。筆者認為,在貢院舊址上創辦的不是其他新式學堂,而恰恰是師范學堂,這個巧合耐人尋味,它似乎暗含了上文所提到的,晚清政府正是想用師范教育來取代科舉制下的官學體系,師范學堂成為國家掌控教育的一個重要載體。
兩級師范學堂期間,歷任學堂監督(校長)一職的,有邵章(杭州人)、喻長霖(臺州人)、王延揚(金華人)、沈鈞儒(嘉興人)、夏震武(杭州富陽人),他們無一例外都是浙江興學初期頗為活躍的地方精英。其中,有人有豐富的辦學經驗,如邵章辦過蠶學館;有人有先進的理論基礎,如王延揚曾東渡扶桑考察日本教育;有人在政界資深望重,如沈鈞儒擔任過教育司司長、咨議局副議長,還被推舉為眾議院議員。當然,也有人站在時代潮流的對立面,如夏震武就持守舊思想,結果與教師意見不合,造成教員離校、課務停頓,本人最終辭職收場。省立第一師范期間,歷任校長的主要有,經亨頤(紹興人)、姜琦(溫州人)、何炳松(金華人)、馬敘倫(杭州余杭人)、沈溯明(湖州人)等,這些人大多有過留學經歷,接受了民主主義的進步思想,其中馬敘倫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教育部的第一任部長,他們對當時的教育改革乃至整個社會發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除了上述“一把手”之外,在其他教學管理和普通任課教師崗位上,還有錢家治、許壽裳、夏丏尊、沈尹默、張宗祥、蔣夢麟、魯迅、李叔同、姜丹書、胡源東、劉大白、陳望道、朱自清等,可謂名家薈萃,人才濟濟。正是在這些人的共同努力下,浙江省立第一師范為中國的師范教育史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章,為當時社會秩序重構培養了一大批新式力量。
本文擬以這所規模宏遠、設備齊全、師資雄厚為浙省之冠的師范學校(以下簡稱為“一師”)為個案,進一步分析我國的中等師范教育在當時的社會結構改造過程中,是如何做出自己獨特的回應的。
(一)教學改革
師范生的品行教育一直是師范教育的重點,一師也不例外。經亨頤在擔任一師校長期間,就非常看重“人格教育”,注重學生的精神生活和人格養成,提出“勤、慎、誠、恕”四字校訓。他一直強調學校不是“販賣知識的商店”,而要以陶冶人格為主旨。尤其是師范學校,培養的是未來的教師,所以對師范生必須重視操行考查,高要求嚴標準對待。平時該如何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呢?經亨頤從情感陶冶入手,一反原來只注重智力訓練的教育傳統,對音樂、美術、體育等“副科”尤為偏愛。甚至專門去上海請來李叔同擔任音樂和圖畫教師,并配備專門的美術教室、音樂教室。李叔同就是在一師任教期間,創作了膾炙人口的《送別》等校園歌曲。在課程安排上,音樂、手工等科目的自修和教授時間的比例,與國文、數學一樣均為二比一。體育課更是不準學生無故缺席,在經亨頤的大力倡導下,一師的文體活動十分豐富,學生德智體美得到全面發展。
在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基礎上,一師進一步提出了“自動、自由、自治、自律”的口號,培養學生的“民主意識”,給學生一定的自由度,要求教員能信任學生、尊重學生,讓學生自己管理自己。這種對“自治精神”的追求,首先體現在課堂教學改革上。經亨頤在任期間,力挺夏丏尊、陳望道、劉大白、李次九(被譽為“四大金剛”)主持一師國文教學改革。國文教材多取自《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等雜志上的白話文章,從內容上打破了傳統的禁錮,給學生傳遞了不少新思想。課堂教學形式也逐漸地從以教師講授為主的知識傳遞,演變為以學生爭辯社會人生問題為主的研討會。一師學生、民國著名戰地記者曹聚仁后來曾回憶過這段時光: “到了秋涼開學,整個學校的風氣都變換過了; 先前那幾位國文教師: 陳子韶、單不庵、劉毓盤都走了,來的乃是陳望道、劉大白和李次九,說是提倡新文學的。從那個秋天起,老是罷課游行,很少有一星期完整的課可上;即算是上課,也只是討論討論人生問題、社會問題,課本上的事,反而擱開了。”而正是這種對各類社會問題是非對錯的定性及其解決方案的討論,導致學生走出課堂,進行社會實踐,干預現實,對一師學生投身于學運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11]另外,在學制授課考試方面,學生也獲得了更大的自由。1919年開始,廢除了留級制度與頻頻的小考、月考,各科分數到畢業學年再行結算; 1920年起試行學科制,精簡學科、教材與授課課時,共減少了10科合計760課時,如此一來,學生有更多的空間進行自主學習,有利于個性的發展。[11]在學校管理方面,經亨頤推行民主治校,學校設評議會作為全校最高議事機構,討論包括財政預算在內的校內重大事務。評議會議長由校長擔任,評議員則按一定比例從教職員工和學生中民主選舉產生。此外,學校還成立了學生自治會,諸如食堂管理、內務整潔等老大難問題,都在學生的自我管理下得到了解決。 “一師風潮” 之后,學生自治的職權更有所提高,例如官府任免校長須經全體學生同意; 學生有權向校方推薦優秀教師;有權過問教職員的進退等。[12]
(二)社團與刊物
中國近代師范教育在創辦之初,就被賦予了一種獨特的地位:地方精英控制了初等教育,使得中央政府必須要找到一條新的出路來控制新式學堂的課程與學生的思想,并最終將此重任交給師范學堂。國家掌握師范學校并由此來統一教育思想,如同科舉時代讓官學管理府州縣學一般,獨立設置的師范教育體系擔負了官學在科舉制度下所承擔的責任。
民國時期,無論是孫中山、袁世凱,還是后來的北洋政府、南京政府,都把教育統一看成是國家統一的基石,總體上看,教育部對師范學校的重視比清末有過之而無不及。師范教育受到如此的重視,直接就導致了師范學校的師生對政局變化、新思想傳播的敏感度要比普通中學的師生來得更強烈。以“五四”運動為例,如果把歷史的鏡頭從北京、上海這些中心城市拉到地方上,可以發現各省城活躍著的師范生們的身影也是清晰而讓人激動的。浙江、湖南、山東等地的省立師范學校的學生們都是“五四”在地方上扛大旗的要角,師范生們成為近代中國新思想傳播道路上的先遣隊。
“五四”之后,一師的各種社團如雨后春筍,比較著名的有施存統等辦的“全國書報販賣部”,推銷《新青年》《星期評論》《資本論》等書刊;有潘漠華、馮雪峰、汪靜之等創辦的“晨光社”等。其中,晨光社是浙江省最早成立的新文學團體,也是繼“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之后,全國最早的新文學團體之一。每月會定期聚會交流詩歌創作心得,有自己的章程和周刊,指導老師為朱自清、葉圣陶等。在三潭印月、曲院風荷、柳浪聞鶯這些西湖景致中,學生社員在老師的帶領下走出課堂,體悟自然萬物、現世人生,以新文學載體開始了對普世價值的追求。在朱自清、劉延陵等編輯的《詩》雜志上,經常能看到晨光社員的作品。如學生馮雪峰最早時期的稚嫩詩作,1921年底的《小詩》與1922年的《桃樹下》便都發表在《詩》第二期上。[10]類似的社團不僅證明在經亨頤掌舵下的一師,學生有著豐富多彩的課余生活,更體現了當時師范學校學生對新事物、新文化的接收已然走在普通中學生的前面。
除了“晨光社”所創辦的《晨光》之類的純文學刊物,一師在“五四”洪流中還涌現出了傳播新思想的刊物,其中最有影響力莫過于《浙江新潮》。《浙江新潮》的誕生,與上文提到的“全國書報販賣部”有著密切的關系。在《新青年》《新潮》等進步雜志的影響下,一師學生俞秀松、施存統等與甲種工業學校學生夏衍、省一中學生查猛濟等創辦了“浙江新潮社”,并于1919年11月1日推出以提倡新文學、鼓吹新思想為主旨的《浙江新潮》。該刊第一期上的《發刊詞》,鮮明提出了改造舊社會,實現理想中的“自由”“互助”“勞動”的新社會的戰斗目標,強調知識分子必須和勞動者聯合。第二期刊發了施存統寫的《非孝》一文,引起軒然大波。*《非孝》一文發表后 ,在社會上引起很大沖擊。反動勢力嘩然駭怪,群起而攻擊的對象,不僅僅是施存統個人,而是擴大到整個一師,尤其是校長經亨頤身上。當時的浙江省長是吉林人齊耀珊 , 以他為首形成了“倒經”一派,要求經亨頤辭去校長職務,一師學生會發起“挽經護校”運動,從而掀起了轟動全國的“一師風潮”。省政府派人將正在浙江印刷公司排印的第三期底稿全部搜去,勒令印刷公司不準再印。結果,學生們找到上海《星期評論》社,替他們印出了《浙江新潮》的第三期,這一期上,有傅彬然寫的《廢孔》一文,在當時也堪稱驚世駭俗之作。最后,北洋軍閥政府從北京發出“查禁浙江新潮”的電報,致使這份四開小報被迫停刊。《浙江新潮》的生命雖然短暫,但影響卻極為深遠。陳獨秀后來在《新青年》上曾專門撰寫文章,對《浙江新潮》給予高度評價,并說,“我禱告這班可愛可敬的小兄弟,就是報社封了,也要從別的方面發揚《少年》、《浙江新潮》的精神,永續和窮困及黑暗奮斗,萬萬不可中途挫折。”[13]果然,在一師內部,校友會十日刊繼續刊行,在杭州,繼《浙江新潮》后又出現了《錢江評論》、《杭州學生聯合會報》、《浙人》等新興刊物,革命思想薪火相傳。
正是因為當時的師范教育所承載的獨特的社會功能,正是因為有以經亨頤為代表的一批具有民主思想、開明作風的師長,才有了一師內這些新興社團和刊物成長的一片沃土,省府的師范生們一邊在斗爭中得到鍛煉,一邊又自覺承擔起了傳播新思想的重任,使得一師成為浙江省的新文化陣地。陳望道曾經評價:“五四前后的新文化運動,從全國范圍來講,高等學校以北大最活躍,在中等學校,則要算是湖南第一師范和杭州第一師范了。”[14]
四、結 語
在教育國家化的思路下,師范學校與社會轉型之間的互動,在一師這個個案上表現得尤為生動。從清末在貢院舊址上創辦兩級師范學堂,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一師學生的作用,在對一師個案的研究中,既可以覺察出不同政府對師范教育的重視,也可以細辨出師范學校對教育國家化的回應。
20世紀初的師范學校的變遷,反映了中國當時重大社會和政治變革的脈動,它是民族-國家建設過程中的一面鏡子,從不同的角度折射出了這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
[1]李友芝.中國近現代師范教育史資料第一冊[M].(出版地不詳)1983:130.
[2]董標.教育、教育學、民族-國家同構論[J].山西大學學報(哲社版),2014(4).
[3]陳元暉.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實業教育 師范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567.
[4]叢小平.師范學校與中國的現代化——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社會轉型1897-1937[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18.
[5]陶行知.師范教育下鄉運動[J].新教育評論,1926,1(6).
[6]陳元暉.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實業教育師范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1994:568.
[7]朱有瓛.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下)[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224.
[8]舒新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第二冊)[M].上海:中華書局,1928:10.
[9][美]費正清.劍橋中華民國史(上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199.
[10]DAVID C,EVIE Z.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Education[M].London: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2005.
[11]張直心,王平.民初文學教育考論 ——以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為考察中心[J].文藝爭鳴,2011(15).
[12]董舒林.中等教育的改革者經亨頤[J].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986(4):158.
[13]倪維熊.浙江新潮的回憶.[EB/OL].http://www.ccyl.org.cn/zhuanti/09_54/54zlg/gsh/200904/t20090429_229597.htm.
[14]陳望道.“五四”時期浙江新文化運動[J].杭州地方革命史資料,1959 ( 1 ).
The Path of Nationalization in Teacher Education-A Case Study of Zhejiang First Normal School
ZHENG Wei-jun
( School of Educ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China)
Compared to other countries, teacher education in China was given a special status at the beginning of its birth--local government had to find an approach to integrate education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control young people’s mind on the context that primary education had already been controlled by local elites. Finally, they found teacher education.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in normal schools was conducted in an impressive way, in the meantime, normal schools responded positively. This paper intends to sort out the development of normal schools in China from 1897 (the year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rst normal school in China) to 1927 (the year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explore its distinctiveness, and discuss its historical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normal education; nationalization; uniqueness; tutor
2016-04-23
鄭煒君,博士生,從事教育基本理論研究。
G650
A
1009-1734(2016)12-00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