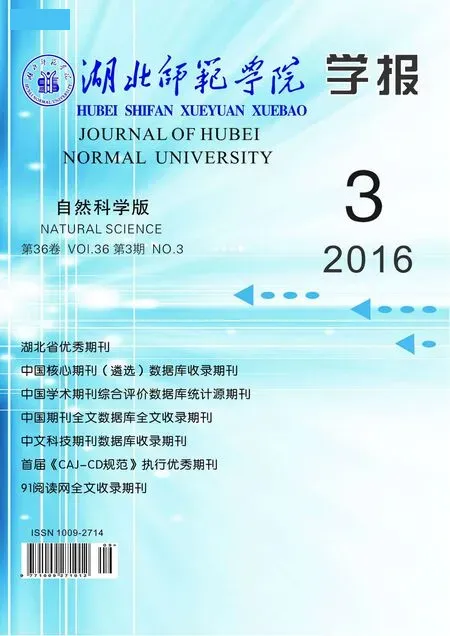通過期刊群的建立來平衡科技期刊與網(wǎng)絡(luò)數(shù)據(jù)庫之間的關(guān)系
黃睿春
(武漢大學(xué)《數(shù)學(xué)雜志》編輯部, 湖北 武漢 430072)
?
通過期刊群的建立來平衡科技期刊與網(wǎng)絡(luò)數(shù)據(jù)庫之間的關(guān)系
黃睿春
(武漢大學(xué)《數(shù)學(xué)雜志》編輯部, 湖北 武漢430072)
分析科技期刊與網(wǎng)絡(luò)平臺之間的合作現(xiàn)狀,提出利用期刊群的建立來平衡科技期刊和網(wǎng)絡(luò)數(shù)據(jù)庫關(guān)系的構(gòu)想。
科技期刊;網(wǎng)絡(luò)平臺;期刊群;平衡關(guān)系
一直來,科技期刊的發(fā)展以及發(fā)行都深深打上了科技發(fā)展的烙印,從最初的紙質(zhì)期刊,到光盤,直到時下的數(shù)字化發(fā)展,科技期刊的網(wǎng)絡(luò)平臺也跟隨著計算機和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發(fā)展應(yīng)運而生,如今,以網(wǎng)絡(luò)和數(shù)字化出版為鮮明標(biāo)志的發(fā)展趨勢正深深影響著科技期刊的載體形式和話語權(quán)的歸屬。仲偉民教授在文獻[1]中指出了學(xué)術(shù)期刊與網(wǎng)絡(luò)平臺之間的顛倒,李巍等在文獻[2]中探討了科技期刊與網(wǎng)絡(luò)數(shù)據(jù)庫共生共榮之道。作者在文獻[3]中提出了通過專業(yè)期刊的融合和合作開展學(xué)術(shù)期刊縱向改革之路,此文隱約給出了期刊群建立的雛形與設(shè)想。 在本文中,筆者分析了科技期刊與網(wǎng)絡(luò)平臺合作的現(xiàn)狀,結(jié)合《數(shù)學(xué)雜志》目前面臨的困境,發(fā)展的瓶頸以及困惑,明確提出了通過期刊群的建立來平衡科技期刊與網(wǎng)絡(luò)平臺之間的關(guān)系,本文為筆者在文獻[3]的基礎(chǔ)上對期刊群研究的進一步延伸。
1 科技期刊與網(wǎng)絡(luò)平臺之間的合作現(xiàn)狀
科技期刊作為科學(xué)研究的發(fā)布平臺,學(xué)術(shù)成果的呈現(xiàn)載體和媒介,它本身獲得了長足的發(fā)展,而科技期刊的網(wǎng)絡(luò)平臺是隨著計算機和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的發(fā)展而因勢而生。它的發(fā)展讓科技期刊的傳統(tǒng)傳播方式發(fā)生了深刻的變革。如今,數(shù)字化出版已經(jīng)成為了科技期刊傳播的最主要的方式。 《數(shù)學(xué)雜志》作為中文核心期刊,其數(shù)字化發(fā)展的模式跟大多數(shù)科技期刊的數(shù)字化發(fā)展模式基本一致,很具有代表性,在此筆者以它為例。
《數(shù)學(xué)雜志》有自辦的網(wǎng)站,由于經(jīng)費和人員不足,目前網(wǎng)站僅僅利用了采編系統(tǒng)。 同時與中國知網(wǎng)簽訂有獨家協(xié)議以及優(yōu)先出版協(xié)議,編輯部和中國知網(wǎng)之間的合作模式很簡單,編輯部給網(wǎng)絡(luò)數(shù)據(jù)庫提供刊發(fā)的稿件電子版,網(wǎng)絡(luò)數(shù)據(jù)庫將論文上傳網(wǎng)絡(luò),以有償?shù)姆绞教峁┙o作者網(wǎng)絡(luò)文獻檢索,給讀者下載相關(guān)文獻。而網(wǎng)絡(luò)數(shù)據(jù)庫給編輯部提供相關(guān)的服務(wù),比如不端學(xué)術(shù)論文檢測,文獻檢索,科技期刊的相關(guān)數(shù)據(jù)分析報告等,此外,每年支付給編輯部一定的文獻檢索費,而編輯部以稿費的形式支付給作者。
從上述的合作現(xiàn)狀我們可以看出,如果把期刊的數(shù)字化出版看做作一環(huán)緊扣一環(huán)的生產(chǎn)鏈,科技期刊編輯部就會處于原材料加工的最底層,他們負(fù)責(zé)原始作品的送審,編輯,加工,刊發(fā)等一系列繁瑣而精細的工作,將最后的作品傳給各個網(wǎng)絡(luò)數(shù)據(jù)庫之后,編輯部與作者的互動基本就結(jié)束了。而此時網(wǎng)絡(luò)數(shù)據(jù)利用自身的優(yōu)勢,如眾多科技期刊的匯聚地,非常方便快捷的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平臺, 即便因為期刊種類的繁多,文獻檢索的精準(zhǔn)定位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但是作者因為各種不同的需要花錢去開具檢索報告,同時,讀者也只能夠通過網(wǎng)絡(luò)數(shù)據(jù)庫下載他們需要的文獻。這樣導(dǎo)致,在目前的形勢下,無論是讀者還是作者使用的都是網(wǎng)絡(luò)數(shù)據(jù)庫發(fā)布的產(chǎn)品,而不是各個編輯部刊發(fā)的論文,因此各個科技期刊編輯部淪為了數(shù)字化出版生產(chǎn)鏈上的加工廠,而不是學(xué)術(shù)研究成果發(fā)布的前沿陣地。
從經(jīng)濟利益的角度來看,科技期刊的數(shù)學(xué)化出版是一個巨大的經(jīng)濟利益共同體,只不過占據(jù)經(jīng)濟利益主導(dǎo)和主要份額的屬于網(wǎng)絡(luò)數(shù)據(jù)庫。因為期刊網(wǎng)絡(luò)數(shù)據(jù)庫是眾多期刊的匯聚地,不同需要的人都可以從這個網(wǎng)絡(luò)平臺得到他們需要的資料或者文獻,網(wǎng)絡(luò)數(shù)據(jù)庫利用這樣獨有的優(yōu)勢通過付費檢索和下載獲取相關(guān)利潤。而對于期刊編輯部,無論有沒有自辦的網(wǎng)站都很難實現(xiàn)付費下載,因為可提供的資源太少,不能滿足眾多的需求,僅僅利用有限的版面費以及少量的發(fā)行費來維持編輯部的日常運作。比如《數(shù)學(xué)雜志》編輯部,雖然有自辦的網(wǎng)站,但是因為資金不足和人手不夠,雜志歷年來的過刊到目前還沒有上線,同時為了緩解稿件刊發(fā)周期過長的問題,我們將論文的優(yōu)先出版權(quán)轉(zhuǎn)讓給了網(wǎng)絡(luò)數(shù)據(jù)庫,這就意味著編輯部在數(shù)字化出版的這個利益體中處于極端的劣勢,沒有絲毫的話語權(quán)和主動性。而對于網(wǎng)絡(luò)平臺依賴或者掛靠主辦單位或者網(wǎng)絡(luò)數(shù)據(jù)庫的期刊編輯部,情形差不多。
科技期刊與網(wǎng)絡(luò)數(shù)據(jù)庫合作之初,因為計算機技術(shù)和網(wǎng)絡(luò)的限制,兩者之間的合作項目僅限于光盤的制作,兩者的合作關(guān)系相對簡單,一方面,科技期刊借助于光盤的發(fā)行擴大自身的影響力,提高期刊的傳播力,另一方面,網(wǎng)絡(luò)數(shù)據(jù)庫將期刊制作成電子版,為后期數(shù)字化的發(fā)展積累了資源,也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chǔ),但是伴隨著數(shù)字化出版的蓬勃發(fā)展,當(dāng)網(wǎng)絡(luò)數(shù)據(jù)庫在合作中占據(jù)諸多優(yōu)勢,處于經(jīng)濟主導(dǎo)地位,隨后,網(wǎng)絡(luò)數(shù)據(jù)庫開始調(diào)整合作以及服務(wù)的方向,也不斷引入國外的一些服務(wù)項目,因此推出了獨家,優(yōu)先出版,DOI,最近又發(fā)來了ORCID的合作協(xié)議。而對于科技期刊而言,各個編輯部十年如一日的不斷地給網(wǎng)絡(luò)數(shù)據(jù)庫上傳經(jīng)過精細選擇,編輯加工后的電子稿,以方便論文的網(wǎng)絡(luò)檢索和下載。當(dāng)網(wǎng)絡(luò)數(shù)據(jù)庫越來越強大,點擊率越來越高時,數(shù)字化的發(fā)展蒸蒸而上時,科技期刊紙本的發(fā)行量卻越來越少,發(fā)行費還不足以支付期刊的印刷費,當(dāng)科技期刊在網(wǎng)絡(luò)數(shù)據(jù)庫中被拆分成一篇一篇獨立的論文時,期刊的整體性也不再存在,當(dāng)有一天期刊不再發(fā)行紙本的時候,從一定意義上講,也就意味著紙質(zhì)期刊將不再存在。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科技期刊與網(wǎng)絡(luò)平臺之間的這種關(guān)系是一種失衡的,有失公正的,它隨著出版環(huán)境的改變慢慢裂變,并且將隨著數(shù)字化出版的發(fā)展而持續(xù)惡化。更讓人感覺悲觀的是,科技期刊編輯部根本無力改變現(xiàn)在這種局面,而相關(guān)的管理部門也沒有相關(guān)的政策或者規(guī)定來平衡或者干預(yù)。針對這種局面,每一個科技期刊編輯部都應(yīng)該開始思考如何改變現(xiàn)狀,如何在將來嚴(yán)峻的競爭中不被淘汰,究竟該怎樣改變和打破科技期刊與網(wǎng)絡(luò)平臺之間的僵局?
2 矛盾和現(xiàn)狀催生期刊群的建立
從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處于絕對優(yōu)勢方的網(wǎng)絡(luò)平臺哪怕深知矛盾也不愿意去改變現(xiàn)狀,期刊的行政管理部門無心也沒有有效的手段來改變現(xiàn)狀,對于科技期刊編輯部而言,我們無力改變,但是又迫切需要改變。以《數(shù)學(xué)雜志》為例,一方面,即便我們有了自辦的網(wǎng)站,但是沒有跟兄弟單位的融合和合作,獨自為陣,在同網(wǎng)絡(luò)平臺的合作中沒有話語權(quán)和主導(dǎo)權(quán),只能被動接受所有的合作條件和協(xié)議。另一方面,作為中文核心期刊,稿源質(zhì)量不高,出版手段單一,對外的宣傳和合作受人員和經(jīng)費的限制,地位尷尬,雖然力量有限,但是我們渴望打破僵局。在這種矛盾和現(xiàn)狀之下,期刊群的建立就顯得尤為迫切。
3 通過期刊群的建立來平衡科技期刊和網(wǎng)絡(luò)平臺之間的關(guān)系
所謂期刊群是指多種期刊的“集聚化” 模式,類似于一種產(chǎn)業(yè)集群,它不僅是單本刊到多本刊的量變,更是發(fā)展規(guī)模、經(jīng)營理念以及經(jīng)營模式的改變[4-6]。 當(dāng)多種期刊聚合在一起謀求發(fā)展是意味著科學(xué)合理的分配,優(yōu)化和共享資源,節(jié)約辦刊的成本,同時為做大、做強期刊奠定了堅實的物質(zhì)基礎(chǔ)。更為重要的是,期刊群的建立有利于平衡科技期刊與網(wǎng)絡(luò)平臺之間的關(guān)系。
一方面,對于網(wǎng)絡(luò)平臺而言,期刊群的建立有利于打破網(wǎng)絡(luò)平臺在經(jīng)營上的壟斷,期刊群本身就代表著一定的主導(dǎo)性和話語權(quán),在與網(wǎng)絡(luò)平臺的合作中力量不會像單本刊那么薄弱,而是具有更強的力量可以與網(wǎng)絡(luò)平臺平等對話,在這種公平、公正的合作環(huán)境中,可以為科技期刊向網(wǎng)絡(luò)平臺爭取更多的經(jīng)營分配額,同時要求網(wǎng)絡(luò)平臺為科技期刊提供更優(yōu)質(zhì)、個性化的服務(wù);期刊群的建立可以改變依賴于網(wǎng)絡(luò)平臺出版的單一出版模式,期刊論文通過期刊群平臺的發(fā)布就是另外一種出版模式,這種平臺的建立促進了期刊出版模式多樣化的發(fā)展,有利于期刊的對外宣傳和曝光度,有利于更進一步提高期刊的知名度。
另一方面,對于科技期刊而言,期刊群可以給期刊提供更個性化的服務(wù),一改科技期刊在網(wǎng)絡(luò)平臺中的平庸和單調(diào),它提供給期刊一個更適合更個性化的平臺,這個平臺有利于期刊影響力的提升、傳播和宣傳;期刊群可以促進新刊的孵化,美國物理學(xué)會下的各個期刊的孵化和發(fā)展模式就是最好的證明,期刊群以它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成為新刊創(chuàng)立的必備條件;期刊群的建立讓科技期刊能夠真正的面對市場,通過期刊群每個期刊可以知道我們的訂戶是誰,我們的消費群體是什么,他們需要什么樣的服務(wù)和內(nèi)容,一本期刊只有了解市場,了解我們的客戶以及客戶需要,了解研究學(xué)科領(lǐng)域內(nèi)研究的熱點和未來發(fā)展的方向,并且及時地將相關(guān)信息通過期刊群的平臺推送給讀者、作者、研究機構(gòu)、評價體系等,只有這樣的存在方式才能讓科技期刊擺脫孤立無援、發(fā)展沒有方向的現(xiàn)狀。而上述期刊群的諸多優(yōu)勢也是網(wǎng)絡(luò)平臺無法達到的。
由上述我們不難看出,期刊群的建立是打破和改變目前現(xiàn)狀的必由之路,它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動搖了網(wǎng)絡(luò)平臺在數(shù)字化出版發(fā)展道路上的絕對地位,同時,它讓各個憑借一己之力艱難生存的科技期刊找到了后盾和發(fā)展的動力,改變刻不容緩。
4 結(jié)論
當(dāng)然,期刊群的建立是同領(lǐng)域的期刊的融合還是不同學(xué)科領(lǐng)域的期刊融合是我們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就目前科技期刊與網(wǎng)絡(luò)平臺之間合作的現(xiàn)狀來看,期刊群的建立是打破和改變這種失衡關(guān)系的唯一出路。
[1]仲偉民. 緣于體制:社科期刊十個被顛倒的關(guān)系[J]. 南京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人文科學(xué),社會科學(xué)), 2013, (2): 1~18.
[2]李巍,林強,張薇,等.科技期刊與網(wǎng)絡(luò)數(shù)據(jù)庫共生共榮的發(fā)展之道[J].中國科技期刊研究, 2014, 25(6): 793~796.
[3]黃睿春. 寫在學(xué)術(shù)期刊編輯部體制改革之時——以《數(shù)學(xué)雜志》為例[J]. 中國科技期刊研究, 2013, 24(6): 1063~1065.
[4]胡志強,周寶東. 多類型組合科技期刊刊群經(jīng)營實踐與理論研究[J]. 編輯學(xué)報, 2012, 24(1): S28~S30.
[5]劉澤林. 探索刊群模式, 促進規(guī)模發(fā)展——卓眾出版的刊群建設(shè)實踐[J]. 編輯學(xué)報, 2010, 22(5): 428~431.
[6]張輝玲, 白雪娜, 馬力,等. 廣東省農(nóng)業(yè)期刊現(xiàn)狀調(diào)查與刊群建設(shè)思考[J]. 中國科技期刊研究, 2014, 25(4): 582~587.
2016—05—03
黃睿春(1977—),女,碩士,編輯,主要研究方向為泛函分析及其應(yīng)用.
G232
A
1009-2714(2016)03-001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