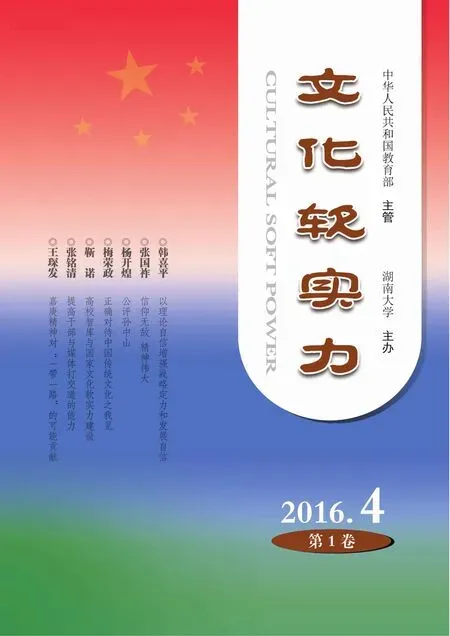嘉庚精神對“一帶一路”的可能貢獻(xiàn)
王 琛 發(fā)
嘉庚精神對“一帶一路”的可能貢獻(xiàn)
王 琛 發(fā)
從陳嘉庚的生平來看,他深受儒家天下為公觀念影響,兼具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雙重理想。他的曲折經(jīng)歷塑造了他復(fù)雜的國家觀念與國際視野,也即是既要堅(jiān)持南洋華人的文化認(rèn)同,又要維護(hù)當(dāng)?shù)厝A人在南洋的開拓主權(quán)。因此,對嘉庚精神要有一個(gè)整體性認(rèn)識(shí),不僅要重視他堅(jiān)持民族氣節(jié)的高尚情操,還應(yīng)注意到他很早就主張跨族群支持泛亞洲反殖大業(yè)的國際視野。陳嘉庚的思想遺產(chǎn),是中國與南海周邊國家共同的外交資源與文化紐帶。
陳嘉庚;愛國主義;國際主義;一帶一路;公共外交
一 共同財(cái)富:嘉庚精神與南海格局
陳嘉庚出生于1874年,逝世于1961年。在他有生之年,親眼目睹了從近代列強(qiáng)紛爭、到兩次世界大戰(zhàn)、再到美蘇冷戰(zhàn)三個(gè)不同歷史時(shí)期南海地區(qū)局勢的復(fù)雜變化。時(shí)至今日,我們要探尋嘉庚精神對“一帶一路”的時(shí)代意義,不妨重溫他在《南僑回憶錄·弁言》中對二戰(zhàn)后國際局勢的警惕和呼吁:“此次勝利國諸大領(lǐng)袖,均有偉大善愿,欲措世界各國于長期和平之前途。然欲違此目的,必須監(jiān)察既往,揣度未來,以公平道義為根據(jù),消除不平及無理之舊狀態(tài),方能熄滅戰(zhàn)爭之導(dǎo)火線,而達(dá)到弭兵之期望。……此次世界大戰(zhàn)后,蘇美英諸領(lǐng)袖,既欲以道義造福人類,當(dāng)然對于不平等苛政,不仁義權(quán)利,必須鏟除或改善。”*陳嘉庚.南僑回憶錄:上冊[M].美國:八方文化企業(yè)公司,陳嘉庚國際學(xué)會(huì),1993:5.然而,在他去世后的半個(gè)多世紀(jì)里,仍然有不少仁人志士在為同樣的理想而奮斗和犧牲著,而他理想中的“天下為公”從未真正實(shí)現(xiàn)。
陳嘉庚是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的愛國華僑領(lǐng)袖,“一帶一路”則是中國近年才提出的國際合作新倡議,二者似乎關(guān)系不大。尤其是如果對陳嘉庚的歷史認(rèn)識(shí)不夠完整深刻,片面地描繪他個(gè)人選擇“落葉歸根”的愛國主義傾向,就可能忽略他長期南洋生活塑造的國際主義傾向,也可能受上世紀(jì)南洋地區(qū)一些關(guān)于他的消極言論的誤導(dǎo),從而疑惑于今天宣揚(yáng)嘉庚精神能否避免各國內(nèi)部對華人效忠的質(zhì)疑,擔(dān)憂他的“落葉歸根”會(huì)否加劇各國內(nèi)部對華人“落地生根”的猜忌?*王琛發(fā).林語堂的南洋大學(xué)恩怨:活在理想與政治糾纏之間[J].閩臺(tái)文化研究,2015(3):68.
事實(shí)上,歷史上更全面、更真實(shí)的陳嘉庚,他既是民族的、愛國主義的,也是跨越族群的、國際主義的。同一個(gè)陳嘉庚,除了擁有“愛國華僑”的一面,也曾經(jīng)支持其他民族的獨(dú)立斗爭,為著泛亞洲反殖民運(yùn)動(dòng)奔走呼吁,堅(jiān)持亞洲新興國家的多元民族應(yīng)有公平的在地權(quán)利,主張各族平等合作建國。從國際合作,以及各國華人定位的角度來看,嘉庚精神當(dāng)中這個(gè)部分,能讓大家更清楚認(rèn)知,歷史上除了“中國的陳嘉庚”,還有個(gè)“國際的陳嘉庚”。陳嘉庚從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繼承的天下觀,使得他既自覺支持亞洲各民族解放、贊同南洋華人應(yīng)聯(lián)合當(dāng)?shù)馗髅褡褰▏质撬嬲\選擇回歸中國的思想根源。
今天,當(dāng)中國倡議以“一帶一路”為框架構(gòu)建新型國際關(guān)系之時(shí),探尋嘉庚精神當(dāng)中的這一組成部分,尤其是其思想淵源與歷史表現(xiàn),將有助于說明在陳嘉庚生活過的南洋地區(qū),也就是海上絲綢之路所包括區(qū)域,陳嘉庚的國際主義精神應(yīng)如何延續(xù)與發(fā)揚(yáng)。
陳嘉庚的思想遺產(chǎn),不是也不應(yīng)該是中國所獨(dú)有的,而是中國與南洋各國可以一道汲取、繼承以及運(yùn)用的共同文化資源。這份資源的共同開發(fā)將有利于構(gòu)建各國的華人認(rèn)識(shí),也有利于各國華人更積極、更合理地在祖國與南洋各國的雙邊、多邊關(guān)系中扮演促進(jìn)各方溝通互信的重要角色。
二 國際視野:呼吁華人支持真反殖
陳嘉庚支持亞洲各國獨(dú)立運(yùn)動(dòng),在這一方面已經(jīng)有很多的研究。陳嘉庚既是英屬殖民地最早通電支持印尼獨(dú)立運(yùn)動(dòng)的華人領(lǐng)袖,也是戰(zhàn)后南洋地區(qū)第一個(gè)公開支持印度獨(dú)立的華人領(lǐng)袖,后世可以探尋的不單是其主張與行動(dòng)本身,更在于支撐其主張與行動(dòng)背后的思想淵源,亦如他在《南僑回憶錄》中所說的那樣:“以公平道義為根據(jù),消除不平及無理之舊狀態(tài)”。
陳嘉庚對印尼獨(dú)立運(yùn)動(dòng)的認(rèn)識(shí)和支持,起源于日軍投降以后。陳嘉庚從瑪瑯出發(fā)回新加坡,一行人從泗水乘火車到吧城途中,發(fā)現(xiàn)蘇卡諾主動(dòng)派出便衣衛(wèi)士一路沿站保護(hù)。*黃丹季.陳嘉庚先生瑪瑯避難記[C]//《陳嘉庚先生紀(jì)念冊》編輯委員會(huì).陳嘉庚先生紀(jì)念冊.北京:全國歸僑聯(lián)合會(huì),1962:44.當(dāng)時(shí),陳嘉庚為著在新加坡的商業(yè)經(jīng)營與自由出入,還是保持著英國公民身份。可是,他在登機(jī)離開吧城前夕,已經(jīng)不太在乎英荷在印尼境內(nèi)的軍事同盟關(guān)系對他可能造成的不利影響。他以南洋華人領(lǐng)袖和廈門大學(xué)校主的身份,在歡送會(huì)上公開呼吁印尼校友“要為華僑教育事業(yè)努力,并幫助印尼爭取獨(dú)立”*黃丹季.疾風(fēng)知?jiǎng)挪荨惣胃壬敩槺茈y紀(jì)實(shí)[M]//全國政協(xié)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huì)等合編:回憶陳嘉庚.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 95.,這就充分證明了其勇氣與自信。而且,陳嘉庚安抵新加坡后,還通電感謝蘇卡諾對華人的友好行為,坦誠告知蘇卡諾自己意識(shí)到蘇門答臘華人與本地其他民族存在若干矛盾,并已主動(dòng)為印尼獨(dú)立運(yùn)動(dòng)斡旋當(dāng)?shù)厝A人,他希望蘇卡諾也呼吁各地印尼人與華人保持友好。*陳嘉庚.南僑回憶錄:下冊[M].美國:八方文化企業(yè)公司,嘉庚國際學(xué)會(huì),1993:444.這封電報(bào)收錄在1946年出版的《南僑回憶錄》,其意義是指明南洋華人應(yīng)持的立場,也足以說明他不怕英荷追究其“通叛”。而且,正當(dāng)荷蘭人謀劃重新入侵革命首都日惹,印尼共和國派出龐大代表團(tuán)秘密前往印度參加新德里亞洲會(huì)議(Inter-Asian Relations Conference),代表團(tuán)成員沒有一個(gè)身上有外幣,他們也是上門聯(lián)系陳嘉庚,陳嘉庚除了支持印尼代表團(tuán)500元叻做路費(fèi),還主動(dòng)提出獻(xiàn)捐巨款。*蕭玉燦著.黃書海等譯.五個(gè)時(shí)代[M].香港:地平線出版社,1982:131.
如果深入了解陳嘉庚當(dāng)時(shí)所處國際形勢,再重讀陳嘉庚在1947年2月14日所發(fā)《為荷蘭慘殺華僑并奪船劫貨封鎖貿(mào)易事》通告,*陳嘉庚.陳嘉庚言論集[M].新加坡:新加坡怡和軒俱樂部等,2004: 279-281.以及發(fā)表于2月16日的《新加坡僑民大會(huì)開會(huì)情形》,*同⑤281-285.就會(huì)發(fā)現(xiàn),自新加坡 14 個(gè)華人社團(tuán)成立“保障南洋華僑安全委員會(huì)”,推李光前為主席,向荷蘭政府交涉,再到委員會(huì)公推陳嘉庚出面主持,陳嘉庚號(hào)召南洋華僑聲討荷蘭政府的言論,已經(jīng)是把“保護(hù)華僑”上升到以反殖最終解決全局問題的高度。正如《新加坡僑民大會(huì)開會(huì)情形》報(bào)道其演講反復(fù)指責(zé)殖民主義那樣,陳嘉庚意識(shí)到荷蘭企圖壟斷海貿(mào)、乘機(jī)對獨(dú)立運(yùn)動(dòng)進(jìn)行經(jīng)濟(jì)封鎖,于是他便主張南洋華人與荷蘭斷絕經(jīng)貿(mào)關(guān)系,這在主客觀上都相當(dāng)于發(fā)動(dòng)華人支援印尼獨(dú)立運(yùn)動(dòng)。*同⑤,原刊于南僑日報(bào)[N].1947-02-18.也正因此,荷蘭副總督派遣四人代表團(tuán)到新加坡規(guī)勸,要他重新考慮印尼華人利害關(guān)系。而陳嘉庚除了重申南洋華人要求荷蘭政府道歉、賠償、退還貨物船只、停止限制人口出入、以及保證不犯,*同①33,原刊于南僑日報(bào)[N].1947-02-18.也預(yù)言荷人終遭印尼人民驅(qū)逐出境。*楊進(jìn)發(fā)著.李發(fā)沈譯.陳嘉庚-華僑傳奇人物[M]. 美國:八方文化企業(yè)公司,1990: 333-334.
同一時(shí)期,陳嘉庚所指的那些在“蘇門答臘”騷擾獨(dú)立軍的華人,以及他們在印尼境內(nèi)的支持者,卻是受到了中國內(nèi)外右翼勢力影響,打著“護(hù)僑”旗號(hào)組織“華僑保安隊(duì)”,接受荷軍提供武器彈藥,配合荷英軍隊(duì)作戰(zhàn)。這不僅造成華人內(nèi)部分裂,加深華人和印尼人民的感情誤解,后來也成了別有用心者排華和反華的借口。從這點(diǎn)看,陳嘉庚要求華人支持蘇卡諾,告訴蘇卡諾期待“兩民族間睦誼增進(jìn)”*同③.,是較明智的表態(tài)。
如果陳嘉庚鼓勵(lì)南洋華人支持印尼反殖運(yùn)動(dòng)是以“護(hù)僑”為切入點(diǎn),那么他對于同屬英國殖民地的印度,則是公開熱烈地支持其獨(dú)立運(yùn)動(dòng)。當(dāng)印度尼赫魯在1946年3月訪問新加坡時(shí),他親自以“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huì)”主席身份出面,率領(lǐng)地方華人領(lǐng)袖到機(jī)場迎接對方,又在怡和軒俱樂部門口設(shè)起牌坊,高懸其親撰對聯(lián):“真自由要向監(jiān)獄爭取,大領(lǐng)袖須從群眾中做來”。*楊進(jìn)發(fā)著.李發(fā)沈譯.陳嘉庚-華僑傳奇人物[M]. 美國:八方文化企業(yè)公司,1990: 333.當(dāng)然,支持尼赫魯比起支持蘇卡諾,所承受的各方面壓力相對較小。由于大英帝國早在1931年通過《威斯敏斯特法案》,允許殖民地國家最終取得與英國同等的地位,英國已逐步放棄直接干預(yù)各屬地內(nèi)政和外交,并試圖在原殖民地扶持未來可以合作確保英國利益的新政府;而印度國大黨經(jīng)過長達(dá)40年的反抗殖民主義斗爭,尼赫魯從1921年12月至1945年6月,先后9次被捕,坐了將近9年牢,在獄中撰寫《自傳》、《世界歷史一瞥》和《印度的發(fā)現(xiàn)》等書,聲名遠(yuǎn)播,卒之成為英政府在壓力下考慮交托政權(quán)的對象。
陳嘉庚固然稱譽(yù)尼赫魯奔走于解放印度人民的努力,可當(dāng)他說到“世界中有堂堂大國及一國中有權(quán)威之領(lǐng)袖,對誠信二字完全放棄”*陳嘉庚.陳嘉庚言論集[M].新加坡:新加坡怡和軒俱樂部等,2004: 240.,卻不免從歐美到蔣介石政府都被他不點(diǎn)名批判,說他們“許人獨(dú)立,往往食言;又如開口屢言民主,實(shí)則行獨(dú)裁專制。”*同②240-241.但陳嘉庚看來很能把握尺度,從通電支持蘇卡諾到歡迎尼赫魯,既控制在英國政府所能接受的限度內(nèi),又能闡明他的立場,繼而引導(dǎo)大眾。
翌年,陳嘉庚受邀出席尼赫魯在印度新德里召開的第一屆亞洲會(huì)議,以及上文提及他資助印尼代表團(tuán)秘密參與該會(huì)議之事,最能代表陳嘉庚的國際反殖立場(陳嘉庚其時(shí)與國民政府與會(huì)代表團(tuán)一致,將會(huì)議譯為“泛亞洲會(huì)議”)。雖然陳嘉庚最終沒能出席這次從1947年3月22日至4月2日舉行的會(huì)議,但是他以書面提出了《向泛亞洲會(huì)議提案訂結(jié)亞洲公約促進(jìn)亞洲文化》,證明他始終關(guān)心各國反殖運(yùn)動(dòng),希望各國能團(tuán)結(jié)一致探討他的幾個(gè)設(shè)想:“(一)建立亞洲民族聯(lián)誼協(xié)會(huì)案;(二)向亞洲各國政府建議訂結(jié)亞洲公約并建立亞洲區(qū)域安全機(jī)構(gòu)案;(三)促進(jìn)亞洲各族文化交換并共同努力提高亞洲人民文化水準(zhǔn)案。”*陳嘉庚.向泛亞洲會(huì)議提案訂結(jié)亞洲公約促進(jìn)亞洲文化[J].集美校友,1947-04-20(30).
依當(dāng)時(shí)國際形勢來看,陳嘉庚的三個(gè)提案,顯然是期待亞洲新生反殖力量在未來各自建國成功后依舊能團(tuán)結(jié)一致,也希望新興國家在今后的安全與和平方面繼續(xù)互相支持。最后一道提案,還說明陳嘉庚一貫的重視民族教育與文教強(qiáng)國的理念。
此次亞洲會(huì)議在4月2日結(jié)束,印度“圣雄”甘地的閉幕演說至今仍在被宣揚(yáng)和傳播。會(huì)議翌年出版的文論集刊,也確如陳嘉庚所期待的那樣,使用“泛亞組織”( Inter-Asian Relations Organization)的名稱。可惜,以胡適和國民黨秘書長吳鐵城為首的中國代表團(tuán)在會(huì)上答應(yīng)1948年由中國輪值,成了空話,*LEW Y T.The Best of Two Whorlds:Notes of My Spiritual Pilgrimage[M].New York:Universe,2008:32-33.一如陳嘉庚屢次對國民政府的預(yù)測與批評。
三 南洋主權(quán):不忘祖本而落地生根
回顧陳嘉庚如何看待南洋華人的文化認(rèn)同之內(nèi)容,可以從中認(rèn)識(shí)到他長期生活在南洋的思想演變過程。無論他的民族觀或國際觀,可以說都是在生活實(shí)踐中逐漸形成的。陳嘉庚雖然選擇了落葉歸根,但是他也看到其他南洋同胞開拓新天地的犧牲與貢獻(xiàn),因此堅(jiān)持南洋華人應(yīng)該在自己付出血汗的土地上擁有落地生根的合理主權(quán)這一理念是頗為務(wù)實(shí)的,也是頗具前瞻性的。
正如上述新興印尼共和國獨(dú)立運(yùn)動(dòng)過程中,就有許多華人參與其中。在參加新德里亞洲會(huì)議的代表團(tuán)當(dāng)中,負(fù)責(zé)聯(lián)系陳嘉庚的蕭玉燦,*蕭玉燦著.黃書海等譯.五個(gè)時(shí)代[M].香港:地平線出版社,1982:131.便是在思考華人遭受的殖民主義壓迫以后,認(rèn)為華人只有與印尼各族人民一起奮斗一起生活,才是出路。*《蕭玉燦百年誕辰紀(jì)念文集》編委會(huì).蕭玉燦百年誕辰紀(jì)念文集[C].香港:生活文化基金會(huì),2014:3.在這些印尼華人影響下,新生的印尼共和國的中央國民委員會(huì)主張,只要在國家獨(dú)立之前出生的印尼華人,無須申請,都自動(dòng)成為本國公民;而蕭玉燦等人在政府內(nèi)部也反對民族同化,主張保留華人特性、姓名、語言、文化、風(fēng)俗習(xí)慣和生活方式。*同⑦5.在新馬,陳嘉庚女婿李光前同樣主張華人擁有馬來亞國民權(quán)利,堅(jiān)信華人落地生根的開拓主權(quán)的同時(shí),也堅(jiān)持多元文化,反對“強(qiáng)迫文化”。*新加坡星洲日報(bào)[N].1946-10-12.
實(shí)際上,陳嘉庚也曾公開表明自己在這一問題上持有相同的立場。1945 年 10 月至 1947 年初,英殖民政府多次和馬來亞 9邦蘇丹秘密商議,此后便提出了馬來亞制憲建議書,準(zhǔn)備派遣英國高官協(xié)助馬來亞建立聯(lián)邦;但建議書提出把新加坡從馬來亞分離,成為英國直轄地區(qū)。陳嘉庚當(dāng)時(shí)不顧這是秘密建議,親自撰文指出,馬來亞若是規(guī)定非馬來人申請“公民權(quán)”,等于把一種額外的資格要求附加在原本應(yīng)有的公民國籍上邊,顯失公允,且實(shí)際上并沒有解決雙重國籍或雙重效忠問題。陳嘉庚反過來點(diǎn)明,確保效忠的重點(diǎn)應(yīng)該是實(shí)現(xiàn)全民民主。他向政府呼吁:“馬來亞民主政治正在締造中,因此使一切公民承認(rèn)馬來亞為其效忠之唯一對象,如此方可奠定民主政治的基礎(chǔ)”、“吾華人都向來尊重其他民族應(yīng)有之地位和權(quán)利,亦希望他民族尊重吾人的地位與權(quán)利”。*新加坡中南日報(bào)[N].1947-03-10.他也提到,要實(shí)現(xiàn)自治,首先應(yīng)使人民有選舉權(quán),有參政機(jī)會(huì),最少應(yīng)有學(xué)習(xí)參政的機(jī)會(huì),但英國的建議書中沒有提及選舉立法議員規(guī)則,令人不滿。因此他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馬來亞各族各階層人民,必須團(tuán)結(jié)互助,共謀地方之建設(shè)與繁榮。馬來亞經(jīng)濟(jì)應(yīng)成為一體,而民族間之同情與友誼為其紐帶。反之,如過分重視民族間之差別及分歧,引起互相傾軋,則實(shí)非建設(shè)新馬來亞之道也!”*同①.
就南洋華人本身歷史認(rèn)知而言,陳嘉庚所處的那個(gè)時(shí)代,已有不少碑文與史籍記載著南洋華人自明代以來秉承祖先文化墾殖南洋各地的歷史事實(shí)。在陳嘉庚看來,一個(gè)人甚至數(shù)代人依靠祖先文化在另一片土地上創(chuàng)造新的生命歷程,同時(shí)熱愛祖先文化以及現(xiàn)在生活的土地之間并不矛盾。按儒家觀念,不忘本是美德,對祖先父母能有報(bào)本反始之心,才有可能以同理同情看待他人,確保對他人的誠與信。因此,各民族熱愛祖先文化,把它在本土發(fā)揚(yáng),除了能豐富建設(shè)本土的精神資源,還能保障新興國家與各族祖籍地增添友好與理解,這種雙重效忠并不會(huì)影響各族人民對所屬國家的效忠。更何況,只有落實(shí)各民族互相尊重、公道、仁義、民主,才能構(gòu)成一個(gè)國家各民族共榮之基礎(chǔ)。陳嘉庚思想中這樣的理念是一貫的,亦如他在二戰(zhàn)結(jié)束后不久,也曾寄望蘇美英三國領(lǐng)袖會(huì)如他期待的那樣:“以愛國之道義,推廣兼愛世界”。*陳嘉庚.戰(zhàn)后補(bǔ)輯[M]//陳嘉庚.南僑回憶錄:下冊.美國:八方文化企業(yè)公司,嘉庚國際學(xué)會(huì),1993:461.
陳嘉庚本人就是其理念的實(shí)踐踐行者。英政府雖然佩服陳嘉庚的能耐,但是英殖歷任總督對待陳嘉庚都不太友好,他們屢次遇到和陳嘉庚之間有立場矛盾時(shí),就會(huì)考慮各種對付方法,包括驅(qū)逐出境、扣留、取消公民權(quán)利、阻止他從中國回到新加坡等等,也給他制造過各種軟硬兼施的壓力。*楊進(jìn)發(fā).陳嘉庚:為振興中華而不悔[M]//林水檺主編.創(chuàng)業(yè)與護(hù)根: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儒商篇.吉隆坡: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2003:43.可是,這一切都阻止不了他的理想與信念,阻止不了他既選擇效忠中國,又熱愛南洋同胞,不僅如此,他還主張將心比心,將此心推而廣之,去同情南洋各民族的反殖運(yùn)動(dòng)。即使陳嘉庚最后選擇“落葉歸根”,選擇了參與中國政治為整個(gè)民族做出更大貢獻(xiàn),但他依然關(guān)心南洋社會(huì)動(dòng)向,關(guān)切從親朋戚友到一般大眾的南洋華人及其他各族人民的未來。
1956年10月,陳嘉庚在北京接見來訪的新加坡中華總商會(huì)會(huì)長高德根時(shí),表達(dá)了其對新加坡華人爭取公民權(quán)運(yùn)動(dòng)的關(guān)注,他說:“過去在殖民地政府統(tǒng)治下的新加坡人民,除了英籍民外,其余都被當(dāng)做外國人看待,即使已在新加坡居住數(shù)十年,也享受不到絲毫的公民權(quán)利。雖然如此,但他們?nèi)匀粺嵝墓娲壬聘@聵I(yè),對當(dāng)?shù)厣鐣?huì)盡其應(yīng)盡的責(zé)任”, “現(xiàn)在你們新加坡即將自治獨(dú)立,你們既已把新加坡當(dāng)做永久居住的家鄉(xiāng),就要爭取成為新加坡的公民,效忠新加坡,并要比過去在殖民地統(tǒng)治下的我們一輩,更加努力為你們的新國家效力。”*高德根.悼一代偉人陳嘉庚先生[M]//陳嘉庚.南僑回憶錄:下冊.美國:八方文化企業(yè)公司,嘉庚國際學(xué)會(huì),1993: 34-35.而陳嘉庚本人則在1957年去信其子陳國慶,表明其既在中國政府任職,就不愿再保留雙重國籍。陳嘉庚隨信寄了本身在集美區(qū)政府官員面前簽字、加蓋集美區(qū)公章的放棄英國國籍聲明,請律師們通知新加坡當(dāng)局,代辦一切手續(xù)。*楊進(jìn)發(fā).戰(zhàn)后的陳嘉庚與英國政權(quán)[M]//楊進(jìn)發(fā).陳嘉庚研究文集.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8: 206.這樣兩件事例,足以反映陳嘉庚對待“國籍”與“效忠”的明確態(tài)度。他自己雖然選擇依托故國去服務(wù)整個(gè)民族,卻也不忘叮嚀南洋同胞維護(hù)落地生根之主權(quán),本身又做出拒絕雙重國籍的榜樣;而在整個(gè)過程其中,他并沒有放棄兩地親情、信任與關(guān)懷,所以總會(huì)流露出對南洋華人的關(guān)心。1961年陳嘉庚去世,高德根舊事重提,高度評價(jià)陳嘉庚說:“那時(shí),陳先生離開新加坡已多年,年紀(jì)已八十多歲,我真意料不到他仍然走在時(shí)代的最前頭,認(rèn)識(shí)得比我們當(dāng)時(shí)一般人更徹底更清楚,實(shí)在不愧為一個(gè)偉大的先知先覺者。”*高德根.悼一代偉人陳嘉庚先生[M]//陳嘉庚.南僑回憶錄:下冊.美國:八方文化企業(yè)公司、嘉庚國際學(xué)會(huì),1993: 35.
正如陳嘉庚理解和支持南洋華人應(yīng)擁有的國民權(quán)利,他也認(rèn)為文化、親情認(rèn)同和國家效忠可以并行不悖,所以他認(rèn)為選擇回歸祖國并不等于放棄南洋的一切。當(dāng)南洋華人社會(huì)浩浩蕩蕩推動(dòng)在新加坡建立南洋大學(xué),期許提供全體華裔學(xué)生繼續(xù)深造,陳嘉庚依然從遙遠(yuǎn)中國熱心關(guān)心,甚至提醒校長人選的人格問題。*1954-07-02陳嘉庚函林崇鶴[M]//陳嘉庚.南僑回憶錄:下冊.美國:八方文化企業(yè)公司、嘉庚國際學(xué)會(huì),1993: 23.這在冷戰(zhàn)時(shí)代,當(dāng)然也易于落人口實(shí)。那些有心人刻意忽略國籍差別不應(yīng)否定民族血脈親情,利用傳媒散播,把陳嘉庚的關(guān)心扭曲為政治上的不懷好意。*王琛發(fā).林語堂的南洋大學(xué)恩怨:活在理想與政治糾纏之間[J].閩臺(tái)文化研究,2015(3):77.作家韓素音形容其時(shí)氛圍,曾說:“人們總是要把文化認(rèn)同混淆到政治”。*HAN S Y.My House Has Two Doors[M].London:Jonathan Cape,.1980:88.時(shí)至今日,世界進(jìn)入全球化時(shí)代,人們會(huì)比過去更能接受多元價(jià)值認(rèn)同。而過去某些觀念是構(gòu)建在排華反華的意識(shí)形態(tài)基礎(chǔ)之上的,實(shí)不應(yīng)接受這種刻意混淆文化親近與國籍效忠之看法,也不應(yīng)一再與這類論述隨風(fēng)起舞。
四 嘉庚精神:海上絲綢之路與多邊公共外交的思想資源
陳嘉庚一生既堅(jiān)持民族氣節(jié),又注重跨越族群支持泛亞洲反殖大業(yè),這是他國際主義精神最本質(zhì)的寫照。而陳嘉庚這種難能可貴理念的思想源于中華文化熏陶塑造的人生觀、價(jià)值觀和世界觀。這一點(diǎn)既表現(xiàn)在其本身的言行,也蘊(yùn)含于他對孩子的二十條規(guī)勸。這其中最重要的規(guī)勸,是大家所熟悉又經(jīng)常忽略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陳厥祥.集美誌[M].香港:僑光印務(wù)有限公司,1963:77-178.儒家經(jīng)典《論語·雍也》有云:“博施于民而濟(jì)眾……己欲立而立于人,己欲達(dá)而達(dá)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能“博施于民而濟(jì)眾”,既要博施給自己民眾,又要救濟(jì)外國困苦大眾,最終就是把自己的思想理念落實(shí)到服膺《禮記·禮運(yùn)》大同篇中的“天下為公”理想之中。因此,陳嘉庚思想的國際主義傾向不再只是停留在紙面上的文字,而是來自從小受到的文化熏陶和人生實(shí)踐。身處亞洲各民族深受苦難的共同情境,他個(gè)人的命運(yùn)與商業(yè)生涯都是直面各方列強(qiáng)勢力,其思想上難能可貴之處就在于其既能夠繼承傳統(tǒng),將圣賢教導(dǎo)貫徹落實(shí)于追尋民族復(fù)興與同情泛亞解放的實(shí)踐之中,又能內(nèi)化到自身以南洋社會(huì)歷史作為運(yùn)作脈絡(luò)的人生觀與國際觀。
回顧歷史,嘉庚精神應(yīng)當(dāng)形成于歷史上那個(gè)令他痛心疾首的悲壯年代。《南僑回憶錄·弁言》曾這樣敘述:“我國各業(yè)既落后,洋貨復(fù)自由入口,滿清時(shí)每年已入超數(shù)萬萬元,民國光復(fù)至七七事變廿余年中,入超近百萬萬元。我國既不能出產(chǎn)金銀,其所以免致破產(chǎn)者,端賴海外華僑逐年外匯輸入現(xiàn)款二三萬萬元,故能抵塞漏卮。外國人以貨品出口換金錢,而我國則以華僑人身代之也。”*陳嘉庚.南僑回憶錄:上冊[M].美國:八方文化企業(yè)公司,嘉庚國際學(xué)會(huì),1993: 2.當(dāng)陳嘉庚撰寫《我國“行”的問題”》時(shí),他更是悲憤地指出:“自中外交通以來,政治腐敗,主權(quán)喪失,舶來品日來侵蝕,不但衣食住之物品源源輸入,而行所需要之舟車,竟完全倚靠外來物,或操于外人之手。”*陳嘉庚.我國“行”的問題[M].香港:嘉庚風(fēng)出版社,1946:1.
進(jìn)入21世紀(jì),嘉庚精神終于迎來了全新的歷史性變局。中華民族終于以現(xiàn)實(shí)的國際建設(shè),回應(yīng)了陳嘉庚在《南僑回憶錄》和《我國“行”的問題”》中的憂患意識(shí)。自陳嘉庚到印尼躲避日寇迫害70年以后的今天,習(xí)近平總書記于2013年10月正式訪問印尼,當(dāng)代中國終于向著陳嘉庚生前念念不忘的“南洋”,提出共圓“21世紀(jì)海上絲綢之路”的多邊合作戰(zhàn)略構(gòu)想。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jì),自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到2015年,在東北亞、中亞、南亞以及東南亞各國,已決定聯(lián)合修建公路通道13條、鐵路8條;另外,中國為推動(dòng)海上絲綢之路和自貿(mào)區(qū)建設(shè),已簽署涉及20個(gè)國家以及地區(qū)的14項(xiàng)自由貿(mào)易協(xié)定,正在談判的8項(xiàng)自貿(mào)協(xié)定又涉及22個(gè)國家;而到了2015年4月,中國倡建的亞投行已經(jīng)擁有57個(gè)會(huì)員國。*王紹森, 楊哲, 趙亞敏. “一帶一路”戰(zhàn)略下海上絲綢之路規(guī)劃思考[J].西部人居環(huán)境學(xué)刊,2016:16-19.陳嘉庚生前設(shè)想過的、未見實(shí)現(xiàn)的“泛亞洲”共同體,終于迎來了即將被后人全方位超越的歷史性機(jī)遇。
從公共外交的角度來看,公共外交有別于傳統(tǒng)外交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它雖是以國策為主導(dǎo),卻是通過國與國之間互相信賴的“第三方”作為溝通各方的載體。尤其伴隨著國際政治學(xué)界長期反思霸權(quán)政治和強(qiáng)權(quán)外交的潮流,當(dāng)代國際外交深受“新公共外交理論”(New Public Diplomacy)影響,從傳統(tǒng)政府外交轉(zhuǎn)變到多領(lǐng)域與多層次外交。而各國因此會(huì)更關(guān)注當(dāng)代涉及外交活動(dòng)的組織和個(gè)人,愈加重視運(yùn)用其中有利情勢,以國家文化歷史形象,配合民間組織、非政府組織及個(gè)人的影響力,潛移默化地發(fā)揮恰當(dāng)?shù)耐饨蛔饔谩?Melissen J Ed."Introduction"[M]//Melissen J Ed.The New Public Diplomacy: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asingstoke,UK:Palgrave Macmillan,2006.正如該學(xué)科的倡導(dǎo)者梅里森(Jan Melissen)所述,傳統(tǒng)外交更傾向于向他人宣揚(yáng)某種內(nèi)容,而公共外交最大的不同在于“聆聽”,從多方角度去持續(xù)“聆聽”對象國家,構(gòu)成整體外交運(yùn)作基礎(chǔ)。*Melissen J Ed.The New Public Diplomacy: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M]//Melissen J Ed.The New Public Diplomacy: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06:18.
基于南海各國公共外交層面的考量,且從南海到印度洋地區(qū)的思想文化交流始終是發(fā)展變化的。在昔日陳嘉庚發(fā)揮過影響力的南洋地區(qū),如何認(rèn)識(shí)與說明“嘉庚精神”就顯得尤為重要。在南洋地區(qū)的社會(huì)記憶中,“陳嘉庚”三個(gè)字曾經(jīng)為各方所熟知,不論是列強(qiáng)殖民政權(quán)、英美冷戰(zhàn)勢力、不同時(shí)代的各國政府,甚至華人社會(huì)不同政見陣營,都各自構(gòu)建過不同的“陳嘉庚”的歷史形象。自2015年10月以來,在海上絲綢之路涵蓋的區(qū)域,中國繼續(xù)闡釋“一帶一路”命運(yùn)共同體的重要性,而東盟十國也在2015年底簽署協(xié)議構(gòu)建“東盟區(qū)域一體化”。2016年2月4日,美國和日本等12國聯(lián)合簽署TPP協(xié)議。美國奧巴馬政府原來的設(shè)想,是要通過一系列新協(xié)議把全球重新納入由美國主導(dǎo)的國際新秩序,作為其中最重要一環(huán)的TPP協(xié)議當(dāng)中就包括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中的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文萊。在多邊互動(dòng)的形勢下,歷史上的南洋地區(qū)局勢的復(fù)雜性和敏感性日益凸顯。在“21世紀(jì)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中,談?wù)摦?dāng)?shù)厝A人和其他民族曾經(jīng)熟悉的陳嘉庚,不管涉及其歷史定位還是其時(shí)代價(jià)值,必然會(huì)聯(lián)系到南海各國對族群關(guān)系與國際關(guān)系的認(rèn)知。
由此可見,不論從正確理解歷史的角度, 還是從客觀審視陳嘉庚的定位如何影響中國、東盟和東盟內(nèi)部華人公民等三個(gè)層面關(guān)系的角度,從陳嘉庚人物研究到闡釋其精神影響,都不僅是其“落葉歸根”的中國故事,還可以是南洋各國華人支持參與反殖獨(dú)立進(jìn)程的本土故事。不論是各國、各地區(qū)關(guān)于陳嘉庚研究的各種議題、與陳嘉庚發(fā)生過歷史關(guān)系的組織、抑或是陳嘉庚歷史遺產(chǎn)的管理、研究與紀(jì)念單位,甚至包括批評反對陳嘉庚的組織及其言論,都可能形成各方的公共外交載體。亦即說,要從整體上關(guān)注這些研究、評價(jià)陳嘉庚的各種組織和個(gè)人以及他們的言論,因?yàn)樗麄兌伎赡馨缪菡婊蚍疵娴摹暗谌健苯巧?/p>
從更高的層面來看,公共外交不等同于單純的跨國社團(tuán)聯(lián)誼或者民間交流,其內(nèi)容的背后時(shí)常會(huì)有國策在主導(dǎo),當(dāng)然也包括以大眾熟悉的歷史文化議題去加強(qiáng)國與國的溝通,以贏得對象國家民眾的欣賞、理解與支持。走入陳嘉庚生前生活過的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各國,發(fā)掘嘉庚精神之中的國際主義內(nèi)涵,將可能有助于闡釋中華傳統(tǒng)中如何看待世界的人文理念。正如嘉庚精神中所蘊(yùn)含的他自小從祖先文化中傳承的民族觀與國際觀,包括他主動(dòng)由“推己及人”與“修己安人”到追求“天下為公”的思想理念,既體現(xiàn)在他主張同胞落地生根融入當(dāng)?shù)亟ㄔO(shè),也體現(xiàn)在他義無反顧支持各國反殖建國。這樣便足以通過典型人物為證:凡像陳嘉庚那樣誠心繼承和服膺祖先傳統(tǒng)的中華后裔,必定信仰世界大同,誠意與當(dāng)?shù)孛褡宄删兔\(yùn)共同體。因此,推動(dòng)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各國重新完整認(rèn)識(shí)在他們國家歷史上出現(xiàn)過的陳嘉庚,會(huì)有利于構(gòu)建國與國、民與民、族與族之間相互信任、相互尊重、榮辱與共的新歷史觀。
按照信息論的原理,信息之所在即實(shí)力之所在。各國之間的公共外交,如何于“我方”與“對象國家”之間布置與發(fā)展有效的交流載體是其基礎(chǔ),在此基礎(chǔ)之上方能通暢的發(fā)放信息和接收反饋。陳嘉庚作為一個(gè)在中國與南海周邊國家均有影響力的共同歷史人物,長期以來,各國對其評價(jià)各有不同。而陳嘉庚作為一個(gè)概念本身,其實(shí)質(zhì)是從中國到南洋華人,乃至于其他民族,所共有的跨國、跨族群認(rèn)識(shí)。由此而言,不同國家涉及紀(jì)念或研究陳嘉庚的組織或者個(gè)人,一旦發(fā)展成為常態(tài)的、長期的多邊交流,無形中自會(huì)形成中國與南海周邊各國的公共外交載體之一,成為各國政府和民間均可善加利用的溝通平臺(tái)。尤其是對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各國的華人更是意義非凡。一方面,各國華人擁有共同的文化淵源;另一方面,各國華人又在數(shù)代以來把血汗和記憶深耕在自己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對各自所在的國家有著深厚的主權(quán)意識(shí)與感情歸屬。所以,各國華人會(huì)自然而然的對中國和所在國擁有雙重的歸屬感,也就更衷心地寄望于中國與其所在國實(shí)現(xiàn)友好共贏,也更能勝任中國與各國交往過程當(dāng)中雙方均信任的協(xié)調(diào)者、說明者、聆聽者和轉(zhuǎn)述者。
各國對陳嘉庚的不同描述與定位,實(shí)際上也是各方互相溝通的載體。不論是為了撥亂反正錯(cuò)誤的歷史,還是為了更好地服務(wù)于公共外交,陳嘉庚生平歷史、思想與定位,固然不應(yīng)在他生前活動(dòng)和影響過的各國被淡忘或淡化,更應(yīng)當(dāng)使之有效地服務(wù)于南洋各國對中國和本國華人的再認(rèn)識(shí)。不管各方原來抱著什么目的討論和研究陳嘉庚,陳嘉庚三個(gè)字一旦涉及他在中國以外的歷史論述,客觀上也就有了影響公共外交的可能。
最后需要再次強(qiáng)調(diào)的是:陳嘉庚作為全體中華民族在近現(xiàn)代歷史上的代表人物,又是南海諸國現(xiàn)代史中無法回避的評價(jià)對象,嘉庚精神確有可能也應(yīng)該發(fā)展成為各國所共享的文化資源,使之有利于多邊公共外交向好發(fā)展。而嘉庚精神畢竟是源自中華傳統(tǒng)思想落實(shí)在當(dāng)年南洋情境的本土實(shí)踐,所以才會(huì)表達(dá)了民族觀相契于國際觀之“天下為公”的理念,也正是這一理念指引和推動(dòng)著陳嘉庚曾經(jīng)跨越國界、跨越族群地去支持亞洲各國的反殖運(yùn)動(dòng),也才會(huì)使之提出“泛亞共同體”這一高瞻遠(yuǎn)矚的倡議。時(shí)至今日,當(dāng)中國提出“21世紀(jì)海上絲綢之路”倡議并下定決心將其付諸于國際實(shí)踐的時(shí)候,就更有必要關(guān)注嘉庚精神中的這份思想遺產(chǎn),繼續(xù)發(fā)掘、解讀、闡釋和學(xué)習(xí)其中的歷史內(nèi)涵并以之啟示當(dāng)下,以期進(jìn)一步推動(dòng)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各國更積極地看待華人之思想傳統(tǒng),更深刻地理解中華文明從過去到現(xiàn)在、乃至將來對各國已經(jīng)、正在和必將做出的貢獻(xiàn)。
(編輯:孫國偉)
王琛發(fā):馬來西亞亞太研究會(huì)會(huì)長,馬來西亞道理書院院長,孝恩文化基金會(huì)執(zhí)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