驅(qū)逐、辯護(hù)還是監(jiān)督
——柏拉圖《理想國(guó)》詩(shī)學(xué)思想管窺
汪韶軍
(海南大學(xué) 人文傳播學(xué)院,海南 海口 570228)
驅(qū)逐、辯護(hù)還是監(jiān)督
——柏拉圖《理想國(guó)》詩(shī)學(xué)思想管窺
汪韶軍
(海南大學(xué) 人文傳播學(xué)院,海南 海口 570228)
摘要:圍繞柏拉圖對(duì)詩(shī)的態(tài)度,學(xué)界存在兩種對(duì)立觀點(diǎn):驅(qū)逐說(shuō)與辯護(hù)說(shuō)。但實(shí)際上,柏拉圖在這個(gè)問(wèn)題上看法是一貫的,并不存在矛盾之處。驅(qū)逐說(shuō)固然未能揭示柏拉圖詩(shī)學(xué)思想的真面目,“辯護(hù)”卻也不至于,稱(chēng)“監(jiān)督”則比較合適。柏拉圖要做的是本著真善美三位一體,對(duì)詩(shī)歌進(jìn)行“純凈化”。這是其以哲學(xué)指導(dǎo)政治之思路的延伸。
關(guān)鍵詞:柏拉圖詩(shī)學(xué);驅(qū)逐說(shuō);辯護(hù)說(shuō);監(jiān)督說(shuō)
在《理想國(guó)》里,柏拉圖嚴(yán)厲指責(zé)了詩(shī)歌,也對(duì)詩(shī)人下過(guò)逐客令,這使他成為詩(shī)學(xué)史上一個(gè)極富爭(zhēng)議性的人物。長(zhǎng)期以來(lái),人們一再征引卷三中的那段驅(qū)逐令,將柏拉圖詩(shī)學(xué)的這一面放大再放大,以至偏離了事實(shí)。近來(lái)有學(xué)者對(duì)柏拉圖詩(shī)學(xué)做了進(jìn)一步研究,如國(guó)外埃利阿斯(Julius A. Elias)著有《柏拉圖對(duì)詩(shī)的辯護(hù)》(Plato’sDefenseofPoetry)一書(shū),國(guó)內(nèi)王柯平先生亦作有《柏拉圖如何為詩(shī)辯護(hù)?》一文。面對(duì)同一文本,人們得出兩種截然相反的詮釋?zhuān)候?qū)逐與辯護(hù)。到底哪種看法更接近柏拉圖詩(shī)學(xué)思想的真面目?抑或是兩種看法都有值得商榷之處?筆者以為,柏拉圖固然沒(méi)有不分青紅皂白地把所有詩(shī)人都驅(qū)逐出去,卻也不存在為詩(shī)辯護(hù)的問(wèn)題,談不上什么直接辯護(hù)與間接辯護(hù)、強(qiáng)勢(shì)辯護(hù)與弱勢(shì)辯護(hù)。應(yīng)該說(shuō),他對(duì)詩(shī)的態(tài)度是一貫的,并不存在什么矛盾之處。柏拉圖只是想通過(guò)對(duì)詩(shī)的“純凈化”,使詩(shī)服務(wù)于理想國(guó)的建構(gòu),這可以說(shuō)是他用哲學(xué)來(lái)指導(dǎo)政治的延伸。
一、作為詩(shī)人哲學(xué)家的柏拉圖
柏拉圖是古今少有的詩(shī)人哲學(xué)家。哲學(xué)史家梯利(Frank Thilly)驚嘆道:“柏拉圖是一個(gè)詩(shī)人和神秘主義者,也是哲學(xué)家和論辯學(xué)家。他以罕見(jiàn)的程度把邏輯分析和抽象思維的巨大力量,同令人驚奇的詩(shī)意的想象和深邃的神秘感情結(jié)合起來(lái)。”*[美]梯利:《西方哲學(xué)史》,葛力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95年,第61頁(yè)。這一評(píng)價(jià)非常恰切。柏拉圖熟諳古希臘神話(huà)、史詩(shī)和悲劇,在論證自己的觀點(diǎn)時(shí),經(jīng)常從中旁征博引。埃利阿斯曾做過(guò)統(tǒng)計(jì),柏拉圖對(duì)話(huà)集中共引用荷馬史詩(shī)142處、赫西俄德史詩(shī)32處、品達(dá)頌詩(shī)13處,此外還有對(duì)埃斯庫(kù)羅斯等其他詩(shī)人的多處引用。*參見(jiàn)王柯平:《<理想國(guó)>的詩(shī)學(xué)研究》,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300頁(yè)。柏拉圖在《理想國(guó)》中對(duì)荷馬史詩(shī)也經(jīng)常信手拈來(lái),證明他對(duì)詩(shī)的驚人的熟悉程度。
柏拉圖早年喜愛(ài)詩(shī)歌和劇作,自己也寫(xiě)過(guò)悲劇和詩(shī)歌。水建馥先生所譯《古希臘抒情詩(shī)選》中收錄了3首柏拉圖的詩(shī)作。20歲時(shí),柏拉圖在蘇格拉底的影響下投身哲學(xué),將此前自己創(chuàng)作的劇本付之一炬。柏拉圖是出于一種高度的使命感和責(zé)任感,試圖通過(guò)哲學(xué)來(lái)改造政治,為全體公民謀求最大幸福,引領(lǐng)人們走出洞穴得見(jiàn)光明。這種對(duì)政治和道德的關(guān)注,使得對(duì)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和本體研究不再成為他的核心關(guān)切。他寧愿做詩(shī)人所贊頌的英雄,也不愿做贊頌英雄的詩(shī)人,但我們并不能就此說(shuō)他從此以后不愛(ài)詩(shī)。事實(shí)上,詩(shī)已經(jīng)浸入到他的骨子里,在他的哲學(xué)著作中以另一種形態(tài)延續(xù)著。
作為一名詩(shī)人哲學(xué)家,柏拉圖并不拒斥詩(shī)歌,他從未想過(guò)要壓抑自己的詩(shī)才。盡管在當(dāng)時(shí)有一場(chǎng)詩(shī)與哲學(xué)之爭(zhēng),柏拉圖站在哲學(xué)一邊對(duì)詩(shī)和詩(shī)人進(jìn)行了嚴(yán)厲批評(píng),但實(shí)際上,詩(shī)與哲學(xué)在他那里并非死敵,相反,他在深層次上將兩者融匯了起來(lái)。其對(duì)話(huà)體不僅是一流的哲學(xué)著作,也是一流的文學(xué)作品,可以說(shuō)是哲學(xué)與詩(shī)的奇妙化合體,達(dá)到了人所不及的境地。后世曾有人(如法國(guó)啟蒙思想家狄德羅)模仿此體裁,但遠(yuǎn)不如柏拉圖的精彩。趙敦華先生評(píng)價(jià)道:“柏拉圖的對(duì)話(huà)有很高的文學(xué)鑒賞價(jià)值,對(duì)話(huà)人物性格鮮明,場(chǎng)景生動(dòng),對(duì)話(huà)充滿(mǎn)情趣,嚴(yán)密的論證配以?xún)?yōu)美的語(yǔ)言,行云流水的雄辯夾雜著雋永的格言,達(dá)到了哲學(xué)與文學(xué)、邏輯與修辭的高度統(tǒng)一。”*趙敦華:《西方哲學(xué)通史》第1卷,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6年,第102頁(yè)。讀過(guò)柏拉圖對(duì)話(huà)錄的人,都會(huì)被那詩(shī)化的表述方式所感染。他喜歡引用和編造故事,善于用具體事例和象征、借喻的方式來(lái)說(shuō)明抽象的、難以表述清楚的哲學(xué)理論。《理想國(guó)》中的日喻、線喻、洞喻、床喻,《會(huì)飲篇》、《斐德羅篇》中愛(ài)的故事,《斐德羅篇》中的靈魂馬車(chē),這樣的例子在其著作中俯拾即是,所有這些都是那么引人入勝。《理想國(guó)》卷五中的“三個(gè)浪頭”,真可謂是一浪高過(guò)一浪,掀起了一次次的論辯高潮。當(dāng)然,柏拉圖并未采用詩(shī)的體裁、詩(shī)的格律,他是使詩(shī)為我所用,服務(wù)于哲學(xué)的表述,服務(wù)于理想國(guó)的建構(gòu)。
二、柏拉圖對(duì)詩(shī)的監(jiān)督
柏拉圖對(duì)詩(shī)的魔力有著深切感受,《伊安篇》533D-533E中的磁石說(shuō)就是對(duì)此做出的生動(dòng)描述*參見(jiàn)[古希臘]柏拉圖:《伊安篇》,王曉朝譯:《柏拉圖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4頁(yè)。。他認(rèn)為,在詩(shī)歌的長(zhǎng)期熏染下,人們會(huì)逐漸形成一種習(xí)慣,而習(xí)慣是人的第二天性,它會(huì)影響到人的一言一行,影響到人的言談思想方法。既然如此,一首“好”詩(shī)就有益于塑造美好的心靈,而一首“壞”詩(shī)也就會(huì)爆發(fā)出可怕的破壞力量。柏拉圖明白詩(shī)對(duì)心靈與性格塑造的重要性,所以他非常強(qiáng)調(diào)詩(shī)樂(lè)教育,把它列為“七科”之一,并時(shí)刻警惕著“壞”詩(shī)的負(fù)面效應(yīng)。
(一)卷三的“逐客令”
《理想國(guó)》卷三寫(xiě)道:“假定有人靠他一點(diǎn)聰明,能夠模仿一切,扮什么,像什么,光臨我們的城邦,朗誦詩(shī)篇,大顯身手,以為我們會(huì)向他拜倒致敬,稱(chēng)他是神圣的,了不起的,大受歡迎的人物了。與他愿望相反,我們會(huì)對(duì)他說(shuō),我們不能讓這種人到我們城邦城來(lái);法律不準(zhǔn)許這樣,這里沒(méi)有他的地位。我們將在他頭上涂以香油,飾以羊毛冠帶,送他到別的城邦去。至于我們,為了對(duì)自己有益,要作用較為嚴(yán)肅較為正派的詩(shī)人或講故事的人,模仿好人的語(yǔ)言,按照我們開(kāi)始立法時(shí)所定的規(guī)范來(lái)說(shuō)唱故事以教育戰(zhàn)士們。”*[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guó)》第3卷,郭斌和、張竹明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6年,第102頁(yè)。這就是人們一再征引的“逐客令”,我們可以從中抽繹出兩點(diǎn)。
其一,柏拉圖驅(qū)逐的只是某一類(lèi)外來(lái)詩(shī)人,并非不分青紅皂白地要把城邦里的所有詩(shī)人都掃除出去。柏拉圖認(rèn)為,每個(gè)人都有各自的自然稟賦,都應(yīng)該按其天賦集中畢生精力專(zhuān)門(mén)從事某一行業(yè),精益求精:“鞋匠總是鞋匠,并不在做鞋匠以外,還做舵工;農(nóng)夫總是農(nóng)夫,并不在做農(nóng)夫以外,還做法官;兵士總是兵士,并不在做兵士以外,還做商人,如此類(lèi)推。”*[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guó)》第3卷,第102頁(yè)。如果一個(gè)人什么都干,結(jié)果將是沒(méi)有一樣能干好。具體到詩(shī)歌領(lǐng)域,柏拉圖認(rèn)為,一位詩(shī)人或誦詩(shī)人無(wú)論如何也不能同時(shí)搞好兩種模仿,哪怕是很相近的兩種模仿,譬如悲劇與喜劇。而這里被驅(qū)逐詩(shī)人的一大特點(diǎn)就是模仿一切,為了能夠扮什么像什么,他們就得耍些小聰明以嘩眾取寵,而這是柏拉圖無(wú)法接受的。
其二,盡管柏拉圖一再貶低模仿,但詩(shī)人的模仿在他那里并非可有可無(wú)。柏拉圖在禁絕前述詩(shī)人的同時(shí),仍然強(qiáng)調(diào)要任用“較為嚴(yán)肅較為正派”的詩(shī)人,以模仿“好人”,導(dǎo)人向善。“逐客令”后面還有一大段類(lèi)似的話(huà):“我們要不要監(jiān)督他們,強(qiáng)迫他們?cè)谠?shī)篇里培植良好品格的形象,否則我們寧可不要有什么詩(shī)篇?我們要不要同樣地監(jiān)督其他的藝人,阻止他們不論在繪畫(huà)或雕刻作品里,還是建筑或任何藝術(shù)作品里描繪邪惡、放蕩、卑鄙、齷齪的壞精神?哪個(gè)藝人不肯服從,就不讓他在我們中間存在下去,否則我們的護(hù)衛(wèi)者從小就接觸罪惡的形象,耳濡目染,有如牛羊臥毒草中嘴嚼反芻,近墨者黑,不知不覺(jué)間心靈上便鑄成大錯(cuò)了。因此我們必須尋找一些藝人巨匠,用其大才美德,開(kāi)辟一條道路,使我們的年輕人由此而進(jìn),如入健康之鄉(xiāng);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聽(tīng)到的,藝術(shù)作品,隨處都是;使他們?nèi)缱猴L(fēng)如沾化雨,潛移默化,不知不覺(jué)之間受到熏陶,從童年時(shí),就和優(yōu)美、理智融合為一。”*[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guó)》第3卷,第107頁(yè)。可以看出,柏拉圖是要斬除腐蝕性的“毒草”,禁絕一切“邪惡、放蕩、卑鄙、齷齪”的東西,而留用追隨真善美的“鮮花”。正如梯利所言,柏拉圖“敵視一切卑下和庸俗的東西”*[美]梯利:《西方哲學(xué)史》,第61頁(yè)。。“寫(xiě)文章本身并沒(méi)有什么可恥的地方。……但是可恥地或邪惡地講話(huà)和寫(xiě)作,而不是像應(yīng)該做的那樣去講話(huà)和寫(xiě)作,我想這才是可恥的。”*[古希臘]柏拉圖:《斐德羅篇》,王曉朝譯:《柏拉圖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3-174頁(yè)。筆者認(rèn)為,《斐德羅篇》中的這段話(huà)道出了柏拉圖對(duì)詩(shī)的真實(shí)態(tài)度,即:他并不反對(duì)詩(shī)歌本身,而只是要求詩(shī)人盡其為人師的職責(zé),“為靈魂而歌唱”(《法律篇》),為理想國(guó)服務(wù);他并不反對(duì)模仿本身,而只是反對(duì)模仿和宣揚(yáng)非理性的東西。
(二)柏拉圖對(duì)詩(shī)歌的全面審查
由于“詩(shī)歌有三個(gè)組成部分——詞,和聲,節(jié)奏”*[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guó)》第3卷,第103頁(yè)。,柏拉圖便從內(nèi)容到形式,從講什么到怎么講,對(duì)詩(shī)歌進(jìn)行了全面審查:對(duì)過(guò)去的詩(shī)作進(jìn)行了刪削,對(duì)未來(lái)的詩(shī)作提出了一系列的規(guī)范。
怎么講?那種挽歌式、哭哭啼啼的調(diào)子和甜膩的、軟綿綿的靡靡之音,如伊奧尼亞調(diào)、呂底亞調(diào),必須徹底廢棄,因?yàn)樗鼈儠?huì)使人變得萎靡不振、軟弱消沉。而一剛一柔、模仿勇敢與節(jié)制的聲音,如多利亞調(diào)和弗里基亞調(diào),被留用了下來(lái)。
講什么?“我們首先要審查故事的編者,接受他們編得好的故事,而拒絕那些編得壞的故事。”*[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guó)》第2卷,郭斌和、張竹明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6年,第71頁(yè)。評(píng)判好與壞的標(biāo)準(zhǔn)是什么呢?著名美學(xué)家塔塔科維茲(Wladyslaw Tatarkiewicz)曾指出:“柏拉圖是著名的三位一體‘真、善、美’的創(chuàng)造者,它集中概括了最高的人類(lèi)價(jià)值。”*[波蘭]塔塔科維茲:《古代美學(xué)》,楊力譯,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90年,第151頁(yè)。柏拉圖正是本著真善美三位一體,要求美同時(shí)必須是真、善。以此為標(biāo)準(zhǔn),他對(duì)詩(shī)歌做出了取舍,凡是不真、不善的東西,都堅(jiān)決舍棄。
其一,詩(shī)必須真。
柏拉圖在本體論高度上,斷定“模仿術(shù)乃是低賤的父母所生的低賤的孩子”*[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guó)》第10卷,郭斌和、張竹明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6年,第401頁(yè)。。在《理想國(guó)》卷十中,他通過(guò)“床喻”貶低了詩(shī)的模仿,認(rèn)為詩(shī)是“摹仿的摹仿”、“影子的影子”,與真實(shí)隔著兩層。詩(shī)人制造的只是可感事物的影像,不能給人以真理和知識(shí),詩(shī)人所用的想象處于認(rèn)識(shí)的最低階段。“我們是不是可以肯定下來(lái):從荷馬以來(lái)所有的詩(shī)人都只是美德或自己制造的其它東西的影像的模仿者,他們完全不知道真實(shí)?”*[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guó)》第10卷,第396頁(yè)。可以說(shuō),柏拉圖在這里徹底否定了詩(shī)與真的聯(lián)系。在他看來(lái),詩(shī)人貌似無(wú)所不知,實(shí)則一無(wú)所知。他指責(zé)詩(shī)人只是“影像的模仿者”,而未做出一些實(shí)際的事務(wù),如救死扶傷、發(fā)明創(chuàng)造、指揮作戰(zhàn)、治理城邦、教育公民等等。他質(zhì)問(wèn)荷馬:“有哪一個(gè)城邦是因?yàn)槟愣恢卫砗昧说模袼拱瓦_(dá)因?yàn)橛腥R庫(kù)古,別的許多大小不等的城邦因?yàn)橛袆e的立法者那樣?有哪一個(gè)城邦把自己的大治說(shuō)成是因?yàn)槟闶撬麄兊膬?yōu)秀立法者,是你給他們?cè)旄5模俊?[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guó)》第10卷,第394-395頁(yè)。這是柏拉圖反復(fù)申說(shuō)的一個(gè)道理,在《伊安篇》中,他曾以駕車(chē)、治病、占卜等為例,說(shuō)明一個(gè)圈子的事情只有圈內(nèi)人士最在行,詩(shī)人或誦詩(shī)人不可能知道一切。在《斐德羅篇》中,他又根據(jù)靈魂觀照到“真實(shí)存在”的多少,將城邦公民分為九類(lèi):第一類(lèi)是“智慧或美的追求者”或“繆斯的追隨者和熱愛(ài)者”,而“詩(shī)人或其他模仿性的藝術(shù)家”則屈居第六類(lèi)。*參見(jiàn)[古希臘]柏拉圖:《斐德羅篇 》,王曉朝譯:《柏拉圖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2-163頁(yè)。然而,第六類(lèi)是否囊括了所有詩(shī)人?“繆斯的追隨者和熱愛(ài)者”中是否有詩(shī)人?這些都是問(wèn)題。第六類(lèi)中的詩(shī)人無(wú)疑是模仿性的、技藝性的詩(shī)人,但據(jù)柏拉圖的迷狂說(shuō)來(lái)看,這些詩(shī)人并非詩(shī)人的全部。柏拉圖似乎對(duì)模仿性的詩(shī)和詩(shī)人基本上持否定態(tài)度,但對(duì)迷狂的詩(shī)和詩(shī)人卻是非常推崇。陳中梅先生認(rèn)為:“并非每一位詩(shī)人都是兩度(或三度)離異于真理的卑劣的摹仿者”*陳中梅:《詩(shī)與哲學(xué)的結(jié)合》,《外國(guó)文學(xué)評(píng)論》1995年第4期,第119頁(yè)。,筆者以為,明確這一點(diǎn)非常重要。
盡管如此,柏拉圖在論述時(shí)很少做這種區(qū)分,從而給人一種全稱(chēng)判斷的錯(cuò)覺(jué)。他認(rèn)為,詩(shī)不僅不能給人以真理,而且撒謊。柏拉圖一再?gòu)?qiáng)調(diào),神只是好事物的原因,而不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好事物的原因只能是神。至于壞事物的原因,我們必須到別處去找,不能在神那兒找。”*[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guó)》第2卷,第75頁(yè)。這與他矢口否認(rèn)卑賤物、污穢物有相應(yīng)的理念是一個(gè)道理。柏拉圖認(rèn)為神如同理念,是盡善盡美的,永遠(yuǎn)自身同一的。可當(dāng)時(shí)的詩(shī)歌又是怎樣一種情形呢?在他看來(lái),許多詩(shī)句褻瀆了神明,沒(méi)有描繪出諸神與英雄的真實(shí)本性,反而把他們描寫(xiě)得丑惡不堪,比如說(shuō)他們明爭(zhēng)暗斗,貪財(cái)戀色,受情感的支使,時(shí)而唉聲嘆氣,時(shí)而大哭大笑,全然沒(méi)有神的尊嚴(yán)。而這是非常糟糕的,它們既不真也不善,非但不能使人敬畏神明,以之為楷模,反而給人們以托辭,以為既然神與英雄都這樣,凡人作惡又有什么要緊?柏拉圖在此似乎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對(duì)荷馬史詩(shī)、赫西俄德《神譜》等詩(shī)作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對(duì)其中所包含的古希臘神話(huà)的批判,而不是針對(duì)詩(shī)本身,其目的是要將一切擬人的成分從神性中驅(qū)除出去,以便為現(xiàn)實(shí)人生樹(shù)立一個(gè)個(gè)典范。我們知道,古希臘神話(huà)的一個(gè)重大特征是神人同形同性,即神具有與人相似的形體和七情六欲,也會(huì)干出偷盜、奸淫、爾虞我詐之類(lèi)的丑行。如果說(shuō)柏拉圖之前的愛(ài)利亞派哲學(xué)家克塞諾芬尼(Xenophanes)著重批判了神人同形觀,那么,柏拉圖就著重批判了神人同性觀。
其二,詩(shī)必須善。
如果說(shuō)詩(shī)對(duì)知識(shí)的獲得沒(méi)有多大價(jià)值和意義,那么,它對(duì)德性的培養(yǎng)卻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柏拉圖對(duì)其作用的討論涉及到他的靈魂學(xué)說(shuō)和正義說(shuō)。
柏拉圖把靈魂分為理性、激情和欲望三部分。按照他的“馬車(chē)之喻”,理性就是那個(gè)居于領(lǐng)導(dǎo)地位的駕車(chē)人,而激情和欲望則分別是拖著馬車(chē)跑的良馬和野馬,處于被領(lǐng)導(dǎo)地位。如果理性能發(fā)揮其作用,欲望簡(jiǎn)單而有分寸,領(lǐng)導(dǎo)著的領(lǐng)導(dǎo)著,被領(lǐng)導(dǎo)的被領(lǐng)導(dǎo)著,就能產(chǎn)生靈魂的四種德性——智慧、勇敢、節(jié)制、正義。相反,如果本應(yīng)俯首貼耳的部分起來(lái)造反,企圖在靈魂內(nèi)部取得生來(lái)就不屬于它的統(tǒng)治地位,那么這種僭越就將導(dǎo)致亂套、不正義。
柏拉圖對(duì)靈魂的三分無(wú)非是想把人性分為神性的和動(dòng)物性的兩個(gè)部分。他鄙視一切與感官、感性、肉體、欲望相關(guān)的東西,在他看來(lái),無(wú)論什么,只要一沾上感性,就變得不完美、不純粹而更為低級(jí)了。肉體對(duì)于靈魂來(lái)說(shuō),是一種障礙;靈魂附著肉體,就像河蚌困在蚌殼里一般。柏拉圖崇尚一種理智主義的幸福觀,認(rèn)為用理性指導(dǎo)一切行動(dòng)方為至善之道。他要求人們永遠(yuǎn)走向上的路,用靈魂的高貴部分統(tǒng)率低賤的部分,使自己成為自己的主人,而不要成為情感、欲望的奴隸。也就是說(shuō),城邦的所有公民(包括統(tǒng)治者)都要掙脫肉體的蒙蔽,禁絕肉體的快樂(lè),轉(zhuǎn)而去追求心靈的快樂(lè),去觀照理念世界的至善純美。在筆者看來(lái),《理想國(guó)》卷三末尾金銀銅鐵的故事主要也不是為了論證人間的等級(jí)秩序,而是通過(guò)譬喻,強(qiáng)調(diào)用理性來(lái)統(tǒng)率國(guó)家。他所說(shuō)的“上等人”、“下等人”,并不是從權(quán)勢(shì)地位上來(lái)區(qū)分的,而是就一個(gè)人身上理性成分的多少而言。柏拉圖強(qiáng)調(diào)服從統(tǒng)治者,實(shí)際上是服從理性的另一種說(shuō)法,即用理智和正確信念來(lái)指導(dǎo)情感和欲望。
柏拉圖將其靈魂學(xué)說(shuō)和正義說(shuō)貫徹到了詩(shī)學(xué)領(lǐng)域,認(rèn)為悲劇滿(mǎn)足了人們的感傷癖和哀憐癖,喜劇的插科打諢使人于不知不覺(jué)中變得像個(gè)小丑。總之,詩(shī)歌把靈魂的低劣成分激發(fā)、培育起來(lái),從而導(dǎo)致理性部分的毀滅:“在我們應(yīng)當(dāng)讓這些情感干枯而死時(shí)詩(shī)歌卻給它們澆水施肥。在我們應(yīng)當(dāng)統(tǒng)治它們,以便我們可以生活得更美好更幸福而不是更壞更可悲時(shí),詩(shī)歌卻讓它們確立起了對(duì)我們的統(tǒng)治。”*[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guó)》第10卷,第406頁(yè)。在柏拉圖看來(lái),一個(gè)人應(yīng)該時(shí)刻用理性克制自己,保持心靈的平靜。那些刺激性的、撓人心志的東西,無(wú)論如何都是不相宜的,都是必須擯棄的。
柏拉圖對(duì)詩(shī)的內(nèi)容和形式不僅定出了幾條原則性的東西,還做了許多細(xì)節(jié)規(guī)定,如要求詩(shī)人稱(chēng)贊地獄生活,不要把陰間描繪得那么陰森凄慘,以免使人產(chǎn)生恐懼怕死之情,以為好死不如賴(lài)活。柏拉圖認(rèn)為,這一點(diǎn)對(duì)城邦保衛(wèi)者的教育來(lái)說(shuō)顯得尤為重要。
(三)“理想國(guó)”中留用的詩(shī)作
可以這么說(shuō),柏拉圖的刪詩(shī)和逐客令恰恰從反面證明了他對(duì)詩(shī)歌功能的特別關(guān)注,因而籠統(tǒng)地說(shuō)柏拉圖驅(qū)逐詩(shī)人是有失偏頗的。與其使用“驅(qū)逐”一詞使人產(chǎn)生誤解,不如改用“監(jiān)督”更為確切。以荷馬史詩(shī)為例,盡管柏拉圖對(duì)它進(jìn)行了大力刪削,但他同時(shí)也承認(rèn),荷馬史詩(shī)中有許多東西值得贊美。《理想國(guó)》卷十稱(chēng)“我從小就對(duì)荷馬懷有一定的敬愛(ài)之心”*[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guó)》第10卷,第387頁(yè)。,在《伊安篇》中尊荷馬為“最偉大,最神圣的詩(shī)人”*[古希臘]柏拉圖:《柏拉圖文藝對(duì)話(huà)集》,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63年,第2頁(yè)。。事實(shí)上,柏拉圖認(rèn)為,德才兼?zhèn)涞脑?shī)人不僅不應(yīng)離開(kāi)城邦,而且應(yīng)該積極參與到城邦的道德教育中去,成為民眾的良師益友。詩(shī)歌作為一種“技藝”,與其它技藝一樣,在柏拉圖的理想國(guó)中有著它自己的位置,只不過(guò)它要服從哲學(xué)的指導(dǎo),否則又將導(dǎo)致“不正義”。
經(jīng)過(guò)柏拉圖的刪削,理想國(guó)中只剩歌頌神明和贊美好人的頌歌。正如柏拉圖心目中的“統(tǒng)治者”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統(tǒng)治者,他所留用的那些頌詩(shī)也并非通常意義上的為統(tǒng)治者歌功頌德的詩(shī)作。歸根結(jié)底,這類(lèi)詩(shī)作歌頌的是理性和由它帶來(lái)的四種德性。那么,這些留用的詩(shī)歌是否純是味同嚼蠟的道德說(shuō)教,還是同時(shí)兼具極高的審美價(jià)值?“如果他們能說(shuō)明詩(shī)歌不僅能令人愉快而且也有益,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詩(shī)于我們是有利的了。”*[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guó)》第10卷,第408頁(yè)。可見(jiàn),柏拉圖對(duì)詩(shī)的審美價(jià)值也沒(méi)有完全否定,詩(shī)歌給予人的審美愉悅在一定范圍內(nèi)還是被許可的。當(dāng)然,柏拉圖的主要標(biāo)準(zhǔn)還是“有益”。
三、結(jié)語(yǔ)
總體說(shuō)來(lái),柏拉圖對(duì)詩(shī)歌的態(tài)度是主張對(duì)其加以監(jiān)督;傳統(tǒng)的“驅(qū)逐說(shuō)”不符合事實(shí),后來(lái)的“辯護(hù)說(shuō)”也未能得其真。柏拉圖不是要“翻天”,而是要“補(bǔ)天”。他并不反對(duì)詩(shī)歌本身,他反對(duì)的是詩(shī)人忘卻自己的職責(zé),宣揚(yáng)一些不真亦不善的東西。柏拉圖的詩(shī)學(xué)主張?jiān)诟旧鲜菫槠淅硐雵?guó)中的道德教育服務(wù)的,他要求詩(shī)擔(dān)當(dāng)起責(zé)任和使命,起到一種有益于城邦管理與社會(huì)生活的教化作用。
應(yīng)該說(shuō),柏拉圖詩(shī)學(xué)中的認(rèn)識(shí)論原則和道德理想主義本身并沒(méi)有什么問(wèn)題,對(duì)詩(shī)歌的存在也不會(huì)構(gòu)成真正的威脅,因?yàn)檫@種思想原則無(wú)疑會(huì)減少空洞無(wú)物和藏污納垢之什。柏拉圖的偏頗之處在于,在他那里,詩(shī)與哲學(xué)的地位是不對(duì)等的,他強(qiáng)調(diào)哲學(xué)君臨于詩(shī)之上,用哲學(xué)來(lái)統(tǒng)攝詩(shī),這在實(shí)際操作過(guò)程中容易導(dǎo)致哲學(xué)對(duì)詩(shī)的吞并。真善美本是相互獨(dú)立的三大價(jià)值,但柏拉圖再三再四地強(qiáng)調(diào)詩(shī)必須真、詩(shī)必須善,卻很少提及詩(shī)必須美,美于是成了真與善的附庸和工具,詩(shī)歌本身的審美特性被冷落了。
(責(zé)任編輯:王學(xué)振)
An Analysis of the Poetics Idea in Plato’sTheRepublic
WANG Shao-j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Abstract:There exist two contradictory viewpoints on Plato’s attitude towards poetry—Banishment and Defense. In fact, Plato’s attitude in this aspect has been consistent rather than contradictory. Neither Banishment nor Defense can reveal the truth of Plato’s poetics idea which can be more properly referred to as “supervision”. What Plato really wants to do is to purify poetry based on the trinity of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which is an extension of his idea of directing politics through philosophy.
Key words:Plato’s poetics; banishment; defense; supervision
基金項(xiàng)目:海南大學(xué)“中西部高校綜合實(shí)力提升工程”子項(xiàng)目“海南文化軟實(shí)力科研創(chuàng)新團(tuán)隊(duì)”(編號(hào):01J1N10005003)
收稿日期:2015-12-10
作者簡(jiǎn)介:汪韶軍(1973-),男,浙江淳安人,哲學(xué)博士,海南大學(xué)人文傳播學(xué)院副教授,主要從事老莊哲學(xué)、魏晉玄學(xué)、禪宗、美學(xué)的研究。
中圖分類(lèi)號(hào):B502.232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674-5310(2016)-04-009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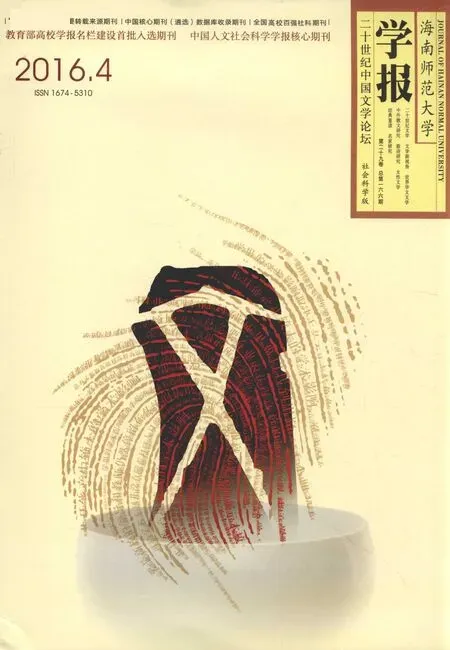 海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6年4期
海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6年4期
- 海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的其它文章
- 海南義務(wù)教育階段學(xué)生輟學(xué)的原因及對(duì)策研究
- 海南鄉(xiāng)鎮(zhèn)中學(xué)英語(yǔ)教師校本專(zhuān)業(yè)發(fā)展現(xiàn)狀的調(diào)查:制約因素與對(duì)策
- 基于語(yǔ)料庫(kù)探究“同志”的歷時(shí)演變
- 英語(yǔ)母語(yǔ)者漢語(yǔ)指示指稱(chēng)詞語(yǔ)習(xí)得近指和遠(yuǎn)指偏誤研究①
- 《橫沖直撞好萊塢》:“自我”在“他者”中的一次旅行
——從西方構(gòu)建的自我形象探討全球化的困境與立場(chǎng) - 現(xiàn)代電視與當(dāng)代說(shuō)唱藝術(shù)興衰
——以相聲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