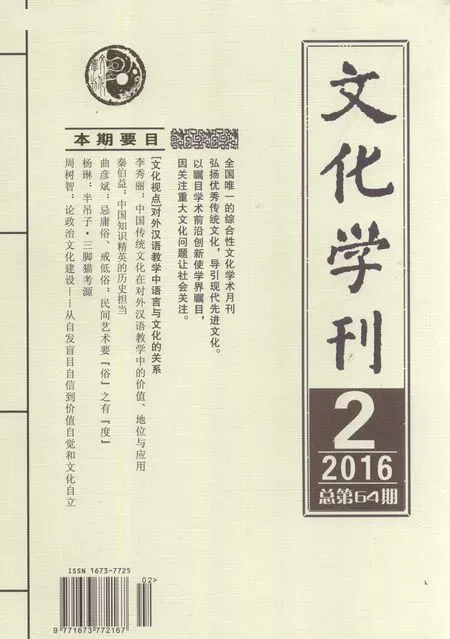唐代幽州城與桂州城營建格局初探
蔡宛平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北京 100048)
?
【文史論苑】
唐代幽州城與桂州城營建格局初探
蔡宛平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北京 100048)
唐代幽州與桂州行政位置相近,使得其城池營建格局具有可比性。在兩城城池營建方式、格局外圍建設等異同點的影響下,兩城的營建格局也具有相似之處和獨有的特點。一方面,兩城均是軍事重鎮,其共同的營建選址和不同的子城位置都對其軍事作用的發揮有重要影響;另一方面,兩城營建的地理位置一定程度上使兩城成為交通樞紐,但兩城的主要交通方式和城市格局開放程度存在差別,這對兩城日后交通的主要發展走勢和城市性質轉變產生影響。
唐代;幽州城;桂州城;營建格局
唐代幽州城(今北京)位于河朔三鎮最北端,是北方的軍事重鎮、交通中心。清代學者趙翼指出,唐代幽州是“東北之氣始興而未盛”[1]的時期。唐代桂州城(今廣西桂林)亦是嶺西(嶺南西道,主要為今廣西境內)地區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重鎮。研究唐代幽州城與桂州城的營建格局有利于對比了解唐代南北方城市建設格局、特點。這一研究有助于進一步研究整個唐代南北邊境地區歷史地理情況。然而,關于這方面的研究,國內外雖有很多成果,但仍略顯不足。
一、唐代幽州與桂州行政建置異同
唐代幽州是唐朝的北境門戶及戰略要地,唐朝統治者對此極為重視,唐初在此地設置級別較高的行政建置。武德元年(618)十二月,羅藝以幽州歸唐,唐高祖李淵置幽州總管府,以羅藝為幽州總管,治幽州薊城(今北京)。武德五年(622)八月升為大總管府;[2](又《舊唐書》卷39《地理志一》“幽州大都督府”條,記此事于武德六年(623),今從《通鑒》)武德七年(624)改總管府為都督府,幽州大總管府為大都督府;武德九年(626)改為都督府。及至中唐,隨著幽州地位的上升,其建置亦得到提升。唐玄宗開元年間(713-741)再升為大都督府,天寶元年(742)改稱范陽郡。(《舊唐書》卷9《玄宗紀下》載,唐玄宗天寶元年(724),詔“天下諸州改為郡”幽州改稱范陽郡。但唐肅宗乾元元年(758)恢復幽州舊稱。有唐一代政區雖屢有變遷,幽州一地卻皆以“幽州”為稱,因而文中所引之幽州涵蓋唐代整個幽州地區的建置[3])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復改范陽郡為幽州。自唐睿宗景云年間起,唐廷陸續給北、西邊境軍事重地的都督增加節度使的名號,以重其事權。幽州在唐玄宗時即設置范陽節度使,規制較為完備,統兵九萬一千四百人,馬六千五百匹。節度使所率經略軍駐扎在幽州城內。不難看出,幽州在唐代的建置變遷,多在總管府、都督府、大都督府級別范圍內波動。
桂州在唐代為西陲重鎮,統治者對其亦較為關注。宋人樂史編《太平寰宇記》載:“唐武德四年(621)平蕭銑,復置桂州總管府……天寶元年(742)改為始安郡,依舊都督府。至德二年(757)九月改為建陵郡。乾元元年(758)復為桂州,刺史充經略軍使。”[4]據此可知,唐代桂州行政建置一直位于總管府、都督府、經略軍使級別,并無較大波動。
由上可知,唐代的幽州與桂州的行政建置雖屢有波動,但皆為地方軍鎮都督府,統經略軍。依據唐制,地方上相同的行政建置,其所對應的治所所在城市的建城規模也有較為嚴格的規定。因而,唐代幽州與桂州行政建置的接近,也使唐代幽州城與桂州城的營建格局具有了可比性。
二、唐代幽州城與桂州城的城池營建
《舊唐書》稱:“自晉至隋,幽州刺史皆以薊為治所。”[5](東漢朱浮為幽州刺史時已治薊城,故應自東漢始。唐玄宗開元十八年(730),另置薊州(治今天津薊縣),此后多以“薊”專稱今天津薊縣地區,原幽州薊城則多稱幽州城)可見幽州城池營建歷史較為悠久,其應是在繼承原薊城的基礎上營建起來的,營建過程中原有城池的基礎占了較大比重。《太平寰宇記》引《郡國志》載:“薊城。郡國志云:‘薊城南北九里,東西七里,開十門。慕容儁鑄銅為馬,因名銅馬門。’今大廳前石函長二尺,高一尺,歷代不敢開,銘曰‘泰建元年造銅虎符’。”[6]由此可知,唐幽州城城池周三十二里,依每唐里約合今0.72里換算,約合今二十三里,是一座南北略長、東西略窄的長方形城市。雖然史料對唐代幽州城在唐時的擴建沒有過多記載,但從考古發現的資料中仍然可以確定,唐代幽州城在有唐一代曾有擴建。1929年,在今北京西城區二龍路教育部院內發現的仵氏墓志中記載,其墓位于“唐幽州城東北五里”。另《(光緒)順天府志》載,康熙年間,在西安門內發掘出的唐貞元十五年(799)卞氏墓志和在西四羊肉胡同發現的貞元六年(790)任氏墓志,各稱在唐幽州城東北五里或北五里。但前后兩批發掘出的地點相差較遠。可見唐幽州城的北城垣曾向外推進,這意味著城池曾經擴建,故可以推論,唐咸亨元年(675)至貞元六年(790)的120年間幽州城曾進行過擴建。
唐代桂州城由于唐以前長期的州治遷徙,未有建城,故而唐代為桂州城的建城之始。而唐桂州城的營建是通過一次基礎營建和二次大規模擴建完成的。首先,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李靖主持修筑桂州子城,號“始安郡城”(一稱衙城)。所修子城“在漓江西,周三里十八步,高一丈二尺。”[7](文為“周三十里十八步”,嘉靖本《廣西通志》卷39及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107皆為“周三里十八步”,據以校正)建成后的桂州子城不但是唐朝在嶺西地區重要的官署所在地,也是桂州第一個有詳細記載的城池。子城修成后多年間,桂州無大規模修筑城池,但仍時有小規模的修筑以滿足桂州城市發展需要。唐中宗景龍年間,時任桂州都督的王晙就進行過一定規模的城池修筑。《新唐書·王晙傳》載:“景龍末(710),(王晙)授桂州都督。州有兵,舊常仰餉衡、永,晙始筑羅郭,罷戍卒。”[8]此后,桂州城又歷了兩次大規模營建,一次是唐宣宗大中年間蔡襲(暫從)進行的大規模擴建。《(嘉慶)廣西通志》載:“外城,唐大中間蔡襲筑。周三十里(約合今16.2里),高三丈二尺。”[9]所筑之城為與宋代余靖所筑外城相區分,故后世志書多稱之為“古外城”。另一次是唐末僖宗光啟年間,在桂管觀察史陳環帶領下,進行了一次大規模擴建。唐人莫休符《桂林風土記》載:“夾城,從子城西北角二百步北上,抵伏波山,緣江南下,抵子城逍遙樓,周回六七里。光啟年中,前政陳太保可環剏造。”[10]據此可知,此次修筑是在城池以北增筑夾城。
唐代幽州城與桂州城最終皆成為氣勢恢弘的大城市,但其營建方式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幽州城是通過在原有較大規模城池基礎上擴建而成的,唐代桂州城則是通過由基礎營建到擴建來實現的。產生兩城間營建方式差異的原因是,桂州地處偏遠邊境,唐以前軍事地位較弱,開發程度較低,其城池營建跟不上中原的正常步伐。而幽州雖亦處邊境,但早先中原王朝曾多次與北境邊國發生戰爭,戰時則多以幽州為后方基地。如隋煬帝三次用兵高麗,都以涿郡(幽州)為基地,集結兵馬、軍器、糧儲。因此,幽州在唐以前就有較好的城池營建基礎。
唐代幽州城與桂州城雖然同為大規模城市,但其營建方式存在著一些異同點,這對其城池營建后所相應產生的軍事作用、交通地位有重要影響。
三、唐代幽州城與桂州城的營建及其軍事作用
唐代幽州“關山險峻,川澤流通,據天下之脊,控華夏之防,鉅勢強形,號稱天府”,[11]具有十分重要的軍事地位。《薊門紀亂》云:“史思明留駿馬百余匹在其廄中……每日則于桑干河飲之。通儒將入,潛令康孝忠以數十人持兵詣飲處,馳取其馬,閉于城南毗沙門神之院。”[12]毗沙門神在古代北方為隨軍護法、乞勝利之神。唐幽州城內置毗沙門神寺,說明其為北方的軍事重鎮。唐代幽州城也是唐廷在北方邊境重要的屯兵城市。《舊唐書》稱:“范陽節度使,理幽州……經略軍,在幽州城內,管軍三萬人,馬五千四百匹。”[13]足見其屯兵之盛。為便于屯兵和官署治理,唐代幽州城內建有子城。唐會昌六年(846)采師倫《重藏舍利記》云:“智泉寺……子城東門東百余步,大衢之北面也。”[14](這證明唐代幽州城內有子城。子城位于城之西南隅,依傍幽州城西、城南垣而建,為官署衙門所在,唐代幽州都督、范陽節度使的治所均在子城內。同時,子城又是城內主要的屯兵場所。唐貞觀十八年(644)出兵高句麗,分水陸兩路,陸路即以幽州為后方大本營,集結兵馬、軍器、糧儲。唐中期,安祿山以幽州為基礎,發動“安史之亂”,動搖唐朝根基。《讀史方輿紀要》云:“唐之中葉,漁陽倡亂,藩鎮之患,實與唐室相終始。”[15]
唐代桂州,從整個唐朝版圖看,“東控海嶺,右扼蠻荒”[16],是扼湘桂走廊西南出入口,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顧氏在《讀史方輿紀要》中道:“乾符三年(875)黃巢自桂州出湘水,至湖南,遂為中原大禍。”[17]強調了桂州對唐末中原大禍的引發作用,可見唐時桂州有較大的軍事作用。桂州城亦是唐朝在嶺西地區的重要屯兵城市。《舊唐書·王晙傳》載:“景龍末(710),(王晙)累轉為桂州都督。桂州舊有屯兵,常運衡、永等州糧以饋之……奏罷屯兵及轉運。”[18]桂州本身的糧餉不足以屯兵之用,因而常用水路從湖南等地運糧補濟,這說明其長期以來皆為屯兵之所,且屯兵人數很多。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19]即使在戰事緊急時,唐廷也很重視留兵屯守桂州。另外,桂州也是嶺西地區主要的發兵城市。較小規模的叛亂一般情況下僅靠從桂州所發之兵便可平定。唐太宗貞觀十二年(638)“鈞州獠反;遣桂州都督張寶德討平之”,[20]即為此例。而當規模較大,需要多地區協從作戰時,桂州也是嶺西地區首選的發兵城市。唐懿宗咸通二年(861),南詔攻邕州,唐廷敕“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州”,[21]其余城市則多按兵不動。
唐代幽州城與桂州城均是軍事重鎮,然而其營建格局上一些異同點對其軍事作用的提升有重要影響。首先,唐代幽州城與桂州城,其城池營建選址均極適合屯兵。史載,唐雖多次與北方邊國發生戰亂,但幽州城多次逃過劫難,不僅展現了其城池防御能力,也增加了統治者在此屯兵的安全感。同樣,桂州城的營建選址也使之得以避免成為西南吐蕃、南詔等少數民族政權進攻的前沿城市,較好地避免城池因戰亂而毀壞,從而保證其所駐兵士與所屯糧草的安全。唐中后期,南詔、吐蕃等南疆少數民族多次攻唐,但沒有一次將戰火直接燒到桂州城下。而與桂州一樣同為嶺西地區重鎮,但位置較為偏南的邕州則有不一樣的遭遇。唐末,邕州多次被南詔圍攻洗劫,以致城市破敗,滿目瘡痍,最后“時南詔知邕州空竭,不復入寇”。[22]
可見,唐代幽州城與桂州城這種營建選址上的共同點,促使兩城成為南北重要的軍事屯兵重鎮。
其次,雖然兩城皆為重要的軍事屯兵城市,其子城皆為重要屯兵之所,但城池營建格局中子城所選位置差異較為明顯。幽州城營建時,將子城建于城池西南隅;而桂州城營建時,將子城建于城池中央東面。這與兩城在唐王朝的地理位置和軍事職能有關。一方面,幽州城相對唐都長安、洛陽偏東北,若將子城官署建于城西南,東北敵人入城時可起緩沖作用,還可為與唐都和南方中原溝通提供便利。而桂州城相對唐都偏西南,桂州城交通以城東南北縱橫的河流為主,將子城建于城東,可方便出城溝通南北。另一方面,幽州城的軍事職能,除屯兵外,還有戰時集結兵馬的作用。幽州地處唐朝東北,需向西南方才能集結兵馬,故而將子城建在西南隅。桂州城軍事職能則主要為屯兵和發兵,子城建于東面可更好地發揮其職能。
由上可得,唐幽州城與桂州城在唐代皆為重要的軍事重鎮,兩城的城池營建格局中,子城位置雖有差別,但都適應各自地理位置和軍事作用發揮的需求,對兩城軍事作用的發揮提供了幫助。
四、唐代幽州城與桂州城的營建及其交通地位
幽州城營建選址原本便扼唐朝疆域東北咽喉,南下直入中原,北上直通渤海國,是河北平原北端陸路交通的樞紐。入隋后更是增加水運優勢。《隋書·閻毗傳》載:“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于涿郡(唐幽州城,隋設為涿郡),以通運漕。”[23]此渠即為永濟渠。隋大業四年(608)開,引沁水南通黃河,北達幽州,此后運河上常“舳艫相次千余里”。該渠鑿通,使幽州成為南北大運河的北部終點,往南經水路可直達洛陽、杭州,幽州從此成為北方水陸交通的中心。
對桂州來說,自秦始皇修靈渠連接湘、漓以來,自湘江南下過靈渠入漓水的“湘桂走廊”成為嶺西地區溝通中原地區的重要通道。唐代將桂州城筑于靈渠以南的漓江西岸,扼湘桂走廊的西南出入口。這使之得以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交通網。于東北方向,有直達西京長安、東京洛陽的交通線路;于東南方,開辟有至廣州、廉州的交通經路;此外,還開辟出了與周邊其他地區的交通線路。《資治通鑒·唐紀十一》載:“(太宗貞觀十三年)六月,渝人侯弘仁自牂柯(今貴州境內)開道,經西趙出邕州,以通交、桂,蠻、俚降者二萬八千戶。”[24]此路開通后,自桂州出,過相思埭,經柳江、融江,到邕州,再經西趙,便可到達渝州。完善的交通網得以建立后,桂州城逐漸成為嶺西地區的交通中心。
唐代幽州城與桂州城均建在南北、東西交通的重要位置,使兩城確立了交通樞紐城市的地位,但兩城的城市交通格局也存在著一些差異。
首先,唐代幽州城交通是以陸路交通為主,而桂州則以水路交通為主。這一差異是受其城池營建固有的區位條件影響所形成的。一方面,幽州城地處北方,河流較少,主要以陸路交通為主,幽州雖因有運河而得以增加水運優勢,但運河非天然河流,其水量、運向等皆有較為嚴格的限制,這是不可消除的阻礙。而桂州地處南方,河流眾多,四通八達,桂州所依賴的運輸河流除靈渠外皆為天然河流,水量大、流向縱橫南北,水運較為便利。另一方面,幽州地處平原,地勢較為平坦,使用陸路行馬路程短直。而桂州雖地處平坦之地,然南北皆為群山包圍,陸路行馬路程較遠并曲折。兩城主要交通方式的差別對其日后交通的主要發展走勢產生影響。
其次,唐代幽州城與桂州城城池營建目的雖均帶有較濃的軍事色彩,但幽州城因為與邊患之地距離更近,常有戰事發生,所以城池營建格局較為封閉,防守意味濃厚。從考古發掘看,唐代幽州城城墻較高,城墻上雉堞、馬面等一應俱全。此外,唐代嚴禁夜行,“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25]幽州城對這一規定更為嚴格。
而桂州離邊患常發之地尚有一定距離,且其周邊有大量的風景名勝可供游覽,因此其城池營建格局并非典型軍事重鎮那般封閉,而是相對比較開放。其子城城墻僅高“一丈二尺”,于一個軍事重鎮而言,這并不算高。另外,漓江東岸的雉山崖壁有題名記曰:“自逍遙樓出桂江,泛舟至雉山觀巖洞。微雨不可登絕頂,沂流過壽寧,復還逍遙樓置酒。”[26]作為桂州城主要城門的東江門,不但經常洞門大開,讓外出、歸來的游人穿行其中;且作為東江門城樓的逍遙樓,也成為官員文人的晏飲之所,可見其營建格局中保留了較大的開放空間。這種相對開放的城市環境十分有利于桂州城池交通吞吐能力的提升和交通容納力的提高。
綜上,幽州城防守意味較濃的營建格局對其鞏固交通優勢,吸納各方資源和保障城市安全產生影響。桂州城較為開放的城市格局則有力地促進其周邊風景名勝的開發和提高其交通容納力。此后,隨著兩城這一格局差別不斷發展,幽州逐漸成為莊嚴的政治中心,而桂州則逐漸成為詩意的游覽、文化勝地。
五、結語
唐代幽州城與桂州城兩城的營建格局具有相似之處和獨有的特點。其一,營建后的唐代幽州城與桂州城均是軍事重鎮,但其共同的營建選址和不同的子城位置都對其軍事作用發揮有重要影響;其二,兩城營建的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兩城交通樞紐城市的地位,但兩城的城市交通格局亦存在著主要交通方式和城市格局開放程度的差別,而這將分別影響兩城日后交通的發展走勢和城市性質轉變。
[1]趙翼.二十二史札記[M].北京:中國書店,1987.276.
[2][12][19][20][21][22][24]司馬光.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56.5953.7109.8102.6141.8095.8110.6148.
[3][5][13][18]劉昫.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215.1516.1387.2985.
[4][6]樂史.太平寰宇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7.1399.1399.
[7][9]謝啟昆.嘉慶廣西通志[A].續修四庫全書:第680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89.289.
[8]歐陽修.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4154.
[10]莫休符.桂林風土記[A].張智.中國風土志叢刊:第53冊[M].揚州:廣陵書社,2003.22.
[11][15][17]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M].賀次君,校.北京:中華書局,2005.440.440.4813.
[14]于敏中.日下舊聞考[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981.
[16]白居易.嚴謨授桂管觀察使制[A].祝穆,祝洙.方輿勝覽:第38卷[M].北京:中華書局,2003.683.
[23]魏征,顏師古,孔穎達等.隋書[Z].北京:中華書局,1973.1595.
[25]長孫無忌.唐律疏議[M].北京:中華書局,1983.489.
[26]汪森.粵西叢載校注(上冊)[M].黃振中,校注.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2007.56.
【責任編輯:王 崇】
2015-11-25
蔡宛平(1989-),女,廣西河池人,主要從事城市與區域歷史地理研究。
K901.4
A
1673-7725(2016)02-02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