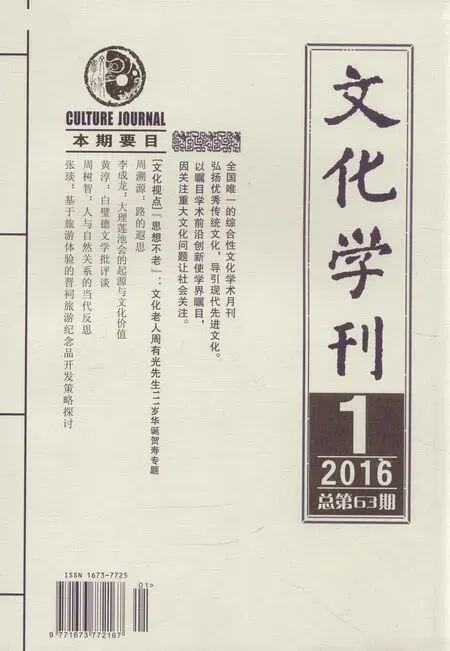當代中國少女文本“瑪麗蘇”現象的意識形態剖析
孫穎睿 史 萌
(華中師范大學,湖北 武漢 430079)
?
【文學評論】
當代中國少女文本“瑪麗蘇”現象的意識形態剖析
孫穎睿 史 萌
(華中師范大學,湖北 武漢 430079)
“瑪麗蘇”一詞譯介自域外,并在意義上產生了一定的變異。在中國,它指各媒介文本中一個處于中心的吸引力和影響力過分強大的女性角色。這類文本的創作主體和接受對象主要是少女,其中包含了一種由少女參與、為少女專門建構的意識形態,兜售女性氣質、強調愛情本位和歌頌女性美德。“瑪麗蘇”文本實際上是由在日常中接受了男權意識形態的少女用男性氣質話語,以一種看似以女性為中心、實際上仍屈從男權的理念的創作建構起來的。
瑪麗蘇;少女文本;意識形態
近年,“瑪麗蘇”一詞在我國網絡文學圈及影視圈中無人不曉。人們已習慣性地以諷刺和貶低的意味,用“瑪麗蘇”來形容那些文學或影視作品中人見人愛、過分強大的女主角。“瑪麗蘇”一詞也逐漸由一類女性角色的代名詞演變為概括某些作品類別的形容詞(如“瑪麗蘇文”“瑪麗蘇劇”),并正逐漸形成一種具有一定特征的新興文化現象。“瑪麗蘇”文本由少女創作,閱讀者也主要是少女。作為一種少女觀念的集合,它在少女的閱讀實踐中產生了意識形態的力量,實際上承載著對父權制社會實踐和意識形態的推崇。本文試圖從女性主義的立場出發,對“瑪麗蘇”文化現象進行深入分析,揭示其意識形態本質及其所建構的少女對象的特點。
一、少女意識形態的傳播和變異
“瑪麗蘇”原文“Mary Sue”,是作家寶拉·史密斯1973年發表在同人雜志*同人文或同人小說是指利用原有的漫畫、動畫、小說、影視作品中人物角色、故事情節或者背景設定的基礎進行的再創作。同人雜志即刊載同人文的雜志。The Menagerie上的《星際迷航》同人文A Trekkie’s Tale中的一個角色。這篇《星際迷航》的同人小說在原作故事背景基礎之上集合了大量自我意淫的元素,塑造出一個原作中本不存在的完美女性“瑪麗蘇”作為小說的主人公。在受到讀者廣泛關注之后,“Mary Sue”一詞便逐漸成為一類具有相似特征的女主角的代名詞。她以不可阻擋之勢在文學和影視圈內滲透,也逐漸被傳播至除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
“瑪麗蘇”一詞雖于21世紀才由國外譯介而來,但含有“瑪麗蘇”元素的小說在中國卻早已可見。從20世紀席卷文壇的瓊瑤小說,到20世紀末開始興起的網絡小說,再到21世紀初的青春文學,在“瑪麗蘇”一詞得以在中國大規模傳播并成為一種現象之前,“瑪麗蘇”便蟄伏于中國通俗文壇,而并非是純粹的舶來品。正是由于其由來已久,因此“瑪麗蘇”一詞才在中國得以廣泛傳播,進而成為一種文學類型,成為一種隱蔽而強大的意識形態建構的代名詞。“瑪麗蘇”一詞也在這樣的建構中被不斷更新著意義。在歐美,“瑪麗蘇”一詞通常僅用于指稱同人小說(Fan Fiction)中的完美女主角,而中國的“瑪麗蘇”并不強調其主角來自同人小說的特性,其文本性質更類似于范圍稍廣的言情小說(Romantic Novel)。當歐美“瑪麗蘇”小說因其同人性質而面臨難以實體化的危機時,“瑪麗蘇”小說中的優秀者則被出版*已被實體化實的瑪麗蘇小說如《步步驚心》(桐華2005年版權屬于起點中文網)、《傾世皇妃》(慕容湮兒2008年版權屬于起點女生網)、《甄嬛傳》(流瀲紫2007年版權屬于晉江文學網)等。,甚至還不斷以改編的形式被搬上熒幕*《宮鎖心玉》 2011年1月播出于視湖南衛視《金鷹獨播劇場》首播期間平均收視率2.49%,位居年度第二;《步步驚心》于2011年9月湖南衛視首播,前六集平均收視率超過1.56%,位居同時段第一位。,從而獲得了更廣泛的受眾。中國“瑪麗蘇”文本種類的擴充以及傳播媒介的豐富使得閱讀群體和意識形態的影響范圍由此擴大。
更重要的是,文本的中心,“瑪麗蘇”的特征也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轉變。作為作者理想形象的投射,“瑪麗蘇”在誕生之初本是十全十美的。美國網民于2011年5月在書評博客“佐伊的修辭(The Zoe-Trope)”上對“瑪麗蘇”角色特征進行了討論:*http://thezoe-trope.blogspot.com/2011/08/you-can-stuff-your-mary-sue-where-sun.html.他們認為“瑪麗蘇”是一個“沒有什么明顯缺陷的角色”,在情節的發展中“沒有什么進步、變化或成長”。但在中國,并不完美的“瑪麗蘇”經過重重磨難,最終成長為更完美的女性的故事,已成為“瑪麗蘇”小說的典范類型。由“瑪麗蘇”概念從西到中傳播中的穩定和變異,我們可以給當代中國的流行詞“瑪麗蘇”下一個定義:各媒介文本中一個處于中心的、吸引力和影響力過分強大的女性角色。亦可用于指稱一種含有此類女性角色的文本類型。
從完美到不完美,從定型化到成長型角色的改變,打破了“瑪麗蘇”形象單一的現狀,某些時候甚至給文本蒙上了勵志的面紗。這就給這類小說在接受上提供了合法性,使這種帶有男權色彩的意識形態更具有復雜性和迷惑性。
二、為少女建構的意識形態
從閱讀體驗中我們可以看出,“瑪麗蘇”文本由少女創作,專為少女設計,與少女的知識和文化價值觀念在最大程度上一致。無論是古代宮廷還是現代都市,科幻世界還是靈異空間,都很少見到超出少女閱讀習慣或理解力的經驗。不同于學校的推薦讀物,少女閱讀這類作品幾乎遇不到任何困難。不僅如此,“瑪麗蘇”小說的價值觀念幾乎從不與少女的價值觀產生沖突:愛情是美好的;男女關系必須有深厚的精神聯系而不僅僅訴諸肉體,女孩應該是機智或單純的,而男孩應該富有“男子氣概”,等等。這就使“瑪麗蘇”文本在少女群體中具有極大的易讀性,從而使其在閱讀中獲得巨大的滿足感,進而為接受這種意識形態提供了可能。
一旦少女進入故事情節(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她們幾乎全都將自己“代入”小說塑造的角色中。這種“代入”指的是將文本中不同特質的女性角色認同為理想的自我的過程,通過這種“代入”,少女們便毫無困難地獲得小說中“瑪麗蘇”角色的生活經驗,通過逐愛、斗惡、成名等一系列情節獲得成功的快感,而不必去冒失敗的風險。即使“代入”的角色死去,少女們還可以從其他人的敘述中感受到自己在道德上占據了高地。
易讀性和快感機制使少女們深深陷入“瑪麗蘇”的世界。全媒體閱讀時代,閱讀空間為少女們建構了一個完整無缺的烏托邦,面對網頁、書架甚至電視,少女們幾乎可以找到在任何地點發生的“瑪麗蘇”故事,如學校、街頭、公司……現實就這樣被一張巨大的幻想之網,也是意識形態的陰影所籠罩。“瑪麗蘇”文本的烏托邦敘事有其現實根源,正如塔尼亞·莫德萊斯基所說:“閱讀言情小說的過程既包含了對真實困境的表達,又體現著對真實困境的抗爭。”[1]創作和閱讀“瑪麗蘇”小說的少女們通過“代入”,不僅體驗著與現實迥異的空間,獲得新奇的知識;還釋放著萌芽而被壓抑的情感需要。她們通過創作和閱讀拒斥著枯燥的學生生活和貧乏的情感世界,隱秘地抒發對現實的不滿。在這種抵抗之中,現實生活的煩悶壓抑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化為烏有。
當少女對世界不完整的感知與專為這種感知所設定的虛擬的意識形態相遇,她們的視野便有可能被簡單化了的“現實世界”和兩性沖突所遮蔽。這樣,少女們既無法獲得現實世界相對完整的經驗,更加無法建設真正的屬于女性的烏托邦。這種快感是替代性的、暫時的,將少女理解和反抗社會的可能被白日夢式的幻想帶來的滿足感打斷。更甚者,這為少女進一步接受父權意識形態的建構準備了條件。
三、被意識形態建構的少女
上文提到,無論是在少女的價值觀念還是“瑪麗蘇”文本里,女孩被認為應是“機智或單純的”。實際上,多數“瑪麗蘇”小說中的正面女性角色基本都逃不出這個套路。此外,她們還必須有較為出眾的外表(無論這種外表是先天具有的還是通過小說的發展而形成的),或者是其他受人稱贊的美德等,這就使“少女”真正成為了一種被建構的意識形態,而在這種意識形態的內部,她們的形象是同質化的。阿爾都塞認為,意識形態具有將“個體”建設為“對象”的功能[2],而這些少女正是被“瑪麗蘇”文本背后強大的觀念變為了合適的受眾,她們在思想和實踐上都將受到影響。在“瑪麗蘇”文本中,“少女”這一意識形態是由在日常中接受了男權意識形態的少女,用男性氣質話語,以一種看似以女性為中心、實際上仍屈從于男權社會的理念的創作建構起來的。它的主要表現有三點:
(一)兜售“女性氣質”。我們在“瑪麗蘇”小說中很容易讀解出其預設的“女性氣質”標準:以完美型少女為主角的“瑪麗蘇”小說(一般是早期的“瑪麗蘇”小說)里通常都包含著大量的外貌描寫。作者不厭其煩地贊美著女主角美麗的面龐,優雅的姿態,落落大方的言談,這些描寫的一致程度令人吃驚,也令人感到無聊。與之相對應,不完美的少女通常以單純甚至愚蠢的姿態出現,用不諳世事的純潔打動男性的心靈,仿佛女性除了美麗,就只有笨拙一條路可以走了。通過強調這種“美麗或單純”的女性氣質,“瑪麗蘇”小說以男性美學的標準來塑造模范女性,模糊了少女之間的差異,強化了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偏見和個性壓抑。
(二)強調愛情本位。間接或直接以女主角愛情的發展為線索,將愛情置于生活的首位是“瑪麗蘇”小說的核心標志之一。創作主體將擁有眾多優秀男性的愛作為女主人公重要、主要乃至唯一的人生目的,相當數量的作家甚至直接將小說終止于完美愛情達成的瞬間。這種將女性的人生目標,至少是人生目標的一大部分局限為獲得配偶的行為,為少女在今后的成長中依附男性制造了合法性。雖然創作主體時常試圖讓主人公發出人格獨立、要求尊嚴與自由的聲音,但這種聲音的傳達在大多數情況下達到了吸引男性的目的,這種意圖并非主人公的本意,但無疑是出于創作者的主觀意念。也就是說,在這些創作者的潛意識里,要求獨立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吸引男性。這種“獨立的聲音”在“瑪麗蘇”小說里被大規模地復制著,將愛情至上的內核被女性自尊的假象包裝起來。
(三)歌頌女性“美德”。出于自戀和代償心理,“瑪麗蘇”們被塑造成為在道德上完美無瑕的人。她們永遠占據著道德制高點,在大多數文本中,女主角也正是因此而獲得了心儀對象的青睞。這無疑簡單化了倫理與社會關系的內涵。不僅如此,在遭遇突發狀況時,“瑪麗蘇”們總會走上以德報怨的道路,甚至走向犧牲自己成全他人的極端。在悲劇和不公面前,“瑪麗蘇”們選擇隱忍,在艱難的選擇面前,小說更從未按照女性的本來面目感同身受地去描寫,而是樹立了一個類似“圣母”的符號。這不僅給少女們設定了過高的道德門檻,也讓大眾(包括女性自己)對女性產生不切實際的道德期待。這無疑使女性陷入了更不利的境地。
如網絡評論所說的,閱讀者在獲得快感的同時,也確實獲得了力量——一種在現實中成為相似的角色的愿望。無論少女的本來狀況如何,她們都渴望成為同質化的“瑪麗蘇”,因為她們在文本中得到了一種虛假的許諾:只要這樣,我就能過上與她一樣的生活。它起到的是一種類似阿多諾和霍克海默提出的“社會黏合劑”的作用,使少女在心理上適應社會對女性或單一或高尚的要求,并以之作為判斷自己和他人行為的標準。這種以男權優勢話語塑造出的新時代的“天使”,使“美麗”與“美德”的少女意識形態深入人心,滲透到少女的生活中,為他們成為男性美學中“真正的女性”作準備。
作為一種由國外傳入卻早已萌芽于中國傳統文化深處的新興文化現象,“瑪麗蘇”的崛起是必然也是偶然。扎根于傳統文化的、在當代社會仍具有廣泛而深刻影響的男權意識,加上高速發展的經濟造成的人們對物欲和性欲的盲目追求,以及精神上的恍惚與缺失感:當代中國社會已儼然成為培養這種文學模式的沃土。正如《美好而不真實——瑪麗蘇的150年》(Too good to be true——150 years of Mary Sue)中所說:“‘瑪麗蘇’是一個作者在寫作上邁出的第一步”,[3]“瑪麗蘇”是所有作者們極易塑造出的也是極易吸引眼球的一類角色。在易造和易讀的前提下,涉世未深的少女們無形中成了男權意識形態建構的同謀。少女們有自行選擇閱讀對象的權利,但當大量此類帶有極重男權意識形態的文化產品在文化市場攻城略地之時,所創造的讀者和引發的反應應引起我們的警惕。
[1]TaniaModleski.Loving with a Vengeance:Mass Produced Fantasies For oman[M].Connecticut:Archon Books,1982.47.
[2]阿爾都塞.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A].圖繪意識形態[M].孟登迎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168.
[3]Pat Pflieger. Too Good To Be True: 150 Years of Mary Sue [J], American Speech, 2001, 11.
【責任編輯:董麗娟】
I207.42
A
1673-7725(2016)01-0070-04
2015-10-25
孫穎睿(1995-),女,山東濟南人,主要從事歐美文學與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