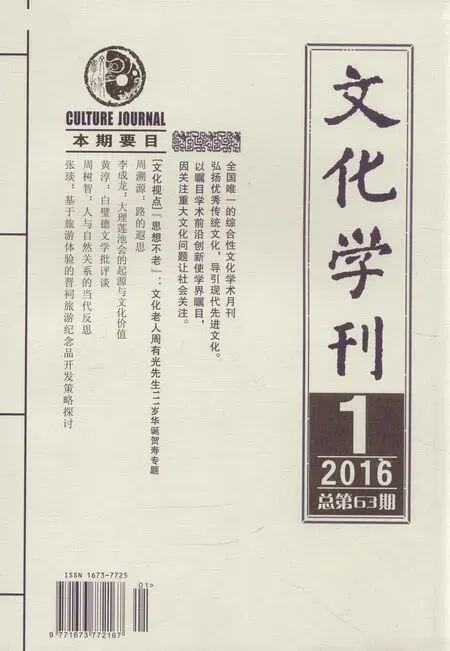殷人之天帝觀與王權意識的發展
李 莉
(河南大學,河南 開封 475000)
?
【文史論苑】
殷人之天帝觀與王權意識的發展
李 莉
(河南大學,河南 開封 475000)
任何一個政權的建立都離不開對權力來源的闡發,而且無不把王權合法性的依據訴諸天命。天命與王權相系始自三代,特別是殷商,在當時的認知能力下,似乎只有宗教神學方能解答其代夏而立的正當性,同時也開啟了天命王權的歷史篇章。本文主要就殷人天帝觀及其王權意識的發展展開論述。
殷商;天命;帝;貞人;王權
殷商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正式以戰爭形式推翻前朝而建立的國家政權。夏至十四代王孔甲轉入衰敗期,至十七代王桀,更加暴虐,百姓怨聲載道。商部落首領成湯看到桀無道,欲伐之。在戰前誓師大會上,商湯宣稱,“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1]以天命號召民眾反抗夏桀,為權力更替找到了合法性依據,開啟后世“暴力革命”獲取政權的先例。
一、殷人天帝觀
殷人以“帝”代天,郭沫若認為,殷商卜辭中稱至上神為帝,絕不稱天。[2]侯外廬亦認為,殷人所崇拜的不是一般上帝,也不是所謂的“天”,而是“祖先=上帝”的宗教形態。[3]陳家夢提出異議,“殷人的上帝或帝,是掌管自然天象的主宰,有一個以日月風雨為其臣工使者的帝庭……先公先王可賓于天,上帝對時王可以降福禍,示諾否,但上帝與人王并無血緣關系。”[4]帝可以像君王一樣發號施令,祖先是帝廷的臣工,上帝通過祖先傳達意愿。任繼愈也認為,殷人是祖宗神與天神分離的二元神崇拜。[5]劉澤華站在歷史發展的角度,認為商朝中期以前是二元神分離期,晚期才形成上帝和祖宗一元神的信仰。
以上學者似乎都忽視了對商的人文分析。《禮記·表記》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可見,“尊神”是一種全民行為,且非一神,而是多神崇拜。陳家夢將殷人的神靈觀分為三類:天神、地示、人鬼,[6]掌管自然界的神被殷人稱為“帝”,管理人類世界的神也被稱為“帝”,顯然殷人的神靈觀有兩個系統,一個是主宰自然現象的虛擬的神靈,一個是與人王有血緣關系的祖先神靈,這兩種神靈都是商王統治的正當性來源。前者掌管天庭的各路神,后者管理人間的社會秩序,馬克思說,“宗教本身是沒有內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間。”[7]普列漢諾夫也說,“人是社會環境的一個產物,至于神靈,是人按照自己的模樣造出來的。”[8]殷人比擬人王與臣下的關系,虛構了與天神之間的等級關系。
總之,“帝”概念的產生,是殷商社會階級差距加大的結果,是殷商王權進一步發展的結果。
二、殷人王權意識的發展
民族神的興衰通常與這個民族的命運相系。殷朝的建立是在征服其他部落的基礎上,從一個游牧部落發展為定居于中原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強大部落。而帝概念的出現,正反映了殷民族統一戰爭的勝利,王權進一步得到提升的事實。大體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考察。
一方面,占卜權力的轉移。商朝前期的占卜由貞人與商王共同完成,貞人負責向神靈詢問吉兇禍福,充當與神靈交流的中介人,王則是貞人卜問后的發布者或決斷者,如武丁卜辭:
壬子卜爭貞我其王乍邑帝弗左,若。
癸丑卜爭貞勿王乍邑帝若。
丙寅卜古,王告取若。古固曰:若,往。[9]
自貞,王曰ㄓ孕女力。日大曰:女力。[10]
前兩條意思是,貞人不贊同修筑城邑。[11]后兩條表明貞人也有發布占卜的權力。由此可見,王此時尚未完全掌控神權。相反,貞人不但是神意的傳達者,還有顯赫的地位。晁福林認為,貞人為各族首領。[12]學者牛長立在對黃國進行考察時發現,有些卜辭就有記錄黃王派遣貞人在殷商王朝供職的事實。[13]丁山考證出,祖甲時貞人“先”即祖甲之子廩辛,他有時會代王而卜。[14]據《史記·殷本紀》言,“契為子姓,其后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在商王朝的發展之路上,諸侯表現出不同的態度,如湯時“諸侯畢服,湯乃踐天子之位”,太甲時“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雍己時“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太戊時“殷復興,諸侯歸之”,中丁以后“比九世亂,于是諸侯莫朝”,盤庚時“殷道復興,諸侯來朝”。貞人一面是王的宗族,與王有一定的血親關系,另一面又是方國首領,自然不會絕對服從于商王。還有一部分貞人仍未與商融合,他們之所以擔任貞人之職,與后世封王即任中央朝廷要職,又有封國為食邑相類似。
但是,在殷商中后期,貞人地位呈下降趨勢,神權隨即被王完全掌握。董作賓在為甲骨文作分期考察時指出,商后期出現了大批沒有記刻貞人名字的卜辭,甚至帝乙和帝辛還親自擔任貞人之職。[15]與貞人地位下降相反的是太史寮職位的上升,他們開始從幕后記錄祭祀活動或搜集、整理相關歷史資料的工作中走出來,公開參與祭祀活動并主持祭祀和占卜。陳家夢曾就商末卜辭中習見的“工典”做過考證,“乙辛周祭卜辭于每一祭季完畢之時即有工典執行一種儀式,此工典亦可能是為一官名。”[16]此外,從卜問內容看,前期以軍政大事為主,后期則是王為己行的占卜內容。簡言之,王與貞人之間的矛盾,也可以說是王權與族權之間的斗爭,王最終剝奪了神職人員對神的專享權,將神權整合于王權之中,王權與神權合二為一。
祖先神靈最后與帝的結合,也是殷人日益發展的王權觀念的集中表現。劉澤華指出,在商前期,帝與祖先表現為二元關系,直到晚期才出現帝祖合一的現象。[17]“祖先”本身就是血緣觀念的產物,借祖先與后世子孫之間的生理性血緣聯系,最大限度地發揮祖先神彌合族類差別的作用。后世子孫在遠眺同一祖先時,潛在的政治功利是借祭祀祖先的功績以加強共同血緣觀念,鞏固以血緣為基礎的共同體內部的團結,增強社會凝聚力。因為生理性血緣關系,就會存在遠近親疏之別,必然會催生出嫡庶觀念,進而服務于王權意識,以解決權力繼承問題,同時也是宗法制度確立的必要前提。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祖先崇拜能體現出權力傳承的威嚴與秩序,壟斷祭祀話語權,是最高統治者對他族進行精神羈縻的王權政治主題,而“王”則是這一神權內核的起點。那么,把王權歸于帝旨,神化王權,商王不僅要奪取貞人的占卜權,還要提升本族祖先神靈的地位,故編造了許多上帝立商的神話,鼓吹祖先就是上帝的子孫,試圖從血緣上找到商王獨享天命的權威性依據。所以,盤庚能理直氣壯地宣稱自己受天命和祖先之命實施刑罰,還將國家治理不好的罪責攬于己身。同樣,巫祝向神祗“請示”,再也不是原初單純地揣測神意,更增加了對王心意的窺測,與其說是“神判”,不如說是一定意義上的“王判”。
三、結論
殷人尚鬼、崇鬼、信鬼、戀鬼,對神靈過分依賴,使整個社會充斥著濃厚的宗教神學味道。受神之擺布,確切說是貞人之擺布,即使君王也要“聽令”于貞人。這是因為貞人與商王有一定的血緣關系,他們受封于王畿以外的方國,具備一定的軍事力量,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能與王抗衡。當商王對貞人獨擅天帝意志越發不滿時,實際也是表明對王權尚未真正達到至尊的不滿,于是王與貞人之間不時爆發激烈的矛盾,甚或以武力解決。直到商晚期,與帝溝通的神權完全為王所有,才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神權與王權合一,為后世王權神授觀奠定基礎。
[1]孔丘.尚書·湯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1.
[2][5]郭沫若.青銅時代[A].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21.
[3]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68.
[4]陳來.古代宗教與倫理[M].北京:三聯書店,2009.111.
[6]陳家夢.殷墟卜辭綜述[M].北京:中華書局,1988.561.
[7]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436.
[8]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2卷)[M].劉若水,譯.北京:三聯出版社,1961.76.
[9]明義士.殷墟卜辭[M].上海:別發洋行出版社,1917.124.
[10]商承祚.殷墟遺存[M].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1981.586.
[11]張秉權.殷墟文字丙編[M].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8.147.
[12]李雪山.商代封國方國及其制度研究[D].鄭州:鄭州大學,2001.
[13]牛長立.黃國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0.
[14]丁山.商周史料考證[M].北京:中華書局,1988.147.
[15]董作賓.中國考古學報第四冊·殷墟文字乙序[M].臺灣: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49.280.
[16]陳家夢.殷墟卜辭綜述[M].北京:中華書局,1988.519.
[17]劉澤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2.
【責任編輯:王 崇】
B968
A
1673-7725(2016)01-0199-03
2015-10-15
李莉(1976-),女,河南開封人,博士,主要從事中國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