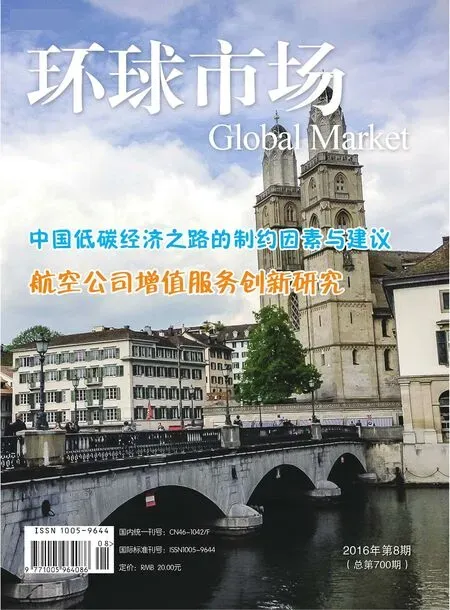高考對社會流動性的影響研究
——以北京大學(xué)和中國政法大學(xué)數(shù)據(jù)(1978-2008)為例的量化分析
楊濟(jì)菡 張春華 高 璇 齊媛媛
中國政法大學(xué)商學(xué)院2015級
高考對社會流動性的影響研究
——以北京大學(xué)和中國政法大學(xué)數(shù)據(jù)(1978-2008)為例的量化分析
楊濟(jì)菡 張春華 高 璇 齊媛媛
中國政法大學(xué)商學(xué)院2015級
本文以北大和政法大學(xué)的學(xué)生數(shù)據(jù)統(tǒng)計(jì)分析高考對社會流動性的影響,結(jié)果表明,高考制度的恢復(fù)使得高等精英教育生源出現(xiàn)了多樣化,打破了以往被上層子女壟斷的現(xiàn)象,提供了社會流動的機(jī)會。
高考、社會流動性、量化分析
一、文獻(xiàn)綜述
從古至今,教育以及與教育相關(guān)的考試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都影響社會的流動性。以往學(xué)者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三個(gè)方面,一是考試制度對社會流動性的影響,二是家庭背景對教育的影響,三是教育水平對社會流動性的影響。科舉制度的設(shè)立和取消都對社會流動有著重要的影響。在《Family v s.Meri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 》一書中,克拉克教授對宋朝中國家庭背景和科舉考試成功者的關(guān)系研究表明科舉考試制度對于打破社會分層,促進(jìn)社會流動方面有著積極的意義。新中國建國以后,高考制度的恢復(fù)在極大程度上提高了各階層的流動性。梁晨,李中清在《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xué)與蘇州大學(xué)學(xué)生社會來源研究(1952-2002)》(2012)一文中得出統(tǒng)一的高考招生制度,高等教育生源的多樣化以及重點(diǎn)中學(xué)制度的設(shè)置提高了工農(nóng)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促進(jìn)了社會的流動性。家庭背景對教育產(chǎn)生影響的一個(gè)重要方面主要是家庭經(jīng)濟(jì)條件對于教育資源可獲取的差異,針對這點(diǎn),李力行,周廣肅在《代際傳遞、社會流動性及其變化趨勢——來自收入、職業(yè)、教育、政治身份的多角度分析》(2014)中研究發(fā)現(xiàn)父親的收入對子女的收入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教育是社會流動的動力機(jī)制,教育機(jī)會以及教育選拔機(jī)制被認(rèn)為是社會經(jīng)濟(jì)分化最重要的機(jī)制。周作宇在《教育、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2011)一文中指出,考試能促進(jìn)合理的社會流動,而教育又有助于考試的成功,因此教育本身也可以成為社會流動的必要條件。針對教育是如何對社會流動性產(chǎn)生影響,楊鳳英在《教育影響社會分層的原因和條件》(2007)一文中表明,教育通過提供文化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網(wǎng)絡(luò)資本影響社會成員的職業(yè)選擇,影響社會成員收入的多寡和穩(wěn)定性,因此教育是影響社會流動的重要變量。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學(xué)者的主要關(guān)注考試制度本身對社會流動的作用、缺少教育系統(tǒng)內(nèi)各地區(qū)資源分布、家庭的經(jīng)濟(jì)收入等更具體因素對社會流動性的影響分析;其次,絕大部分對于教育考試,流動性的分析采用的仍然是綜合定性分析的方法。
二、研究數(shù)據(jù)介紹
本文以北京大學(xué)和中國政法大學(xué)學(xué)生的資料作為研究資料,分析整個(gè)高考制度對社會流動性的影響。北大的數(shù)據(jù)分析結(jié)果參考李中清《無聲的革命》,政法大學(xué)數(shù)據(jù)我們通過政法大學(xué)各地的校友會,采用調(diào)查問卷的形式收集78-08級入學(xué)學(xué)生的資料,在學(xué)生檔案不一定可以獲取的情況下,通過校友會的方式收集數(shù)據(jù)是可取的,同時(shí)資料也是可信的。這些問卷數(shù)據(jù)提供了詳盡的學(xué)生家庭住址、民族性別、父母的職業(yè)構(gòu)成、家庭經(jīng)濟(jì)收入的變化、畢業(yè)高中學(xué)校信息,這些信息為分析學(xué)生群體的家庭的社會階層屬性、地域來源等提供了堅(jiān)實(shí)的保證。
在共收上來的408份問卷中,男性校友占比56.86%,女性校友占比43.14%。被調(diào)查者的民族分布也很廣泛,其中漢族占絕大多數(shù),占比達(dá)到88%,少數(shù)民族中維吾爾族、回族、哈薩克族數(shù)量稍多。他們的生源地也非常廣泛,覆蓋了每一個(gè)省,雖然不排除發(fā)放問卷的時(shí)候存在區(qū)域扎堆的現(xiàn)象,但是,數(shù)據(jù)涉及面相對來說比較廣。
三、研究發(fā)現(xiàn)
我們將學(xué)生來源分為東、中、西部,分別考察重點(diǎn)中學(xué)和職業(yè)背景對入學(xué)人數(shù)的影響。因此,該問題的解釋變量是1978--2008年進(jìn)入政法大學(xué)的分別來自東、中、西部地區(qū)的入學(xué)人數(shù) ;解釋變量依次是學(xué)生是否來自重點(diǎn)中學(xué)以及父親的職業(yè)背景。
1.重點(diǎn)中學(xué)對東部、中部、西部學(xué)生入學(xué)影響
建立方程:yt=βH+ε,通過對數(shù)據(jù)進(jìn)行分類整理,用SPSS軟件進(jìn)行回歸得出結(jié)果方程,y=1.1H+3.29,回歸方程顯著值為0.000<0.005,在95%置信度下,我們拒絕原假設(shè),即重點(diǎn)中學(xué)對東部入學(xué)人數(shù)存在影響。同理,建立重點(diǎn)中學(xué)對中部入學(xué)影響的回歸方程:y=1.114H+4.036;重點(diǎn)中學(xué)對西部入學(xué)影響的回歸方程:y=1.152H+0.937。從以上模型中,我們可以看出,重點(diǎn)中學(xué)對東、中、西部入學(xué)人數(shù)存在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這表明重點(diǎn)中學(xué)影響這學(xué)生的入學(xué),且對西部地區(qū)的影響最為明顯。
北大的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中,可以得出其學(xué)生主要來源于重點(diǎn)中學(xué),偶爾提供學(xué)生的普通中學(xué)其地理分布非常集中,比如就普通中學(xué)而言,生源主要集中在北京。越是不發(fā)達(dá)的地方,重點(diǎn)中學(xué)越是重要。
2.父母的職業(yè)背景對東、中、西部學(xué)生入學(xué)的影響
將父親的職業(yè)分為四大部分:農(nóng)林牧漁水利生產(chǎn)人員和國家機(jī)關(guān)(H)、黨群機(jī)關(guān)和企事業(yè)單位負(fù)責(zé)人(G)、商業(yè)服務(wù)人員(S)、專業(yè)技術(shù)人員四部分(Z),建立方程:y=a1H+a2G+a3S+a4Z+ε,通過對數(shù)據(jù)進(jìn)行分類整理,用SPSS軟件進(jìn)行回歸得出西部地區(qū)父親職業(yè)背景對學(xué)生入學(xué)影響結(jié)果方程:y=-8.19H+10.667G+7.865S+2.132Z-4.617,顯著性水平都為0.000<0.005,拒絕原假設(shè),即父親的職業(yè)對入學(xué)率有影響。而且從中我們看出,在西部地區(qū),農(nóng)林牧漁水利生產(chǎn)人員這種職業(yè)對升學(xué)率的影響為負(fù),這說明,農(nóng)林牧漁水利生產(chǎn)人員這種從事第一產(chǎn)業(yè)的人員可能收入不穩(wěn)定,在某種程度上影響教育的獲得,而黨群機(jī)關(guān)和企事業(yè)單位負(fù)責(zé)人員對子女教育獲得的影響最為顯著。但是東部和中部地區(qū)得出的模型不能通過顯著性的檢驗(yàn)。
北大的數(shù)據(jù)表明,在改革開放以前,父親從事農(nóng)林牧漁的學(xué)生占比最少;改革開放以后,雖然干部子女比例增長;專業(yè)技術(shù)人員子女從1990年代中期以后開始下滑,工人和農(nóng)民所占的比重平均達(dá)到總?cè)藬?shù)的30%以上。從兩個(gè)學(xué)校的數(shù)據(jù)可見,在中國,父親職業(yè)對子女教育的影響較小,高考制度削弱了父母職業(yè)對子女教育的影響,提供了社會流動的機(jī)會。
四、結(jié)論
通過對兩個(gè)學(xué)校學(xué)生資料的分析,本文以為,高考制度恢復(fù)之后,打破了以往高等教育為社會上層子女所壟斷的現(xiàn)象,各個(gè)階層的子女均由機(jī)會接受精英教育。首先,重點(diǎn)中學(xué)對偏遠(yuǎn)地區(qū)學(xué)子上大學(xué)起到了積極的促進(jìn)作用,在很大程度上為他們上一流大學(xué)提供了平臺;其次,父輩的職業(yè)并不是影響子女教育獲得的重要因素,工農(nóng)子女在學(xué)生中的占比有所上升,這說明高考制度為各個(gè)階層的后代提供了向上流動的機(jī)會。
[1]梁晨,李中清,張浩,李蘭,阮丹青,康文林,楊善華.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xué)與蘇州大學(xué)學(xué)生社會來源研究(1952—2002)[J].中國社會科學(xué),2012
本成果獲得中國政法大學(xué)研究生創(chuàng)新基金資助(2015SSCX180),文章有所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