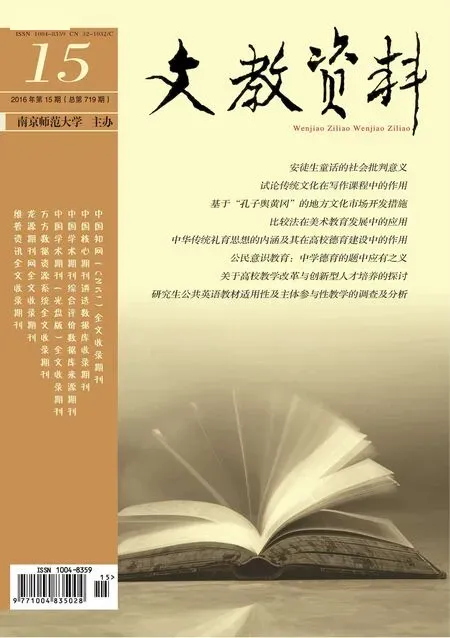霍夫曼恐怖小說(shuō)與蒲松齡《聊齋志異》中的詭異主題
李香
(浙江越秀外國(guó)語(yǔ)學(xué)院,浙江 紹興 312000;上海外國(guó)語(yǔ)大學(xué),上海 200000)
霍夫曼恐怖小說(shuō)與蒲松齡《聊齋志異》中的詭異主題
李香
(浙江越秀外國(guó)語(yǔ)學(xué)院,浙江 紹興312000;上海外國(guó)語(yǔ)大學(xué),上海200000)
德國(guó)浪漫派后期代表人物霍夫曼和中國(guó)志異作家蒲松齡都以描繪荒誕離奇的詭異世界而著稱(chēng)。他們的作品讓人毛骨悚然,不戰(zhàn)而栗。作者旨在分析恐怖小說(shuō)和聊齋小說(shuō)詭異主題的基礎(chǔ)上,展現(xiàn)其創(chuàng)作手法背后的中西方文學(xué)思想和文化傳統(tǒng)的不同影響。
詭異主題多重人格《聊齋志異》
E·T·A霍夫曼(1776-1822)是德國(guó)浪漫派后期,對(duì)后世有重要影響的人物之一。幾百年以后他的作品還是不斷地被人們重新閱讀、闡釋?zhuān)鹑藗児缠Q。中國(guó)文學(xué)史上的志怪小說(shuō)大師蒲松齡在描寫(xiě)詭異題材時(shí)絲毫不比霍夫曼遜色。《聊齋志異》中的孤魂野鬼、悍婦、人鬼相戀等也讓人毛骨悚然,不戰(zhàn)而栗。在鬼怪離奇的世界里,難以分清現(xiàn)實(shí)和虛幻。德國(guó)著名作家黑塞曾將霍夫曼的藝術(shù)童話(huà)和蒲松齡的聊齋小說(shuō)做了簡(jiǎn)單比較,指出他們之間的相似之處就在于“人類(lèi)與鬼神世界沒(méi)有明顯的區(qū)分;鬼怪們大都在白天活動(dòng),并且與人類(lèi)在相互愛(ài)慕和友好的氣氛中密切往來(lái)”。我旨在分析恐怖小說(shuō)和聊齋小說(shuō)詭異主題的基礎(chǔ)上,展現(xiàn)其創(chuàng)作手法背后的中西方文學(xué)思想和文化傳統(tǒng)的不同影響。
一、E·T·A霍夫曼和蒲松齡詭異主題描寫(xiě)上的相同點(diǎn)
霍夫曼和蒲松齡這兩位作家有一個(gè)最大的共同點(diǎn),他們都是志異小說(shuō)家。他們的小說(shuō),都以神秘的故事為題材,描繪神奇的魔法,變換的世界,互相轉(zhuǎn)化的人、動(dòng)物和植物,談狐說(shuō)鬼,談妖道異。在這兩位作家的筆下,世界都具有雙重性,它既是現(xiàn)實(shí)存在的日常生活場(chǎng)景,又隨時(shí)會(huì)發(fā)生意想不到的變化,展現(xiàn)出變幻莫測(cè)的幻景,在魔法的作用下處處都有奇跡。
《侏儒查赫斯》中描寫(xiě)了容貌丑陋、性情詭異的小查赫斯,由于仙女對(duì)他的憐愛(ài),在仙女魔力的幫助下被賦予了一種神奇的魔力,之后他開(kāi)始改名為齊恩諾貝,魔力的作用使他當(dāng)上了國(guó)務(wù)總理,過(guò)上了高貴甚至不可一世的生活。這番梳理能解除任何企圖破壞這種魔法的行動(dòng)。《金罐》中的那個(gè)又老又丑的賣(mài)蘋(píng)果的女人,她時(shí)而是戶(hù)籍官家里漂亮的銅門(mén)環(huán),時(shí)而是討厭的算命者老埃林夫人,時(shí)而是女主人親愛(ài)的保姆老麗莎。神秘的宮廷戶(hù)籍官林特霍爾斯的小女兒塞彭蒂娜竟然能化身成一條小蛇,用她銅鈴般的歌聲吸引了主人公安澤爾穆斯。這些匪夷所思的魔法卻都那么自然而然地出現(xiàn)在霍夫曼的故事里,讓讀者沉迷在這魔法的世界里。
蒲松齡《聊齋志異》中的主人公也是魔法超群。狐通過(guò)修煉,化身為擁有美麗迷人外表的狐女。嬌娜“嬌波流慧,細(xì)柳生姿”;青鳳“弱態(tài)生嬌,人間無(wú)其麗也”,蓮香“傾國(guó)之姝”;嬰寧“容華絕代,笑容可掬”,等等。她們或有不沾塵俗的天真之美,或有大家閨秀的端莊之美,或有坊間妓女的風(fēng)流曼妙之美。此外,狐女還有把荒野變庭院的法力。作者用歡快的筆調(diào),描寫(xiě)了狐女?huà)雽幧畹牡胤绞前策m自然、幽潔可愛(ài)的鄉(xiāng)居雅舍,雖然真實(shí)的場(chǎng)景是“廬舍全無(wú),山花零落”的荒郊野外,但是在法術(shù)的作用下,我們看到的是人間生活的溫馨家園。
此外,除了題材的巧合外,霍夫曼和蒲松齡還有許多息息相通的地方。首先,他們的作品都帶著現(xiàn)實(shí)色彩及民眾的氣息。就像海涅說(shuō)的,霍夫曼雖然描繪了無(wú)數(shù)“千奇百怪的鬼臉,卻始終牢牢地依附著人間的現(xiàn)實(shí)”。蒲松齡設(shè)茶煙于道旁,邀路人談,收集了大量民間傳說(shuō),再加以修飾改寫(xiě),匯成一部以唐傳奇筆法寫(xiě)成的文言小說(shuō)集,一改魏晉以來(lái)筆記體文言小說(shuō)質(zhì)樸簡(jiǎn)略刻板的文風(fēng),文筆生動(dòng)優(yōu)美,描寫(xiě)真切傳神,情節(jié)波瀾起伏,人物栩栩如生,成為文言小說(shuō)的高峰。
二、詭異主題的差異性
霍夫曼和蒲松齡都是志異大師,但他們?cè)诒憩F(xiàn)詭異主題所選取的元素卻大相徑庭。
霍夫曼往往通過(guò)對(duì)主人公精神世界的描寫(xiě)制造一種詭異的氣氛。《絲蔻黛莉小姐》中的巴黎名匠雷納﹒卡迪拉克就是個(gè)精神分裂,具有多重人格的典型人物。白天他是全巴黎“正直的規(guī)矩人,不自私、胸襟坦白、沒(méi)有隱情、樂(lè)于助人”,但一到晚上,他受黑暗勢(shì)力驅(qū)使,作惡多端,罪行累累。其實(shí)這一切悲劇的根源在于卡迪拉克無(wú)法從藝術(shù)的世界里走出來(lái)。他沉浸在自己的藝術(shù)世界,沉醉于創(chuàng)作,在藝術(shù)上精益求精。他所奉行的信條是:萬(wàn)般皆下品,唯有藝術(shù)高。
《沙人》中的主人公大學(xué)生納塔乃爾也是個(gè)典型的人格分裂和妄想癥患者。他是個(gè)憂(yōu)郁、脫離現(xiàn)實(shí)的大學(xué)生,一直生活在童年“沙人”的陰影中。他把父親的死亡歸咎在“沙人”身上。其實(shí)這一切都是主人公自己的想象。他父親的死亡純粹是一起化學(xué)實(shí)驗(yàn)的意外事件。盡管在克拉拉和家人的影響下,納塔乃爾漸漸走出了考普留斯的陰影。但主人公離不開(kāi)考普留斯,他需要考普留斯的存在,以此證明“自我”存在的真實(shí)性。最終,發(fā)了瘋的納塔乃爾站在燈塔上,翻過(guò)欄桿,跳了下來(lái)。納塔乃爾的詭異感和內(nèi)心恐懼始終與外部世界突如其來(lái)的變異有關(guān):父親的離奇死亡,曾經(jīng)以為世界上的唯一知己一下子變成了木偶人。現(xiàn)實(shí)世界的巨大反差和變化進(jìn)一步加速了他內(nèi)心世界分裂的進(jìn)程,最終導(dǎo)致精神完全崩潰。
霍夫曼之所以擅長(zhǎng)描寫(xiě)人物的多重人格,精神分裂,其原因就在于通過(guò)作者筆下的主人公,他看到了真實(shí)的自己,通過(guò)作品,他進(jìn)行自我分析、自我反思。霍夫曼白天是個(gè)公職人員,但一到夜晚時(shí)“把大部分精力和創(chuàng)作才能用來(lái)觀察自己的心境,為了觀察入微,每天都要寫(xiě)日記”[1]。他游離在真實(shí)和虛幻之間,不能自拔。他逐漸意識(shí)到夢(mèng)幻、錯(cuò)覺(jué)、瘋狂這些力量的強(qiáng)大。此外,德國(guó)浪漫派從問(wèn)世起就同德國(guó)唯心主義哲學(xué)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霍夫曼作為浪漫派后期代表人物,繼承并發(fā)展了這一傳統(tǒng)。而且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人們開(kāi)始把目光投向自身,開(kāi)始審視自己的心理和潛意識(shí)。
蒲松齡在表現(xiàn)詭異主題時(shí),往往采用冥婚式人鬼相戀或起死回生等敘述方式。冥婚式人鬼相戀的小說(shuō)之所以具有詭異的意象,之所以與一般的人鬼相戀不同,是因?yàn)橐婚_(kāi)始進(jìn)入故事的環(huán)境即令人不寒而栗。人與鬼或處古墓,或在靈柩停放之處,或在月夜陰森的環(huán)境中。其中的女鬼往往在篇首即言明身份,與常人有異。由于女主人公一開(kāi)始即是以鬼的身份活動(dòng),其環(huán)境恐怖詭異,故讀者在閱讀之初便有“人鬼殊途”之感。有時(shí)作者又從民俗的方面細(xì)致地描述鬼與常人之異:吃的是冷飯蔬菜,穿的是生前的衣服,性交往往會(huì)對(duì)男性有傷害,鬼的后代在太陽(yáng)下沒(méi)有影子,等等。這些描寫(xiě)不僅表現(xiàn)出塑造形象的細(xì)致思考,也使小說(shuō)始終保持著恐怖的張力。
《聊齋志異》死而復(fù)生小說(shuō)的魅力首先在于其數(shù)量之多、類(lèi)型之豐富。據(jù)統(tǒng)計(jì),在《聊齋志異》中含有死而復(fù)生的作品十分豐富,一共61篇。有游冥后復(fù)生的,如《棋鬼》中的馬成,《鬼作筵》中的杜秀才夫人,《酒狂》中的繆永定,《劉姓》中的劉某等。借尸還魂的有《長(zhǎng)清慎》中的長(zhǎng)清慎,《朱兒》中的小兒等。在仙人、道士、狐仙、鬼、仙藥幫助下得以復(fù)活的有《畫(huà)皮》的王生,《張誠(chéng)》中的張?jiān)G等。蒲松齡在敘述這種詭異的事件時(shí),偏愛(ài)在漆黑的夜晚,灰暗朦朧,最容易令人生出種種幻想,也是奇異故事發(fā)生的最佳時(shí)間。
《聊齋志異》突出展現(xiàn)了鬼、狐妖或神仙,以及起死回生的描繪,體現(xiàn)著神話(huà)和古老宗教的影響。在中國(guó)古老宗教傳統(tǒng)上,早在石器時(shí)代就記載著先民們相信靈魂不死說(shuō)。人死后靈魂首先變成鬼,又與人事相結(jié)合,善終者為善鬼或成仙,兇死者為惡鬼。佛教教義中蘊(yùn)含了生死輪回、死而不滅的思想;道教中有追求長(zhǎng)生、逃避死亡、超越死亡的思想;就連中國(guó)正統(tǒng)文化中都會(huì)有追求生命不息、死而復(fù)生的思想,在正史典籍里存在很多死而復(fù)生事件的記載。
三、結(jié)語(yǔ)
在高度發(fā)達(dá)的工業(yè)社會(huì),信息劇增、知識(shí)爆炸、科學(xué)技術(shù)日益介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它們固然帶來(lái)了各種方便,但同時(shí)也使人產(chǎn)生了失落感。科技使世界變得越來(lái)越小,但同時(shí)也拉遠(yuǎn)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淡泊了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生活節(jié)奏的加快,生活壓力的增加,使人長(zhǎng)期處于緊張、壓迫的狀態(tài)下。因此,精神奔潰、人格分裂等現(xiàn)象與日俱增。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急需一些不同尋常的、詭異的東西刺激自己的神經(jīng),以使整日繃緊的大腦得到片刻的放松。霍夫曼的藝術(shù)童話(huà)和蒲松齡的志異小說(shuō)既滿(mǎn)足了人類(lèi)的好奇心,又讓人類(lèi)的一些不良情緒在受到刺激、驚嚇、產(chǎn)生快感的同時(shí)得以釋放。盡管兩位作家的作品已經(jīng)過(guò)去了幾個(gè)世紀(jì),但還是具有其時(shí)代和現(xiàn)實(shí)意義。
[1]霍夫曼,著.張威廉,韓世鐘,譯.絲蔻黛莉小姐——霍夫曼小說(shuō)集.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
[2]勃蘭兌斯,著.劉半九,譯.十九世紀(jì)文學(xué)主流:德國(guó)的浪漫派(第二分冊(cè)).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7.
- 文教資料的其它文章
- 基于網(wǎng)絡(luò)資源的大學(xué)英語(yǔ)聽(tīng)力微技能訓(xùn)練
- “S-ESE”模式參照下的英語(yǔ)人才職業(yè)能力培養(yǎng)體系的構(gòu)建研究
- 大學(xué)生英語(yǔ)水平與雙語(yǔ)教學(xué)效果實(shí)證分析
——基于334個(gè)樣本數(shù)據(jù) - 研究生公共英語(yǔ)教材適用性及主體參與性教學(xué)的調(diào)查及分析
- 見(jiàn)微知著:“中國(guó)近現(xiàn)代史綱要”課程“嵌入式”微課模式的開(kāi)發(fā)與實(shí)踐
- 愛(ài)國(guó)救國(guó):晚清留學(xué)生道路之選擇
—— 以容閎和嚴(yán)復(fù)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