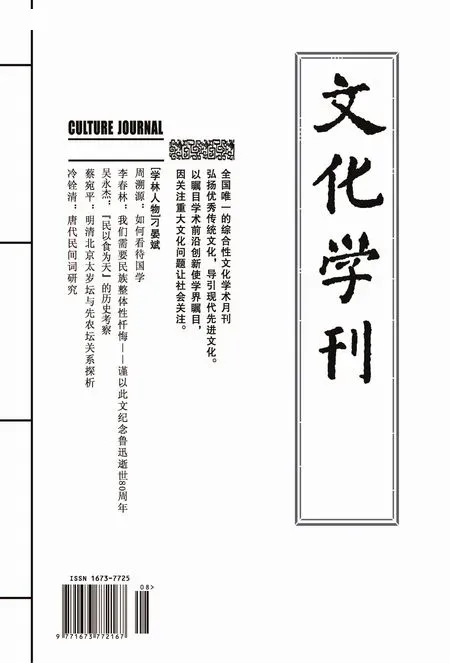晚明社會(huì)的文化心態(tài):從萬歷怠政到文官集團(tuán)的“名節(jié)”行為
劉 黎
(曲靖師范學(xué)院人文學(xué)院,云南 曲靖 655011)
?
【文史論苑】
晚明社會(huì)的文化心態(tài):從萬歷怠政到文官集團(tuán)的“名節(jié)”行為
劉 黎
(曲靖師范學(xué)院人文學(xué)院,云南曲靖 655011)
本文以萬歷皇帝怠政為視角切入點(diǎn),把張居正改革身死名敗及其與萬歷皇帝關(guān)系的變化、“爭國本”事件進(jìn)行串聯(lián)分析,剖析明代文官集團(tuán)的文化心態(tài),在這一系列事件背后所表現(xiàn)的是虛妄的“名節(jié)”,缺乏對實(shí)際問題解決的思想和實(shí)踐,一種焦灼和不知所謂。
制度;關(guān)系;矛盾;靜止;調(diào)適
朱元璋創(chuàng)建明帝國,御宇期間所主持設(shè)計(jì)的一系列關(guān)于政治、經(jīng)濟(jì)和文化思想意識形態(tài)的制度框架,對后世中國傳統(tǒng)社會(huì)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體制創(chuàng)制設(shè)計(jì)隨著時(shí)間及人事變化發(fā)生了偏離設(shè)計(jì)者的初衷理念,或者說是制度設(shè)計(jì)者缺乏長遠(yuǎn)目光,以落后的財(cái)政思想著眼于經(jīng)濟(jì)發(fā)展,僵化的體制和思想意識形態(tài)管理全國民眾,對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的動(dòng)態(tài)性變化考慮不足,導(dǎo)致制度發(fā)生負(fù)作用,鉗制了社會(huì)、國家人與事的適時(shí)變動(dòng)。
一、張居正與萬歷關(guān)系的解讀:從元輔張先生到敵人的轉(zhuǎn)變
萬歷皇帝9歲登基,而本朝體制不允許藩王、即皇帝的叔伯堂兄等代為攝政,換言之,皇帝缺乏皇族中人的支持。張居正既是皇帝的老師,又是帝國的實(shí)際主宰者。他的權(quán)力遠(yuǎn)遠(yuǎn)超越前代任何一個(gè)丞相,但他的權(quán)力不是法定的,或者說不是儒家政統(tǒng)認(rèn)定的,而是靠關(guān)系與人情維持。萬歷八年,萬歷皇帝與太監(jiān)酗酒,遭到了其生母李太后的嚴(yán)厲責(zé)罵,繼而李太后拿出《漢書·霍光傳》,皇帝明白這其中的深意,霍光廢立過皇帝。事后,張居正代皇帝寫了《罪己詔》。十八歲的皇帝對此洞若觀火,這是一個(gè)重要的轉(zhuǎn)折點(diǎn)和導(dǎo)火線。在萬歷皇帝心中,我是皇帝,為何會(huì)被一個(gè)臣下所挾制?這勾起了皇帝早年的另一事件,“初,上在講筵,讀《論語》‘色勃如也’,誤讀為‘背’,居正遂厲聲日;‘當(dāng)讀作勃!’上悚然驚起,同列皆失色,由此上益心憚居正。時(shí)比之霍氏驂乘云。”[1]這些事件連在一起,皇帝的不滿、忿恨和厭惡在膨脹,繼而指向最高權(quán)力的爭奪。張居正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每況愈下,從元輔張先生變?yōu)橐粋€(gè)敵人。這與萬歷五年張居正因父親去世“奪情”,皇帝下詔再議論張居正奪情者格殺勿論,已是天壤之別了。隨著皇帝日益成長,而張居正卻手握屬于他的權(quán)力。萬歷皇帝的生母李太后在他成長教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從現(xiàn)代教育觀點(diǎn)來看,她的教育方式客觀上對皇帝產(chǎn)生了巨大的誤導(dǎo)性。萬歷八年張居正在皇帝醉酒事件后,提出辭職,在她的授意下,皇帝下詔不允許張居正辭職,此時(shí),皇帝早已18歲,按理應(yīng)該臨朝親政,但她卻要皇帝“與張先生說,……張先生親受先帝付托,豈忍言去!待輔爾到30歲,那時(shí)再作商量。……”①《張文忠公全集》卷四四《謝圣諭疏》轉(zhuǎn)自林延清,《李太后與張居正改革》,《南開學(xué)報(bào)》2005年第5期。皇帝不能違背母親的意愿。皇帝的母親或是錯(cuò)誤估計(jì)了兒子的心理態(tài)度,或是她不能洞悉帝國權(quán)力人事關(guān)系的厲害。萬歷十年六月張居正去世,十二月皇帝便開始了對張居正徹底的清算,這是皇權(quán)體制下的必然,他朱翊鈞對張居正的清算,才能樹立自己作為皇帝的權(quán)威,這也是文官集團(tuán)的看法。
二、晚明社會(huì)的文化心態(tài):制度與文化、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邏輯矛盾
萬歷皇帝對張居正去世后進(jìn)行了徹底清算,他以激昂的斗志保持對皇帝職責(zé)的履行,萬歷十一年,京畿地區(qū)大旱,皇帝以步行的方式到天壇祈雨。這是一種態(tài)度,一種信念,他要把這個(gè)帝國治理好,這是對清算張居正的一種回應(yīng),可這一行為沒有能保持他御宇帝國的始終,從萬歷十四年下半葉開始至萬歷十五年,皇帝開始逐漸發(fā)生了性情改變,以各種理由推脫不出席皇帝應(yīng)該出席的各類活動(dòng),最后深居簡出,開始了長達(dá)三十余年的長期消極怠政。
萬歷五年,按照本朝慣例,張居正的父親去世,他要回家丁憂守制二十七個(gè)月,但改革剛剛進(jìn)入秩序,張居正如果離開,改革事業(yè)必將陷入停頓,于是只能選擇“奪情”。在這次“奪情”事件中,張居正的兩個(gè)門生,趙用賢和吳中行上書彈劾張居正,被皇帝下令處于梃杖。在這次事件中,文官集團(tuán)的“名節(jié)”行為或被歷史學(xué)家們所忽視,趙用賢的夫人在丈夫受刑后,從丈夫被梃杖打落的臀部碎肉中挑選了一塊制成臘肉掛于家中,以戒示后人,同時(shí)更重要的是表達(dá)對張居正的永不妥協(xié),在他們心目中,上書彈劾張居正是“天理”,因?yàn)閺埦诱`背了“人倫”,“天理”不可更改的。當(dāng)時(shí)張居正已是權(quán)傾朝野,看似無人能撼動(dòng),但當(dāng)事件出現(xiàn)時(shí),這只是表面現(xiàn)象。他的兩個(gè)門生的行為在道義上代表了整個(gè)文官集團(tuán),及其所信仰的儒家道學(xué)。或許在客觀上,他的兩個(gè)門生是真情實(shí)意的希望老師能歸鄉(xiāng)守制,但在巨大的文官集團(tuán)的背后這樣的意思其實(shí)不盡實(shí)然,反對“奪情”的背后是權(quán)力的爭奪和利益的追逐。更有甚者,后任內(nèi)閣首輔的申時(shí)行和王錫爵竟然徑自到張居正的府邸,王錫爵把張居正逼迫得拔劍欲自刎。十六年后,任內(nèi)閣首輔的王錫爵因?yàn)椤叭醪⒎狻保w南星上門逼迫他,相信他感覺到了當(dāng)年張居正的難處,進(jìn)退維谷,他變成了另一個(gè)“張居正”。在這些看似“光明”的行為背后,不盡實(shí)然,用繼任首輔申時(shí)行的看法即是整個(gè)文官集團(tuán)的陰與陽的平衡距離越來越遠(yuǎn),在“陽”的背后是“陰”的涌動(dòng),即私欲的膨脹,“陽”的實(shí)質(zhì)不是內(nèi)心的理念,而只是一種手段而已。萬歷皇帝在這種網(wǎng)狀的困境中無法突破,最后他只得選擇長期消極怠政,與群臣進(jìn)行無聲的對抗。“爭國本”事件無疑是對他影響最大的事件。他欲立自己心愛的鄭貴妃之子,即皇三子朱常洵為太子,但恭妃王氏已生下皇長子朱常洛,即后來的泰昌帝。皇帝與群僚對抗了十幾年之久,牽動(dòng)了整個(gè)帝國的朝局,幾位內(nèi)閣首輔被迫離職,數(shù)百位高級官員卷入其中,而皇帝的心理也隨著這樣的無助心灰意冷,對整個(gè)文官集團(tuán)最終失去了耐心和信念,皇帝和群僚的關(guān)系最終變得不可彌補(bǔ)。關(guān)于皇位繼承人,從永樂皇帝開始從法理上就不具備長子繼承的合法性,永樂皇帝用武力奪取了侄子建文帝的帝位。從法理上講,萬歷皇帝可以從諸子中選擇一人繼承自己的地位,皇長子和其他諸子地位是平等的。那么其先祖永樂皇帝的地位就是非法的,這對于文官集團(tuán)來說是一個(gè)不能言語的癥結(jié)。于是這個(gè)繼承問題被轉(zhuǎn)化為一個(gè)道德問題,因?yàn)榈蹏男姓砟畈皇且苑ㄖ卫硖煜拢且缘赖潞投Y儀。在“爭國本”事件中各大小官員前赴后繼的上書與皇帝對抗,最后皇帝只得妥協(xié),立皇長子為太子,皇三子到河南之國。萬歷皇帝心灰意冷,他無法以一身之力量對抗整個(gè)文官集團(tuán),他用道家的“無為”為幌子與群僚進(jìn)行對抗,他不補(bǔ)缺官員的缺額,意味著這一職位的利祿將被作廢,官員的晉升之路就被阻塞,他不能提拔自己喜歡的官員,但他可以選擇罷黜自己厭惡的官員,這是他唯一的手段,但這樣最終結(jié)果乃是帝國政治行政體制癱瘓和崩潰。這樣看來,“身為天子的萬歷,在另一種意義上講,他不過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權(quán)力大多帶有被動(dòng)性。”[2]
在萬歷皇帝消極怠政的背后,可以窺見整個(gè)文官集團(tuán)的文化心理,在他們“名節(jié)”行為的背后,不盡全是一種“陽”的理念,而是私欲的牟取。一方面這是宋明理學(xué)“內(nèi)圣”與“外王”,即“禮”和“仁”分化所形成的結(jié)果。原生儒學(xué)是“禮”和“仁”的雙重合一,“禮”是一種外在的規(guī)制和原則,“仁”是一種情感的交融,至宋明理學(xué)發(fā)展時(shí)期,“仁”的地位和內(nèi)容被擴(kuò)大的深化,融入的佛教的概念,而外在關(guān)乎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禮”,即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規(guī)范被邊緣化或被置于“仁”的統(tǒng)領(lǐng)下而遭到弱化,“內(nèi)圣”的心性修養(yǎng)超越一切,到王陽明的心學(xué)發(fā)展到了頂峰。“外王”是基于“內(nèi)圣”為出發(fā)點(diǎn)。另一方面是體制的緣故,本朝的體制建立在文官集團(tuán)的基礎(chǔ)之上,以宋明理學(xué)朱熹的儒家道統(tǒng)為開科取士的標(biāo)準(zhǔn),而且本朝官員俸祿極低,“內(nèi)圣”的修養(yǎng)缺乏外在“禮”的規(guī)制,這樣導(dǎo)致人的文字道德與社會(huì)道德相分離,即在物質(zhì)利益的吸引下,人的精神人格分離。萬歷皇帝消極怠政是對此極大的無聲抗?fàn)帲驗(yàn)樗聪み@一切,“爭國本”的背后就是權(quán)力和利益的爭奪,因?yàn)閾砹⑻熳邮遣皇乐ΑN墓賯兩蠒毖苑干希砻婵此剖恰疤炖怼钡囊环N堅(jiān)持,即做所謂的諍臣,因?yàn)橥庠凇岸Y”的規(guī)范的弱化,這變成了一種近似低俗的“吵罵”,翻閱明代言官的上書史料,這樣的表現(xiàn)比比皆是,太過注重“名節(jié)”,而不注重社會(huì)實(shí)際,逐漸演變?yōu)橐环N沽名釣譽(yù)。群臣的爭吵無助于現(xiàn)實(shí)問題的解決,后當(dāng)李自成的大軍兵臨城下,帝國的大臣們作鳥獸散,崇禎皇帝身為儒家信徒,只能無奈的選擇殉國,不妥協(xié),不投降。萬歷皇帝的難處就在于他要做一個(gè)近似宗教徒“先知”一樣的角色,而不是一個(gè)完整的“人”。而文官集團(tuán)們則是對這種行為的監(jiān)督,雙方日益成水火之勢,而不可協(xié)調(diào)。
帝國傳統(tǒng)體制限制了經(jīng)濟(jì)發(fā)展所促進(jìn)的文化觀念的轉(zhuǎn)變,中央集權(quán)的體制和內(nèi)圣的文化觀念,導(dǎo)致權(quán)力頂端需要的僅僅只是一個(gè)道德和禮儀的木偶,而不需要太多的主觀能動(dòng)性的和多重性格的皇帝,皇帝的行為被程式化、標(biāo)準(zhǔn)化,對此萬歷皇帝無能為力,他只能選擇長期的消極怠工,導(dǎo)致帝國的臣僚們相互攻訐,形成黨爭,致使帝國政局一發(fā)而不可收拾。晚明社會(huì)的文化心態(tài)是焦灼和惶恐的,文官集團(tuán)的名節(jié)行為也是一種不得已為為之的行為,面對殘酷的現(xiàn)實(shí),不能解決,只能用所謂的心的體驗(yàn)來掩蓋內(nèi)心的不安。因?yàn)轶w制的高度程式化,近似于宗教的設(shè)計(jì),使得陰與陽的文化心理距越來越遠(yuǎn)。這預(yù)示這一種體制即將崩潰,長期的社會(huì)革命將不可避免,而且是撕心裂肺的革命。體制改革和適應(yīng)對一個(gè)社會(huì)、國家的發(fā)展至關(guān)重要,體制應(yīng)當(dāng)跟上文化和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張居正的改革和萬歷皇帝的長期消極怠政對體制和文化、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同步認(rèn)識和理解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shí)借鑒意義。
[1]夏夔.明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52.1582.
[2]黃仁宇.萬歷十五年(增訂本)[M].北京:中華書局,2007.86.
【責(zé)任編輯:董麗娟】
G09
A
1673-7725(2016)08-0209-03
2016-05-05
劉黎(1981-),女,云南曲靖人,主要從事文化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