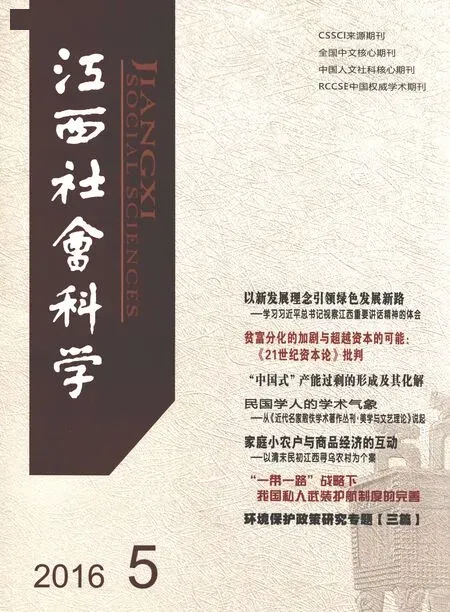論章學誠“以古文為時文”對宋代文章學的接榫與更革
■王 苑
論章學誠“以古文為時文”對宋代文章學的接榫與更革
■王 苑
清代文章學批評以好談文法為特點,且文法內涵范疇包羅寬泛,立足高遠,視角宏觀。雖然文章之學發展之清人手中幾近乎極致,但其中很多文章學觀點,無論是抽象理論還是具體操作,無論是古文時文的相濟為用還是積學養氣,無論是文成法立還是死法變活等種種理論建構與發展,都可以上推至宋代的文章學建構之中。其間,章學誠作為清代文史理論研究與建構集大成者,正可作為綰合自宋至清文法論發展演變脈絡的代表人物,并可從中尋繹出其間的傳承與革新。
宋代文章學;時文;古文;章學誠;文法論
王 苑,南開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天津 300071)
清代文章學批評有一重要特色,即好談文法。所謂“文法”,正如章學誠在其《文史通義·傳記》中所提出的一個新范疇——“例義”[1](P249)。而“例義”在某種意義上,正可與清人的文法理論內涵暗通。其實,在很多時候,談“例”就是談“法”,二者可等而視之。而且,清人的文法范疇包羅寬泛、意蘊豐厚,并不僅僅局囿于狹義的“法”的概念,而是立足于更高遠也更宏觀的角度,審視文章寫作中涉及的方方面面,實質上涵蓋了文章學中的內容法度兩層意思,二者相輔相成,不可截然分開。而注重文法,根據文章的寫作宗旨制定一系列具體細致并行之有效的法則,并以之為作文的指導規范,乃清代文章學之特質。
這其間,前人多將關注的目光投射于自明代的唐宋派,衍生至清代的桐城派所謂“義法”古文理論上,并以乾嘉時期挺立而出、脫拔時俗的章學誠作為真正建立系統文法理論體系的集大成者。但其實,由于明清時期是中國科舉文化制度真正發展至巔峰狀態并盛極轉衰、日趨熟濫,科場之文精嚴深細、體制邃密與煩冗瑣碎、作法自斃并存。清人早已意識到了此種弊端與危機,所以,我們現在再看清人文論,多是借古文之名,談時文之實。這也是利祿之途所寄,反映在文化領域中的社會態勢。關于此點,前人之論已夥,但百密終有一疏,雖然文章學發展到清人手中幾近精博完備,但倘若我們沿流溯源,清人的很多文章學觀點,無論是抽象理論還是具體操作,無論是古文時文的相濟為用還是文成法立、死法變活等理論與現象,都可以上推至宋代的文章學建構中。當然,這與宋代的科舉文化臻于鼎盛條件下,衍生出的文學發展新貌密不可分。那么,清代何以興起以法論文風氣,蓋可管窺。而這種風氣有何具體表現?以章學誠為代表的清人文法觀,對宋代文章學有何繼承與拓新?其對于文法日趨嚴苛,并流為弊病的應對方法,對宋人有何因襲與發展?體現了清人怎樣的文章學旨趣?正為本文的觀照重心所在。
一、宋代文章學的成立與在清人文論中的投射
王水照在其主編《歷代文話》后附帶的論述文稿中,曾明確界定帶有學科性質的文章學,是成立于宋代的:“文章學之成立,殆在宋代,其主要標志在于專論文章的獨立著作開始涌現。”[2](P32)對此,宋元文章學研究專家祝尚書也撰文表示認同,并進一步把籠統的“宋代”的時間范疇,精確地限定在了南宋孝宗朝,根據之一,便是一系列適用于科場的文章名家的名作總集與具體行文中的法則評點的大量涌現,如陳傅良《止齋論訣》、呂祖謙評點本《古文關鍵》、陳骙《文則》等等。[3](P14)
文章學的成立不是偶然的,它必須具備適當的內部、外部條件。南宋科舉制度文化下催生出的場屋論文之習,官祿之途下誘發出的精研時文的風氣以及為提升時文的思想境界與文化品位,而做出以古文之精神實質濟養時文形式外殼,以時文之精細結構參合古文之逶迤筆法等具體理論,為建構學科意義上的文章學做了充分儲備。也意味著,宋代興起的文章學理論勢必誕生于科場,也最初應用于時文寫作。沿襲至清,桐城文派恢張唐宋八家,并以獨承文統自命,其作雖為古文,卻終因沾染時文習氣而為當時人如章學誠輩詬病。其病灶所在,即宋代場屋時文參以古文筆法的文法傳統。所以,從宋代著眼,其適合文章學形成并日漸成熟的文化制度與政治生態、唐宋古文大家韓柳歐蘇典范意義的確立以及致力于文章學研究的學者群體日益成長壯大等因素,對促成宋代文章學正式成形與定性意義深遠且重大。
中國的文章研究源遠流長,不過,學科意義上的文章學,蓋發軔于先秦,到漢代已有相當發展,至魏晉六朝,已經產生了如摯虞《文章流別論》、劉勰《文心雕龍》等專門論著。但即便如此,魏晉六朝時期,仍只能是文章學發展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而遠非終結,也不能算嚴格意義上的“文章學”。隨著隋唐科舉取士的文官選拔制度的普及,事關廣大知識分子的仕途爵祿,文章學獲得了新的發展助力,故而廣義上的文章學,諸如種種瑣細局部的詩賦文 “格”,或“式”,逐漸由萌芽、成長以至繁茂。據《宋史·藝文志》著錄的唐人撰著,就有王正范的《文章龜鑒》、孫郃的《文格》、馮鑒的《修文要訣》多種,雖皆已亡佚,但依舊可從中窺探些許文學文化風尚的轉向。據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匯考》,唐代尚存有《賦譜》一卷,乃專門研究適用于科考的律賦,從框架結構、修辭句法、格律聲韻、起題收束等方面不厭瑣細地設計營構,實為現存最早的一部體系完整的應試文章學著作。[4](P167)所以,中國的文章學自其產生之日起,就深深打上了科舉的烙印。
南宋之后,以古文、時文、四六文文法為主體的研究成為社會上廣泛文人的矚目所在,并且也逐漸超越科舉功利性質的牢籠,文章學由是大盛,并與詩學、賦學分疆劃界、鼎足三分。而這,又與長時期內,學者們的孜孜矻矻慘淡經營密不可分,無論是精華還是腐朽,其深遠的影響都不可避免地延續至有清一代。眾所周知,清代文學的突出特點便是文成法立、會通化成,集諸文體之大成,故而分門立派,法度森嚴。文法說的興盛既出于對文體意識的自覺、對文場積弊的挽救等種種現實原因,也是文章學自身在形式法度的要求規范下,長遠考量的結果。如章學誠《古文十弊》便以“論古文辭義例”為鵠的,程千帆箋曰:“蓋所謂義者,制法以垂世;所謂例者,依義以發凡。亦或變文言義法。”[5](P283)其實質,就是將“義例”與“義法”一脈貫通,無疑將章氏的“義例”說與桐城派方苞的“義法”等而視之,其觀點提綱挈領,高瞻遠矚,大處而言,洵為確評。正如唐代進士詞科的重心所在,不僅促使格律詩形制的快速成熟,也催生出了大量詩格類著作,從而間接地構建了詩學理論的框架與范疇。此后,這種風氣因宋代科場風氣的轉變,以經義策論為重心的考核內容,也誘發了時人對論體文及其寫作程式的廣泛關注,各類文章選集與評點類著作應運而生,蔚為大觀。
宋人的《古文關鍵》《論學繩尺》等匯編文集與評點著作,充分體現了傳統文章學研究以程文軌范與具體操作技巧為中心的特點。這類書籍產生于高度成熟與發展的文官選拔制度中,為舉業而編,帶有關乎現實利益的實用性與工具性,所以,當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旦魚躍龍門、應舉得第后,便往往將之棄置不顧,甚至鄙視鄙夷。所以,可想而知,這類帶有文章學建設意義的選本與撰著,勢必難以長久流傳。在這種境況下,清人針對文壇上各類積重難返的弊端,力圖在宋人基礎上建立具有普適性與高品位的文章學規范,并進而上升為理論形態的文論思想。基于這個理想,清人高倡義法文則,并將之運用到古文寫作中,從而興起了探討古文法度,并將之應用于時文寫作的理論浪潮,標志著古代文章學理論構建的又一次進展。清人文法說不像傳統文格說,而是力圖將原本糾纏于具體的程文科條的宋人論述,賦予普遍的理論意義,從而恢拓其視域,高拔其價值,雖然也時常失之瑣屑贅冗,但“其標準則折衷于事理”[6](P428),則大略不誣。
二、章學誠的時文觀對“以古文為時文”的宋代文章學因創
時文“以古文為法”,是自宋代以來,文章學的主流,也是宋人論文動機所由。延續至清,已成為文論家們的口中常談。但如果忽略古文唯談時文,只有時文的程式法則,就不可能成為內含豐富的文章學;反之,如果只有古文而不及時文,也不是那時文章學的完整面貌,更無法深入獲悉所謂文法的生發契機。唯有二者結合,相輔相成,文章學理論建構才能內涵完善且評判客觀。因此,時文“以古文為法”,反之又以時文解析古文,才有了由宋至清文章學的龐大體系與豐厚成果。
明季出現了不少著名的制舉文名家,高揚“以古文為時文”的口號,并留下了深遠影響。到了清中葉,桐城派鼻祖方苞編《欽定四書文》,在《凡例》中開首言明,明代正德、嘉靖年間的制舉之文,開始將古文筆法打并入時文體制之中,從而達到“融液經史,使題之意蘊隱顯曲暢”,明文因而之于極盛。隨后方氏又在此書中編選的歸有光《五十有五而志于學》一文后評說明代唐宋派古文“以古文為時文”理論的探索實踐歷程,即“自唐荊川始,而歸震川又恢之以閎肆”。但其實,后人們也往往將關注的焦點集中于明清兩代的唐宋、桐城派標舉的“以古文為時文”的浩大聲勢中,從而將研究的重心放在明清文學與教育、科舉等制度文化的領域內,成果不可謂不豐碩,但遺憾的是,對于“以古文為時文”這條文章學理論的源流追溯,卻很少有人致意問津,早在南宋時期,以古文為法則指導場屋時文的寫作,已讓士人群體趨之若鶩,并留下很多書面文字的表述。明人詹仰庇《文章指南序》曰:“文,一而已矣,后世科舉之學興,始歧為二焉。學者遂謂古文之妨于時文也,不知其名雖異,其理則同。欲業時文者,舍古文將安法哉。”[7](P1738)
事實上,正是時文“以古文為法”,使宋代成熟起來的文章學影響深遠。從清代文論可知,時文與古文往往是一對時常并提、不可分割的概念,時文寫作水平的提升離不開古文文法的給養固毋庸置疑;同樣地,古文虛與委蛇、錯綜變幻的靈活手眼亦須借助于時文之定法,才能具體落實到具體的行文中,才能有義例可據、有脈絡可循,使人按圖索驥、沿波討源而不致無所歸依、謬以千里。
據祝尚書考證,現知最早明確提出“以古文為時文”理論的,是北宋徽宗朝文士唐庚,他曾提出時文“以古文為法”。其《上蔡司空書》云:“宜詔有司,以古文為法。所謂古文,雖不用偶儷,而散語之中,暗有聲調,其步驟馳騁,亦皆有節奏,非但如今日茍然而已。”[8](P53)
唐庚欲時文“以古文為法”,實是想以之為武器,來扭轉當時王安石新法遺留下來的重經術輕辭章的學界積弊與文壇頹風。在徽宗朝,科場中的經義策論之文已形成一定之規并日漸僵化,一如黃茅白葦,千篇一律,故而形成了矯揉造作的頹敝文風。唐庚在《上蔡司空書》一文中提出要以古文為作時文之法,其意圖便是將古文中合于圣人道德經旨的言詞,與散句的節奏聲調,運用于科場時文的寫作中。可知,唐氏對于過度駢儷、雕琢刻繪的時文風習深致不滿。除此之外,黃庭堅在《答洪駒父書》中提到:“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為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而其《答王子飛書》一文中,論及陳師道寫作文章,也說:“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9](P293)由此可見,宋人研究古文,主要著眼于具體的,帶有可實際操作性的法則上,諸如 “關鍵”、“開闔”、“步驟”。這與發展到清人那里的“以古文為時文”表述形式雖有差異,但在內涵上,卻一脈相承。
(一)章學誠的“積學明道”論與宋人的“立意”說
宋人陳睽的《文則》中有言:“辭以意為主,故辭有緩有急,有輕有重,皆生乎意也。”所謂“辭”,即是文句。而此句言論的意圖,便是說明文章之“意”的優劣高下直接影響著文章成就的高低。所以,立好“意”始終是文人寫作文章時的三致意處。
詩歌在唐代比較盛行,故唐人對立意的探討主要集中于作詩上。如舊題王昌齡《詩格》中便有論及:“夫作文章,但多立意。令左穿右穴,苦心竭智,必須忘身,不可拘束。思若不來,即須放情卻寬之,令境生。”[4](P162)文句中的“文章”即詩歌,“立意”則指構建營造詩語中透露的意境,這過程須借助思力,故謂之“境思”。其后皎然的《詩式》亦復如此。但文章學意義上的立意,尚須等待宋人發明,南宋的陳傅良在其《止齋論訣·立意》中才針對時文,即當時科場的論體文提出自己的見解:“凡論以立意為先,造語次之。如立意高妙,而遣辭不工,未害為佳論;茍立意未善,而文如渾金璞玉,亦為無補矣。”又言:“立意既當,造語復工,則萬選萬中矣”。
故而,若想使功利性的時文有超越性的價值,也必須講求立意。同樣,呂祖謙也在其選編的《古文關鍵》的緒論中說:“第一看大概主張。”一如真德秀:“讀書須先看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于言上求之。”所謂“意”,就是文章之主旨所在,也是一篇文章的頭腦、眉目與統帥,而正是因為其地位的非同尋常,其本身便具有脫略苛法束縛的高貴,自不可用一定之規來繩律,也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成式,所以要想在實際操作的層面構思立意便極為困難。宋人王應麟在其應用于詞科選拔的《詞學指南》一書中也提出“知格律”、“立意”與“語贍”兼顧的作文原則,并舉柳宗元《柳州學記》為例,要作者由題切入并加以發揮;而元代的陳繹曾在其《文說·立意法》中也認為“意以理為主”,故而要“據理”為文。
概而言之,“意”即性靈魂魄,于詩于文皆是如此。只是,在唐人那里已予以相當關注的詩歌立意法,到了宋人這里,因科場文化的變遷與士人寫作旨趣的轉移,開始對文章的立意密切關注、熱情討論,并將之推向成熟的學科理論建設。費袞在其《梁溪漫志》(卷4)中便形象地記敘了蘇軾對后學傳授的作文心得:
譬如市上店肆諸物,無種不有,卻有一物可以攝得,日錢而已。莫易得者是物,莫難得者是錢。今文章詞藻、事實,乃市肆諸物也,意者錢也。為文若能立意,則古今所有翕然并起,皆赴吾用。[10](P37)
故而陳繹曾借用東坡的“意而已”來闡明自己的觀點:“作文之事料散在經史子集,惟意足以攝之,正此之謂。”因之,“煉意”也就當仁不讓地成為作文過程中的重中之重。
與古人作文立意求“奇”的審美取向相映成趣,宋代右文崇古,回向三代的政治文化理念,使宋人在“奇”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古”的楷式,如南宋人謝采伯《密齋筆記》中所言:“字古不如語古,語古不如意古。”[11](P56)這就在深層次上暗含了復古宗經明道的潛在要求,自然而然與清人文章學的經學文化背景遞傳接軌。
到了明清兩代,八股文成為科場中的時文主流,利祿之途既開,弊端自然隨之滋生。清初王夫之的《夕堂永日緒論外編》即嚴以責之并對之寄予高遠追求與深切厚望:“不犯一時下圓熟語,復不生入古人字句,取精煉液,以靜光達微言。”[12](P239)到了章學誠這里,進而提出了“有質八股”的時文主張。他主張“有境界”的八股文應以學問為根底,以明道為指歸。如他在《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中要求文章本于經史之學,無疑與清代學風暗合,從而在內部改造了宋人文章學具體與瑣屑,深入到時文的內涵思想層面。章氏用“山必積高而后能興云雨,水必積深而后能產蛟龍”作喻,來說明學問的厚積對寫好時文的決定作用,否則,腹笥寒儉,貧瘠狹隘,寡聞孤陋,則會“堆阜斷港,封其神明”。
但章學誠尚未于此止步,而是由積學上升至明道。他在《踐〈屠懷山制藝〉》中說:
試士以舉業者,志不在舉業,而在經史辭章有用之材。富家廣有金錢,正以布帛菽粟,生人日用所需,無所不聚之所致也。士子習為舉業,而忘所有事,則如鍛工鑄匠,僅能熔造金錢,而家無布帛菽黍之儲,雖金錢出入其手,而其身仍不免于饑寒者也。[13](P323)
正是持有八股時文雖 “非經非史非辭章”,但卻是“經史辭章之學無所不通”的見解。要想作得好,只有淡泊名利,脫略紛俗,熔液經史,淘洗靈魂、變化氣質,才能厚積薄發,援筆為文。
(二)章學誠“養氣”論中的宋儒異質
宋人李塗在《文章精義》中寫道:“做大文字,須放胸襟如太虛始得。太虛何心哉,輕清之氣旋轉乎外,而山川之流峙,草木之榮華,禽獸昆蟲之飛躍,游乎重濁渣滓之中,而莫覺其所以然之故。人放得此心,廓然與太虛相似,則一旦把筆為文,凡世之治亂,人之善惡,事之是非,某字合當如何書,某句合當如何下,某段當先,某段當后,如妍丑之在鑒,如低昂之在衡,決不致顛倒錯亂,雖進而至之圣經之文可也。”這里摻雜了宋人文論中特有的理學思致,其“氣”自有特定內涵而不同于以往。前人論“氣”已夥,最有名的當屬《孟子·公孫丑》的“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曹丕《典論·論文》的“文以氣為主”,韓愈《答李翊書》的“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大概都是指人精神的強度與情感的氣勢。宋孝宗贊蘇軾文“氣高天下”,也是此義。
郭紹虞有一句精到的評論:“道學家之論氣,重在修養;古文家之論氣,重在閱歷。”[6](P219)以后者為例,則有蘇轍在《上樞密韓太尉書》中,向韓琦述說了自己學文的經過,以孟子、司馬遷為例,對“養氣”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蘇轍主張的其實是基于閱歷的“養氣”說,頗帶縱橫家之習氣。而與之相異的,是理學家們的主張,則有濃重的道德倫理寓意。如真德秀在其《跋豫章黃量詩卷》一文主張:故欲詩文美善,就必須“養心”,這實際上是與“養氣”相通的,只是暗中更換了其本質內涵,從而賦予了養氣說更加鮮明的道德本體意義,由德之厚善推論至文之佳美,總之,要皆以修養為本。所謂“蓋圣人之文,元氣也,聚為日星光耀,發為風塵之奇變,皆自然而然,非用力可致也”[14](P89)。至于朱熹的主靜涵養說:“故欲其先習為端莊嚴肅,不至放肆怠惰,庶幾心定而理明耳。”[15](P257)以及李塗《文章精義》中:“做大文字,須放胸襟如太虛始得。”由此可見,宋人已將起源于孟子,歷經曹丕、劉勰、韓愈等人發展起來的“養氣”說剔其情感氣勢與風骨力量的動態化的內核,而暗換成靜態的、德性的、義理的道學本色了。到了明人那里,在講求“以古文為時文”時,也主張“養氣”,如唐宋派的歸有光,就說“文章以理為主”,“為文必在養氣,氣充于中而文溢于外,蓋有不期然而然。……不期文而自文,謂非正氣之所發乎”
章實齋談作文法則,上承前代的文章美學傳統,強調文氣流貫在整篇文章中至關重要的地位。他在《雜說》中申明的“文以氣行”,在《史德》中導揚的“文非氣不立”,連為友人私下寫作的序跋,探討文理時,也對此念念不忘。他為梁少傳《杜書山時文》所作的序文,又再次明確了他“文者,氣之所形”的論斷,都無疑與前人的觀點一脈相承。
至于如何“養氣”,這個問題涉及了章氏所謂“氣”的本質內涵。于此,章學誠又提出“集義養氣”的觀點。所謂“集義”,就是通經學古,博覽旁搜,沉潛心志,積釀意匠,從而長期歷練鍛造培養,胸中九流清似鏡,自有一股勃郁之氣蟠紆胸中,這種氣配義、道與理,然后發而為辭,落筆成文,自如“火燃泉達”,“浩乎沛然”。在這一點上,實齋的“集義養氣”說,與孟子的“知言養氣”說,雖是古今懸隔,卻是異貌同心,即都是強調一種由道德的負載力量支撐起來的浩然正氣,并以圣賢的經籍垂訓作為涵養的正途。這種“氣”中活躍著宋儒們少見的激揚氣概,與其靜中涵養、守靜自持的“養氣”說有所差異。
所以,章學誠在倡導“氣貴于平”、與宋人相通的文氣論同時,另主“氣貴于昌”。他在《史德》中云:“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13](P40)其《跋〈香泉讀書記〉》中又說:“其識卓而醇,其氣昌以肆。”[13](P322)只有文氣昌盛,橫貫無礙,濃烈誠摯的情感才會流溢其中,雄肆豪邁的氣概才會顯現其外。故“文如駭馬下坡,賞其氣勢可耳”、“如火燃泉達之不可已”。氣“昌”之所以可貴,在于此種氣得之于陽剛,究其實質,就是貴在一種浩氣血性,一種勁健蓬勃的生命力。具體呈現在行文中,便是文氣凌轢超拔,如旭日東升,噴薄而出,運行于天際,萬物得其光澤,文章也因此剛健有力,氣勢充沛。同時,與清人論文重法度的特色一致的是,章學誠的“氣貴于昌”還涉及文脈、文理等技術層面的問題,如果氣之積淀不能深厚暢達,文勢自然凝滯阻塞。就像其《雜說》中所提到的情況,即便事理明確詳備,依舊于文勢無補,讓人有意猶未盡之憾,正是“辭氣有所受病而不至”的緣故。所以,讀者自然會感到郁澀湮堵,將并文氣文詞之失,也一并歸罪于“所載之事與理而亦病”[13](P55)。所以,章學誠要提倡的正是其《〈淮南子洪保〉辨》中所說的“文氣連注”[13](P59),一如飛流傾瀉,抽刀不可使之斷的一邁直往。目的也是使文章貫通順暢,易于理解,而為世所用。
由此可知,雖然皆是注重“養氣”之說,但章學誠體現出的觀點卻是與宋儒論文截然不同的,或許與章氏本人的學術傾向有別于宋學的虛靜迂闊有關吧。
(三)宋代文章學“法”流于“技”的弊端與章學誠“活法”說
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時文 “以古文為法”的理論亦不例外。因為作文講求法度準繩,主要體現于科舉時文的揣摩課業中,為的是符合官方的評判標準,日久必生腐臭僵化,因而,自科舉制度形成之日起,批評之聲就不絕于耳。但就本質而言,“時文”與一般文體并無區別,正如元代劉將孫談到的“文字無二法”之說[16](P58)。自韓愈高舉復興古文的大旗,創立“古文”名號,之后的論文者強劃疆界,拘執固陋,非此即彼,斷為兩截,自然不能理解文貴辭達、古文時文在更高理論層次上的相通。時文其實就是一般的文體,但當它專用于科考并成為定式之后,就自成一類了。而后人詬病科舉,罪狀之一就是時文的程式化。到宋代,雖有歐、蘇的古文運動,但此種格局仍不能改變。元代劉壎在《隱居通議》(卷18)中將古文中雜糅進舉子語,形象地比作“金盤盛狗矢”。到了明代正德、嘉靖年間,情況依舊如此。唐宋派古文家高倡“以古文為時文”,制藝臻于極盛,顯然是上接宋人傳統。唐順之、歸有光等提出的“以古文為時文”,也與宋人一樣,仍是強調技法。
對于時文之文法,章學誠無疑是肯定其內在價值的。他在《與邵二云論文》中說:“殊不知規矩方圓,輸般實有所不得已,即曰神明變化,初不外乎此也。”[13](P613)他認為“規矩方圓”等法度,即使是公輸般也“有所不得已”,必須遵循繩墨標準,事物的神明變化也是從法度中表現出來的,他在《評沈梅村古文》中指出:如果作文時不“繩之以法”,那行文就猶如脫韁的野馬、崩決的洪水,一發而不可收,給文章帶來危害,因此,他認為八股文寫作也應有一定的法度。故“童子欲其成章,譬如梓匠輪輿,莫不有繩墨也”。時文寫作不可無法,只有這樣,才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但他又認為時文雖有一定之法,但非一成不變,故提倡靈活運用的“活法”,反對機械呆板的“死法”。他在《古文十弊》中說:“古人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13](P20)故法隨文變,法為文用。章學誠在《〈文格舉隅〉序》中說:“格者,因題定法之謂也,法出于理,理貫全章,而題有限畫,法之所有生也。”“古人文無定格,意之所至,而文以至焉,蓋有所以為文者也。文而有格,學者不知所以為文,而兢趨于格,于是以格為當然之具,而真文喪矣。”[13](P320)文無定格,文隨意生,意變化不拘,意不同文則不同,法亦靈活變化。至如其《趙立齋〈時文題式〉引言》中:“余惟古人文成法立,如語言之有起止,啼笑之有收縱,自然之理,有一定式哉?文而有式,則面目雷同,性靈錮蔽,而古人立言之旨晦矣。然國家取士用四書文,自前明以來,其與選者,皆謂中式。豈以錮蔽性靈,雷同面目,求天下士哉!”[13](P321)論之再三,旗幟鮮明。
鑒于上述所論,章氏一方面主張時文須遵循一定法式,另一方面又認為文無定法,不可拘泥膠著、作法自斃。其實,章氏之論早在時文“死法”之弊出現的宋代,便有以啟之,但最初萌生于詩學領域。南宋高宗朝時,江西詩派領袖呂居仁在其《夏均父集序》一文中,詳細闡釋了他構思醞釀已久的詩歌活法論,即“規矩備具,而能出于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背于規矩”。同時,呂氏亦不忽略規矩之外的自身體悟,曾說:“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幸可得也。”[17](P594)并拿東坡作文、山谷寫詩來作典范。其實,蘇軾早已在文章中對自己的作文方式有所論述,即“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以及“行于所當行,于不可不止”云云[18](P2069),任天機而黜人巧,實質上,都是對文章學中活法理論的形象闡述。
此外,南宋初年,張孝祥在《題楊夢錫客亭類稿后》中評論楊氏文章“不膠于俗,縱橫運轉如盤中丸,未始以一律拘,要其終亦不出于盤”,同時亦申明了“為文有活法”的宗旨,而那些“能今而不能古”者,正是拘泥執之的結果。[19](P218)無論是思想特質還是措辭風格,都可以視作呂本中的“活法”詩論在文論領域中的挪借。除此之外,南宋紹熙年間的王正德在其《馀師錄》中便對北宋蘇洵“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的“風水相遭”理論,進一步發揮:“文章態度如風云變滅,水波成文,直因勢而然。”所以若“執一時之跡以為定體”,終會墮系風捕影之謬妄。[7](P362)而慶元時期的俞成在《螢雪叢話》中亦道:“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而死法則“膠古人之陳跡而不能點化其句語”。故而可知,剽奪蹈襲即謂“死法”,自然千篇一律、頹敝枯槁,無新人耳目之效;奪胎換骨即謂“活法”,自能觸處生春、左右逢源,令人賞愛不倦。延至宋末,持此論者依舊不絕,陳模《懷古錄》便言“文法好處只用得一回新,蓋常用則腐”,“作古文須要不法度而自法度”又“文字須要自我作古,其次師經,師古文又次之。”[7](P524-525)至于后世論文,雖零散冗雜,但語言表述卻多有相似相通之處,實難于此一一詳述,茲舉數例,以窺其大端。
綜上所述,“活法”既是一種學理上的觀念表述,也是創作中的理想境界,它無形卻有力,沉淀于作文者的潛意識里,并在冥冥之中引導著作家的價值取向與實踐操作。正如宋人將風行場屋的四六文,按照不同名家的不同風貌,劃分為“荊公派”和“東坡派”,一為謹守法度、規模古制,另一則逸出常軌、另生波瀾。路數迥異,特色與成就自然也相去甚遠。但不可否認,文章學的建構與成熟起于科場,一路伴隨著文法的從無到有,又從謹嚴精細到作法自斃。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地總結經驗教訓,調整既成的法則,使之適應于不斷發展的審美旨趣,既是對“法”的建構,也是對“法”的超越,看似循環,實為升華;看似疏離,實為深化。章學誠其實也正是在這條宋人開辟的軌道上,將這種文法論進一步拓展、提升、完善、充實起來,他的理論高度正是建立在宋代文章學的基石之上。
三、結語
行文至此,倘若套用一句宋人論文的專用習語來概括總結,即宋代文章學實是我國古代文論發展過程中的“關鍵”與“緊要”所在。但后人在論及涉及文法的種種問題時,總是喜歡將關注的目光,聚焦于明清以來日漸紛雜的學統文派與苛細的法度繩律,文法論便是典型代表。但其實,這是割裂的、片面的,因為中國文法論的發展脈絡源遠流長,而宋代尤其是一個漸趨成熟的時期,宋人的很多理論建構,對于后世都影響深遠。故而,祝尚書將這個時期的文章學發展所取得的成就、其觸發的拓展創新點、對后世的沾溉意義,評定為前無古人,后無來者。是有其道理的。
就這一點而言,以清代這樣一個文學發展包羅萬象的集大成時期,以章學誠這樣一個文史理論建構的杰出代表,作為考察支點,探究宋代文章學中“以古文為時文”的經典論說,與后世尤其是清代章學誠文法論的綰合之處,來尋繹其間的發展演變脈絡,雖只是以管窺豹、以蠡測海,庶幾有所創獲。
[1](清)章學誠.文史通義校注[M].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
[2]王水照.文話:古代文學批評的重要學術資源[J].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4).
[3]祝尚書.論宋元時期的文章學[J].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2).
[4]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匯考[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5]程千帆.文論十箋[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9.
[6]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
[7]王水照.歷代文話[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8](宋)唐庚.唐先生文集[M].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4.
[9]曾棗莊,劉琳.全宋文[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
[10](宋)費袞.梁溪漫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1]謝采伯.密齋筆記[M].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
[12](清)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外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
[13](清)章學誠.章學誠遺書[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4](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M].上海:上海書店,1989.
[15](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6.
[16](元)劉將孫.養吾齋集[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17](宋)呂本中.童蒙詩訓[M].宋詩話輯佚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
[18](宋)蘇軾.蘇軾文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6.
[19](宋)張孝祥.于湖居士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責任編輯:張 麗】
I207.6
A
1004-518X(2016)05-009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