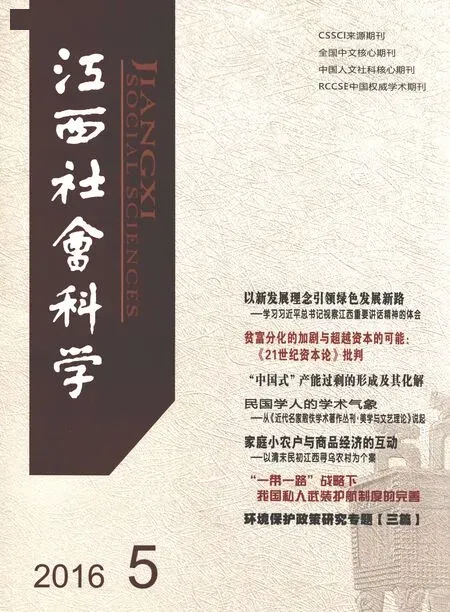對立統一的平衡美
——論蘇洵散文的藝術追求
■李亦凡
對立統一的平衡美
——論蘇洵散文的藝術追求
■李亦凡
蘇洵自稱其文“得乎吾心,成于自然”,而實際上,蘇洵的文章也有刻意錘煉的一面。他文章中對立要素的平衡與統一是一大特色,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蘇洵之文,確具構思之功。這一特色表現在風格、修辭、結構、語言等四個方面,具體展示為犀利與委婉、雄剛與溫淳、工整與變化、凝練與生動的統一。這種對立統一使蘇洵散文呈現出平衡美,不同于同時代其他作家的散文而別具風貌。蘇洵散文之所以具有這一藝術特色緣于蘇洵所處的文道和諧的政治時代、置身的三教合一的思想環境和自身的落拓曠達的性格氣質,此三者的合力造成了蘇洵散文風格、修辭、結構和語言的兩重性特征。
蘇洵;散文;對立統一;平衡美
李亦凡,贛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江西贛州 341000)
一、前言
蘇洵(1009-1066),字明允。他的文學成就在散文,尤好議論。在《嘉祐集》中,議政如《審勢》《遠慮》《養才》等;議兵如《心術》《法制》《強弱》等;議經如《易論》《禮論》《春秋論》等;議史如《六國》《項籍》《高祖》等;議文如《仲兄字文甫說》。所涉范圍甚廣,且精義迭出。因此,以議論行文是蘇洵散文的一大特色。
表面觀之,蘇洵散文以氣勢充沛、雄辯有力見長。實際上,蘇洵散文并不一味追求力度,而是在更深層次上,尋求對立要素之間的平衡。這種對立統一呈現的平衡美,蘇洵也有一定自覺,在《上歐陽內翰第一書》中論及孟子、韓愈和歐陽修之文時曾云:“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自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余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①蘇洵在此反復用“而”字來凸顯這種對立的平衡顯示了這種對立平衡的審美觀,既是蘇洵對孟、韓、歐創作風格的概括,也是他的夫子自道,言己一脈相得。隨后在《上田樞密書》中一段學文自述,可以看作是他對自己寫作風格的總結:“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疏闊,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蘇洵自許“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兼得眾家之長“優柔”、“溫淳”、“雄剛”、“精深”、“簡切”而融為一體,追求對立統一之平衡。這些正是蘇洵散文特色的精確概括。
二、蘇洵散文的藝術特色
(一)風格:犀利與委婉
蘇洵散文詞鋒犀利,言必中當世之過,但與此同時,又很注意在行文時折轉筆鋒,緩和語氣,改變文章節奏,使人易于接受。樓昉評曰:“議論精切,筆勢縱橫,開闔變化,曲盡其妙。詞嚴氣切,筆端收斂頓挫,十分回斡精神。”[1]以《遠慮》為例,此文為蘇洵有感于慶歷中范仲淹入相府,推行新政,功未成而罷去,慮及天下或將有卒然之憂、不測之變而作。開篇以圣人之道起,曰“經”,曰“權”,曰“機”,引出天子不可一日無腹心之臣,娓娓道來,語氣舒緩。再援征故實,暗藏鋒芒:“《傳》曰:‘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于其間邪?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推論至此,筆勢才起,鋒芒乍現,一改前文指事析理的平緩語氣,矛頭直指當時天子昔日任相之過:“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為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舍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于下,而天子煢煢于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責讓一番,筆勢復又回落,語氣趨緩,再轉而規勸:“圣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臥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疏,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后可以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遠慮》以圣人開篇,又以圣人作結,首尾關鎖,神完氣足,本意仍是希望當時天子應有人君之機,“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既犀利揭示問題,又留有余地,對當時天子有所回護,落腳點還是為天子分憂,而非議論“君德”。全文既顯鋒芒,又存體統,文意幾番曲折,歸于安和,呈現對立平衡的特殊美感。讀之者,但見其可悅,不見其可憎。
縱觀蘇洵之政論,大多采用這種剛柔相濟的寫法。如在《上皇帝書》中指陳任子制度弊端,措辭尖銳,直言廢除這一制度,但對廢除任子制度的益處,則語氣舒緩,與《遠慮》正是同一機杼。
(二)修辭:雄剛與溫淳
蘇洵散文氣勢磅礴,感情充沛,所向披靡,不可遏止,給人以雄健、剛強的感覺,但轉而又會淡化筆勢,溫淳語氣,使“雄剛”和“溫淳”達到平衡和統一。謝枋得評曰:“議論精明而斷制,文勢圓活而委曲,有抑揚,有頓挫,有擒縱。”[1]以《養才》為例,蘇洵有感于當時國力貧弱,強鄰壓境,亟須擢用奇杰之士以施振作,而朝廷因循碌碌,致豪杰之士淪落不偶,故發此刺骨振聵之論。開篇排比、對偶疊加,遞進、摹狀反復,文氣雄健難當,看之賞心悅目,讀之瑯瑯上口,鏗鏘有力,產生一種氣勢美,但轉而蘇洵又輔之以譬喻和設問反復論證。“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賢于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舍其弓以揖讓于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易勉也。”語氣溫和淳樸,使人不覺其厭,宜乎人樂聞也。再如《仲兄字文甫說》,極寫風水之觀,實為立象盡意,抒發風行水上自然成文之理。文字鋪張揚厲,“如大山之云出于山,如大川之滔至于海”,[2]一瀉千里,勢不可擋,雄偉壯觀。然轉而文勢頓收,“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將成文之理輕輕道破,雄剛與溫淳自然契合。
(三)結構:工整與變化
蘇洵散文結構工整嚴謹而又富于變化,隨物賦形,不拘一格,內容和形式有機統一。曾鞏評曰:“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3]
蘇洵文章結構可歸納為三種形式:宮殿式、園林式和塔樓式。宮殿式結構中軸突出,左右對稱,首尾呼應,一貫到底,立論在文首,論題嚴肅,多采此結構,如《六國》;園林式結構七折八轉,九曲回廊,雖布置無方,但錯落有致,立論在文中,論題復雜,多用此結構,如《審勢》《辨奸論》等;塔樓式結構基礎堅實,層層剝離,尖端突出,前文醉翁之意不在酒,立論或文眼在文末,抒懷明志寓情,多選此結構,如《送石昌言使北引》《木假山記》等。三種結構在外表上都工整嚴謹,內部卻變化無窮。
如《春秋論》可分為五段,像一座標準的中國式五重體殿堂,莊嚴肅穆。文章開篇即提出一個嚴肅問題,即“賞罰權”的問題,由此帶出主題,即孔子是否有權以魯國立言賞罰天下“其何以賞天下”?此為第一個問題。全文據此以“賞罰權”為中軸展開。第二段為過渡段,蘇洵卻轉而談“位”和“道”的關系,說“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并說“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于是非”,并提出:“夫子賞罰何以異此?”此為第二個問題。第三段為主體,先正面論述孔子作《春秋》是為魯國作史,為公不為私。接著再提出既為魯史,那就只能于魯國之內進行賞罰,為什么連及天下,僭用天子之權?此為第三個問題。蘇洵為之解釋,因為魯為周公封地,魯君為周王苗裔。周室衰落、天子失權、諸侯紛爭之下,魯承周公之緒,攝天子之權以定天下之是非,作《春秋》是“天子之權授于魯”,于道義合法給予了回答。再接著蘇洵筆鋒又一轉,為什么要以魯,而不以齊、晉來行賞罰呢?此為第四個問題。回答為齊、晉表面尊重周天子,實際卻意在壯大自己的力量,“與其事不與其心”,所以賞罰之權不能給予齊、晉。第四段為補充段,批駁子貢等人以《春秋》為夫子個人之作的認識,以“夫子《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回答了開篇所提兩個問題。最后一段點出“《春秋》有天子之權”作結。全文以“賞罰權”為線索,引繩穿珠,層層緊扣,一以貫之,首尾呼應,結構工整,無懈可擊;行文上卻又四辯四解,枝葉橫生,一節未盡,又生一節,變化多端。工整與變化巧妙配合,收相得益彰之效,既具大家氣度,又不失細節精致,增強了文章的感染力。
(四)語言:凝練與生動
蘇洵散文語言字字珠璣,既古樸凝練,又生動形象,質而實綺,簡而多姿,令人回味無窮。姜寶評曰:“文似孫子,而文采過之。老泉自謂‘孫、吳之簡切,無不如意’,非夸辭也。”[1]以《心術》為例,文章首論治心之重要,其下分論七事,看似各不相屬,實皆治心之要。全篇逐節自為段落,先后不紊,個別字的變化帶動全文,由治心而養士,由養士而審勢,由審勢而出奇,由出奇而守備。每段行文皆緊湊簡潔而又形象生動,語句之凝練,多成名言。
又如:“噫!隱而章,則后人樂得為善之利;直而寬,則后人知有悔過之慚;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樂之為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為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為《春秋》繼,而使后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史論中》)高度凝練的警句,置于文首,為文章制造了氣氛,吸引讀者的注意力;置于文中,使文章波瀾壯闊,跌宕起伏,提升了文章的感染力;置于文末,使文章干凈利落,發人深思,可謂各有所宜。
三、蘇洵散文藝術特色形成的原因
蘇洵散文之所以形成犀利與委婉、雄剛與溫淳、工整與變化、凝練與生動這樣對立統一的藝術特色并非偶然,與他所處的政治時代、置身的思想環境、自身的性格氣質息息相關,正是三者的合力造成了蘇洵文章風格、修辭、結構和語言的兩重性特征。
首先是文道和諧的政治時代。北宋開國之初,宋太祖趙匡胤便制定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國策,廣開言路,鼓勵士大夫直諫敢言,針砭時弊,營造了宋代當時寬容淳厚的政治氣氛。至蘇洵所處時代,士大夫自身強化了時代的責任意識,強調“通經致用”。歐陽修:“六經所載,皆人事之切于世者。”[4]士大夫關心國家命運,高揚崇高氣節,體恤民生疾苦。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成為這種自主氣節的突出表率。之于文學,從唐韓愈的“文以明道”至周敦頤的“文以載道”再至歐陽修的“文道并重”,形成了有史以來未有的文道和諧氣氛,道倚文而永存,文因道而增輝。處在這樣一個文道和諧、政治寬厚的時代,蘇洵不但在思想上受到了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和直言敢諫品格的熏染,而且在藝術創作上也受到了和諧統一氣氛的感發。
其次是三教合一的思想環境。北宋儒道并立,佛釋兼容,三教合一,使宋代士大夫對儒家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天下有道則進,無道則隱”這一沖突的傳統價值觀念與處世方式進行了中和。于其身,勇于擔當的社會責任感與追求個性的自由、人格的獨立已不再彼此對立,儒家“內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和事功思想融于內,道家輕去就、任自然和佛家追求自我超脫化于外,借此消解社會責任和政治抱負加之于身的壓力,求取內心的適意與自由,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三教合一的思想環境對蘇洵思想的兩重性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蘇洵在三次應試不舉后,轉而絕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學術,寫就策、論、書百篇,正是受儒家“進則立功、退則立言”的思想影響;與此同時,閉門讀書,清靜無為中所著策、論、書,全系究古考今,談兵論政,又顯現了道家老子無為而無不為的思想。
再次是落拓曠達的性格氣質。蘇洵遠祖歷史上曾取得輝煌的功烈和顯赫的地位,而至其曾祖、祖、父,三代布衣,清貧自守,聲名不顯于世。作為后世子孫,蘇洵性格里一方面承繼著先人積極進取、建功立業的精神,另一方面又感染著父輩們世事洞明、通達豁然的氣質(《族譜后錄下篇》),加之蘇洵個人際遇,青年時期的“落拓鞍馬”、“從士君子游”,壯年時節的屢試不第,磨礪了蘇洵落拓與曠達的性格氣質兩重性,落之于筆端,形成了蘇洵散文藝術的兩重性。
四、結語
蘇洵認為,文章要“得乎吾心”,要“有為而作”,“言無有善惡者,茍有得乎吾心而言也,則其詞不索而獲”。“得乎吾心”強調自然,不索而獲,是情到深處,厚積薄發。他的確是按照這個標準來寫文章的。但所謂“得乎吾心”的自然,并非排斥淘洗之功,相反,蘇洵散文正因為經過了精心錘煉,方使各種對立要素統一起來,達成了一種微妙的平衡;進而言之,最終更達到了自然和有為的對立統一,形成了獨具一格的風貌,也彰顯了蘇洵思想性格的兩重性。正如清人邵仁泓在《蘇老泉先生全集序》中所言:“先生之文,蓋能馳騁于孟、劉、賈、董之間,而自成一家者也”。[5]
注釋:
①本文所引蘇洵文均據蘇洵:《嘉祐集箋注》(曾棗莊、金成禮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以下僅注篇名于正文中。
[1](宋)蘇洵.嘉祐集箋注[M].曾棗莊,金成禮,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宋)張方平.張方平集(卷39)[M].鄭涵,點校.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3](宋)曾鞏.曾鞏集[M].陳杏珍,晁繼周,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4.
[4](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卷47)[M].李逸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1.
[5](清)邵仁泓.蘇老泉先生全集(卷20)[M].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邵仁泓安樂居刻本.
【責任編輯:田 鑫】
I206.2
A
1004-518X(2016)05-01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