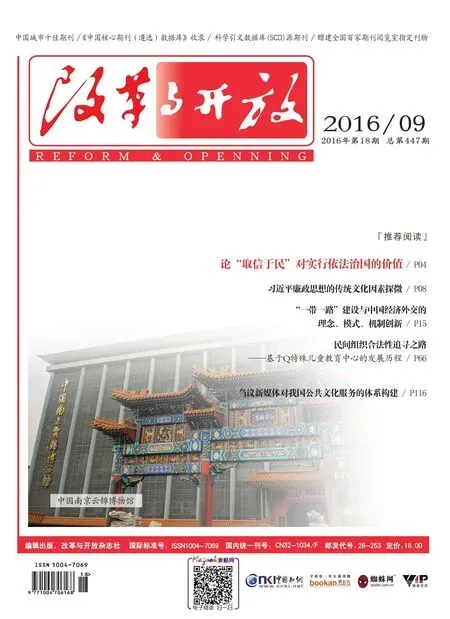“互聯網+”時代版權技術措施的法律保護
——以北京精雕科技有限公司訴上海奈凱電子科技有限公司案為例
劉亞川琦
?
“互聯網+”時代版權技術措施的法律保護
——以北京精雕科技有限公司訴上海奈凱電子科技有限公司案為例
劉亞川琦
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信息傳播的快捷、廉價,導致著作權人的權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本文援引北京精雕科技有限公司訴上海奈凱電子科技有限公司案,并根據“互聯網+”時代下版權保護的新情況,展開對于技術保護的細化分析。本文主要從技術保護的理念以及技術保護的措施來分析“互聯網+”時代下,如何更好地利用技術措施來達到權利人和公眾間的利益平衡。
網絡版權;利益;技術措施;資源配置
在“互聯網+”的時代背景下,權利人與傳播者以及公眾之間的利益取舍,不僅對當下世界的版權保護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也為我國建設創新社會提出了難題——即網絡版權保護對法治體系建設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的同時,如何平衡利益與正義,權利人采取何種技術措施才能更好地實現資源的最優化配置。這成為當下版權法治建設的必然要求。
一、北京精雕科技有限公司訴上海奈凱電子科技有限公司案件引發的思考
1.案件概述
北京精雕科技有限公司自主開發了精雕CNC雕刻系統,該系統的JD Paint軟件通過加工編程計算機運行生成Eng格式的數據文件,再由運行于數控控制計算機上的控制軟件接收該數據文件,將其變成加工指令。2006年年初,上海奈凱電子科技有限公司宣傳其開發的NC-1000雕銑機數控系統全面支持精雕各種版本的Eng文件,并且數控系統中的Ncstudio軟件能夠讀取JD Paint軟件輸出的Eng格式數據文件,而北京精雕科技有限公司對Eng格式采取了加密措施。
2.案件評析
法院認為Eng格式數據文件中包含的數據和文件格式均不屬于JD Paint軟件的程序組成部分,不屬于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的保護范圍。精雕公司在本案中采取的技術措施,不是為保護JD Paint軟件著作權而采取的技術措施,而是為獲取著作權利益之外的利益而采取的技術措施,奈凱公司開發能夠讀取JD Paint軟件輸出的Eng格式文件的軟件的行為,并不屬于故意避開和破壞著作權人為保護軟件著作權而采取的技術措施的行為。
“互聯網+”時代背景下,促進了技術和信息的自由傳播,網絡的終端設備遍及全球,要確認網絡中某個行為的實施者已實屬不易,而此時要將侵權行為等內容通過證據加以固定,的確很難做到。因此界定何種技術措施屬于法律準許的技術保護措施以及何種技術規避措施不屬于侵權行為在案件審理中顯得尤為重要,本文擬就此做出探討。
二、“互聯網+”時代下計算機軟件保護范圍的界定
在上述案件中,法院認為北京精雕科技公司的格式數據文件本身不是代碼化指令序列,也無法通過計算機運行和執行,那“互聯網+”時代版權下,計算機軟件著作權保護范圍到底該如何確定?
根據我國《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第二條規定:“本條例所稱計算機軟件(下稱軟件),是指計算機程序及其有關文檔。”第四條規定:“受本條例保護的軟件必須由開發者獨立開發,并已固定在某種有形物體上。”通過此法條可以得知,計算機軟件是以保護程序和文檔為限的。但是更進一步討論,卻發現在現行的司法實踐中,軟件程序和文檔該如何界定沒有一個統一規定。
三、技術措施保護下是否適用合理使用制度
在互聯網高速發展的當下,技術性措施給權利人帶來了安全感,但是從另一方面也給大眾接觸作品增加了難度。首先,在“互聯網+”的時代背景下,不僅傳統作品的形式被改變,而且對現有作品的傳播方式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但正因為網絡環境對于版權人的保護不佳,權利人一旦不受限制地使用技術性措施,總是會將其使用到極致。正如美國斯坦福大學萊斯格教授指出:“著作權法律原先只是一面盾牌,保護著作權人不受傷害,而如今有些人卻肆無忌憚地將其作為刀劍揮舞,無情地將文化自由踐踏于地下。”而法律又必須限制這種信息的壟斷,因為版權法的立法目的不僅在于保護權利人的權利,同時也要保證信息更好地傳播。所以,傳統版權中的合理使用制度是否能夠在此適用則顯得尤為重要。
在“互聯網+”時代下,如果版權人采取了一定的技術控制,則公眾要以合理使用為前提接觸作品,就必須要征得版權人的同意,讓版權人取消技術保護,或者只能采取一些破解或者規避技術保護的措施。現有的技術保護措施采取的是全有或者全無的保護措施,技術保護措施根本無法自動區別公眾接觸作品的行為屬于合理使用范圍還是侵權行為。
筆者認為,在互聯網時代下我們應該以信息記錄的方式來保護合理使用制度。此種技術措施的保護符合版權法的立法目的,也具有現實的可操作性。對信息進行記錄,一方面可以讓版權人對自己的作品實際享有控制權的同時,還有利于權利人對于他人使用自己的作品進行監督,有利于發現侵權行為;另一方面可以讓社會公眾接觸到作品,繁榮社會文化。
四、互聯網版權技術保護措施的新思維
1.技術措施保護范圍的新理念
在新的網絡環境下,有的學者提出,在網絡信息保護中,我們可以通過技術對信息加以控制,使其私有化。日本學者中山信弘主張采取雙軌制版權結構,對傳統媒體與數字媒體采取不同的版權保護模式。德國的著名經濟學家阿諾德·匹克特在他的著作《網絡經濟》一書中認為現在網絡的影響將推翻一些傳統的市場規則。這種新的市場規則使得我們的一些法律規則不再適用這種新的虛擬的現實。一些支持知識產權法的基本的假設被動搖了。我們不可能再按照傳統的版權保護理念對“互聯網+”時代下版權進行保護,因為保護的主體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原來的老辦法也就失效了,我們需要新的保護理念來對網絡環境下的數字作品進行實質性的保護。
筆者認為信息記錄的技術保護更具有現實意義。在網絡環境下,要保護好版權人的利益,必要的技術措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著作權絕不僅僅偏向于權利人,而且更應該顧及公眾利益。在Feist案中,美國最高法院指出了版權法的兩個基本原理:版權保護的目的不是為了回報作者,而是為了增加整個社會的知識財富;任何人都不能對“事實”或“思想”享有版權。如果我們的著作法將所有的權利全部交給版權人,那就等于剝奪了其他人在某種程度上模仿的自由。所有的作品都產生在借鑒前人的成果之上,如果公眾無法接觸到作品,何來創作呢?
2.規避技術措施處理的新理念
馬克思曾說過:“利益就其本性說是盲目的、無止境的、片面的,一句話,它具有不法的本能。”我們需要在商業價值和社會價值最大處來確定技術措施采取的限度,對版權人的權利進行限制。“權利限制”,就其本質講,是指有的行為本來應屬侵犯版權人的權利,但由于法律把這部分行為作為侵權的“例外”,從而不再屬于侵權。因此,有些國家的版權法中,把“權利限制”稱為“專有權所控制的行為之例外”。
對于技術規避措施,我們應該根據“設計目的標準”和“推銷目的標準”來判斷。如果一個作品僅僅具有設計目的,而不具有推銷目的,則不應認為其具有侵權行為。因為根據我國著作權法22條的相關規定,合理使用是法律為了推動社會科學、文化的發展而賦予公眾的一項權利,那么如果版權人采取了技術手段則會侵犯公眾的權利。但是我們現有的技術保護措施是“要么全部進行技術保護,要么全部不進行技術保護”,技術保護措施根本無法自動區別公眾接觸作品的行為屬于合理使用的范圍,還是侵權行為。所以只有在一個技術規避措施具有推銷的目的,也就是向不特定的人提供時,才認定其構成侵權。
在技術保護措施下,是不可能分辨出使用者的行為到底是侵權或者是合理使用而對其進行區別對待。并且版權人自己可以通過技術措施來對自己的作品進行控制和保護的,對于依賴國家給予強有力的保護也相對減弱,“互聯網+”時代下的版權也不應再受合理使用制度的限制。對于網絡環境中的數字作品,我們能夠通過技術保護措施對其實現保護,因此,也應該給其脫下傳統版權法中權利限制的大衣。
綜上,在“互聯網+”新時代下,網絡環境本身就偏愛使用者一方時,要加大對版權人的保護。所以版權人應該更多地依賴技術措施對自己的權利進行保護,并且通過市場經濟的調整力量,我們根本不用擔心采取技術措施會阻礙知識的傳播或者技術的創新。
[1]從立先.網絡版權問題研究[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2]楊柏勇.網絡知識產權案件審判實務[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3]鄭成思.知識產權—應用法學與基本理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4]羅伯特·考特,托馬斯·尤倫.,張軍,等譯.法和經濟學[M].上海:上海三聯出版社,1994.
[5]梅術文.著作權法上的傳播權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6]鄭成思.知識產權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7]麥拉·J·陶菲克.國際版權法與作為“使用者權利”的合理使用[N].版權公報,2005(2).
[8]梁清華,汪洋.數字數代版權領域的利益沖突及解決思路[J].知識產權,2004(5).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
10.16653/j.cnki.32-1034/f.2016.18.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