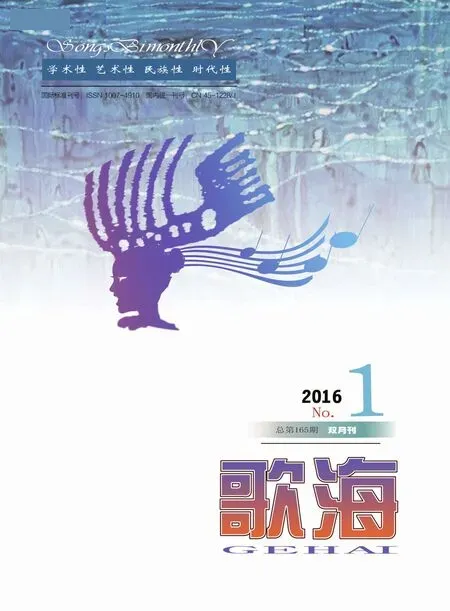談地方戲的題材挖掘——兼評壯劇《馮子材》
●馬瑜萍
?
談地方戲的題材挖掘——兼評壯劇《馮子材》
●馬瑜萍
[摘要]馮子材以70歲的高齡出征打敗法國的侵略者,取得了我國近代史上難得一見的勝利——鎮(zhèn)南關(guān)大捷。壯劇《馮子材》呈現(xiàn)了民族英雄馮子材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敢于擔(dān)當(dāng)、不屈不撓、英勇頑強(qiáng)的氣節(jié),是一部愛國主義和廣西民族特色結(jié)合得非常好的新編歷史壯劇。
[關(guān)鍵詞]馮子材;鎮(zhèn)南關(guān)大捷;祭墻;九命貓
2015年11月14日,廣西戲劇院精心打造的新編歷史劇《馮子材》在南寧人民會堂上演。劇院外,朔風(fēng)凜冽、冷雨敲窗;劇院內(nèi),演員熱情飽滿,觀眾情緒高昂;舞臺上,演員們驚艷亮相,以嫻熟的技藝演繹精彩故事;舞臺下人氣爆棚,座無虛席。劇場內(nèi)不時爆發(fā)出暴風(fēng)驟雨般的掌聲和此起彼伏的喝彩聲宣告著觀眾的認(rèn)可和喜愛。
廣西是壯族文化與嶺南文化匯聚交融之地。由于西南邊疆移民、湖南籍為主的嶺北移民遷入桂東北,以及以廣東、福建籍為主的嶺南移民遷入,形成了廣西獨(dú)特的地域文化。這里也是首批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壯劇”的發(fā)祥地。
壯劇《馮子材》講述的是清末光緒年間,國弱民窮,內(nèi)憂外患,西方列強(qiáng),覬覦華夏,虎視眈眈。1885年,法國侵略軍在主帥尼格里指揮下,悍然對廣西鎮(zhèn)南關(guān)發(fā)動攻擊。時任廣西巡撫潘鼎新不戰(zhàn)而退,致使鎮(zhèn)南關(guān)被毀,并被法軍插上“中國廣西南大門不復(fù)存在矣”的恥辱性木牌。此時的清廷,已然左支右絀,不得已任命早已解甲退隱的原提督馮子材出任廣西關(guān)外軍務(wù)幫辦、前敵元帥。馮子材心系家國安危,不顧七十高齡,在危局中毅然赴任。他向兩廣總督張之洞分析敵我態(tài)勢,帶領(lǐng)跟隨他幾十年的老親兵“九命貓”親赴前線,勘察軍情;冒險闖入鳳凰寨,說服壯族首領(lǐng)青鳳與朝廷聯(lián)手,共抗強(qiáng)敵;為勵士氣,他將馮家子弟兵“萃營”,布防于最前線,并命人抬著為自己打造的鐵皮棺材上陣,以示不惜性命,以身許國的決心。一場輸不起的戰(zhàn)爭,即將在鎮(zhèn)南關(guān)打響。“國是我的國,我命是國命!”眾將士在馮老將軍的感召下,與氣勢洶洶的法軍展開了生死搏殺……這是鴉片戰(zhàn)爭前后一百年間中國對抗列強(qiáng)的唯一勝仗,勝得雖是慘烈,卻也動人心魄。
對于這個發(fā)生了百余年,大家耳熟能詳?shù)臍v史事件,如何寫出新意?如何寫出時代感和地域性?如何寫出具有符合現(xiàn)代人審美需求、具有現(xiàn)代審美意識的戲劇?在筆者看來,有兩點(diǎn)十分重要。
首先是回歸戲劇本源,立足劇種特色。壯劇主要有三種表演風(fēng)格:第一種的音樂接近板腔體,表演風(fēng)格接近京劇、粵劇、滇劇等大劇種,這以“哎咿呀”、“哎的”和“乖海咧”三大聲腔為代表;第二種的音樂為聯(lián)曲體,類似廣西彩調(diào)、云南花燈那樣的民間小戲,以“咿嗬海”聲腔為代表;第三種是解放以后吸收了當(dāng)?shù)孛耖g歌舞新發(fā)展起來的品種。藝術(shù)本體特征是劇種生存、發(fā)展的核心和優(yōu)勢。劇本從創(chuàng)作之初就堅持和充分發(fā)揮劇種的獨(dú)特優(yōu)勢,凸顯劇種的本體特征,處處體現(xiàn)出對傳統(tǒng)藝術(shù)的敬畏,尊重藝術(shù)規(guī)律,圍繞演員寫戲,把舞臺充分地留給演員。如第八場《祭墻》一段:
靈兒:我看見阿叔還有阿伯們了……阿爺,給……
給靈兒戴朵花……
馮子材:好,好,戴花,戴花……(四處找花)
靈兒:(伸手掐下身邊石縫里的小花插在鬢角,微笑)阿爺……你……好笨啊……(死去)
馮子材:(撕心裂肺)靈兒、靈兒,我的靈兒哪!
面對“靈兒”的死,馮子材高腔、彈腔兼唱,唱做并重,濃墨重彩地寫下數(shù)十句唱段,演員唱的時候一氣呵成,行腔走板,猶如高山流水,響遏行云,演員唱得痛快,觀眾聽得過癮。
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方言鄉(xiāng)音的不同,民風(fēng)民俗的不同,寄寓了一方人的精氣神,也是本地戲曲藝術(shù)豐厚的土壤。
廣西壯劇,心口相傳,結(jié)合本地音樂、小調(diào)和語言,傳承至今,歷久彌新,本地觀眾爭相觀看,不僅僅因?yàn)樗且婚T供人觀賞的表演技藝,更因?yàn)樵谟^賞之中能感受到壯劇藝術(shù)所傳達(dá)出的深厚人文內(nèi)涵與豐富的社會背景,感受到戲曲藝術(shù)所傳遞出的不同歷史發(fā)展時期的時代精神、民眾意志以及藝術(shù)審美的趣味追求。因此劇本在有效傳承劇種藝術(shù)特色的同時,還有意書寫了廣西獨(dú)特的山水美景、風(fēng)土人情、歷史文化、傳說故事、民族歌舞和壯族人火辣辣的情感。
馮子材和壯族人民聯(lián)合起來,動員了壯族同胞的力量,共同抗擊外國侵略者。該劇用壯劇的形式來演繹,表現(xiàn)壯鄉(xiāng)的民族特點(diǎn)、地域風(fēng)情, 渾然天成。
其次是把握時代意識,致敬古典情懷。題材可以是歷史的,但創(chuàng)作理念和立意必須是現(xiàn)代的。站在現(xiàn)代人的立場上再現(xiàn)經(jīng)典,適當(dāng)取舍,挖掘經(jīng)典中歷久彌新的永恒主題,讓厚重的經(jīng)典成為現(xiàn)代人源源不斷的心靈慰藉。當(dāng)白發(fā)須眉的將軍,挎刀上戰(zhàn)場的時候,展示了馮子材的情懷。馮子材的仁愛、情感在劇中得以展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理念拉近了古人和現(xiàn)代人的距離。
劇本除了重塑了馮子材的形象,還塑造了九命貓、青鳳等人物形象。青鳳、靈兒、老夫人就好似壯族人的群體畫像:火辣、直爽、愛憎分明,明辨是非,英勇彪悍。豐富了潘鼎新的原有形象:陰險狡詐,詭計多端,貪生怕死。五個個性豐滿、形象鮮明的人糾葛在一起,觀眾愛看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不得不承認(rèn)該劇在武打、格斗上也有一定的缺陷。或許導(dǎo)演是千方百計地掩蓋演員的弱點(diǎn),但如果能更多地呈現(xiàn)戰(zhàn)爭的殘酷和血腥,這樣可能會更好。有幾個演員是不錯的,飾演馮子材兒子的演員嗓子不錯,一張嘴就有戲。飾演九命貓的演員也不錯。馮子材夫人的表演有點(diǎn)弱,如果是老旦來唱的話,那會更好一些。
另外,壯劇的特點(diǎn)還不夠鮮明。比如我們的彩調(diào),“多謝了”,三個字這么幾個音符,一聽就是彩調(diào)。能不能在壯劇最典型的幾個音符里做文章,把壯劇的味道唱出來,這樣對人物也是一種提升。雖然可以讓主演以情或者其他的方面取勝,但還是要想辦法揚(yáng)長避短。
在二度創(chuàng)作中,依然讓戲曲回歸本源。總導(dǎo)演熊源偉說,整部戲完全繼承了傳統(tǒng)戲曲的程式,四功五法樣樣俱全,保留了戲曲的根和精華。在舞美、音樂、燈光方面,又運(yùn)用了創(chuàng)新的手法,貼近現(xiàn)代觀眾,在繼承傳統(tǒng)的基礎(chǔ)上有新發(fā)展。劇本很有厚重,有一定的文化底蘊(yùn),用壯劇這個劇種演繹是非常合適的。編劇和演職人員按戲曲規(guī)律來創(chuàng)作和演繹。熊源偉說,在當(dāng)下藝術(shù)風(fēng)格越來越趨同的形勢下,能堅持傳統(tǒng)理念,保留傳統(tǒng)文化和戲曲的傳統(tǒng)程式是非常值得推崇的。
這部戲很壯觀,先聲奪人,有一種以勢壓人的感覺,征服了觀眾。但這個戲本身的情感還沒有勾出來了。劇中講三千人死了兩千,是很空洞和概念性的東西。數(shù)字可以說明問題,但震撼性沒有具體地表現(xiàn)出來。馮子材當(dāng)時已是70歲的老人,他在戰(zhàn)爭期間承受的精神、肉體壓力是巨大的。一個民族英雄,一個大英雄,不僅心系國家,一定也有兒女情長。要考慮大局和小局,形而上、形而下的結(jié)合,這樣塑造出來的人物一定是有血有肉、立體豐滿。目前已經(jīng)有所呈現(xiàn),但還不是很濃烈。戲主要還是寫一個“情”字,如何能在宏大的故事中寫出情,讓故事更加扣人心弦,真正使觀眾感動乃至潸然淚下,這是歷史題材戲曲重要的課題。
作者簡介:馬瑜萍,女,廣西戲劇院二級編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