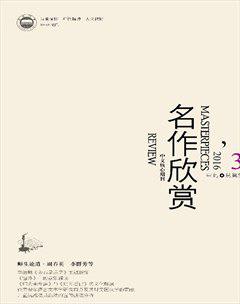漢代三種經學形態考辨
摘 要:今文經學、古文經學、讖緯經學并稱漢代三大經學形態。其中,今文經學多微言大義,標榜“經世致用”;古文經學注重訓詁與考據,追求對經書本身作確實的理解;讖緯經學吸收陰陽、天文等多方面的知識,包羅萬象、事豐奇偉,但多牽強附會,遭人詬病。
關鍵詞:今文經學 古文經學 讖緯經學
在漢代,儒學之位愈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儒家經典奉為國策,開設五經博士。由此,“經學”之名始出。學術與權術的結合,勢必為儒學在漢代之發展糅進新的元素。
今文經學、古文經學、讖緯經學并稱漢代三大經學形態,它們分別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占據主流地位。我們知道,“五經”即指《易》《書》《詩》《禮》《春秋》五部儒家經典,本文將以《春秋》為例,試述此三種經學形態之要義。
一、今文經學
漢武帝開設五經博士之初,今文經學即占據官學席位。今文經俱為口耳相傳,至漢初方用時下通行的隸書著于竹帛,并緣此得名。以《公羊春秋》而言,“(公羊)高傳于其子平,平傳于其子地,地傳于其子敢,敢傳于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及其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著于竹帛。”其間歷五世口傳,漢初始固定為文本,后立為官學。
《公羊傳》《谷梁傳》以及《左傳》并稱“春秋三傳”。傳為解經之書,此三者皆是對“春秋經”之說解,但在說解的內容與方法上卻大相徑庭。今文經多微言大義,附會陰陽災異,并宣揚“經世致用”。這一點上,《公羊傳》要比《谷梁傳》走得更遠。它所微言之“大義”最為著名的有“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這后來被董仲舒闡發為“三世說”:“《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于所見微其辭,于所聞痛其禍,于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董仲舒是西漢治《公羊傳》的大儒,著有《春秋繁露》。他在《公羊傳》數稱災異的基礎上,推而演之,將災異附會為上天對下界的警示,即神秘的“天人感應”。今文經學作為官學主流,為肉食者謀成為其安身立命之所在,但一味標榜“經世致用”也使它在某種程度上淪為政治的附庸。以《尚書·禹貢》治河,以《詩經》當諫書,以《春秋》治獄,把經學變為純粹的服務現實統治之工具,消融甚至泯滅其學術性。以《春秋·隱公元年》中“鄭伯克段于鄢”條為例,《公羊傳》這樣記載: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
借由這段文字,我們可以直觀地了解到《公羊傳》“解經”的重點并不在于把《春秋》寥寥幾筆記載的某一歷史事件詳細化——這是古文經學的特點,此為后話——其對字詞的說解,也并不是著眼于對經書本身的理解。透過一連串環環相扣的設問,傳者想要借助這一史實傳達些什么呢?是人倫綱常。鄭伯之惡,段之不弟,二者的行為都是有違人倫綱常的,皆不可取。“鄭伯克段于鄢”短短六個字在這里被發揮到倫理的層面,今文經學之微言大義以及“六經注我”的特點不言自明。這一傳統對后世影響深遠,宋明理學及心學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二、古文經學
古文經是流傳下來或重新發現的先秦保存下來的用六國文字書寫的經書古本,如比較著名的“孔宅壁書”。相較于今文經學被立為官學的顯赫地位,古文經自重新發現之初,不僅被排斥于官學之外,還屢遭詰難。質其偽者有之,譏其“非圣人所欲說”者亦有之。但歷史將會證明,立足于文字訓詁、名物考釋的古文經學反而以其厚積薄發擁有著更為強大的生命力。古文經學認為六經皆史,在說解經書時主要訓釋文字章句、考據名物典制。古文家追求對經書本身作確實的理解,故多在一字一詞間用功,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理論也就扎實、可靠。如此一來,古文經學雖然始終未能在官學之爭上壓倒今文經學,但在學術界卻逐漸取得優勢。至東漢時,各家多從古文經學,而治今文經的名家卻只有何休一人。《左傳》于《春秋》而言,意味不淺。前人曾這樣表述:“《左氏傳》于《經》,猶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圣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及至晉杜預“集春秋經與左氏傳而解之”“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后世多經傳并提,極少分而言之。與此對比鮮明的是,《公羊傳》與《谷梁傳》卻日益衰微。
《左傳》對“鄭伯克段于鄢”條的記載較長,此處不再贅述。前面談到過,《左傳》的大量筆墨都集中在對史實的再現,事件的起因、經過、后續發展完整地被記述下來。這就極大地幫助了我們理解經書原義。只有篇末一小段可以視為傳者的總結性陳詞:
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比之《公羊傳》的微言大義,這段話對經文幾乎是不作發揮的。觀之后世,古文家“我注六經”的勤勤懇懇,是古文經學擁有更為強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清代樸學是集大成者,考據被運用至學術研究的方方面面,結出累累碩果。無論何時何處,學術研究都不能缺乏端正客觀的態度以及翔實的資料準備。
三、讖緯經學
讖與緯多合而言之。事實上,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有了讖的身影。《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有條著名的記載:“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胡也。”秦始皇誤以為“胡”即胡人,甚至下令發兵擊之。相比之下,緯的出現就要晚得多了。一般認為,緯學興起于西漢末的哀平之際,至東漢蔚為大觀。之所以讖緯并稱,是因為緯書“言五經者,皆憑讖為說”。二者互為表里,相輔相成。與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以原典為中心的做法不同,緯學試圖另起爐灶,再造經典。正因為此,它作為經學一種的定位才顯得有些模糊。但不可否認,緯學是依托經書而存在的。只不過它以讖解經、以經文附會吉兇禍福,失卻了經書本有的質實。后世多稱緯學“儷經”之功,但病其荒誕者亦多。
讖緯之學在誕生之初就與權力的爭斗糾纏在一起。這無疑是它迅速崛起、盛極一時的主要推力,但也為日后屢遭禁毀直至佚亡埋下禍根。王莽曾借“告安漢公莽為皇帝”這一符命制造輿論,助己奪權。此后,劉秀平王莽之亂登上帝位,也借符命之說為自己正名。然而,讖緯在度過一段黃金時期后,開始為統治者所懼,焚毀、禁絕屢屢有之。被視為定型文本的東漢光武帝劉秀所頒布的圖讖八十一篇,早已散佚,今已無法得見全貌。我們只能從散見于類書中的以及經書注解引用的只言片語中略窺其面目。
《春秋緯》有《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緯書的書名已經給人晦澀的感覺了,至于內容更是包羅萬象、玄之又玄。這些緯書大都脫離《春秋》原典,只是擷取某一事件或人物,然后將其神秘化。具體方法有符命、異表、感生之說等。如《春秋演孔圖》中關于異表之說:“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堯眉八采,是謂通明。舜目重瞳,是謂無景。禹耳三漏,是謂大通。湯臂三肘,是謂柳翼。文王四乳,是謂含良。武王駢齒,是謂剛強”。關于感生之說:“孔子母顏氏徵在游大冢之陂,睡夢黑帝使請己,己往夢交,語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于空桑之中。”那么透過這些描述,緯學家要傳遞的是什么信息呢?是單純地要將這些歷史人物推向神秘嗎?或是通過這些神化的人物讓自己的學說顯得更為高深莫測?還是借助近似神話的話語使得文章更具可讀性?毋庸置疑,這些因素都是有的,但我們并不能將對緯學的認知停留于此。比起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它更大的價值在于文學想象及思想史層面。人類社會早期,生存于廣袤蒼穹下的人,對于頭頂這片未知的世界,是滿懷敬畏之心的。雷、雨、霧、雹、風、閃電、云氣等眾多自然現象都被當作“天”降下的某種警示,與人事息息相關。董仲舒就此附會出“天人感應”之說,讖緯更進一步,將這一觀念滲透至方方面面。而這種天人關系的認知,已經積淀為中華民族集體的文化心理,是傳統文化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小結
漢代經學在整個學術史及思想史上都有舉足輕重的位置。其中,古文經學的成就主要在學術方面,而今文經學與讖緯經學則主要是對思想史有所貢獻。它們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精華與糟粕之分未免太過絕對,但三者各自的價值與缺陷還是值得我們仔細甄別的。今文經學重視經書的實用價值,講求“經世致用”,自有其獨到之處。然凡事都是過猶不及,強解經意以合私意必將深陷主觀、附會之泥淖,于學術更是南轅北轍。古文經學立足文字訓詁、名物考釋,追求對經書作確實的理解,其質樸扎實的學風歷來為人稱道。但若一味索解字詞、名物,難免會有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之憾。讖緯經學包羅萬象、事豐奇偉,但它的賣弄玄虛、荒誕無稽也是不爭的事實。在學術這片土地上,每個學說都是一粒種子。生于茲,長于茲,方可成參天大樹。如若不根植于土壤,全憑主觀任意發揮,必將難以取信于人,從而走向衰微。
參考文獻:
[1]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第3版)[M].北京:中華書局,2009.
[2] (清)趙在翰輯,鐘肇鵬、蕭文郁點校.七緯(第1版)[M].北京:中華書局,2012.
[3] 張澤兵.讖緯敘事研究(第1版)[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4] 李宗桂.關于漢代經學的若干思考[J].學術研究,2011(11).
[5] 丁鼎.漢代今古文經學研究二題[J].史林,2013(6).
[6] 黃樸民.兩漢讖緯簡論[J].清華大學學報,2008(3).
作 者:謝冰冰,吉林師范大學文學院在讀研究生。
編 輯:張晴 E?鄄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