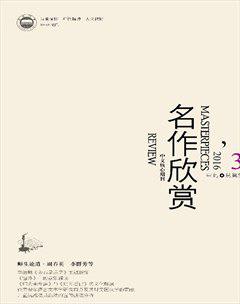宇文所安唐詩英譯的模糊表現形式及傳譯策略
劉永亮 劉澤青
摘 要:宇文所安唐詩翻譯的模糊表現形式呈現出多樣性,主要有語詞模糊、語法模糊、辭格模糊和意象模糊。語詞的模糊性使譯文語義精煉深邃,語法的模糊性使譯文詩句濃縮而經濟,辭格的模糊使譯文生動形象、意蘊豐富,意象的模糊使譯文產生深遠的聯想義。宇文所安在唐詩翻譯中利用移情、轉義、留白等傳譯策略,使唐詩的模糊美、意蘊美較好地傳達給了讀者。
關鍵詞:宇文所安 唐詩 模糊表達 傳譯策略
作為美國最著名的漢學家之一,宇文所安深諳模糊表達在詩歌中的重要性。故在唐詩翻譯中,宇文氏利用語言的模糊性特征,把中國古典詩詞的模糊美充分傳譯出來。通過研究其譯文,讀者會發現其充滿大量的模糊表達,既有語詞模糊、語法模糊,又有辭格模糊和意象模糊。這些模糊表達極大地提升了其譯文質量,使其譯文呈現出中國古典詩詞的意蘊美。究其因,這些模糊表達的實現策略主要取決于宇文氏對移情、轉義、留白等傳譯策略的充分運用。
一、宇文所安唐詩英譯中模糊表現形式
宇文氏譯介中模糊思維的表現形式呈現出多樣化特征。具體來說,有語詞模糊、語法模糊、辭格模糊及意象模糊。這些模糊手段的采用極大地提升了語詞的張力,豐富了譯文的聯想義,深化了譯文的意境。
1.語詞模糊
中國古詩大多篇幅短小、語言精煉,有著豐富的蘊意和情感內涵,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模糊語詞的選用。成功的模糊語詞運用能使詩句具有更強的啟示性和暗示性,也使語言材料具有廣闊、深邃的可挖掘潛勢。宇文氏在翻譯過程中同樣注重模糊語詞的廣泛使用。例如,杜甫的《曲江二首》:“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宇文氏譯為:“When a single petal falls away, it is springs diminishment, a breeze that tosses thousands of flecks quite makes a man dejected.”①譯文中出現“single”“away”“diminishment”“toss”“thousands of”“dejected”等若干模糊詞語,“single”和“away”二詞表現出花之零落的景象,“diminishment”譯“減”字準確表達出了作者的惜春之情,“toss”譯“飄”字表達出了作者目睹花飄的傷感之情,“dejected”一詞充分表達了詩人的觸景傷感。這些模糊性的語詞表現出了語義上的多重性和暗示性,傳遞出作者豐富的情感,這些詞語在譯文中同樣充當著詞眼。
2.語法模糊
袁行霈云:“在其他文體中不允許出現的句子,卻可以成為詩中之佳句。”{2}語法模糊是詩人造境抒情的常用手段之一。為達到這種特殊的表達效果,宇文氏在翻譯中經常采用三種“模糊語法”。其一,省略謂語動詞。例如,杜甫的《獨立》:“空外一鷙鳥,河間雙白鷗。飄搖搏擊便,容易往來游。”宇文氏譯為:“A single bird of prey beyond the sky; A pair of white gulls between riverbanks.Hovering wind-tossed, ready to strike; The pair, at their ease, roaming to and fro.”{3}四句詩詞中沒有謂語動詞,但在此并沒有妨礙讀者對語義的理解,反而使譯文顯得潔凈、清純,充分體現了譯文的洗練之美。其二,省略主語。例如,孟浩然《自洛之越》前兩句:“皇皇三十載,書劍兩無成。”宇文氏譯為:“Restless and troubled for thirty years now, with nothing achieved by book or by sword.”{4}譯文中把主語“我”省略,免去了自己個性對詩意的侵擾,不僅使語言凝結簡練,而且極大拓展了詩的藝術容量。其三,語序倒裝。例如,李白的《月下獨酌四首·其一》中:“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宇文氏譯為:“Here among flowers one flask of wine, with no close friends,I pour it alone.”{5}譯文中的倒裝不僅有利于詩句的濃縮和經濟,而且在韻律上呈現出變化多端的節奏逶迤美。
3.辭格模糊
辭格在翻譯中也被廣泛采用,對其合理的運用使譯文生動形象、意蘊豐富。多數辭格直接使用了具有模糊性質的詞語或辭格本身就具有較強的模糊性,如“移情”“擬人”“比喻”“夸張”等辭格。比喻是將兩種截然不同的事物通過其相似點讓讀者產生模糊審美體驗。例如,李白《烏夜啼》中:“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窗語。”宇文氏譯為:“Weaving brocade upon her loom, a girl from the rivers of Qin. Speaks beyond a window of gauze green like a sapphire mist.”{6}譯文運用明喻,讓讀者透過煙霧般的碧紗窗依稀看到秦川女伶俜的身影,感受到她們內心的情感。夸張是對描寫對象進行夸大或縮小,以鮮明地突出某一事物。例如,杜甫《春望》中:“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宇文氏譯為:“Wars beacon fires have gone on three months, Letters from home are thousands in gold.”{7}譯文中用模糊詞“thousands”翻譯原文中的夸張辭格,突出了詩人眷戀家人的感情。辭格在譯文中俯拾皆是,在此不做贅語。
4.意象模糊
象乃詩詞的形象構件,一首詩往往有若干意象群組成。孤立地看,象與象之間沒有必然聯系,但被詩人或譯者組合起來成為一個有機整體后,便呈現出完整畫面。讀者通過聯想和想象,捕捉到貫穿意象的情思,填補了象與象之間的空白,從而使詩歌產生深遠的聯想義。例如,王維的《木蘭詩》:“秋山斂余照,飛鳥逐前侶。彩翠時分明,夕嵐無處所。”宇文氏譯為:“Autumn hills draw in the last sunlight; birds in flight follow companions ahead. The glittering azure is often quite clear, and nowhere is evenings haze to be found.”{8}譯者在品味“秋山”“余照”“飛鳥”“彩翠”“夕嵐”等物象的基礎上,直譯為“autumn hill”“last sunlight”“bird in flight”“evenings haze”“azure”,并沒有介入作者自己的情感,而是通過對原詩中意象的“二度感物”,臨摹了原文的意象。通過“glittering”“clear”等模糊語詞的點綴,把原詩中的夕陽、秋山、飛鳥、山嵐和明滅閃爍的彩翠奇觀很好地描摹出來,使譯文讀起來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與原文在言與形上基本達到等值。
二、宇文所安唐詩的傳譯策略
宇文氏在唐詩翻譯中通過廣泛地采用移情、轉義、留白等傳譯策略,實現了英漢語的模糊對等,把中國古典詩詞的模糊美充分地表達了出來。
1.移情策略廣泛使用
移情(empathy)本是一個美學概念,指審美活動中主體的感情移入對象,使對象仿佛有了人的情感,其漢譯為移情作用。{9}移情作用是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覺得外物也有同樣的情感,好像自己歡喜時,所看到的景物都像在微笑,悲傷時,景物也像在嘆氣。近年來有學者把移情引入翻譯研究。卓振英闡述了移情的兩個層面——移情于原詩作者和所謂“移情于詩歌意象”,研究主要側重于第一個層面,即在移情方式上與原詩作者保持一致性,即“內模仿詩人的審美感知、審美情感和審美意志”,在談論漢詩英譯時重點強調譯者移情于原作詩人的可行性、科學性和重要性,認為“漢詩英譯是否運用移情,這往往關系到譯作的成敗優劣”。{10}
移情是一種審美常態,是人們審美認知必然要經歷的心理過程。詩歌翻譯,作為一種跨語言文化的文學再創造過程,審美主體——譯者的移情是必不可少的。在詩歌翻譯過程中,譯者的審美對象不是自然界的客觀景物,而是凝聚著詩人主觀情感的詩歌作品。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詩的意蘊,譯者必須在深入理解原詩的基礎上,設身處地、細致入微地體會詩人寄托在詩歌中的情感,即必須要有譯者情感的移入。移情的作用在于更好地表現自然,抒發感情,闡述道理。詩在寫景,在抒情,甚至許多哲理隱含其中,其表現手法主要包括擬人、隱喻、明喻及夸張等。宇文所安在譯介中國古典詩詞模糊性時充分利用了這種移情手法,把原文本的模糊現象充分表達了出來。以杜甫的《春望》頭二聯“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為例:
A kingdom smashed, its hills and rivers still here,
spring in the city, plants and trees grow deep.
Moved by the moment, flowers splash with tears,
alarmed at parting, birds startled the heart. {11}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兩句移情于物,以物擬人,賦予了花與鳥以生命,以及人的情感,宇文氏的譯文中保留了原詩悄然的移情手法,“Moved by the moment, flowers splash with tears, alarmed at parting, birds startled the heart.” 這兩句詩明確告訴讀者:帶露的春花, 由于感傷時局的動蕩混亂而濺下眼淚;啼叫的小鳥,也因為痛惜骨肉的離散而膽戰心驚。詩人將自己感時傷世、憂國思家之情悄然移諸草木、花鳥,使得由于戰亂而淪陷的國都之中的草木、花鳥都帶上了“感時”“恨別”之感情色彩,語詞之間帶有較強的模糊性。正是借用這種手法,譯者把詩人對國之淪喪的復雜心情更加生動、直觀地傳遞給了讀者。
2.轉義手法廣泛使用
英語詞匯意義大致可分為本義(denotation)和轉義(connotation)。本義是詞語的基本義,直接、明確地表示所指對象。轉義是詞語的暗示意義或引申意義,與語境和文化相關聯,體現出生動形象的修辭色彩。《辭海》對“轉義”有釋義:一個詞由基本義派生出來的意義,包括引申義和比喻義兩類,比喻義暗示了其修辭功能。轉義的修辭功能不僅僅是比喻,還有擬人、夸張等。翻譯是一種跨語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動,忠實于原文是其基本要求,因此譯者要透過原文的表層結構深入到語言的深層結構,根據目的語的語言和文化特征,再現其語用意義,此語用意義實乃為轉義。轉義這種手法本身具有較強的模糊性特征,為達到一定的修辭效果對原文進行一定的“模糊”。下面以宇文氏對李白《月下獨酌》的翻譯為例來分析轉義手法在詩歌翻譯中的作用。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宇文氏譯為:“I lift up to bright moon, beg its company, then facing my shadow, we become three.”{12}此句用了擬人的修辭手法,把天上之明月當作朋友、伙伴來邀請,加上自己的影子,共計三人。“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譯為:“I sing, and the moon just lingers on; I dance, and my shadow flails wildly.”讀者透過譯文,仿佛能看到這樣一幅畫面:明月、身影、詩人自己,三人載歌載舞,看似其樂融融,實則孤獨凄涼。全詩中貫穿著這種比喻、擬人的轉義手法,以樂寫愁,以靜寫寂,抒發了詩人壯志未酬、懷才不遇的無限惆悵。通過轉義,譯者將原文的模糊意境傳達了出來。
3.留白手法廣泛使用
“留白”本是繪畫術語,是中國畫的一大技法,指中國畫構圖中的無墨處。中國畫中的留白是畫家在作圖時精心設計的一些空白,以此來激發讀者的想象以及增加作品的容量和內涵。而中國的詩與畫可謂同宗同源,正所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詩歌的語言高度凝練,講究虛實相生,用最為凝練的語言創造富含哲理、具有象征意義的審美意象。這種虛實相生的構成特點與中國畫的構圖特點是相通的。詩歌的藝術留白,是詩歌創作的必然,同時也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唐詩,作為中國詩歌的一顆璀璨明珠,運用了大量的留白法來構造詩的意象,看似沒有寫明,卻能在讀者心中激發無限想象,引領人們去追求“象外之象”“言外之意”“畫外之音”,從而“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既然留白在唐詩中扮演著如此重要的角色,唐詩英譯過程中譯者就應盡量保持這一重要特征,這也是對原文的一種“信”。同時,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及審美角度等方面的差異,在唐詩英譯中翻譯的困難和障礙隨處可見,因而在翻譯過程中可能產生諸如文字、文學、文化等方面的缺失,這便使得留白手法在詩歌翻譯中成為一種必然。
宇文所安的唐詩英譯很好地保留了這一特征,在譯文中巧妙地使用留白,成功地傳達了原文的風格與意境,保留了讀者豐富的閱讀和想象空間,再現了原文本的模糊之美。如唐代詩人王維的《竹里館》:“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宇文氏譯為:
I set alone in bamboo that hides me,
plucking the harp and whistling long.
It is deep in the woods and no one knows--
the bright moon comes to shine on me.{13}
這首小詩總共四句。詩寫山林幽居情趣,屬閑情偶寄。此詩以自然平淡的筆調,描繪出清新誘人的月夜幽林的意境,情與景融為一體,蘊含著一種特殊的藝術魅力。前兩句譯為:“I set alone in bamboo that hides me, plucking the harp and whistling long.”寫詩人獨自一人坐在幽深茂密的竹林之中,一邊彈著琴弦,一邊又發出長長的嘯聲。后兩句譯為:“It is deep in the woods and no one knows——the bright moon comes to shine on me.”寫深深的山林無人知曉,皎潔的月亮從空中映照。全詩短短幾十字,卻勾勒了一幅幽靜閑遠、清新脫俗的畫面,夜靜人寂,詩人的心境與自然的景致融為了一體。畫面中除了“幽篁”“深林”“明月”,還有什么,詩人的心境如何,譯文中沒有詳述,給讀者保留了發揮自己想象的空間,完美地演繹了原詩的留白意蘊,動靜結合,虛實相生,產生了“此時無聲勝有聲”的審美效果。
三、結語
宇文氏對唐詩英譯可以說是為中國古典詩詞的翻譯建立了一個典范。詩詞翻譯離不開模糊語言和模糊思維的運用,宇文氏意識到了這一點,意識到中國詩語的“不充分性”,意識到“減損了的文本”{14}不僅不會成為理解的障礙,而且很可能會創造出不可言喻的“言外”。
①③④⑤⑥⑦⑧{11}{12}{13} Stephen Owen.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 to 1911.New York: Norton 1996,第424頁,第426頁,第352頁,第403頁,第399頁,第429頁,第392頁,第420頁,第403頁,第395頁。
② 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
⑨ 卓振英:《漢詩英譯中的移情》,《外語與外語教學》2000年第1期。
⑩ 陶東風:《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216頁。
{14} 宇文所安:《中國傳統詩學和詩歌——世界的象征》,陳小亮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頁。
參考文獻:
[1] 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2] 陶東風.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3] 卓振英.漢詩英譯中的移情[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0(1).
[4] 宇文所安.中國傳統詩學和詩歌——世界的象征[M].陳小亮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