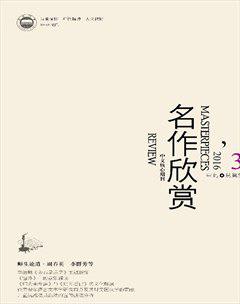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中的政治性評析
摘 要:本文從話語權、權力和宗教三個視角闡釋了《使女的故事》中的政治性,這不僅僅是一部反烏托邦的女性生態預警作品,也是一部反映現實社會中宗教與政治的未來小說。
關鍵詞:《使女的故事》 話語政治 權力政治 宗教政治
《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是加拿大當代著名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1939—)的代表作之一。《使女的故事》描寫的最遠時間距小說寫作時間隔二百多年,以幾名歷史學家的發現,讓一位在基列不幸淪為“使女”,后來僥幸逃出的女性,通過錄在磁帶里的聲音,向讀者講述發生在那個時間之前的故事,即主人公在未來21世紀初的親身經歷,其間夾雜著大量主人公對20世紀80年代生活的回憶與反思。故事發生在2020—2030年期間,在美國領土上由原教旨主義宗教激進分子所建立的神權國家——基列共和國。在基列共和國,階級分明、父權至上,女人則依照功能被授予不同的工作,像夫人、嬤嬤、馬大(使女)、蕩婦(妓女)等,特別是使女們,她們沒有名字,名字都是以主人家來稱呼,例如,主人公奧芙弗雷德(Offred)就表示of Fred-弗雷德家的,當然當她們換主人時,名字也就跟著換了。她們不能讀寫,沒有個人財產,甚至不能與人自由交談,違規的人可能遭到處死的下場。
《使女的故事》是一部未來小說,卻講述了已成歷史的未來,從而使它具有可企及性,是一部“反映現實的未來小說”。國內對《使女的故事》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生態女性主義主題上,忽視了小說中反映的現實政治的主題,雖然未來小說有著科幻成分,但僅從時間結構而言,這個故事將過去、現在、未來三個時間段交織在一起,就能看出瑪格麗特要告訴讀者,故事中基列國的政治制度在歷史上存在過,現在也存在著,而且將來也有可能在歐美國家存在。《使女的故事》中的政治性主要體現在話語政治、權力政治和宗教政治三個方面。
一、話語政治
英國著名學者菲爾克勞指出:“話語是一種權力,它是信仰、價值、欲望的構成模式,是一種機制,一種社會聯系方式,一種具體實踐方式。”在法國哲學家福柯看來,話語給人們提供了解釋文化社會的新視角,因此,需要建立一種“話語結構”并通過它來探尋在我們語言中所隱藏的一些深層秩序和規則。在權力與政治的體系中,語言是實現統治的工具和核心,與政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在《使女的故事》所虛構的反烏托邦社會中,權力是政治運作的核心內容,其最重要的體現形式就是話語的權力。小說中,原教旨主義者控制了國家政權,并對人們的語言做出了嚴格限制。使女們被剝奪了說話的權利,自由交流被絕對禁止,人們只能進行簡單的程式性回答,甚至“那些回答通常并不是你想得到的回答。不管如何,不應該有回答”。語言喪失了交流的作用,成為控制思想的意識形態工具。擁有了語言,就擁有了話語權,擁有了權力和自我身份。的確,根據福柯的理論,話語傳遞并產生著權力,對權力的任何掌控實際上都是通過對話語的掌控實現的。話語和權力的關系相互依存:話語產生權力,權力反過來又影響和控制話語。
《使女的故事》中,對使女話語權的限制實際上就是統治者對話語權的定義和操控。通過獲得話語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原教旨主義統治者獲得了其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小說中神權極端分子對言語的控制尤其表現在對《圣經》的解釋權上。為了使使女保持緘默,大主教全家定期舉行誦經儀式,且《圣經》只能由大主教讀給使女們聽,使女們“自己閱讀是不允許的”。《圣經》平時是鎖起來的,“為的是防止傭人偷竊”。這象征著統治者對話語權的嚴密操控。小說中所描述的基列社會似乎回到了中世紀的黑暗,只有教士才有權解釋《圣經》。對《圣經》解釋權的霸占賦予了大主教所代表的統治階層特殊的話語權。
毋庸置疑,話語運作的一個至關重要的領域就是意識形態領域,如文學、宗教、藝術等。在《使女的故事》中,基列共和國統治下的社會廣泛地使用了國家意識形態機器。所謂國家意識形態機器,是福柯的老師阿爾都塞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它指的是除暴力國家機器如監獄、軍隊等之外的非暴力國家機器,如傳媒工具、文化藝術等,它們以意識形態方式發揮作用。在小說中,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無時無刻不在發揮著作用。原教旨主義者為了加強自己的統治建立了一整套意識形態機制,用以對個體進行體制化規訓和合法化改造。比如,小說中教育感化中心、電影院、電視、圖書館等公共設施一應俱全,它們都發揮著重要的教育功能。這種意識形態手段與軍事暴力形成了鮮明反差,采取一種看似溫和的、對大眾進行勸說的方式實施管制,但其背后卻隱藏著意識形態的勸說,不失為一種有效的社會調控工具。
二、權力政治
福柯認為,權力不僅控制著社會資源,也滲透到社會的各種關系中,是統治階級利用社會機構達到自己目的的統治工具,對統治階級而言,最好的管理方式就是規訓權力。規訓權力是指統治階級對被統治者在思想上的勸說、行為上的訓練以及對違規者的懲戒方面所擁有的權力。規訓權力在《使女的故事》中的基列共和國得到了最直接的體現。基列國很多嚴苛的條例是在森嚴的等級制下實施的,男人也有等級制,被分為衛兵(Guardian)、天使(Angel)和大主教(Commander),只有優秀的天使才能成為大主教。大主教處在權力鏈的頂端,擁有著解釋《圣經》的“神圣”權力。根據基列國法律:不管男女誰違反法規和條例,等待他/她的可能就是被處死的極刑。基列國中處在最底層的女性是最大的受害者,受到了男權社會的種種迫害。但處在底層的男性也是受迫害者和被利用者,比如條例規定,除了老弱病殘所有的男性都必須參軍服役;絕對禁止男性同性戀;除了大主教外,禁止其他男性有性行為;在使女學校的城墻上每天都有被處死的男性。不同的等級有不同的權利和義務,每個人的言行都必須限制在自己所處的等級中,絕對不能逾越。
在這個政教合一的基列國中,凡是提供墮胎的醫生和同性戀都被處以絞刑。統治者就是運用了規訓權力通過各種社會機構牢牢地控制著人們的意識形態和行為。而這種規勸權力比單純的司法和暴力機構更可怕。可見,國家的權力一旦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所擁有,是多么的可悲和可怕。
三、宗教政治
在政教合一的國家體制中,政治永遠是和宗教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宗教為政治服務,政治反過來進一步鞏固宗教在社會政治中的作用。《使女的故事》的故事背景主軸是政治與宗教的上位者引經據典來迫害女性和利用男性,并摧殘上世紀的性解放運動。故事中的基列國以扭曲《圣經》教義來達到統治階級(大主教們)滿足欲望的目的。基列國是個高效的極權主義制度與極端神權宗教結合的國家,作者借由未來的幻想突顯了現實社會中的許多問題。在未來的基列國,女性最大的功能是生育,不能生育的女性就沒有價值。因此,女性的地位是從屬的,工作、讀書識字都是大不韙。
基列國神權基要主義分子把《圣經》當成他們恐怖統治的借口,如“利亞說,上帝給了我后代,因為我把使女給了我丈夫”,基列國將這段《圣經》上的故事當成使女政策的依據;又如“耶和華的眼目遍察大地,要顯大能幫助向他心存誠實的人”,這句來自《圣經·歷代志》的話被用來建立“眼目”這個特務系統以監視人民。《圣經·創世紀》第三章第16節:“我必多多增加你懷胎的苦楚,你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于是統治階層的打手嬤嬤們,不讓分娩的產婦上麻藥,還故意增加其痛苦,并說這一切都是來自上帝的旨意。這完全是斷章取義并扭曲《圣經》原意的極端基要主義。
《使女的故事》中有一段關于電視洗腦的畫面敘述:“這時候播音員出現了,舉止親切,神態如老父般慈祥。健康的膚色,花白的頭發,坦誠的雙眼,眼睛周遭布滿了智慧的皺紋。這一切使他看上去就像一個大眾心目中理想的長者。他那故作平和的微笑在傳達這樣的信息:他所說的一切都是大家好,一切都會好起來,你們要信任我,你們要像好孩子,只管安心睡覺。”如果把這段的播音員改成所謂的宗教領袖,會不會讓我們想起現實社會中的很多政治故事呢?
四、結語
不少研究者認為瑪格麗特的《使女的故事》在警示人們,我們所居住的地球的生態環境在不斷地惡化,人類將來很可能會生活在像基列國一樣的悲劇社會中。的確,這是一部反烏托邦的女性生態主義小說,然而從政治的角度,這何嘗不是一部反映現在不少國家和地區政治生態現狀的文學作品呢?
有些組織正是打著宗教的旗幟,通過曲解各自的宗教經典教義來試圖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可悲的是人們卻看不清這些統治者的真面目,還傻傻地用自己寶貴的生命為這些為了滿足自己的私利而壓迫和利用他們的人服務。有理智的宗教信仰者們,是時候好好反思我們的宗教、我們的社會和我們生活的環境了。而能正確分辨是非的唯一途徑就是知識,只要用知識武裝自己,我們才能擁有話語權,才能擁有真正的政治權利。
參考文獻:
[1] Atwood, Margaret. The Handmaids Tale[M].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1986.
[2] Sheckels, Theodore. The Political in Margaret Atwoods Fiction: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of the tent[M]. Surrey: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12.
[3] 丁林鵬.《使女的故事》中的話語政治[J].外國文學研究,2015(1).
[4] 陳小慰.一部反映現實的未來小說——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評析[J].當代外國文學,2003(1).
作 者:馬吉德,青海師范大學外語系講師,研究方向:應用語言學、英美文學。
編 輯:杜碧媛 E?鄄mail: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