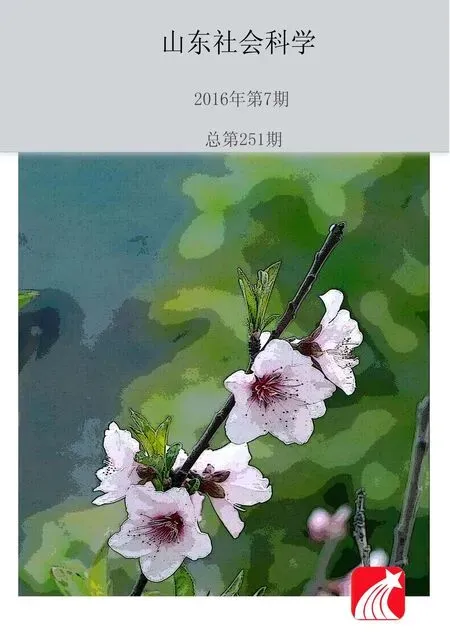馬克思論方法:讀1857年《導言》①
[英]斯圖亞特·霍爾 撰 孔智鍵 譯
?
馬克思論方法:讀1857年《導言》①
[英]斯圖亞特·霍爾 撰孔智鍵 譯
前言
這是一篇關于馬克思1857年《導言》論文的縮減版本,原文在文化研究中心系列研討會上發布并討論過。盡管我還未詳盡思考約翰·米弗姆(John Mepham)等人慷慨提出的進一步實質性的批評,但這篇文章或多或少鑒于之前的討論而有所修改。雖然《導言》中馬克思的許多構想是臨時寫下的,并在篇幅上經過嚴重的壓縮,但在方法論上《導言》是最有實質價值的一個文本。由于在內容闡釋上存在著諸多問題,我已經將自己的工作限制在僅僅閱讀文本上面。馬克思在《導言》中關于方法論的立場,是與如今普遍接受的許多觀點相左的。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一樣,只要適當地理解和靈活地運用,那么在我看來,要解決長期困擾我們學術界的方法論問題就有了一個顯著的、原創且影響深遠的起點,盡管在此論文篇幅限制之中我還不能夠完全建立起這樣的聯系。我認為這篇論文將會推動正在進行的理論和方法論上的澄清工作,而不僅僅是對文本的解釋。但愿在闡述細節過程當中我也可以兼顧這兩個方面。
《導言》是馬克思諸多文本當中最關鍵、同時也是最困難、最被精簡和難以辨別的文本之一。在《大綱》的序言當中尼古拉斯(Martin Nicolaus)就提醒我們說引用馬克思的手稿是有風險的,“因為對馬克思真正想要表達的東西而言,既定文章當中的內容、語法和特定詞匯都可能會引起問題”。
維拉爾(Pierre Vilar)注意到了,《導言》是所有人都會拿來“各取所需”的文本之一*Pierre Vilar, Writing Marxist History, New Left Review 80.。隨著對馬克思方法論和認識論研究興趣的增加,《導言》不斷趨于所有作品當中的中心位置。我分享它的重要性,但往往又讀出了不同于其他解釋者的另一種意義。我的目的在于展開對這個1857年文本的“閱讀”,一種非白板式的、無前提的閱讀,它不可避免地會反映我自己的問題式。同時也希望這有助于我們理解馬克思的問題式。
在1858年1月14日那封著名的信中,馬克思對恩格斯說:
我取得了很好的進展。例如,我已經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潤學說。完全由于偶然的機會——弗萊里格拉特發現了幾卷原為巴枯寧所有的黑格爾著作,并把它們當做禮物送給了我,——我又把黑格爾的《邏輯學》瀏覽了一遍,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幫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這類工作的話,我很愿意用兩三個印張把黑格爾所發現、但同時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東西闡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夠理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9卷,人民出版社,第250頁。
這不是馬克思唯一一次表達上述愿望。在1843年,馬克思寫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其中通常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一起印刷的《對黑格爾整個哲學體系的批判》也是意在揭示和批判黑格爾的辯證法,主要是圍繞著《現象學》和《邏輯學》,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圍繞著前一篇。一直到1876年,他還在寫給狄慈根的信中說:
當我放下了身上的經濟學研究的包袱時,我將寫寫辯證法。盡管是在神秘的外觀下,但辯證法的真正規律在黑格爾那里已經有了,有必要將它從這種形式中剝離出來。*Samtliche Schriften, vol 1. Translated in Hook, From Hegel to Marx.
馬克思的這些愿望沒有實現,因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擔從未被放下。在成熟的馬克思那里,我們并沒有看到對“合理內核”的系統定義、轉變途徑及其作為這種轉變結果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導言》和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還有其他的零散文本一起構成了馬克思計劃中未完成的必要部分,尤其是《導言》表達了馬克思最完整的方法論和理論總結。關鍵在于,我們應當如其所是地去看待它。它是作為所有手稿的導言而著,這些手稿范圍較廣、結構上零碎又復雜,同時也是高度未完成的粗糙的草稿。羅斯多爾斯基認為,《大綱》“引導著我們走進了馬克思經濟學的實驗室,也揭示了馬克思方法論的所有要義和細微線索”。《導言》則可以被具體理解為是對在筆記中高度應用的“方法問題”的摘要與提綱。因此它不是自成一體的,它的手稿性更多地表現在后來馬克思作出的不公開發表它的決定中。《導言》被更為精煉的《序言》所替代,《導言》中的一些核心部分在《序言》那里或被修改或被懸置。這兩者的對比告訴了我們:除了復雜的論證以外,《導言》即使在馬克思的方法方面也具有臨時性。
在《導言》中,馬克思通過批判政治經濟學當中的意識形態前提展開論證。第一部分討論生產,研究對象是“物質生產”。斯密和李嘉圖從“單個的和孤立的獵人與漁民”開始,而馬克思以“社會”個人,因而是“社會個人的生產”作為出發點。包括盧梭在內的18世紀的理論家們,找到了“單個的”生產者這個一般出發點。斯密和李嘉圖將他們的理論建立在這個意識形態投射之上。然而“單個的人”并不能作為起點,只能是結果。盧梭的“自然的人”看似剝離了現代生活的偶然性和復雜性,是對人類深層本質的、普遍人類個體的再發現。事實上,它將“市民社會”的進步都歸入了這種美學的假象之中。直到勞動從封建社會的依賴性形式當中解放出來,并處在早期資本主義革命性的進步過程當中,“單個的人”的現代觀念才完全得以形成。于是,整個歷史和意識形態發展作為前提隱匿在了自然個體和普遍的“人類本質”概念當中。
這無疑是《導言》中典型的思路。首先從政治經濟學中“給定的”出發點開始,然后通過批判表明,這些理論出發點實際上都是需要被證明的東西,它們已經是對全部歷史發展的一個總結。簡言之:政治經濟學理論中作為最具體、常識性的、簡單的、起到建構性作用的出發點,經過考察后都只是先在一些規定的總結。
處于社會之外的生產如同不依賴人的生活和彼此交談的語言一樣不可思議。社會的巨大發展才能形成“孤立的人”的生產者這個概念:只有在發達的社會聯系的高度協作形式下,人們才可以作為無差異的孤立個人在由“看不見的手”所組織起來的“自由”市場當中追逐私利。當然,實際上這種個人主義是看似彼此不相干的“全面依賴”:“毫不相干的個人之間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賴,構成他們的社會聯系。這種社會聯系表現在交換價值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31頁。。
這樣一種觀念,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依賴著假定了個人之間非社會地聯系的“意識形態”形式,是整個《大綱》最主要的實質性主題之一。這個觀點的得出對方法問題也產生了一定影響。用意識形態的表征(representation)來代替現實的關系——對這種代替的批判和揭露而言——就要求一種方法,這種方法揭示出由“表現形式”所假定的必要但又神秘的顛倒背后的“本質關系”。這種方法——馬克思后來把它視為他的辯證法中的科學內核——不僅是這一筆記,而且也是《資本論》的主要的方法論的步驟。這種“方法論”步驟促成了非常重要的理論發現:在它的擴展形式上(在《大綱》里有許多構建此方法的臨時性嘗試),它構成了《資本論》第一卷最為關鍵的“商品拜物教”的基礎*關于“現實關系”和“表現形式”的區分,參見Mepham, the theory of Ideology in Capital (below) and Geras, Essence Appearance: Aspects of Fetishism in Marx’s Capital. New Left Review 65.。
然后,《導言》以邏輯抽象的“通常”形式(‘normal’ types)的批判開始了方法的討論。作為一個理論,“政治經濟學”通過范疇建構自身。那這些范疇怎么形成的呢?通常的方法是通過對所有時期、所有類型的社會形態中“共同的”因素進行抽象,然后孤立和分析某個范疇。這種通過抽象的邏輯來證明一種存在于歷史當中不變的概念核心的做法,實際上是一種“本質主義”。許多的理論化過程都淪為對這種做法的崇拜。黑格爾,德國古典哲學的集大成者,發展出了與靜態相對的思維方式。在馬克思看來,黑格爾對運動和矛盾的把握構建起了一個超越所有理論化邏輯的邏輯。由于黑格爾的辯證法的運動是在唯心主義形式下展現的,他的思想也留有一個存在于所有意識運動當中“本質內核”的概念。馬克思認為,正是觀念中“本質內核”的永恒性,保證了黑格爾辯證法對現存社會關系(如普魯士國家)終極和諧解釋的秘密。古典政治經濟學也談“資產階級生產”和“私有制”,好像就是已經窮盡了歷史內容的“生產”、“所有制”概念的本質。這樣,政治經濟學最好地代表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是一個歷史的結構而是作為事物本質的和不可避免的狀態。在這個意義上,古典政治經濟學甚至將意識形態的假定保留在了自己“科學的”本質中:由于抽象,它將具體的歷史聯系還原至了最低程度共性和超歷史的本質。它的意識形態性就內在于它的方法之中。
相反,馬克思認為不存在“生產一般”:只有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特殊生產形式。令人困惑的是,這些特殊形式當中有“一般的生產”,它基于某種勞動的生產,這種勞動不屬于某個特定生產類型,而是被“一般化”為了 “抽象勞動”(我們稍后討論)。任何生產方式都要依賴“規定條件”,而我們并不能保證那些條件總會得到滿足或不隨時間變化而變化。例如,除了常識性理解,沒有科學形式表明“生產”的概念是特指以“自由勞動”為必要條件之一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它不能被認為與奴隸社會、原始部落社會和共同體社會的生產具有(本質上相同的)“直接同一性”。(后來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告訴我們,作為資本主義“本質”前提條件的從封建奴隸到“自由勞動”的這一轉變有其特定的歷史過程,“這種剝奪的歷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第822頁。。)這是歷史唯物主義作為一個思想和實踐方式的關鍵出發點之一。馬克思在他之后所寫的所有著作中都提醒我們不能忘了這一點。這就是柯爾施所說的馬克思那里“歷史的具體”原則。馬克思方法要生產出來的“統一”(unity),并不是一個弱同一性(weak identity),即抽象掉所有歷史質料而剩下的無差別和無具體內容的本質內核。
如尼古拉斯所言,《導言》回答了一個未寫下的問題:盡管其中一些理論是站得住腳的,但作為我們出發點的政治經濟學,它沒有明確歸納出它的范疇和理論要表達和反映的生產方式的內在結構規律。它只能“附著在資產階級的皮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第622頁。,這是因為在它的內部,歷史關系已經“取得了社會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第93頁。。它的范疇(和庸俗政治經濟學相比)“對于這個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即商品生產的生產關系來說”“是有社會效力的、因而是客觀的思維形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第93頁。。盡管古典政治經濟學已經發現了這些形式下的東西,但它沒有詢問特殊歷史條件下(商品生產的形式與條件)的某些關鍵問題(例如基于勞動力的商品生產的起源:正是在這種形式下價值變為交換價值)。這些錯誤并非偶然,它們已經表現在了自身假設前提、方法和出發點當中。但是,如果政治經濟學必須要超越自己的話,它該怎么辦?從哪里開始?
答案在于“社會個人的生產”,“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政治經濟學趨向于將資產階級生產神秘化、普遍化和去歷史化,如果我們和馬克思一樣堅持從歷史具體的原則出發將會發生什么?我們是否仍然會假定存在著一個共同的、普遍的實踐——已經存在著并服從于能夠被不斷追溯的革命的歷史進步過程中的“生產一般”,這個實踐能夠被我們還原至常識的內容并作為分析的無可爭議的出發點?答案是否定的。無論馬克思是哪一種歷史主義者,他明顯不是歷史進化論者。如他所說的,連小孩都知道,生產一刻也不能停。非要說存在著什么“共同的”東西來回應“生產一般”這種思想的話,那就是:所有的社會都會再生產出維系自身的條件。這樣的一種抽象篩選出了觀念的最低限度的共同特征,并將它等同于科學內容的不成問題的內核。它頂多是一種能有效節省時間的理論化入門方式。如果要洞察一個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那樣既復雜又被虛假表象所覆蓋的結構,我們需要觀念在根本上更具思辨性。那些我們能夠修正、劃分和分解的觀念重新組成為普遍的范疇:有些特征能夠在這個時代發生作用,有的特征則在另一個時代的特定條件下才得以發展,為什么某些關系只在最古的社會形式中出現,有些只在最發達的社會形式中出現,而在別的社會形式中卻沒有。這種概念在理論上遠遠優于那些結合在一個混亂的一般性之下的概念,這種在“生產一般”范疇下的一般性在不同的時候指向不同的東西,這些概念一旦發現了隱藏著的聯系就會發生改變。在很大程度上,馬克思看到了那些能夠差異出保證各種語言的具體發展得以可能的因素的概念,比那些“抽象”出少量簡單又基本的共同“語言一般”更為重要。
我們必須看到,馬克思在這里構建起了同時區別于政治經濟學和黑格爾方法的差異性,這是貫穿于整個《導言》的共同策略,《導言》也因此同時是對上述兩者的批判。在這個語境當中,回顧馬克思之前《貧困的哲學》中著名的“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章是有用的,在那里他通過攻擊蒲魯東同時批判了“黑格爾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他批判蒲魯東的語詞在這里反駁“抽象”問題尤為恰當,它們不僅僅是告訴我們存在著方法論上的謬誤,而且提醒著我們意識是如何作用于現實的、偶然的歷史關系內容。也就難怪:
如果我們抽掉構成某座房屋特性的一切,抽掉建筑這座房屋所用的材料和構成這座房屋特點的形式,結果只剩下一個一般的物體;如果把這一物體的界限也抽去,結果就只有空間了;如果再把這個空間的向度抽去,最后我們就只有同純粹的數量,即數量的邏輯范疇打交道了,這用得著奇怪嗎?用這種方法把每一個物體的一切所謂偶性(有生命的或無生命的,人類的或物類的)抽去,我們就有理由說,在抽象的最后階段,作為實體的將是一些邏輯范疇……,那末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東西經過抽象都可以歸結為邏輯范疇,因而整個現實世界都淹沒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沒在邏輯范疇的世界之中,這又有什么奇怪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140-141頁。
把這些范疇應用到政治經濟學上的話,馬克思認為:
政治經濟學的邏輯學和形而上學……就會把人所共知的經濟范疇翻譯成人們不大知道的語言,這種語言使人覺得這些范疇似乎是剛從充滿純粹理性的頭腦中產生的……在這以前我們談的只是黑格爾的辯證法。下面我們要看到蒲魯東先生怎樣把它降低到極可憐的程度。黑格爾認為,世界上過去發生的一切和現在還在發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維中發生的一切……沒有“適應時間次序的歷史”,只有“觀念在理性中的順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143頁。
馬克思早就指出過黑格爾的“杰出貢獻”:關于世界的范疇(私有權、道德、家庭、市民社會、國家等等)從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不斷產生和消失,成為運動的環節。然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馬克思激烈地批評黑格爾將范疇設想為一種有自發形式的“運動的本質”:黑格爾只在思維里設想它們,于是所有的運動終結于絕對知識。在黑格爾那里,真實世界的組成僅僅是矛盾和運動過程的外在表象,而這些運動和矛盾也只是思想中的思辨存在。“因此,全部外化歷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過是抽象的、絕對的思維的生產史,即邏輯的思辨的思維的生產史。”這當然不是通過政治經濟學的粗糙形式構建起來的簡單的、超歷史和外在的聯系,而是另外一個同樣不可被接受的選擇:意識僅僅在思維形式當中實現與自身的徹底同一。馬克思還認為,“黑格爾用那在自身內部旋轉的抽象行動來代替這些僵化的抽象”。在《神圣家族》中他說得更清楚:
“現象學”……用“絕對知識”來代替全部人類現實,……黑格爾把人變成自我意識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識變成人的自我意識,變成現實的人即生活在現實的實物世界中并受這一世界制約的人的自我意識。黑格爾把世界頭足倒置起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244-245頁。
在《哲學的貧困》中:
他以為他是在通過思想的運動建設世界;其實,他只是根據自己的絕對方法把所有人們頭腦中的思想加以系統的改組和排列而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143頁。
這些早期批判的要義保留到了《導言》。黑格爾的確理解了“生產”和“勞動”,但就像馬克思所說,是“意識的勞動,思維和認識的勞動”。無論運動是多么的辯證,對黑格爾而言,世界的歷史生產過程只是理念實現自身過程的一個環節,是思維的外在表現,總之是意識在通向絕對知識道路中十字路口的一個停留。馬克思在《導言》中的方法與此不同:它不僅僅是精神作用。我們應該走向現實的、具體的聯系當中:這種方法是不要簡單地構建出紛繁歷史現象后面的“本質”,而是要準確地找到保存著“本質性差異”的諸多規定。
馬克思以一個例證結束了討論。像密爾一樣的經濟學家從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入手,并將它們推斷為“永恒自然規律”。他們聲稱除了一些歷史差異外,所有的生產都可以被納入到一般規律當中。其中兩個“規律”分別是:一,生產需要私有財產;二,生產需要司法和警察的保護。馬克思說,私有財產實際上既不是唯一也不是最初形式的財產:歷史地看,最早可以推算到公社財產。而現代資產階級司法關系和警察的出現并不能說明這個體系的普適性,也不能說明每一個生產方式需要和生產的司法以及政治上的結構和關系。正如精神地抽象出所謂“共有的”屬性的結果所揭示的那樣,對生產而言是“共有的”東西并不能保證我們能夠具體地理解每一個真實歷史階段的生產。
那么,我們如何概念化生產、流通、交換、消費等不同階段之間的關系呢?能否把它們看作是“內在有機結合的諸因素”?還是相互之間僅僅保持了偶然的聯系,例如像是簡單的反映關系。簡言之,我們該怎樣去分析這個復雜結構總體之間各部分的關系?在他后期的文本當中,馬克思堅信辯證法的優先性在于它可以找出生產方式當中不同要素之間的內在聯系,而不是偶然的外在排列。那種僅僅將相反要素外在地結合在一起的方法,也就是認為兩個概念如果相近,它們就必然相互聯系的方法,只是表面上“辯證”,三段論就是一種外在排列的邏輯形式。政治經濟學用這種三段論“思考”生產、消費等等:生產制造出商品;流通分配它們;交換使普遍的商品流通具體到特殊的個人;最后個人消費掉商品。這幾乎可以被解釋為經典黑格爾式三段論表達。馬克思在很多方面被認為依舊是一個黑格爾主義者,但他對黑格爾三要素(正、反、合)以及三段論(普遍、特殊、個別)的運用并非如此。這種三段論要求的連貫性在概念上依舊顯得很膚淺*在《1857年導言》中馬克思說:“好像這種割裂不是從現實進到教科書中去的,而相反地是從教科書進到現實中去的。”霍爾認為從邏輯上去考慮黑格爾三段論的錯誤還是停留在教科書的層面上。——譯者。馬克思認為,它的錯誤在于將資產階級生產過程當中表面上看似獨立、自為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環節之間的聯系神秘化了,這些表象都是虛假的,是意識形態的顛倒。觀念的謬誤僅靠“完全在思維之中”的理論實踐是不能澄清的。
在“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整個哲學的批判”當中,馬克思指出黑格爾那里一個范疇對另外一個范疇的替代表現為是對“思維實體的超越”。而黑格爾那里的思維也將客觀創造出來的環節當作是自身的環節,“因為對象對于思維說來現在已成為一個思想環節,所以對象在自己的現實中也被思維看作思維本身的即自我意識的、抽象的自我確證”,于是往往會不顧現實世界中的對象,卻相信在思維中進行轉化就可以克服自身。沒有“世俗的歷史”,沒有“人的本質對人說來的真正的實現,是人的本質作為某種現實的東西的實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第174、175頁。。因而,“人類的歷史變成了抽象的東西的歷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108頁。,思想的運動被牢牢地限制在了自身的循環當中:
黑格爾把這一切僵化的精靈統統禁錮在他的邏輯學里,先是把它們一個一個地看成否定,即人的思維的外化,然后又把它們看成否定的否定,即看成這種外化的揚棄,看成人的思維的現實的表現;但是這種否定的否定由于仍然被束縛在異化中,它一部分是使原來那些僵化的精靈在它們的異化中恢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第178頁。
所以,抽象這個行為是在自身內的循環往復。這里依舊用了非常黑格爾-費爾巴哈式的話語。在《導言》當中這更清楚,“好像這種割裂不是從現實進到教科書中去的,而相反地是從教科書進到現實中去的,好像這里的問題是要對概念作辯證的平衡,而不是解釋現實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31頁。。
無論是政治經濟學本質上的非聯系觀點,還是黑格爾式邏輯的形式揚棄都不能揭示社會過程和社會關系之間的內在聯系,這樣的社會過程和關系構成了一個必須被當作是現實世界中真實的、有差異的過程,而不是抽象自身的形式運動的一個特殊社會類型的“統一”。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現實關系”當中,不同領域看上去是相互獨立、自治的“鄰居”,所以在文本當中就表現為一種偶然的聯系,而不是相反。同一性、相似性、中介性和差異性在思想觀念層面上能夠產生足以解釋思維對象“現實關系”復雜性的“思維具體”復雜性,但問題是我們如何思考它們之間的關系。
《導言》中緊接下來最被壓縮和最難以理解的部分內容為上述問題提供了答案。這部分討論生產、分配、消費和交換之間的關系。首先是生產。生產中,個人消耗他的能力,使用原材料。在這個意義上,生產過程內部存在著一種消費:生產與消費在這里“直接合一”。馬克思似乎認為這種“直接同一”性足夠正確,但正如他之前和后來所表明的那樣,同樣也很“膚淺”,或者說是無關緊要;雖說在簡單的層面是正確,但它導致了觀念的混淆,需要引入進一步的規定和分析。這種“直接同一”的一般性不足清楚地表現在了馬克思對斯賓諾莎的參考中,后者指出“無差別同一性”不能用來說明更加細化的“特殊規定”。然而,只要“直接同一”在簡單層面占統治地位,同一性命題就可以被顛倒為:如果A=B,那么B=A。馬克思接著顛倒了命題:如果在生產當中有消費,那么直接地,消費當中有生產。例如,對食物的消費是人的生產或再生產他物質存在的一種方式。現在政治經濟學看到了這些差異,但它所做的僅僅是將生產中的消費方面分離出去(例如對原材料的消費)。生產,作為一個無差別的范疇被保留了下來。這種“直接同一”因而并不排斥它們“直接是兩個東西”。(這種同一性也接受馬克思原先在1844年手稿中“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整個哲學的批判”部分對黑格爾的批評:“這種思想上的揚棄,在現實中沒有觸動自己的對象,卻以為已經實際上克服了自己的對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第174頁。)
馬克思現在增加了第二種聯系:中介,相互依賴的關系。生產和消費互為中介。通過“中介”,馬克思認為沒有另一方某一方不能存在,不能實現轉變,也不能完成結果。同樣,一方是另一方的完成,一方在自身中為另一方提供了對象。生產出來的產品為消費所消耗,而消費的需求就是生產所要滿足的目的。這里的中介性是目的論式的。一方在另一方中發現自己的終結。馬克思后來發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34頁。,在這個中介運動中,雙方“互不可缺”,但并不等同,它們互相需要,但卻“各自處于對方之外”。
馬克思在這里擴展討論了中介的工作原理。消費在兩方面“生產”出生產。首先是作為生產對象的產品只有在被消費掉才得以最終“實現”*馬克思關于勞動這一“活動”如何在產品中“作為靜的屬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觀點有所發展,參見《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頁)。正是生產性活動向對象化產品形式上的轉化構成了生產到完成消費這個過程的首次中介。第二,消費通過創造出“新的生產”的需要生產出生產。嚴格地講,消費現在所做的是為了再生產提供“觀念上的內在動機”、“內心的圖象”、“需要”、“動力和目的”,這對后面關于作為過程整體的生產的確定性的討論至關重要。馬克思強調“新的生產”,嚴格地說就是消費需要的再生產。
對象如何對他說來成為他的對象,這取決于對象的性質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本質力量的性質;因為正是這種關系的規定性形成一種特殊的、現實的肯定方式。眼睛對對象的感覺不同于耳朵,眼睛的對象不同于耳朵的對象。
如果對對象的消費產生了主觀的再生產沖動,那么對對象的生產創造了特定的、不同歷史和發達的占有,同時形成對象所滿足的需求,“只有音樂才能激起人的音樂感”。
因此“感覺的形成”是客觀勞動的主觀方面,是“以往全部世界歷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第125-126頁。的產物。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發現,“新的需要的產生是第一個歷史活動”。而在這里,“藝術對象創造出懂得藝術……的大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33頁。。接著,生產客觀地構成了消費者占有方式,就像消費再生產出作為主觀經驗的驅動、沖動或動機的生產。在這篇文章中,客觀維度與主觀維度之間復雜的轉換以簡練的語言完成了,而這離開1844年手稿的話是不可理解的,即使“類存在”之類的語言已經通通消失。
重新回到一般性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33頁,這三種類型的同一性關系的區別并沒有人們希望的那么清晰。存在著三種同一性關系,首先,直接的同一性——生產與消費是“直接地”就是對方。其次,相互依存——各自“獨立”于對方,且不能離開它得到完成,不過生產與消費相互仍然在對方之外。第三種,一個沒有準確名稱,但明顯是從屬于彼此的內在聯系,雙方借由歷史時代的現實過程、不同形式的變遷連接在一起。這里,與關系2相比的話,生產不僅僅走向自己的完成形式,也是通過消費的自身再生產運動。在第三種關系中,部分“在完成自身過程中創造他者,也作為他者創造了自己”。這里我們不僅僅會發現使得第三種關系區別于第二種關系的原因,也會發現馬克思最終將確定性置于生產而非消費的原因,這在下一頁會涉及到。他認為,生產啟動了整個循環:在它的“第一步”當中,它形成了消費的對象、形式和需求,消費接下來能做的是“通過在最初生產行為中發展起來的素質通過反復的需要……使產品成為產品的終結行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34頁。。然后,生產要求有消費的渠道再次重新開始它的工作;但在提供“整個過程借以重新進行的行為”當中,生產保持著對于作為整體的循環的優先決定權。馬克思一些最為重要和復雜的區分(后來在《資本論》當中得到發展,例如簡單和擴大再生產)在這一梗概的文章當中獲得了一種格言式、哲學的初步形式。在這第三種關系當中,生產與消費不再是外在于對方,也不是直接地合一,而是“內在地”聯系在一起。這一內在關系并不是一種簡單的同一性,后者只要求三段論中概念之間的逆轉或顛倒形式。這里的內在關系經過了一個特殊的過程。馬克思在其早期對黑格爾批判當中稱之為“世俗”歷史:一個歷經真實世界、歷史時期的過程,其中各個環節需要其決定的條件,服從于內在規律并且不能離開其他環節。它是一個有限的歷史系統。
為什么關系3不是黑格爾式的“直接同一性”?馬克思給出了三個原因。第一,直接同一性假定了生產與消費有著單一主體。“主體”的這種同一性貫穿在它實現過程的后繼“環節”當中——這是黑格爾“本質論”的一個關鍵方面,它使得黑格爾將世界歷史最后理解為一個和諧的循環。然而,在現實歷史中生產與消費的“主體”并不是同一個。資本家們生產,工人們消費。生產過程將他們聯系在一起,但他們并非直接同一。第二,它們不是單一行為的黑格爾主義“環節”,世界精神運動的短暫實現。它們是過程中的循環,有著“實際的起點”:是特定形式下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價值被規定為“自身實現”而前進。第三,盡管黑格爾的同一性形成了自發、自持的循環,其中沒有一個環節具有優先性,而馬克思強調生產和消費經過的歷史過程有它自己的斷裂和決定性環節。是生產,而非消費開啟了這個循環。作為價值實現必要條件的消費,不能夠破壞實現過程起始環節的多元決定性。
這些區分的重要性延續到了最后一個段落當中——馬克思主義和黑格爾主義對資本主義生產形式分析的差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35頁。資本主義趨向于在擴大形式中再生產自身,就好像它是一個自我均衡、自我維持的系統。所謂的“等價交換規律”是這個系統自生方面的必要“表現方式”:“美好和偉大之處, 正是建立在這種自發的、不以個人的知識和意志為轉移的、恰恰以個人互相獨立和漠不關心為前提的聯系即物質的和精神的新陳代謝這種基礎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111頁。。
不過,生產諸領域中的這種走向均衡的恒定趨勢,只有在這個不斷顛倒均衡的反作用形式下才可以執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第412頁。每個“環節”有其決定性條件,各自都服從于自身的社會規律:的確,每個環節通過獨特的確定形式(過程)在循環中與其他環節相聯系。因而,對于生產者(也就是資本家)來說,他所生產的東西能否再次回到他那里是不作保證的:他不會“直接地”占有它。
資本的循環“依賴于它和其他個人的關系”。一個整體,中間的或“中介運動”現在牽涉到了生產者與產品(“中間步驟”),決定著(但仍然是根據社會規律)生產中增殖部分作為他的份額回到生產者的東西。除了維持這些規定性的條件外,沒有任何東西能夠保證這種生產方式在時間上的持續性。
解算大氣可降水量的處理方案為:數據采樣率為120 s,衛星截止高度角為15°,采用 IGS最終星歷,解算每0.5 h對流層天頂總延遲(ZTD)。然后,運用Elgered(1993)天頂靜力延遲(ZHD)公式計算天頂靜力延遲:
正像商品的交換價值二重地存在,即作為一定的商品和作為貨幣而存在,同樣,交換行為也分為兩個互相獨立的行為:商品交換貨幣,貨幣交換商品;買和賣。因為買和賣取得了一個在空間上和時間上彼此分離的、互不相干的存在形式,所以它們的直接同一性就終止了。它們可能互相適應和不適應;它們可能彼此相一致或不一致;它們可能出現彼此不協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97頁。
簡言之,它是一個有限的(finite)歷史系統,一個存在斷裂、不可持續、矛盾和中斷的系統:一個在歷史當中有其界限的系統。它就是這樣一個系統,依賴于其他過程的中介運動,甚至有的沒有被點名:例如分配,生產,消費。那么,分配是與生產和消費直接同一的嗎?他是內在于還是外在于生產?它是自發的還是被決定的領域?
在第一部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31-34頁。當中,馬克思考察了黑格爾式直接統一性術語:對立/同一當中的生產/消費這個對子。然后他借用馬克思式的變形:對立-相互中介、相互依賴-有差別的統一(非同一)揚棄了這個對子。在某種程度上,這個變化的完成明顯受益于從等價交換關系中獲得的規定環節:生產。在第二部分*參見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對工資理論和《資本論》第三卷中對“三位一體公式” 的瓦解。,第二個對子生產/分配通過另一個轉化被揚棄:被決定(determined)——決定(determining)——規定(determinate)。
馬克思寫到:在古典政治經濟學中所有東西都會出現兩次。資本是生產的要素,但也是分配的一種形式(利息+利潤)。工資是生產的要素,但也是一種分配形式。地租是分配的一種形式,但也是生產的一個要素(土地所有權)。每個要素都作為決定的和被決定的出現。打破眾多決定性無縫循環的是什么?只有重新從范疇表面上的同一回到它們有差別的前提(決定條件)才能破解這個問題。
這里,馬克思再一次涉及到了在自我維持的資本循環中建立斷裂的、決定性環節的問題。庸俗經濟學假定了資本在社會過程中的完美契合,這表現在它們的三位一體公式當中。生產的每個要素回歸到它在分配中的位置:資本-利潤,土地-地租,勞動-工資。所以,由于假定的“自然和諧”或與之完全同一的對立的配合的秘密,每個都出現兩次。在常識看來,分配看上去是這個系統的最初運動者。然而,馬克思認為,在分配的顯著形式(工資、地租、利息)下隱藏的不僅僅是經濟學范疇,而是真實的歷史關系,它起源于特定條件下資本的運動和構成。因此,工資所假定的不是勞動,而是特定形式下的勞動:雇傭勞動(奴隸沒有工資)。地租假定了大規模的土地所有權(在共同體社會當中不存在地租)。利息和利潤假定了現代形式下的資本。雇傭勞動、土地所有權和資本并不是分配的獨立形式,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組織的部分:它們促成了分配形式(工資、地租和利潤),這不能反過來講。盡管毫無疑問是一個有差異的系統,但在這個意義上,分配受到生產結構的多元決定。在工資、地租和利潤分配之前,一種初次的“分配”必須發生:生產資料擁有者和使用者的分配,社會成員、階級以致生產不同部門的分配。這種初次分配——從生產資料和生產者到生產的社會關系——從屬于生產:而它的產品、結果——以工資、地租為形式——的分配不能成為出發點。一旦這種資料或使用者的分配完成,它們就形成生產方式中價值實現的起始條件;這種實現過程構成自身的分配形式。然而,第二種的分配在更寬泛和特定類型意義上很明顯是從屬于生產的,而且必須理解為被它多元決定。
在第三部分,交換,演繹更為簡潔。*《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39-40頁。交換也是“生產的一個方面”。它中介著生產和消費,但同樣,作為它的前提,它需要只能在生產中建立起來的決定性條件:勞動的分工、私人交換形式下的生產、城鄉之間的交換等等。這個觀點幾乎立馬會推導出一個結論,它是一個不僅僅對于交換部分,還是對于在88頁提出的整個問題的結論*指的是尼古拉斯的《1857年導言》的譯本的第88頁。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30頁。這個問題見上文:“我們該如何確立不同的生產階段——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之間的關系的概念呢?”。在黑格爾式辯證法的本質論中,作為直接同一的生產、分配、消費和交換是不可能完全被概念化的,只會淪為絕對一元論結果。本質上說,我們必須將物質生產中不同過程之間的關系理解為“整體中的部分,同一中的差別”。也就是說,作為一個結構復雜的有差異的總體,這其中的差異沒有被抹除而是被保存了下來,作為“必要復雜性”的整體恰恰是需要這種差異化的。
黑格爾當然知道關系中的雙方并不一樣。但他尋求的是對立后的同一,差異背后的直接同一性。馬克思并沒有全然拋棄這樣一個層面的論述,即表面上對立的事物有著本質上潛在的相似性。然而這不是馬克思式關系觀的主要形式。對于馬克思,兩個不同的用詞、或關系、或運動、或循環依舊是特殊的且存在差異,盡管它們是“復雜的整體”。不過,這種整體經常是被它們的差異所構建,而且需要維持這種差異。這種差異不會消失,不會由于思想的微小變化或辯證法的形式轉化而被廢除,也不會丟失其具體的特殊性被綜合為更高、更本質的東西。后面這種“非直接性”是馬克思稱之為有差異的共同體。就像它緊密聯系的概念(作為諸多決定和關系整體的具體的概念)一樣,“有差異的統一”是理解這篇文本的方法論和作為整體的馬克思方法的理論鑰匙。這意味著,在對所有現象和關系的審視中我們必須同時理解它的內在結構(在差異地方中的東西)和其他與之成對出現并形成更具包容性的整體的結構。特殊性和聯系(結構的復雜單元)這兩者都必須在對具體關系和具體結合的具體分析中展示。如果這些關系相互接合(articulated),但由于它們的區別而保持特殊性的話,那么這種接合和它的決定性條件基礎必須要得到闡述。它不會從本質主義的辯證法規律中變戲法似的出現。有差異的整體在馬克思那里也是具體的。這樣,這個方法(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在理論分析當中保持了作為優先的和不可消釋環節的參照性具體經驗,而不會淪為經驗主義。
馬克思賦予生產以“多元決定”。但生產究竟是如何決定的?生產具體說明了“不同環節之中的不同關系”。它決定了那些構成復雜整體的結合方式,這就是一種方式的形式接合原則。在阿爾都塞那里,生產不僅僅歸根結底“起決定作用”,而且也決定了使得生產方式成為一種復雜結構的力量和關系的組合形式。生產指定了相似性和差異性的系統,生產方式中所有實體之間的結合點,包括了在任何結合的部分當中處于統治地位的層面。生產起的就是這種方式決定作用,這就是馬克思的全部意思。在它更為狹隘和局限的意義上(僅僅作為一個部分,和他者構成有“差異的整體”),生產有其自身動力和動機,有從循環中其他環節(在這個意義上是消費)衍生出來的規定(determinateness)。馬克思在導言末尾回到了這一討論,即生產方式的不同關系或層面之間的確定性和互補性或接合的本質。它的結果之一,之前已經提示過了,就是“不平衡發展規律”。
馬克思現在回到了開始:政治經濟學的方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34頁。在思考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學時我們應當從哪里開始入手?一個可能的起點是從“實在和具體”開始,一個給定的、可觀察的、經驗性概念:人口。生產過程少不了生產著的人口。然而這一出發點是錯的。人口,和“生產”一樣是具有欺騙性和給定的范疇,只有在常識意義上是“具體的”。*關于黑格爾和馬克思對“具體”的用法,參見克蘭《對馬克思哲學的一些批判性意見》,載于N.洛克維茨主編的《馬克思與西方世界》(Notre Dame(1967))它已經假定了階級的劃分,勞動、雇傭勞動和資本的劃分等特定的生產方式的范疇作為自己的前提。人口只給我們提供了“關于整體的混沌的表象”。甚至,它引出了一種方法論的步驟,即從一種盲目明確的東西走向“越來越簡單的概念”“越來越稀薄的抽象”。這就是17世紀經濟學家們抽象的方法,也是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睿智地和不留情面地嘲笑的普魯東的“形而上學”方法。后來的經濟學理論家從簡單的關系出發然后按圖索驥回到具體。后一種方法馬克思稱之為“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這種“具體”是一種不同于第一種方式中的具體。在第一種情況當中,“人口”在一種簡單的、單方面和常識意義上被理解為“具體”(這顯然是存在的);離開它生產不能夠被理解等等。然而,生產“復雜的具體”的方法之所以具體,在于它是一種“擁有許多決定因素和關系的豐富整體”。接著,這種在思想中(實踐的主動性無疑在這里呈現了)再生產出歷史的具體。現在,這樣一來,反映論和復制論的真理觀都是不充分的。“人口”這個簡單的范疇必須由更具體的歷史關系矛盾地組成才能被重新建構,這些關系包括:奴隸主/奴隸,領主/農奴,主人/仆人,資本家/勞動者。這種區分是特殊的實踐,它要求理論作用于歷史:它構成理論對對象充要的第一步。思維通過將簡單的、統一的范疇分解到組成它們真實的、矛盾的、對抗性的關系來達到這一區分。它追問什么是“直接呈現在資產階級社會”的東西,什么是作為“表現形式”(外觀的必要形式)表現出來,但是“背后進行的一種過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211頁。。
馬克思作了總結。具體,在歷史中、社會生產以及觀念中之所以具體,不是因為它是簡單和可經驗的,而是因為它展現了某種必要的復雜性。馬克思在“經驗給定”和具體之間作了一個重要區分。為了“思考”這種真實的、具體的歷史復雜性,我們不得不在意識中重建構成它的規定條件。在歷史中,已經作為結果被多種因素決定、多樣組合的東西,在思維和理論中不是我們的出發點,而必然是被生產出來的。抽象的決定因素導致思維中具體的再生產。我們現在就看到,這使得“思維的方法”區別于歷史的邏輯,盡管它與思維沒有“截然不同”。對于馬克思,更重要的是歷史具體使得它作為思想的歷史基礎再次呈現。雖然歷史具體不能夠作為理論演繹的出發點,但它是所有理論建構的絕對前提條件:它“是現實的出發點,因而也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
這里馬克思的表述是具有啟發性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41-42頁。近些年它們更是成為關于馬克思認識論整個討論的重要引文。馬克思所說的“思想的路程”必須建立在“歷史現實之上”(“掌握具體”),它通過自己的特定實踐生產出與對象相適應的理論結構(“把它作為具體在頭腦中再生產出來”)。然而要看到,這樣馬克思立刻將自己直接置身于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當中:這種“理論勞動”是否能夠被視為一種“完全發生在思想中的”實踐,“以自身為標準”,并且“不必依靠外在實踐的確證來宣稱它們所生產的知識是‘正確的’”*L. Althusser, For Marx,p. 42, 58.。重要的是,這些評論再一次涉及到了對黑格爾的批判,看似是要警告我們提防任何終極、意識形態的支點。馬克思認為,因為思想有其自身占有方式,因此黑格爾認為“現實”是“思想關注自身、探索自身道路并從外部向自身打開”的想法是錯誤的。那樣很容易再進一步推論思想是絕對(而非相對)自動的,所以“范疇的運動”變成了“生產的實際行為”。他接著說,思想當然就是思想,不是其他的東西;它發生于人的頭腦當中,且需要思想再現與運作的過程。它并不因此形成它自身,它是“思想和理解的產物”,是把表象和直觀加工成概念的產物。任何關于“理論實踐”的理論,例如阿爾都塞的理論,尋求在思想與其對象之間建立一種“無法逾越的隔閡”的做法,都必須讓步于馬克思這里表明的觀點(即思想是從觀察和對觀念的審視中來)中所包含的對具體的參照,這種參照在我們看來不是經驗主義還原。而這種具體內容就根植于馬克思這里清楚明確的觀點,即思想是從“表象和直觀的加工”而行進的。馬克思現在觀察到的這種理論勞動產品就是頭腦中的“思維整體”。不過思維不會消解于在頭腦之外自主存在的“現實主體”(它的對象)。的確,馬克思在簡單地參考思想之于社會存在的關系時表達過對這個意見的贊同,這是與早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所表述的立場是一致的。只要“這個頭腦還僅僅是思辨地、理論地活動著”,那么對象、“現實”總是在頭腦之外。這就是說,只有通過實踐,思維與存在之間的裂縫才能縫合。正如馬克思所說,“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于離開實踐的思維的現實性或非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這里沒有明顯證據表明馬克思已經根本上破除了這樣的觀點:盡管思維有其自身方法,但在實踐那里它的真理性就存在于思維的這種“此岸性”中。實際上,《57-58手稿》內容明確表達了這個觀點:“因此,就是在理論方法上,主體,即社會,也必須始終作為前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43頁。在這個證據之上,我們必須選擇維拉爾簡短但扼要而不是阿爾都塞復雜但不充分的說明:
我承認,任何人都不能把思想錯認為是現實或者把現實錯認為是思想,思想只是在知識關系上接受現實,因為除此之外它什么也不是。整個知識的產生也只會在思想中完成(除此之外它到底會在哪里發生呢?)阿爾都塞著重討論的“一般性”(generalities)那里也存在著秩序與等級差別。不過另一方面,我沒有發現當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偶然地,以一種非正式的形象)寫下概念化的思想會漸漸走向現實時存在著什么“令人震驚”的錯誤。(《新左派評論》,80)
正如維拉爾評論的,一個人想要讀懂《57-58手稿》的《導言》部分這個無聲對象時,他必須留意所有的文字,“當心不要使它所說的東西保持沉默”(《新左派評論》,80,pp.74-5)。
思想對現實有它自身明確且“相對自主”的占有方式。它必須從抽象上升到具體,而不是相反。這與“具體本身成為存在的過程”是不同的。理論的邏輯與歷史的邏輯不會直接同一:它們在同一當中互相接合,又在整體當中互相區別。然而正如我們看到的,為了避免我們陷入另一個謬誤,即認為思想是他自身的事物,馬克思似乎是自然而然地立刻轉向批判黑格爾,這當然是因為后者那里范疇的運動是唯一的能動。這樣,馬克思批判了任何一種企圖把思想的獨特性從現實(就其生產方式而言)轉換為絕對的區別的立場。他對“絕對”斷裂的定位是至關重要的。思想總是將具體基礎納入到自身當中,而范疇則在被考察過的生產方式中歷史地實現。盡管是作為一種相對簡單而非“多邊聯系”的生產關系,如果一個范疇已經存在,那么這個范疇可以在思想中表現出來,因為范疇是“關系的表達”。接著,如果面對一種方式,其中的范疇是以更為發達、多邊的形式呈現的話,我們會再次采用它,但是用來“表達”一種更為發達的關系,這種情況下,它的確保持為真,理論范疇的發展直接地反映了歷史關系的進化:抽象思維的方法,確實與現實歷史過程相一致,從簡單到復雜。在這個有限的例子當中,邏輯與歷史范疇是平行的,所以那種認為馬克思規定了邏輯與歷史的范疇永遠不會有交集的觀點是錯誤的。這取決于具體的情況。
然而在其他情況當中,這兩種運動并非同一。在馬克思關注的事例中,那就是黑格爾的錯誤。馬克思批判那種將思考視為完全自動的做法,認為這導致了唯心主義的問題式,他最終會將世界起源歸結于觀念的運動。無論是黑格爾主義、實證主義還是經驗主義或結構主義的變種,所有這些形式主義的還原都不能逃離這個非難。思想方式的特殊性沒有使思想與其對象——歷史具體完全分離,它所做的是提出這個依舊懸而未解的問題,特殊的思想是如何與對象構成一個整體的,盡管它“歸根到底”是被決定的(馬克思還說到,思想“一開始”就被決定了,因為它的“前提”源于“社會”)。《導言》的后續文字實際上構成了馬克思對歷史對象、思想、理論方法的辯證關系問題的最令人信服的思考,他堅信只要實踐沒有辯證地實現它,保證它為真,那么這些歷史對象生產出的知識就仍舊“僅僅是思辨的、理論的”(這里的“僅僅”沒有問題)。
盡管思想被作為它的對象的社會所接合和假定,但就它自身的方式和方法而言是特殊的,那么這種“漸進的”接合是如何完成的?我們既不能同一地也不能僅僅是外在排列地理解這里的用語。可它們整體的真正本質又是什么呢?如果表達著邏輯范疇的起源異于本質關系的起源,那么這兩者的關系又如何?思想又是如何再生產出歷史世界在思想中的具體?
答案在于歷史是如何進入“相對自主”的思想,也就是馬克思成熟著作中對思想的歷史對象的再思考的方式。歷史與思想的關系顯然不能用強調遺傳起源的歷史進化論來闡述。“基因歷史主義”用外在的“相似性”來解釋任何的特殊關系和它的“歷史背景”,這種關系的“發展”會被線性地理解并通過變種分支來追蹤:思想范疇忠實且直接地反映了這種起源和它的進化進程。這聽起來都像是天方夜譚,直到我們回想起許多當代馬克思主義案例中存在著的機械排列和對未作區分的“聯系”的做法。將馬克思從實證主義歷史方法進化論中區分出來十分重要。我們在這里面對的既不是實證主義的偽裝變體,也不是嚴格的非歷史主義,而是理論模型中尤其是對現代精神而言最困難的一種:歷史認識論。
馬克思在不同的關系之中作出了區分:直接的和中介的。這在之前理論分析時的范疇中得到了應用:生產、分配和交換。這種區分現在又得到了應用,不過這次是來分析思想與歷史的不同關系類型。他舉了個例子。在《法哲學》當中,黑格爾以“所有權”范疇為開端。所有權是個簡單的范疇,但就像“生產”一樣它離不開更為具體的關系而存在,例如擁有所有權的歷史團體。然而在資產階級意義上,占有物離開“私人所有權”的形式的話,這種團體就談不上“占有”他的所有物。不過由于這種關系,即“所有權”雖然是最簡單的形式,但它的確存在,所以我們能夠思考它,這個簡單關系是我們關于它的相對簡單的概念的“具體基礎”。如果一個概念歷史地相對未發展,那我們對它的概念將會是抽象的。在這個層面上,上述關系的歷史發展(簡單)層面和占有它的范疇的相對(稀缺)具體性之間的一種互逆關系的確存在。
然而,馬克思這里使理論/歷史變得更為復雜了。歷史地看,關系的發展并非是進化的。無論是在思想或歷史當中,從簡單向復雜的發展都不是直線的、完整的。在作為一個整體的生產方式內部,一種關系從主導地位變為次要地位是有可能的。而關于主要/次要的問題與之前簡單/發達或者抽象/具體的問題并非是“同一的”。通過在生產方式內部將關系指認為它的接合,馬克思暗示了自己從進步的、連續的或進化的歷史觀向我們可以稱之為“時期分期或方式的歷史”:結構性歷史的重大轉變。這種運動指向了方式和時期分期的觀念,打破了進化論式前進的線性軌跡,用生產方式的演替重組我們的歷史分期觀念,而這種生產方式是由構成它們內部不同關系之間的主次差異來規定的。這是關鍵的一步。如果將注意力放在馬克思用生產方式的接替來劃分歷史的話,那當然是一點原創的東西也沒有,如果這么看,就沒有完全考慮到與基因進化論的相決裂的結果。“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概念經常被當作僅僅好像是大范圍歷史的一般化概括而使用,而其中的較小歷史時期的部分則是被巧妙地排布。不過,馬克思正是用“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概念指認出了結構性的內在關系,這個內在關系打斷、打碎了歷史進化論的平滑進展。這表明馬克思與簡單的、主流形式下的歷史主義徹底決裂。當然在我們看來,這并不是與歷史本身決裂。
以貨幣為例。它在銀行、資本之前就存在。如果我們用“貨幣”這個概念來指稱這種相對簡單的關系,那我們還是在使用一種抽象而簡單的概念(像“所有權”一樣),它不如商品生產條件下的“貨幣”更加具體。由于“貨幣”變得更發達,我們關于它的概念也就變得更加具體。然而,即使是在簡單形式之下,“貨幣”仍然有可能在一種生產方式中處于主導地位。相反地,在更發達、多邊的形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更具體的范疇而言,“貨幣”在一種生產方式當中占據次要地位也是可能的。
在這個雙重適用(double-fitting)的過程當中,簡單/發達或抽象/具體的對子指的是我們稱之為歷時性的弦,分析的發展軸。主要/次要的對子指的是共時性的線軸,在這里給定的范疇或關系作為特定生產方式中與它接合的其他關系存在。馬克思總是按照主要/次要的關系來“思考”后面的這些關系。現代典型的轉向是將我們的注意力從第一個坐標軸轉移到第二種,所以會稱馬克思為潛在的結構主義。然而,困難的是后者并沒有使前者的運動停止,而是延緩或更好地說是取代了它。實際上,歷史發展的軌跡總是在結構的接合中或背后形成。“實踐認識論”的癥結,正是在于將簡單/發達線軸與主要/次要的線軸辯證地關聯起來“思考”這樣的一個必要性上。這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跋當中對自己方法的說明:“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辯證方法嗎?”
舉另外一個例子。秘魯曾經相對比較發達,但那時沒有“貨幣”。在羅馬帝國,“貨幣”存在,但是次于其他的支付關系,例如實物租、實物稅等。貨幣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才“表現出它的充分的力量”,因而,不存在貫穿于每一個相繼的歷史時期的關系以及表達這種關系的范疇的線性發展。貨幣“沒有歷盡一切歷史時期”。在不同的生產方式當中它可能出現,也可能不出現;發達或是簡單的;主導的或次要的。重要的不是連續時間中關系僅有的外觀,而是它在使得每個生產方式成為總體的生產關系中的地位。生產方式形成不連續的結構,在這其中歷史接合自身。歷史在一系列的社會形態和集合體當中運動,但僅僅是在一種被延緩和取代的軌跡上運動著。它借助于一系列的斷裂得到發展,這些斷裂則是來源于每個特定方式的內在矛盾。于是,如果想要充分適用于它的主體(即社會)的話,理論的方法必須立足于連續的生產方式中特定歷史關系的排列,而非簡單、線性結構的連續性歷史。*馬克思對另一個例子即勞動的討論,在這里被刪除了。
馬克思現在定義了思想與歷史的接合。在主要意義上,對一般(例如多邊發展)的最一般抽象只會當社會和歷史的最豐富可能性的具體發展存在時才會出現。一旦這個在現實當中發生,關系就不只是在其特殊形式(例如抽象)下被思考。勞動,作為一個寬泛、內涵豐富的概念(例如所有社會都要勞動才能再生產)已經被更加具體的“勞動一般”(一般性生產)所代替,但這僅僅是因為后一個范疇在資產階級社會指向了一個真實、具體、更加多邊的歷史現象。馬克思令人信服地指出,“一般概念在實踐中變得為真”。它在思想當中已經獲得特殊性,這使得它能夠占用勞動在實踐當中的具體關系。它“只有作為最現代的社會的范疇,才在這種抽象中表現為實際上真實的東西”,所以“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疇”,“同樣是歷史條件的產物,而且只有對于這些條件并在這些條件之內才具有充分的適用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46頁。。
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如果我們沒有放棄同一性或“抹殺一切歷史差別”,那“最發達的和最多樣性的歷史的生產組織”的資產階級社會使得我們可以考察已經消失的社會形態。因為,只要更為古老的生產方式能夠以調整過的方式存活或再現于資本主義,那么對后者的“解剖”才會提供對先前社會形態的“鑰匙”。*《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46頁。同樣,我們在“思考”資產階級社會形態范疇與那些原先已經消失的形態之間的關系時,不能將兩者直接同一起來,而是要保持它們在資產階級社會當中的外觀(也就是發達/簡單、主導/次要的關系)。在這個基礎之上,馬克思實現了對簡單的歷史進化論的批判:“所說的歷史發展總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的: 最后的形式總是把過去的形式看成是向著自己發展的各個階段。”
這是“單方面”的一種方式。但馬克思不是要將歷史從計劃中拋離出去。如果思想是植根于社會存在,而不是進化論式理解的社會存在的話,那它一定是當下社會現實,“最發達的和最多樣性的歷史的生產組織”的當代資產階級社會,它構成了思想的前提、出發點。經濟學理論的對象——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無論是在現實中還是在頭腦中都是既定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47頁。。這同樣適用于科學,它對于分篇計劃具有決定的意義。
最近有爭論認為,馬克思由于發現了范疇的歷史更替和范疇的邏輯更替之間的區別,從而最終是與“歷史主義”分道揚鑣。人們常常忘了馬克思是在討論在根本上是相對認識論的思想本身的起源時的文本中表明了上述觀點,特別是關于邏輯范疇與其所表達的關系(就是范疇所表達的社會存在)的依賴性。并不是思想本身依靠自身內部“機制”生產出來的東西,而是那些已經在頭腦中和在現實中一樣已經被具體給定的東西,才是馬克思這里討論方法的認識論基礎的出發點。
經濟范疇的次序并非按照它們歷史上起決定性作用的順序排列,這并不是因為邏輯范疇在“現實關系”之上或之外產生出自己(對于黑格爾而言這是真實的),這是因為在認識論上思想參照的不是過去而是當下(資產階級社會)的歷史生產組織。這是一種相當不同的觀點。重要的不是范疇在歷史上的順序,而是它們“在資產階級社會當中的次序”。在資產階級社會,每個范疇都不是作為分散的實體(它們的歷史發展是可以被追溯的)存在,而是處于一個“系列”、一種方式當中,處于主要/次要、決定/被決定這樣的關系整體當中。整體的這個觀點打消了任何直線歷史進化論。這一觀點經常被用來證明馬克思與歷史本身的最終決裂——這種決裂以歷史主義/科學這個對子來表達。在我看來,馬克思作出了一個區分,這種區分標志了一種不同的“斷裂”:被相繼的歷史進化論決定的思想/和當下的歷史的社會形態組織之內的思想的規定性。其中生產方式中的各種生產關系接合成為整體。
這兩者之間存在著復雜的內在關系和聯系。在每個生產方式當中都存在一個最終起決定作用的層面,即“決定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也決定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的特定生產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48頁。馬克思堅信,我們應該去注意每個整體的特殊性以及構成每個時代的起決定的、主要和次要作用的關系。這一點指向了阿爾都塞那里作為“被主要矛盾建構的”“復雜結構總體”的社會形式概念,以及“多元決定”和“接合”的補充性概念。這種模式觀念的全部理論啟示在于將馬克思視作一個走向我們成為“結構的歷史主義”方法的人。但由于思想也將自己的起源歸于(總是頭腦中給定的)“現實”,它也是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受到“當下歷史的生產組織”認識論決定。
馬克思通過舉例繼續發展了這一觀點。在資產階級社會,“農業越來越受資本的支配”。盡管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在某種程度上作過類似的歷史概括,但對范疇的次序而言,重要的不是任何一種關系的進化,如從封建所有制向工業資本進化,而是工業資本與土地所有權,或“資本”與“地租”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是封建主義方式)中的關系地位在發揮影響。在后一種情況,“組合”提供了所有理論化的起點。如果我們將那種不按時間順序逐個地追蹤各個關系的歷史發展的方法稱為“反歷史主義”,那上述這種方法就是“反歷史主義”的。但一旦我們認識到作為出發點的資產階級社會并非獨立于歷史,而是當前歷史的社會組織的話,那這個方法在深層意義上還是歷史的。資產階級社會是歷史作為一個“結果”傳到現在的。資產階級的關系總體就是歷史當下。我們可以說,歷史是漸進地實現自己的。然而,理論是“復歸式”把握歷史的。于是,理論從作為事后發展結果的歷史開始。這是它在頭腦中的前提。歷史,只有在作為“結構復雜的總體”實現過程中才會將自身作為理論勞動的認識論前提接合自身。這就是我稱為馬克思的歷史(而非歷史主義)認識論。無論是多么不成熟或不夠理論化,它使得馬克思的方法與那些哲學上非反思的傳統模式區別開來了,包括結構主義那里最終依靠科學自我形成的“科學性”,它始終帶有實證主義痕跡。科萊蒂曾簡明地表達過這一觀點。他觀察到更為理論化的馬克思主義那里存在這一種趨勢,即:
將“歷史上首先”(比如用邏輯過程的起點作為歷史前身的重演)與“現實中首先”或者分析的現實基礎混淆,結果就導致,馬克思邏輯歷史的反思在歷史的同時代性(就如盧卡奇曾說的“作為歷史的當下”)上的核心問題上達到高峰,而傳統馬克思主義已經走到了從時間源頭追溯對現在的解釋的這樣一種歷史哲學的相反方向上。*L. Colletti, Marxism & Hegel, pp. 130-131.
馬克思的“歷史認識論”反映了歷史運動與理論反思的交互接合,它不僅僅是作為一個簡單的同一性,而是整體內部的差別。他在認識論的過程和方法論中保留了被徹底重構過的歷史前提作為最終規定,所以思想與現實之間不存在著“不可通過的壁壘”,也不會無限平行。它意味著一種基于給定的基礎之上的匯集趨勢(恩格斯稱之為漸進運動),這里,資產階級社會既是理論也是實踐的基礎或對象。這種認識論依舊是“開放的”認識論,不是自我形成或自我滿足的認識論,因為它的“科學性”只有思想與“現實”以各自的方式契合才可以保證,它們生產出只能以頭腦中能夠達到的方式去把握現實的知識,同時也提供了洞察到社會表象形式背后的運動,即它們背后深層結構的“現實關系”的批判性方法。對一個社會形態結構規律和趨勢的這種科學把握同樣也是對它“逝去的”規律和趨勢的把握:不是對其可能性的證明,而是一種在實踐中、實踐解決中知識可能性的實現。在階級斗爭中有意識地推翻那些關系,這個階級斗爭圍繞著社會矛盾趨勢的前進,它不僅僅是“純粹思辨”,也遠不是理論思辨。正如科萊蒂所說的,這里我們不再囿于思想中討論“思想存在”關系,而是在思想與現實關系之中言說它。*L. Colletti, Marxism & Hegel, p. 134.
參考《導言》中的方法論觀點來看《大綱》中的一些篇章是有意義的。在《大綱》中詳盡地區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歷史起源”和作為“當下歷史的生產組織”的資本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451頁及后面部分。馬克思討論的資本主義方式依靠貨幣向資本的轉化,所以貨幣構成了“資本的洪水期前的條件,屬于資本的歷史前提”之一。不過一旦它向商品生產的現代形式的轉型完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完成),資本主義就再也不直接依賴對自身延續性歷史前提的重演。“這些前提作為這樣的歷史前提已經成為過去,因而屬于資本的形成史,但決不屬于資本的現代史,也就是說,不屬于受資本統治的生產方式的實際體系”。簡言之,一種生產方式出現的歷史條件會消失在這個生產方式的結果中,而當資本主義“根據自己的內在本質,事實上創造出它在生產中當作出發點的那些條件本身”*《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451頁。設定自身時,這些歷史條件會得以重組。它(資本主義)“不再從前提出發,它本身就是前提,它從它自身出發,自己創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452頁。。這個觀點也是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錯誤的批判之一,他們混淆了使得資本主義成為現在樣子的以往條件和當下資本主義組織條件,馬克思將這一錯誤歸咎為政治經濟學將資本主義的和諧律看作是自然和普遍的傾向。
《大綱》和后來的《資本論》表明,以下的論斷將不會持續太久:《導言》中馬克思關于“范疇次序”的簡單評述是全盤放棄了“歷史”方法,而走向了本質上是共時性、(通常意義上)結構主義的方法。很清楚,馬克思有時會特別執著于關注對資本主義某個核心范疇或關系起源的巧妙重構。我們必須將此與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解剖學”分析區別開來。從分析和理論的角度看,資本主義是作為正在進行中的生產結構、諸個生產性方式結合的“當前歷史的生產組織”,而在“解剖學”方法那里,歷史與結構已經是明確地被重構的。就如《資本論》第一卷跋中所表明的那樣,對于馬克思讀者們的方法論要求是要同時掌握這兩個方法。這樣的嚴格要求使得他的辯證法既獲得了全面性又有著特別的困難。不過人們總是會因為想要逃避馬克思理論中的困難而趨向于二選一(不管是選擇歷史的還是結構的),因為《導言》中也沒有明確的依據。正如霍布斯鮑姆所言:
一個只關注系統持存的結構性方式是不充分的。(充分的)方式必須能夠反映穩定性和破壞性兩種成分的同時存在……這種雙重(辯證)的方式很難建立和使用,因為人們在實踐中往往會根據好惡和場合去操作它,要么把它當作是一種穩定的功能主義要么是一種革命性的變革;有趣的是實際上它兼而有之。*E. Hobsbawm, Marx’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ography, in Ideology & Social Science, ed. Blackburn.
這里不僅僅涉及到了《導言》,也涉及到了《資本論》當中方法問題的核心,在《導言》中是提供了線索但沒有得到解決。例如,戈德利埃(Maurice Godelier)支持“結構研究對于起源和進化論研究的優先性”,這是內在于《資本論》體系結構中的觀點。當然,《資本論》的主要重點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系統分析,而不會對作為社會形態的資產階級社會的起源進行復雜重建。所以,在《資本論》第三卷較長部分的“地租”開篇講到:“對土地所有權的各種歷史形式的分析,不屬于本書的范圍……農業和制造業完全一樣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6卷,人民出版社,第693頁。這并不與其他篇章的中心論點矛盾,雖然那些篇章形式上都直接就是歷史或起源式的(包括《資本論》第三卷關于地租的某些部分),而地租部分的開頭與這些段落的中心思想并不矛盾。的確,這里存在著對不同種類寫作的重要區分。許多我們現在看起來是“歷史的”東西在馬克思看來當然是直接和同時代的東西。《資本論》第一卷中的“工作日”部分生動地描述了歷史圖景,一些理論觀點也以它作為支撐,例如,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工業勞動的形式的分析,以及資本主義制度一開始能夠延長工作日,然而當勞動被組織起來,又轉向限制工作日(“長期的內戰的產物”)。這兩者形態上都不同于同一卷之前宣稱的“指明這種貨幣形式的起源……從最簡單的最不顯眼的形式……炫目的貨幣形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第62頁。。這個起源應該“同時解決貨幣之謎”,但實際上在“貨幣歷史”形式下看不到,而是要去分析“價值形式”。不同于《資本論》第一卷中大量的歷史材料,所有這些材料都是要處理“起源”問題的,而馬克思對此是有意地把它們放在基本理論闡述之后,而不是之前。所有這些都不能改變我們對貫穿于《資本論》全部的深層歷史想象。重要的是,《資本論》的體系化的形式絕不會切斷基本的歷史前提,這個歷史前提制定了整個解釋框架,而且矛盾的是,馬克思所宣稱的《資本論》的“科學性”恰恰依賴于這個歷史前提:歷史特定的,因而短暫的東西,這就是資本主義時代以及表達它的范疇的本質。早在1846年他在評論普魯東時已經向安年柯夫說過:“他沒有看到:經濟范疇只是這些現實關系的抽象,它們僅僅在這些關系存在的時候才是真實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7卷,人民出版社,第482頁。這一想法從未改變。*馬克思在同樣的意義上毫不猶豫引了《歐洲通報》的評論家的評論,見《資本論》第二版跋。
毫無疑問,整個來看《資本論》處理的是資本主義系統擴大規模再生產所需的形式與關系,就是它的結構及其變異。恰恰是手稿中一些最令人費解的部分構成了對資本循環形式的“揭露”,而資本的循環保證了這種“形態變化”的發生。不過馬克思的方法是基于將兩個辯證相關但不連續的層面作出的區分,即支撐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的矛盾、對抗性“現實關系”和其中矛盾以看似“平衡”的方式顯示著的“表現形式”。正是后者顯示了對系統“承擔者”的意識,并形成了中介它的運動的法和哲學概念。批判的科學必須揭露資本結構演變的顛倒形式,從而揭露其對抗的“現實關系”。關于“商品拜物教”(現在有時流行將它和其他黑格爾主義痕跡一樣拋棄)難懂卻極其重要的開頭部分不僅僅實質上為剩下部分的闡述奠定基礎,它們也成為了一種邏輯與方法演繹的杰出代表,《資本論》中其他發現的產生依靠的也是這一邏輯和方法。*最近,從對馬克思的“反歷史主義”的闡釋的角度重申“拜物教”在《資本論》中所占據的中心地位,讓人耳目一新:參見《與科萊蒂的訪談》,《新左派評論》1974年第86輯。因而,盡管對于馬克思而言,從外部來看令人驚愕的是資本主義的自我再生產,但他的理論正是由于能夠展示結構的“表現形式”是可以被看透、看穿其前提所以才超越政治經濟學,就像一個人“要猜出這種象形文字的涵義,要了解他們自己的社會產品的秘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第91頁。。馬克思想要讓我們注意到,資本主義永恒的、自我再生產的“外觀”恰恰來源于我們“遺失”(錯誤認識)了它是一種社會創造、在歷史生產形式下的運動:
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這些形式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給勞動產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們試圖了解它們的內容而不是了解它們的歷史性質(這些形式在人們看來已經是不變的了)以前,就已經取得了社會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第93頁。
同樣,“我們前面所考察的經濟范疇,也都帶有自己的歷史痕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第197頁。。它們“對于這個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即商品生產的生產關系來說……是有社會效力的、因而是客觀的思維形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第93頁。。這種解讀方法在其實際狀態下認為:“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余的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6卷,人民出版社,第925頁。,但這種解讀不僅僅是批判。它是對某個特殊類型的批判,這種類型的方法不僅揭露“表面現象”背后的“本質關系”,而且也這樣揭露了只以“表面現象”出現的系統表面之下作用于自我增殖的那個具有矛盾和對抗性的必要內容。對于每一個馬克思“破譯”(decipher)的核心范疇而言情況就是這樣,它們包括:商品、勞動、工資、價格、等價交換、資本有機構成等等。通過這個方法,馬克思結合了兩種分析。第一個分析脫去資本主義工作原理的外觀,發現了它們“隱藏的基礎”,因而可以揭開它的真實工作原理;另一個分析揭露了這種功能主義在深層次上也是自身“否定”的根源(和自然律一樣無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第874頁。。前者引導我們走向意識形態層面,“表現形式”在視為正當的表面價值上使用:它們“直接地、自發地、作為流行的思維形式再現出來的”,例如是常識性觀點的流行形式。后者考察“隱藏在它們背后的基礎”的“本質關系”:它們“只有科學才能揭示出來”。古典政治經濟學證明了(但只是通過批判)為第二種科學層面分析提供了基礎,因為它“幾乎接觸到事物的真實狀況,但是沒有自覺地把它表述出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第621-622頁。。馬克思的批判超越了它的政治經濟學來源,這不僅是因為它有意識勾畫出了沒有說的東西,還是因為它揭露了“自動的方式”、“自發的生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第180頁。下隱藏著的對抗性運動。《資本論》開頭對商品二重性(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初看起來僅僅是正式闡述的分析只是說出了第一個實質性結論,到了“資本的總公式”這一章等量的流通(M-C-M)被重新定義為不等量的流通(M-C-M’), 這里“我把這個增殖額或超過原價值的余額叫作剩余價值”,“正是這種運動使價值轉化為資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第176頁。。正如尼古拉斯評論的:
剝削在交換過程背后繼續進行……生產包含一種交換行為,另一方面它也包含與交換相反的行為……等量交換是生產的基本社會關系,所以對非等價物的抽出也是生產的基礎性力量。*In Blackburn, (ed), op. cit. pp. 324-5.
如果把馬克思僅僅當作是一位研究“結構與其變異”,而不關注結構的界限、斷裂和超越的理論家,那就是出于一種完全抽象的科學主義目的,將辯證分析置換為一種結構功能主義分析。
戈德利埃注意到了,對一個結構變異的分析必須要有矛盾的觀點。但是這位結構主義者在這方面的處理當中總帶著“功能主義”的影子。因而,對于戈德利埃而言,馬克思對系統的分析存在著兩個功能性矛盾:資本與勞動(生產的社會關系結構內部矛盾)和工業大生產條件下勞動的社會化本質和資本的生產力(結構之間的矛盾)。戈德利埃看重后者(來源于系統的客觀屬性)超過前者(階級斗爭)。而馬克思意在將兩者聯系起來:在系統的客觀矛盾趨勢當中找到階級斗爭的自我意識實踐。*這兩條線索的完美和復雜的結合出現在諸如《資本論》第一卷的一些篇章中。戈德利埃提供了一個清晰的二元對立,即具有客觀物質性、系統的“科學”矛盾與附帶的、具有目的論色彩的階級斗爭實踐的對立,這兩者在面對理論與實踐的本質內在聯系時消失了。柯爾施很久之前就正確地指出,“將社會階級間的對立貶低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基礎性矛盾是黑格爾主義的”*K. Korsch, Karl Marx, p. 201.。馬克思寫完信時概括了第三卷的理論依據:“最后,既然這三種形式(工資、地租、利潤(利息))是……這三個階級的收入來源,結論就是階級斗爭,在這一斗爭中,這種運動和全部臟東西的分解會獲得解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2卷,人民出版社,第75頁。
當戈德里埃引用馬克思給庫格曼的信——“我不僅把大工業看作是對抗的根源,而且也看作是解決這些對抗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的創造者”時,戈德利埃貌似完全沒有看到后半部分內容。對馬克思來講,正是內在貫徹了伴隨著階級斗爭政治的生產方式的客觀矛盾,才使得他的理論超越“烏托邦”的層面成為了科學;同樣,正是“自為”階級的形成與充要理論的一致,保證了理論與實踐的“復雜同一性”。在馬克思那里,尤其在批判過黑格爾之后,理論與實踐的同一性不會單單立足于理論。
《導言》總結部分依舊是非常模糊的筆記,*《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50-53頁。是“應該在這里提到而不該忘記的各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50頁。。在這段內容當中迅速列出來的要點的確在理論上具有最高的重要性,然而幾乎沒有任何我們可以稱得上是“說明”的東西。它們最多稱得上線索,告訴我們馬克思的頭腦里已經有了這些非常重要的問題,但沒有揭示馬克思究竟是怎么思考這些問題的。它們主要與上層建筑的形式相關:“國家形式和意識形式同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關系、法的關系、家庭關系”。現代的讀者也許會用至少和“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一樣長的篇幅來論述,但是《導言》那里并沒有。
于是,我們只能注意到在他那里面對哪些問題。這些問題涉及諸如如何準確理解“生產力”、“生產關系”等關鍵概念。更重要的是,它們在更具中介性的層面上對以下概念作了規定,包括從戰爭到軍隊、從文化史到歷史學、到國際關系、藝術、教育和法律等等這些基礎概念之間的關系。最具重要性的兩個概念構想得到了簡明闡述。首先,要再一次區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不要把它們當作是兩個沒有關聯的結構,要辯證地去理解。這個辯證關系的邊界在任何(被決定的)理論的豐富性當中都要詳細說明,這個辯證聯系地看待這兩個術語,而非“直接同一”,它沒有懸置二者真實的差異。第二,從藝術發展、教育和法律到物質生產的關系要作為構成“不平衡發展”的關系來詳細說明,這同樣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理論指示。
之后,在藝術發展和物質生產的問題上馬克思作了簡單的擴充。藝術對生產的不平衡關系是用一個對比來說明的,在還處于早期的社會組織“骨骼”的希臘文明與從中產生的偉大藝術作品。史詩作為一個發達范疇出現在了簡單而古老的生產方式當中。這就不同于之前“貨幣”的例子,那時的貨幣外觀依舊是局限于不發達的生產關系當中。“結構與上層建筑關系的不平衡規律”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雖然馬克思在這里展開了這個問題,但他并不是要特地發展出一個馬克思主義美學,更多地是關注方法和概念化的問題。他的觀點表明,就像貨幣、勞動一樣,藝術絕不會隨著它的物質基礎歷經一個從早期到晚期、從簡單到發達的單一、有序的進程。我們必須站在特定階段來看待它的形態聯系。
他所舉的希臘藝術的具體例子是服從于同樣的理論問題。希臘藝術假定了一系列特定的關系為前提,它需要古代社會生產力的具體組織,這些都是與精紡機、鐵道和機車不相適應的。它需要自己的特殊生產方式,是不同于電力和打印機的史詩歌謠。而且,它還要求它自身意識的形式:神話。當然,不是所有的神話都可以,例如埃及神話就屬于另一個不同的思想結合體。在人們對自然的科學掌握和改造沒有充分完成之前,作為(在思想層面的)思維形式的神話才能夠存在。只要科學和技術沒有取代對自然的社會和物質的魔法妥協,神話就會持續下去。因此,神話是一種意識的形式,只有在一定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上才有可能。由于神話構成了具有史詩特點的內容和想象方式,所以史詩(通過復雜且不平衡的中介鏈)與希臘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生聯系。那么,這種歷史連接是可逆的嗎?難道古代社會和史詩不是一起消失的嗎?在現代戰爭中還可以想象出阿里基斯的英雄形象嗎?
馬克思沒有在論證藝術和物質形式的歷史共存時結束自己的思考。他發現,更大的理論困難是去理解如此明顯的古代形式如何與“生產的當下歷史組織”發生聯系。這里馬克思又舉了一個具體的例子,按照他的方法將對具體案例的分析、復雜結構的跨時代發展和當下生產方式中各種關系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結構性“規律”結合了起來。盡管簡明概要,但他的說明是很有代表性的。就“人類童年時代”帶給我們愉快這方面來講,為什么我們依舊會肯定地回應史詩或希臘歌劇?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幾乎在所有方面都不能令人滿意,它們都是一帶而過式的。這些令人費解又偏理論的(而且在我們的時代日益關鍵和重大的)話題是在文體(stylistically)意義而非概念(conceptually)意義上得到解決的。
如果有的話,1857年這篇導言對馬克思“理論斷裂”問題會有什么樣的啟示?馬克思認為古典政治經濟學是新興資產階級的新科學,在它的古典形式中,它力圖總結出資本主義生產的規律。馬克思從未幻想過政治經濟學在沒有被轉變的情況下,能夠在理論上成為一個足以引導革命行動的科學。他一次又一次地嚴格區分了“古典”的和庸俗的形態,前者開始于配第、布阿吉爾貝爾和亞當·斯密,結束于李嘉圖和西斯蒙第,后者則是馬克思不屑一顧、卻又后來終其一生徹底閱讀和激烈爭論的那些人。盡管如此,馬克思從未幻想(未經轉型的)政治經濟學能夠在理論上成為革命行動的科學指導。他的部分最尖銳的批判留給了所謂“激進”政治經濟學家——“左派李嘉圖主義”,像是布雷、歐文主義者們、洛貝爾圖斯、拉薩爾和普魯東,他們認為政治經濟學在理論上自足就行,而不顧政治應用時的偏差,按照理論的需要來提出對社會關系的相應變革。在李嘉圖派的社會主義者看來,由于勞動是價值的來源,因而所有的人都應該可以按照勞動的等價交換變成勞動者。馬克思選擇了更艱難的一條路。等價交換雖然在某個層面是“足夠現實”,但在另一層面上非常地“不現實”。這就是政治經濟學無法逾越的地方。然而,僅僅知道這個真相,在馬克思那里并不能保證實踐的現實。這些規律(指等價交換)只能在實踐中被拋棄,即它們不可能在范疇的戲法中得到改造。于是,在這一點上,對政治經濟學及其激進修正主義的批判合并到了對黑格爾及其激進修正者(左派黑格爾主義)的形而上學批判當中。當然,當馬克思說普魯東“在政治經濟的異化范圍內來克服政治經濟的異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53頁。,如果不是有意模仿,那就是直接恢復了普魯東對黑格爾已作的批判。
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關系要在理論上被完全超越,就必須在實踐中首先被推翻,正是這一點解釋了馬克思成熟作品與政治經濟學之間復雜且矛盾的關系,也說清楚了我們嘗試準確地厘清作為“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在何處最終完全與政治經濟學劃清界限是極其困難的。這種困難突出地表現在,這些年馬克思與黑格爾關系問題已經成為首要問題,我們可能不得不暫時收回已有的相同答案,重新回到每一個問題的形式上來。
馬克思整個成熟的作品都是對政治經濟學范疇的批判。1857年導言開啟了對方法的批判,但沒有收尾。但政治經濟學依舊是馬克思僅有的理論出發點。就像擺脫李嘉圖工資理論外衣或者突破懸置的剩余價值概念一樣,甚至當政治經濟學已經被征服和改造了,馬克思仍然會回到它那里,凝練出與自己不同的地方,審視它、批評它、超越它。因而,即使當馬克思的理論表述為歷史形態的唯物主義科學奠定了基礎時,政治經濟學的“規律”依舊在理論上統治著這片領域,因為它們在實踐中主導著社會生活。要解釋馬克思關于德國“理論意識”的觀點,不在理論上拋棄政治經濟學的話,它在實踐中是不能實現的,就像從另一方面來講,只有在理論上已經實現它才可以在實踐中被拋棄。
這里決不是要否認馬克思的“偉大發現”。無論如何,《資本論》中揭露和重新表述的雙重意義,它的長期懸置(馬克思揭露資本的循環“似乎實際如此”,只是為了在后一部分表明當我們回到它們真實聯系的“純粹情況”時會發生什么),它的轉變都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科學”批判奠定了基礎。它到最后都保留著這個批判,當然,這個批判(回到1857年的本文)是以作為他的方法科學性的形式出現的。
有必要講清楚他的批判所指向的最終本質。它并非企圖建立一個科學上自足的理論來取代政治經濟學結構上的不足,他的工作不是用一個知識代替另一個知識的“理論式”(theoreticist)。在1848年革命之后,馬克思的思想很清楚越來越多表現在理論工作中。無疑他作品中系統且規范的性質使得它獨樹一幟,迫使它具有排斥和吸收的形式:那些文字強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盡管如此,在后繼手稿和為《資本論》準備的手稿中的理論勞動中有不同于“科學基礎”的其他東西,這是和他的預期結果自相矛盾的。我們至今仍不能假裝已經掌握了這種相當復雜的接合,這個接合聯接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形式和階級斗爭的革命實踐。但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馬克思理論的力量和歷史重要性正是與理論與實踐的雙重接合(double articulation)相關聯的,盡管某些方面我們還沒有完全理解。到目前為止,我們熟悉了對論戰性文本(例如《共產黨宣言》)的“閱讀”,但只是冰山一角,也就是說,理論是透過更為“直接的”政治分析和修辭折射出來的。在后面的著作當中,當我們只能一瞥階級斗爭運動,也就是說,階級斗爭運動是透過理論結構和觀點折射出來時我們依舊會感到困擾。一種強烈的沖動使得我們相信,后來只有科學會繼續存在。
我們認為,馬克思業已成熟的方法并不是要找到代替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封閉理論,也不是要通過“真實的人”用唯心主義方式取代異化的資產階級關系。的確,他作品中偉大的部分是由深刻的革命和批判的任務組成的,這個任務展示了政治經濟學規律是如何真實運作的。它們中部分地是通過每個形式來運作,他耐心地分析了“表現形式”。馬克思的批判使得我們能夠看到和揭示資本主義的真實關系。在系統闡述這個批判的節點時,政治經濟學作為上述關系精神范疇的最高表達,為我們提供了唯一可能的起點。馬克思就從那里開始。《資本論》依舊是《政治經濟學批判》,而不是《共產主義:資本主義的一個替代》。認為馬克思與政治經濟學之間存在著一種終極的、徹底和完全的“斷裂”是個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觀點,這一觀點不可能公平對待理論勞動的復雜性,而這卻是《資本論》和整個工作所必需的。
在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關系問題上也是如此,即便我們更容易指出二者之間存在的實質性“斷裂”(不管怎樣,馬克思自己一次又一次提到了這個問題)。馬克思與黑格爾在方法上的關系問題長期以來一直困擾著我們。馬克思與恩格斯從來都是這樣一個標志,黑格爾思想中的唯心主義框架必須被徹底地放棄。唯心主義形式的辯證法也必須經歷一個徹底轉型,以便其真實的科學內核成為對歷史唯物主義有用的科學起點。已經得到證明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可以從黑格爾唯心主義外殼中發掘合理的東西時,意思并不是特別清楚。然而,那些習慣于在語言中用觀念來說明歷史的人,似乎特別沉迷于“內核”和“外殼”這樣令人費解的隱喻之中。當黑格爾的體系作為神秘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垃圾而必須被徹底摒棄時,通過徹底轉型才能發掘的黑格爾方法中還有什么東西呢?但這就像在問,既然李嘉圖標志著資產階級科學的終結(還是一位必須被趕走的有錢的銀行家),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者還能從他那里學到什么東西嗎?顯然可以有,馬克思的確這么做了。即便是處在解體李嘉圖的痛苦之時,他也從未停止向李嘉圖學習。他從來沒有逃避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砥礪,即使他知道這門學問無法擺脫資產階級的思維習慣。以同樣的方式,只要馬克思涉及到對黑格爾體系的徹底批判,他總是強調自己是那位“偉大的思想家”的學生,強調“顛倒過來”的辯證法的積極意義。與《資本論》的作者不是李嘉圖主義者一樣,成熟馬克思也不是一個“黑格爾主義者”。否則,就是對作為知識形式和辯證方法的“批判”本質的最大的誤解。可以說,在1857年《導言》中,恰恰是在馬克思明確學習或再學習黑格爾辯證方法的地方,黑格爾一次次被放棄和推翻。該文本中所展現的馬克思成熟時期方法論上的結構性變化、對于黑格爾和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返回-轉型”,直到今天都為我們奠定了光輝的理論典范。
(責任編輯:周文升)
[中圖分類號]A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45[2016]07-0005-19
·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學術主持人:張亮)·
①在本文的后期校對過程中,譯者部分地參考了范雪麒的譯文,特此說明并致謝!——譯者
編者按: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1932—2014)是當代英國最有影響力的左派公共知識分子之一。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他領導新成立的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簡稱CCCS)對一系列具有重大社會關切的文化現象進行開創性研究,創立文化研究中的伯明翰學派,也由此被尊為真正的“文化研究之父”。按照霍爾自己的說法,20世紀70年代是他與馬克思主義關系最密切的一個時期。由于缺乏必要的文獻支持,國內學界對霍爾的這個自述往往是將信將疑,無法確信。事實上,70年代確實是霍爾“最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時期。對此的一個有力證據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霍爾等積極推動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英譯,并在1973年英文全譯本出版后,在中心內部組織專題研討班,發表了題為《馬克思論方法:讀1857年〈導言〉》的工作論文,對《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導言》進行了創造性的解讀。這種解讀為其70年代的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支撐。從某種意義上講,不了解《馬克思論方法:讀1857年〈導言〉》,我們很難真實而全面地把握霍爾70年代文化研究的總體內在邏輯及其走向。1973年,《馬克思論方法:讀1857年〈導言〉》首先以中心的工作論文油印發表,次年它的修訂版在美國的《文化研究》雜志正式公開發表,2003年《文化研究》雜志再次發表該文。該文的經典性和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有鑒于此,本刊特組織翻譯了這篇經典文獻,并配發了譯者撰寫的導讀論文,希望以此推動國內霍爾研究以及伯明翰學派研究的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