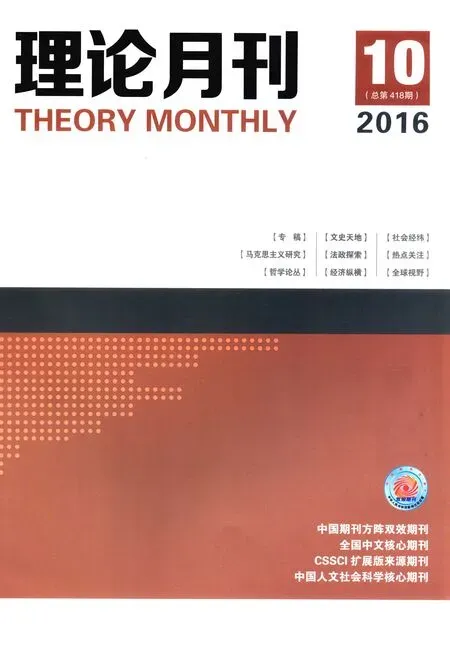朱珔假借違背訓詁原理和形式邏輯研究
□陳正正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北京 100875)
朱珔假借違背訓詁原理和形式邏輯研究
□陳正正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北京 100875)
朱珔是清代假借研究的大家,其《說文假借義證》一書作了大量的假借字的搜集與系聯工作。但其假借研究有違背訓詁原理與形式邏輯之處,需要我們加以注意。研究朱珔的假借研究失誤,有助于我們認識訓詁工作是一項復雜且理性的工作,既要充分占有材料,也要符合訓詁原理和邏輯規則。要在“經驗訓詁學”基礎上,上升到理論層次,糾正相關錯誤,增強結論的可靠性。
朱珔;說文假借義證;假借;訓詁原理;形式邏輯
[DOI編號]10.14180/j.cnki.1004-0544.2016.10.015
朱珔的《說文假借義證》[1]一書是清代假借研究的重要著作,全書共對《說文》三千多個字頭的通假字進行了系聯歸納,他是清代假借研究的重要學者。可是朱氏的假借字考訂工作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違背訓詁原理,也有一些不合形式邏輯之處,這些需要我們作出進一步清理。
1 有違訓詁原理之處
1.1定義過寬,誤定假借
朱珔的假借判定標準與前人不同,他的根本在于“義證”,即他尋找的本字是一定要符合文獻意義的,或者說能夠在原文講得通的字。而這樣的判定就違背了假借音義關系的訓詁原理。故劉志成即批評道“其中不辨古今字、異體字及形音毫無關系的同義異文,故其訛誤隨處可見。”[2]
1.1.1以訓釋字為假借。朱氏的邏輯認為進行訓釋后就可以使文意理順、明確無誤,故將相當多的訓釋詞列為本字,而對訓釋詞本身的特征及復雜性認識不足。
王寧先生曾強調義與訓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概念,“義是詞形所負載的客觀內容,它是詞進入使用狀態后在確定的語境中自然顯現的,而訓則是對這種客觀內容的人為表述”。[3]而且訓釋又包括兩類,一類是對客觀詞意進行表述的“詞義訓釋”,一類是講解詞在文中的具體含意,疏通句、段、章的思想內容的“文意訓釋”。[4]訓釋合于“義證”就將其定為假借顯然是不妥當的:第一,文意訓釋只存在于特定的語境當中,只是說明某一特點,解釋作者意圖,屬于具體言語行為,而非語言現象,無法遷移;第二,因為詞義本身的復雜性,即便是詞義訓釋也只能解釋一部分的詞義,不能做到面面俱到,尤其是隨文釋義當中詞義與訓釋更不可能對等;第三,訓釋里有一種特定類型的“聲訓”,它揭示是詞源意義,是解釋事物得名之由,而并非使用的詞匯意義,更是不能簡單的代換分析。比如以下的訓釋絕非假借:
則,《玉篇》:“則,法也”。《爾雅·釋詁》:“則,常也”。疏謂常禮法也。《周禮·天官冡宰》:“以八則治都鄙”,鄭注:則,法也。是則可為法之假借(卷八)。
既,《禹貢》:“沱潛既道,荊岐既旅”,《史記·夏本紀》“既”俱作“已”,此以已訓既,既即已之假借,今既字多如此義,罕有本義者(卷十)。
按:如朱氏所言,既的本義為“小食也”,即盡食也。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契文象人事矣,顧左右而將去之也,引申之義未盡。”盡即已經義。
如朱氏這樣“以訓代義”,又“以義代字”,出現了雙重邏輯替換,違背了“假借”這一用字現象的社會約定性事實。出現這類錯誤一方面在于朱氏過于迷信古注,另一方面也在于朱氏的假借觀,將能夠替換且文意不走樣的“直訓”詞當作假借字來分析。朱氏從字的層面來探求假借關系,忽視了漢字在語言文字當中是作為不同單位而出現的,我們不能透過“字本位”觀察語義的表現,看到字詞義所處的不同層次。
1.1.2以同義字為假借。古代小學家在訓釋詞語時,多選擇義同、義近的字詞來進行訓釋,而朱氏卻將其當作了假借。如:
高,《檀弓》:“以從先大夫于九京也”,注:京當為原,《晉語》同,是京為原之假借。高平曰原,與京之本義亦通(卷十)。
按:《說文》:“京,人所為絕高丘也”,原為“高平曰邍”的“邍”的借字,本義為水源泉,也有高處義。
鼠,《史記·灌夫傳》“首鼠兩端”,《后漢·鄧訓傳》“首施兩端”,注:首施,猶首鼠也。《西羌傳》亦作“首施”,是以施為鼠之假借。施音弛,與鼠音轉(卷十九)。
按:據考證,鼠在此處當“尾”講,詞義是因為老鼠的形體特征而引申的。鼠名以尾,鼠引申有尾義。施也當“尾”講。[5]朱氏以訓代字,非是。
同義字的特點是有共同的記詞功能,在一定語境之下可以互換。而在用字假借關系當中,確定本字的前提即有借字不存在的記詞功能。朱氏在“義證”的假借觀指導下,忽視了本字、借字在記詞功能上的差異。
1.1.3以異體字為假借。釆,《易》:“剝牀以辨”,鄭注:“足下稱辨”。虞翻曰:“指間稱辨”。錢謂應作此,蓋以辨為釆之假借,義亦本通(卷三)。
按:《說文》:“釆,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其古文字字形為“”、“”、“”,其形似獣爪之形,與番、蹯同義。王筠《說文釋例》:“釆字當為獣爪為正義,辨別為引申義,以其象形知之”。[6]可知《說文》為引申義。《說文》中常用“讀若”以當代通前代,溝通古字與后出字,[7]“辨”當為“釆”后出異體字。
駃,《尸子》云:“黃河龍門,駃流入竹箭”。駃流,快流也。駃或為快之假借。俱從夬聲也(卷十九)。
按:駃、快為異體字,快為明確表義作用更換形符,其記詞功能相同。《說文·馬部》:“駃,今俗與快同用”。
異體字的著眼點在于記錄語詞的功能相同,其只不過是在不同文獻當中的用字選擇不同。朱氏卻將其定義為假借字,擴大了假借的范圍。
1.1.4以分化字為假借。漢字因為漢語的詞義引申以及假借借用,導致一字承擔多個職能,為了使表意更加明確,更好地記錄漢語需求。漢字常通過增加、改換、調整構件的方式來達到漢字的孳乳與分化。而朱氏則強調專字專用,即本字只有一個。對于漢字孳乳過程當中的本義分化與引申義分化均視作假借現象,實則是擴大了假借的范圍。
丩,《魏風》:“糾糾葛屨”,《毛傳》:“糾糾猶繚繚也”。糾當為丩之假借。本部糾,繩三合也,引申為糾察、為糾聚,皆借義也,字亦作糺(卷五)。
按:丩是糾的古字,《說文》:“丩,相糾繚也。一曰:瓜瓠結丩起。象形。”參照古文字字形“”、“”、“”,許說無誤。丩為象形字,表相糾纏義,后加“纟”旁強化本義,后“丩”廢棄不用,“糾”屬于后起字。
恒,《詩·生民》:“恒之秬秠”。《毛傳》:“恒,徧也”。《釋文》:“本又作亙”。案:《木部》:“,竟也,古文為”,竟與徧義合,則恒當為亙之假借(卷二十六)。
按:亙是恒的古字,姚孝遂先生即認為則恒為亙的孳乳字,并非假借關系。[8]加心為強化表義。亙古文字形體為“”、“”,舟為月變形。
與其同時代的朱駿聲也存在不認可文字孳乳現象,將后起本字歸入假借字類,王力先生對其作出了批評,如:
本來,漢字最初的數量是不多的,同音假借的情況最為普遍。所謂的“本字”往往反而是后起的字。因此,“本字”是經典中罕見的,甚至是沒有的。[9]
裘錫圭先生也有類似的分析,認為:
朱氏之所以這樣做,是由于他跟其他清代文字學者一樣,過分推崇《說文》,不加分析地把《說文》奉為用字的圭臬的緣故。[10]
王力、裘錫圭先生對朱駿聲的批評在朱珔身上一樣是適用的。《說文》一書后人認為“許書之要,在明文字之本義而已”,[11]《說文》主要任務是解讀本字本義。朱氏否認了漢字發展的現實,將《說文》當中收錄的字,不關注其產生的年代,一律將其視為“本字”,忽略了“后起本字”的現象。朱氏將由于語詞的引申而推動文字孳乳產生的“后起本字”一律視為假借字,是欠妥當的。在另一方面也顯示了朱氏對文字假借與詞義引申未能完全區別開的局限之處。
1.1.5以同源詞為假借。相當多的假借字的本字是很難找尋的,有些本字早已經廢棄不用。清代小學家常為了“炫博”,為很難找到本字的假借字找到一個音義關系密切的本字。正如裘錫圭先生所批評的那樣:“從清代以來,有很多人給方言、俗語里的詞找本字。那些找得根本不對頭的且不去說他,就是那些找得比較好的,所找到的也往往并不是真正的本字,而只是代表同源詞的字”。[12]比如胡,《廣雅·釋詁》:“胡,何也”,與《詩》:“日月胡能,有定風雨,云胡不夷”。《毛傳》同,胡蓋何之假借,音相轉(卷八)。
按:胡在此處為疑問代詞,相當于“何”,胡、何屬于關系密切的同源詞。
泉,《周禮·外府注》:“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曰水泉,或作錢”。案:《金部》錢字云,銚也,古者田器。引《詩》:“庤乃錢轉”。小徐曰:“一曰貨也”。后以錢謂泉之假借,錢行而泉廢。
按:錢、泉為關系密切的同源詞,“錢”為“泉”的派生詞,因為二者均有貯藏與流通兩種特性。[13]詞源意義相通。
1.1.6以聯綿詞異形為假借。假借的出現伴隨著產生了閱讀障礙,因用字產生的差異,造成了字詞關系的不對應。因此有學者主張,假借必須是一個詞義單位,同時要具有詞義轉移的特征。而“聯綿詞”的特點是“記音不記形”,無所謂正字存在,本質是雙音節單純詞,與假借字的“借音不借義”存在著本質區別。段玉裁認為“古有以聲不以義者,如猶豫雙聲,亦作猶與,亦作冘豫,皆遲疑之貌”。[14]朱氏卻都將這些“本無其字”的假借當做了“本有其字”的假借,將文字學上假借當做訓詁學上的假借,必求其本字、正字,是不適宜的。如:
扶,《禮記·檀弓》引詩“扶服救之”,今《邶風》作“匍匐救之”,又《左氏昭廿一年傳》“扶伏而擊之”,皆當為匍匐之假借(卷二十三)。
丁,《字書》有“伶仃”字,許不收。仃,《晉書·李密傳》“零丁孤苦”,則“伶仃”當為“零丁”之假借(卷二十八)。
以上的分析中扶服、匍匐、伶仃、零丁等均為聯綿詞,這些詞的字形并不表示意義,僅借字之聲以標義,幾種形式均可,只是后來使用過程及詞匯規范整理時,按照約定俗成的原則確定了一個正字。裘錫圭先生將沒有本字的詞當中,常用習慣字命名為“俗本字”,[15]這應當是比較恰當科學的。
以聯綿詞的不同形式為假借,根由還是朱氏的正字觀的指導,而忽略了聯綿詞形成的原因。聯綿詞的本質就是只記音,而不記形的。
1.2拘泥《說文》,脫離用字
《說文》一書在清代成為重點研究的對象,其收字、釋義均被奉為圭臬而不可更改。但是從東漢至清代,漢字的使用一直在發生變化。這其中既有詞匯的發展推動新字的產生與舊字的改造;也有一些漢字歸并造成的某些字摒棄不用。而朱氏對假借的判定多拘泥于《說文》所收字形,忽略了漢字形體的變遷。
1.2.1以《說文》為準,忽略漢字發展事實。朱氏以《說文》收錄字來進行分析,如果某字《說文》無,那將在《說文》中另外尋一本字。這種脫離用字實際來進行假借判定,是缺乏動態發展的眼光,也是拘泥《說文》字形的表現。
詣,《關中記》“建章宮有枍詣殿”,《西都西京賦》并同,《三輔黃圖》注:“枍詣”,木名,言宮中美木茂盛也,因之“詣或作栺”,《木部》所無,乃誤字,非假借也(卷五)。
按:栺非誤字,《玉篇·木部》:“栺,栺栭,木”,《廣韻·脂韻》:“栺,栺栭,栭柱”,《集韻·脂韻》:“栺,栺栭謂之柱”。后起字書均有收錄,非假借。
講,《漢書·曹參傳》:“講若畫一文”,穎曰:講或作較。《史記·世家》作“顜”,本書所無,惟有“斠”字。今以為校讎字,顜或為斠之異體。較亦與校通。《鄭語·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韋注:講,校也。是較、校、斠與講并音轉,可為通借。《索隱》又云《漢書》作講,講亦作“顜”,顜乃講之假借,疑《史記》顜字本“覯”之訛(卷五)。
按:朱氏的判定單以《說文》收字為準,認為不見于前代字書、韻書、而漢字結構又講不通的字斷定為訛字。實則“顜”在金文中《五祀衛鼎》作“”、《九年衛鼎》作“”已有收錄。《史記》正存古字,《說文》未收,并非訛誤。
根據朱氏的判定,可以判定其一個共有觀念:當某字《說文》未有收錄,則必須找尋一個《說文》已收錄的音同或音近字(多為同聲符字)為本字,排斥唐以來大量的后出字、俗體字。這也可以看作其他判定本字的一個準則。
以《說文》收字為準,是存在很大問題的。究其原因:第一,許慎收字之時未能盡備,當時已經產生且流行的相當多文字就有未收錄,代表例證就是相當多的《說文》說解用字不見正文與重文。[16]第二,《說文》在流傳過程中,已經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脫、衍、訛、倒等錯誤,而且又有人不斷篡改,清人所見《說文》版本已非許書之原貌。第三,從《說文》到清代不斷有新事物、新概念產生,后根據記錄語詞的事物屬性加示義構件,是漢字不斷類化的表現,也是漢字系統內部調整的一大規律。漢字是適應漢語語義的需要進行“改音易字”,也是漢字的特點本身決定的。第四,并非所有的新詞都有文字來記載,也未必能夠在《說文》中尋得本字。漢語當中有些外來詞、方言詞可能就沒有本字。王力先生曾說:“以為現代方言里每一個字都可以從漢以前的古書尤其是《說文》里找出來,而不知兩種情形是超出古書范圍以外的。”[17]有些詞可能有音無字,沒有記錄符號;有的來自外域傳入,難以溯源。《說文》析形說義能用來參考,但是若字字都要從《說文》當中尋得依據,找尋本字,就走得太遠,忽略了用字實際。
1.2.2以《說文》說形釋義為準,以訛傳訛。許慎在編排《說文》時為構建540部首達到“分部別居”的需要,將部分的筆畫、構件作為部首,并對其意義進行了分析,如一、丶、、丿,這些部件只是作為構字元素而存在,既無確定的讀音,也無確定的意義。而朱氏卻將其視作具有形音義的漢字,認為具有記錄語詞的特征。且《說文》未見到更早的甲骨文等字體,對文字的形體解釋存在不當或臆測之處,而朱氏皆從其說。
主,部首“丶”字云:“有所絕止,丶而識之也”。段謂“凡主人主意字,本當作丶”,今以主為丶之假借,而別造鐙炷字(卷九)。
按:“丶”當為古代讀書時一種標點符號,并不記錄語言,非字。朱駿聲即言:“今誦讀點其句讀,亦其一端也”。[18]朱氏承襲段說,認為“主”的本字為“丶”,非是。
1.2.3對《說文》新附字的處理欠妥。《說文》自東漢問世以來,流傳中屢經篡改,宋代經徐鉉、徐鍇補充校訂,對《說文》一書很大貢獻,尤其增加了很多許慎未收錄的字形。徐鉉《上校定〈說文解字〉表》曰:“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以廣籀、篆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他一共增加了402個字,后人稱為新附字。
朱氏在判定假借時涉及了很的新附字,他認為這些后出的新附字多為借字,論定只有《說文》本身收錄的字才為正字。
按:“狘”本義為“獣走貌”,《說文新附·犬部》:“獸走皃。從犬、戉聲。”《廣韻·月韻》:“狘,走皃”。可能是“”的后出字,非假借。
逍,《檀弓》“消搖于門”,注,又作“逍遙”,《辵部》“逍遙”字在新附,當即借“消搖”為之(卷二十一)。
按:《說文》:“臣鉉等案:《詩》只用‘消搖’。此二字,《字林》所加。”逍、遙乃后出字。逍遙為聯綿字,無正字,屬于一詞多形現象。
2 有違形式邏輯之處
李運富先生曾從論據、證明、結論檢驗等三方面探討了訓詁活動必須遵循形式邏輯,要求思維嚴密,論證謹慎。[19]朱珔的研究有相當多違背形式邏輯之處,從材料上講,對原材料缺乏核查,推論上觀點先行,論證中強求一律,而忽視了語言文字表達的多種可能性。
2.1囿于古書,疏于考察
朱氏研究遍引古代字書以及經傳疏文獻,但有些疏于考察而直接采用,對材料的性質特點認識不清,偶察不當之處,這對其判定假借形成了干擾。
丕,《漢書·匡衡傳》:“未丕揚先帝之盛功”。顏注:丕,大也。字或作本,是以本為丕之假借。丕,本聲之轉(卷一)。
按:朱氏按照顏師古注確定“丕”為“本”之假借。實則“本”為“”的形近訛誤字。“”作“丕”見《熹平石經》、漢《魯峻碑》,《劉熊碑》為“”、《劉衡碑》為“”。《玉篇》:“或作”,《廣韻·脂韻》:“,同丕”。均認為“”為“丕”的異體字。宋代婁機《漢隸字源》誤將“”釋為“本”字。之后宋劉球《隸韻》、清顧藹吉《隸辨》均引漢碑材料進行了辨證。其下所引《后漢書·耿秉傳》注解犯了一樣的錯誤,均是將形近訛誤字當作假借字來看待。
聿,下筆字云:“秦謂之筆”,是聿本筆之省借。《爾雅·釋器》“不律謂之筆”,則法律字亦可為聿之假借(卷五)。
按:“筆”是不律的合音,朱氏誤解了訓釋材料,將無關用字當作假借現象。
朱氏判定假借多來自古書訓釋材料,而古代訓釋材料輾轉相抄,性質又不統一,對材料分析判斷的角度也并非一樣。依從舊注而不加考察,故朱氏判定中有不少失誤之處。
2.2為求義證,另立新說
朱氏以“義”為出發點求本字思路是可取的,但是不能強求文獻義證而忽略原文的背景,甚至另造新說來屈就文意,這就走得太遠,偏離語言文字社會性的本質,而以今律古、以今釋古了。
矢,《易》虞注:“矢,古誓字”,《詩·考盤》:“永矢弗諼”,《論語》“夫子矢之”,矢皆訓誓,是矢為誓之假借。若《表記》引《詩》:“信誓旦旦”,《釋文》:“信本作矢”,此當為下“誓”字之誤,信與矢義未合也(卷十)。
按:朱氏認為《經典釋文》存在錯誤,認為“信”當為“誓”。雖然古書當中確實存在“矢”與“誓”相通的事實,但此處是將同音巧合看作假借現象。矢有陳述義,如《爾雅·釋詁上》:“矢,陳也。”又如《詩·大雅·卷阿》:“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毛傳》:“矢,陳也”,“矢言”即“陳述誓言”,文意順暢。此處朱氏忽略了異文材料存在的多樣性,認為異文即應該語義完全相同,強求一致,而另造新說。另外古音矢為書母,脂部;誓為禪母,月部。古音雖相近,但是作為通假的依據尚不足。裘錫圭先生認為朱珔此處為妄改古書,“信誓旦旦”一本作“矢言旦旦”是完全可能的,作為通假字缺乏依據,[20]誠然。
九,《論語》:“桓公九合諸侯”,說者以九數之多,參差不合,當與 《僖廿四年左傳》“故糾合宗族于成周”同,又 《莊子·天下篇》“而九雜天下之用”,注:九讀“糾”,糾合,錯雜也,是皆以九為糾之假借(卷二十八)。
按:此處朱氏承襲了朱熹的錯誤,將糾誤認為“九”的本字。實則“九”在古代文獻中常常虛指,如清汪中《述學·釋三九》即認為古人常用“九”、“三”來虛指多。楊伯峻《論語譯注》正是選擇了此解釋而排除了假借為“糾”的可能。[21]
假借研究必須“以音正字”,而非“以義正字”,如若先有義的觀念,再去確定本字,很容易產生錯誤。
2.3必尋本字,強求一律
朱氏的假借以廣博取勝,但是在很多用本字本義或者引申義完全可以解釋清楚,無須“破假借”時,朱氏往往從異文材料中另外尋一個本字。
柔,《頁部》:“脜,面和也,讀若柔”,案:《玉篇》:“脜,今為柔字,謂柔色以蕰也,是內則之”。“柔”本借“脜”,柔行而脜廢矣(卷十一)。
按,《說文》:“柔,木曲直也”,段玉裁注:“凡木曲者可直,直者可曲曰柔……柔之引申,為凡耎弱之稱”。[22]可知柔的本義為“木質軟和,可以曲直”,后引申為柔和、溫順,如《廣雅·釋詁一》:“柔,弱也”。“脜”表“面色溫和”義,后因用法較少,被“柔”代替。這屬于同詞異字現象,屬于因為詞義概括性引起的“形分異同”,陸宗達、王寧先生認為:“《說文》中有許多字義稍別而字形不同的字,從詞的角度看,便可歸納為一個廣義的詞”。[23]柔、脜當為廣義分形字,與假借無涉。
另一種情況是,根本不需要尋找本字,朱氏卻在文獻中為其尋找“本字”,顯得不倫不類。如:
按:莫字為無定代詞,本身即是假借用法,并非“嗼”字所借。
在尋找本字問題上,清代相當多學者在假借問題上都犯了類似的錯誤,“必有本字”的“本字觀”影響了他們的分析判斷,為一些表達毫無問題的字尋找本字。
3 結語
余國慶先生稱朱珔《說文假借義證》為“此書之學術價值,應可與清代《說文》四大家之‘段注’、‘義證’、‘句讀’、‘定聲’之成就并列,于‘說文學’居第五把交椅之地位。”。[24]對前人的六書研究,要在挖掘第一手材料基礎上,理性地分析其研究思路和研究結論。對傳統六書學史的總結,不僅要在學史上,在前后左右的歷史觀照中分析其研究成就,更要從學理上指出其研究失誤。[25]朱氏的研究反映“經驗訓詁學”的問題所在,有些根據只言片語的材料就直接作出結論性判斷,有些混淆了不同的語言文字概念,未能作出進一步系統化、理論化的梳理。朱氏研究對我們文字學、訓詁學走向科學化提出了要求:要嚴格遵守訓詁學原理,厘清不同的語言文字學現象;又要能夠思維嚴密,保證材料來源可靠,堅持發展的觀點,將理論的分析與實踐的操作結合,將規律的探討與文獻的例證結合。
[1]朱珔.說文假借義證[M],合肥:黃山書社,1995.
[2]劉志成.中國文字學書目考錄[M],成都:巴蜀書社,1997.343.
[3][4][13]王寧.訓詁學原理[M],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6.88,60,155.
[5][7]陸宗達,王寧.訓詁與訓詁學[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215,52.
[6][清]王筠.說文釋例[M],北京:中華書局,1985.2.
[8]姚孝遂.許慎與《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1983.86.
[9]王力.中國語言學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97.
[10][12][15][20]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版)[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175,194,185,262.
[11][14][22][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788,477,243.
[16][23]陸宗達,王寧.訓詁方法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64,52.
[17]王力.龍蟲并雕齋文集:第一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0,318.
[18]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M].北京:中華書局,1984,355.
[19]李運富.漢字漢語論稿[G].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311,323,333.
[21]楊伯峻.孟子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9,149.
[24]余國慶.《說文假借義證》詞例之分析[J].辭書研究,1998,(05):122.
[25]陳正正.漢語形聲字研究三十年[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版),2014,(1):77.
責任編輯文嶸
H022
A
1004-0544(2016)10-0080-05
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重大科技工程項目(0610-1041BJNF2328/11)。
陳正正(1990-),男,河南焦作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