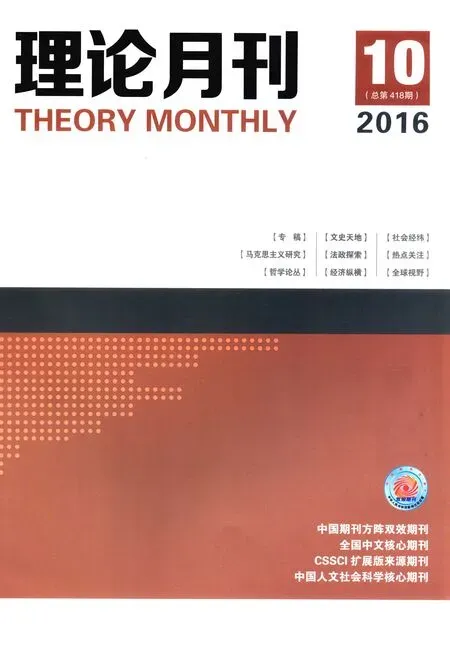上海百貨業職業工會的成立及演變
□巴 杰
(鄭州大學歷史學院,河南鄭州 450001)
上海百貨業職業工會的成立及演變
□巴杰
(鄭州大學歷史學院,河南鄭州 450001)
職業工會是抗戰勝利后上海百貨業店職員的重要組織形式。職業工會成立后,積極參與政治事件及店職員的經濟斗爭,開辦針對店職員的福利事業及職業、子弟教育,通過書報雜志傳播“進步思潮和言論”。職業工會并未將自身定位為上海全體百貨業店職員的利益代表團體,反而強調工會與店職員、會員與非會員的區別及工會獨立性。工會福利雖有成效,但“不便拒絕非會員的同事”,入會店職員因而缺乏對職業工會的內在認同。職業工會的活動呈現出與國家政權的“對立、斗爭”,這與中共的宣傳、動員密不可分,也是店職員維護職業生活正當性的外在體現,一定程度上彰顯了國共兩黨的實力消長及最終命運。
職業工會;運行狀況;利益代表;共產黨
[DOI編號]0.14180/j.cnki.1004-0544.2016.10.016
作為職業群體,近代店員經歷了會所 (手工幫)——工會 (職工會)——同業公會——職業工會的組織形式演變。目前,學界對店員工會,同業公會、會所中的店員團體,進行了一定的研究①可供學界參考的研究成果有,朱英:《國民革命時期的武漢店員工會》,《江漢論壇》2010年第2期;巴杰.《論國民革命時期的武漢店員工會》,《理論月刊》2015年第7期;馮筱才:《北伐前后的商民運動(1924—1930)》,臺灣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魏文享:《中間組織——近代工商同業公會研究(1918—1949)》,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但對抗戰勝利后上海百貨業店職員組織的職業工會知之甚少,其運行狀況、政治傾向、與國民革命時期店員工會的異同等,均缺乏認真的研究。本文擬對此略作探討。
1 職業工會的成立及其運行狀況
抗戰勝利后,店員的經濟斗爭頗為激烈:重慶等原大后方店員開展反對解雇、裁員,增加工資的斗爭;上海、北平、天津等所謂收復區店員,復工就業、按生活費指數增加工資的斗爭開展得轟轟烈烈。[1](P619)經濟斗爭的同時,店員的組織訴求漸趨強烈,以“團結同人,聯絡感情,砥礪品德,研究技術,提高知識水準,增進同人福利”為宗旨的同人聯誼會紛紛成立。截至1946年7月,上海店職員建立同人聯誼會及類似組織93個,會員86 262人。[2]
從組織章程、功能觀察,同人聯誼會已不局限于其標榜的“消遣、娛樂交誼”性質,成為以店職員為主體、帶有民主性質的準政治團體,初具工會的規模與性質:永安職工聯誼會設全體會員大會作為最高組織,全體會員均可表達意見,執行委員會(常務執行委員會)執行決策、檢查委員會監督決策執行情況;[3]先施同人聯誼會每月至少召開1次會員大會,定期會面討論切身利益事項。[4]
同人聯誼會的基礎上,百貨業店職員依照 《工會法》的規定,向上海社會局提出建立全市百貨業工會。1945年10月27日,上海百貨業工會籌備委員會成立,“永安丁盛雅、大新劉才章負責”。上海社會局以“該會內部分子復雜”為由,“在未物色干練書記前往領導時,不同意成立上海市百貨業職業工會”,[5](P94)只允許成立上海市三區百貨業職業工會。1946年3月31日,上海市三區百貨業工會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召開,通過工會章程、選舉產生理監事,陳施君擔任理事長,韓武成、丁盛雅任常務理事(不設副理事長),事實上“在全市百貨業范圍內組織工會”。[6](P98)需要指出的是,與江蘇吳縣等地 “店員不得加入工會”“百貨業職業工會停止籌備”①抗戰勝利后,吳縣各業店員要求加入、組織職工會。吳縣縣商會、華洋雜貨商業同業公會因之致電江蘇省社會處和吳縣政府,“商店店員組織工會于法無依,請加取締”“應即指示該商業工會停止籌備”。1946年9月25日,國民政府社會部發布《店員不得隸屬工人團體令》,認為商店店員系為商業從業人員,“不能視同以勞力換取工資之工人加入工會”。馬敏等編:《蘇州商會檔案叢編》第6輯1945年—1949年(上),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505—508頁。相比,上海社會局“允許成立、限制活動區域”的做法尚較溫和。
職業工會成立后,集中力量將上海各百貨公司聯誼會改組為分會或獨立支會。經過改組,職業工會下設26個分會,每個大公司均成立1個分會,規模較小的商店,幾家合起來,成立1個分會,“囊括近萬名職工店員”。[7](P55)職業工會的會務由總務股、組織股、康樂股承辦,設置調查委員會、文化委員會、福利委員會負責勞資糾紛調解、刊物出版、會員福利及娛樂等。與國民革命時期店員工會的文書、理財、宣傳、調查、交際、庶務、救濟7科相比,[8](P13)上海三區百貨業職業工會缺少專門的經濟部門。這表明職業工會的著眼點在于群眾動員、政治活動,“伙計們只有靠自己的團結”、“爭取民主”,[9](P673)經濟訴求不是其開展活動的主要考量。
職業工會的權力運作由全體代表大會、理監事聯誼會負責:代表大會有代表194人,由店職員直接選舉產生,“每20人可推一代表,不滿20人者,也可推一代表”。代表大會“每半年召開1次,討論經濟項目及有關重大問題的解決”。1946年9月19日召開的全體代表大會,各分會代表102人到會,聽取各股工作報告、通過提案22件。[9](P668)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每周舉行1次,討論會務、解決各會員的困難,及推動福利工作之進行。理事會設理事9人,其中常務理事3人,候補理事6人;監事會設監事3人,其中常務監事1人,候補監事2人。所有理、監事均不支薪金。②職業工會的每月支出,只有“2位職員薪金25萬元、伙食費14萬元”,據此可以推斷出其理、監事不支薪金。
職業工會的收入主要是入會店職員繳納的會費,薪金在10萬元以上者,每月每人繳1500元,5萬元以上者900元,5萬元以下者300元。支出方面,1/3用于福利,1/3為分會辦公費,1/3為總會辦公費。實際運作中,上海三區百貨業職業工會每月收入80萬元,支出84萬元:刊物32萬元,車馬費、文具費8萬元,向總工會繳納5萬元,2位職員薪金25萬元、伙食費14萬元。[9](P668)從收支平衡的角度觀察,上海三區百貨業職業工會屬“入不敷出”,這無疑會影響到其在店員運動中的立場及對入會店職員的利益代表程度。
2 職業工會的主要活動
上海三區百貨業職業工會成立后,積極參與政治事件以凸顯自身存在和影響力。對于戰后美國貨物的“洶涌而入”,職業工會呼吁“愛用國貨、抵制美貨”,抵制范圍限于“奢侈品,本國廠商已能生產之出品及代替品,有特殊功能或需要者外(如西藥等)”。[10]后因“特務”擾亂“愛用國貨抵制美貨委員會”成立大會,職業工會發起以國民政府為對象的抗暴斗爭。國民政府推出凍結生活費指數的舉措,職業工會以請愿游行的方式進行抗議,要求生活指數“迅予解凍”。[11]迫于壓力,國民政府宣布生活指數有條件解凍,“底薪在30元以下者,按公布的指數足額發給,30元以上至100元的,每10元為一級,逐級遞減10℅”。[12](P1683)
創辦圖書館、書報代辦組,通過“進步書報雜志”在店職員當中傳播“進步思潮和言論”是職業工會的重要活動。通過主動推薦、銷售及借閱,百貨業店職員訂閱最多的報紙為“進步的”《文匯報》、《時代日報》,占店職員訂閱量的66.9℅,《民主》、《文萃》、《群眾》等“進步”雜志的銷售數,經常在200份以上,而閱讀國民黨的《中央日報》、《東南日報》的僅占0.4℅。[5](P97)職業工會及其分會亦創辦有針對店職員的報刊雜志。③較具代表性的有:會報、加薪公報、百貨職工通訊、百職會報、福利快報、劇藝、快報、康樂特訊、百貨通訊等。見《上海工運志》編纂委員會:《上海工運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327—329頁、第339—340頁。職業工會還利用文藝晚會、邀請名人演講等方式,啟發店職員的“愛國、進步”思想。
作為職業社團,入會店職員的內在認同是職業工會存在的合法性前提,福利事業則是職業工會構建認同最直接的方式。職業工會的福利事業,一是通過工會福利股設置福利貸金組和小額貸金組:福利貸金每人每月可貸款10萬—300萬不等,免息、分期償還;小額貸款,每月2期,期限10天,會員遇有急用,即可申請。永安分會從成立到1947年秋,福利貸金組共貸給會員及其家屬39人,貸款法幣900多萬元,生育貸金18人,貸款280萬元。死亡捐助6人,捐助金額300多萬元。小額貸款舉辦26期,貸款人數2 485人次。[5](P100)二是組織消費合作社。大新分會全體職員以一個月早餐費1 200萬元成立“大新同人消費合作社”;永安分會制定《永安同人福利委員會章程》、《永安同人消費合作社章程》,確定“每股1萬元,每人至少認3股”,籌集股金6 000萬元、股東680人;新新分會消費合作社,公司同人均可認股(包括工會會員、上層職員及資方),但工會會員均得認基本股3股,每股定額1萬元,總股金3 000萬元。股權不論股份多少,每人均為1權。紅利40%分給認股者,60%分給購買者。[13](P41)體育活動、醫療服務等也是職業工會“吸引、團結”店員的福利措施:組建話劇組、京劇組、歌詠組,足球、籃球、乒乓球隊;創辦“百貨職工診療所”,免收掛號費,藥品按成本配給生病的入會店員。從工會福利基金中撥款,組織會員進行體檢等。
職業教育是職業工會的重要活動之一。作為基層職業群體,店員大多“學歷不高、知識不足”,“繼續進修”的內在訴求較為強烈,①民國時期,提升“商業智識”是報刊媒介關于店職員的重要討論話題,店員來信亦大多要求“有學習的自由”。“舉辦補習學校”“完全取得職業教育權”,因之成為店員團體的重要活動。②上海藥業伙友聯誼會、上海店員聯合會、武漢店員總工會等團體均設有負責店職員進修、學習的專門機構。店員工會主導的罷工行動亦要求“公司出資創辦補習學校,優待青年職工及學徒,免費入學”。職業工會成立后,支持各公司聯誼會創辦的“為本行業職員服務的補習學校或補習班”,并從福利金中撥款創辦百貨職工補習夜校,以滿足店職員的進修訴求。職業工會還延續店員團體子弟教育的行業傳統,“自辦三區百貨業職工子弟學校,路遠不能入子弟學校的給予助學金補助”。[13](P42)永安分會將抗戰時期開辦的永安夜小學改造為永樂職工子弟小學,“只收永安公司同人子弟,不收外人”,入學學生達245人。學校一切財務及管理皆由校董會負責,[14]“名義上雖不屬于工會領導,實際上是在工會支持下開展工作”。
3 職業工會的“整頓”
人數眾多且與社會生活息息相關的店員是國共兩黨群眾動員的重要對象,③國民革命時期,國民黨認為店員“實有參加國民革命之需要與可能”(《商民運動決議案》);中共則將“建立赤色手工業、店員工會”作為“目前必要的任務”(《第五次全國勞動大會·工會組織問題決議案》)。在店職員當中發展黨員是二者的共同訴求。截至1947年7月,上海百貨業店員有近200名中共黨員,建有百貨業黨委、店員工作委員會、第二店員工作委員會;[15](P308)國民黨黨員則有210人:國貨5人,大新24人,永安46人,新新47人,先施80人,麗華6人,中華2人。[13](P43)
職業工會成立伊始,國共爭奪即充斥其中:籌建上海百貨業工會時,永安公司推派參會的江承隆實為國民黨上海三區黨部執行委員,有中統背景;三區百貨業職業工會首屆理監事,擔任理事的永安百貨公司店員丁盛雅、楊瑞俊系中共地下黨員。《百貨職工》刊發的一篇批判文章,雖有較強的政治傾向,但大致可以反映出國共兩黨之于店員工會的“激烈”爭奪:破壞者是不會甘心的,……他們招兵買馬,調兵遣將,請吃飯,到大三元請喝茶,開房間集會;對同事戴帽子威脅,拿津貼利誘……偽稱參加他們的工會將來可做官,乘車看戲可不要錢,可做部長。[16]
富通事件④富通印刷公司印刷的《上海各職工團體為揭破“總動員令”陰謀聯合宣言》,蔣介石極為震怒,要求“嚴查”。1947年9月19日,國民黨當局全面搜查富通公司,將在場的公司職工和外來接洽業務的客戶統統扣押審查,即為富通事件。《富通印刷所多人遭搜捕》,《時代日報》1947年9月22日。后,國民黨當局以“《百貨職工》與富通有聯系”為由,分頭逮捕了上海三區百貨業職業工會的10位負責人,指定龔祥生等5人組成整理委員會,由上海市社會局六科科長方顯民為指導員,“接受”工會:本市破獲共黨機關,調查結果,百貨業工會負責人多名與共黨勾結,發動工潮,圖謀擾亂,危害治安,顛覆民國。今奉社會局訓令予以整理。凡共黨分子,限令立即自首,否則嚴懲不貸。[12](P1747)并張榜通緝職業工會的常務理事許克瑞、楊俊瑞,《百貨職工》主編樂爾登等5人。
國民黨當局對職業工會的“整頓、接受”,工會反映強烈。韓武成、劉才章、朱維仁、呂培裕、凌元繩等理監事聯名印發《告各界人士書》,韓武成以個人名義發表《告三區百貨業職工書》,抗議“迫害職工、逮捕工會領導人”,號召店職員“起來斗爭”。并發動各公司店員于1947年10月3日下午舉行聯合罷工:國貨公司罷工持續1小時即恢復營業,4名店員代表被捕;永安、大新、新新、先施、麗華等公司均因軍警監視無法實施罷工計劃。
罷工失敗后,職業工會通過“兄弟會”發動百貨業店職員開展“不合作運動”,“不參加工會,不交會費,不做任何工會工作”,[5](P142)宣傳職業工會為店職員謀福利的好處,組織被捕店員家屬向整理委員會討還親人,“每天有一批職工去催問回信,職工還集體簽名要‘整理委員會’出面保釋丁盛雅和罷工中被捕的3名職工”。[12](P1749)對抗“整頓”的同時,“兄弟會”組織募捐救濟被捕店職員家屬:永安公司店職員認捐1 700萬元,平均每人3.5萬元;國貨公司店職員認捐865萬元,平均每人3.5萬元;大新公司店職員認捐200萬元,平均每人4萬元;新新公司店職員認捐1 128萬元,平均每人6.5萬元;先施公司店職員認捐350萬元,平均每人8.5萬元。[13](P45)
與職業工會的強硬對抗相比,中共應對工會 “整頓”的方式較為務實——轉移、營救具有中共背景的店職員,①以永安公司為例,職業工會“整頓”期間,周炳坤、陶志泉、徐克瑞、楊瑞俊、曾永全、樂爾登、鄭思帆、景本年、馬德蔭等9名店員由中共安排撤離。強調斗爭的技巧性——加入“整理委員會”、逐步奪取工會領導權:要求“整理委員會”發出聘書,從上到下,從少到多,從而占領工會陣地;在積極分子與基本群眾中進行醞釀,取得群眾支持;挑選比較適宜的地下黨員打入工會領導層。[17](P60)從實踐層面觀察,中共的滲透措施頗有成效:永安干事會、民主工會,積極分子約占40%,工會小組長(部門代表),積極分子約占50%至60%,各股干事,積極分子幾乎占了100%;新新公司干事會30%的干事、各組干事會60%的干事及40℅的小組長為積極分子;大新公司干事會10%的干事、各組干事會80%的干事及20%的小組長為積極分子;“其他單位的力量,大部分還是跟我們走的”。[13](P46)國民黨政權敗退臺灣后,中共將職業工會模式推向全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店員的主要組織形式,直至1956年店員加入商業工會。
4 結語
是否強制入會是近代社會團體制度建設中的核心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出入會是否自由被作為判斷一個組織是否具有現代性的重要標志。店員組織一直有強制入會的傳統,“以某項商業為范圍,在此規定范圍內之同業,均得加入本會,以資保障,不得另組別會,破壞同業組織”。[8](P13)國民革命時期,上海店員總會以煙兌業另有組織,與“本會所屬之下本有煙兌業職員公會之籌備”相左,“忠告全埠煙兌業職員,須集中統一組織之下”。[18]
與店員工會的“強制入會”不同,職業工會吸收會員,須“由老會員一人介紹,填寫志愿書,領會章”,[9](P668)強調入會店職員對職業工會的內在認同,在此基礎上區別我群與他群的界限。可以說,職業工會并未將自身定位為上海全體百貨業店職員的利益代表團體,反而強調工會與店職員、會員與非會員的區別及工會的獨立性。
與之相應,職業工會成立后,并未開展加薪、改善待遇等店員運動的常規訴求,只是致力于勞資糾紛的“調解”,“其實所謂調解呢,是工會幫助職員說話,求寬恕、達到復職的意思”,“實在不是對付老板的,他們希望幫助老板”。[9](P669)店職員縮短工作時間的要求,職業工會認為 “很難辦理”,“實際上中國當時沒有這種問題,商店在習慣上都是從早到晚開鋪,也沒有分班的現象”。
國民革命時期,店員工會的活動多在國家政權的許可范圍之內。戰后職業工會的活動,則呈現出與國家政權的“對立、斗爭”。缺乏群體認同的職業工會,何以能動員“待遇相對較好、勞資間有濃厚鄉親互賴文化”的上海百貨業店員②上海百貨業店職員待遇相對較好,勞資間多為同鄉:1940年代,先施公司與新新公司內粵籍干部的比例高達83%、79%,勞資沖突因而相對較少。《1948年先施同人俱樂部會員名單》,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檔號:Q6—13—545;《1949年新新同人俱樂部會員名單》,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檔號:Q6—13—522。參與以國家政權為對象的罷工活動?
首先,職業工會對店職員的宣傳、動員頗見成效。職業工會的前身——同人聯誼會,即強調彰顯店員的政治訴求,“希望同人不要把‘聯誼會’只當成俱樂部,而是一種‘斗爭的武器’,用來反抗周遭環境的壓迫”。[19]職業工會成立后,“團結積極分子,展開了以反對國民黨政府為中心內容的宣傳教育活動”,凸顯國民黨政府的“反人民本質”。[5](P97)并“確實提高了店職員的政治意識”,“同人聯誼會與工會的成立,使勞資關系日趨緊張”。[20]具有政治熱情的店職員開始群體性涌現,通過娛樂活動、組織業余社團“吸引、團結”普通店職員,彰顯階級訴求的基礎上參與罷工行動。
其次,維護職業生活的正當性。作為職業群體,維持職業生活的正當性是店職員參與社會活動的首要考慮因素。國民革命時期,店員沒有選擇“代言”自己的中國共產黨,而是選擇了實力更為雄厚的中國國民黨,原因即在于共產黨激進的店員運動政策及力量較為薄弱這一表象影響到店員職場生活的正當性,店員因而產生了一定的背離情緒。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權沒能有效應對戰時國統區出現的嚴重社會危機,實為“劫收”的戰后“接收”又激發了原淪陷區民眾與政府的對立情緒。普通民眾在勝利幻象中的不幸遭遇,激發了店職員的失望、不滿情緒,“(我國政府)對于各處治安,無法處理,處處呈現軟弱無能之象”,[21]開始擔憂職業生活正當性,“商人至此,誠難乎為繼矣”。[22]國共戰爭爆發后,中共勢力的崛起使店職員有了維持職業生活正當性的別樣選擇,暢想“總統引退”后局勢即可改觀。[23]
[1]鐘明主編.中國工運大典(1840-1997)[M].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1998.
[2]毛齊華.論上海的工會組織[A].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上海工人運動史資料[Z].1953,(2).
[3]永安職工聯誼會組織圖(1945年)[Z].上海市檔案館檔案,Q225-1-1.
[4]上海先施公司同人聯誼會簡章(1945年10月訂)[Z].上海市檔案館檔案,Q6-5-1176.
[5]上海華聯商廈黨委、《上海永安公司職工運動史》編審組編.上海永安公司職工運動史[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6]中共上海市黃浦區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上海市黃浦區黨史大事記(1920.9-1998.3)[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
[7]上海市總工會編.解放戰爭時期上海工人運動史[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2.
[8]廣州市店員工會章程[A].陳友琴編.工會組織法及工商糾紛條例[Z].上海:上海民智書局,1927.
[9]上海市第三區百貨業工會[A].陳達.我國抗日戰爭時期市鎮工人生活[M].北京:中國勞動出版社,1993.
[10]為愛用國貨抵制美貨籌委會告各界人士書(油印件)[Z].上海總工會工運研究所抄件,1947-02-08.
[11]要求無條件解凍生活指數 工人代表昨赴社會局請愿[N].文匯報,1947-05-08.
[12]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上海史(1920-1949):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3]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抗日戰爭以后上海大百貨公司工人運動(草稿)[A].中國工運史料[Z]. 1960,(3).北京:工人出版社,1960.
[14]永樂小學校常務校董使用永安公司房屋校具之借據[Z].上海市檔案館檔案,Q225-2-44.
[15]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上海市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上海市組織史資料(1920.8-1987.10)[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6]保衛工會、保衛職工利益[J].百貨職工,1947,(24).
[17]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上海黨史大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18]店員總會常務委員會紀[N].申報,1926-12-29.
[19]何岳中.我對聯誼會的希望與感想[J].熱流(油印本),1946,(2).上海市檔案館檔案,Q227-1-72.
[20]連玲玲.日常生活的權力場域:以民國上海百貨公司店職員為例[J].(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7,(55).
[21]1947年 (日月不詳)郭琳爽致郭樂第1408號函[Z].上海市檔案館檔案,Q225-2-42.
[22]1948年10月28日郭琳爽致郭泉第57號函[Z].上海市檔案館檔案,Q225-2-42.
[23]1949年1月22日郭琳爽致郭泉、郭順第582號函[Z].上海市檔案館檔案,Q225-2-42.
責任編輯文嶸
D693.74
A
1004-0544(2016)10-0086-05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4FZS038);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第八批特別資助項目(2015T80775);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2014CLS020)。
巴杰(1982—),男,河南鄲城人,歷史學博士,鄭州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