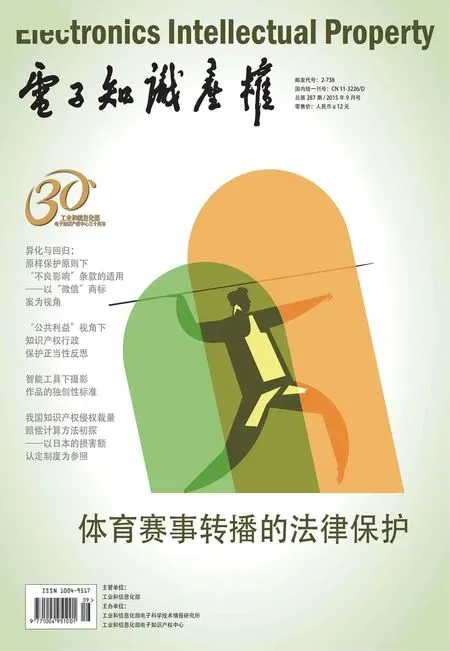商業標識共存的法律問題研究
文/戴哲 張蕓芝
商業標識共存的法律問題研究
文/戴哲 張蕓芝
近年來,商業標識共存已經成為解決我國商業標識權利沖突的有效路徑,其可分為商業標識協議共存與商業標識法定共存兩種類型。從成因上看,商業標識共存既是商業發展的結果,也是基于現有商業標識多頭立法下的無奈選擇,亦是實用主義哲學在法律上適用的結果。考慮到商業標識形態下符號表達的有限性,以及保護財產利益的客觀要求,法律應當準予商業標識間的共存,商業標識共存具有正當性。商業標識共存之認定應從四個方面入手,在不造成相關公眾混淆的情況下,法院應尊重商業標識使用所形成的市場格局,允許經過善意、規范性使用的商業標識共存。
商業標識;共存;類型;考量因素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商業標識的經濟價值逐漸為人們所認識,如在蘋果與唯冠之間的iPad商標糾紛案中,雙方以6000萬美元的和解費結案,而在“中國包裝裝潢第一案”——王老吉與加多寶關于紅罐涼茶的包裝裝潢歸屬之爭中,一審廣東高院更是判決加多寶侵權并賠償廣藥集團1.5億元。與此同時,商業標識間的權利沖突現象愈發突出。據統計,僅2000年至2007年間,上海市二中院共受理四十余件知識產權權利沖突類案件,其中90%以上涉及商業標識間的權利沖突1參見王蓮峰:《論我國商業標識立法的體系化》,載《法學》2007年第3期,第100頁。。在現有法律未作明確規定情況下,法院在“鱷魚案”、“狗不理案”等一系列商業標識權利沖突的案例判決中做出有效嘗試,基于商業標識使用的市場格局,認定了不同商業標識間的共存關系。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論述商業標識權利沖突時指出,“要妥善處理最大限度劃清商業標識之間的邊界與特殊情況下允許構成要素近似商標之間適當共存的關系”并“實現經營者之間的包容性發展”2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審判職能作用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和促進經濟自主協調發展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文化大繁榮意見》)。。由此可見,商業標識間的共存已經逐漸成為解決商業標識沖突的有效路徑。但從現有研究上看,學界對商業標識共存法律問題的研究多集中于商標共存領域,對商業標識間的共性認識不足,在這一背景下,研究商業標識共存的法律問題無疑具有重要意義,這之中亟需分析商業標識共存的成因及其正當性,并梳理出認定商業標識共存的考量因素。
二、商業標識共存之概念界定
我國現行立法尚未對商業標識作出明確定義,更未對商業標識共存現象進行解釋。但考慮到近年來商業標識領域下權利沖突現象愈發突出,“法律體系在回應公眾權利訴求的過程中,接納的權利種類亦變得更為豐富”3梁迎修:《權利沖突的司法化解》,載《法學研究》2014年第2期,第61頁。,在此背景下,2008年《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稿)首次在我國引入了商業標識的概念,其中規定,“商業標識是指在經濟活動中,能夠區分經營者和商品來源的標志,包括商標、企業名稱、字號、姓名、域名以及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等標志”4《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稿)第五條第二款。。從其字面含義上看,商業標識須能夠同時區分經營者和商品來源,這反而限縮了商業標識的內涵,無法與其保護外延對應,應將修訂稿原文中的“和”改為“或”,即商業標識是指能夠在經濟活動中區分經營者或商品來源的標志。值得一提的是,《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稿)擴充了現有《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商業標識的保護范圍,加入了商標、字號、企業簡稱、域名等標識,并對商業標識進行統一歸類保護5參見《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稿)第五條第一款對保護商業標識作出的四項規定。,這對解決當前我國商業標識類權利沖突和共存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明晰商業標識含義后,我們可以借鑒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對商標共存的定義6See IP and Business: Trademark Coexistence.http://www.wipo.int/wipo_magazine/en/2006/06/article_0007.Html.(lastvisitedOct.13,2014).,將商業標識共存定義為:不同的市場主體使用相同或近似的商業標識從事商品銷售或服務而不必然影響各自商業活動的情形。
三、商業標識共存之類型化
如前所述,商業標識子類豐富,外延廣闊,由此可見商業標識間共存形式之多樣、現象之復雜,若欲對商業標識共存現象進行全面綜合性地探析,并且不依托某種單一形式的商業標識共存決定論,就有必要對商業標識共存進行類型化分析。在商業標識共存類型的建構上,由馬克斯?韋伯提出的“理想類型”理論將可以為我們提供指引,韋伯指出,“一種理想類型是通過片面突出一個或多個觀點,通過綜合許多無聯系的、偶爾存在、偶爾又不存在的個別具體現象而形成的,這些現象又基于那些被片面強調觀點而被整理到統一的分析結構之中”7【德】馬克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楊富斌譯,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頁。。
沿著“理想類型”的路徑,我們有必要基于商業標識最本質的特征探析商業標識共存的類型。從商業標識間的共性上看,其首先是一種具有識別性的特定標記,無論是商品商標、服務商標,還是企業名稱、域名、地理標志等等,都具有標記性,這使得商業標識有別于其他智力創造所產生的知識產權客體,法律有必要對此進行專門規范8同注釋1,第103頁。。由此,商業標識成為一項獨立權利的客體,權利人有權處分其所享有的商業標識,基于該商業標識的私權屬性,不同商業標識權利人可以通過協議直接實現商業標識的共存,但協議共存并不是商業標識共存的唯一方式,在不存在共存協議的前提下,行政授權與司法審判渠道中亦能夠間接推導出商業標識間的共存關系。基于此,商業標識共存可分為協議共存與法定共存兩種類型。
(一)商業標識協議共存
商業標識協議共存是經濟發展的產物,不同的經營者為了避免商業標識侵權糾紛,同時保障其市場份額,彼此會簽署商業標識共存協議。盡管我國現有立法對商業標識共存協議未予規定,但參照國際商標協會對商標共存協議的定義9INTA Glossary, available at http://www.inta.org/info/glossary.html(lastvisitedOct.13,2014).,商業標識共存協議可被定義為:“在不引發市場混淆的前提下,一份由雙方或多方簽訂的,允許擁有類似商業標識的當事人能夠在市場上同時使用商業標識的協議”。商業標識協議共存在判例法國家早已存在,并且通過司法實踐發展出了較為完整的適用規則。美國法院在認定商業標識共存協議效力時,嚴格信守契約自由,除了共存協議損害公共利益的情形之外,美國法院以尊重當事人之間的協議自由為出發點,準予不同商業標識的共存。
從我國的司法實踐上看,商業標識協議共存已經得到認可,并且也采用了類似于美國司法實踐的裁判規則。如在“良子”商標糾紛案中,北京良子公司與山東良子公司為合法登記并核準的企業,兩者在先簽訂了一份商業標識共存協議,其中約定北京良子公司放棄對山東良子公司申請“良子”字樣的商標提出異議,之后北京良子公司違反了該約定,在山東良子公司申請商標過程中提出了異議,工商局和一審法院都主張撤銷“良子”商標,而在二審及再審程序中,北京高院和最高院都認定了該商業標識共存協議的有效性,最高院在判決中指出,“共存協議系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當事人各方應嚴格遵守”10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書(2011)知行字第50號。,最后維持了商標的注冊。再如在“STEPHENSBROTHERS”商標案中,引證商標權利人出具同意書,明確支持異議商標的注冊,一審法院北京一中院認為,“在無證據表明同意書會對消費者利益造成損害的情況下,應當尊重引證商標權人對其商標的處分”11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3)一中知行初字第2411號行政判決書。,北京高院在二審也支持了一審判決理由12參見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4)高行終字第1396號行政判決書。。在立法層面,我國也趨向于對商業標識協議共存創設空間,舉例而言,我國新《商標法》第59條為商標在先使用人創設了商標先用權,商標在先使用人可在原使用范圍內繼續使用該商標,可以預見的是,伴隨著該條款的設立,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商標在先使用人傾向于為界定在先使用范圍以及規避侵權風險而同商標權人達成共存協議。由此可見,商業標識協議共存是基于對契約自由的尊重而孕育發展的共存類型。
但需要注意的是,“作為啟蒙運動和自由主義產物的契約自由,從來就不是不受限制的”13【德】羅伯特?霍恩、海因?科茨、漢斯?G.萊塞:《德國民商法導論》,楚建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頁。,允許商業標識協議共存并不意味著經營者在處分其商業標識時具有絕對自由。如果商業標識相同或近似程度較高,并且商品種類相同或類似,容易引起市場混淆,那么,即便存在共存協議,法院也不會予以采信,商業標識協議共存將無法成立。在前述“良子”案和“STEPHENSBROTHERS”案中,法院雖都認定了共存協議的有效性,但法院也強調了消費者利益和公共利益保護,只有在共存協議未對消費者利益和公共利益造成損害的情況下,商業標識權利人方能依其意志處分商業標識。此外,作為民事合同,商業標識共存協議也受到我國傳統民法之約束,現有《民法通則》、《合同法》都將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作為認定合同無效的事由。在商業標識協議共存中,衡量公共利益受損的主要依據在于,該商業標識共存是否容易造成消費者混淆14參見石必勝:《商標共存協議只作為適用商標法第二十八條考量因素》,載《中國知識產權報》2013年8月9日第7版。。由此可見,根據意思自治原則,在未侵犯公共利益的情況下,即未造成市場混淆的情形下,法院將允許商業標識協議共存。
(二)商業標識法定共存
我國商業標識立法雖沒有明文規定,但這并不意味著商業標識的共存缺乏法律依據,依據我國現有的商業標識立法、行政法規和司法解釋,我們可以從側面推定出不同的近似商業標識間的共存關系。并且,從我國司法實踐上看,商業標識法定共存已成為我國商業標識共存的主要類型。
首先,我國法律已準予商標共存。結合我國新《商標法》第九條、第三十二條、第四十五條的規定,在先使用的未注冊商標在達到一定影響的情況下,其有權在商標注冊之日起五年內向商標評審委員會提出請求以撤銷以不正當手段搶先注冊的在后商標,此時,若在先商標使用人未在五年內提出請求,那么在先使用商標和在后注冊商標在實質上構成共存。再如我國新《商標法》第五十九條也準予了在先使用并具有一定影響的商標可與在后注冊商標共存。在司法實踐中亦已認可商標共存,如在“散利痛”與“散列通”商標糾紛案中,盡管就商標的構成要素而言,兩商標具有近似性,但最高法院在審理過程中考量了商標使用的時間與狀態,對商標背后的市場格局進行了分析,由此,針對該兩商標權人互相提出的撤銷申請,最高法院均未予以撤銷15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07)行監字第111-1號駁回再審申請通知書;最高人民法院(2009)行提字第1號行政判決書。,從側面認可了該近似商標的共存。再如“紅河”與“紅河紅”商標糾紛案,法院認為“紅河紅”商標經過長期使用,已經具有一定市場知名度,與“紅河”商標產生整體性區別,“紅河紅”商標使用行為未侵犯“紅河”商標權人的注冊商標專用權16參見最高法院(2008)民提字第52號民事判決書。。
其次,我國法律已準予企業名稱共存。我國《企業名稱登記管理規定》中指出,“企業名稱經核準登記注冊后方可使用,在規定的范圍內享有專用權”。由此可見,我國企業名稱的法定保護范圍就是禁止他人在同一層級轄區內同行業登記相同或者近似的企業名稱,不同地域范圍內允許使用相同或近似的企業名稱,這意味著我國法律準予了不同地域范圍下企業名稱的共存。
再次,我國法律已準予商標與企業名稱共存。依據最高法的司法解釋,即便企業名稱使用行為侵犯了商標權或者構成不正當競爭,企業名稱使用人仍可規范使用其企業名稱,而非絕對禁止其使用企業名稱17《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注冊商標、企業名稱與在先權利沖突的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四條中規定:“被訴企業名稱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或者構成不正當競爭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原告的訴訟請求和案件具體情況,確定被告承擔停止使用、規范使用等民事責任”。,這即意味著法律從側面準予了企業名稱與注冊商標之間的共存。在司法實踐中亦已認可商標與企業名稱共存,如在“錢柜”案中,原告錢文公司為“錢柜”商標的被許可人,被告陽光錢柜公司的企業名稱登記在后,其在字號上使用了“錢柜”二字,一審法院認為,被告企業名稱(字號)雖然登記在后,但被告廣泛持續使用其字號“陽光錢柜”,獲得較高顯著性與知名度,沒有為爭奪市場份額而搭原告便車的動機與現實需求,相關公眾能夠將涉案商標與企業名稱(字號)對應的服務區別開來,不會導致混淆,法院最終駁回了原告訴求,認定了原告的商標與被告的企業名稱共存18參見尹為、魏大海、杜健:《特殊情況下構成要素相同商業標識的善意共存——錢文公司訴陽光錢柜公司侵犯商標權糾紛案評析》,載《科技與法律》2012年第3期,第59頁。。
此外,我國法律已準予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共存。依據最高法司法解釋19《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中規定:在不同地域范圍內使用相同或者近似的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在后使用者能夠證明其善意使用的,不構成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因后來的經營活動進入相同地域范圍而使其商品來源足以產生混淆,在先使用者請求責令在后使用者附加足以區別商品來源的其他標識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知名商品特有名稱、包裝、裝潢權利具有地域性,不同地域范圍內不同的市場主體可以善意使用相同或者近似的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這意味著我國法律準予了不同地域范圍下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的共存。并且,在不造成混淆的情形下,即便同一地域范圍內相同或近似的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亦可以共存,但為了避免產生混淆,在先使用人可以請求在后使用人附加其他區別性標識。
最后,其他商業標識亦存在法定共存情形。上述列舉的幾種商業標識間的法定共存情形是商業標識法定共存的典型形態,但并未窮盡所有情形。從我國現有司法實踐上看,商業標識法定共存還包括域名共存、商標與地理標志共存、商標與商品名稱共存等。在域名共存的經典案例——“quna.com”案中,廣東高院最后支持了“qunar.com”域名與“quna.com”域名之間的共存20參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粵高法民三終字第565號民事判決書。。在“金華火腿”案中,法院亦準予了商標與地理標志的共存21參見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3)滬二中民五(知)初字第239號民事判決書。,在“狗不理”案22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三監字第10-1號民事判決書。、“諸葛釀”案23參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07)粵高法民三終字第318號民事判決書。中,法院也允許了商標與商品名稱共存。
四、商業標識共存之成因
“制度絕非憑空從某一種理論而產生,而系從現實中產生者”24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頁。。商業標識共存的產生由現實情境下的商業發展逐漸演化而來,法院在對待該商業發展時采用了實用主義哲學的觀點,基于商業發展所形成的市場格局最終準予了近似商業標識間的共存。
(一)商業標識共存是商業發展的結果
在商業發展之初期,多數商業具有地域性色彩,換言之,不同地域的商人之間往來較少,由此,不同地域的商人可能在彼此都不知情的情況下采用相同或近似的商業標識。在這些情況下,由于不同地域的消費者亦各不相同,此時,由于缺乏競爭性,即便帶有相同商業標識的產品進入市場亦不會造成消費者的誤認,因此,不同地域的商人銷售商品的行為不會產生欺詐公眾的法律問題。然而,隨著交通運輸產業的快速發展,特別是遠洋貿易的興起,商業市場逐漸由地域性轉向區域性,甚至趨向于全球性。與此相伴的是,從前采用相同或近似商業標識的商品開始進入同一市場進行銷售,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業標識的商人之間開始進行商業競爭,并可能在市場上面對潛在并相同的消費群體銷售商品,由此,消費者面臨著混淆的可能。但是,不同的商業標識人取得商業標識的手段是合法有效的,其使用商業標識亦具備一定歷史,法律沒有隨意撤銷這種權利的空間。并且,由于商業標識上承載著營業商譽的,假使營業商譽被分割,商業標識可由兩人以上的繼承人獲得。為了滿足這種情景,善意共存原則應運而生25參見劉維:《試論商標善意共存理論的適用——評鱷魚商標案與百威商標案》,載《電子知識產權》2012年第8期,第43頁。。
(二)商業標識共存是基于現有商業標識多頭立法下的無奈選擇
TRIPs協議已經明確了知識產權的私權屬性,商業標識權作為工業產權的一種,屬于知識產權權利范疇,亦具有私權屬性,但從我國商業標識立法歷史上看,商業標識立法多為行政性質的法律規定,突出強調對商業標識的管理。如我國的商標立法,“總的脈絡是私權到公權,再到‘私權+公權’,最終思路仍然是,將商標法作為公共管理的工具,然后才是對商標私權的保護”26黃暉:《馳名商標和著名商標的法律保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頁。。再如我國采用具有濃厚公法色彩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對企業名稱、字號、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進行保護。這些立法無不彰顯了公權力對商業標識立法介入,與商業標識的私權屬性不相協調。
與此同時,由于我國立法多以行政部門主導為主,我國商業標識的授權部門分屬不同的公權力部門,不同部門對不同商業標識的規定存在效力位階上的高低之分,并且,不同部門之間缺乏溝通,這使得我國商業標識立法缺乏統一性與協調性,不同的商業標識的保護范圍可能存在交叉,最后導致商業標識在交叉范圍內權利沖突,這一點在地理標志保護上尤為明顯27筆者注:在我國,地理標志既受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公布的《地理標志產品保護規定》規制,又受《商標法》規制,還受《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農產品地理標志管理辦法》的規制。。而誠如馬克思所言:“資本總是在瘋狂地追逐利潤”28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39頁。,高利潤與高效率緊密相關,商業標識的多頭立法與管理將加重市場主體的負擔與運行成本,于是,現有商業標識立法無法滿足市場效率性的要求。在這一背景下,市場從側面倒逼立法者、司法者、執法者采取有效的手段以適應市場的發展,考慮到部門利益協調的長期性與現實困境,商業標識的統一立法在短期內無法完成,由此,商業標識共存由此便成為在現有商業標識多頭立法之下較為無奈的選擇。
(三)商業標識共存是實用主義哲學在法律上適用的結果
實用主義哲學是發祥于美國的一股哲學思潮,其強調“哲學應當立足于現實生活,講究實事求是,并將獲得效果作為最高目的”29宋斌、閆星宇:《杜威實用主義哲學的現實審視》,載《求索》2013年第6期,第92-93頁。。對于商業標識立法而言,現有商業標識的多頭立法產生了商業標識間的權利沖突,在未有協調沖突的立法出現前,法院不得不對做出積極回應,并尋求法律背后最佳的市場效果。而“實用主義倡導的正是在沖突的利益格局中做出明智的抉擇”30同注釋29。,盡管從邏輯推演的角度分析,法院可以基于標識在先使用與權利登記取得為由,維護一方商業標識權人的商業標識,撤銷另一方的商業標識,但“實用主義哲學重視行動和變化,拒斥絕對論,并且,實用主義哲學提倡實事求是,與追求形式典雅、邏輯嚴密的傳統哲學相比,兩者存在很大的不同”31同注釋29。。由此,法院遵循了實用主義哲學的思維觀,基于對商業發展所形成的市場格局的考量,最終選擇了準予商業標識共存的裁量方法以平衡不同市場主體的利益沖突,否則,輕易地撤銷一方商業標識權利人的商業標識將有可能損害法律的社會效用。當然,商業標識共存并不是絕對的,除去對商業格局的尊重外,仍需考慮對消費者利益的保護,只有在不造成消費者混淆的前提下,商業標識共存方有存在之必要。
五、商業標識共存之正當性
“正當,原是道德范疇,是對人的行為所做出的價值判斷”32周世中:《論法的正當性》,載《學術論壇》2001年第4期,第132頁。。具體到商業標識共存上,正當性探討的是應當還是不應當準予商業標識共存這一命題。考慮到商業標識形態下符號表達的有限性,以及保護財產利益的客觀要求,法律應當準予商業標識間的共存。
(一)商業標識形態下的符號表達具有有限性
“人類的智力成果,在形態上表現為符號,符號是人為創設的具有指代功能的信號”33李琛:《商標權救濟與符號圈地》,載《河南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第65頁。。商業標識在形態上亦為符號,而在商業標識立法過程中,受公權力介入之影響,登記注冊制度成為商業標識獲權之主要渠道,于是,商業標識形態下的符號被市場主體通過登記注冊的手段逐漸圍欄圈地。但是商業標識形態下的符號在表達上具有有限性,“意識形態、約定俗成等因素一直扮演著對符號多樣性進行限制的角色”34陳明達:《多樣性與有限性——廣告語言符號的批判性解讀》,福建師范大學,2010年博士論文。,在語言學中,《康熙字典》雖有4.7萬字,《辭海》亦有9萬余詞,但相對于其所表達的對象相比,又少的可憐,更何況我國累計商標注冊量在2014年已達907.5萬,全國市場主體更是達到6130.22萬戶。在后市場主體在設計其商業標識符號時不可避免地攝入在先符號的元素,若簡單地運用邏輯推理,將這種元素的攝入認定為標識的近似而加以撤銷,將進一步縮減在后商業標識的符號創作空間。由此可見,圈地亦不意味著符號的絕對排他,符號中的全部元素不應由一方獨占,否則這將對在后市場進入者造成過高的進入門檻,亦對商業環境下的表達自由造成損害。此時,商業標識共存將有效平衡商業環境下的符號圈地與自由表達之間的矛盾,無疑具有正當性。
(二)保護因使用所形成的財產利益之客觀要求
從商業標識的形態上看,商業標識下的符號本身并沒有價值。法律之所以保護該符號,是因為符號背后蘊含著財產利益,即符號上承載著的市場主體的商譽,此種商譽的形成與獲取須經過市場主體使用該符號才能夠實現,由此,商業標識具有識別功能,能夠識別商品來源或經營者本身,倘若一個符號不能指明商品來源或經營者出處,那么,該符號將無法成為商業標識。依據洛克的勞動財產理論,“在人類的原始狀態,一切資源都為全人類所共有,單個人使某個任何東西脫離全人類所共有的東西,他就已經摻進他的勞動,在這上面摻進他自己所有的某些東西,因而使它成為他的財產”35【英】洛克:《政府論》(下),葉啟芳、瞿菊農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9頁。。市場主體在經營活動中對其商業標識進行投資并摻進勞動,使該商業標識具有了識別商品來源或經營者的功能,脫離了符號原有的自然狀態,并且,市場消費者通過購買帶有商業標識的產品,對該商業標識產生認可,于是,商業標識上逐漸形成并積攢商譽,其符號背后蘊含著的財產利益亦由此產生。基于此,商業標識轉化為標識使用人的財產,無疑應當受到法律的保護。
六、認定商業標識共存之考量因素
商業標識共存之認定應從四個方面入手,在不造成相關公眾混淆的情況下,法院應尊重商業標識使用所形成的市場格局,允許經過善意、規范性使用的商業標識共存。
(一)認定商業標識共存應當尊重商業標識使用所形成的市場格局
商業標識共存體現了法律對商業標識使用所形成的市場格局的尊重,否則,倘若法院嚴格依照法律邏輯,直接判定一方當事人撤銷商業標識,那么,這將使商業標識使用人在長期經營活動中取得的成果付之東流。正如孔祥俊庭長所言,“不能人為地以商業標識構成元素的近似性而無視市場格局,去撤銷一個注冊商標”36孔祥俊:《商標法適用的基本問題》,中國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124頁。。在《文化大繁榮意見》中,最高人民法院在論述商業標識共存時指出,“要妥善處理最大限度劃清商業標識之間的邊界與特殊情況下允許構成要素近似商標之間適當共存的關系”,“注意尊重已經客觀形成的市場格局”,“實現經營者之間的包容性發展”。在司法實踐中,如在“錢柜”案、“金華火腿”案和“狗不理”案等案件中,法院亦基于商業標識使用后形成的市場格局,認定了不同商業標識間的共存。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只要有使用歷史的商業標識都應準予共存,“實現經營者的包容性增長,應當限于極其特殊的例外情況,通常屬于因復雜歷史因素而導致的共存,或者其他客觀因素致使的善意共存”37《準確把握當前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政策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available at http://www.court.gov.cn/zscq/sfzc/201304/t20130426_183682.html (last visited June.16, 2015)。。
(二)共存的商業標識使用人對標識的使用應為善意使用
法諺有云:任何人不得從錯誤行為中獲利。主觀上具有惡意的商業標識使用行為,法律不應予以保護。在《文化大繁榮意見》中,最高人民法院也指出,應將使用者的主觀狀態作為認定商業標識邊界與共存的考量因素之一。在司法實踐中,法院也做了同樣的分析,如在“錢柜”案中,法院考量了商業標識使用者的主觀狀態,認為被告沒有為爭奪市場份額而搭原告便車的動機與現實需求,即主觀上不存在惡意,最后認定被告不侵權38同注釋18。,從側面準予了原被告商業標識間的共存。在“狗不理”案中,二審法院亦將被告主觀上的善意使用作為認定原告商標與被告商品名稱之間共存的因素之一39參見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07)魯民三終字第70號民事判決書。。與之相對的是,在“特侖蘇”案中,被告以合理使用其企業名稱為由進行抗辯,但法院認為被告主觀上存在明顯惡意,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違背了公認的商業道德,依法應當承擔停止使用、變更企業名稱的民事責任40參見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13)三中民初字第00001號民事判決書。。由此可見,當一方商業標識使用人的主觀狀態為惡意時,法院將不予支持不同商業標識間的共存,只有當商業標識使用人善意使用標識時,法院方有可能認定商業標識共存。
(三)共存的商業標識使用人對標識的使用應為規范使用
商業標識使用人應當嚴格規范其標識使用行為,在核定的使用范圍內使用標識,倘若商業標識使用人用簡化、拆分等方式不規范使用商業標識,造成公眾混淆,法院將仍認定其構成侵權,而不予共存。如在“特侖蘇”案中,法院認為,企業在對外經營活動中應當依法規范使用企業名稱,企業在其產品或者包裝上使用的企業名稱應當同企業營業執照上的企業名稱保持一致,企業對字號的使用不得與他人的注冊商標相混淆,而該案中,被告將與原告商標相同的文字作為企業字號在其生產的相同商品上突出使用,并未規范使用企業名稱,因此,法院認為,該使用突出使用行為容易引發混淆,侵犯了原告的商標權41參見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13)三中民初字第00001號民事判決書。。同時,需要注意的是,規范性使用要求一方商業標識使用人對商業標識的使用應在原使用范圍內進行,不得進行擴張性使用。如新《商標法》第五十九條第三款規定了在先商標使用人的商標先用權,即商標在先使用人可在原使用范圍內繼續使用該商標,再如“狗不理”案中,一、二審法院和最高院都認定了原告商標與被告商品名稱之間的共存關系,被告可以保留涉案菜品名稱,但禁止其作其他擴張性使用42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三監字第10-1號民事判決書。。此外,規范性使用還可要求一方商業標識使用人附加區別性標識,如依據新《商標法》第五十九條第三款,商標權人可以要求在先商標使用人附加適當區別標識,再如“quna.com”案中,法院雖支持了“qunar.com”域名與“quna.com”域名之間的共存,但也指出,被告有義務在與域名相關的搜索鏈接及網站上加注區別性標識,以使消費者將上述域名與原告所使用的標識相區分43參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粵高法民三終字第565號民事判決書。。
(四)商業標識共存不得導致相關公眾混淆
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稿)對商業標識的定義,商業標識在經濟活動中,能夠區分經營者和商品來源,此即商業標識具有識別功能,這也是商業標識最基本的功能,而一旦發生相關公眾混淆,則意味著商業標識識別功能發生了減損,這將使得商業標識逐漸進入公共領域,只有商業標識保有其識別功能,商業標識才具有存在之可能,共存理論方有適用之余地。因此,商業標識共存以不存在混淆為前提,在司法實踐中,法院亦對此作出了相同的考量。如“錢柜”案中,一審法院最終認定了商標與企業名稱之間的善意共存,其指出,“衡量能否善意共存取決于現實共存是否會導致相關公眾的混淆或混淆可能性”44尹為,魏大海,杜健:《特殊情況下構成要素相同商業標識的善意共存——錢文公司訴陽光錢柜公司侵犯商標權糾紛案評析》,《科技與法律》,2012年第3期,第59頁。。在“特侖蘇”案中,法院也指出,“企業對字號的使用不得與他人的注冊商標相混淆”45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13)三中民初字第00001號民事判決書。。但是,商業標識“在使用過程中不免會產生混淆,雙方對此均有容忍的義務”46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粵高法民三終字第565號民事判決書。,“將是否足以產生市場混淆作為認定商標近似的重要考量因素,主要是要求相關標識具有不產生市場混淆的較大可能性,并不要求達到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均絕對不會誤認的程度”47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三終字第3號民事判決書。。
結語
此次《反不正當競爭法》(修改稿)對商業標識的保護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規定,不僅對商業標識進行了定義,還擴充了現有《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商業標識的保護范圍,加入了商標、字號、企業簡稱、域名等標識,并對商業標識進行統一歸類保護。考慮到商業標識形態下符號表達的有限性,以及保護財產利益的客觀要求,法律應當準予商業標識間的共存,商業標識共存具有正當性。但限于現有商業標識立法上的多頭性,商業標識權利沖突一時難以避免,商業標識共存將繼續在司法上發揮作用。本文呼吁,立法者應當趁《反不正當競爭法》修改之際,在其中加入商業標識共存條款,使認定商業標識共存的考量因素上升為成文規則。這將有助于司法裁量標準之統一,更有利于調和現有商業標識的權利沖突,以創造一套更加科學、系統的商業標識保護體系。
Research on Legal Issues of Commercial Signs Coexistence
In recent years, commercial signs coexistence has become one of the eff ective path to solve the confl icts among China's commercial signs rights.It can be divided into agreement coexistence of commercial signs and legal coexistence of commercial signs.Look from the origin, commercial signs coexistence is the result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is also a helpless choice that based on the existing legislation of commercial signs, also is the result of the pragmatism philosophy in applying law.Considering the limit of symbolic expression in commercial signs and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for protecting the property interests, commercial signs coexistence has legitimacy.Commercial signs coexistence should be identifi ed from four aspects, in the case of no relevant public confusion, the court should respect commercial market pattern formed by the use of commercial signs, and allow commercial signs which is used normatively and in goodwill coexist.
Commercial signs; Coexistence; Type; Consideration factor
戴哲,華東政法大學法學博士,法國埃克斯-馬賽大學法學博士研究生。
張蕓芝,法國埃克斯-馬賽大學法律與經濟專業碩士研究生。
本文為2013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信息服務與信息交易法律制度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華東政法大學研究生創新項目“現代知識產權權利保障的利益融合與矛盾沖突”階段成果,項目編號:HDZF-2014-2-4126;華東政法大學優秀學位論文培育項目“追續權制度的創設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HDZF2016-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