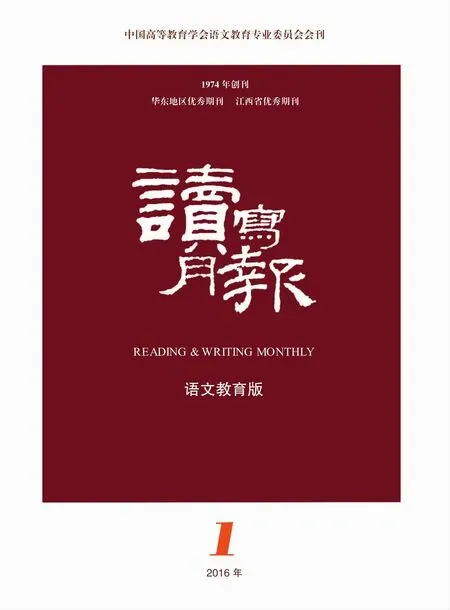互文性文本解讀和互文本類型
張斗和
互文性文本解讀和互文本類型
張斗和
文本解讀必須進入文本的內部,傾聽文本語言非常細微的聲響。由是,互文性文本解讀就成為一種必要。常見的幾種互文性文本類型分別是:同類文本、刪節文本、原型文本和闡釋文本。研究者需要對之進行創造性解讀。互文性理論,使一線語文教師的文本解讀有了新的解讀視角和更多的支撐與依傍,也為一線語文教師多元解讀文本指明了新的方向與思路。
互文性;文本;解讀;互文本類型
文本解讀肯定要進入文本的內部,傾聽文本語言非常細微的聲響。但是,由于文本的意蘊隱藏得很深,有時僅從“這一篇”中無法發掘更加豐富、更有價值的意義,這時就需要我們放開視野,本著基于文本、超越文本而又不偏離文本的原則,嘗試在“這一篇”的基礎上進行橫向延伸與縱向拓展,這樣的解讀方式我們稱之為互文性文本解讀。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又譯為“文本間性”或“文本互涉”,最早由法國符號學家克里斯蒂娃于1966年在《巴赫金,詞語、對話和小說》一文中提出。她認為:“任何文本的構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對另一個文本的吸收和轉換,互文性概念占據了互主體性概念的位置。”[1]也就是說,任何一個文本都不是封閉的、與外界絕緣的話語系統,而是與其他文本相互參照、彼此牽連,存在著這樣或那樣聯系的開放網絡。
文本總是相互指涉的,每一個文本都只有在別的文本的相互關聯和比較中顯示自己的意義和價值。互文性理論在強調文本開放性的同時,卻忽視了文本相對獨立的事實。因此,在進行互文性文本解讀時,我們把被解讀的文本視之為“主文本”,而把與之相互參照、彼此牽連的文本稱之為“互文本”,互文性文本解讀要立足于“主文本”,根據需要適時、適度地引進“互文本”,從而更準確、更科學地解讀“這一篇”,獲取更豐富的文本意蘊。
那么,到底有哪些“文本”與主文本構成互文本?一般而言,這里的互文本可以是其他前人的文學作品,也可以是主文本作者的其他文學作品,還可以是其他文學遺產,甚至是具有文化意義的社會歷史文本。[2]這樣看來,構成互文本的“文本”的范圍很大,下面從中學文本解讀的實際要求出發,將其范圍適當縮小,梳理出互文本幾種常見的類型。
一、同類文本
互文本來自同類文本的最多。此處的同類,既指情節、結構等形式方面的同類,也包括主題、語言風格等內容的同類。同類文本互文性是指需要我們解讀的主文本和互文本在某一方面存在相似或同一的關系,為了更深入準確地把握主文本主題和其審美特性,我們就需要借助互文本來和主文本進行比對、參照,從中發現差異性,捕捉文本意義生長點,挖掘文本深層意義。
孫紹振教授說過:“分析的對象是差異或者矛盾,而藝術形象是天衣無縫的、水乳交融的。要進入分析,就要把未經作家主體同化(創作)的原生的形態想象出來,‘還原’出來,有了藝術形象和原始形態之間的差異,才有了分析的切入口。”其實,提供比較的不只是需要想象出來、“還原”出來的原生的形態,同類文本也能與主文本提供比較的參照,讓文本解讀更加通暢而到位。
這里,以孫紹振教授解讀毛澤東的《沁園春·雪》為例,他是這樣進行解讀的:
在《卜算子·詠梅》中,我們看到毛澤東的詩學中有一種追求嚴酷美感的傾向。在《沁園春·雪》中,似乎也有類似的風格。至少在把大地寫得“千里冰封”這一點上和《卜算子·詠梅》的“懸崖百丈冰”,也是相通的。但是,這只是表面的相似,實質上有根本的不同。
首先,《沁園春·雪》中的“雪”和《卜算子·詠梅》中的“冰”,在意象的情感價值上是不一樣的。《卜算子·詠梅》中的“冰”,是一種逆境嚴酷環境的象征,與花枝的俏麗是對立的,而爛漫山花的想象,是戰勝了嚴酷冰雪的預期。《沁園春·雪》中的“雪”是不是這樣的呢?從最初幾行詩句來看,好像格調相近:“千里冰封,萬里雪飄”,其中的“封”字,至少給人某種貶義,但是,下面“萬里雪飄”的“飄”字,則似乎并沒有在貶義上延伸下去。“望長城內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貶義顯然在淡化,壯美的感覺油然而生。
這是很奇特。嚴酷的冰封作為一種逆境的意象,與對嚴寒抗爭的情致聯系在一起,早在唐詩中就有了杰出的經典,比如岑參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邊塞詩人把嚴酷的自然條件當作一種美好情感的寄托,詩人感情豪邁,變酷寒為美。“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冰雪畢竟是與苦、寒聯系在一起的。可是在毛澤東的《沁園春·雪》里,冰雪卻沒有寒的感覺,也沒有苦的感覺。冰封和雪飄,本身就是美的。
面對千里冰封、萬里雪飄,卻沒有苦寒,沒有嚴酷的感覺,這才是理解這首詞的關鍵。不僅沒有苦寒、嚴酷之感,相反,眼界為之一開,心境為之一振,充滿了歡悅、豪邁的感覺。在冰雪的意象中把寒冷的感覺淡化,把精神振奮的感覺強化,創造出一種壯美的境界,發出贊美,這是一種頌歌。在頌歌中,有一種壓抑不住的鼓舞和沖動。這在中國詩歌史上,乃至世界革命文學史上,都可能是空前的。[3]
孫紹振教授的解讀,巧妙借用同類文本:既有作者的《卜算子·詠梅》,又有岑參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這樣進行互文性解讀,就能夠準確把握住毛澤東《沁園春·雪》所表現的追求嚴酷美感的獨特美學意蘊。
二、刪節文本
編者根據教學的需要,常常對選入教材的文本進行“二次創作”,因此編入教材的文本和作者文本常常有出入,有的“動手術”不多,影響不大,但如果刪去的是一些關鍵部分,對文本的解讀可能就會帶來誤讀的結果。這時,就需要把刪節文本作為解讀主文本的互文本。
例如,法國著名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說名篇《我的叔叔于勒》,在選作課本時,就刪去了開頭和結尾兩個部分。
開頭部分是:“一個白胡子窮老頭向我們乞討小錢,我的同伴約瑟夫·達佛朗司竟給了他5法郎的一個銀幣。我覺得很奇怪,他于是對我說:這個窮漢使我回想起一樁故事,這故事我一直記著不忘的,我這就講給您聽。事情是這樣的。”
結尾部分是:“此后我再也沒有見過我父親的弟弟。以后您還會看見我有時候要拿一個5法郎的銀幣給要飯的,其緣故就在此。”
如果對這個文本進行互文性解讀,再結合小說中約瑟夫給于勒十個銅子的小費,心中的默念等細節描寫,就可以概括出“同情說”的主旨:小說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下層人物——于勒被整個社會遺棄的悲慘命運的描述,寄予了作者最深切的同情和憐憫。
而這樣的互文性解讀,可能比“金錢關系說”更接近作者文本的本義。莫泊桑的老師福樓拜曾說過:“所有杰作的秘訣全在這一點:主旨同作者性情的符合。”莫泊桑有過十年小職員的生活經歷,對小資產階級的痛苦遭遇感受頗深,因而在代表其創作主要成就的短篇小說中,絕大多數是寫當時法國社會中的底層人物,對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下層人物的深切同情,構成了他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基本傾向。
不僅如此,還有許多文本就是節選部分。這時,原來的“部分”成了主文本,而原來的“主體”反而構成了互文本。
例如,解讀沈從文的《云南的歌會》,一般會側重于云南歌會三種不同場景的民歌對唱,從文字出發,細讀文本,能夠感受到趣味盎然、生動豐富的云南民風民俗,從中得到美的享受。
其實,《云南的歌會》題目乃編者所命,它只是一篇節錄文章,出自沈從文散文集《新景與舊誼》,該集收錄了沈從文1956至1981年間所寫的回憶性散文13篇。《云南的歌會》節選自《過節與觀燈》,該篇分三個部分,分別是《端午給我的特別印象》、《記憶中的云南跑馬節》、《燈節的燈》。 《云南的歌會》又是《記憶中的云南跑馬節》中的一段,對歌是跑馬節中重要的精彩活動之一。按照王榮生教授的理解,《云南的歌會》一文應在沈從文于1963年回憶云南過節的文本體式上展開。因此,歌會熱烈的場面固然重要,但云南人過特具地方性的跑馬節時聚會、跑馬、對歌等重要活動更應該重視。聚會很熱鬧,跑馬賽馬是其重頭戲運動,但沈從文卻對其并不感興趣,反倒對歌會的對歌情有獨鐘。原因就在于歌會的對歌,唱出了人們對生命的頌歌,這種激情表演,成為跑馬節上最精彩的活動。再聯系作者創作的時代背景,當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之年,人的生命在天災人禍面前脆弱不堪。因此,沈從文選取跑馬節上獨具意味的歌會對歌作為重點,言此意彼,寓含生命的哲學,“生命的頌歌”真正揭示了節選部分文字(也就是《云南的歌會》)的主旨。
三、原型文本
不少文本雖然在表達、結構等方面存在不同,但卻有著共同的原型,從而構成原型互文性,它一般存在于敘事性文本當中。一方面,由于原型本身的限制,而使在此基礎上創作的文本解讀的空間相對穩定;另一方面,由于作者主觀取向的不同而使文本呈現不同的面目和版本,從而使其豐富多彩而寓意十足。
例如,蒲松齡的《范進中舉》中最核心、最吸引人的情節是胡屠戶打一巴掌治范進的瘋病。其實,這個故事并不是蒲松齡的首創。清人劉獻廷在《廣陽雜記》中載有這樣一個故事:
子孺言:“明末高郵有袁體庵者,神醫也。有舉子舉于鄉,喜極發狂,笑不止。求體庵診之。驚曰:‘疾不可為矣!不以旬數矣!子宜亟歸,遲恐不及也。若道過鎮江,必更求何氏診之。遂以一書寄何。其人至鎮江而疾已愈,以書致何。何以書示其人。曰:某公喜極而狂。喜則心竅開張而不可復合,非藥石之所能治也。故動以危苦之心,懼之以死,令其憂愁抑郁,則心竅閉。至鎮江當已愈矣。’其人見之,北面再拜而去。”吁!亦神矣。
科舉時代這類事到了吳敬梓那里,它卻像一塊強磁石落進記憶的倉庫,把平素積貯的對于科場士人的種種觀察和感受吸附到周圍,迅速排列組合形成一個完整的藝術結晶體——范進中舉發瘋的故事。
原來,范進中舉喜極而瘋的事脫胎于這個故事。如果對二者進行互文性解讀,就會發現科舉時代因中舉而發瘋的事情絕非僅有,而是時有發生,并在儒林中作為趣聞到處流傳,此其一;其二,原型文本表達的重點是突出袁體庵醫術之神,而到了吳敬梓這里,“瘋病”相同,但治病的方法卻變成了“狠狠打他一個嘴巴”。蒲松齡對封建科舉制度有深刻的體驗和認識,情郁于中自然發之于外。于是,他在原型文本基礎上,巧妙改編,借這個看似荒誕的療法來表達自己強烈的情感傾向,那就是對戕害人、異化人的科舉制度深惡痛絕。
四、闡釋文本
文本解讀就是分析,而分析就是揭示問題和矛盾。不少文本的問題和矛盾需要尋找相關文本來作合理闡釋,這時,闡釋文本就構成了互文本。
例如,閱讀傳統名篇《愚公移山》,文本中有這樣一個為許多人所忽視、也令人費解的細節:“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為什么操蛇之神“懼其不已”,而帝則“感其誠”呢?也就是說,同樣是神,在對愚公的態度上為何呈現出如此大的差異?
對此,東晉玄學家張湛這樣注釋:“《山海經》云:‘山海神皆執蛇’”,“必其不已則山會平矣。世咸知積少可以高大,而不悟損多可以至少。夫九層起于累土,高岸遂為幽谷。茍功無廢舍,不期朝夕,則無微而不積,無大而不虧矣。今砥礪之,與刀劍相磨不已,則知其將盡二物。如此,則丘壑消盈,無所致疑。若以大小遲速為惑者,未能推類也”。[4]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操蛇之神就是山海之神,他們“懼其不已”,就是怕愚公如此堅持下去會改變原有的山海形貌,無山,山神居何處?無海,海神司何海?因此,帝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如此一來,單就文本本身所傳達的信息看,過去只強調“愚公精神”的觀點是一種不全面的理解,忽視了文本隱含著的多重信息、意義的表達。而通過張湛將“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的互文性解讀,還讀出了這則寓言蘊含保護自身居住環境生態的意義。
利用互文性文本解讀,得出的意義我們稱之為文本的“互文性意義”,互文性意義并不完全就是文本本身的意義,從這個層面上講,互文性文本解讀利用構成文本與文本之間的差異關系,符號與符號之間的差異性,造成了文本的意義延宕,消解了文本的意義中心,讓文本充滿了復義。[5]因此,互文性理論,使我們的文本解讀有了新的解讀視角和更多的支撐與依傍,也為我們多元解讀文本指明了新的方向與思路。
注釋:
[1]秦海鷹:《互文性理論的緣起與流變》,《外國文學評論》,2004年第3期,第19頁。
[2]莊照崗:《互文性文本解讀的切入點》,《教學與管理(中學版)》,2011年第1期,第2頁。
[3]錢理群、孫紹振、王富仁:《解讀語文》,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88頁。
[4]張湛:《列子注·湯問第五》,中華書局,1954年,第55-56頁。
[5]蔣濟永:《文本解讀與意義生成》,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72頁。
(作者單位:安徽省懷寧縣教育局教研室)
責任編輯:周建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