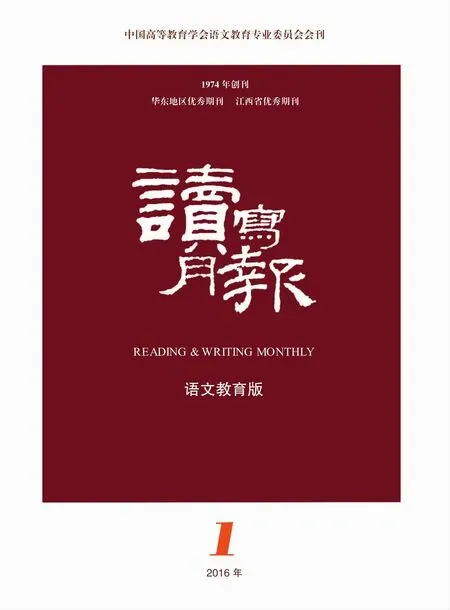教育異化的摯誠書寫及其批判
——論俞莉的中篇小說《潮濕的春天》
楊舒晴
教育異化的摯誠書寫及其批判
——論俞莉的中篇小說《潮濕的春天》
楊舒晴
當下應試教育的“流水線產業”滋生出的一系列問題,直接影響到教育個體、教育事業乃至整個國家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對其進行合理的審視、分析和應對迫在眉睫。俞莉的中篇小說《潮濕的春天》通過書寫劉詩詩、馮屏貞等人的個體經歷,映射出當下教育中存在的異化現象及部分教師庸碌的教學面貌,從而表達對教育生機的欲求,并就教育的發展發出“尊重生命”的吁請。這是作者基于自身的生命體驗對教育問題作出的批判性認識與積極回應,也是個體對社會良知的有力擔待。
《潮濕的春天》;教育小說;應試教育;教育異化;教育批判
中篇小說《潮濕的春天》中,主人公劉詩詩與一些已出現在我們視野中的成績優異的孩子一樣“突然”脫離了原有的學習和發展軌道,并在后來被送往精神疾病防治中心。但當我們試圖追問這樣一種現象的時候,會發現這其實是“流水線”教育“產業”上出現的一種“必然”。作為教師的俞莉,尊重且熱愛著自己的崗位,她同時正是當下許多教育奉獻者的見證人;但另一方面,作為作家的俞莉,又以敏銳的感知清楚意識到這之間的傷害、壓抑與痛楚,并無法做到坐視不管,她尊重每個生命個體,正如尊重生命本身。也許,正是基于這一雙重身份體驗間的張力,她秉懷著摯誠進行書寫與呈現,并將這一中篇小說命名為 “潮濕的春天”——一種漉濕、凝重但生長欲求遍布的所在。
《潮濕的春天》原載于2015年第5期《清明》雜志,隨后被《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2015年第6期轉載。我們注意到,《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在2015年度將較多篇幅投向了當下的教育小說。教育是當前一個顯豁而急迫的問題,雖然其在一定程度上由國家整體考量與主導,但也需要教育者與被教育者對此抱以應有的關注,同時更應該有包括小說家、批評家在內的社會個體以批判的立場介入對其的思考。
一、“流水線”教育異化的當下呈現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站在勞動、生產實踐這一歷史和現實的基點上,對異化勞動和人的異化進行了深入探討。他指出:異化是指主體在一定的發展階段,由于自己的活動而產生出自己的對立面,而這個對立面又變成外在的、異己的力量,并轉過來反對主體本身,即人被自己的創造物所支配和奴役。我們可以分析到,這之中有兩個層次的蘊涵:其一,事物在發展過程中違背了其價值預設中的本真意義;其二,這種自身活動及其產物成為統治、支配、奴役自身的異己力量的變化過程是在不自由的狀態中發生的。正如我們前述所提及的“價值預設”,即存在一個人們對該事物“應然”面貌的預設。馬克思這一關于人的本質的異化理論,其實就是首先認為人應該是完整的、全面發展的。“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1]我們對于教育問題的認識,顯然也需要我們對“人”及“人的發展”問題有這一根本性的理解。同時,我們需要合理認識到的是,作為“異化”下屬概念的“教育異化”一定程度上也正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并且,我們可以具體地回顧到,誕生于工業革命之后的現代教育,其重視的是如何在一定的時間內訓練大量的專業人才,本質是一種培養工匠的教育,教育在此已萎縮為職業的附庸。因此,大學以前的教育環境,習慣強調所有事物都有標準答案,而考試的目的通常就是寫出標準答案。那么,“現代教育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應試教育”[2]這一觀點就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重視了。在前述的一個價值預設的認同基礎上,我們則可以說現代教育的此般面貌也就正是其中一種“教育異化”的表現。事實上,正如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在2015年3月所指出的:學生成為流水線上的標準化“產品”,這個問題早已不再新鮮。然而,當下社會生活中的個體是否對這一雖不新鮮卻依舊緊迫的問題有正視、持續關注乃至尋求改變的勇氣,卻是值得關注和探討的。在中篇小說《潮濕的春天》的創作談《教育之殤》中,作家俞莉寫道:“功利化的教育模式下,我們失去了本真。教育已變成了和生產工業產品一樣的流水線。每個活生生的孩子,他們必須要適應這條流水線。這種‘流水線’異化了人,也異化了教育。”[3]這表達著俞莉本人對教育生態的一個基本判斷,也正是俞莉筆下的受教育者劉詩詩在教育體系中的現實處境。我們需要指出,這一認識是準確而到位的。并且,通過俞莉的書寫,我們可以看到“流水線”教育異化在鮮活的當下所呈現的一些面貌。
俞莉將筆觸聚焦于高二年級中 “最拔尖”的班級——火箭班。“火箭班是動態的,實行末位淘汰制,每次大考之后,成績落在后面的同學就要進到下一階梯‘實驗班’,若實驗班還不行,再下到普通班。相反,考得好的也可成功晉級。”[4]可以看到,在這個班級,衡量學生是否有資格存在的唯一標準即是“考試成績”,也即班主任馮老師所說的 “一切按分數來”,所謂的“拔尖”實際上即與“分數高”劃等號。并且,在這里一切也都“圍著”分數轉,為此,學校規定學生不允許帶手機、各個年級的領導也都想盡辦法能讓學生在周末到學校“補課”,以集中管理而提高效率和成績。正如有論者所指出的,“追求學業的成功本來并不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但教育把這種生活價值制度化之后,學業的成功就成為一種權威性的生活原則,它借助于制度化的力量統治著每一個人的生活選擇。”[5]在這種單一的權威性的評判標準之下,尤其是在火箭班,“你見不到交頭接耳,見不到躲在抽屜里偷偷讀小說、玩手機的現象,也不會有不學習,眼睛癡傻地盯著窗外的景象。”甚至作為唯一的與劉詩詩有相同氣息的曾逸凡也已經下意識地以“分數高”作為評判“好學生”的單一標準。“曾逸凡輕蔑地‘噓’了一聲,誰以為你是好學生?自我感覺良好吧?成績在班上倒數,上學期期末考跌出前四十。”對學生的評判以分數論,學校對教師的考核標準也無不同,“能冒出一個全市前列,木棉中學大大紅了一把,馮老師因而也榮獲當年的高考先進個人。”可以說,教師“名”、“利”的獲得,與其“業績”即學生分數直接掛鉤,也就是說教育評價已經是“定量化”的。那么,不僅學生處于一種“不自由的狀態”,教師也在一定程度上被鉗制與支配。而有些反轉意味之處又在于,當教師認同并順應于這樣一種評價機制之時,其自身的方向性努力又會進一步將學生規導于這種被異化、被統治的狀態之中。由是,我們可以認同這一觀點,“現代教育陷入了功利主義,這是可悲的事情。這種風氣帶來了兩個弊端,一個是學問成了政治和經濟的工具,失掉了本來應有的主動性,因而也失去了尊嚴性。另一個是以為惟有實利的知識和技術才有價值,所以做這種學問的人都成了知識和技術的奴隸。因此產生的結果是人類尊嚴的喪失。”[6]
并且,正如拉普曾向我們昭示的:“當人們宣布現代技術的積極成就時,就必定會失去一種易于理解的、具有直接意義的生活方式。由技術所引起的異化,就是為肉體上的舒適和增強利用物質世界的能力必須付出的代價。為了能夠實際利用機械過程所增加的效率,人們必須屈從于它們的內在邏輯。”[7]當下,技術已越來越廣泛而深入地滲透進我們的日常生活,甚至已然成為一種我們并不會醒覺的生活方式而存在。在小說中,我們注意到為利于班級的管理工作,馮老師“辦公室前方有個黑色監控頭,一打開,就可以看見她的班級。這是上學期末才裝的,學校采買了一批新的監控頭,多出的就給領導和名師辦公室裝上了。”并且,這位木棉中學的“老”教師,也需要“進到校門,在門口的手模儀上,按一下手印,這是木棉中學的考勤方式。”顯然,深圳這個以現代工業文明著稱的城市,把工廠管理模式也運用到學校了。事實上,我們也可以注意到,攝像頭與手模儀,在中國當下的學校尤其是城市學校的管理中,已經較為普遍地存在著。而就異化作為一種體驗方式來說,個人事實上會感覺到一種顯明的“疏離感”。當知曉小工正在辦公室安裝“監控頭”的時候,劉詩詩愣了,接著“身體好像被誰猛推了一下,朝后仰了仰,眼神復雜。”
二、“共犯”——一種庸碌的教師面貌存在
教育是多維度的,而“生命”無疑是其中最為核心的一維。“教育是一種幫助人們尋求生命的答案,最終導向人的靈魂覺醒的活動。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教育當本著生命的原則,盡可能多地關注人本身,在促進生命與生活發展的基礎上完成人自身的進化的升華。一句話,教育的目的在于掃清人自由發展的所有障礙,盡可能多地提供給人以各種可能,從而促進人的真正全面發展。”[8]作家俞莉也認識到:“教育的本質應該是促進生命個體的健康成長,是喚醒人的內在生命意識,‘教育即生長’,生長就是目的,在生長之外別無目的。”[9]教師作為教學活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需要有這樣一種認識與意識,且應該積極將之投入到自己的日常教學軌道之中。我們可以認識到,馬克思在對蘊含于現代社會和現代性中的異化現象的普遍性及嚴重性進行充分論述的同時,實際上也堅持認為異化現象是可以被揚棄的。那么,我們明白教育異化是發展的一個必然過程,但也該意識到其也只是一個過程而可以尋求更為合理、更有韻致的面貌。在這之中的教師,就不應該僅僅屈從并服務于現有的“分數就是一切”這一“信條”,當下的教師依然需要執著追求上述教育應有的“生命”這一重要維度。并且,我們甚至可以說,以分數為唯一導向的教師只是一種庸碌的存在,實際上其正是導致當下教育中一部分學生事故的“共犯”。
無疑,《潮濕的春天》中不乏所謂的“好”老師。正如俞莉所寫的“我身邊的老師大都非常敬業,令人敬佩。作為一名教員,我尊重這個崗位,也尊重我的教師同行。”[10]然而,作為當下的教育工作者,就只是應該盡力在現有的教育評價與價值體系里帶領學生追求發展,同時也獲得“利益”與“名利”嗎?火箭班的班主任馮貞屏老師,“是木棉中學出了名的拼命三郎,她40歲從湖南到深圳,之前已經成績卓著,是學科帶頭人,全國教育系統勞模,職務上做到校黨委書記。一年就解決了戶口。第一屆高考,她帶的班級出現了全市最高分,數學平均成績躍居全市第二,這在木棉中學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為此,她起早貪黑,“一天到晚做題、鉆研,一絲不茍,給學生的作業從來都是精挑細選,絕不是網上隨便找來下載粘貼拼湊而成”,“每天除了幾小時睡眠,其余大部分時間都泡在學校,泡在班級,樂此不疲地給孩子們輔導講解,處理他們遇到的各種問題。”正如小說中給馮老師的這句描述,她“百煉鋼化成繞指柔,真心實意地愛這個職業,愛她的學生。”作為讀者的我們甚至可以說,在該小說的閱讀過程中,不僅有一份痛楚,也有一份情感的溫醇,而那正是通過班主任馮老師對學生們的愛而生發出來的。但是,劉詩詩被送往精神疾病防治中心這一后續結局,難道就沒有馮老師及與之相似的“教育奉獻者”身上的催生因素嗎?
我們明白,未成年的學生,其價值觀與人生觀尚處于正在形成的階段,在這一過程中,師者的價值觀對學生的價值觀念顯然具有較為深刻的影響作用。我們可以對劉詩詩的行為心理軌跡做這樣的一個爬梳,劉詩詩曾是馮老師相中的“能人”,“馮老師欣賞她,因為劉詩詩身上有跟她一樣鐵面無私的敬業精神,劉詩詩不怕得罪人,也敢管。”“她是一個女生,一個一直優秀的女生,是班主任的得力助手左膀右臂。”在這樣一個輔助班主任進行班級管理工作的過程中,馮老師將“規訓”曾逸凡的一部分任務交給了“馮二”——劉詩詩。比起火箭班里其他同學的“整齊劃一”,曾逸凡聰明、有潛力的同時,還調皮、會玩、點子多,他在課堂上偷吃泡面、不交作業、善于和老師 “斗智斗勇”……在馮老師眼所不及之處,有被他稱為“劉狗”的劉詩詩盯著并進而打報告,他才終于“老實”了許多。然而后來,劉詩詩卻比曾逸凡顯得更“特別”。首先是在化學課上的展示,她開口道:“你們以為我是好學生,乖學生,NO!其實,你們都錯了,我骨子里不是好孩子,我很壞,你們被我騙到了。”并由此發表了自己的系列看法,讓科任教師不知如何是好,這事實上直指一部分身處教育系統中的人能體會到的痛楚。接著,她在某個晚自習離開座位,并引起全班的尋找,后來“劉詩詩在宿舍里得意洋洋地說,她混進高一家長會會場,在里面一個勁地打手機,周圍的家長都看著她,好過癮。”然后,“第二周的升旗禮,劉詩詩穿了件寬大的黑風衣,很扎眼地站在清一色的校服隊伍里,像一只不協調的大黑色垃圾袋。從來都是對老馮服服帖帖的劉詩詩,在辦公室跟班主任爭辯起來,她說她沒錯,沒有哪一條法律規定她不能穿風衣。”在宿舍,“午睡的時候,劉詩詩一個人不睡,把窗簾拉得開開的,借著外面的陽光看書。”并由此引起了同宿舍同學的不滿與爭吵。除此之外,她還“代表全班”勸退年輕的楊老師,在政治課、語文課上打岔發表意見,在一次迎接儀式之后主動辭退班長職務……在劉詩詩的這一系列略帶反抗性質的行為中,我們看到班主任馮老師的多次勸服、批評及聯系家長協商。而且在課堂上,在劉詩詩的反問中,“政治老師給問住了,干咳了一聲,敲敲桌子說,大家看題目,不要扯沒邊的東西,我們搞清楚問題要問的是什么,這里講的是稅收和公民依法納稅的義務……”,“語文老師說,你們可以有不同觀點,但注意了,高考作文題,你們在考試的時候千萬不可造次,不要亂質疑,要按照規范去寫,盡量正面。”在一次成績進步的月考后,劉詩詩在晚自習時卻在偷掉眼淚,她說是因為曾逸凡“嘲笑我,看不起我,他恨我……我可是為他……”。由此可見,詩詩是想和那個與大家“不一樣”的曾逸凡靠近一些,那個被她參與“規訓”的調皮的同學身上有吸引她的東西,大概那就正是 “生氣”——一種并不是死氣沉沉的存在。而曾逸凡那邊,對這個他口中的“劉狗”的靠近仍然是避之不及。
詩詩本質上一直都是一個向上的尋求發展的孩子,正如其父親敘述的“她自己以前想上中大,最近又改變主意了,想出國,去國外念書。”同時她也眼見并心疼父母的辛勞,“詩詩也很體貼家人,說出國的事等以后再說,等將來上了大學,爭取拿獎學金出去。”但及至小說最末,她已然有了一系列精神異常的行為,“劉詩詩在學校整夜整夜不睡覺,總是精神百倍地在宿舍里忙活,一會兒把所有人的水桶接滿,說學校要停水;一會兒又在前門和后門掛滿不知哪里弄來的水果刀,還有一把隨身別在自己腰間,說,有壞蛋要來搞恐怖活動,她是要保護大家。她在宿舍來回走動,聽到遠處的青蛙鳴叫,就大喊‘壞蛋來了’……”而后,其被送往深圳精神疾病防治中心住院。
當劉詩詩在異化體驗中感受到傷痛和困惑的時候,沒有一個教師真正切中或者解開她的心結,依然是以“考試分數”的達成為導向展開具體行為或言語行動,“教育”更多地成為了一種“產業”。有論者分析道,“現代教育異化的一個根本原因就是生活價值的異化。以世俗幸福為旨歸的現代教育致力于人們的種種功利需求,致力于解放人的物質欲望,教育只是為了滿足生存的需要,成為單純的謀生手段。實用與效率成為近現代教育追求的理想,知識、技能、工藝成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追求的惟一目標。教育開始真正的墮落,開始滑向反精神、反道德、反心靈的深淵,放棄‘育人’這一根本目的。”[11]然而于此,人取得的成就,已經遠遠比不上人自我的創造力、他的生命以及生存的藝術,后者實際上才是其所向往的教育指向。正如我們在前文指出的,這一“突然”事件,其實是“流水線”教育“產業”上出現的一種“必然”。并且,在這個意義上,這種面貌的教師其實都是當下應試教育制度的“共犯”,都在加深對“劉詩詩們”的傷害,都是促成其后續結果的“推動力”。小說中描寫到,深圳的春天帶著蝕骨的寒意,而南中國的木棉卻開得鮮紅耀眼。木棉花,別名“英雄花”,在料峭寒風里,沒有樹葉的環繞而獨自開滿于黑黢黢的枝頭。當我們意識到庸碌的、對教育缺少宏大關懷而只是執著于“分數”的教師,是教育異化的“共犯”之時,更渴望其能擁有如木棉花一般在“寒冷”里屹立開放的堅守、倔強與勇毅。小說最后馮老師夢見劉詩詩的求救呼喊“馮老師救我——”,她失聲痛哭,切身意識到了這之中的傷害:“哦,詩詩,親愛的孩子。我會的,我一定會的。”一代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對教育做出臻于理想境界的展望:“教育是幫助受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終極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的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12]由是,蔡元培時代的北大也就尤為強調終極價值體系的世界觀教育。在這個異常功利的年代讀來,這大概要讓許多教育從業者深感愧疚。
三、社會個體的批判性認識:教育生機的可能
在上述的相關論證中,我們可以形成這樣的一個基本共識,即中國當下的教育存在著許多嚴重的問題或者說正遭遇一定的危機。對此,除國家之外,我們每一個社會個體都應保持必要的批判性認識并在此基礎上訴諸合理的行動,唯有這樣,教育的生機才有呈現的可能。
教育者與被教育者顯然是教育活動中最為關鍵的兩維,其尤為需要對教育問題有清晰的認識。并且,受教育者由于自身經驗及認識的貧乏,其對事物的認識尤其需要教育者的引領。在上述的第二部分內容中我們已經提及教育者對被教育者價值觀形成的重要影響,并且,教育者需要擁有一種超越現有體制和體系的整體性眼光和終極性價值觀,對“教育”、“教育何為”與“人的培育”問題有一個根本性的認識及系統實踐教學的規劃。我們并不否定教育的功利目的,當下的教師們當然需要擁有外在的世俗幸福生活,我們更強調的是在這一基礎之上的對人的內在生命的生長及精神之幸福的追求。而今,一個普遍的狀況是教育和生命之間有了更多 “疏離”,“教師在教育中沒有真真實實地存在著,他扮演著一個角色,完成責任,遵從指示;教育既與自身疏離,也與教材和學生疏離。同時,學生與教師、教材和他自身也是疏離的,這種疏離使教育中的人日益成為客體中的客體,物件中的物件。”[13]也正如李政道所指出的,“如今的教育并不缺少先進的教學方法和教學設備,并不缺少教育思想和教育著作,也不缺少教育學的教授和博導,但惟獨缺少有靈魂的教育。那種飽含對生命的終極關懷,對人的自由、公正和生存尊嚴的教育已經遠離我們,被淹沒在利己主義的冰水之中。可以預見,未來浮出水面的將是一群有知識無智慧、有目標無信仰、有規范無道德、有欲望無理想的一代人。”[14]而他們卻正是我們民族的未來。當更多的教育從業者能深刻意識到這一點,也許就能更有力量地超越我們前述的那種“唯分數論”的庸碌教學,更能體會到作為教師需要對學生有一個合理明確的價值觀、世界觀乃至負載人類終極關懷的信仰的引導,而追求教育應該有的生命維度。并且,生命是流動變化的,而不是靜止單一的,教師自身的生命及教學行為也需要不斷地發現、更新和重建,當教師和學生的生命之間能在彼此交融中實現相互的轉化和創生,教師所經歷的教育時光也許就不會再是“瑣碎”、“平庸”、“煩擾”、“平面”的代名詞。同時,我們也需要指出,這對教育從業者個人的認識、素養及德性無疑都提出了挑戰。
正如小說中同時也呈現的,教育環節里還有關鍵的一環——家長。曾逸凡的母親,在兒子的狡辯撒謊中,竟然選擇嬌慣,“馮老師打電話向他媽媽求證,他媽媽電話里先是一愣,然后就說,確實是撞車了,耽擱了一些時間,責任在我。”劉詩詩的父親母親,在女兒一些情緒與行為反常的體現時,也表現出一種顯明的無力感,“我跟孩子她媽說,詩詩現在有點不正常,她媽反怪我,說,劉詩詩只是上次沒考好,學習壓力大,如果她不正常,那不正常的也太多了。”“他不相信,這個一直斯文懂事優秀的女兒,會變成……一個瘋子?”對于一個孩子的成長,學校教育之外毋庸置疑最重要的就是家庭教育。在這個層面上,我們需要提出,家長在何種程度上認識教育及相關問題,對孩子的發展亦起著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
在《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轉載小說《潮濕的春天》的卷首語中,有這樣一句話,“全社會應當反省:我們如何把變態的欲望強加到孩子身上,無情地摧殘下一代的成長。”[15]俞莉說:“作為一名寫作者,我不由自主地要批判、要懷疑。畢飛宇說,寫小說的人本質上是弱者,他有悲觀的傾向,對傷害有一種職業性的關注。”[16]可以看到,這是一個作家自覺擁有的一種對社會良知的擔待,基于此,她進行書寫,將當下教育中的這一份凝重及其底下涌動的生機欲求呈現給我們。俞莉的成名作《遍地杜鵑》是反映深圳的代課教師題材的作品。對自己熟悉的生活領域進行書寫呈現,發表系列的教育小說,強調文學與社會生活的內在勾連,這正是俞莉的一種自覺選擇。對這樣一種以現實主義為根本美學原則的作品無疑是需要給予肯定的,而我們也的確在作品之中感受到了作家的摯誠。同時,也需要指出的是,正如在前述第二部分所評價的以及俞莉在創作談中提到的,“是的。在這里我看到了傷害,看到了扭曲,看到了痛苦。我無法做什么,只能拿筆把它們呈現出來。”[17]俞莉這篇中篇小說在批判的力度方面是缺乏的,其本人也更多地選擇最終順應現有的這一體系,而沒有更多地體現出個體可以從自身開始去尋求的價值堅守與現狀突圍,其筆下的馮老師及至小說末尾才有傷痛與尋求改變的意識的顯露,更多的也只是一種“可能”。
教育問題,可以說是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復雜問題,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等眾多領域。它直接影響到個人、群體,同時也是影響社會進步及發展的原動力和催化劑。政府需要在這之中承擔重責,而我們社會個體,也應該以思考與行動去自覺有效地介入。我們的教育,不僅該有其應具備的莊重,也必須同時蘊含“春天”般的輕靈、律動與盎然。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3頁。
[2]陳愛民:《現代教育的異化及其哲學思考》,《攀登》,2005年第4期,第141頁。
[3][9][10][16][17]俞莉:《創作談:教育之殤》,《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2015年第6期,第135頁,第135頁,第135頁,第135頁,第135頁。
[4]俞莉:《潮濕的春天》,《清明》,2015年第5期,第58頁。該作品引文具體出處以下行文不再一一標示。
[5][11]甘劍梅:《論新時代的教育異化》,《寧波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3年第1期,第34頁,第33頁。
[6][英]湯因比、[日]遲田大作:《展望21世紀——湯因比與遲田大作對話錄》,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61頁。
[7][德]弗里德里希·拉普:《技術哲學導論》,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年,第126頁。
[8]安琪、吳原:《教育的異化與人的全面發展》,《天水師范學院學報》,2008年第6期,第137頁。
[12]陳平原、謝泳:《民國大學:遙想大學當年》,東方出版社,2013年,第303頁。
[13]劉鐵芳:《現代教育的反思》,《教育理論與實踐》,1998年第6期,第21頁。
[14]李政濤:《沒有靈魂的教育》,《新課程》(綜合版),2014年第1期,第1頁。
[15]俞莉:《潮濕的春天》,《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2015年第6期,第122頁。
(作者單位:江西師范大學文學院)
編輯:舍予
責任編輯:周建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