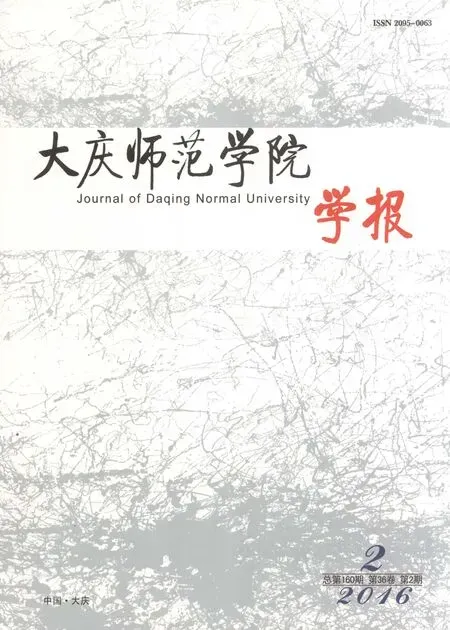科學證據及其應用問題探討
劉宇飛
(蘇州大學 王健法學院,江蘇 蘇州 215000)
?
科學證據及其應用問題探討
劉宇飛
(蘇州大學 王健法學院,江蘇 蘇州 215000)
摘要: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科學證據在訴訟活動中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科學證據具有促進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積極價值;另一方面,科學證據的不當運用也會產生侵犯人權,拖延訴訟,甚至造成錯判的消極影響。這需要對科學證據的涵義、價值角度做重新分析,對我國科學證據的應用需注意的問題進行重新探討,以使科學證據在司法實踐應用中引起高度重視。
關鍵詞:科學證據;價值分析;訴訟制度
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廣泛應用,科學技術在提高人們生活水平與生產能力的同時,也被應用到司法領域中。面對現代社會層出不窮的各種犯罪,在刑事司法實踐中,將科學技術引入司法證明過程是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其目的在于提高訴訟證明的技術含量。我國臺灣著名證據法學者蔡墩銘教授指出:“今日刑事審判不應再只重自白,而應重視物證,尤其藉法科學進行采證取得之物證,亦即科學證據。從而所謂證據裁判主義,于今日法科學應用之時代,應改稱為科學證據裁判主義。”[1]該學者表明科學證據在訴訟中的積極價值,即科學證據的運用有助于案件事實的查明,促進實體公正的體現。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當看到,科學證據也存在失真與錯誤的可能,對于刑事訴訟程序的正當和案件事實的準確查明可能帶來一些負面影響,甚至成為錯案的“幫兇”,需要高度重視并防范。本文通過對科學證據的深入分析,并結合我國刑事司法實踐,探究科學證據在刑事訴訟應用中所需注意的問題,期望能對我國科學證據制度的完善有所幫助。
一、科學證據的涵義
(一)域外學者關于科學證據含義的認識
英美國家盡管出版了大量的有關科學證據的著作,但都沒有直接明確的定義“科學證據”的含義,而大多數只是列舉出“科學證據”的范疇,然后對這些科學證據的運用再逐一進行研究。例如由英博和莫森斯合著的《刑事案件中的科學證據》一書認為科學證據包括如下領域:(1)醉酒的化學分析;(2)精神病學、心理學和神經學;(3)槍彈證據和比較顯微檢驗;(4)法醫病理學;(5)毒理學和化學;(6)指紋鑒定;(7)顯微分析;(8)中子活化分析;(9)可疑文書;(10)照相、電影和錄像;(11)聲紋鑒定;(12)車速的科學鑒定;(13)測謊檢查;(14)麻醉分析和催眠術;(16)其他科技證據,如素描技術、民意測驗等。[2]45
美國著名的證據法學家喬恩·R·華爾茲教授則從以下諸方面對“科學證據”進行了論述:(1)精神病學和心理學;(2)毒物學和化學;(3)法庭病理學;(4)照相證據、動作照片和錄像;(5)顯微分析;(6)中子活化分析;(7)指紋鑒定;(8)DNA鑒定;(9)槍彈證據;(10)聲紋鑒定;(11)可疑文書證據;(12)多電圖儀測謊審查;(13)車速檢測。[3]
與英美不同,許多日本學者試圖對科學證據作出明確定義,依石井一正教授的觀點,科學證據就是利用科學的統計學的概率原理來進行科學證明的證據。[4]三井誠教授指出:“科學證據系指活用各科學領域之知識、技術、成果所得之刑事法上之證據。科學證據當然不限于經過科學搜查活動所得致者,然而實際上乃指科學偵查活動結果所得之證據居多。”[5]
(二)國內學者對科學證據含義的不同認識
雖然科學證據已經在司法實踐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但國內學界對什么是科學證據仍存在種種不同的見解,觀點不盡統一。筆者從中選取一些代表性觀點,歸納如下:
第一種觀點認為,“所有通過科學方法所獲得證據都是科學證據,其主要包括鑒定結論和視聽資料”;并認為“科學證據是與認證、物證、書證和司法檢驗并列的一種證據形式”[6]。
第二種觀點認為,以“語義結構和證據功能”為分析框架,認為“科學證據是運用具有可檢驗特征的普遍定理、規律和原理解釋案件事實構成的變化發展及其內在聯系的專家意見”[7]。
第三種觀點認為,“凡是借助科學原理和技術方法收集到的證據材料以及借助科學原理和技術方法揭示出其證明價值的證據,都屬于科學證據。相反,不是通過科學技術手段發現、收集和揭示出來的證據都不屬于科學證據”。該學者進一步指出:“科學證據是指運用科學技術手段發現、收集和揭示出來的證據。其內涵是運用科學技術獲取的證據;其外延包括所有用科學技術手段獲取的證據,既包括過去,也包括現在和將來運用科學技術手段獲取的一切證據。”[8]
第四種觀點認為,科學證據是一個包含眾多證據形式的證據種類。由于幾乎每一種科技證據從產生到走進司法程序,都經歷了一個長時間不停爭辯的過程,所以,科技證據應當是指“具有一定技術水平,但同時要么由于其技術的可靠性難以得到科學界的一致肯定,要么因其對人權的巨大侵犯而被許多法學家所排斥而導致其容許性經歷或正在經歷一個不斷肯定和否定的反復過程的證據種類”[9]。
(三)科學證據涵義之我見
國內外學者關于科學證據的不同定義,實際上都具有相當的合理性和啟迪意義。通過對國內外學者不同觀點的比較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學者們對于科學證據定義產生爭論的原因關鍵在于大家思考問題的角度不同,而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必然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筆者更傾向于從科學證據的價值角度考慮——為何司法實踐中需要運用科學證據?簡言之,有了科學證據,我們便可以更加準確地探知案件事實的真相;科學證據是準確判定高科技犯罪的案件事實不可或缺的證據,缺少科學證據,高科技犯罪之類案件的偵破與證明便陷入困境。基于以上思考,筆者認為,科學證據是指能夠幫助人們證明案件事實,具有科學技術含量,而且不與訴訟效率、人權保障等價值相沖突的一類證據。
二、科學證據的價值分析
(一)積極價值
1.科學證據可以促進實體公正
作為科學技術在訴訟中運用的科學證據,是以追求客觀真實為根本目的的。在刑事訴訟中,辦案人員運用科學證據能夠更好的查明案件事實的真相,科學證據與其他證據相比發揮著無法替代的作用。原因在于司法人員通過運用科學技術來提高訴訟認識,借此避免認識主體受到感性認識上的不良影響,同時增強了認識主體理性認識的能力。相比言之,科學證據在發現事實真相上的作用主要有:(1)打擊高科技犯罪。對于當代越來越多利用高科技手段實施的犯罪,都具有犯罪主體智商高、反偵查能力強、犯罪地點多變、社會危害巨大等特點。因此,國家對付這些高科技犯罪的必要手段就是“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利用高科技手段調查收集證據,達到控制科技犯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有利局面。(2)對付傳統犯罪也發揮重要作用。例如,現在公安部門建立的指紋數據庫、DNA數據庫等數據庫為偵破一些傳統犯罪提供了巨大便利。這些數據庫的建立,可以將犯罪現場遺留的人體物證與嫌疑人比對,使得偵查人員迅速識別、認定犯罪分子。同時,現代社會大量使用各種監視錄像、閉路電視,對于準確快速地認定犯罪分子提供了有力的證據。(3)可以用來發現和糾正錯案。例如,1986年,英國中東部發生了兩起強奸并謀殺英國女學生的案件。警察在犯罪現場提取了精斑檢材和一名犯罪嫌疑人的血樣,由剛剛發明“DNA指紋圖”的遺傳學家阿萊克·杰弗里斯進行DNA對比。杰弗里斯證實兩起案件是同一人所為,但是罪犯并不是警察拘留的那名嫌疑犯—一名廚房的勤雜工。這名廚房的勤雜工成為世界上第一位用DNA證據證實的無辜者。
2.科學證據可以促進程序公正
科學證據的廣泛運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減少刑訊逼供的發生和保障被追訴人質證權的行使,從而促進程序公正的實現。一方面,科學證據的廣泛運用可以幫助追訴機關盡可能的擺脫對被追訴人口供的依賴,從而可以減少刑訊逼供現象的發生,保證程序正義的實現。刑訊,作為刑事司法程序上最大的不公,使得犯罪嫌疑人在定罪前受到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摧殘。當前,我國刑事司法實踐中發生的張氏叔侄、佘祥林、杜培武等重大冤假錯案,都與刑訊逼供密切相關。因此,在刑事證據程序公正中,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對刑訊逼供的防范。對此,陳學權教授指出,根治刑訊逼供的最有力辦法不是使追訴機關不能進行刑訊逼供,而是使追訴機關主觀上就覺得不想、也感覺無必要刑訊逼供。而要實現此目標,唯有開出“中藥”——向科技證據要破案率![2]142可以預見,隨著科學證據的普遍運用,追訴機關的破案壓力將會逐漸減輕,刑訊逼供必然會逐漸減少,屆時我國刑事司法在程序公正方面必將會取得巨大進步。另一方面,通過視聽技術,有助于解決證人出庭作證難的問題,確保被追訴人對證人進行質證,從而促進程序公正的實現。不可否認,雖然證人通過視聽技術作證有利于改變證人出庭作證難的問題,但是與要求證人親自出席法庭作證相比,顯然不利于法庭和控辯雙方“察言觀色”。盡管有缺陷,但就我國而言,在實踐中證人幾乎都不出庭作證的情況下,通過視聽技術讓證人作證,與在法庭上直接宣讀偵查階段的證人證言筆錄相比,已算是向前邁進了一大步,這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可以保證被追訴人質證權的行使,從而促進程序公正在我國的實現。
(二)消極價值
1.科學證據的運用可能侵犯人權
2012年,第二次修正的《刑事訴訟法》第2條明確規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權”是我國刑事訴訟的任務。顯然,科學技術在現代刑事訴訟中的運用也必須符合人權的要求。新修正的《刑事訴訟法》第130條規定勘驗、檢查時可以提取指紋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樣本,如果犯罪嫌疑人拒絕檢查,偵查人員認為必要時,可以強制檢查。血液、尿液等生物樣本作為物證需要專家利用科學技術進行解讀才能顯現價值,然而這種生物物證的提取,稍有不慎,便會與人的隱私權、身體健康權等憲法權利之間產生尖銳沖突。房保國教授指出:“強制采樣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權。如,強制沒有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到指定的場所接受采樣,是對被采樣人人身自由的限制。”[10]實際上,在刑事司法實踐中運用科學證據必然會受到一系列人權問題的挑戰,這也提醒我們在刑事訴訟中運用科學證據必須保持一定的限度。例如杜培武殺人冤案中測謊異化為刑訊逼供的幫兇進而造成錯案。杜培武就是因拒不承認犯罪,被偵查人員帶去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心理測試,結果測試表明杜否認殺人的供述90%以上是謊言。于是,偵查人員便對杜進行“生不如死”的刑訊逼供迫使其“承認”罪行。鑒于此,筆者認為對于測謊結論這類科學證據在取證階段要堅持自愿性原則。即偵查機關在對犯罪嫌疑人進行測謊之前,應征得被測謊人的同意,這是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具體體現。如果進行強制測謊可能會得出可靠性較低的結論,催生刑訊逼供,嚴重侵犯人權。
2.科學證據的運用可能導致訴訟拖延和成本增加
科學證據在實踐中的運用可能會導致訴訟陷入停滯狀態中,與訴訟效率目標產生沖突,同時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帶來訴訟成本的不合理增加。一方面,科學證據的生成本身就需要一個過程,在司法審判中,有些科學證據從程序啟動到證據的產生再到法庭上的質證和最終采信,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這些時間無論是否計入審理期限,都會造成案件遲遲得不到解決,使得訴訟過分遲延,在公正與效率之間無法得到平衡。況且案件的復雜和專家證人作證技巧的高明經常會導致審判法官面對“似真似假”的科學證據陷入難以分辨的泥潭,本來用于發現真實的科學證據在對抗制度下卻成為發現真實的障礙。裁判者難以做出裁決,也導致了訴訟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對于司法機關來說,科學鑒定證據的生成需要使用大量高科技設備和專業技術人員,費用昂貴,開支巨大;同時,由于法官作為事實的審判者在有關科學專業知識領域是門外漢,面對科學證據難以定奪,需要花費更多時間來認定事實,使得案件久拖不決,影響法院其他工作的開展,浪費司法資源,造成訴訟成本不合理增加。對于當事人來說,科學證據的作用日益重要,有時直接影響訴訟的成敗。因此,聘請專家、不惜代價聘請“一流”專家做出有利于己的鑒定證據已經成為一種必要的訴訟開支,勢必會給當事人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
3.科學證據的失真可能導致錯判
由于科學并非是絕對客觀以及運用過程中一些人為因素的影響,科學證據也可能失真,從而可能產生誤判,成為發現事實真相的阻礙。首先,科學證據的規范性和技術性要求非常高,但是在其收集、采樣、保管、鑒定等多個環節都可能出錯。例如在保管環節,收集完的物證將會隨即進行空間和時間的轉移,在移送的過程中,其中任何一次交接不清都可能導致待檢材料的混亂或受到外環境污染,一旦保管不善將會導致其證據證明力的喪失。其次,科學證據本身并非絕對權威,訴訟主體過于迷信科學證據。被奉為現代“證據之王”的DNA證據,在實踐中都被辦案人員視為“鐵證”,以為弄一個DNA鑒定證明嫌疑人犯罪就“鐵證如山”。事實上,DNA鑒定也存在很大程度的不確定性:人體基因本身的不確定性;人為操作的失誤;DNA數據的概率統計錯誤;DNA鑒定人員資質參差不齊。在實踐中,存在不少因DNA鑒定導致的錯案。如1998年發生在河北省邢臺市的徐東辰強奸殺人冤案。偵查人員將徐東辰的血樣和被害人陰道提取的衛生紙精斑進行DNA鑒定后得出“不排除死者陰道擦拭用紙上的精斑是嫌疑人徐東辰所留”的結論,警方據此認定徐為犯罪嫌疑人并屈打成招,迫使徐東辰認罪,并最終被判死刑。正是公檢法三機關對于DNA證據確信無疑,從而最終導致案件發生錯判。這表明,科學證據并非絕對可靠,有時反而妨礙了準確認定案件事實。我國刑事司法實務人員不應盲目輕信DNA的證明力,在刑事案件中不能僅僅憑借DNA鑒定結論來認定犯罪事實。
三、科學證據的應用需要注意的問題
(一)確立理性看待科學證據的態度
科學是柄雙刃劍,科學證據也有其兩重性,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我們無法忽視科學證據的科學性和時代性,同時,那種迷信科學證據的證據能力和證明力的觀點是不可取的。一方面,我們必須承認科學證據的科學性,承認其對常識證據的超越。科學證據依托強大的科技力量,能夠更為準確地判斷事實是否發生以及發生情況,為司法活動服務,為事實裁判者帶來更為準確的結果,從而推動司法公平與正義的實現。另一方面,在承認科學證據科學性的前提下,我們要認識到科學證據本身的缺陷,以及運用科學證據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科學證據本身不可能達到絕對客觀與中立,并且相關專家在生成科學證據時可能受自身的主觀傾向影響或操作失誤,造成誤差甚至完全錯誤,從而導致錯判讓無辜者蒙受不白之冤。
科學證據時代的到來是時代潮流的趨勢,科學證據有其明顯的積極功能,我們的法律工作者應該順應科學證據時代,學會利用科學證據查明案件事實,追尋真相,但是同時也必須認識到科學并不是萬能的,科學證據不可能完全取代經驗常識。因此,法院應慎重對待訴訟中的科學證據,法官應成守望者,清醒地看到科學證據光明之下的陰影,用公正、合理的證據規則才能去除司法的陰霾,讓科學證據走下神壇,回歸理性,與其他證據攜手共同維護司法的公正。[11]
(二)確立惟科學證據不能定罪原則
上文提到的徐東辰案件,司法辦案人員僅憑DNA證據便認定徐有罪并最終導致錯判。對此,我們認為,一方面,包括科學證據在內的任何一種證據都不能保證絕對的100%的準確無誤,即便是在科學證據準確無誤的情況下,還存在著該證據證明力問題。例如徐東辰案件中的DNA鑒定,即使該DNA鑒定結論完全準確,但也只能證明徐東辰可能曾在某特定時段內與被害人發生過性關系,同時也不能就此排除其他人在案發時與被害人發生過性行為的可能性,更加無法直接或間接證明殺害被害人的兇手就是徐東辰。另一方面,一旦在立法或司法實踐中確立了“科學證據是證據之王”的類似規則及理念,則不可避免地會導致訴訟實踐中過分迷信乃至不擇手段地獲取科學證據的危險。因此,針對司法實踐中過分倚重科學證據證明力的問題,有學者提出確立“惟科技證據不得定罪規則”,即指在只有一個科技證據證明被追訴人實施了犯罪行為的情況下,不得僅憑該科技證據認定被追訴人有罪。[2]321筆者對此觀點十分贊同,因為科學證據大多只能作為間接證據,刑事司法實務人員不應盲目輕信科學證據的證明力。我們必須明確的是,在只有一個科學證據證明被追訴人實施了犯罪行為而又沒有其他證據能相互印證的情況下,不得給被追訴人定罪。只有當存在充分的證明犯罪事實的其他相關證據時,并且這些相關證據與鑒定結論相結合能夠組成閉合的證據鎖鏈,對所認定的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的條件下,法庭審判人員才可以據此做出有罪判決。
(三)科學證據的收集應遵循的原則
證據收集,是指偵查、檢察、審判人員和當事人及其律師等享有收集證據權利的各類主體,通過偵查或調查,依法發現和取得與案件有關的各種證據材料的活動。對于科學證據而言,其收集包括鑒定基礎材料的獲取,視聽資料和電子證據等實物證據的獲得,以及技術偵查措施等。所有科學證據的收集都應遵循如下取證原則:(1)合法性原則。科學證據的收集應當符合法律的要求,遵循法治原則。新修正的《刑事訴訟法》第54—58條明確增加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于非法收集的科學證據,一律應當予以排除。(2)及時性原則。收集科學證據必須迅速,不能錯過最佳的取證時機,否則會導致所取證據喪失真實性。針對某些容易被刪除、修改、污染甚至毀壞的科學證據,應盡可能在其被破壞之前迅速收集。(3)利用專門技術設備取證原則。科學證據的發現、收集和保全,尤其是用來鑒定的檢驗材料的收集,離不開專門的技術和設備。(4)專家參與原則。科學證據以現代高科技為依托,科技因素比較多,因此,在取證時,需要有關科學專家和技術人員的參與,并且要與法律工作人員互相配合,一同完成收集工作。(5)收集過程監督原則。科學證據取證的整個過程都必須接受監督。在具體實施過程中,要有合法、規范和完整的筆錄以證實取證的合法性、真實性。
(四)鑒定人義務的完善
為了防止司法實踐中出現的鑒定結論作假、鑒定人操作失誤等原因導致科學證據失真造成錯案的情況,筆者認為,應當完善鑒定人的義務。首先,鑒定人最重要的義務就是完成鑒定工作并出具鑒定意見。但是,僅僅在鑒定書上注明鑒定結論是不夠的,鑒定人還負有制作規范、標準的鑒定文書的義務。這是因為,無論是案件的被害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公訴人還是法官,都需要通過鑒定文書來了解整個鑒定過程,進而才能判斷鑒定意見的可靠性。筆者認為,為了確保司法鑒定文書的規范、標準,防止鑒定人違反相應的說明義務,應該規定鑒定人違反制作規范、標準的鑒定文書義務的后果,對于鑒定書中未說明法定事項的,司法鑒定文書無效,法官應當排除該鑒定意見作為證據使用。其次,必須強化鑒定人出庭接受質詢義務。科學證據不能取代法院的司法裁判權,科學證據對于法官和陪審員來說并無法定的拘束力,都應該受到法庭的審查。法官作為事實裁判者需要辨別科學證據的正誤,而鑒定人出庭作證義務能夠有效幫助法官審理案件。除法律規定的原因外,鑒定人必須出庭作證,應就鑒定過程進行釋義:說明鑒定材料的收集程序、鑒定實驗的過程、運用的科學方法、獲取鑒定意見的科學依據,接受當事人雙方和法官的提問。將鑒定的啟動到科學證據產生的整個過程暴露在“陽光下”,這有利于法院做出公正的判決。
[參考文獻]
[1] 蔡墩銘.刑事證據法[M].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4.
[2] 陳學權.科技證據論 以刑事訴訟為視角[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
[3] 喬恩·R·華爾茲.刑事證據大全[M].何家弘,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456.
[4] 石井一正.日本實用刑事證據法[M].陳浩然,譯.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10-11.
[5] 王彬.論科學證據的科學性判斷標準及構建[J].河南司法警官職業學院學報,2008(4).
[6] 徐靜村.刑事訴訟法學: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73.
[7] 張斌.論科學證據的概念[J].中國刑事法雜志,2006(6).
[8] 何家弘.證據學論壇:第四卷[M].北京:中檢察出版社,2002:380-381.
[9] 樊崇義.刑事訴訟法實施問題與對策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1:287.
[10] 房保國.科學證據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38.
[11] 劉建華.讓科學證據走下神壇[J].中國司法鑒定,2011(5).
[責任編輯:才瓔珠]
Scientific Evidence and Its Application Problems
LIU Yu-fei
(Kenneth Wang School of Law,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0, China)
Abstract:As high-tech develops rapidly, scientific evidence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edings. It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entity justice and procedure justice.Meanwhile, the improper use of scientific evidence also violates human rights, delays litigation, even leads to wrong convictions. Therefore, the concept and value of scientific evidence should be analyzed again, and th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evidence in our country calls for people's attention.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evidence should b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Key words:scientific evidence; value analysis; litigation system
中圖分類號:D9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0063(2016)02-0066-05
收稿日期:2015-11-02
作者簡介:劉宇飛(1991-),男,江蘇連云港人,訴訟法學專業2014級碩士研究生,從事訴訟法學研究。
DOI 10.13356/j.cnki.jdnu.2095-0063.2016.0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