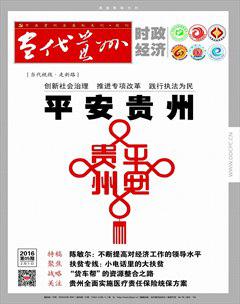陽(yáng)明學(xué)與日本國(guó)民道德建設(shè)
姚源清?韋佳妤
編者按: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陽(yáng)明文化東傳日本是濃墨重彩的一筆。王陽(yáng)明作為明代著名哲學(xué)家、心學(xué)集大成者,其心學(xué)思想是如何傳入日本,并被日本人認(rèn)知、吸納和改造的?對(duì)日本社會(huì)和思想道德建設(shè)起到怎樣的作用?記者就此專訪劉金才教授。
陽(yáng)明心學(xué)東傳日本
:陽(yáng)明心學(xué)作為中國(guó)儒家文化的組成部分,是繼朱子學(xué)之后全面影響日本的重要精神資源。陽(yáng)明心學(xué)東傳日本最早是在什么時(shí)候?
劉金才:1510年,日本“后五山僧侶”之一了庵桂悟奉幕府將軍足利義澄之命出使中國(guó),在中國(guó)逗留了3年。1513年,王陽(yáng)明與門人徐愛等游四明而經(jīng)寧波時(shí)會(huì)見了庵,同年五月還寫了《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歸國(guó)序》相贈(zèng)。在與了庵交往的過(guò)程中,王陽(yáng)明把自己寫的書也贈(zèng)送對(duì)方帶回日本,書中就談到了自己的思想。這可以說(shuō)是日本人與王陽(yáng)明的最早接觸。
從這樣的史料來(lái)看,日本最早接觸王陽(yáng)明、接觸王陽(yáng)明心學(xué)應(yīng)該是在16世紀(jì)初。但是,了庵桂悟回國(guó)后第二年即謝世,不可能為陽(yáng)明學(xué)的傳播做出更多的貢獻(xiàn)。根據(jù)日本學(xué)者柴田五郎的研究推測(cè),陽(yáng)明的文錄、文集、則言、《傳習(xí)錄》等,基本上是在16世紀(jì)中葉的“后五山僧侶”時(shí)期傳入日本的。但由于17世紀(jì)初,中國(guó)出現(xiàn)了對(duì)王陽(yáng)明的良知心學(xué)進(jìn)行反省的風(fēng)潮,德川幕府也為了建立絕對(duì)化的政治體制和嚴(yán)格的等級(jí)身份制道德秩序,將朱子學(xué)確立為官學(xué),因此初傳日本的陽(yáng)明心學(xué)的命運(yùn)并不順利,直到17世紀(jì)40年代中江藤樹由朱子學(xué)轉(zhuǎn)向陽(yáng)明學(xué),開創(chuàng)日本陽(yáng)明學(xué)派,日本的陽(yáng)明學(xué)才算真正誕生,中江藤樹也因此被譽(yù)為“近江圣人”“日本陽(yáng)明學(xué)始祖”。
:陽(yáng)明學(xué)傳入日本后能夠扎根下來(lái),并對(duì)日本國(guó)民性格及其社會(huì)產(chǎn)生深遠(yuǎn)影響,原因何在?
劉金才:事實(shí)上,近代以前,“陽(yáng)明學(xué)”一般被稱為“王學(xué)”或“余姚之學(xué)”,“陽(yáng)明學(xué)”這一學(xué)名的確定,以及把陽(yáng)明學(xué)定性為具有普世價(jià)值的東方哲學(xué)思想資源之一,并非始于中國(guó),而是開始于日本。具體地說(shuō),“陽(yáng)明學(xué)”這一名稱,是在日本的明治中期開展的“國(guó)民國(guó)家”道德教育運(yùn)動(dòng)中,由井上哲次郎等日本知識(shí)精英提出來(lái)的,之后才“反輸入”到中國(guó)。
為什么陽(yáng)明學(xué)產(chǎn)生于中國(guó),而它的學(xué)名卻是由日本人來(lái)命名,并且成為了近代日本“國(guó)民道德”教育的思想基礎(chǔ)呢?直接的原因是,無(wú)論是致力于推翻幕府封建統(tǒng)治的幕末維新志士,還是明治中后期旨在重建因西化風(fēng)潮而頹廢了的國(guó)民道德的國(guó)家主義知識(shí)分子,幾乎都毫無(wú)例外地崇尚陽(yáng)明心學(xué),并把陽(yáng)明學(xué)用作了他們行動(dòng)的思想武器。更深層的思想史原因則是,17世紀(jì)40年代初日本儒學(xué)者中江藤樹創(chuàng)始日本特色的陽(yáng)明學(xué)后,其把“明德”視為“萬(wàn)物一體之本體”、以“孝德”為“明德”倫理之核心、以良知為鏡而慎獨(dú)、自省和踐行,以及反對(duì)泥古而強(qiáng)調(diào)“時(shí)、處、位”之權(quán)變等思想,一直得到薪火相傳。
明治維新的精神先導(dǎo)
:作為陽(yáng)明學(xué)的重要分支,“日本陽(yáng)明學(xué)”對(duì)日本近世庶民道德培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體現(xiàn)了王陽(yáng)明學(xué)說(shuō)的哪些精髓?
劉金才:日本陽(yáng)明學(xué)的思想精神,首先體現(xiàn)在認(rèn)同王陽(yáng)明“心即理”的命題,認(rèn)為“心”是萬(wàn)物之本,從而強(qiáng)調(diào)了個(gè)體的存在價(jià)值。這對(duì)于促動(dòng)嚴(yán)格等級(jí)身份制下商工階級(jí)道德主體意識(shí)的覺醒具有積極意義。
第二,日本陽(yáng)明學(xué)認(rèn)為孝德是任何人都具有的“本心”,是人之所以為人之根本,天地萬(wàn)物都“存在于吾本心孝德之中”,孝乃天地萬(wàn)物造化之原理。不分將軍、大名、武士或農(nóng)民等身份和職業(yè)的不同,所有人都是來(lái)源于孝這一生命的根源,由此為武士以外的社會(huì)階層確立一種主張平等的自我意識(shí)。
第三,日本陽(yáng)明學(xué)認(rèn)為,內(nèi)在于人心之中的“良知”即“明德”,“明德”之本即是“孝”,而“明明德”之本則在于以良知為鏡而慎獨(dú)。這對(duì)于教化庶民養(yǎng)成以“孝·明徳·良知”為核心并能“明辨善惡是非”的正直德性發(fā)揮了作用。
第四,日本陽(yáng)明學(xué)注重踐履,強(qiáng)調(diào)知行合一。如日本陽(yáng)明學(xué)始祖中江藤樹,自己一邊研修、吸納陽(yáng)明心學(xué)思想,一邊開辦書院、教書育人,身體力行“知行合一”,既體現(xiàn)了儒家傳統(tǒng)的仁愛原則,又奉行了陽(yáng)明心學(xué)“致良知”,將 “良知”與“致知”有機(jī)統(tǒng)一,為實(shí)現(xiàn)民風(fēng)德化教育終其一生。
:近代著名學(xué)者章太炎說(shuō):“日本維新,亦由王學(xué)為其先導(dǎo)。”梁?jiǎn)⒊舱f(shuō):“日本維新之治,心學(xué)之為用也。”可以看出,陽(yáng)明學(xué)對(duì)日本實(shí)現(xiàn)明治維新這一重大歷史變革的重要作用。
劉金才:事實(shí)上,中江藤樹之后,陽(yáng)明學(xué)在日本形成了兩種類型。其中一類是具有強(qiáng)烈內(nèi)省性格的德教派(一說(shuō)存養(yǎng)派),以淵岡山、梁川星巖、春日潛庵等人為代表,忠實(shí)地繼承和傳播中江藤樹的思想和言說(shuō)。另一類則是注重踐履,以改造世界為己任的主事功派,代表人物有熊澤蕃山、大鹽中齋、吉田松陰等人。江戶時(shí)代后期涌現(xiàn)了大量憂國(guó)憂民、勇于實(shí)踐的學(xué)者兼實(shí)干家,最主要的是主事功派的陽(yáng)明學(xué)者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這里重點(diǎn)介紹一下吉田松陰。吉田松陰是倒幕維新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先驅(qū)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被稱為明治維新的精神指導(dǎo)家和實(shí)干家。在陽(yáng)明學(xué)的影響和鼓舞下,他積極主張尊王攘夷,為倒幕獻(xiàn)出了生命。吉田松陰曾辦過(guò)私塾,據(jù)說(shuō)80個(gè)學(xué)生中有近半數(shù)是明治維新的英杰。明治維新前后叱咤風(fēng)云、雄飛廟堂的許多俊杰之輩,如伊藤博文、木戶孝允、高杉晉作等,皆出自松陰門下。
正是這些信奉或傾向陽(yáng)明學(xué)的杰出人物,以陽(yáng)明學(xué)為思想武器或動(dòng)力,倡導(dǎo)尊王攘夷和倒幕變革,推動(dòng)了明治維新的實(shí)現(xiàn),瓦解了日本封建體制,由此而開啟了日本社會(huì)通向近代化的大門,而受陽(yáng)明學(xué)影響的明治開國(guó)元?jiǎng)滓撂俨┪摹⑽鬣l(xiāng)隆盛則直接提倡民權(quán)、民主、廢藩置縣,為日本實(shí)現(xiàn)近代資本主義奠定了基礎(chǔ)。
匡救時(shí)弊的良藥
:明治維新之后,陽(yáng)明學(xué)的用途及精神指向在日本“國(guó)民國(guó)家”道德教育中亦有所體現(xiàn),這一時(shí)期陽(yáng)明學(xué)呈現(xiàn)出哪些特點(diǎn)?
劉金才:日俄戰(zhàn)爭(zhēng)以后,日本擠入一流國(guó)家,但在西方風(fēng)潮的影響下,金錢萬(wàn)能的思想甚囂塵上,道德頹廢等各種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問(wèn)題迭出。為了打破這種危急狀態(tài),日本開始重啟傳統(tǒng)思想和文化。在此背景下,明治時(shí)期的陽(yáng)明學(xué)復(fù)興運(yùn)動(dòng)應(yīng)運(yùn)而生。
在近代國(guó)民道德建設(shè)運(yùn)動(dòng)當(dāng)中強(qiáng)調(diào)的陽(yáng)明學(xué),其特點(diǎn)主要是強(qiáng)調(diào)對(duì)良心的皈依、徹底的行動(dòng)主義,強(qiáng)調(diào)內(nèi)心的純粹以及至誠(chéng)、積極的獻(xiàn)身主義等。因此,官派學(xué)者井上哲次郎倡導(dǎo)陽(yáng)明學(xué),著書梳理“日本陽(yáng)明學(xué)”的譜系,將陽(yáng)明學(xué)定位為代表心德的東洋道德的精華和東洋哲學(xué)史的構(gòu)成部分,其宗旨就在于以此讓國(guó)民“領(lǐng)悟陶冶和熔鑄吾邦國(guó)民之心性的德教精神”。而高瀨武次郎則將陽(yáng)明學(xué)與《教育敕語(yǔ)》的“忠孝一本”國(guó)體精神扯上關(guān)系,認(rèn)為“吾人有先天固有之良知,若以之對(duì)君則為‘忠,若以之對(duì)親則為‘孝,……所謂國(guó)民道德之事,亦豈離良知而別存有之哉”,因而他與井上氏同樣,被稱為近代國(guó)家主義陽(yáng)明學(xué)的代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xiàn)了日本近代陽(yáng)明學(xué)被國(guó)體主義惡用的一面。
明治陽(yáng)明學(xué)塑造出了兩個(gè)與陽(yáng)明學(xué)相關(guān)的模范國(guó)民形象——“孝親愛人”的榜樣中江藤樹和“勤勉好學(xué)、至誠(chéng)報(bào)德”的榜樣二宮尊德,加入到了建設(shè)國(guó)民道德的隊(duì)伍之中,并被寫進(jìn)國(guó)定修身教科書,作為具體事例列入至誠(chéng)、孝行、勤勉、力行等德目之下。
:公民道德建設(shè)的重要性在當(dāng)下不言而喻,日本運(yùn)用陽(yáng)明學(xué)重建國(guó)民道德,這對(duì)當(dāng)前中國(guó)加強(qiáng)公民道德建設(shè)有何啟示?
劉金才:陽(yáng)明學(xué)對(duì)于日本國(guó)民道德的建構(gòu)是卓有成效的,但也應(yīng)該注意到二戰(zhàn)結(jié)束前,近代國(guó)家主義陽(yáng)明學(xué)有相當(dāng)一部分被日本軍國(guó)主義所惡用的事實(shí)。也就是說(shuō),只有戰(zhàn)后恢復(fù)的基于近代(1868年始)前的陽(yáng)明學(xué)所建構(gòu)的道德,才能真正體現(xiàn)日本陽(yáng)明學(xué)道德價(jià)值的實(shí)相。
就當(dāng)下中國(guó)而言,加大公民道德建設(shè),既需要從中華傳統(tǒng)思想文化中汲取正能量,也需要從他國(guó)借鑒國(guó)民道德建設(shè)的經(jīng)驗(yàn),尤其是他國(guó)活用中華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經(jīng)驗(yàn)。事實(shí)上,社會(huì)主義核心價(jià)值觀中提倡的“愛國(guó)、敬業(yè)、誠(chéng)信、友善”等公民個(gè)人層面的價(jià)值準(zhǔn)則,本就與陽(yáng)明學(xué)倡導(dǎo)的“萬(wàn)物一體為仁”“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有著密切的傳承關(guān)系。而前面所說(shuō)的日本陽(yáng)明學(xué)用于近世庶民道德培育的經(jīng)驗(yàn)、日本近代啟用陽(yáng)明學(xué)加強(qiáng)國(guó)民道德建設(shè)和匡救時(shí)弊的有效性,以及現(xiàn)代日本陽(yáng)明學(xué)者將陽(yáng)明學(xué)用于思考和解決現(xiàn)代人“倫理弱化”等問(wèn)題的視角,都對(duì)我們當(dāng)前加強(qiáng)民族文化自信,挖掘陽(yáng)明學(xué)的現(xiàn)代價(jià)值為社會(huì)主義核心價(jià)值觀培育和公民道德的建設(shè)服務(wù),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責(zé)任編輯/姚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