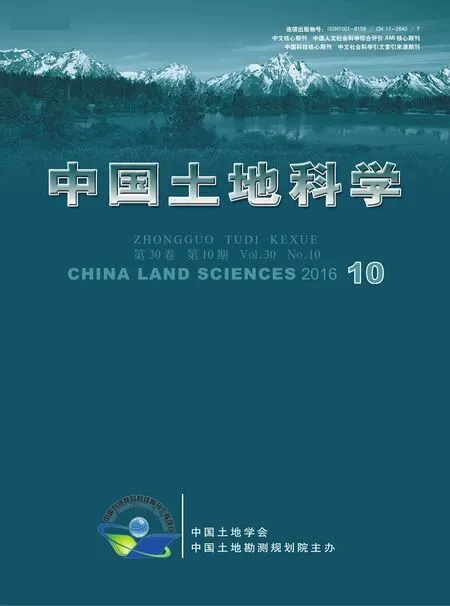空間視角下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的影響研究
周 游,譚光榮
(1. 湖南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湖南 長沙 410079;2. 湖南涉外經濟學院商學院,湖南 長沙 410205)
空間視角下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的影響研究
周 游1,2,譚光榮1
(1. 湖南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湖南 長沙 410079;2. 湖南涉外經濟學院商學院,湖南 長沙 410205)
研究目的:從空間視角研究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中國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的決定作用,為新型城鎮化建設進程中合理安排城市產業布局、促進土地利用方式轉變、實現城市經濟和土地集約利用協同發展提供新思路。研究方法:空間計量分析法。研究結果:中國城市間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和土地集約利用在地理分布上具有顯著空間關聯性;全國層面,生產性服務業通過專業化集聚、多樣化集聚產生的技術外溢效應和集聚規模產生的規模經濟效應顯著提高了城市土地集約利用水平;分板塊層面,生產性服務業多樣化集聚和集聚規模對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的正向效應呈現東、中、東北、西部板塊依次遞減現象,而專業化集聚對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的技術外溢效應在西部地區更明顯。研究結論:提升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和人口集聚有利于中國城市集約利用土地資源。
土地利用;生產性服務業集聚;STIRPAT模型;空間計量分析
1 引言
現行城鄉土地二元分割制度背景下,以“土地引資”和“土地財政”為引擎的城鎮化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城市經濟增長,但也導致中國城市土地資源利用的矛盾日益突出[1],因此,積極探索促進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的新型驅動機制,推動城市土地利用方式由粗放低效向集約高效轉變是實現中國城市經濟和土地可持續發展的客觀需要。2009—2014年,中國第二產業用平均45.53 %的產值份額提供了社會28.94 %的就業崗位,而第三產業卻用45.11 %的產值份額提供了社會35.37 %的就業崗位。與第二產業相比,服務業具有更強的就業和人口集聚能力,而具有高附加值和高技術含量特征的生產性服務業將是服務業未來發展方向[2]。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能夠有效促進城市產業結構調整,推動城市土地立體空間的多維利用,從而優化城市土地空間布局并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3]。《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亦提出將順應制造業向產業鏈高端發展作為優化城市產業結構的核心內容,將促進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與多樣化發展,指引其在城市核心區和制造業集中區集聚作為優化城市產業結構的主要內容,以期促進城市經濟轉型升級并提高城市空間利用效率。可見,提高現代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化水平是優化城市產業結構、推動城市人口集聚和產城融合,進而有效促進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的重要突破口。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服務業逐步取代傳統制造業成為推動經濟增長新動力,產業和區域經濟研究也開始從制造業轉向服務業領域。與制造業相比,服務業能夠產生更大集聚效應[4]。Marshall[5]和Jacobs[6]的技術外部性理論為解釋城市土地集約利用中生產性服務業集聚作用提供了理論基礎,該理論認為生產性服務業主要通過產業內專業化集聚或不同產業多樣化集聚產生技術經濟外部性,這些布局有利于企業間知識或技術的合作與交流并促進專業化勞動力市場共享。通過專業化或多樣化集聚產生的“動態外部性”是提升企業技術效率、提高城市土地產出效益的重要來源[7]。Eswaran和Kotwal[8]認為生產性服務業中的金融、研發等具有創新能力的部門集聚不僅改善了當地投資環境,而且推動了企業間技術交流,提高了地區勞動生產率。近年來,生產性服務業已成為中國中心城市的主導服務行業,且中心城市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外圍城市產生了較大輻射作用[9]。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將帶動城市其他服務業和工業發展,通過推動城市產業結構升級促進土地集約利用[3]。以上研究表明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有利于推動本土技術創新和科技進步,提高區域技術擴散效率進而促進土地集約利用,但并未具體解答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技術溢出效應具體來源于哪種模式。另有學者從垂直關聯理論出發,認為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有利于降低產業鏈上下游企業交易及生產成本,進而產生規模經濟[10-11],這種不同產業集中分布形成的產業間集聚有利于產業結構優化進而促進城市土地集約利用。此外,相關研究表明區域環境質量[2]、對外開放度[12]、人力資本[13]、交通條件[2]等對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外溢效應起調節作用,因而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城市土地集約利用影響效果可能呈現明顯區域差異。
上述研究深化了對生產服務業集聚與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的認識,但仍存在不足之處,主要體現在:首先,現有文獻多從產業層面研究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土地集約利用的關系,但鮮有從空間維度方面進行探討。若不考慮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間的空間相關性對模型的影響,估計結果將變為有偏或無效[14];其次,多數研究認同城市同一產業專業化分工或不同產業多樣化分布形成的技術外溢效應和不同產業集中分布形成的規模集聚效應是土地利用效率遞增的來源,但并未將兩者納入同一框架研究。為此,在已有研究基礎上,選取2004—2014年中國286個城市數據為樣本,構建城市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集聚、多樣化集聚、集聚規模和土地集約利用指標體系分析其空間分布趨勢及關聯性,并在外部性理論和垂直關聯理論框架下構架空間計量模型,實證檢驗全國和分東部、中部、東北、西部4大板塊①由于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統籌實施“四大板塊”和“三個支撐帶”戰略布局,故將中國城市分為“東部、中部、東北、西部”4大板塊進行實證分析。城市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土地集約利用的影響。
2 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城市土地集約利用評價指標體系
2.1 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指標選擇
根據城市劃分行業就業統計口徑,把19個行業中具有生產性服務業特征的9個行業②這9個行業分別為電力煤氣供水、建筑、交通運輸倉儲郵政、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批發零售、金融、租賃和商業服務、科技服務和地質勘查、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合并代表生產性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各集聚模式指標說明如下:
(1)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集聚M。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集聚指標可表示為[15]:

式(1)中,Ei,j和Ei分別表示i城市某生產性服務業j就業人數和i城市總就業人數,E'j和E'分別代表全國生產性服務業j就業人數(除城市i外)和全國就業總人數(除城市i外)。該指標系數為正則表明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存在“馬歇爾技術外部性”(即由同一產業專業化集聚引起的知識或技術溢出效應)。
(2)生產性服務業多樣化集聚D。改進Combes[16]衡量產業多樣化的指標(Herfindahl-Hirsh-man-index系數)來衡量生產性服務業的多樣化集聚,改進的H-H系數(式(2))不僅考慮了各產業在經濟結構中的權重,還注重了城市層面與國家層面產業的相比性。

式(2)中,Ei,j、Ei、E'j變量解釋同式(1),Ej為全國生產性服務產業j就業人數,E是全國總就業人數,Ei,j'表示i城市除產業j外其他某產業j'就業人數。該指標值越大,表明某城市生產性服務業多樣化程度越高。該指標系數為正則表明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存在“雅各布斯技術外部性”(即由多個產業的多樣化集聚引起的知識或技術溢出效應)。
(3)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規模PS。利用各城市生產性服務業就業規模占該城市所在省份就業總數比例衡量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規模[17]:

式(3)中,PSi表示i城市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規模,Ei,j表示i城市某生產性服務產業j就業人數,E表示i城市所在省或直轄市(自治區)就業總人數。
2.2 城市土地集約利用水平指標
借鑒彭沖等[1]估計方法,從土地投入強度、利用強度、利用效益和利用結構4方面構建指標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計算土地集約利用水平(I)。其中,城市容積率用該城市建筑面積與建設用地面積的比值表示,而城市平均建筑密度用該城市建設用地面積與城區面積的比值衡量。鑒于表1中描述的14個指標變量原始數據量綱的顯著差異,首先對各變量進行標準化處理,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測算結果①具體標準化公式和主成分數值計算過程參照廖進中等[18]:《長株潭地區城鎮化對土地利用效率的影響》。,為便于后續實證研究,最后采用統計學中的3σ原則,運用坐標平移公式Yti= L + Yt消除主成分分析結果中負值的影響,得到城市土地利用的綜合指數值,土地利用綜合指數值越大表明城市土地集約利用水平越高。

表1 城市土地集約利用指標體系Tab.1 The assessment indicators on the intensive urban land use
3 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的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
3.1 空間自相關檢驗
為檢測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的空間集聚度,可采用Moran指數及其散點圖分析。結果發現②篇幅所限,2004—2014年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的Moran指數表未給出,如有需要可以向筆者索取。,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集聚、多樣化集聚、集聚規模變量的Moran值為正且均在5%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說明生產性服務業各集聚模式的空間分布并非是無序的,而是表現出空間正相關現象。對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的Moran值考察,除2006年外,其他年份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的Moran值均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并呈現出波狀起伏趨勢,整體看,城市土地集約利用具有空間自相關性,其在空間分布上存在集群現象。
Moran指數散點圖可將集群分4種模式:即第一象限的HH集聚區(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高的城市被同是高集聚水平的其他城市包圍)、第二象限的LH集聚區(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低的城市被高集聚水平的其他城市包圍)、第三象限的LL集聚區和第四象限的HL集聚區。城市生產性服務業和土地集約利用的Moran散點圖顯示大部分城市位于第一和第三象限,因此大部分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集聚、多樣化集聚、集聚規模水平和土地集約利用水平高的城市在空間上相互集中,而其水平低的城市被同樣是低水平的其他城市所包圍。

圖1 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集聚(D)、多樣化集聚(M)、集聚規模(PS)和城市土地集約利用(I)Moran散點圖Fig.1 Moran scatter diagram of all kinds of productive service agglomeration and intensity of urban land use
3.2 空間關聯局域指標LISA集群圖
為進一步分析城市生產性服務業和土地集約利用的局域空間關聯性,采用局域空間關聯指標LISA測算局部地區間空間關聯模式。從圖2可知,2004年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集聚、多樣化集聚和集聚規模區域空間分布比較分散,除部分沿海城市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處在高值(HH)集聚區外,大部分城市均處于中值(HL和LH)或低值(LL)集聚區,總體看, 城市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特征并不明顯。到2014年,城市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集聚、多樣化集聚和集聚規模的空間分布層次較清晰,形成了沿海城市為縱軸(由遼寧、山東、江蘇、浙江和廣東轄區沿海城市串聯而成)的中高值集聚帶(主要為HH和HL集聚區);沿京哈京廣線城市為縱軸的綿延(由黑龍江、吉林、遼寧、北京、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城市串聯而成)中值水平集聚帶(主要為HL和LH集聚區);以包昆鐵路沿線(由內蒙古、陜西、四川、云南城市串聯而成)為縱軸的低值水平集聚帶(主要為LL集聚區)。總體而言,2014年生產性服務業多樣化集聚比專業化集聚和集聚規模的空間分布層次更明顯,且中西部和東北部城市帶生產性服務業各集聚模式值普遍分布在中低值(HL、LH和LL)集聚區,而東部城市位于高值(HH)集聚區的數量更多。
相比于生產性服務業各集聚模式,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的空間分布演化路徑與其具有較為明顯相似性和同步性。2004年,雖有少部分東部沿海城市土地集約利用水平處于高值(HH)集聚區,但總體而言,全國大部分城市處于較低水平集聚區,基本呈現由東至西依次降低態勢,到2014年,東、中、東北板塊城市土地集約利用水平明顯提高,但甘肅、陜西、四川、云南等西部城市則一直處在中低值集聚區(主要為LH和LL集聚區)。圖3顯示,2004—2014年,遼寧、天津、山東、江蘇、浙江、廣東等轄區沿海城市利用自身地理優勢不斷提高了土地集約利用水平,其高值(HH)集聚區面積不斷擴大,在鄰近東部沿海地區帶動下,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中部城市土地集約利用不斷向中高水平發展,呈現出以點帶線、以線促面的集聚特征。總體而言,東部地區土地集約利用的鄰域輻射效應大于其他三大板塊。
從城市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集聚、多樣化集聚、集聚規模和土地集約利用水平的空間布局看,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和土地集約利用分層集聚格局存在較明顯的同步性和相似性,兩者間具有顯著的空間依賴特征,因而有必要進一步構建空間計量模型進行實證檢驗。

圖2 2004、2014年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集聚(D)、多樣化集聚(M)和集聚規模(PS)的LISA集群圖Fig.2 LISA cluster diagram of all kinds of productive service agglomeration in 2004 and 2014

圖3 2004年、2014年中國城市土地集約利用水平(I)的LISA集群示意圖Fig.3 LISA cluster diagram of urban land intensive use in 2004 and 2014
4 模型設定和變量說明
4.1 模型設定
結合外部性理論和垂直關聯理論對集聚經濟效應的解釋,認為生產性服務業集聚主要通過技術外溢效應和規模經濟效應作用于城市土地集約利用:(1)生產性服務業技術外溢效應。根據外部性理論,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和多樣化集聚是生產性服務業產生技術外溢效應的主要途徑[5-6]。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集聚能夠提升區域企業效率,激發城市產業發展活力,不僅有利于吸引高素質人才向該城市集聚,而且促進了技術研發活動集聚,對于提高土地生產效率具有顯著推動作用[7]。生產性服務業多樣化集聚會對城市產業間競爭尤其是技術競爭產生正外部性,競爭性較強的高新技術產業將在市場選擇效應下脫穎而出,進而提高單位土地生產效率,促進城市土地集約利用。(2)生產服務業集聚的規模經濟效應。根據垂直關聯理論,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規模產生的規模經濟效應也是促進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的重要力量[10-11]。一方面,生產服務業集聚規模會引致城市人口集聚和產業集聚,進而會降低工業成本,產生規模經濟,帶來單位土地投入強度不斷增加和產出效益不斷提升;另一方面,產業集聚將促進并深化各地區產業內或產業間的專業化分工,有助于提升企業間和產業間的關聯效應,更好地發揮產業間協同作用,不僅優化了城市土地利用結構,也提高了城市土地經濟密度,從而促進了土地集約利用。
為進一步檢驗中國城市生產性服務業各集聚模式對土地集約利用的影響,引入Dietz and York[19]建立的分析環境壓力與人文驅動力關系的STIRPAT模型:

式(4)中,I為環境影響,土地利用是環境影響的關鍵因素,用土地集約利用水平衡量;a為常數項,P是人口規模;A為人均財富;T為技術進步水平(由技術條件和規模經濟決定);e為隨機擾動項。生產性服務業在城市集聚是促進區域技術進步的重要途徑,主要表現為技術外溢和集聚規模(PS),而技術外溢效應主要來源于專業化集聚(M)和多樣化集聚(D),因此,將技術進步函數T = f(s)= T0sθ= T0(s0MαDβPSχ)帶入式(4)并取對數得:

式(5)中,A0= lnaTd0sθd0,λ1= αθd,λ2= βθd,λ3= χθd,εit= lneit;i,t分別表示城市和年份。
由空間數據分析可知,城市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土地集約利用存在較明顯的空間關聯性,因此模型中需納入空間相關性。此外,考慮回歸結果穩定性和樣本數據可得性,加入以往研究中已達成基本共識的重要影響因素作為控制變量,主要包括城市環境質量(EQ)、對外開放度(Open)、人力資本(HC)和交通條件(TRA)。

根據觀測值空間相關性沖擊方式不同,空間計量模型可分為空間滯后模型(SLM)和空間誤差模型(SEM)。SLM模型為:式(6)中,wit是服從標準正態分布的隨機誤差項,ρ為空間滯后系數,反映其他城市土地集約利用觀測值對本城市的作用;Xit代表控制變量;Wij代表空間權重矩陣。Wij的計算借鑒引力模型思想,如式(7),該矩陣不僅反應了不同城市經濟間關聯性,還較好地刻畫出變量作用隨距離衰減規律[20]。式(7)中,Q表示樣本期內兩城市人均GDP均值的積,di,j代表兩城市中心距離①數據來源于衛星定位系統Google earth的測量和地理網(www.geobytes.com/citydistance)。。

空間誤差模型表達式為:

4.2 變量與數據說明
數據為2004—2014年全國286個城市面板數據②拉薩數據缺失嚴重故剔除。,主要來源于2005—2015年各省《統計年鑒》、《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中國國土資源統計年鑒》以及《中國城鄉建設統計年鑒》。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集聚(D)、多樣化集聚(M)、集聚規模水平(PS)和城市土地集約利用水平(I)用前文所述指標測算。人口規模(P)用城鎮人口規模表示,人均財富(A)以人均GDP作為替代變量。城市環境質量主要受環境污染和綠化水平影響,借鑒韓峰[2]的方法,用城市環境質量綜合指數(EQ)衡量③首先對影響環境質量的正向指標(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和逆向指標(市工業廢水、二氧化硫、煙塵排放量)進行標準化處理,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評價城市環境質量的綜合指數。。對外開放度(Open)采用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存量衡量,結果采用永續盤存法計算得到。人力資本(HC)用普通中學和高校畢業生人數占當地總人口比重表示。交通條件(TRA)與城市道路建設有關,用市人均道路鋪裝面積(m2)近似表示。
5 計量檢驗與結果分析
對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前需檢驗城市土地集約利用及其影響因素是否存在空間自相關。為保證結果更好地適用模型,分別采用Moran Walds、Lratios、Lmsar、Lmerr等指標檢驗。SEM估計結果顯示,模型1—5中所有檢驗都在5%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表明城市土地集約利用與各自變量間具有顯著的空間自相關。Robust Lmerr統計量在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而Robust Lmsar統計量未通過10%的顯著性檢驗,因而空間誤差模型(SEM)結果更合理。進一步進行Hausman檢驗結果支持原假設,因而選擇空間誤差固定效應模型。LR檢驗(經似然比)結果表明存在地區效應而不存在時間效應,且空間固定效應模型擬合優度和Log Likelihood值明顯大于無固定效應模型④根據對空間效應和時間效應的不同控制,固定效應可以分為無固定效應(nonF)、空間固定效應(sF)、時間固定效應(tF)、既有空間又有時間固定效應(stF)。,說明考慮空間相互作用因素后模型的穩健性和合理性得到了提高,這意味著中國城市土地集約利用存在明顯的空間集聚特征,土地集約利用水平變化主要受同期城市間土地集約利用差異的影響,一個城市土地集約利用水平不僅受到周邊鄰近城市土地集約利用水平的相互沖擊,還受到城市間結構性差異的誤差沖擊。
模型1中空間誤差系數λ顯著為正,說明中國城市土地集約利用存在顯著的空間依賴性,城市土地利用行為具有明顯的“局域俱樂部集團效應”(即局部地區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的高值或低值在空間上趨于集聚)。模型1中,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和多樣化集聚系數在1%的水平線顯著為正,這意味著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集聚產生的“馬歇爾技術外部性”和多樣化集聚產生的“雅各布斯技術外部性”對城市土地集約利用具有明顯正向促進作用。進一步分析發現,城市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集聚對土地集約利用的促進作用更為突出。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規模變量系數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生產性服務業集聚通過城市間不同產業間企業的投入產出關聯確實可以促進土地集約利用。可能的原因是,生產性服務業企業集聚產生的規模經濟效應減少了供應鏈上下游企業生產成本,促進其上下游企業更大規模集聚,進而提高城市土地經濟密度和城市土地產出效益。
模型2、3、4、5結果表明,東、中、東北、西部4大板塊城市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土地集約利用的影響程度存在明顯差異。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集聚對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的效應顯著為正,且作用效果在西部地區更為明顯,說明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集聚產生的“馬歇爾技術外部性”對欠發達地區城市土地集約利用至關重要。其原因可能是:相對于其他板塊城市,西部地區城市大多屬于資源性城市,通過發展與當地比較優勢相適應的生產性服務業并依靠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集聚產生的技術外溢與資源稟賦的互補效應,將更有利于當地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生產性服務業多樣化集聚對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的影響效應由東至西依次遞減,說明生產性服務業多樣化集聚產生的“雅各布斯技術外部性”在東部經濟發達城市更明顯。與其他三大板塊城市相比,東部地區城市產業部門種類齊全,因而與之配套的生產性服務業功能多樣,有利于降低東部城市企業生產成本,提高企業全要素生產率,進而提高單位土地利用效率。生產性服務業空間規模集聚對各板塊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的影響顯著為正且呈現由東向西依次遞減現象,表明生產性性服務業集聚規模所產生的規模經濟效應在東部地區比在其他三大區域更明顯。東部地區城市群規模和生產性服務業規模均明顯大于中部、東北和西部地區,因而東部地區市場規模遠大于其他三大地區,這有利于充分發揮市場規模經濟效應,而中部、東北和西部城市大部分分布在內陸,彼此間聯系較少,受限的市場規模阻礙了規模經濟效應發揮。
各控制變量中,城市人口規模顯著促進了東、中部和東北地區城市的土地集約利用,而對西部地區的影響雖然為正但不顯著;人均財富(人均GDP)對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的影響效應由東至西依次遞增,原因可能是經濟發達地區過度追求GDP增長造成城市土地資源亂開發現象嚴重,造成土地資源浪費,抵消了其對土地集約利用的積極影響;城市生態環境質量對西部城市土地集約利用影響顯著為正,而對其他3大板塊城市的影響為負;對外開放度對四大板塊城市土地集約利用影響顯著為正,且對中、西部地區促進作用更大,因此,鼓勵外資流向相對缺乏資本的中西部地區有利于當地產業發展;人力資本對4大板塊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的影響均顯著為正,對中部和東北板塊城市的正向促進作用尤為明顯;城市交通條件的改善對4大板塊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的影響顯著為正,但對中部和東北地區的促進作用更明顯。
6 主要結論與政策啟示
生產性服務業主要通過專業化集聚、多樣化集聚和集聚規模三個途徑影響城市土地集約利用水平。全國層面實證結果表明,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集聚和多樣化集聚產生的技術外溢效應是推動中國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的重要因素,但專業化集聚產生的“馬歇爾技術外部性”作用甚于多樣化集聚產生的“雅各布斯技術外部性”,此外,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規模產生的規模經濟效應也顯著促進了城市土地集約利用;進一步分板塊檢驗發現,生產性服務業多樣化集聚和集聚規模對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的影響呈現由東、中、東北、西部依次遞減現象,而專業化集聚對西部城市的作用強于其他3大板塊城市。
各板塊城市要注重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特點,促進其在規模較大、功能較全的中心城市聚集,通過市場一體化、信息化等手段,來加強中心城市生產性服務業的輻射能力和帶動能力。同時,統籌中心城市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和多樣化集聚產生的技術溢出效應,以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優化城市產業結構、促進人口城鎮化和空間城鎮化并進發展,為提高城市土地集約利用提供新動力。
應在保證東、中部和東北板塊中心城市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發展的同時更加注重其多樣化發展,以“人無我有,人有我專”的發展思路打造形式多元、功能齊全的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區,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西部地區則應發展與當地制造業和資源優勢相匹配的生產性服務業,重點依托其中心城市專業化的高新技術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帶動當地產業結構升級,提高城市就業吸納能力,促進人口和產業集聚進而推動城市土地集約利用。
(References):
[1] 彭沖,肖皓,韓峰. 2003—2012年中國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的空間集聚演化及分異特征研究[J] . 中國土地科學,2014,28(12):24 - 31.
[2] 韓峰,洪聯英,文映. 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推進城市化了嗎?[J] .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4,(12):3 - 21.
[3] 楚明欽. 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城市土地集約化利用[J] . 稅務與經濟,2013,(4):13 - 16.
[4] Illersis S., Philippe J. Introduction: The role of services i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J] .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1993,13(2):3 - 10.
[5] Marshall A. Principle of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Volume[M] .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61:89 - 105.
[6] Jacobs J. The Economy of Cities[M] . New York: Vintage press, 1969:45 - 62.
[7] Glaeser E., Kalial H. D., et al. Growth in cities[J]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2,100(6):1127 - 1152.
[8] Eswaran M., Kotwal A., Scheinkman J. A. The Role of Service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J] .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2,68(2):401 - 420.
[9] 鐘韻,孫建如. 中心城市生產性服務業與外圍城市制造業的互動關系——基于上海與蘇州的實證研究[J] . 經濟問題探索,2015,(4):80 - 87.
[10] Venables A. J. Equilibrium locations of vertically linked industries[J] . 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 1996,(37):341 - 359.
[11] Duranton G., Diego Puga. Micro-foundation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J] .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4,(42):1 - 14.
[12] 宣燁. 生產性服務業空間集聚與制造業效率提升——基于空間外溢效應的實證研究[J] . 財貿經濟,2012,(4):121 - 128.
[13] 韓鋒,張永慶,田家林. 生產性服務業集聚重構區域空間的驅動因素及作用路徑[J] . 工業技術經濟,2015,(7):64 - 71.
[14] Anselin, L. Spatial Econometrics: Methods and Models[M] .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8:32 - 45.
[15] Ezcurra R., Pascual, M. Rapun.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J] . Regional Studies, 2006,40(6):601 - 616.
[16] Combes P. P. Economic structure and local growth: France, 1984—1993[J] .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0,(47):329 - 355.
[17] 韓峰,王琢卓,李玉雙. 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城市經濟增長——基于湖南省地級城市面板數據分析[J] . 產業經濟研究,2011,(6):19 - 27.
[18] 廖進中,韓峰,張文靜,等. 長株潭地區城鎮化對土地利用效率的影響[J] .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0,20(2):30 - 36.
[19] York R, Rosa E. A., Dietz T. STIRPAT, Ipat and Impact: Analytic tools for unpacking the driving force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s[J] .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3,46(3):351 - 365.
[20] 候新爍,張宗益,周靖祥. 中國經濟結構的增長效應及作用路徑研究[J] . 世界經濟,2014,(5):88 - 111.
(本文責編:陳美景)
The Impacts of Productive Services Agglomeration on the Intensity of Urban Land Use from the Spatial Perspective
ZHOU You1,2, TAN Guang-rong1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9, China; 2. College of Business, Hun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05, China)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roductive services clustering on the intensity of urban land use in China from the spatial perspective, it is significant to provide suggestion for government to arrange reasonable industrial layout, to promote the conversion of urban land use, and to achiev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and land intensive use in the process of new urbanization in China. Methods of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spatial econometrics analysis were employ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it exists significant spatial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productive services agglomeration and intensive urban land use; 2)on the national level, there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s of productive services agglomeration on the intensive urban land use through the technologyspillover effect by specialized agglomeration, diversification agglomeration and the economies of scale by agglomeration scale; 3)on the regional level,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diversification agglomeration and agglomeration scale on the eastern, central, northeast and west areas present a phenomenon in descending order, moreover, the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of specialized agglomeration is more evident in the west than that in the other three regions of China.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enhancing the level of productive services clustering,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romoting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re all helpful to the intensity of urban land use in China.
land use; productive services clustering; STIRPAT model; Spatial Econometrics Analysis
F301.2
:A
:1001-8158(2016)10-0037-10
10.11994/zgtdkx.20161026.140620
2016-05-22;
2016-09-02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6BJY144);湖南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5YBA249);湖南省軟科學研究課題(2015ZK3008);湖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項目(16C0929)。
周游(1984-),男,江西撫州人,講師,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產業經濟學、城市經濟學。E-mail: 24968451@qq.com
譚光榮(1963-),男,湖南湘鄉人,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產業經濟學、城市經濟學。E-mail: 46674881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