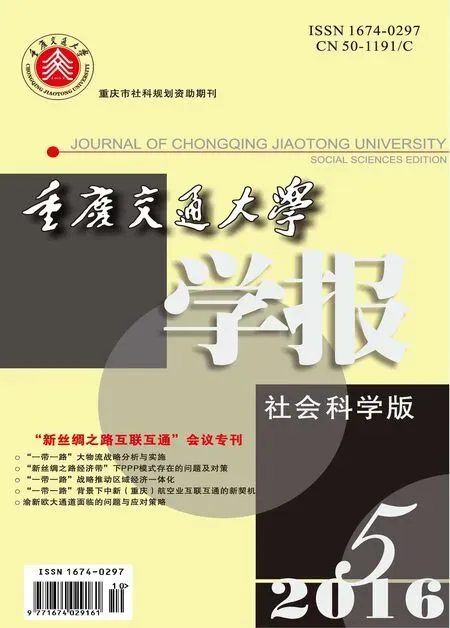中國地理學界的馬克思主義首傳及其異質性
——卡爾·魏特夫與上海“中華地學會”的思想史解蔽
龍其鑫
(中山大學 哲學系,廣州 510275)
?
·歷史文化·
中國地理學界的馬克思主義首傳及其異質性
——卡爾·魏特夫與上海“中華地學會”的思想史解蔽
龍其鑫
(中山大學 哲學系,廣州 510275)
上海中華地學會成立于20世紀30年代初,是中國首個將馬克思主義觀點引入地理學的學術團體。他們在傳播馬克思主義之中,尤其注重對德國法蘭克福學派成員卡爾·魏特夫關于地理學批判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引介,這在當時以蘇聯馬列主義為主的社會思潮中可謂是一個異質性的思想景觀,有著許多與蘇聯馬列主義不同的理論特質。對這一段思想史的解蔽,有利于彰顯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多元性與開放性。
中華地學會;地學季刊;卡爾·魏特夫;異質;馬克思主義
上世紀30年代是馬列主義系統傳入中國的重要時期,在該時期,馬克思主義也通過上海“中華地學會”(1932—1936)的引介而首次傳播至當時的地理學界。然而,這一時期所傳播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范式主要是源于蘇聯的馬列主義,故以往的研究在論述這段思想史時,較多地將中華地學會所傳播的馬克思主義與來自蘇聯的馬列主義相聯系,而極少注意到德國法蘭克福學派成員卡爾·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①及其地理學批判的馬克思主義在這段思想史中的重要影響。本文試圖對這段思想史進行解蔽,進而重新梳理與解讀相關文獻,重現近代中國(上海)地理學與馬克思主義的首次交會之本真狀況,并指出中華地學會在近代中國地理學界首傳的“地理學馬克思主義”中所蘊藏的思想異質。
一、多維際遇:中華地學會與卡爾·魏特夫的邂逅
20世紀30年代是眾多社會思潮交會于中國的重要時期,包括地理學在內的許多學術領域,亟待從中獲取自我提升的思想資源。其中,德國法蘭克福學派成員——卡爾·魏特夫的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觀點為致力于將馬克思主義引至地理學界的中華地學會所關注。當時卡爾·魏特夫的學說觀點“由日本流入中國,對中華地學會成員的學術思想產生了較大影響。后來,在論及馬克思主義的地理學著作中,魏特夫的觀點也隨處可見”[1]42。然而,中華地學會之所以引入魏特夫的地理學觀點,并非偶然的機緣巧合,而是具有多維向度的原因,涉及當時中國地理學科發展、社會思潮信仰與現實關懷等方面,是一個具有復雜層次而遞進的因素體系。
(一)學術史之維:馬克思主義發展與近代地理學轉型的時代際遇
在中華地學會成員看來,近代地理學轉型與發展需要有新的地理學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是一門嶄新而科學的地理學理論基礎,其中又以魏特夫的探索研究最為系統。“地理大發現”(Great Geographical Discovery)使近代“記述”的地理學得到極大的發展,但19世紀以來,隨著地理發現的趨減以及地理學所倚靠的自然與社會科學的迅速發展,地理學研究的基本內容與理論范式需要作出一個較大的轉型。對此,正如學會主要成員李長傅所指出的,“甚而言之,所謂記載地理學,還是地理資料,現在充其量不過年鑒,報告書的變相”[2]22。于是,近代的地理學家紛紛轉入新的研究內容,關于人與地理環境關系的“人地關系”思想成為了近代哲學世界觀和科學世界圖景的基本內容,諸如地理決定論、人地相關論與地緣學等“資產階級地理學”應運而生,其中地理環境決定論與人地相關論的影響尤為深刻。但在中華地學會主要成員看來,上述資產階級地理學具有形而上學性,并不能科學解釋“人地關系”這一地理學的基本問題。對此,學會成員李長傅指出,19世紀中葉馬克思主義誕生,確立了生產勞動的基礎觀點,給地理學界詮釋“人地關系”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理論視角。其中,普列漢諾夫、盧卡奇、考茨基、布哈林與庫諾等蘇俄或西歐的馬克思主義者已經嘗試將馬克思主義引入地理學研究中。上述馬克思主義者僅是哲學者或社會學者,而不是地理學者,在地理學界影響甚小,且具有一定的理論偏頗。與之不同,來自德國的魏特夫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成員,其研究兼具批判性與實證性,不僅對地理學研究有一定的造詣,而且系統地將馬克思主義運用到地理學中,因而“確立辯證法的地理學者,不得不推德國的威特福噶爾氏(K.A. Wittfogel)(即卡爾·魏特夫,筆者注)”[3]27。另一學會成員楚圖南也指出,具有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地理學新研究已經出現,包括普列漢諾夫、布哈林與莫希尼柯夫在內的學者已經作出探索,但是“其方法和體系的大致規定,則始于威特福噶爾的地理學批判”[4]30。
(二)社會歷史之維:“魏特夫熱”與中國地理學發展的氛圍際遇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地理空間危機迫使中國學人擯棄舊有的地理觀,而去探求一種先進與科學的地學思想,以解決近代中國的國家空間危機,即如中華地學會會刊——《地學季刊》的發刊詞所言:“發展地學;內而國計民生,外而國際狀況,俾有真切之認識。其有裨于中華之建設,固意中事也!……地學之宗旨,在于研究人地相互之關系,使吾人于世界各處之風土人情,能詳釋其因果,尋求其系統,以明今后應如何改造之途徑……同人有鑒于此,組織中華地學會,以期交換知識,發展地學。”[5]為了應對近代中國的地緣空間危機,“以明今后應如何改造之途徑”,魏特夫以“唯物史觀”研究中國歷史地理問題的思想觀點,成為了當時中華地學會所要選取的先進學說。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學界尤其是上海學界出現了翻譯和傳播馬列主義的熱潮,這段時間恰是卡爾·魏特夫與中國學者建立廣泛聯系的時期。而魏特夫的東方學說與馬克思主義又有著很深的理論淵源,于是當時中國學界刮起了一股“魏特夫熱”,包括陳翰笙、王毓銓與杜任之等左翼學者紛紛譯介他的著作,其中包括自覺引介馬克思主義的中華地學會主要成員,他們都希望從中探尋解救國家空間危機之道。學會主要成員盛敘功指出,“威特福格爾是現代德國著名者,特別對于中國問題的研究,蜚聲世界”,卡爾·魏特夫的著作“對于我國經濟與社會的結構,以唯物史觀的見解,作緊密獨到的分析。就中論生產諸條件與生產過程諸基本特征,特別置于地理的背景,與一般脫離空間關系泛論我國經濟社會問題者,顯獨具眼識。同時現在國內地理學者單記述諸自然諸要素而與社會、生產關系相分離,讀此亦可恍然大悟”[6]71。
(三)個人因素之維:中華地學會成員的研究旨趣
中華地學會之所以選取卡爾·魏特夫的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說,與盛敘功、楚圖南和李長傅三位學會主要骨干的研究旨趣有關。三位成員都是當時地理學界的知名人士,也是現當代中國地理學的奠基人與老前輩,他們的求學背景都與馬克思主義或魏特夫有著密切聯系:其一,盛敘功曾在日本留學,深受日本經濟地理學左翼學者的影響,因而盛敘功通過譯介黑正嚴與佐藤宏等左翼學者的著作,最早引介馬克思主義。魏特夫對當時日本地理學界有一定的影響,加之上世紀30年代中國學界刮起一股“魏特夫熱”,所以盛敘功對魏特夫的著作也非常關注,并翻譯了不少他的著作。其二,與盛敘功一樣,李長傅也有日本留學的經歷,他曾經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史地系學習,受到日本地理學界左翼學者的影響,由此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且越來越熱心向國內傳播。正如當時的學者方天白所言,以“唯物辯證法”解釋地理學“敢說在中國除了先生(即李長傅,筆者注)以外是沒有再適當的人了”[7];學者周宋康亦言,將“唯物史觀辯證法”應用于地理學方面,“在中國那不得不推李先生(即李長傅,筆者注)為第一人了”[8]。李長傅的理論旨趣在于推動近代地理學的理論轉型,他主張要“把歷來的地理學,放在新觀點中,重加以估價,加以批評,而給予新理論的基礎”,他所謂的“新觀點”與“新基礎”就是馬克思主義,其直接的理論來源就是“威特福噶爾氏學說”[9]。其三,楚圖南早在20年代就開始跟隨李大釗研習馬克思主義,且翻譯“十月革命”、馬克思主義有關的書籍,后于1922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并在李大釗的指導下編輯小報《勞動文化》以宣傳馬克思主義。楚圖南一直致力于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工作,中華地學會與《地學季刊》就是他在上世紀30年代向地理學界引介馬克思主義的平臺。在三位成員中,楚圖南最早引介魏特夫的學說觀點[1]34-46。
二、在引介中內化:對“地理學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與深化
中華地學會對卡爾·魏特夫的“地理學馬克思主義”引介工作主要由盛敘功、楚圖南與李長傅三位學會成員負責。雖然三位學會成員的分工不盡相同,但是他們對卡爾·魏特夫思想觀點的認同與關注卻是一致的,且都有一個由淺入深、由表及里的深化研究進程。三位成員分工合作,分別從譯介、闡釋與深化等方面研究卡爾·魏特夫的“地理學馬克思主義”。
(一)盛敘功對卡爾·魏特夫關于中國問題研究的譯介工作
20世紀30年代是魏特夫與中國學者密切聯系的時期。尤其是在1935年,魏特夫的著作及其觀點得到了廣泛傳播。當時中國學界紛紛著手翻譯魏特夫的著作,其中包括《中國之經濟與社會》(《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今譯名為《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盛敘功翻譯了該書的部分章節,并發表在會刊《地學季刊》上,如《中國農地的灌溉問題》(《地學季刊》1935年第2卷第2期)、《中國的治水事業與水利工事》(《地學季刊》1935年第 2卷第 4期)就是翻譯自《中國之經濟與社會》的第2篇第2章第1節。
盛敘功翻譯的《中國農地的灌溉問題》主要涉及魏特夫將馬克思“亞細亞生產方式”觀點對中國歷史地理問題研究的運用,即中國傳統農業生產對水源與水利條件十分倚重,所以農業經營建基于“人工灌溉”之上,“依據馬克思的意見,亞細亞式的社會型式是置其基礎于人工灌溉上的,同時也就是其支配的生產部門農業的存在所筑。人工灌溉原來是一種基本條件,而在東方,則為農業上必須的條件”[6]71。人工灌溉事業還決定了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國家的社會政治結構。由于歷代中國社會都必須建立基于治水事業之上的公共機關,以及設置相應的官職以從事具體的治水工作,從而產生了一個龐大的官僚階級,例如專司天象事務的官員、主導治水工事的土木建設部門即六部中的工部。中國社會需要有一個龐大的官僚階級,“據馬克思恩格爾的意解,這種司掌治水水利事務的職官,在‘亞細亞式’專制支配政治物質基礎的構成是具有重要的作用的”[10]69,官民對立是一以貫之的。而在盛敘功翻譯的《中國的治水事業與水利工事》一文中,則包含了魏特夫對中國古代政治的看法。魏特夫認為,包括印度與中國在內的東方國家都是國家的、地方的與私人的水利工事相共存的,但是大規模的水利工事依然是主導型基礎,所以“由農業社會的基礎之置于其大規模的灌溉以及排水事業上看來,亦足以表示‘亞細亞式’的特性”[10]68。
盛敘功在《地學季刊》上刊發的《中國農地的灌溉問題》《中國的治水事業與水利工事》是對魏特夫《中國之經濟與社會》部分章節的翻譯,是魏特夫運用馬克思“亞細亞生產方式”觀點最為集中的部分。盛敘功本人也意識到魏特夫的《中國之經濟與社會》“對于我國經濟與社會的結構,以唯物史觀的見解,作精密獨到的分析……同時現在國內地理學者單記述諸自然諸要素而與社會,生產關系相分離,讀此亦可恍然大悟”[6]76。可以看出,盛敘功不但與當時其他中國學者一樣想從魏特夫的著作觀點中尋找理解中國社會經濟的途徑,而且對以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去理解中國經濟地理寄予很大的希望。
(二)楚圖南對卡爾·魏特夫關于“勞動過程”觀點的引介
1935年6月,楚圖南在《地學季刊》第2卷第1期中發表《人文地理學之發達及其流派》一文,闡明了自己將馬克思主義與地理學相結合的理論旨趣。他指出:“關于Karl.M.譯作嘉爾(即卡爾·馬克思,筆者注),Materialism 譯作物質主義……對于地理學的新見解,新的觀察,并且也給與了新的方法,規定了新的原則。這卻是地理學的一大變動。雖說著者不一定是地理學家,但這沒有多少大關系。”[4]18
在《人文地理學之發達及其流派》一文中,楚圖南詳細梳理了人文地理學的思想脈絡,以引出“新社會派的人文地理學”派別并進行了介紹。楚圖南認為,這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的人文地理學派別,但是自己“一時想不到妥當的稱謂,暫且就用著新社會這個名稱”[4]30。楚圖南認為,雖然魏特夫與普列漢諾夫、莫希尼柯夫一樣都是“新社會派的人文地理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該學派的理論成體系地體現于魏特夫的《地緣政治學,地理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一文之中②。根據文中所述,卡爾·魏特夫之所以能夠得到楚圖南的推崇,就在于魏特夫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觀點——勞動過程:近代地理學在分析自然與社會的關系上,往往“省略了中間項”,“將勞動過程脫落了”,“將自然環境給予過多的評價,忽略了勞動的及經濟的領域內的意義”[4]31-32,地理現象變遷的決定因素并不是自然,而是經濟領域的勞動過程。
(三)李長傅對卡爾·魏特夫關于自然與社會“主客關系”批判觀點的深化
1935年6月,李長傅先生在《地學季刊》第2卷第1期發表的第一篇含有馬克思主義觀點的論文——《地理學研究的新階段》,是對魏特夫《地緣政治學,地理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一文的介紹與解讀。李長傅在該文中主要闡釋魏特夫關于“人地關系”批判觀點:近代資本主義工業化與自然科學的發展決定了近代地理學必然以舊唯物論為理論基礎,而百科全書派、愛爾維修、費爾巴哈與孟德斯鳩的“人地關系”思想都屬于“地理的唯物論”(Geogaphischer Materialismus),主要以地理決定論、人地相關論與地緣學等為基本范式,并指出他們都忽視了馬克思主義的勞動過程觀點的中介作用。與楚圖南一樣,李長傅對勞動過程這一觀點的闡釋,為他們以后研究的進一步深化奠定了理論基礎。
1935年6月,李長傅又在《地學季刊》第2卷第3期發表《地理學研究的新階段(續)》《科學的地理學之新轉向》兩篇論文,以卡爾·魏特夫的理論觀點為批判視域,對地理學思想史進行梳理,重點批判了地理環境決定論與人地相關論,并評判了考茨基、盧卡奇、普列漢諾夫等馬克思主義者的地理學觀點,指出他們的觀點存在唯心主義或舊唯物主義的傾向。此外,李長傅還將自己在《地學季刊》中的譯著以及運用卡爾·魏特夫學說觀點而論述地理學理論的論文編纂成一本論著——《轉形期的地理學》,并于1935年在上海三五書房編印發行。《轉形期的地理學》可以說是李長傅在中華地學會時期的集大成之作,該書的理論基礎主要來源于卡爾·魏特夫的馬克思主義地理學批判思想,對當時地理學理論格局頗有批判鋒芒。在魏特夫的理論啟示下,李長傅又在1936年3月于《地學季刊》第2卷第4期寫作《轉形期的地理學淺釋》一文。在該文中,李長傅理清了唯物史觀的歷史動力問題,指出歷史發展的動力不在于單一的自然或人類,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才是歷史發展的“主動力”[2]25-26。
1936年3月,李長傅在《地學季刊》第2卷第4期中發表了《自然環境之真義》一文。在此文中,李長傅重述了魏特夫主要的地理學批判觀點,尤其是闡釋了魏特夫所言的“歷史的自然”內涵,而自然的真義應該是魏特夫揭示的“歷史的自然”,其基本特征是具體的社會歷史特性。因此,“人地關系”即人(社會)與自然的關系應當是自然以勞動過程為媒介,才與人類社會發生作用,“人類社會生活之發展過程與其相關聯中,自然成為不斷的變化的東西而出現了,這才是最具體的自然”[11]13。
三、比較的異質性:中華地學會“地理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特質
中華地學會首傳至當時地理學界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以卡爾·魏特夫的“地理學馬克思主義”為載體,具有一定的西方左翼“批判理論”色彩,這在當時以蘇聯馬列主義為主流的理論界中是一個很具有異質性的思想景觀。具體而言,主要體現在經典權威、本體論、歷史唯物論與中國社會性質等問題上,二者之間有著較為明顯的理論差異。
(一)地理學界批判話語中的馬克思主義經典權威
20世紀30年代,中國理論工作者翻譯了大量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也翻譯出版了來自蘇聯理論界的馬列主義哲學著作。在此過程中,他們以蘇聯范式的馬列主義為基本視域,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與斯大林等為經典權威,而且普列漢諾夫、考茨基、布哈林與德波林等的哲學著作也被視為馬列主義權威。然而,在中華地學會的“地理學馬克思主義”視域中,馬克思主義思想譜系顯出另一種圖景,與蘇聯馬列主義有著明顯的差異,且隱藏著對后者的批判性。
其一,雖然雙方都認同馬克思與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但是中華地學會成員還認為馬克思與恩格斯是“新社會派的人文地理學”或“科學的地理學”的理論奠基人。如楚圖南就指出:“關于Karl.M.譯作嘉爾……對于地理學的新見解,新的觀察,并且也給與了新的方法,規定了新的原則。這卻是地理學的一大變動。”[4]18“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也正是一部良好的,精辟的,地理哲學書。”[12]其二,與蘇聯馬列主義以及當時中國馬列主義學界極其重視列寧、斯大林的思想理論不同,在魏特夫的敘述影響下,中華地學會成員對列寧和斯大林的理論觀點甚少提及。在中華地學會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譜系之中,列寧與斯大林可謂是“缺席”的。其三,除了盧卡奇之外,如考茨基、德波林與普列漢諾夫等人都曾被蘇聯馬列主義以及當時中國馬列主義學界視為理論權威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中華地學會的馬克思主義視域中,他們卻有著理論上的偏頗:一是他們的理論具有唯心主義傾向。如盧卡奇在論述社會與自然之相互關系時偏于社會一側,“以為自然只是‘社會化的范疇’”,而“柯茨基(即考茨基,筆者注)本來主張地理環境論的,但是他晚年的著作趨向于技術論”[3]27,“太強調了能動的活動的契機,而蔑視了實際的自然的側面”[13]14,所以盧卡奇與考茨基都有演變為唯心主義觀念論的危險。二是他們的理論具有形而上學性。典型者如普列漢諾夫,他太強調自然而蔑視社會,以至于“地理的環境之性質,制約生產力之發展,生產力之發展,制約著其它隨同發展的社會關系之發達……蒲氏(即普列漢諾夫,筆者注)之說是地理環境論者,因為他受拉塞爾影響之故”。其三,他們的理論具有二元性,最后又不得不滑向一側。如布哈林是自然與社會二元的均衡論者,但是他論及“社會與自然之均衡”時則偏重于自然;此外,庫諾強調人與自然相互影響,但是他又“由自然偏重說而趨向記述偏重說”[3]26。
(二)對物質(自然)一元論的否棄
資料顯示,2007年,韓、杜二人南下,以2000萬元拿下了常州延申90%的股份,將其改組成為江蘇延申,韓剛君擔任董事長。兩年后,延申生物涉偽劣狂犬疫苗案,次年被懲處,總經理被判刑,董事長韓剛君毫發未傷。
20世紀30年代以后,蘇聯的馬列主義辯證唯物論對中國理論界的影響越來越大,很多理論研究者紛紛加入唯物論與辯證法的研究之中。在當時的理論認識中,辯證唯物論與舊唯物論都以“物質(自然)一元論”為基礎,如當時研究辯證唯物論的學者吳亮平認為,辯證唯物論與舊唯物論在本體基礎上是一脈相承的,都以自然—物質為第一性,而“辯證法的方法,被應用唯物論的基礎之上,這樣就形成了新的唯一的科學的宇宙觀——辯證唯物論”[14]。另外,當時著名的馬列主義學者張如心也認為,辯證唯物論與舊唯物論都以物質為第一性,辯證唯物論就是馬克思對黑格爾辯證法與費爾巴哈唯物論的綜合[15],因而他也對舊唯物論頗有贊譽。然而,與當時主流的辯證唯物論不同,在魏特夫的理論影響下,中華地學會成員對物質(自然)一元論持較為徹底的批判態度,如李長傅指出,近代地理學以舊唯物主義為基礎,其本體論偏重于自然,是為地理學唯物論的自然本體論,但是該自然本體只不過是“廣義的,空漠的自然而已”,離卻了人類主體,因而是一種空洞而無規定性的形而上學概念[16]12。此外,李長傅還指出,近代的舊唯物論深受自然科學的影響,因而其對自然的認識帶有一定的形而上學性,“自然,并不是如自然科學者所謂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活動的東西。如海洋在原始社會,有‘水之沙漠’之稱,自十五世紀世界發現之后,轉變為世界的交通路了。所以威特福噶爾曾予以‘歷史的自然’之名”[2]26。質言之,中華地學會成員主張不存在抽象的自然物質,而僅存在經過勞動過程中介的“歷史的自然”,即“人類社會生活之發展過程與其相關聯中,自然成為不斷的變化的東西而出現了,這才是最具體的自然”[11]13,也才是人類社會相與對待的客體。因此,中華地學會對舊唯物主義自然本體的非保留性批判,實質上是對物質(自然)一元論觀點的徹底否棄,這與肯定與繼承舊唯物論物質第一性的馬列主義辯證唯物論有著明顯差異。
(三)歷史唯物論的新輪廓:地理學史觀及其時空耦合性
在蘇聯馬列主義中,自然在邏輯上先于社會,歷史唯物論的理論“輪廓”一般被描述為唯物辯證法—自然辯證法在社會歷史領域的“擴張”,如李達在其《社會學大綱》中有言:“所謂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關聯,這句話的本來的意義,就是徹底地把辯證唯物論應用并擴張于歷史的領域。”[17]然而與蘇聯馬列主義的“擴張論”不同,中華地學會成員認同的是魏特夫的地理學史觀,并不認可社會是自然的擴張領域,抽象的自然及其規律也并非是社會歷史的基底,因為勞動過程是自然與社會二者的基底,自然需要通過勞動過程的中介才與社會發生相互作用,“自然的諸力乃至自然的諸物質,在人類之社會的勞動過程之中,即勞動力的,或勞動對象的,或勞動手段的所構成要素之發見。依此經過特定之社會生產力形成之條件,而成歷史發展之基礎”[16]128。即是說,勞動過程才具第一性,自然與社會二者共時性地相互作用于勞動過程的基礎之上。只有通過勞動過程的中介作用,才能使自然獲得社會歷史特性,自然的地理與社會的歷史才得以實現辯證統一,使歷史唯物論獲得了一定的時空耦合性:第一,歷史的辯證動態性得以立足于地理的唯物主義基礎,從而“對抗所有一切非現實的或超現實的歷史觀”[16]114,避免了墜入歷史唯心主義觀念論。第二,地理的唯物主義獲得了歷史學的辯證動態性,使其得以擯棄形而上學性,從而不再把自然看作是“游離孤立的東西”或“對于人類為外力而支配人類,人類認定為不能動的物質”,又或“將自然或物質視為靜止的東西,死的東西,不動的東西”[16]116。質言之,勞動過程的中介作用使歷史唯物論獲得了時空耦合性,型構了地理學史觀的新輪廓。
(四)“亞細亞”概念的傳播及其潛藏的社會理念張力
上世紀30年代,中國學界展開了一場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在此之間,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觀點得以出場。然而,當時大部分中共人士與左翼學者接受的是斯大林的社會形態五階段論,并深受其影響,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概念“比較沉默”,“基本上傾向于拒絕這一概念的有效性”[18],并且他們在中國社會性質的討論中基本上以斯大林的判斷為準,進而指認中國社會的革命方向。與之相反,魏特夫對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觀點頗為倚重,論述指出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國家就是亞細亞式的“灌溉社會”。受魏特夫的理論影響,中華地學會的成員與當時主流的馬列主義學界不同,他們對亞細亞問題關注有加,且甚為認同,還通過中華地學會的會刊《地學季刊》向當時地理學界傳播與介紹“灌溉社會”觀點。李長傅曾在其文章中指出:“威氏不但為德國的唯物史觀的地理學者,且為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其所著中國經濟與社會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是用唯物辯證法研究中國之白眉。”[13]16在魏特夫的思想影響下,另一成員盛敘功認為,“據馬克思的意見,在東方文化發展的階段上,此種灌溉水利事業問題,因為土地面積在實現自然發生的統一上,太過于廣大之故,其結果,就會引起中央集權化的政府權力的干與”[10]65,即灌溉水利事業使東方國家具有集權專制的社會強結構性。這與列寧、斯大林主張東方國家可通過社會主義革命,以變革與重構社會結構而實現發展的理論觀點是相悖的③。質言之,雖然魏特夫與列寧、斯大林都關注東方國家的社會發展問題,但是他們的認識有著一定的距離,后者認為東方國家的社會性質使其具有革命任務,正處于社會變革的歷史趨勢之中,社會主義革命可以重構東方國家的社會結構;前者則堅持東方國家是所謂的灌溉社會,具有政治集權的社會強結構性,對社會革命及其歷史期待結果具有潛在的銷蝕性,因而魏特夫的灌溉社會觀點對社會革命的取向具有抵牾作用。中華地學會成員不以蘇聯馬列主義為師,不以蘊含革命觀點的“社會形態五階段論”去理解中國社會,而是以魏特夫的灌溉社會觀點去指認中國社會集權的強結構性。無論他們是否意識到此二者之間的政治理念張力,對于當時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的中國馬列主義學界而言,都是一個異質的思想景觀。
四、余論
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蘇聯范式的馬列主義以其“正統”的理論形式向自然、社會與人文科學等領域傳播,并逐漸確立起其思想主導的地位,包括地理學在內的中國自然科學界基本都以自然辯證法—辯證唯物論作為自己學科的指導思想。在人們眼中,近代中國地理學所傳入的馬克思主義初始形態近乎等同于當時主流的蘇聯馬列主義。然而,以盛敘功、楚圖南與李長傅為代表的中華地學會成員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經過爬羅剔抉,主要選取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成員魏特夫的學說觀點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而不是當時炙手可熱的蘇聯馬列主義,這在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傳播潮流中可謂是一個“異質”的思想景觀。因此,在思想史的功能性視域中,對于當時主流的蘇聯馬列主義理論界而言,中華地學會是一個“弱互補性”與“潛批判性”的存在。
此外,正是通過引進魏特夫的思想理論,中華地學會為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輸入了蘊含部分西方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思想“異質”。在一系列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問題中,中華地學會的論述話語都與當時主流的蘇聯馬列主義存在著許多不一致性,尤其體現于對馬克思主義思想譜系的批判性敘述,對物質(自然)一元論的否棄,對歷史唯物論“輪廓”的地理學改造,以及對“亞細亞生產方式”觀點的贊同等,以上這些理論特質都具有一定的西方左翼批判理論的思想色彩。一方面,盡管這或許是中華地學會不自覺的引介,但是至少在地理學領域中是魏特夫的馬克思主義,而非蘇聯的馬列主義,首先開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歷程。另一方面,雖然相較于李達、艾思奇與沈志遠等馬列主義著名學者,以盛敘功、楚圖南與李長傅為代表的中華地學會成員在馬列主義學界并非赫赫有名,但是他們都是當時地理學界的知名人士,也是現當代中國地理學的奠基人與老前輩。他們懷著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信奉,向當時處于轉型與形成期的中國地理學傳入馬克思主義,且尤為注重魏特夫的學說,這是對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工作的一大貢獻,而這一思想景觀在以往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史幾乎是屏蔽的。對這一異質性的思想景觀的解蔽,重現的是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中別具一格的思想境況。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正因為這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地理學界的首次傳播,傳播過程中又以魏特夫的思想觀點為主,所以這不僅使中華地學會成為近代中國地理學界中獨樹一幟的學術團體,而且使這次傳播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別具一格的一段。對這一異質性的思想景觀的重現與解蔽,不僅可以恢復馬克思主義傳播工作在地理學領域的歷史在場,而且佐證了一個思想史實: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并非是一元的單線歷程,而是一個多支流匯聚的多元思想體系,中國馬克思主義從來都是一個多元與開放的理論體系。
注釋:
①卡爾·魏特夫,猶太人,原籍德國,美國漢學家。先后在萊比錫、柏林、法蘭克福等大學攻讀社會經濟史,1928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25年入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成為該所核心成員。1920年加入德國共產黨,后任德共中央委員。1933年被納粹投入集中營,不久出獄,移居美國。1935—1937年來華,搜集有關中國社會經濟史資料。1939年與共產主義運動決裂,入美國籍。他曾在多所大學任教,為美國太平洋學會會員、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歷史編纂處”主任、華盛頓大學中國史教授。參見:李孝遷.魏特夫與近代中國學術界[J].人文雜志,2010(6):121-129.
②中譯名參見:魏特夫.東方專制主義[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1957年導論第17頁;德文為Geopolitik , Geogaphischer Materialismus und Marxisimus,載于1929年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mus. 1929, Vol. 111, nos. 1, 4, 5. 魏特夫于1971年以書的形式出版;日文版主要有佐藤宏譯本與川西正鑒譯本,皆取名為《地理學批判》。最早的中譯本是沈因明以川西正鑒譯本為原文而翻譯的,亦取名為《地理學批判》,于1935年2月由上海辛墾書店出版;李長傅對此文進行了解讀,取名為《地理學研究的新階段》,收入其專著《轉形期的地理學》,并于1935年7月由上海三五書房出版。
③對此,卡爾·魏特夫在《東方專制主義》一書中有自己的解釋,并判定“蘇聯對亞細亞概念的逐漸拋棄,在1938年以斯大林對于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著名提法的修正達到了頂點,而這在邏輯上也正是列寧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前夕放棄亞細亞概念的必然結果”,“1932年,蘇聯有人批評我所著的《中國的經濟和社會》,斥責我對科學的科學性的信仰。也正是在這個時候,蘇聯的出版機構不再印刷我的關于分析亞細亞社會、特別是關于分析中國社會的論著”。參見:魏特夫.東方專制主義[M].徐式谷,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導論17-18.
[1]劉寅春.中國首倡馬克思主義的地理學學術團體:中華地學會[J].中國科技史雜志,2012,33(1).
[2]李長傅.轉形期的地理學淺釋[J].地學季刊,1936,2(4).
[3]李長傅.科學的地理學之新轉向[J].地學季刊,1935,2(3).
[4]楚圖南.人文地理學之發達及其流派[J].地學季刊,1935,2(1).
[5]發刊詞[J].地學季刊,1932,1(1):2.
[6]魏特夫.中國農地的灌溉問題[J].盛敘功,譯.地學季刊,1935,2(2).
[7]李長傅.方序[M]//轉形期的地理學.上海:三五書房,1935:2.
[8]李長傅.周序[M]//轉形期的地理學.上海:三五書房,1935:1-2.
[9]李長傅.自序[M]//轉形期的地理學.上海:三五書房,1935:1.
[10]魏特夫.中國的治水事業與水利工事[J].盛敘功,譯.地學季刊,1936,2(4).
[11]李長傅.自然環境之真義[J].地學季刊,1936,2(4).
[12]楚圖南.中國歷史地理學發凡[J].地學季刊,1935,2(3):58.
[13]李長傅.地理學研究的新階段[J].地學季刊,1935,2(1).
[14]吳亮平.辯證唯物論與唯物史觀[M].上海:心弦書店,1932:56.
[15]張如心.辯證法與唯物論[M].上海:光華書局,1932:2.
[16]李長傅.轉形期的地理學[M].上海:三五書房,1935.
[17]李達.社會學大綱[M].上海:筆耕書店,1938:388.
[18]德里克.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1919-1937[M].翁賀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156.
(責任編輯:張璠)
First Spreading of Marxism with Heterogeneity in China’s Geography Profession Intellectual History’s Uncovering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and Chinese Geography Association
LONG Qixi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In China, Chinese Geography Association was the first academic group to introduce Marxism into geography research. They especially pay attention to Marxist view of criticism about geography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who is the member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in Germany. In the socialist trend focusing on the Soviet Union’s Marxism and Leninism, Chinese Geographic Association is a landscape heterogeneity of thought. So uncovering the history of ideas is conductive to enrich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arxist propagation, and show the diversity and openness of early Chinese Marxism.
Chinese Geography Association; The Geography Quarterly; Karl August Wittfogel; heterogeneity; Marxism
2016-03-15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延安學術文化組織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16DBJ006);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延安紅色文藝與中國共產黨形象塑造研究”(16CDJ007)
龍其鑫(1988—),男,中山大學哲學系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國馬克思主義解釋史。
D630
A
1674-0297(2016)05-009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