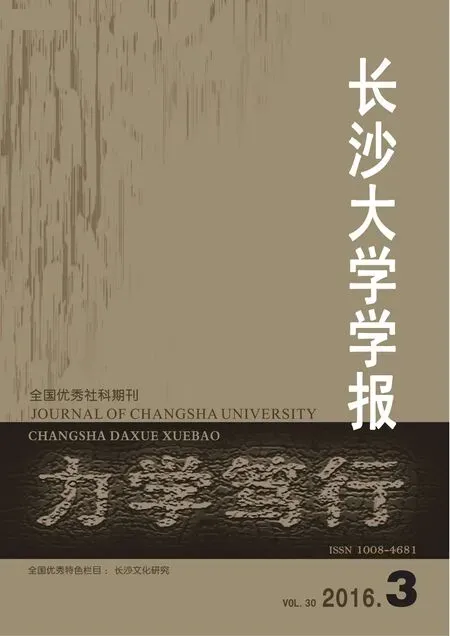集體談判制度的發展困境及完善
劉志玲
(中共馬鞍山市委黨校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教研室,安徽 馬鞍山 243000)
?
集體談判制度的發展困境及完善
劉志玲
(中共馬鞍山市委黨校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教研室,安徽 馬鞍山 243000)
摘要:集體談判制度是解決勞資矛盾的一種有效方式,在我國尚處于起步階段。一方面,勞方未形成集體化力量維權,另一方面,資方的過于強勢和政府的強力控制又制約了集體談判制度在我國的發展。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完善:建立多層次的集體談判制度、健全相關法律、擺正政府角色、培養專業人才。
關鍵詞:集體談判;勞資關系;困境
隨著市場經濟和工業化的推進,勞資糾紛大量爆發,呈逐年上升趨勢,涉及的當事人越來越多,勞資矛盾日益凸顯。甚至還引發激烈的群體性事件。當前勞資關系已經成為社會基本關系之一,勞資矛盾成為國家工業化過程中無法回避的矛盾,如何協調勞資關系、化解勞資矛盾成為一個亟需解決的問題,集體談判作為西方比較成熟的化解勞資矛盾的制度化方法進入人們視線。
集體談判最早起源于英國,英國工業革命后,經濟快速增長,勞動者的生活狀況卻在不斷惡化,為了形成力量與資本家對抗,英國勞動者組成工會,在19世紀初出現了最早的集體談判。從西方集體談判制度的發展過程看,集體談判的發展總與工業化聯系在一起,已經被看作是“民主社會的必要組成部分”和“處理公共部門中勞資關系的正常手段”[1]。本文采用國際勞工組織對集體談判的定義:雇主或雇主團體組織為一方,勞動者組織為另一方,為確定工作條件調整工作關系所進行的所有談判(ILO,1981)[2],集體談判的最終結果是形成集體合同。
一集體談判制度在我國的發展及困境
以往我國在處理勞資矛盾中,更多地是用“協商”一詞,“協商”詞性較為溫和,符合維護、和諧勞資關系的本意。20世紀90年代,我國引入集體協商制度,1994年的《勞動法》中對集體協商制度做出了規定,后在1996年正式確定了三方協商制度。隨后在全國各地企業中推廣三方協商制度以協調勞資關系。目前已有30多個省市自治區建立了省級三方協商機制,全國已建立三方協商組織1萬多個。對比“協商”,“談判”一詞詞性顯得更為尖銳,更多地強調勞資雙方存在的沖突。但是如果說協商一詞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初期對于穩定的強調,那么在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在勞資矛盾日益顯化和激化的時代,略帶對抗性質的“談判”一詞可能比“協商”一詞更適合當前的社會背景。總體而言,集體談判在我國尚處于起步階段,機制尚未完全建立,在協調勞資關系、化解勞資矛盾方面還未能發揮真正作用,在我國的發展還面臨諸多困境。其困境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
(一)來自勞方
一是未形成集體制度化的力量維權。中國勞動者中有個龐大的特殊群體——農民工,目前我國農民勞動者數達到1.3億人,這部分人規模最大,變動程度也大。農民工為城市建設做出巨大貢獻,在勞動維權上卻完全處于弱勢地位,由于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未能簽訂正規勞動合同等原因,在勞動爭議方面他們更加訴求無門,更談不上以制度化的方式維權。不過,目前勞動者維權意識正逐步增強,正通過各種方式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但是多以個體化的分散力量去對抗強大的利益集團,個人勞動爭議高于集體勞動爭議,從1996年到2008年的13年間,集體勞動爭議占當期受理案件數比例一直較低,平均僅為5.7%,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勞動者申訴案件占很大比重,從1996年到2008年年均高達93.22%[3]。這些一方面反映了當前勞動者的組織化程度較低,勞動者組織在維護勞動者利益方面的缺位,另一方面也顯示在當前的社會轉型期,發展不平衡所導致的利益訴求焦點不一致,以及勞動者之間由于利益訴求點不一致所導致的未形成一致的利益集團。二是“權利爭議”為主使得勞動爭議易表現出較強的對抗性。當前的勞動爭議更多地圍繞著勞動者的基本權利,比如未履行勞動合同、未買保險等內容,這些都是法律所給予勞動者最基本的、最低層次的、應該享有的勞動利益。據統計,從2001年到2009年,由勞動報酬和社會保險所引發的勞動爭議占到當年勞動爭議案件的半數以上。不同于西方的勞動爭議多集中于利益爭議,我國勞動爭議不是在基本權益得到滿足后對于更高權益的爭取,而是基本權利的抗爭,關乎勞動者的生存,因而往往時不時表現出較強的對抗性,表現形式較為激烈。三是缺乏來自勞動者利益的推動。有著百年多歷史的西方集體談判制度是在勞動者利益訴求的需要下應運而生的,是作為與資方進行工資條件和工資報酬的協商制度而存在,而中國的集體談判帶有較重的官辦色彩,最初在中國的集體談判制度也是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導在企業當中推行。在此過程中,缺乏來自勞動者利益的主動推動,也是使得集體談判流于形式的一個重要原因。四是工會缺乏獨立性。工會即工人聯合會,這一社會組織成立的意圖是形成組織代表勞動者利益與資方進行就勞動條件及報酬等的談判,但傳統上的工會地位一直較為尷尬,在很多勞動者的實際生活中,工會的作用只限于組織業余活動、發放勞保用品。很多企業的工會由資方直接任命,或是政府指派,不能真正做到完全獨立的代表勞動者利益,導致勞動者對工會是否真正代表勞動者利益持懷疑態度,并不將工會視為維護勞動權益及聯系資方的基本組織,更談不上依靠工會進行勞動報酬和勞動條件等事項的談判。遇到重大勞資事項如薪酬增減、保險福利等問題,工會更難以發揮作用,不能取得實質性效果。
(二)來自資方
我國市場長期表現為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狀況,以往勞資關系形成“強資本,弱勞動”的關系格局,資本處于絕對強勢,勞動者處于絕對弱勢地位,在勞資關系中很多時候資方未把勞方作為一個平等體看待,對于勞方更多表現為權力與控制,強調命令與服從,不允許也不接受勞方與資方談判。隨著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勞動要素在生產要素中的地位逐步凸顯。原本的“強資本,弱勞動”格局在發生著變化,勞動者在勞資關系中的主動性越來越明顯,權利意識越來越強,利益訴求愿望也愈發明顯,這時的關鍵是引導勞動者以一種制度化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利益訴求,而不是漠視甚至無視他們的訴求。此時,一個獨立意義上能真正代表勞動者利益的工會至關重要,如果資方還是對獨立意義的工會不抱歡迎態度,就會使得勞動者在表達自己利益訴求時,直接跳過集體談判階段,進入到實施罷工階段,沒有經過談判就直接罷工往往會給勞資雙方帶來較大損失,一方面貿然罷工會導致資方因生產中斷而損失慘重,另一方面一些帶頭的勞動者也有被辭退的風險[4]。
此外,我國實行的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因而在我國,企業具有多層次多類別的特點,既有國有企業,又有私營企業,還有外資企業、合資企業等的存在,國企的改制、私企的規模不一、外資企業的參差不齊等都會影響到集體談判制度在行業內的推進。
(三)來自政府
在我國集體談判制度的發展過程中,政府的控制力較強,政府主導傾向明顯。誠然在勞資矛盾爆發的時代背景中,解決勞資矛盾需要政府的主動介入,這也是世界發展歷史所表明了的,如美國和歐洲的一些國家,在二戰初期集體談判制度的建立發展過程中政府就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在我國的集體談判發展過程中,政府的影響力可說是無處不在,如,行政任命工會領導、官方推動集體談判推進、下達任務指標等。政府強大的社會控制力在某個階段是必要的,也能取得一定的積極效果,但是再往后發展反而會成為一種束縛。政府的強力干預隨著制度的發展會限制勞方力量的成長,讓勞方形成依賴心理,事事找政府亦會加重政府負擔。
另外,在改革發展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我國將發展中心放在經濟上,急于追求GDP,對于資本有著大量的需求,地方政府為了經濟發展效益,在本就有著強弱差別的勞資關系中,仍在一定程度上偏向資方,違背了社會公平原則,也造成資方在做出違規行為時較少考慮社會后果。
二我國集體談判制度的完善措施
(一)建立多層次的談判體系
當前對于集體談判制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一企業資方與勞方之間,要將集體談判放在宏觀背景下看。基于當前中國很多私營企業規模小,自身發展尚不健全,工會力量薄弱,或是形同虛設,參照外國集體談判制度經驗,可實行多層次談判,除了企業內部之間,在行業與國家層次上也應建立起集體談判級別。如果一個國家的集體談判多集中在國家及行業層次,被稱之為集權化的談判,若多集中在企業層次的集體談判,則被視為分散化的談判。西方大多數國家如英、法、芬蘭等國家的集體談判多為獨立于企業之外的行業談判,雖有一些國家如英國是在企業或公司層次進行集體談判,但他們是經過集權化的談判之后再發展到較為分散的談判,與我國還未經過集權化談判階段的情況不盡相同。因而,可以推廣建立在行業協會工會基礎上的行業級別的談判,這樣一種多層次的集體談判體系的建立在我國能發揮彌補小企業工會力量不足的作用。
(二)健全相關法律制度
我國法律最早在1994年的《勞動法》第三十三條中就有關于集體談判的規定:“企業職工一方與企業可以就勞動報酬、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士、保險福利等事項,簽訂集體合同”。但這一規定過于籠統,缺乏可操作性,且缺少強硬性,對于實踐中勞資雙方是否簽訂集體合同更多地強調自愿而非強制性。此后也出臺了相關的通知和意見來推行集體談判制度,但是也未能明確尤其是對于不簽訂集體合同的法律上的強制懲罰。要使集體談判以法律為強大后盾,真正做到有法可依,首先要提高關于集體談判的立法層次。我國目前沒有專門的集體合同法,最高層次只是2004年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集體合同規定》,僅僅是一部部門規章,更勿論其他法律條文中的一些零星規定,因而制定一部高層次的專門法律是當務之急。同時,應在法律規定中明確規定具體事項,加大操作性,不宜使用自愿意味濃厚的“可以”等詞,而應使用一些帶有法律強硬色彩的“必須”等詞,對于不按法律操作的懲罰措施也應界定清楚。此外,應就與集體談判相關的一些事項,如罷工原則、程序和相關的職責義務等做出規定。健全的法律才能保障制度有效的運行,涉及集體談判中的一個重要法律條文內容就是要承認和維護勞動者的罷工權,若勞動者未獲得合法權益,在集體談判未取得一致前提下勞動者可以通過罷工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這是集體談判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前我國法律中對于罷工是采取既不支持也不反對的態度[5]。在當前中國,罷工現象已經出現,在多數情況下,勞動者們的罷工會傾向于一種比較溫和的方式,甚至有的地方用“休息”來替代罷工這一較為敏感的字眼。其實,罷工是一種經濟手段,是調節勞資關系的一種方式,無需談之色變,從長遠中國勞資關系的發展看,罷工權利的正常化、正當化是必然趨勢,這樣才能更好地發揮集體談判的作用。
(三)擺正政府角色地位
一般來說,在工業化加快發展,勞資矛盾比較集中爆發的時期,對于勞資矛盾的解決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國家的立法立規,二是勞方的自我團結。兩種方式不同時并重,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家也有所側重,主要取決于各國具體的政治經濟環境[6]。我國長期的計劃經濟時代背景和傳統的全能型政府角色地位使得在改革開放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都是政府推動勞資關系的規制與監管,隨著市場要素的發展與成熟,政府的角色地位要逐漸適應現階段及未來的發展要求,在勞資關系的集體談判中角色應側重于輔助協商,糾正不規范行為。政府在集體談判中的主要任務應該是在輔助協商的基礎上,在勞資雙方中扮演利益協調者,維持兩者之間的利益均衡,找到雙方利益的平衡點。在集體談判階段,一般來說,勞資雙方的利益都是合法的,都是需要保護的,而雙方之間如果未形成一致的利益點,就需要政府引導勞資雙方,尤其是勞方盡快形成獨立性力量,增強其集體談判能力。集體談判就是要勞資雙方協商自治,尋求共識,使雙方的意愿訴求在談判中得到真實表達,勞資雙方和諧勞動關系的確立最終是建立在雙方自覺自愿的合作基礎之上。
(四)培養談判人才
集體談判過程是一個雙方相互博弈達成利益一致的過程,是充滿討價還價的、艱難的過程,是不斷言語較量試探的過程,正是有這種過程,很多勞資糾紛才得以解決。而這一過程,也是充滿技術與能量的過程。在集體談判階段,為了促使雙方能在利益博弈過程中達成一致、提高談判的層次和水平、形成合法的集體合同,參與談判的人要有較強的觀察力和反應力,還要有一定的組織協商能力。所以有必要對參與談判的人員進行專業的談判水平的培訓,勞資雙方特別是勞動者一方,要重視談判人才的培養,這些人才可以通過內部推選,然后再進行輔以專業的談判技術培訓。
參考文獻:
[1]伊特韋爾,米爾蓋特,紐曼.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卷1)[M].北京: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
[2]趙曙明.國外集體談判研究現狀述評及展望[J].外國經濟與管理,2012,(1).
[3]吳忠民.中國改革進程中的重大社會矛盾問題[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1.
[4]李俠.我國中小企業融資問題及對策研究[J].長沙大學學報,2016,(1).
[5]高瑾.我國集體談判法律制度構建障礙及克服設想[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0,(2).
[6]袁國敏,朱夢妍.對集體談判中政府的角色定位的認識[J].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2).
(責任編校:簡小烜)
Development Plight and Perfection of the Collective Bargaining System
LIU Zhiling
(Department of Basic Theory, Ma’anshan Municipal Party School of CPC, Ma’anshan Anhui 243000, China)
Abstract:Collective bargaining system is an effective way to resolve labor conflicts. The system in our country is only at a preliminary stage. It is faced with the plight from employees, employers and the Government. Collectivized labor force is not formed to safeguard their rights,Strong employers and strong control of the government restr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ctive bargaining system in China. We were perfect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o establish of a multi-level system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d improve relevant laws ,and straighten the role of government, and training professionals.
Key Words:collective bargaining; labor relations; plight
收稿日期:2016-03-04
作者簡介:劉志玲(1983— ),女,安徽郎溪人,中共馬鞍山市委黨校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教研室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社會學。
中圖分類號:D412.2;D92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681(2016)03-006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