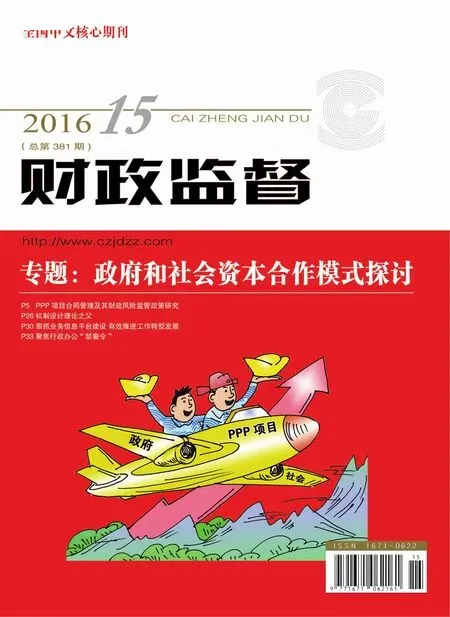聚焦PPP風險 直面待解難題
●本刊評論員
聚焦PPP風險 直面待解難題
●本刊評論員
隨著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興起,重塑政府、以企業家精神改造政府成為很多國家政府改革的潮流。其中通過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將市場、競爭、消費者導向、私人資本的專業能力和企業家精神引入到公共品和公共服務的PPP模式自上世紀末起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我國在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引進PPP,近幾年更是得到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視。
我國新一輪改革強調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注重轉變政府職能,更充分地發揮市場主體作用。順應這一頂層設計,PPP更有用武之地。但是,其推廣過程中面臨的問題,可能產生的各種風險,究竟能否更大地促進財政績效,仍存在諸多難題待解。這不僅表現為政府和民間資本的互信不夠、風險預期不確定導致全國多數推介項目“叫好不叫座”,還表現為具體PPP項目失敗風險及其集中體現的財政風險的凸顯。跳出財政風險來看待PPP,還有一些事關改革和國家治理的問題需要厘清。
PPP的財政風險集中表現為項目效益不理想、項目失敗導致財政支出超能力、超預期,社會投資轉化為政府債務以及項目周期內產生的公共資金的浪費和國有資產的流失,如果因此形成政府支付危機,還會產生政府信用危機。PPP財政風險的來源,有政策風險、不可抗力、信息不對稱、管理能力不足導致營收下降或項目失敗,更多是來自政績驅動下超范圍推行、項目本身的“假PPP”屬性、違規操作、違規擔保融資等。
跳出單純的財政功能,從體制改革、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角度,也要防范PPP“幫倒忙”的風險。其中,有幾個理論和現實問題應引起高度重視。第一,引入PPP,能否防范政府擴張頑疾,實現“更小的政府、更多治理和服務”?社會資本的進入,更多地向社會購買服務、更多的職能外包(市場化)必須與政府自身的改革、節省政府自我消耗式的財政開支結合起來。否則,社會資本沒能置換出政府投入,實際使公共服務成本更高、機構更臃腫,效能政府的目標就會大打折扣。
第二,引入PPP,怎么防范政府卸責風險?PPP理應改善公共品和公共服務供給,彌補短板,而非把政府應盡的責任推向社會。PPP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必須更加明確,有些地方居然將城市管理執法“外包”,這是明顯的卸責行為。
第三,引入PPP,能否防范政府低效率風險?例如,一些PPP實行特許經營,中標者實際上形成壟斷,有成為“二政府”的風險,市場力量不僅得不到發揮,還可能制造更嚴重的低效率;很多PPP項目并不重視社會化營運,只是追求投資融的增長,仍是“翻牌政府”。
第四,PPP能否節省整個社會的交易費用,解決代理問題,使政府、企業、公眾三贏?我們注意到一些地方政府推行PPP并非以降低行政成本為目的,而在部門利益、擴權收費、與企業合謀上打“小算盤”,除政府的代理風險外,還產生參與企業這一層次的代理風險。其結果是不僅未能降低公共服務成本和代理成本,還增加了公眾負擔。
PPP在我國正處于方興未艾的時代,其面臨的風險和問題也很多,如何更好地體現出在國家治理、公共服務、財政績效上的治本、治標功能,頂層設計、微觀管理還有更多的改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