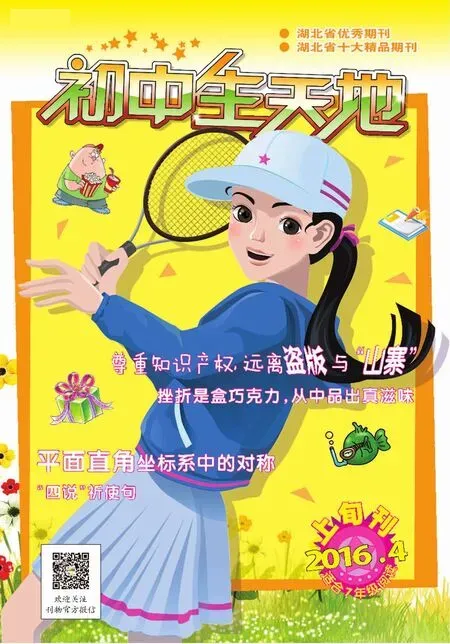為情感抒發找個“泉眼”
□周啟群
?
為情感抒發找個“泉眼”
□周啟群
無論是實用文體,還是文學體裁,一篇好的文章都不可能脫離情感單獨存在。文章的情感猶如人體的氣脈,氣脈的強與弱、滯與暢都決定著文章情感的抒發。在寫文章時,為情感抒發找個“泉眼”展現出各自的情味體態,讓情感或如長江大河波濤洶涌,或如山澗溪流叮咚作響,或如湖水沉靜蘊藉……這樣,一篇文章的生命與活力便有了。那么,情感抒發的“泉眼”在哪兒呢?
“泉眼”蘊含在景物描寫中。景物本身沒有情感可言,但作者卻可以借助景物傳達感情,或借景抒情,或移情于景。以端木蕻良的散文作品《土地的誓言》為例:
當我躺在土地上的時候,當我仰望天上的星星,手里握著一把泥土的時候,或者當我回想起兒時的往事的時候,我想起那參天碧綠的白樺林,標直漂亮的白樺樹在原野上呻吟;我看見奔流似的馬群,深夜嗥鳴的蒙古狗,我聽見皮鞭滾落在山澗里的脆響;我想起紅布似的高粱,金黃的豆粒,黑色的土地,紅玉的臉龐,黑玉的眼睛,斑斕的山雕,奔馳的鹿群,帶著松香氣味的煤塊,帶著赤色的足金;我想起幽遠的車鈴,晴天里馬兒戴著串鈴在溜直的大道上跑著,狐仙姑深夜的讕語,原野上怪誕的狂風……
作者多次運用“我想起……”這樣的句式形成排比,列舉了東北特有的物產和景物。這些景物之間沒有時間或空間上的關聯,只是以短句的形式鋪排開來,讓人一看到這些景物,就會想起東北特有的地域特征,這樣的景物鋪排,增強了文章的語勢,表達出作者熱愛家鄉的思想感情,從而增強了文章的感染力。
“泉眼”蘊含在內心獨白中。內心獨白,是人物情感的外化,它不需要借助外物,而是以第一人稱的方式描述自己內心所想的內容。內心獨白的形式比較靈活,文章中可以用一整段話來描寫自己內心所想,也可以零散地分布在一段話當中,讀者可以通過揣摩人物的內心獨白來把握情感。以都德的小說《最后一課》小弗郎士的一段內心獨白為例:
我幾乎還不會作文呢!我再也不能學法語了!難道這樣就算了嗎?我從前沒好好學習,曠了課去找鳥窩,到薩爾河上去溜冰……想起這些,我多么懊悔!我這些課本,語法啦,歷史啦,剛才我還覺得那么討厭,帶著又那么沉重,現在都好像是我的老朋友,舍不得跟它們分手了。還有韓麥爾先生也一樣。他就要離開了,我再也不能看見他了!想起這些,我忘了他給我的懲罰,忘了我挨的戒尺。
當小弗郎士知道鎮公所布告牌上的壞消息是怎么一回事時,當小弗郎士嘆息這是最后一節法語課時,當小弗郎士由“害怕責備”到“心里萬分難過”時,他復雜的心情便在內心獨白中展現出來:有對以前沒有認真學習的懊悔,有對不能再學習民族語言的失望,有心中油然而生的愛國之情,有對侵略者的憎恨。這樣,作者借助小弗郎士的內心獨白,就很好地表達了普法戰爭中法國大敗后當地人民的愛國情感。
“泉眼”蘊含在細節描寫中。細節,是一篇作品最容易觸動人心的部分。細節描寫,它集中在人物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上,能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可以說,任何一篇文學作品,無論是刻畫人物性格,還是展開故事情節、描繪典型環境,都離不開真實而又生動的細節描寫。好的細節描寫能把人物或事物最本質的性狀,鮮明而又逼真的呈現在讀者面前,從而增強作品的真實感和藝術感染力。例如:
“我的朋友們啊,”他說,“我——我——”但是他哽住了,他說不下去了。他轉身朝著黑板,拿起一支粉筆,使出全身的力量,寫了兩個大字:“法蘭西萬歲!”然后他呆在那兒,頭靠著墻壁,話也不說,只向我們做了一個手勢:“放學了,你們走吧。”
最后一課結束的時候,作者對于韓麥爾先生沒有進行過多的語言描寫,因為祖國的淪陷已使他深陷痛苦之中,而是著眼于動作細節的描寫上,通過他使出全身的力氣寫字,可以感受到他對祖國必勝的堅定的信念。最后以手勢而不是慷慨激昂的語氣作結,把韓麥爾先生的愛國形象深深地刻在讀者心中。
“泉眼”蘊含在客觀敘述中。客觀敘述,也是作者情感流露的場所。客觀冷靜的敘述,看似只是呈現事情的原貌,其實在具體客觀的敘述中,情感已蘊含其間。只要好好揣摩,情味就出來了。如:
那一天,韓麥爾先生發給我們新的字帖,帖上都是美麗的圓體字:“法蘭西”“阿爾薩斯”“法蘭西”“阿爾薩斯”。這些字帖掛在我們課桌的鐵桿上,就好像許多面小國旗在教室里飄揚。個個都那么專心,教室里那么安靜!只聽見鋼筆在紙上沙沙地響。有時候一些金甲蟲飛進來,但是誰都不注意,連最小的孩子也不分心,他們正在專心畫“杠子”,好像那也算是法國字。
這一段文字通過第一人稱“我”的視角進行敘述,敘述的內容主要有兩項,一是韓麥爾先生發給我們的新字帖,一是教室里的人安靜的聽課、做筆記。這些事情,如果是放在平常,可能意義不大,但是放在法國的阿爾薩斯、洛林被普魯士士兵占領的背景上來寫,法國人民的愛國情感就得到了很好的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