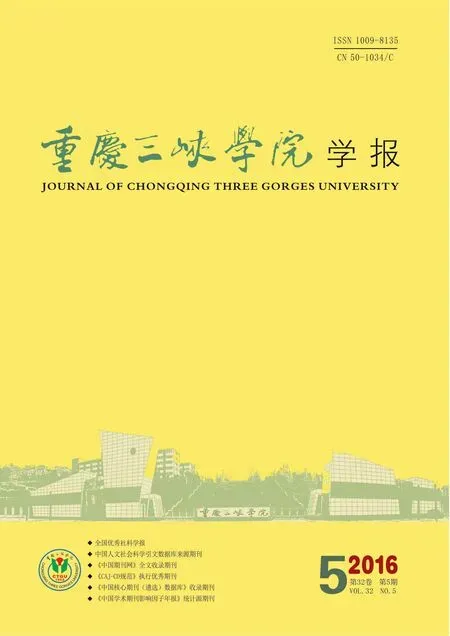蘇童與谷崎潤一郎唯美寫作的相似性分析
陳劍雨
?
蘇童與谷崎潤一郎唯美寫作的相似性分析
陳劍雨
(重慶師范大學,重慶 401331)
蘇童與谷崎潤一郎具有相近的文學趣味,在唯美寫作方面,兩者的相似性表現在手法上擅于記夢與感官體驗的形象化,選材上借不同文化書寫人性,情感表達上對女性之死的感傷與男性之死的快感。通過對比蘇童與谷崎潤一郎在唯美寫作方面的相似性與成因,分析蘇童唯美寫作的另類氣質與谷崎潤一郎惡魔性氣質的相似性,進一步探討蘇童與日本及日本文學間的聯系。
蘇童;谷崎潤一郎;唯美寫作;相似性
二十世紀初西方唯美主義傳入日本,谷崎潤一郎深受唯美主義影響,成為日本唯美主義代表作家之一,并將唯美主義發展為惡魔主義。五四時期,谷崎潤一郎的作品被五四新文學家介紹到中國,當時的文壇掀起了一股唯美主義之風,這些作家的筆下出現了大量女體的描繪、性的苦悶,然而他們對唯美主義的最初嘗試顯得過于西化,作品整體的藝術韻味不高,很難有作家可以與谷崎潤一郎的文學趣味相較。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唯美主義創作少之又少,直到八十年代,唯美主義創作才日漸活躍,許多作家又顯露出借鑒唯美主義方法創作的痕跡。唯美主義雖然沒有形成聲勢浩大的文學流派,但形成了一股潛在的力量,支撐起眾多作家的唯美之作。新時期具有唯美寫作特征的作家大體分為兩種,一是汪曾祺與張承志的較為明顯的“詩性”唯美寫作,二是“從題材到文本形式將唯美——頹廢表達到一定程度的當屬賈平凹和蘇童”[1]。蘇童是一位難以歸類的作家,他因為不同時期的不同創作風格,被貼上了新歷史主義、先鋒等標簽,對蘇童的評價一直未有統一的標準,直到當下,以張學昕為代表的學者才提出蘇童寫作的唯美特征,筆者認為這是對蘇童創作整體風格的恰當概括。
蘇童筆下的血腥、暴力、性等主題與谷崎潤一郎創作中女體崇拜、性與欲望、虐與被虐的主題,都通過記夢和感官體驗形象化的方式呈現,這些主題都表現出難以遏制的人性沖動,而且,谷崎潤一郎與蘇童都將“人性”進行了文化包裝,通過刺青文化、茶文化、米文化等文化表現人性,收獲了藝術化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蘇童與谷崎潤一郎小說中的主題、情節、人物都與“死亡”相接續,在表達女性之死的感傷之情與男性之死的快感方面具有相似性,既成就了二者陰郁的詩美世界,又使小說傳出一種令人戰栗的陰翳之感。
一、記夢與形象化的感官體驗——唯美寫作手法之相似
蘇童的小說善于用抒情的筆法,將病態美描寫得富有詩情畫意,對南方傳統世界的描繪散發出一種神秘夢幻的氣質。谷崎潤一郎也擅長用抒情的筆調打造夢幻世界,利用大膽的想象打造夢境,極具典雅陰柔的抒情美。谷崎潤一郎與蘇童的小說都表現出抒情性,而這種抒情美首先體現在對夢境的描繪。
谷崎潤一郎的《異端者的悲哀》以夢境開篇:“白色的鳥兒像緞子般展開閃光的翼”[2]54,“他確實看見這女子一邊如隨風裊娜的輕煙飄然起舞,一邊展示各種各樣的媚態。”[2]55主人公借助夢境,隨心所欲地將鳥兒幻化成妖艷的女人,對女子體態美的執著追尋竟在夢里得以滿足。谷崎的小說《春琴抄》,春琴毀容與佐助失明后,佐助依靠夢境來還原春琴的樣貌,按自己內心的想法塑造了夢幻般的春琴。蘇童在《城北地帶》中這樣描寫達生夢里的美琪之魂靈,“那個濕潤而神秘的身體是無法推卻的,它像一束花散發著芬芳歪倒在他的枕邊,像一片月光清冷地歪倒在他的枕邊。”[3]83達生終抵御不了美琪魂靈的魔力,傾心于美琪的少女之美,但隨著美琪的死,達生已無法擁有這種純然的少女之美,然而夢使一切成為可能,在夢里終于貼近了美琪。再如蘇童的《河岸》,主人公“我”夢見“很多年輕貌美的女子像孔雀一樣開著屏”[4]28,令他陶醉在“一種陌生而美妙的幻覺里”[4]28,小說中這種無法企及的美在夢中得以呈現。這三部作品中的夢境描寫提到了“女子”、色彩詞、花、鳥等美麗的事物,這些事物本身的美感增加了小說的抒情性。谷崎潤一郎與蘇童都擅長于借夢境抒情,而且對夢境的描寫都顯現出柔美與詭異。一方面,他們極力展現女子的美;另一方面,將女性的美妖魔化,夢境因此而變得神秘悠遠,抒情氣息十分濃郁。
作家們借助夢境的描繪,展現了不平凡的生活訴求,這不僅可以解釋現實的夢的成因,還可以解釋作家在作品中記夢不僅為了展現生活中不可能擁有的女性純然的美,而且表現小說世界里無法實現的愿望。兩位作家之所以在作品中大量描寫夢境,描寫夢境中的女子,與他們的人生經驗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系。谷崎潤一郎有著深厚的戀母情結,他在多部著作中表達了對亡母的依戀之情。蘇童說:“我對女性的認識多半來源于自己的生活經驗。”[5]62蘇童的外婆留給了蘇童關于女人的最初印象——“命苦”,因此,蘇童筆下的女性常常遭受男性的壓迫。谷崎潤一郎與蘇童以夢的形式將這種童年的訴求訴諸于筆端,形成了二者唯美的寫作風格。
谷崎潤一郎與蘇童作品的抒情美還體現在形象化地描繪感官體驗。《城北地帶》中,蘇童用“滾動的樹棍”形容米生的斷腿給人的視覺感受;《刺青時代》中,“我”覺得小拐手上的刺青看上去像“枯萎的樹葉”。《舒農》中,舒農決定不再尿床時的那個秋夜,自己就像是落葉在南方漂浮。《妻妾成群》中,頌蓮得知那井是“死人井”時是這樣描繪內心的感官體驗的:“感覺到一種堅硬的涼意,像石頭一樣慢慢敲打她的身體。”[6]34《河岸》中,“兩雙芭蕾舞鞋,像四把美麗而柔軟的刀子,”[4]28在《飛越我的楓楊樹故鄉》中,當我在年邁的族公家翻找幺叔的靈牌時,聞見罌粟花的香氣,“我”覺得老族公“幻變成碩大的罌粟花”[7]162。縱觀蘇童的一系列小說,以形象化的比喻述說不可琢磨的心境與感官體驗的現象比比皆是,一方面,這些意象增加了小說的抒情意味;另一方面,通過一種間接的方式激發讀者的想象與聯想,增加了小說的魔幻性。與蘇童一樣,谷崎的小說也善于形象化的表達感官體驗。
谷崎潤一郎的小說也重觸覺、聽覺等感官享樂,在表達感官享樂時也常常借助形象化的比喻。如《麒麟》中將五彩的宮殿描繪成“猛獸”,將其發出的震耳的鐘聲比喻成“吼叫”。《麒麟》文本相較于傳統題材,形象化的描述使“聲”、“色”、“味”的感官體驗表現出一種恐怖、陰翳之感,極盡夸張的描繪為文本增添了一種戲謔與解構色彩,也使文本擁有了隱喻之美,豐富了小說的內涵。又如《春琴抄》中佐助失明后覺得春琴臉上的繃帶好像“接引佛一般浮現在柔和的光環中”[8]43。將佐助對光的感覺形象地表現出來,佐助刺瞎雙眼的行為得到了升華。《春琴抄》中除了“女體”描繪,“鳥鳴”與“琴音”也是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作者對聽覺這一感官體驗的描寫極盡筆墨,構筑了文本的有聲世界,作者在文中描繪琴聲時往往以想象的方式將琴音這種聽覺的感官體驗形象化的表現出來。
蘇童與谷崎潤一郎通過形象化地表現感官體驗的恐怖陰森,描繪出一個陰翳世界。沈從文描寫了純樸柔美的湘西世界,而谷崎潤一郎與蘇童將類似于湘西的關西和南方世界描寫得極具魔性,這種魔力與沈從文、川端康成等作家描寫的小說世界異趣。究其原因,二者通過一種審丑的方式以達到對關西和南方文化反思的目的。總而言之,記夢和形象化的感官體驗的寫作方式,既豐富了蘇童與谷崎潤一郎作品獨特的意象,又增加了二者創作的抒情性和唯美色彩。
二、借文化書寫人性——題材與主題之相似
蘇童與谷崎潤一郎都善于從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細心澆灌作品的“人性”主題,作品在擁有深厚文化內涵之時,主題表達更加耐人尋味。谷崎潤一郎的小說《刺青》描寫了刺青大師清吉享受為男性刺青時他們的呻吟聲,他希望能找到至美的女體為她刺上絢麗的蜘蛛圖紋,讓所有男性都跪拜于她的美麗。一次偶遇,他終于找到了夢寐以求的女體,然而,他自己也成為眾多被虐者之一,匍匐在女體之美下。谷崎潤一郎表現的肉體受虐與精神被虐的變態性欲作用下的一種“沖動”,貫穿于文本之間的刺青文化藝術化地表現并彰顯了這種“人性”,將藝術性融于其間,將受虐與被虐的行為放大,甚至將這種行為變成了一種儀式,供閱讀者賞鑒。蘇童的《刺青時代》描寫的刺青文化已衍生為一種暴力崇拜,男孩小拐對刺青的鐘愛達到了著魔的地步,刺青文化粉飾了原始血性。除了性欲這一主題之外,中國新歷史主義作家的筆下還挖掘了“血性”這一原初的人性。例如小拐觸及天平手上的豬頭刺青時,激發了小拐的血性。由此可見,刺青文化令血性和原始力量放射出迷人的光彩。
谷崎潤一郎的《刺青》與蘇童的《刺青時代》都偏愛借文化書寫人性,以達到藝術化的效果。而谷崎潤一郎所借取的文化不僅有日本文化還有中國傳統文化,谷崎潤一郎能夠嫻熟地借鑒漢學典籍與中國傳統文化書寫人性,在于他少年時燃起了對中國古代典籍的興趣,在秋香塾學習漢學典籍為他能夠借中國文化書寫人性提供了便利。《刺青》中的一幅畫描繪的是“中國公主”冷眼傲視臺下即將被砍頭的犯人,這幅畫是谷崎潤一郎表現受虐欲望的來源。谷崎潤一郎的另一篇借儒家文化書寫人性的小說《麒麟》,對孔子周游列國故事的改造,不僅小說的語言具有唯美特征,就連角色也進行了重新解釋,主題也由儒家文化的“道德批判”轉向了張揚人性的“肉體享樂”,作者借儒家文化對衛靈公的性欲望進行了藝術化的處理。
蘇童表現的文化除了上述的刺青文化,還包括中國的“米”文化、“茶”文化等。蘇童的小說《米》,受到中國的“食色性也”的民間文化的啟發,用“米”文化來表現主人公五龍的性欲與血性,作品中性交場面的描繪幾乎都有米的出現。蘇童為什么選擇以“米”這樣一種生命不可或缺的東西來寫一部作品?原因在于米的歷史悠久,它與原始血性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就像是一把鑰匙,五龍通過“米”將原始的血性激發,米生又從父親那繼承了血性。茶文化很難令人聯想到血性,但正是香椿樹街迷惑人的茶品與茶道激發了人們的血性,在香椿樹街,茶文化變成了一種俗文化,喝茶的人喝下的是茶,回味的卻是俗人俗事。蘇童的小說《南方的墮落》中,小小的茶館映照了這條街的人文世界,例如“茶館很容易讓一個少年聯想到兇殺、秘密電臺、偷匿黃金等諸如此類的罪惡”[9]110,茶館老板娘姚碧珍舉止輕浮,品茶人喝茶之余也賞玩著她,此外還有“活幽靈”金文愷,“無業游民”李昌,遇人不淑的紅菱姑娘,祖奶奶的風流韻史,借茶文化與茶客表現了腐俗的人性。
谷崎潤一郎與蘇童善于借文化來書寫人性是源于對傳統文化的喜愛。谷崎潤一郎在《芥川君和我》中說道:“芥川君和我早就溯流而動,在愛好東方古典這一點上,我們的興趣極為相投。”[10]369谷崎潤一郎對漢學的了解為他改造中國古典典籍記載之事提供了便利。中國古籍簡略的記載,給予了谷崎潤一郎極大的文學想象空間,也為其故事的審美性改造提供了便利。例如《麒麟》文本的矛盾沖突由“正邪對立”轉變為“靈”與“肉”的激烈對抗。蘇童也喜歡從古代典籍中挖掘古典文化來書寫人性,他重塑神話的經典之作《碧奴》便是其唯美寫作的典范。《碧奴》取材于“孟姜女哭長城”之事,在現代化的語境下,蘇童通過輕快的抒情、唯美的敘述抖落了歷史沉重的包袱,展現了人性本真。
蘇童與谷崎潤一郎的小說在表現人性時,并非以直接的方式呈現,而是借助文化外衣,不僅形象地描摹了人性,而且具有一種原始氣息與奇幻色彩。更難得的是,在書寫人性時,既借助文化又不拘泥于文化,體現出一種超越性。因此,谷崎潤一郎與蘇童在藝術化的表現人性這方面具有內在一致性。
三、女性之死的感傷與男性之死的快感——情感表達之相似
蘇童與谷崎潤一郎的作品中皆存在“死亡”主題,即一切美好的丑陋的事物終將消亡,“死亡”是作品“陰翳”之美的主要呈現方式。谷崎潤一郎多描繪婦人之死與男性的毀滅。蘇童的筆下有描寫美妙少女的消逝、已婚女子在男權壓迫下的消弭、腐俗男性之死。然而,值得探究的是谷崎潤一郎與蘇童對女性之死流露出同樣的感傷情緒,對男性之死表現出一種相似的快感,情感表達的相似性表明蘇童與谷崎潤一郎擁有相近的情感評價,但兩位作家產生同樣情感體驗的原因卻不盡相同。
谷崎潤一郎小說中的男性形象通常是受虐者,而蘇童筆下的男性則是施虐者,相同之處在于,施虐者與受虐者都有一個“死亡”結局,相較于女性之死,谷崎潤一郎與蘇童對于男性之死更多地表現了一種痛快感。如谷崎潤一郎的《瘋癲老人日記》,寫了老人遭受性欲的折磨,瀕臨死亡的邊緣,卻仍然樂在其中,追求受虐的快感。蘇童的小說《米》、《城北地帶》中的男性人物如五龍和李修業是施虐者的形象,對女性遭遇的同情使作者描繪這類形象時,表現出一種“復仇”的快感。雖然兩位作家筆下的男性之死的原因不盡相同,但是作者通過他們的死,都抒發了一種極致的快感。
谷崎潤一郎的小說《細雪》中,幸子回憶她的母親,寫到母親之死時,說:“惋惜美好事物離開塵世的一種悲痛,是一種伴有音樂妙味的悲痛”[11]126,在蘇童的少年世界里有一位美麗的少女美琪,她的命運便是“死亡”。蘇童作品中美琪擁有無與倫比的少女之美,因為她無法抵御的美,使紅旗失去了理智,他強暴了美琪。這是美的第一次毀滅。之后,美琪受不了他人的異樣的目光,投河而死,這是美的徹底毀滅。蘇童的行文間表現出濃郁的惋惜之情。蘇童《米》中還表現了婦女的美的毀滅,表達了對女子掌控不了命運的痛惜之情。二者的小說文本中對美的消逝充滿了失望、悲觀、惋惜等灰暗的色調,與曾經絢麗無比的美相對比,運用對比手法突出對女子“死亡”的感傷與痛惜,是童年經驗的折射。
對女子之死流露出濃郁的感傷情緒,除了上述提及兩位作家的童年經歷的原因之外,還有傳承了各國傳統小說中對女子美的極力推崇和女子之美消逝的惋惜之情。例如,《源氏物語》中對紫姬的描繪,容貌氣質出眾,最終卻香消玉殞。谷崎潤一郎的作品與《源氏物語》確有承繼關系,評論者劉青梅說:“三次將《源氏物語》譯成現代日本語,……,谷崎潤一郎的作品不僅在內容和情節上和《源氏物語》有一定的相似性,內含的兩大主題——戀母情結和女性崇拜均來源于此”[12]。
蘇童的作品與《紅樓夢》之間也有較多聯系。在被問及日本文學對他的影響時,蘇童則說:“給我啟發很大的是我國古典小說《紅樓夢》、‘三言二拍’。”[13]105蘇童《妻妾成群》中“姨太太”的題材便是受《紅樓夢》等作品的啟發,他說:“這個故事的成功也許得益于從《紅樓夢》、《金瓶梅》至《家》、《春》、《秋》的文學營養。”[14]340蘇童筆下的姨太太既具有“紅樓女兒”之美,如學生時代的頌蓮,又有“趙姨娘”般的毒辣,在她們身上,蘇童既有對舊式家庭對新式女子的摧殘的惋惜,又感傷于舊式女性這樣一群舊家庭的衛道者。蘇童對逝去的女子之美都表現出了憐惜,對她們的死表達出了感傷之情。這種情感,多延續和繼承來自于《紅樓夢》中的情感體驗。
四、“先鋒”作家蘇童與日本及日本文學
中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先鋒小說家的唯美寫作較多受歐美文學的影響,但隨著八十年代日本文學的重新譯介,小部分先鋒作家也受到了日本文學的影響。據李振聲《中國當代文學閱讀視野中的日本現當代小說》回憶,在先鋒作家出現的八十年代出版過一套小說叢書——“日本文學流派代表作叢書”[15],其中便收入了唯美主義作家谷崎潤一郎的作品《異端者的悲哀》。此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上海譯文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聯袂推出過一套規模甚巨的‘日本文學叢書’”[15],這套叢書中包括了谷崎潤一郎的《細雪》與《春琴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翻譯的日本文學“名頭最響的是川端康成”[15]。可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日本文學并未淡出人們的視野。雖然蘇童自述其創作多源自于歐美文學的影響,但是蘇童與日本以及日本文學也存在聯系。
依據《蘇童文學年譜》記載,2008年,“蘇童進行了第一次的日本之行”[16]251,同年《蘇童·繁華千尋》出版,記載了蘇童的日本之行,包含了蘇童對日本的諸多看法以及與日本漢學家們的交流。這次日本之行是蘇童與日本的第一次實際接觸。蘇童到日本之時,正值櫻花盛開,日本的櫻花給蘇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蘇童的文學創作風格方面,中國評論家王干說:“日本文學的‘幽玄’之美經翻譯過來的文字風格是:句子很長,結構綿軟、細致。”[17]163他還認為像翻譯過來的日本文學語言一樣,“有意識地進行語言的細部用力,已經說不清是先從哪一個先鋒作家開始的,單從文本留下的跡象而言,可能是莫言的《紅高梁》,但最成功的,無疑是格非,此外是蘇童、余華。”[17]163學者王干從蘇童小說語言特點方面入手,研究了其語言風格形成的部分日本因素。1980—1984年,蘇童就讀于北師大,他十分喜愛學校自由的學術氛圍,那時藏書頗豐的北師大圖書館是蘇童常去的地方,各國文學經典唾手可得,而且,當時正值日本文學新的譯介熱,蘇童或多或少地接觸到了日本文學,對蘇童產生了潛在的影響。蘇童在散文《平淡的生活》中說,在北師大讀書期間他“在某個小影院里看一部拷貝很久的日本電影《泥之河》。”[18]210該片講述的是小主人公信雄與喜一間的兒時友誼,信雄居住于岸上,喜一一家住在大阪河邊船上,其間貫穿著大阪河。筆者不禁聯想到蘇童近年發表的小說《河岸》中關與“河”與“岸”的描繪。電影《泥之河》與小說《河岸》濕漉漉的氣息十分相似。
據《蘇童·花繁千尋》中記載的“蘇童訪日座談會”實錄,日本漢學家吉田教授在被問及“閱讀蘇童的小說有沒有類似日本作家的作品的感覺?”[19]34時說:“從文體上看應該有的,而且還不止一個。”[19]34他認為蘇童的平穩淡薄之風與川端康成等作家的風格相似,因此,吉田教授的看法是:“從日本上一代的作家可以找到類似蘇童風格的小說。”[19]34谷崎潤一郎是深得日本文學“幽玄”美的,從他的兩篇代表作《春琴抄》與《細雪》可看出他融化傳統的努力。蘇童小說細節的考究和語言的綿密可見“幽玄”之風的影響,這令他們具有頗多相似性與可比性。蘇童與谷崎潤一郎似乎是透過多棱鏡觀察描寫中國南方世界與日本的關西世界,這種“變態”與詭異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由此形成蘇童的先鋒氣質與谷崎潤一郎的惡魔氣質相近。由此觀之,兩位作家的小說最大的相似之處在于游走于古典創作風格與現代小說技法之間。
谷崎潤一郎對美的苛求表現于女體描繪的官能享樂,加之對日本“幽玄”、“物哀”美的傳承,使其創作不自覺地在惡魔性書寫中表現了唯美傾向,使古典氣息與現代氣息完美融合。蘇童的先鋒氣質相比于其他先鋒作家顯得十分另類,將他完全歸類于先鋒作家群體顯然有些不妥當。細心體味與觀察蘇童與谷崎潤一郎的惡魔氣質則較為接近,蘇童的文學作品風格詭異、荒誕,描寫夸張、大膽,同時注重“細節的打磨,……,自我感覺的咀嚼”[17]164,使其創作頗具唯美色彩。縱觀記夢與形象化的感官體驗、借文化書寫人性、女性之死的感傷與男性之死的快感三方面特點,這些相似性表明在中國唯美主義潛流發展的近一百年里,蘇童是能夠與谷崎潤一郎相比較的作家。
參考文獻:
[1] 張學昕.蘇童與當代作家的唯美寫作[J].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2):58-64.
[2] [日]谷崎潤一郎.惡魔短篇小說[M].于雷,等,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
[3] 蘇童.城北地帶[M].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4.
[4] 蘇童.河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5] 蘇童,王宏圖.蘇童王宏圖對話錄[M].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3.
[6] 蘇童.妻妾成群[M].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4.
[7] 蘇童.神女峰[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
[8] 谷崎潤一郎.春琴抄[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
[9] 蘇童.南方的墮落[M]//蘇童作品精選.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7.
[10] 張福貴.華夏文化論壇:第10輯[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3.
[11] [日]谷崎潤一郎.細雪[M].周逸之,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12] 劉青梅.試論谷崎潤一郎作品與《源氏物語》間的關聯[J].日本問題研究,2009(2):53-57.
[13] 汪政,何平.蘇童研究資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2007.
[14] 劉復生,張宏.中國現當代文學名著[M].北京:藍天出版社,2008.
[15] 李振聲.中國當代文學閱讀視野中的日本現當代小說[J].中國比較文學,2010(3):111-121.
[16] 張學昕.穿越敘述的窄門[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17] 王干.現代小說語言:在權勢與自由之間[M].蕪湖: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
[18] 謝冕.哲理美文[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4.
[19] 蘇童.蘇童·花繁千尋[M].上海: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2008.
[20] 郁勤.蘇童小說于傳媒時代中的生產與傳播[J].長江師范學院學報,2015(5).
(責任編輯:鄭宗榮)
On the Similarity of Aesthetic Writing Between Su Tong and Tanizaki Junichirou
CHEN Jianyu
Su tong and Tanizaki Junichirou have similar taste for literature. In the aspect of aesthetic writing, they are similar in the methods of recording people’s dreams and visualizing sensory experiences.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two writers is also shown in material selection, i.e., they often describe human nature by culture. And Su tong’s Emotion expressions have much in common with Tanizaki Junichirou’s. They are both sad for the death of woman and pleasant for the death of man. By compa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causes of aesthetic writing, readers can analyze the similarity between Su tong’s unique temperament and Tanizaki Junichirou’s temperament of diabolism, so that we can further inquire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 tong and Japan as well as Japanese literature.
Su Tong; Tanizaki Junichirou; aesthetic writing; similarity
I0-03
A
1009-8135(2016)05-0033-05
2016-03-18
陳劍雨(1992-),女,江蘇鹽城人,重慶師范大學在讀研究生,主要研究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