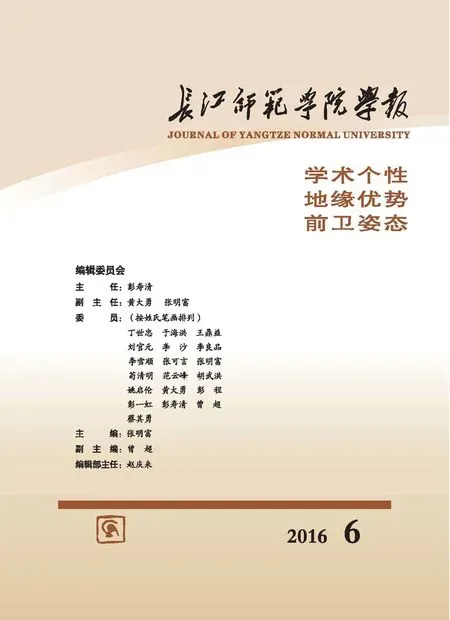“平淡而近自然”:張愛玲后期中短篇小說風格論
唐娒嘉
(北京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北京 100871)
“平淡而近自然”:張愛玲后期中短篇小說風格論
唐娒嘉
(北京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北京 100871)
張愛玲自1952年離滬赴港,創作風格開始發生轉變。其后期注重對生活本來面貌的還原,小說創作漸趨顯現出一種 “平淡而近自然”的風格,這在其中短篇小說創作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本文希圖從語言修辭風格、敘事方式、心理描寫3方面著手,探討其后期 “平淡而近自然”風格的具體文本表現,以及此種風格形成的影響質素。
張愛玲;后期寫作;創作風格;平淡自然
一、前言
1952年7月,張愛玲只身離滬赴港,研究者一般以此為界,將其創作分為前后兩期。相較于張愛玲前期創作研究成果的豐富,學界對其后期創作的研究力度明顯不夠,而重點又主要集中在自傳性小說《小團圓》以及包括 《小團圓》共同構成的 “自傳三部曲”(《雷峰塔》《易經》)上,且明顯存在研究分散、研究力度不均、深度廣度不及等問題。同時,并沒有一篇研究文章以其后期中短篇小說為整體進行系統論述,只在部分論述中零星可見。只有被改編為電影的 《色,戒》有較多的論者涉足。
現今學界對張愛玲后期創作風格的研究,缺乏較為系統深入的剖析。學人們多是通過較為零散的經驗式分析或是技巧性討論對其后期風格的轉變進行過論述,既缺乏對作家后期創作風格較為全面、具體的展示,也沒有能夠為其后期風格轉變提供較為可靠和合理的解釋。我們欲以張愛玲后期中短篇小說為例,對其后期中短篇小說 (即中篇 《同學少年都不賤》、短篇 《相見歡》《色,戒》《浮花浪蕊》《五四遺事》)進行深入細致的文本分析,兼合對前期創作的相關對照研究,通過語言修辭風格、敘事方式、心理描寫3個主要方面探討其后期 “平淡而近自然”風格的具體文本表現,以及其 “平淡而近自然”風格形成的影響質素。
二、張愛玲后期中短篇小說的語言修辭風格
(一)從 “絢麗”到 “平淡”
蘇青在 《〈傳奇〉集評茶會記》中曾盛贊張愛玲:“我讀張愛玲的作品,覺得自有一種魅力,非急切地吞讀下去不可,讀下去像聽凄幽的音樂,即使是片段也會感動起來。”[1]對其小說語言更是不吝溢美之詞:“它的鮮明色彩,又如一副圖畫,對于顏色的渲染,就連最好的圖畫也趕不上,也許人間本無此顏色,而張女士真可以說是一個 ‘仙才’了。”[2]譚惟翰也曾對張愛玲的語言做出過評價:“張女士的小說有三種特色,第一是用詞新鮮,第二色彩濃厚,第三比喻巧妙。”對張愛玲創作抱有極高期許的傅雷,也在他的《論張愛玲的小說》中直言道:“外表的美永遠比內在的美容易發現,何況是那么色彩鮮明,收得住,潑得出的文章。”[3]張愛玲本人在 《天才夢》中對此也有過自陳:“對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極為敏感;我學寫文章,愛用色彩濃厚、音韻鏗鏘的字眼,如‘珠灰’‘黃昏’‘婉妙’‘splendou’‘melancholy’,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4]
“色彩濃厚絢麗”在其前期中短篇小說創作中自是可見一斑。我們對 《傳奇 (增訂本)》中的15篇小說和后期5篇中短篇小說中的顏色詞做了詳盡的統計,意圖通過對照分析其前后期中短篇小說中顏色詞的不同使用情況,明晰出其后期的語言風格特色。
我們發現,張愛玲后期中短篇小說中顏色詞的使用,無論數量還是密度上,較于前期都有大幅減弱。張愛玲在其前期中短篇小說中,對于顏色詞的重視,可說是精雕細琢、不吝筆墨;其后期的5篇中短篇小說中,顏色詞使用最多的中篇 《同學少年都不賤》有50處,最少的是 《相見歡》有21處。而 《傳奇(增訂本)》中收錄的其前期15篇小說,顏色詞使用超過50處的則有5篇,低于21處的僅有 《封鎖》1篇。在其前期的中短篇小說中,《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的顏色詞使用都超過了100處,可謂滿篇 “活色生香、絢麗奪目。”而 《金鎖記》和 《傾城之戀》的顏色詞使用,無論頻次還是密度,也頗為著力。
其后期中短篇小說中顏色詞的使用相較前期,則存在很大的差別。
第一,顏色詞的數量和密度大大降低,且顏色種類明顯減少,不再似前期般異彩紛呈,主要集中在黑色、白色、紅色、綠色、黃色詞上,而且不再似前期中短篇小說那樣偏愛色彩濃烈炫目的詞,而主要使用黑色、白色等疏淡素雅的詞。比如紅色、綠色等顏色詞大幅減少,《五四遺事》中 “紅”色詞3處,“綠”色詞3處;《色,戒》“綠”色詞只有1處; 《相見歡》“綠”色詞僅有1處;《浮花浪蕊》“紅”色詞4處,“綠”色詞3處。而 《同學少年都不賤》“黑”色詞有9處,“白”色詞有8處;《浮花浪蕊》中“黑”色詞7處,“白”色詞10處;《色,戒》中 “黑”色詞6處,“白”色詞8處。整體的色彩感由絢麗奪目轉向淡然疏朗。
第二,對顏色詞的使用,不再如前期著意和用心。同一色系的顏色詞不再像前期中短篇小說那樣,而是細化和區分出不同的描述,對于 “紅色”的描述便僅有 “紅”“深紅”“大紅”“粉紅”,不再像其前期所述 “荔枝紅”“石榴紅”“梅紅”“櫻桃紅”等各項形象化的描述。在前期顏色詞使用中,張愛玲投入了不少主觀感覺,如 “白辣辣”“蒼白”“昏黃”“蟹殼青”“黑壓壓”“紅焰焰”“紫陰陰”等詞,調動了味覺、視覺、觸覺等多重感官,將本來抽象化的色彩形象化、可感化。這些主觀化了的顏色詞,在營造氛圍、推動情節發展上都發揮了不容小視的作用。作者在創作后期,則抹掉了情緒化、主觀化的成分,不再精心磨琢引人聯想的色彩詞匯,而是將其簡單化。如描述 “白色”,在后期的5篇中短篇小說中,僅使用 “白色”“雪白”這兩個簡單詞匯,全然摒棄掉了前期小說中對 “白色”詞的多樣化記述。“象牙白”“蔥白”“瑩白”“乳白”“銀白”“粉白”“藍白”等在前期小說中頻繁出現的 “白色”詞描述,在后期中短篇小說中,全然不見蹤影。這不能不說是作家創作重心轉移的一處外在顯露。
張愛玲前期創作,投入太多的心力在技巧上,刻意通過新奇陸離的 “顏色王國”帶給滬上市民讀者新鮮刺激的閱讀體驗,也是其 “職業寫作”考慮讀者需求和市場期待的 “討巧”之舉。同時,和張愛玲前后期不同的審美趣味和傾向也不無關聯。張愛玲以 《第一爐香》一夜成名,1943年、1944年的她,沉浸在創作繁榮期,是上海灘眾人關注的 “文壇寵兒”,喜歡 “標新立異”的她,或為滿足讀者的獵奇心理,或為創造神秘詭譎的氛圍,在對顏色詞的處理上,極盡濃墨重彩、華麗奢靡之能事。1952年7月,32歲的張愛玲只身離滬赴港,開啟了她后半生居無定所、漂泊無依的艱辛歷程。在經歷了情感重創、謀生艱難、海外創作受挫等接連打擊后,張愛玲也逐漸從 “張揚”走向 “內斂”,她不再是當初那個高喊著“出名要趁早”、肆意揮霍才華的個性女子,而是逐漸拔除掉生命華美的袍、拼命 “瘙癢”的無奈之人。美國新聞處對她創作題材的限制,讓她苦不堪言,“寫 《赤地之戀》真怨,Outline(大綱)公式化——好像拼命替一個又老又難看的婦人打扮——要掩掉她臉上的皺紋,吃力不討好。”[5]“這幾天總寫不出,有如精神上的便秘。”[6]而 《赤地之戀》的慘淡反響和 《北地胭脂》的出版受阻,讓她心境慘然,華麗炫目的色彩自然無法引起她的共鳴。她后期創作的5篇中短篇小說,雖仍是以上海、香港這兩處她十分熟悉的地點作為創作背景和環境,但小說中的 “上海”和 “香港”,已然不是作者身在其中的 “上海”和 “香港”。與作者和接受者的現實生活均處于疏離狀態,張愛玲自然不可能如同前期一般,傾入太多的主觀感覺,不能身臨其境,而主要依靠記憶書寫,自然不似前期般精雕細刻,形象逼真如在目前。
而對于 “桃紅配蔥綠”參差對照效果的偏好,在后期中短篇小說創作中,也顯然被張愛玲放棄了,作者不再希圖通過紅綠對照的藝術沖擊力去刺激讀者的感官,而是更多地選擇淡化,給人一種 “平淡而近自然”的內在張力。換言之,“顏色”已然不再是張愛玲刻畫人物形象、營造氣氛、推動情節發展的利器,更多地轉為客觀化的敘述,是對物品、對場景、對人物著裝的客觀描述。
(二)從 “繁復”到 “精簡”
在用語的經濟、繁復上,前后期也存在很大的不同。前期用詞考究、注重煉字鍛句,甚至有失之繁復之嫌,后期語言則很經濟,修飾性語言大幅減少,小說里含有不少夾縫文章。以 《色,戒》為例,即便故事題材是極易展示 “張氏”技巧的間諜題材,卻很難找到如同前期般刻意煉字鍛句的痕跡,敘述簡約節制,用語經濟,表現隱晦,讀者很難完全明白,后來張愛玲不得不寫 《羊毛出在羊身上——談 〈色,戒〉》做解讀。而幾乎全篇以人物對話推動情節發展的 《相見歡》,張愛玲也是選擇不做過多的文辭 “賣弄”,后不得不做 《表姨細姨及其他》為讀者釋疑。小說之所以充滿了 “淡味”,一方面表現的是一對中年表姐妹的情感余溫,自然不可處理得太過絢麗;另一方面,即便是小說中細膩、微妙的心理刻畫,作者都處理得極盡平淡經濟,更可證明作者后期小說語言確是向 “平淡而近自然”的風格轉化。
伍太太有點詫異,她表姐竟和一個釘梢的人搭話。她不時發出一聲壓扁的吃吃的笑聲,“咕”的一響,表示她還在聽著。[7]《相見歡》
伍太太微笑不語,其實她盡可以說一聲 “你來跟我住”。但是她不愿承認她男人不會回來了。[8]
這些微妙心理的刻畫,文字精簡,寥寥數語,把伍太太對表姐與盯梢之人搭話的 “不以為然”和“輕蔑”、對自己不愿在人前承認丈夫已然拋棄自己的勉強的自尊心理展現無遺。這與其前期或借用景物襯托、或借助意象暗示,都顯得經濟平淡了許多。寥寥數語、不多著一字,剔除過濾掉了烘托、襯映的技巧手法,幾乎不見修飾性話語,只把本真的一面還原給讀者。
前期的妙語警句頗多,后期則難覓。《傾城之戀》寫一對亂世中的普通男女、平凡夫妻,因為一場城市的傾覆,實現了所謂的 “永恒”和 “真心”,文中的妙語警句不勝枚舉。
柳原嘆道:“這一炸,炸斷了多少故事的尾巴!”流蘇也愴然,半晌方道:“炸死了你,我的故事該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還長著呢!”[9]《傾城之戀》
他不過是一個自私的男子,她不過是一個自私的女人。在這兵荒馬亂的時代,個人主義是無處容身的,可是總有地方容得下一對平凡的夫妻。[10]《傾城之戀》
后期的中短篇小說 《浮花浪蕊》《同學少年都不賤》多是以作者的生平經歷為素材,在敘述中,雖有很多孤獨漂泊的身世之悲,作者語調克制、平鋪直敘,不做過多渲染。如:
船小浪大……一時竟不知身在何所。還在大吐——怕聽那種聲音。聽著痛苦,但是還好不大覺得。漂泊流落的恐怖關在門外了,咫尺天涯,很遠很渺茫。[11]《浮花浪蕊》
“甘西迪死了,我還活著,即使不過是在洗碗。”[12]《同學少年都不賤》
粗看很是枯淡無味,但結合小說內涵,這種經濟簡約的語言,正適合表達女主人公洛貞羈旅天涯漂泊無依的悵然渺遠 (《浮花浪蕊》)以及趙玨因和少時密友在后來人生際遇中的云泥之別,心生自卑和不甘,對自己最粗糙最原始的安慰 (《同學少年都不賤》)。張愛玲后期中短篇小說語言的這些轉變,恰巧做到了傅雷早年對她的期許:“寶石鑲嵌的圖畫被人欣賞,并非為了寶石的彩色;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詞藻,多一些實質:作品只會有更完滿的收獲。”[13]
張愛玲在寫給胡適的信中直陳:“希望這本書 (《秧歌》)有點像他評 《海上花》的 ‘平淡而近自然’”[14]。更見其后期對 “平淡而近自然”風格的自覺追求。張愛玲后期長期從事 《紅樓夢》和 《海上花列傳》的研究和翻譯工作,對其 “寫實主義”精神的接受和認可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其小說創作。《紅樓夢》的悲天憫人、曲筆隱言,《海上花列傳》的平實敦厚、自然疏淡,極大地影響了她的創作思想。同時對 《紅樓夢》《海上花列傳》等古典文學作品的浸淫,也促使張愛玲向古典文學復歸,從她為其后期中短篇小說的命名上便可見一斑,小說名多選用中國古詩詞。《五四遺事》的副題 “羅文濤三美團圓”像是 《三言二拍》類似話本的回目。《同學少年都不賤》源于杜甫 《秋興八首》第3首的最后一句 “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張愛玲改 “多”為 “都”。“浮花浪蕊”也出自古詩,“相見歡”是詞牌名。
(三)從 “多樣”到 “簡約”
修辭方式多種多樣,主要包括比喻、擬人、夸張、排比、對比、設問、引用、反復、借代、對偶等。就張愛玲的小說而言,比喻是她眾多修辭手法中最為出彩的。我們僅以比喻為例,說明張愛玲前后期中短篇小說修辭方式上的轉變。總體而言,其后期小說中的比喻修辭,無論從數量還是密度來看,較之前期都大大減少。比喻句的使用,《色,戒》中有6處,《五四遺事》中有4處,《相見歡》中有3處,《浮花浪蕊》中有3處,《同學少年都不賤》則無一處。我們對 《傳奇 (增訂本)》中的15篇小說做了詳細的梳理,發現其在前期小說創作中,稱得上是建立了一系列龐大的比喻群,《金鎖記》中有比喻句17處、《傾城之戀》有16處、《第二爐香》有14處、《紅玫瑰與白玫瑰》有13處、《第一爐香》有8處。她以玲瓏剔透、華彩恣肆的文字,采用或通俗時尚、或古典婉約的比喻意象,對世情世相、俗世悲歡的展現著實令人嘆服。無論是 《金鎖記》中將月亮比作銅錢大小的濕暈、云朵軒信上的淚珠,將備受母親摧殘的長安比作鹽腌過的雪里紅;還是 《茉莉香片》中比作屏風上霉蛀了的織金云朵鳥的馮碧落;抑或是 《封鎖》中如同柔滑前移的曲蟮的電車,無不展現著前期張愛玲的感覺之敏銳、獨特。其比喻數量多,密度大,構思巧,收效奇,近乎肆意 “揮霍”,著實令人驚艷。而再觀其后期中短篇小說,除在數量上較前期明顯減少外,構思、達意、藝術表現力上也有明顯的差別。
一種失敗的預感,像絲襪上一道裂痕,陰涼的在腿肚子上悄悄往上爬。《色,戒》
他們有了兩個孩子之后不想要了,祖銘是個漏網之魚。《相見歡》
只是個華僑模樣的東方婦人,腦后梳個小髻,黃胖栗子臉——剝了殼的糖炒栗子。《浮花浪蕊》他們正在吃菱角,一只只如同深紫紅色的嘴唇包著白牙。《五四遺事》
不難看出,在前期小說中,張愛玲以比喻為手段,借助一些最尋常的事物傳達出了獨具性格魅力的比喻意象,取得了生動、傳神的藝術效果。她善于將各種感官打通,刻畫人物心理狀態、反映世態人情,使比喻新奇而富于聯想。后期比喻句在數量、密度上大幅降低,藝術效果也褪色良多,言語簡省、多用明喻、表述直白,很難如前期一般給讀者自由聯想的空間。
“對于一個不再有故鄉的人來說,寫作成為居住之地。”[15]張愛玲的后期創作,含有不少自敘傳色彩,她更多地傾向于表達自己的切身感受,對世界的感覺逐漸平淡,她后期深居簡出、頻繁搬家,為生活所累,且身在異鄉,上海、香港于她而言,已是模糊的悵惘;所處的美國,她也始終只是一個流落海外的異鄉人,“流亡者存在于一種中間狀態,既非完全與新環境合一,也未完全與舊環境分離,而是處于若即若離的困境,一方面懷鄉而感傷,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16]作者自己的感受在反復敘寫中不斷膨脹、不斷被渲染,而對外在世界的感覺便在自然不自然中地逐漸鈍化、漸趨平淡。
三、張愛玲后期中短篇小說的敘事方式
(一) “敘事人”位置的轉變
張愛玲在 《表姨細姨及其他》一文中說:“我一向沿用舊小說的全知觀點羼用在場人物觀點,各個人的對話分段,這一段內有某人的對白或動作,如有感想就也是某人的,不必加 ‘他想’或 ‘她想’。”[17]其前后期小說一直采用全知敘事的視角,然而即便都是全知敘事,敘事人的位置在前后期中短篇小說中也發生了轉變,即從前期的 “顯身”轉變為后期的 “隱身”,從前期冷靜客觀的 “旁觀者”到后期自憐自傷的 “當事人”。
前期小說敘事人 “顯身”最明顯的小說,主要有 《金鎖記》《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茉莉香片》《傾城之戀》等。在這些小說里,作者保留了舊小說 “說書人”的痕跡,在進入故事之前,先以 “話本說書”的形式開場,繼而在神秘古韻中,聽敘事人娓娓道來一個 “傳奇”的故事,結尾則往往又回到 “說書人”的立場,收束全篇。
其前期小說中,張愛玲作為敘事人,似乎始終一副冷靜客觀、置身事外,甚至有高高在上的感覺,從 《傳奇》的封面即可看出。“封面是炎櫻設計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張時裝仕女圖,畫著個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可是欄桿外,很突兀地,有個比例不對的人形,像鬼魂出現似的,那是現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窺視,如果這畫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氣氛。”[18]很明顯,這是張愛玲的一種暗示:敘事人本身在窺伺、在張看,并未置身其中,而是隔著 “欄桿”朝里望。作者以一個現代人的形象暗喻敘事人,刻意地將敘事人和故事中的人物拉開距離,使敘事人充當故事的 “見證者”。同時正是因為旁觀者的姿態,可以客觀冷靜地評述 “欄桿”里發生的一切,因而敘事人又扮演了 “評判者”的角色,可以淡然從容地對筆下的人物進行刻寫與審視。
在張愛玲前期小說中,對敘事人聲音的處理并不避諱,敘事人常以 “顯身”的姿態穿插在行文敘述中,間或出現,而其后期中短篇小說創作,因涉及很多自傳性材料的書寫,敘事立場不可能做到客觀冷靜,不可避免地會帶入很多的主觀感受。“《浮花浪蕊》里面是有好些自傳性材料,所以女主角脾氣很像我。”[19]女主角洛貞的確很有幾分張愛玲自敘傳的色彩,前途未卜、飄渺天涯;《同學少年都不賤》更是注入了許多張愛玲的親身經歷,教會女校的生活、同父親抗爭、為了愛情不顧名分、和愛人分開、獨自在海外以翻譯為生,等等。因此其后期中短篇小說中,“身世之感”常會不自覺地流露在紙上,尤以 《浮花浪蕊》和 《同學少年都不賤》為最。作者儼然已從冷漠超然的 “旁觀者”轉化為自憐自傷的 “當事人”,敘事人的態度更為含蓄、隱藏,不再以 “說書人”的姿態暴露,也不再與人物刻意地拉開距離,而是時常隱蓄在人物之中,自覺不自覺地流露出敘事人的態度。“秋夜、生辰,睡前掀簾一瞥下半夜的月色,青霜似的月色,半躺在寒冷的水門汀陽臺欄桿上;只一瞥,但在床上時時察覺到重簾外的月光,冰冷沉重如青白色的墓石一樣地壓在人心胸上,恒古的月色,閱盡歷代興亡的千百年來始終這樣冷冷地照著,然而對我,三十年已經太多了,已經像墓碑似的壓在心胸上。”[20]前期的人生經歷帶給張愛玲太多的沉重與傷痛,自幼家庭破碎、父母親情疏淡、愛情背叛,無一不給張愛玲的心靈烙下了不可磨滅的傷痕。因而張愛玲在《浮花浪蕊》《同學少年都不賤》等后期中短篇小說中,采取了一種隱晦、不直露的表達方式,把敘事人的聲音隱藏其間,相較于前期那種由 “旁觀者”造成的距離感在這里消失了,更多的真切感受在行文中流蕩。敘述人仿佛與主人公合為一體,那種親切可感的確是作者后期 “平淡而近自然”風格的極好印證。
“甘道迪死了。我還活著,即使不過在洗碗。”是最原始的安慰。是一只粗糙的手的撫慰,有點隔靴搔癢,覺都不覺得。但還是到心里去,因為是真話。《同學少年都不賤》
船小浪大,她倚著那小白銅盆站著,腳下地震似的傾料拱動,一時竟不知身在何所。《浮花浪蕊》
因為投射了太多自傳性材料的緣故,女主角趙玨宛如張愛玲的化身一般,因而她在美國的生活窘困就如同張愛玲在美國孤獨艱難的生活寫照一般。面對自身生活的不如意和友人恩娟夫榮妻貴的云泥之別,她只能用自嘲似的原始安慰撫平自己內心的塊壘。而孑然一身、天涯羈旅、遠赴海外謀生的洛貞,作者更是在散漫的敘事中,寄予了太多的身世之悲。人在途中的不確定感、隔離時空的孤獨感、顛簸不平的行旅、前途未卜的惘然,都在洛貞漂泊的苦痛中盡現。“當事人”的敘述姿態使其在前期小說中頻繁出現的反諷和調侃難尋蹤跡,取而代之的是一種 “感同身受”的認同與無奈。然而即便有很強的自傳色彩和主觀情感的滲入,張愛玲的敘述也始終是平淡自制的,文中的語氣始終都是淡淡、不起波瀾的,她鎮定從容、一樁樁生活細節、一個個場景還原,娓娓道來,沒有過度的情感宣泄,沒有刻意的雕琢打磨,如璞玉般自陳讀者面前,這同前期張愛玲帶給讀者的傳奇化敘事方式存在很大的不同。
(二)從 “注重情節”到 “淡化情節”
張愛玲在前期小說創作中向來都是注重情節的,她在 《論寫作》一文中曾說:“是個故事,就得有點戲劇性;戲劇就是沖突,就是磨難,就是麻煩。”[21]1944年 《傳奇》出版時張愛玲在扉頁題詞中寫道:“書名叫傳奇,目的是在 《傳奇》里面尋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尋找傳奇。”雖然作者刻意地強調她的“去傳奇化”敘事,但也僅僅是從 “普通人”的人生經歷里去創造 “傳奇”,絕沒有否定她對情節的關注。前期的主要小說,如 《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金鎖記》《茉莉香片》《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等,都很具有傳奇色彩,小說情節緊湊、故事性也很強。
張愛玲的后期小說在情節方面卻逐漸呈現淡化趨勢,《相見歡》《浮花浪蕊》《五四遺事》《同學少年都不賤》,都不以故事性見長,敘事相當松散,情節單一,沒有戲劇沖突,只于平鋪直敘中完成敘事。只有短篇 《色,戒》具有較為明顯的戲劇沖突。然而,《色,戒》帶給讀者的傳奇之感也主要源于 “間諜”類小說素材的原型本身,并非出于作者對故事本身的刻意經營和對情節的離奇化設置,以張愛玲早期小說中所彰顯出的對情節戲劇化精當處理的絕佳天賦,她自當有能力將這一極富傳奇色彩的素材創造成一個驚險詭譎的作品。然而張愛玲卻并不如我們所期待的一般,在 《色,戒》中她著意于對 “平淡而近自然”氛圍的營造,有意淡化情節,只是通過 “易公館的麻將桌”“印度珠寶商店”這兩個集中場景的轉換交代了整個故事,將一個本可處理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間諜故事,化解得波瀾不興。促使張愛玲后期逐漸淡化情節、消弭傳奇性、故事性的重大轉變,不能不說源于張愛玲對 《紅樓夢》含蓄內斂、平淡自然的內在審美風韻和古典精髓的繼承與挖掘,是張愛玲對紅樓精神內化在小說創作中的表現。
張愛玲前期小說創作,無論是流光溢彩的語言表達、生動傳神的人物塑造還是諸多藝術手法如細節描寫、景物襯托、意象構造等方面,都和 《紅樓夢》都很形似,不難看出作者受紅樓影響之深。而其后期中短篇小說卻難再說與 《紅樓夢》形似了,這自然不是因為張愛玲紅樓情結的消失,她一生鐘愛紅樓,晚年更是花了數十年潛心研究,并創作出 《紅樓夢魘》這部學術著作。她并非放棄了從 《紅樓夢》中汲取創作養料,只是對 《紅樓夢》的理解和領會更為深入透徹,已從前期對紅樓外在形式的模仿轉向對其內在精髓的接受。后期張愛玲在創作中對生活本身的真實再現極其偏愛,而其逐漸淡化情節、追求含蓄韻致的嘗試也是對 《紅樓夢》內在審美的傳承,是一種 “平淡而近自然”風格的內化和蘊藉。《海上花列傳》對張愛玲的影響更是促成了其后期 “平淡而近自然”風格轉化的重要影響質素。“《海上花》其實是舊小說發展到極端,最典型的一部,特點是極度經濟,讀著像劇本,只有對白與少量動作;暗寫、白描,又都輕描淡寫不落痕跡,織成一般人的生活質地,粗疏,灰撲撲的……并無艷異之感,在我所有看過的書里最有日常生活的況味。”[22]張愛玲晚年花費了頗多的時間翻譯吳語版 《海上花列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她欣賞這部小說極富日常生活況味,并在潛移默化間移植于自身創作。誠然,張愛玲是接受并十分贊許 《海上花列傳》的寫實手法的。在《同學少年都不賤》中,作者敘述含蓄、淺近,時斷時續,情節散漫無邊,似乎沒有一個統一的主題,而是把散亂的情節雜糅其間,不斷淡化情節,只將日常生活中的細碎瑣屑一點點地呈現給讀者。這不能不說和 “《傳奇》時代”張愛玲的文風華麗、絢爛奪目形成了極大的反差對照,也著實讓不少讀者頗為不適,很多人不免生出張愛玲江郎才盡、后期創作力衰退之談。亦舒便曾對 《相見歡》做過這樣的評價:“整篇小說約兩萬許字,都是中年婦女的對白,一點故事性都沒有,小說總得有個骨干,不比散文,一開始瑣碎到底,很難讀完兩萬字,連我都說讀不下去,怕只有宋淇宋老先生還是欣賞的。”[23]而我們認為,這一轉變,正是作者后期追求 “平淡而近自然”的美學效果的苦心經營。
《相見歡》以一對久別重逢的表姐妹的對話結構全篇,正如亦舒所言,確是 “一點故事性”都沒有,文中拉拉雜雜,由人物對話漾開,細細碎碎牽扯出表姐妹今昔過往的人生遭際,都是最細碎的真實,既沒有驚心動魄的大喜大悲,也沒有纏綿悱惻的離散聚合,作者特意以苑梅的視角來看這一對表姐妹的生活,她們的時光消磨在對話中,幾個月之前剛說過的話再度提起,聽的人和說的人,居然都全無印象了,苑梅驚訝于這一事實,卻發現當事人根本毫不在意,這就是他們所處的真實生活——瑣碎到毫無意義、無知無覺地過活。張愛玲正是想保持生活本真的質地,因此幾乎犧牲掉了對小說情節的構建,生活稀疏真實的質地才是作者想展示給讀者看的,她想表達的是:這便是生活。在生活中,情節從來不是重點,只有永無止境的細瑣和無聲無息的庸常以及那不斷被磨蝕掉的熱情和生命力。張愛玲就是靠著點點滴滴細碎的、片段化情節以一副破碎的支離面貌結構全篇的。在敘寫趙玨的人生經歷中,不斷被其他人物的經歷所截斷,不斷截斷不斷重續,在斷斷續續的敘寫中,情節的完整性尚且不能保證,更何談情節的傳奇性。從少女時期教會生活的回憶,到中年時期,趙玨漂泊異鄉、為生計所難,而恩娟夫榮妻貴、風光無限,這對昔日的同窗好友,因為境遇的懸殊,早已模糊了舊日的情誼。作者著意描寫她們別后重逢的對話、動作、語言、神情,將二人疏離而各懷心思的尷尬與無奈盡情呈現,在間斷的絮叨回憶和敘述中,無數瑣屑和繁雜的生活片段一點點連串成了趙玨的灰色人生。她不再似前期般追求情節的戲劇性和傳奇性,雖然前后期她一直堅持的都是寫普通人小人物的故事,然而從前期小人物的情節營造轉向對生活質地的自然呈現,這確是其后期中短篇小說 “平淡而近自然”風格的表現。
(三)敘事結構的轉變
張愛玲前期小說大多采用 “焦點透視”的結構,后期則主要采用 “散點透視”的結構。這兩種不同敘事結構的內涵,同繪畫藝術一脈相承,“焦點透視”符合人的視覺真實,講究寫實性,它嚴守一個特定的視點去觀察和摹寫事物。“散點透視”則更符合人的心理真實,強調的是內在的真實,它不拘泥于一個視點,而是通過多重視點、多角度去表現事物,更注重寫意性。張愛玲后期采用 “散點透視”的敘事結構,不再似前期敘事結構緊湊、集中,而是平鋪直敘,不刻意集中在一點上進行敘事,顯得散漫無章。她后期的5篇中短篇小說中,尤以 《浮花浪蕊》結構最散,“《浮花浪蕊》最后一次大改,才參用社會小說做法,題材比近代短篇小說散漫,是一個實驗。”[24]
張愛玲前期小說,主題明確、結構緊湊、敘事集中,即便如 《封鎖》《留情》這樣內容較為平淡的作品,也是情節集中,并無零散之感,或選取固定的敘事地點,或敘事線索明晰,敘事緊湊,環環相扣,并無游離之感。后期的中短篇小說 《相見歡》以一對別后重逢的表姐妹的對白展開,推進情節發展,全篇敘事,似乎沒有一個明確的主題,時而在現實的細碎瑣事中打轉兒,時而插播進一段段回憶,作者到底想表達什么,似乎很難把握。這相較其前期 《金鎖記》《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等敘事完整、主題鮮明的作品來,實在是如同一篇毫無重點的流水賬似的文章。《浮花浪蕊》寫女主人公洛貞輾轉漂泊,從上海,到香港,后來又遠赴日本,一段段艱辛的歷程,又在行文間插入了對鈕太太的敘述,全篇在過去、現在和對將來的惶惑中不斷跳脫、切換,很有一種 “意識流”的感覺,作者也顯然有一種模糊時空的感覺。《同學少年都不賤》的敘事結構顯得更為支離破碎,開頭是從女主人公趙玨看到了 《時代周刊》上恩娟的特寫展開回憶。在回憶過程中,又不斷跳脫出來,插入現在的經歷,以及和恩娟久別重逢后彼此的疏離與相互算計,把各自人生遭遇截取了一個個斷面呈現出來。全文由一個個片段連綴成篇,沒有刻意拼湊的痕跡,只是著實顯得散漫零碎。“散點透視”是張愛玲受 “社會小說”啟發所使用的一種實驗手段。
敘事結構之所以發生了由 “焦點透視”到 “散點透視”的轉變,和她前后期不同的創作環境息息相關。張愛玲前期是在20世紀40年代的上海這樣一個大環境下創作,上海市民是她的主要讀者群,她作為一個以文謀生的職業作家,在商業環境下寫作,必然要考慮到讀者群體的審美趣味和需求。而她的作品大多是在 《紫羅蘭》《亦報》《天地》等通俗期刊上發表,必然要照顧到讀者的口味和期刊的要求,“焦點透視”的結構使小說節構緊湊、情節集中、故事性強、戲劇沖突激烈,這樣可讀性才會高。正是因為“焦點透視”的敘事結構具有以上特點,才成了張愛玲為了博取讀者喜愛、吸引讀者受眾的重要工具。而后期張愛玲,海外英文創作受挫,遠離故國獨居異鄉,擺脫了商業期刊的創作環境,讀者群體也從前期的相對固定變得茫然不定,張愛玲自己在創作過程中,很有可能都不明確自己是在為哪一部分讀者群體來創作。正是因為作者在后期創作過程中,不用再過多考慮讀者期待和期刊要求,她才可以更為自由地選擇自己的創作題材、創作方式和表現手法,不再一味地去吸引讀者眼球,而是可以更多地從自我感受出發,不斷沉淀、升華,寫出自己想要表達而非讀者想看到的作品。
宋淇在 《私語張愛玲》一文中曾說:“多年前我曾勸過愛玲不妨先寫一本暢銷的小說奠定了文壇上的地位再說,并且還自作聰明向她建議一個容易討好的題材,只要動筆寫就行;她的答案是斬釘截鐵的。‘不!我絕不寫自己不想寫的人物和故事。’”[25]張愛玲后期對所寫內容堅持自主性和自我性可見一斑,這也正是她后期堅持使用 “散點透視”結構的執著所在。她后期的這幾個中短篇小說都經過反復修改,“這三個小故事都曾經使我震動,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寫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來只想到最初獲得材料的驚喜,與改寫的歷程,一點都不覺得這其間三十年的時間過去了;愛就是不問值不值得,這也就是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了。”[26]她想表現的不再是傳奇化新奇刺激的故事,那是上海時期商業背景下催生出的 “傳奇”,后期的張愛玲,是遠離了商業社會,摒棄了 “出名要趁早”的浮華、拋下了前半生 “華麗緣”的張愛玲,表現生活最本真的本來質地,才是她的愿景。因此,選擇 “散點透視”的敘事結構,也是和她后期 “平淡而近自然”風格最和諧的匹配。
四、張愛玲后期中短篇小說的心理描寫
(一)直接心理描寫的前后期轉變
“在文字的溝通上,小說是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只有小說可以不尊重隱私權,但是并不是窺視別人,而是暫時或多或少的認同,像演員沉浸在一個角色里,也成為自身的一次經驗。”[27]這種創作觀念無疑使張愛玲的小說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心理深度,張愛玲在前后期中短篇小說創作中,都不乏對人物的直接心理描寫,通過對 《傳奇增訂本》中15篇小說和后期5篇中短篇小說的詳細梳理和分析,我們發現張愛玲在對人物進行直接心理描寫時,主要采用的是間接引語的方式,只在 《金鎖記》《傾城之戀》《第一爐香》《留情》4篇中有一兩處直接引語,后期則只有 《相見歡》《同學少年都不賤》各有一處直接引語。張愛玲小說直接心理描寫的前后期轉變主要集中在以下3個方面。
其一是心理描寫的數量、密度對比前期大幅降低,程度與筆墨較之前期都大為簡省。前期小說 《第一爐香》中直接心理描寫有24處之多,《金鎖記》《傾城之戀》中直接心理描寫有23處,《紅玫瑰與白玫瑰》則有15處,其余的前期小說中直接心理描寫10處以上的有 《年輕的時候》《封鎖》等。在后期的中短篇小說中,使用直接心理描寫次數最多的 《色,戒》也僅有12處,而最少的 《五四遺事》只有2處。前期作者常常采用整段或者連續幾段的大篇幅心理描寫,后期則往往單獨成句,簡筆勾勒,完全沒有借題發揮的意思。
是馬太太話里有話,還是她神經過敏?佳芝心里想。《色,戒》
這個人是真愛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轟然一聲,若有所失。《色,戒》
丈夫弟妹都走了,她不免有落寞之感。《相見歡》
心里不禁想著,其實她也還可以穿得好點。《相見歡》
兩三年了,上海人倒也還是這樣,洛貞想。《浮花浪蕊》
“還是我一句話撮合了他們。”她不免這樣想。《同學少年都不賤》
張愛玲已不再似前期創作一般,著意集中去展現人物矛盾復雜的內心活動,只一味地用最經濟的筆墨,顯得零散隨意。在本文第二章論述中,我們提到張愛玲在后期創作中摒棄掉了前期小說中 “顯身”的、 “旁觀者”的敘事,有意含蓄地將敘事人的聲音隱藏在人物的心聲之中。這就使其后期小說中人物的心理描寫也不似前期集中,“《浮花浪蕊》最后一次大改,才參用社會小說做法,題材比近代短篇小說散漫,是一個實驗。”[28]《相見歡》《同學少年都不賤》《浮花浪蕊》等后期作品,相較前期的敘事,尤其是心理敘事顯得松散了許多,有時會給人一些雜亂無章的渙散之感,這些跟作者的敘事人姿態是不無關聯的。
其二是前期善用參差對照的心理描寫手法,后期心理描寫則無明顯的對立沖突,宛如流水賬一般,只有零星的感覺碎片。
前期心理描寫的參差對照,主要包括兩種:其一,展現不同人物之間的心理沖突。《金鎖記》中的23處心理描寫,橫向展現了七巧、季澤、長安、芝壽、童世舫等不同人物的各異心理。《鴻鸞禧》中,作者也巧妙地運用了參差對照的心理描寫手法。其二,參差對照心理描寫的另一個方面,則是展現同一個人物前后不同的心理變化。這一點在 《第一爐香》中有突出的體現。張愛玲通過對薇龍心理流程的細細描摹,將薇龍由一個女學生走向墮落交際花的心理過程描繪得細膩、流暢、自然。
張愛玲后期小說中人物的心理描寫,則只是只言片語零星感覺的碎片,既不似前期創作一般有明顯的心理沖突,也沒有人物前后不同的心理變化,只集中描寫某一人物的心理活動,不再對其他人物的心理過多顧及, 《五四遺事》的心理描寫聚焦在男主人公羅文濤身上,《同學少年都不賤》則集中描寫的是女主人公趙玨的心理感覺,《浮花浪蕊》《色,戒》則分別描寫的是女主人公洛貞、王佳芝的心理。與前期采用參差對照的心理描寫手法或為了塑造人物性格,或為了襯托環境不同,后期創作中作者所要體現的,正是跟隨意識的流動,節制地展現不同生活斷面或情境的人物細碎真實的感覺。因為作者的后期小說對情節的淡化處理,使人物本身不太可能被置于矛盾沖突劇烈的情景之下,沒有起伏波瀾的戲劇沖突,只是斷斷續續、零散的支離破碎的松散情節,隨意兩筆,簡簡單單、不加修飾、一筆帶過地閃現幾下人物的心理。同時敘事人的位置,也由前期創作的 “顯身”轉向后期創作的 “隱身”,敘事人和人物的心理往往融為一體,于是后期小說中人物的心理描寫,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敘事人的態度情感。
她又是個東方人,也許越共之外的東方人,他們都恨。她心里這樣想著。《同學少年都不賤》
我們這一代最沒出息了,舊的不屑,新的不會,她有時候這樣想。《浮花浪蕊》
不難看出,敘事人的態度始終是平淡自制的,雖然感覺敘事人一直隱匿于主人公心聲之中,與人物同呼吸共命運,然而敘述的語氣始終不起波瀾、從容自制,在一樁樁生活細節和一個個場景交替穿插中,人物的心理感受,如清溪般自然流淌,不著痕跡,全不見刻意經營之工。
其三是前期創作心理描寫內容駁雜,既有對人物變態心理的種種描繪,又有對人格分裂的精彩展示,后期創作內容則單調許多,注重描述人物的直感,不做多余筆墨的延展。在前期小說中,有不少篇目對人物的變態心理都有集中展現:《心經》表現了許小寒的戀父情結;《茉莉香片》表現了聶傳慶扭曲的戀母情結; 《第一爐香》展現了梁太太的變態性心理;《花凋》中的鄭太太不滿坐吃山空如 “泡在酒缸中的孩尸”一樣的丈夫,卻又沒有勇氣離婚,在無意識中轉移著自己的性饑渴,把最大的熱情投注在挑選中意的女婿這件事上,將其視作 “她死灰生命中的一星微紅的炭火”。還有 《第二爐香》中愫細的性停滯和《封鎖》中吳翠遠被家庭和職業所困的性壓抑。《金鎖記》則講一個麻油店家活潑女兒曹七巧,不幸被嫁入姜家,面對無愛的婚姻、非人的精神折磨,逐漸淪為金錢的奴隸,一生情欲得不到滿足的她,又把自己的不幸轉嫁到自己的兒子和女兒身上,先后逼死了兩位兒媳,女兒長安30多歲也沒能嫁出去,最后她在眾叛親離和人格分裂中凄然死去……張愛玲后期小說中的心理描寫,則注重描述人物的直感,往往給人物的心境一個直接明確的界定,不做多余筆墨的延展:
近來羅每次回家,總是越來越覺得對不起密斯范。《五四遺事》
太快了她又有點擔心。他們大概想不到出來得那么快。《色,戒》
這個人是真愛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轟然一聲,若有所失。《色,戒》
她母親當初就是跟父親一塊出去的,她還是在外國出世的,兩三歲才托便人帶她回來,什么都不記得,多冤!聽上去她母親在外國也不快樂,多冤!《相見歡》伍太太有點詫異,她表姐竟和一個盯梢的人搭話。《相見歡》
是真天翻地覆了,她惘惘地想。《浮花浪蕊》
她愛他,趙玨想,心里凜然,有點像宗教的感情。《同學少年都不賤》
趙玨笑了,覺得十分意外,她還以為是她妒忌。《同學少年都不賤》
趙玨心里很感動。《同學少年都不賤》
“對不起”“有點擔心”“若有所失”“多冤!多冤!”“詫異”“惘惘”“凜然”“十分意外”“感動”這些都是對人物直感的描述,作者寥寥數語、不做任何多余筆墨的延展鋪陳,同前期創作通過心理描寫展現龐雜豐富的內容相比,張愛玲后期小說的心理描寫內容擔當的分量顯然輕了太多。既沒有前期創作對人物變態心理的展示,也沒有對人格分裂的剖解,內容單調、只一味直陳。作者顯然摒棄掉了對人物復雜心理世界的深挖和追索,只對日常生活中的人物心理做最直白淺近的記述,這即是張愛玲后期創作對人物心理描寫偏重白描的追求所在。
(二)從重 “意象”到偏 “白描”
除直接的心理描寫之外,張愛玲前期小說采取的心理描寫手法很多,如利用色彩對人物的心理暗示、利用景物描寫襯托人物心理等,而其中最出彩、藝術效果最高的實屬 “意象”手法的使用。在其后期中短篇小說中,作者做了意識流、自由聯想等方式心理描寫的嘗試,以白描展現人物內心則是其后期最為顯見的手段。所謂白描,原是中國繪畫的一種技法,繪制時僅以墨線勾劃物象,不著色彩,而后被引用到文學創作之中,成為一種技法,要求用最簡省平白的筆墨,抓住對象的主要特征,如實刻寫其情態面貌,不事雕飾。
“意象”在張愛玲前期小說里用來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使作品極具聯想和想象,也使寫實性的文本充滿了濃厚的抒情色彩,使其前期小說在展現人物心理時顯得頗為形象精到、引人深思。而后期張愛玲,在進行心理描寫時,尤愛白描,“我是實在向往傳統的白描手法——全靠一個人的對白動作與意見來表達個性與意向。”[29]
張愛玲前后期創作側重不同的心理描寫方式,在其前后期小說的開頭和結尾處,便已有明顯呈現了。在前期小說中,張愛玲的蒼涼,在篇首即以各色紛呈的 “意象”向讀者悠悠道來,這些意象或是難掩凄涼的濕暈月色,或是胡琴拉來拉去的走了板的曲調,或是在霉綠斑斕的銅香爐里燃著的沉香細屑,在結尾處,張愛玲往往再次回到 “意象”本身,前后照應,極具藝術表現力。
相較于前期創作,張愛玲后期中短篇小說中的心理描寫,“意象”難尋,而以 “白描”見長,用極經濟的筆墨,自然勾勒出人物的形態風貌,進而表現人物的內在心理,通過這種 “平淡而近自然”的手法,描摹出人物的微妙心理,展現人物細微真實的感覺狀態和瑣屑煩雜的生存窘境。以后期小說的開頭結尾做舉,《五四遺事》開篇是以兩對青年男女泛舟西湖、吃菱角,互相調侃開頭,而以范文美攜3位妻子隱居于西湖之畔被人調侃 “關起門來正好湊一桌麻將”做結;《相見歡》以一對久別重逢的表姐妹絮叨的家常對話開篇,同樣以日常對話做結,全篇都是由細碎的對話推動情節發展;《浮花浪蕊》的開頭選在一艘即將開船的貨輪上,女主人公即將遠赴外海、漂泊羈旅,結尾也以旅途中的女主人公生出天涯渺遠之嘆收束全篇;《同學少年都不賤》始于認出 《時代周刊》上的一張特寫是自己少時好友恩娟,終于報紙上恩娟的照片,可謂渾然天成、不著一絲刻意。唯有 《色,戒》一篇由于題材的特定性,在后期的5篇小說中,戲劇性和傳奇性色彩較濃,較為重視氛圍的渲染和營造,以麻將桌上的官太太相互攀比鉆戒開篇,強烈的燈光對照和人物的意識流動,但是這一切和前期創作的以 “意象”作為籠罩全篇的氛圍基調相比,誠然是不足為奇的。
在張愛玲前期小說中,多有經典性的意象出現,常選取含義深刻、賦予了多重色彩的月亮、屏風、玻璃、鏡子、玫瑰等這些或易碎易逝、或陰柔脆弱的事物作為意象來敘述故事背景,營造出蒼涼的小說氛圍,用來表現人物的微妙心理和對生命、對人性的悲觀感悟。
張愛玲后期的幾篇中短篇小說,卻常用白描手法揭示人物心理,不刻意經營,也不著意暗示,只一味將普通人最本真的生活質地剖白,于枯淡瘦勁中勾勒出最細微的心靈反應,尤以 《同學少年都不賤》為最。
“喝咖啡?”倒了兩杯來。”“可好?”也只能帶笑輕聲一提,不是真問,她也不會真回答。她四面看看,見是一間相當大的起坐間兼臥室,凸出的窗戶有古風;因笑道:“你不是說有兩間房?”恩娟不確定的 ‘哦’了一聲,那笑容依舊將信將疑。趙玨感到困惑。倒像是騙她來過夜。[30]
少時一對親密無間、無話不談的閨中密友,數十年不見,本該一訴離別之苦、各訴衷腸,然境遇懸殊卻讓二人心存芥蒂、沒話找話、不咸不淡的寒暄和試探,時過境遷、昔日友誼不復,彼此的隔膜和疏離自是心照不宣。《同學少年都不賤》中此類的白描,比比皆是,在人物三言兩語的對話背后,蘊蓄著太多復雜微妙的心理內容,相對于前期創作中人物在表達自己內心想法時或妙語連珠擅用譬喻,或玲瓏智巧不著痕跡,張愛玲在后期創作中展現人物內心世界時的表現的確是惜字如金、藏而不露。只寥寥數語、簡筆勾勒,最粗疏的線條,卻把人物最細致真實的心理活動盡顯無遺。
張愛玲后期一直沉浸于對 “白描”手法的鐘愛,這和她對 《紅樓夢》和 《海上花列傳》平淡自然的精神內涵的深刻領悟是分不開的。
《海上花列傳》出自晚清落魄文人韓邦慶之手,卻得到了張愛玲的青眼有加,這在很大程度上和《海上花列傳》的美學風韻與 《紅樓夢》相似大有關系。“《海上花》其實是舊小說發展到極端,最典型的一部,暗寫,白描又都輕描淡寫不落痕跡,織成一般人的生活的質地,粗疏,灰撲撲的……所以題材雖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并無艷異之感,在我所有看過的書里最有日常生活的況味。”[31]張愛玲所推崇的,正是 《紅樓夢》《海上花列傳》中借重的反映生活本來面貌的白描之法,而正是白描手法的精當使用,使張愛玲后期小說中人物的細微心理得以呈現,并自然而不生硬。《同學少年都不賤》中趙玨在面對中年之后與少時好友恩娟云泥之別的境遇,心中無奈蒼涼又無限感傷,所以當她得知甘西迪死了的消息,便生出了 “甘西迪死了,而我還活著,雖然不過是在洗碗”的心思。她稱這是最原始最粗糙的安慰,雖然不過隔靴搔癢一般,將趙玨微妙曲折幾分自欺欺人的心理摹寫得自然傳神。《相見歡》也是通過一系列細節描寫展現人物情感的。雖然荀太太已人到中年、身體發福,可荀先生對她的感情絲毫不減,從他一進客廳,就十分關心自己妻子的衣飾、從他對妻子溫柔的語氣、深情的目光等細微處便可看出,拼湊起這些 “夾縫文章”,不難看出作者在文中隱蓄的這些意趣和情思來。
白描手法的嫻熟運用,使張愛玲后期的中短篇小說更貼近生活的本真形態,更接近生活的本來質地,觸及到了更真實、更平凡的人性和人情,達到了她后期一直追求的 “平淡而近自然”的審美境界。
五、結語
張愛玲后期創作意在追求中國古典小說中那種 “平淡而近自然”的審美風韻,其創作風格發生了明顯轉變:在語言修辭風格上,從 “絢麗”到 “平淡”、從 “繁復”到 “精簡”、從 “多樣”到 “簡約”;在敘事方式上,敘事人位置從 “顯性”到 “隱性”、從 “注重情節”到 “淡化情節”,敘事結構從 “焦點透視”到 “散點透視”;在心理描寫上,前后期的直接心理描寫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從重 “意象”到偏 “白描”。
不少學者認為張愛玲后期創作與前期創作的巨大差別是其創作力衰退的表現,但我們以為,雖然其前期作品給作家帶來了巨大的聲譽,但她并未停滯不前,而是在后期創作中注入了自己新的思考和追求,進行了大膽和執著的嘗試,希圖將中國古典小說所特有的 “平淡而近自然”的審美風格融入現代小說中,盡管其后期創作成就未必能如同前期創作一般輝煌,也是和作家后期生活境遇、晚年心態、創作追求、審美理念等密切相關的。簡單區分優劣的價值判斷顯然意義不大,我們更應關注作為一個完成了自己文學生命轉變的作家個案,其本身存在哪些特殊性,對于同一時代或者其后的作家創作是否存在影響。不可否認的是,作家后期創作風格的轉變是她對前期創作模式的突破與創新,在一定程度上也為中國小說傳統的現代性轉化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1][2][13]子通,亦清.張愛玲評說六十年[M].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1:23、23、69.
[3]傅雷.傅雷文集(文學卷)[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171.
[4][21]來鳳儀.張愛玲散文全編[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2、82.
[5][6][20][25]宋以朗.張愛玲私語錄[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2:44、45、117、36.
[7][8][9][10][11]張愛玲.張愛玲典藏全集——1945以后中短篇小說作品[M].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2003:63、62、81、85、239.
[12][30]張愛玲.同學少年都不賤[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51、35.
[14][17][22][24][26][27][28][29][31]張愛玲.重訪邊城[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14、135、23、121、121、120、121、133、23.
[15][16][美]薩義德.知識分子論[M].單德興,譯.北京:三聯書店,2009:53、45.
[18]張愛玲.張看[M].廣州:花城出版社,1997:376-377.
[19]夏志清.張愛玲給我的信件[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240.
[23]亦舒.亦舒新經典[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23.
[32][33][34]張愛玲.色,戒[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7:203、192、210.
[責任編輯:志 洪]
I206.7
A
1674-3652(2016)06-0087-11
2016-09-09
唐娒嘉,女,湖北襄陽人。主要從事現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