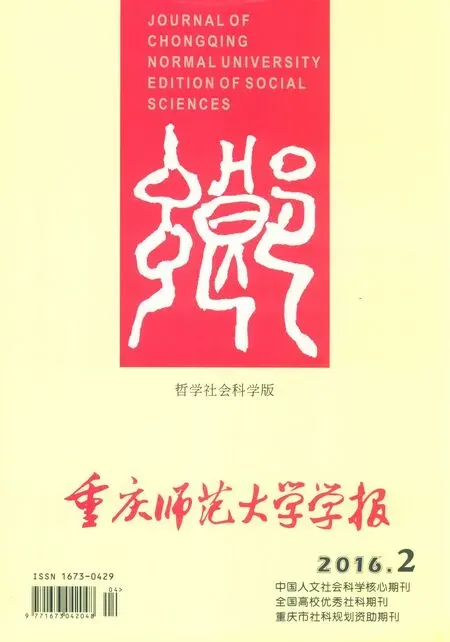從清初科試論侯方域的晚節問題
明 月 熙
(貴州大學 人文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
從清初科試論侯方域的晚節問題
明月熙
(貴州大學人文學院,貴州貴陽550025)
摘要:侯方域作為“復社四公子”之一,在明末清初的士林中頗具影響力和號召力。但因參加順治八年(1651)鄉試一事,侯方域在人格與道德上遭到世人質疑和批判。另外,又因為《桃花扇》中的戲劇形象深入人心,后人對他的認識亦多有爭議,而這種對其為人的偏見甚至還延及了對其詩文的客觀評價。本文本著“了解之同情”的學術態度,通過解析侯方域的詩文作品,對其從歸隱到應試的心路歷程進行全面觀照,從而盡可能地還原易代士人的生存狀況與心靈困境。
關鍵詞:侯方域;明末清初;科舉;晚節
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河南歸德府(商丘)人,為晚明復社四公子之一,入清后又與魏禧、汪琬并稱古文“清初三大家”,而后更因孔尚任《桃花扇》所寫與李香君情事而家喻戶曉。侯方域一生熱衷于政治活動,在明末曾多次協助父親侯恂處理軍務,代擬奏疏,并在南明弘光朝時期,依附史可法、高杰帳下,從事幕僚文書工作。在入清后,侯方域又曾為三省督撫張存仁剿滅榆園軍出謀劃策,上呈《剿撫十議》,總結了自己的平亂剿寇的具體措施,這也成為后人對其進行道德批判的重要原因。而侯方域順治八年(1651)參加豫省鄉試一事,更是令其人格倍受質疑。本文筆者著重從以下三方面來討論侯方域入清后的應舉以及隨之產生的“晚節不保”問題。
一、侯生赴考清試的社會評價
順治八年(1651)豫省鄉試,是侯方域一生中最大的道德“污點”,也是其科舉生涯的又一次失利。這一次清廷科試同樣延續了明代八股取士的方式,但侯方域此次應試卻與崇禎十二年(1639)南雍秋試得到的評價截然不同。南雍秋試侯方域雖然鎩羽而歸,但卻事出有因,他也因為其策論針砭時弊而名噪一時,反倒獲得士林的普遍贊譽。而且,明末的應試屬于封建王朝中士人選擇的正當的進身之道。然而順治八年(1651)清廷科試卻具有鮮明的“華夷大防”的色彩,侯方域的應考在很多士大夫看來無疑是對故明王朝的背叛,對異族政權的臣服,因此侯方域順治八年(1651)的應試受到了頗多質疑與非議。
特別是到了清中葉,當遺民故老中流傳著的故事、傳奇逐漸泯滅,人物形象也逐漸定型,再加上戲劇《桃花扇》的風靡,侯方域作為易代之際立場不堅定,性格懦弱游移的多情公子形象已是深入人心。而且,清中期的士人也往往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對于像侯方域這類存在著“晚節不保”問題的易代士大夫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比如孫原湘就在《媚香樓歌》結尾處極為尖刻地嘲諷侯方域:“氣節何論男與女,樓中如花霜可拒。君不見,天津二月桃花開,又見侯生應舉來。”[1]3
然而對于侯方域赴清廷科試一事,與之同一時期的商丘文人卻大多持理解和支持的態度。他們不僅認為侯方域的應試是“自愿”之舉,并視之為正常行徑,不存在失節之恥,而且還頗為他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忿忿不平。如宋犖所撰《侯朝宗傳》稱:“順治辛卯舉豫省第一,有忌之者,又斥。”賈開宗的《本傳》所載情況也基本一致,而徐作肅在《明經朝宗墓志銘》中則稱“順治辛卯,再舉河南第二,有議者復斥置副車”。對于侯方域考取名次與宋犖、賈開宗所記不一樣,并且還提到侯方域在順治十一年(1654),即“甲午病甚,更勉就試,而其年遂死矣”。徐作肅所記侯方域甲午年再次應試一事,在其他友人為其所撰傳文、商丘縣志及清史稿本傳中均未提及。但總的說來,徐、宋、賈等同時代友人都對侯方域參加清試持肯定態度,并且他們自己亦都參加了清廷的科試。
而清初大儒,亦是侯方域昔日復社同人的黃宗羲則認為:“姚孝錫嘗仕金,遺山終置之南冠之列,不以為金人者,原其心耳。夫朝宗,亦若是而已夫。”[2]225黃宗羲作為明遺民中成就最大的學者之一,他將侯方域仕清與姚孝錫仕金相提并論,認為侯生應試是被迫之舉。黃宗羲以遺民心態揣摩侯生之應試行為,并未對其進行指責和批評,而商丘友人則因感同身受,更無異議。
值得注意的是,時人不管是持自愿之說或是被迫之說,大都對侯方域參加清廷科試一事表示出理解和同情。侯方域第五世族孫侯洵則在《壯悔堂年譜》中解釋了侯方域參加清試的原因:“當事欲案治公以及于司徒公者,有司趨應省試,方解。”對于侯洵的記載,后人卻頗有質疑,認為是為尊者諱,有意回避,加之侯洵為第五世族孫,時隔較遠。但據同時期的宋犖《侯朝宗傳》中所載:“國初河南撫軍某公,廉知方域豪橫狀,將案治”,后經宋犖之父宋權從中調解,侯方域因此有書與宋犖感懷說:“昔叨受太保先公深知,嘗援其難”[3],即指宋權的調解之功,而結合侯洵年譜所言,宋犖在傳文中所記事即為侯方域應試的直接原因,強迫或利誘漢族知識分子應試是清初民族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
實際上,對于普通民眾而言,華夷之辨的意義并不大,他們并不太關注是在怎樣性質的政權下生活,他們更關注于小門小戶的具體生活狀況。然而士大夫長期受儒家夷夏之防思想的熏陶,在民族問題上極為敏感,同時又對南宋滅亡的歷史爛熟于胸,因此他們對于滿清異族政權的敵對和抵制甚至超過了對李自成的大順政權。而士大夫階層是社會的精英人群,他們擅長用筆墨文字將亡國的感受和議論記錄下來,并產生巨大的社會效應。因此,如果不能真正征服“士”這個階層,對于定鼎中原后的滿清政府而言,想要維持長期而穩固的統治是極為不利的。
為此,清廷采用了很多手段來籠絡士大夫,在嚴厲鎮壓他們反抗行動的同時,化解他們的敵對態度,爭取他們的支持或至少采取中立,是非常重要的環節。這是剿撫兼施政策在非戰爭場合中的應用,實際上這與侯恂、侯方域父子在剿撫榆園軍,分化農民起義陣營內部,逐個擊破的思想是一致的。而這種政策的繼續和擴大,體現了攻心為上的策略思想。清廷籠絡士大夫的政策具有系統性、延續性,并且始終作為一種重點政策處理。
二、清初的文化懷柔政策
首先,清廷通過征辟、薦舉、招降等途徑吸收故明官僚入朝為官。睿親王多爾袞從入關之初就一直在這方面進行部署,“諭故明內外官民人等曰:各衙門官員俱照舊錄用”,“其避賊回籍,隱居山林者亦具以聞,仍以原官錄用”;“順治初元,遣官征訪遺賢,車軺絡繹”;“并行撫按,境內隱逸、賢良,逐一啟薦,以憑征擢”。[4]卷一零九清廷這樣做,一方面是撫慰、安定龐大的故明士大夫群體,另一方面也是適應、滿足清朝統治廣大地區的需要。而原明大學士馮銓、李建泰被征為內院大學士,最具示范作用,清廷對故明高官的沿用對于漢族士大夫的吸引力是相當大的。
其次,清廷照搬了明朝科舉取士的制度。順治元年(1644)十月,順治帝于北京即位,頒布《條例》,將“會試定于辰戌丑未年,各直省鄉試定于子午卯酉年”;順治二年(1645)四月,清廷又確定鄉試辦法完全沿襲明朝舊制,不作變動,同時準開武鄉試;當年七月,時任浙江總督的張存仁上疏說:“近有借口薤發反順為逆者,若使反形既露,必處處勞大兵剿捕。竊思不勞兵之法,莫如速遣提學,開科取士,則讀書者有出仕之望,而從逆之念自息。”張存仁的建言得到采納后,順治三、四年,清廷連續舉行會試,取中進士六七百人。
另外,清廷又在刺激故明士人自愿赴考的同時,充分利用政權的力量,強迫各地不愿應考,又很有影響力的士子應試,以此起到示范作用,從精神上打擊和摧毀這些故明“伯夷”、“叔齊”的堅強意志。而侯方域作為晚明“復社四公子”之一,享譽天下,又出身于故明的官宦世家,在商丘當地,乃至中原地區有著文化領袖的地位,他一旦應試將意味著很多仍在觀望的士人必將紛紛效仿。在這樣的環境下,侯方域參加了順治八年(1651)鄉試,成為清廷民族政策的犧牲品。
而今人對侯方域此次應試亦是眾說紛紜,褒貶不一,像梁啟超先生就認為此舉確為晚節不保的失節行為,他說:“(侯朝宗)順治八年,且應辛卯鄉試,中副貢生,越三年而死,晚節無聊甚矣。”[5]512梁啟超這一看法在今人中頗有代表性,但少數學者則認為應該結合侯方域等士大夫當時的處境分析其心境,不必過分苛責。比如陳寅恪先生就認為對古人應有一種“了解之同情”。因此,對于侯方域順治八年(1651)應試一事,筆者認為既不可將“節操標準”虛無化,也不可將“道德尺度”絕對化。在當時士大夫的人生軌跡中有其實際存在的差異,而其各自人品操守亦自有高低,但是他們各自的人生選擇都確然出于自身切實原因,或迫于現實,或出于性情,而不能說遺民就一定比非遺民更高貴,反之亦然。
事實上,在清初,“遺民”是一個流行的時尚,很多士人借此來標榜與凸顯自己。“遺民”是否真的意味著對高尚節操的堅守是有待討論的。像美國學者王德威就已經指出這一疑點:“已有論者提醒我們明遺民論述虛浮、陰暗的層面,魯迅早就指出遺民可能流為沽名釣譽的‘逸民’現象。”[6]因此對于侯方域的應試一事,在本文中不做道德層面的評判,只著重分析其行為產生的原因和由此而來的連帶影響,包括其心態、詩文作品,以及現實處境等等。
三、侯生應試前的復雜心態
順治二年(1645),南明弘光政權覆滅。清廷為了籠絡舊明士紳,分化瓦解反清勢力,施行了一系列征聘措施:“世祖定鼎中原,順治初元,遣官征訪遺賢,車軺絡繹。吏部詳察履歷,確覈才品,促令來京。并行撫、按,境內隱逸、賢良,逐一啟薦,以憑征擢。順天巡撫宋權陳治平三策,首廣羅賢才以佐上理,并薦故明薊遼總督王永吉等。詔廷臣各舉所知。一時明季故臣如謝升、馮銓、黨崇雅等,紛紛擢用。中外臣工啟薦除授得官者,不可勝數。”[4]卷一零九并很快恢復了科舉考試。
同年八月,侯方域的好友彭容園參加了河南鄉試。當年冬天,侯方域自江南返回商丘,有《贈彭子序》與彭容園,其言云:“夫士之遇不遇,豈不以時歟!遇即幸,不遇非盡不幸。”在文中,侯方域認為遇與不遇取決于時機,遇即是幸運,而不遇也并非不幸之事,如好友彭子之才早在十幾年前已應得以重用,但與自己一樣都在崇禎十二年(1639)科試被黜,并引火上身,“當此時,未嘗不嘆彭子誠蚤達,必不如是!由今思之,彭子蚤達,豈止免鍛煉?”現在想來當時的挫折恰是天降大任之前的磨礪與鍛煉,正如彭容園一樣,侯方域本人亦是在科試中屢遭挫折,并在明末因身陷黨爭而輾轉飄零,同樣身為“選而復斥,以至困頓幾死者”,并非缺乏才華,實因“時不利也”,而現清廷科舉開試,選拔人才,正是建功立業的好時機。侯方域以前賢為例,“吾聞唐初如楊師道、封倫,宋初如范質、王溥諸公,其人者皆在前朝通籍,踐履顯赫,爾后乃知命通權,身輔圣主,功名足多者”,楊師道、封倫、范質、王溥等古人均曾歷仕前后幾朝,并在前朝“踐履顯赫”,侯方域并不視之為變節,“然而達節者少硁硁磋然議之,難以龍蛇之道喻也”,反視之“知命通權”,仕新朝而能“身輔圣主”,亦不失為伺機而動的君子所為。因此,在侯方域看來彭容園參加清試并非不光彩之舉,而是正常的用世之舉:“士誠有才,各當其世,乃為貴耳;即使且困窮,豈遂困哉!”[7]
侯方域父親侯恂曾為故明兵部侍郎,長期負責軍務事宜,而侯方域為復社貴公子,父子二人名氣都很大,因此清廷也征辟二人出仕。據康熙時期所修的《商丘縣志·侯恂傳》載:“本朝順治三年歸里,有明臣之在朝者多欲恂出為將,而中州撫按亦交章論薦”,侯恂則“謝不起,筑室城南,偃臥其中,足不入城市。”[8]而侯方域則表態:“嘆急虛名累”,“白幘名堪老,青蠅事可憎”,對于入仕新朝一事很是排斥,表現出對政治風云的厭倦,對于“當衙有薦章”很是無奈,自己“善鳴詆自誤”,只愿如“散木得無傷”,能以終天年。[9]但于此同時,他在清廷的壓力和出仕的誘惑下又很矛盾,“犁鋤春雨外,何以謝黔蒼?”他本有濟世之志,“頗以經濟自詡”,并不甘心就此歸隱,自覺未能盡到士大夫匡時濟世的責任,愧對黎民百姓。
另外侯方域在故明一朝科試受挫,父親侯恂又因陷入黨爭而屢遭迫害,自己也在江南屢次被阮大鋮派兵追捕。因此,可以想見侯方域對于明王朝的情感是比較復雜的,一方面家族深受皇恩,然而伴君如伴虎,宦海沉浮殊為不易,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另一方面他本人在明朝并無功名在身,僅為一介布衣,出仕新朝的負罪感不像故明舊臣,例如父親侯恂那么大。而且順治二年(1645)開科舉時,侯方域僅二十八歲,還不及而立,正是男兒建功立業之機;此外他對于晚明政治有許多不滿,而對崇禎皇帝更是曾有過直言不諱的批評,對于清初的新政還是心存幻想,有所期待的。
因此侯方域在面對清廷的征辟時,雖然拒絕,但并不甘心就此隱居終老,于是發出了“慚愧風云際,尋常牧犢還”[10]的慨嘆。而在《題韓叔夜膝廬四首》其二中,他明確表達了潔身自好,堅守氣節的心志:“鳳鸞愛其儀,不棲惡木陰”;然而在組詩的第四首中,又言“若吟懷大略,隆外日覆翻”,以諸葛亮作《隆中對》的典故自喻,暗含等待明主禮聘之意。這組詩作于順治五年(1648),在同一組詩中反映出來的情懷并不一致,這說明侯方域做出歸隱的決定是相當艱難的,并不甘心在如此盛年一事無成,就此守拙田園。
在侯方域侍奉父親隱居南園三四年后,順治七年(1650)的春天,三省總督張存仁因榆園軍氣盛漸熾一事,親自往商丘城郊南園訪侯恂、侯方域父子。這件事對于侯方域而言是由決意隱居到有心出仕的一個轉折,侯方域因是上呈《剿撫十議》,[11]并開始重新研習、揣摩制藝之道。侯方域早年在南省試策中議論縱橫,氣勢捭闔,然不軌法度,且放意直言,無所顧忌,洋溢著少年無所畏懼的氣息,但終鎩羽而歸。對于其早先之作,錢謙益曾在《贈侯朝宗序》中評價為:“文人才子之文,而非經生之文。”[12]1002
然而在明亡后,飽經挫折后的侯方域,隨著性情的逐漸沉淀,于制藝之途已產生了變化,“(方域)于制科文,始不盡附昔之箋注,而晚依宋儒。”[13]133推究其文之變化,則在順治庚寅年,即順治七年(1650),“朝宗此文,自順治之庚寅。憶爾時,朝宗方與余討今古文于軌度,古文則準之唐宋八子,今文則準之考亭之章句。或間日一作,或日一二作,至命酒高談,將無虛日”[13]47,徐作肅所言之“考亭”,即朱熹;“準之考亭章句”,表明侯方域開始自覺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對儒家經典的闡釋作為自己制藝之文的寫作標準和參照尺度。《清史稿·選舉三》載:“(順治)二年,頒《科場條例》……《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傳》、朱子《本義》……《詩》主朱子《集傳》”[4]卷一零八。從順治七年(1650)開始,侯方域有意地按照清廷頒布的科舉參考書目來規范自己制義文的創作,由此可以猜想他與徐作肅的學術討論并不光是對于作文之道的交流,而是已經有了初步的出仕應考的打算。
與此同時,侯方域與清廷官員的交往也越來越頻繁。入清后,以遺民自命的明代士大夫大多選擇歸隱山野,堅持“不入城”,遠離政治,潛心學術,如黃宗羲、傅山、歸莊等,而侯方域則不同。在順治五年(1648)以后,他與主管商丘地方事務三省總督張存仁、歸德知府王登進、歸德參將陳僖及其繼任者萬欽、河南總兵高第等清廷官僚來往逐漸增多,特別是在順治七年、八年間。
曾有一次,清參將陳僖因拾得被人遺棄的兩只仙鶴,在家中舉辦宴會慶賀,“是日也,考鐘伐鼓,陳清商之樂,大宴其客于堂上,享其士于堂下”[14]。在這場宴會中,有陳將軍門客媚言贊嘆陳將軍“若移其所以養鶴者養士,庶吾軍其振乎!”因侯方域所居南園有“憩鶴軒”,為養鶴之所,“有鶴數只,鼓翼翔舞,引吭高唳”,他平日熟知鶴之習性,于是出言反駁:“夫鶴者,天下清虛之物,寡欲而省費,故可以高人隱士之禮致也;世之戰士,皆驍雄勁悍之徒。……吾一旦欲得其力而效之于死,是必閑居則美妻妾,厭粱肉,六博群飲。……養以有余之財,而作其感恩之氣,然后報其主而不叛,吾未見其可以虛數致也!故子之帥以其求鶴者求士,士未嘗不至;若遂以其養鶴者養士,吾恐士之聞風而來者,將掉臂而去也。”在此文中,侯方域談及養鶴與養士之別,鶴乃清虛高潔之物,而門下之士則借以財利相邀乃至,必有其實際利益的追求,二者不可同日而語。侯方域的議論側面反映了他當時的一種現實心態,士與鶴之不同,正是入仕與隱居之差異。
而在《代司徒公贈萬將軍序》中,侯方域更是對來往密切的官僚贊譽有加:“制府張公,當世所稱善將將者也,于其部下不輕許可,而獨謂萬將軍賢。”因此,“愿得有言以志將軍之勛若勞也”是侯生撰寫此文之動機。繼而他又稱贊萬欽:“將軍顧獨循循然謹守朝廷法度,秋毫無擾于民。郡之人為余言,此兵興以來所罕覲也。……郡之人莫不幸將軍之來,而又惜其來之晚。”而舊明既亡,“清朝締造,皆師武臣力,雖悉其弊,而一時積重之勢,未能遽挽。今天子明圣,張公又久在兵間,數奉詔諭其部下,而將軍乃率先遵約束,有儒將風。此其識量,豈與喑嗚叱咤者同日語哉!”至此,侯方域已明確地表現出對萬將軍的褒賞之意以及對滿清政權的認可。
此外,在入清以后,侯方域對于一些歷史人物的看法也頗有深意,例如他的《王猛論》就跳出陳見,認為王猛本是與諸葛亮一樣識大義的亂世之臣:“然亮之仕于漢而為漢,人所知也;猛之仕于秦而為晉,人之所不知也。”在侯方域看來,王猛改投前秦實非本意,而是形勢所迫,“猛處天下分崩之時,其志未嘗不在中原,及其不得已而見用于異國,猶惓惓不能忘,猛蓋識大義者也。”當其時,桓溫欲效曹操取晉而代之,王猛明知其居心,若仍投于麾下,則“荀彧、郭嘉之下者也”,“晉偏安江左,僅有一桓溫足以有為,而又不可以從”,“不從,溫又必殺猛”,因此王猛不得已投靠前秦,輔佐苻堅,使其國富兵強,而臨終前仍哀求以告苻堅:“晉正統相承,上下輯睦,非所可圖,臣死之后,愿無以晉為念。”侯方域對王猛的評價很高,認為他并非“僅僅功名之人”,但他同時也承認“猛之才,高于諸葛亮,而淡泊寧靜不及”。[15]諸葛亮甘于隱居隆中,而王猛轉而仕秦,不是才能高低的問題,而是二人性格注定有著不同的人生選擇。而侯方域之所以視王猛為識大義者,是因為“猛存則以秦存晉,猛亡猶欲以秦存晉”,他對于王猛的這段議論實在有些劍走偏鋒,相當具有顛覆性。
侯方域的文章歷來有些好發驚人之語,不承前人遺訓,然而在順治年間應試之前作此新奇之語,頗有些耐人尋味。而此前好友黃宗羲與張自烈談論侯方域時就曾說:“朝宗素性不耐寂寞。”[2]224而方以智也評價他“美才而豪,不耐寂寞”[16]。崇禎十二年(1639)應試金陵時,復社諸生曾將侯方域比作昔時之周瑜、王猛,侯方域在性格與才華上與王猛確有幾分相似,同樣年輕氣盛、恃才傲物,同樣不甘平淡,因此侯方域在議論王猛時,未嘗不是在剖析自我。其實王猛與諸葛亮并沒有太多可比性,諸葛亮為漢家江山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而王猛則投靠異族政權,盡管侯方域稱其為存晉而仕秦,但這也只是一家之言,與史實也頗為不符。王猛固然輔佐前秦盡心盡力,但苻堅屢伐中原,只是因淝水之戰大敗后才被迫停止,這與侯方域所言并不一致。而與《王猛論》一樣,侯方域在入清以后的很多文章多少有些為效力于異族政權的歷仕二朝者辯解之意,像之前的《贈彭子序》中談到的楊師道、封倫、范質、王溥等人均為改仕之人。
另外,侯方域還在寄語小弟侯方策時說:“今天下疆土甫定,國家且歌《大風》、思猛士,季弟能用其材武,將來御侮干城,未可量也。”[17]這說明他對于家族成員入仕新朝并不排斥,反而很是鼓勵。他認為在朝廷求賢若渴之時,正是男兒建功立業的良機,因而再三贊賞:“季弟,勉乎哉!”綜觀侯方域在順治七年(1650)以后的詩文,可以看出其心態上發生了較大變化,雖然仍時常流露出沉郁的黍離之悲,但同時亦表達出自己并不甘心歸隱終老的心情,而這種對于故國、故友的思念與對實現個人價值的渴望共同構成了侯方域赴順治八年(1651)鄉試之前的復雜心態。
對于他參加豫省鄉試是否自愿的問題,筆者認為侯生大概有些半推半就,其內心的掙扎矛盾必然相當激烈,但不甘心就此終老田園的心態也是很明顯的。對于一個身閱鼎革的士大夫來說,被迫臣服于一個異族政權,其內心世界與生活處境何其艱難。而勝國遺民在物質生活艱苦的同時,至少他可以標榜其精神世界的崇高,甚至以“遺民”身份沾沾自得。而那些改仕新朝的士大夫,但凡知些廉恥的,不管出于各種原因,都不可能滿心歡喜地接受新朝的官爵。像侯方域的好友李雯當時在貧困交加,生活潦倒的處境下,被迫依附多爾袞幕府,但其愧疚、負罪之情一直伴隨終生,并抑郁而終,而吳偉業、錢謙益亦是如此。
在當時的輿論環境下,殉節者自是第一等,遺民次之,而貳臣則視情況而定,被迫出仕與主動降清在社會上得到的道德評價是不一樣的。然而事實上,殉節者未必就比茍活者更高尚。北都陷落時,左副都御使施邦曜曾留下絕命詩:“愧無半策匡時難,但有微軀報主恩。”這其實是崇禎朝很多士大夫的真實寫照,不光施邦曜一人,大臣們陷入朝內的黨派之爭,對于國事從無半點貢獻,而在“國君死社稷”之后,他們選擇了一種最經濟、最簡單的效忠方式,卻能夠名垂青史。而那些活下來的士大夫很多在為收復河山積極奔走,擔負著復國的重任,親身經歷著亡國滅種的悲劇,而后又不得不因各種原因臣服于異族統治。從這個意義上說,生存比死亡更艱難,也更高貴。
在中國古代社會中,以血緣為紐帶結成的宗族制,使得大家族中每一個成員所代表的不僅僅是他自己,而是家族的一份子,個體成員的行為都將服從并以家族的興衰為首位,無論是婚姻生活還是人生選擇。前文曾提及侯洵《侯方域年譜》所記侯方域為解救父親侯恂而被迫應試一事,而陳寅恪先生也在《柳如是別傳》中分析過侯方域出仕的原因:“朝宗作《壯悔堂記》時,其年三十五歲,即順治九年壬辰。前一年朝宗欲保全其父,勉應鄉試,僅中副榜,實出于不得已。‘壯悔堂’之命名,蓋取義于此。后來竟有人賦‘兩朝應舉侯公子,地下何顏見李香’之句以譏之。殊不知建州入關,未中鄉試,年方少壯之士子,茍不應科舉,又不逃于方外,則為抗拒新政權之表示,必難免于罪戾也。”[18]第四章
像當時侯方域的很多好友,比如方以智、梅惠連、彭賓等人均以貴公子之身逃與方外,為了避免因受到清廷逼迫而有違初衷,只有削發為浮屠,方能不因剃發、易服等事累及家人。而陳寅恪先生又說:“牧齋此次至松江本為復明活動,其往還唱酬之人多與此事有關,故子玄(陸慶曾)亦必是志在復明之人。但何以于次年叩應鄉?表面觀之似頗相矛盾。前論李素臣(李藻先)事,謂其與侯朝宗之應舉皆出于不得已,子玄之家世及聲望約略與侯、李相等,故疑其應丁酉科鄉試實出于不得已。蓋建州入關之初,凡世家子弟著聲庠序之人若不應鄉舉,即為反清之一種表示,累及家族,或致身命之危險,否則陸氏雖在明南都傾覆以后,其舊傳田產猶未盡失,自可生活,不必汲汲干進也。關于此點,足見清初士人處境之不易。后世未解當日情勢,往往作過酷之批評,殊非公允之論也。”[18]第五章
秉承陳寅恪先生所謂“了解之同情”的態度,去考察此一時期士大夫的生存環境,才能盡量避免以今人的是非觀、道德觀去審視與評價古人。筆者認為侯方域正處壯年,平素又是不耐寂寞的性格,不能堅守“遺民”姿態,不甘心終老南園是可以理解的,本不必以“晚節不保”這樣的大帽子去扣在他身上,更不必在自愿或是被迫的問題上糾纏太過,難道自愿應考就意味著品行低下,而被迫赴試就道德高尚了嗎?因此,對于現代很多學者都談及的“遺民的時限性”,筆者亦是深以為然。
[參考文獻]
[1] 黃裳.銀魚集[M]. 北京:中華書局,1985.
[2] 全祖望.全祖望集匯校集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 侯方域.與宋公子牧仲書[A].壯悔堂文集卷三[M]. 上海:中華書局,據通行本校刊.
[4] 趙爾巽.清史稿[M]. 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5] 梁啟超.桃花扇注[M].北京:中華書局,1940.
[6] 王德威.后遺民寫作[M].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
[7] 侯方域.贈彭子序[A].壯悔堂文集卷一[M].上海:中華書局,據通行本校刊.
[8] 侯恂.南園詩[O].南園記,順治十一年家刻本。
[9] 侯方域.四憶堂詩集卷四,村居和徐五作肅三首其一[M].上海:中華書局,據通行本校刊.
[10] 侯方域.四憶堂詩集卷四,舊業其四[M].上海:中華書局,據通行本校刊.
[11] 侯方域.壯悔堂文集卷四,上呈三省督府剿撫議[M].上海:中華書局,據通行本校刊.
[12] 錢謙益.初學集[M].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3] 徐作肅.偶更堂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4] 侯方域. 陳將軍二鶴記[A].壯悔堂文集卷六[M].上海中華書局,據通行本校刊.
[15] 侯方域. 王猛論[A].壯悔堂文集卷九[M]. 上海:上海中華書局,據通行本校刊.
[16] 任道斌.方以智年譜[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
[17] 侯方域. 贈季弟序[A].壯悔堂文集卷一[M]. 上海:上海中華書局,據通行本校刊.
[18]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責任編輯:朱丕智]
Study on Hou Fangyu’s Integrity in His Later Life after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Early Qing Dynasty
Ming Yuexi
(College of Humanitie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Abstract:As one of young leader in the Fu Association, Hou Fangyu was a influential and charismatic figure of intellectuals. But he had been criticized for attending to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In addition, Hou’s drama image in the Peach Blossom Fan was so popular that people had a controversial and prejudicial view on him, and even extended to his works.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cademic attitude of “understanding of sympathy”, we can perspective his bitter and complicated life through analysis from his works, and know more about the intellectuals whose living and spiritual dilemma in that period.
Keywords:Hou Fangyu;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imperial examination; the integrity in later life
收稿日期:2015-02-01
作者簡介:明月熙(1980—),女,漢,四川合江人,四川大學文學博士,貴州大學副教授,研究方向:古典文學,明清散文。
基金項目:貴州省社科規劃項目資助(NO.13GZQN02)。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29(2016)02—00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