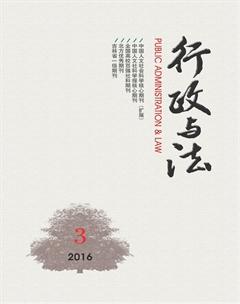環境行政決策失誤界定分析
王楠 顧建亞
摘 要:目前,我國正從權力政府向責任政府轉變。責任政府要求政府在行使社會管理職能的過程中,主動就自己的行為向人民負責;政府違法或者不當行使職權,應當依法承擔法律責任。環境行政決策是政府行為,因而對環境行政決策失誤的認定是追究政府責任的基礎。本文從環境行政決策失誤的內涵入手,認為對環境行政決策失誤的界定既要依據法律和社會評價這一復合型標準,還要充分考慮決策的實質標準和程序標準是否恰當,這樣,才能保證行政決策責任追究的公正與公平。
關 鍵 詞:環境行政決策;責任政府;社會評價
中圖分類號:D92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8207(2016)03-0076-08
收稿日期:2015-12-30
作者簡介:王楠(1978—),女,黑龍江雙鴨山人,浙江科技學院經濟管理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為環境法、經濟法;顧建亞(1971—),女,浙江慈溪人, 浙江科技學院社科部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為行政法。
基金項目:本文系浙江省科技廳軟科學項目“法律有效實施中的權力決策及機制研究——基于環境法的規范分析”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14C35080。
2015年1月1日我國開始實施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與修訂前的《環境保護法》相比,修訂后的《環境保護法》不僅加大了對企業的懲罰力度,也對地方政府實行問責機制。如第二十六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將環境保護目標完成情況納入對本級人民政府負有環境保護監督管理職責的部門及其負責人和下級人民政府及其負責人的考核內容,作為對其考核評價的重要依據。對此可以理解為,如果地方政府主要決策人因盲目進行環境行政決策而產生了嚴重的后果,無論其升職、離職還是退休都要一查到底。這些規定表明,我國正從權力政府向責任政府轉變,因政府行政決策行為和執行決策失誤行為導致的環境損害問題,由政府負責。筆者認為,確認環境行政決策失誤是進行責任追究的前提條件,同時也能對決策責任人起到相應的警示作用,避免盲目決策。
一、環境行政決策失誤的內涵及
導致的后果
環境行政決策是指政府在進行環境利用時,面臨可能產生的環境破壞或者環境潛在風險以及各種環境利用行為的成本問題,綜合作出分析、判斷并最終選擇最優實施方案的行為。[1]環境行政決策屬于政府行政決策的范疇,但由于環境問題自身具有綜合性、影響的潛在性及長遠性等特點,導致環境行政決策也隨之具有更高的風險性,即對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很難作出準確判斷,而且結果也不是立刻顯現。另外,環境行政決策是綜合性政府決策,要平衡多方利益關系,包括經濟效益、環境效益還有當事人權益及相關群眾的環境安全效益,甚至還包括當代人利益和未來幾代人的利益。因此,要在如此多的利益選擇中達到平衡是非常困難的。
目前,關于環境行政決策失誤的界定尚未有定論,筆者認為,可以從行政決策失誤的概念中推理得出。朱廣忠認為,政府行政決策失誤就是指政府決策時違背了客觀事物發展規律,對決策事項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帶來了與預期不同的負面效果。[2]黃凱騰、王鴻詩認為,行政決策失誤是政府行政機關實施預先制定的決策方案后,由于受到主客觀多種因素的作用,導致執行效果不甚理想,給社會造成不良影響的現象。[3]在這兩個概念表述的基礎上,筆者認為,環境行政決策失誤是指政府在進行環境行政決策時,違背自然環境規律、違反相關法律法規而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形成了決策偏差,造成了重大損失,包括認識不足和違反法律法規、盲目決策等。
目前,環境行政決策失誤導致的不良后果主要有以下兩種:
一是生態環境方面,我國目前的生態環境狀況堪憂。在環境保護部和國土資源部于2014年4月17日聯合發布的公告中,關于全國土壤污染調查情況顯示,我國已有16.1%的土壤受到污染,耕地情況不容樂觀,其土壤點位超標率已經達到19.4%。[4]另據環境保護部2014年5月發布的2013中國環境狀況資料顯示,我國的地下水共有4778個環境質量監測點,其中10.4%的水質是優良的,有59.6%的水質比較差或者很差。[5]另外,據中國水安全公益基金2015年發布的資料顯示,在我國29個大中城市中,居民飲用水水質抽檢結果能夠全部滿足抽檢的20項抽檢指標的城市數量只有一半。[6]環境保護部在2015年2月2日發布了城市空氣質量狀況資料,共統計74個城市,2014年只有8個城市各項污染物指標濃度符合要求,被抽查的其他城市都存在不同指標、不同程度的污染現象。[7]
二是社會環境方面,環境群體性事件發生比較頻繁,政府公信力受到影響。1996年以來,我國頻繁出現環境群體性事件,其增長速度達到了29%。[8]這些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環境群體性事件使公眾對政府的公信力產生了質疑。從2007年到2014年,大量的環境群體性事件都是由于市民對即將上馬項目產生的環境污染隱患提出抗議,希望引起政府的注意并滿足其生存環境保護的訴求而引發的。 比如2007年的廈門PX事件、2012年四川什邡市鉬銅項目及2014年杭州余杭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這些項目在選址、審批時忽略了公眾參與,結果導致群體性事件瞬間爆發。為了盡快解決矛盾,地方政府最終都選擇了關停項目的做法,從而使其公信力大幅度下降,也導致公眾愿意選擇極端的方式解決環境問題。
二、環境行政決策失誤界定的必要性
⒈環境行政決策失誤是承擔決策責任的前提。環境行政決策有自由裁量權,但這一權力涉及的問題比較復雜,反應也相對滯后,如霧霾、臟水、山地草原荒蕪與污染等都不是突發事件,相對環境質量保持或者改善時間來說,地方政府領導的任期較短,其往往出于任期內政績考核指標的考慮,在政策選擇上,要么側重經濟發展,要么側重保護環境。地方政府一般選擇發展經濟,這必然會造成口頭上或者形式上提倡生態環境保護的可能,結果是導致生態環境惡化情形越來越嚴重。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2013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建立責任追究制度,對那些不顧生態環境盲目決策、 造成嚴重后果的人,必須追究其責任,而且應該終身追究。 所以,必須對環境行政決策失誤進行界定,只有對“拍腦袋”式的決策進行失誤認定,才能公平、公正地追究決策人的責任。
⒉環境行政決策失誤界定能夠預防決策失誤。目前,全國還沒有界定重大行政決策范圍和權限劃分邊界的統一標準,各地政府規章對此也僅是概括性的說明。[9]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強調了政府的環境保護責任,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負責該行政區域的環境質量,并將環境保護目標完成情況也納入到了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負責人的考核內容。對此可以理解為,地方政府應該讓環境質量變好或者改善,底線是不能變差。在任期內,如果環境質量下降,生態環境變差,就要承擔責任,而且終身追究責任,不論其離職還是退休。環保目標不能實現,采取一票否決的制度。這些規定充分表明,環境責任追究不是一句口號,其必將對環境保護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也可能由此導致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方面畏手畏腳,擔心因環境問題受到懲罰與問責。為此,應當對環境行政決策失誤進行科學界定,因為只有失誤標準清晰,地方政府領導才能知道該如何為或者不為。
⒊環境行政決策失誤界定可以調節政府、企業、相關群眾之間的矛盾,維護政府形象。頻繁發生的環境群體性事件,究其根本原因,很多是由于地方政府行環境政決策失誤造成的,如缺乏公眾參與、程序失當、信息不公開等。群體性事件中的各方利益主體存在矛盾,對環境問題逐漸敏感的群眾往往會以極端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面對難以控制的局面,政府只好選擇停止項目的做法。在行政決策過程中,面對模棱兩可的選擇,如果政府能夠選擇其中最為合適的方法,就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決策失誤,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也會隨之減少。因此,科學、合理地界定環境行政決策是否失誤,是增加政府誠信力,維護政府形象,調節政府、企業、相關群眾之間矛盾的關鍵。
三、環境行政決策失誤
界定的理論基礎
行政決策失誤與否的判斷依據與人們的價值取向、決策的利益分配等密切相關,也與人們對事物發展客觀規律的認識水平相關。也就是說,行政決策失誤的判斷標準,既屬于事物的客觀范疇,也屬于人們的主觀范疇。因此,在行政決策責任追究實踐中,不僅會出現責任難以界定的情形,還會出現責任難以追究的麻煩。[10]
由于不同研究者的研究視角和價值觀不同,導致行政決策失誤認定標準較難統一。在判斷行政決策失誤上大致有以下幾種情況:第一,從決策結果上判斷是否失誤。黃京平、蔣熙輝認為,決策失誤可能因玩忽職守、濫用職權行為引起,導致國家利益受損。[11]朱水城、李瓃認為,政府行政決策失誤有兩種表現:一種是決策目標出現方向性錯誤,后果較為嚴重,損失難以彌補。另一種是決策偏差性錯誤,實施決策沒有達到方案預期目標,造成一定損失。[12]第二,從決策評價上判斷是否失誤。于祖堯認為,政府行政決策失誤是由于錯誤的決策導致國民經濟、社會文化、秩序穩定等諸方面的損失。這種觀點強調除了經濟損失以外,認為錯誤的決策還可能導致更多社會方面的損失。[13]第三,從決策成本收益上判斷決策是否失誤。張峰認為,政府決策失誤的判斷標準應該是行政決策的成本是否大于利潤。[14]如果成本大于利潤就是決策失誤。
環境行政決策失誤界定的標準是否適用于以上三種情況?筆者認為,環境行政決策與其他行政決策相比,具有短時難以預測風險和決策影響的利益主體眾多、難以權衡兩大特點。[15]環境行政決策過程中不僅充滿著不確定因素,而且涉及社會多方面的利益,包括代內利益、代際利益等各種利益沖突,需要綜合權衡后決策。在這一背景下,環境行政決策失誤的判斷標準不應該是單一標準,而應該形成復合型的評價標準。因為環境行政決策具有不確定性,在決策過程中要慎重考慮決策的法律依據,即決策制度標準和程序標準。如果出現違背法律法規的情形,就屬于決策失誤范疇。在環境群體性事件中表現最為突出的就是在決策時缺少程序標準,如沒有進行信息公開、環評作假、缺少公眾參與或者未進行及時的信息溝通等。同時還要考慮決策過程中的社會評價,比如民調民意,也就是公眾參與決策應該真正發揮作用。但環境問題有其自身的特點,不同的行業、不同認知水平的社會公眾可能對環境行政決策產生不同的影響,所以還要輔之專家的觀點,保持信息溝通順暢,最大程度地做到決策公正公平,否則就會產生決策失誤的可能。決策成本是指政府在整個決策過程中進行信息的搜集、整理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時間、財力等各種資源,如果成本總和大于收益,就是決策失誤。但在環境行政決策問題上,還應重點考慮風險成本,因為環境一旦遭遇破壞就是最大的損失。一個合法、適當的公共政策應該與政府價值目標相一致,符合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符合社會評價標準,即通過對各種備選方案進行預測以及實施決策方案后與可能產生的后果進行分析比對,對決策方案的投入——產出進行評估,最終選擇綜合利益最佳的方案或令大多數人滿意的方案,從而不斷地強化公共政策的價值取向。[16]所以,環境行政決策失誤的認定標準應該滿足法律依據標準和社會評價標準。
四、環境行政決策失誤界定的難點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發展成果考評體系,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2014年11月12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加強環境監管執法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通知》明確提出,出現以下四類情形,有關領導和責任人將被依法追責:對發生重特大突發環境事件,任期內環境質量明顯惡化,不顧生態環境盲目決策、造成嚴重后果,利用職權干預、阻礙環境監管執法的,要依法依紀追究有關領導和責任人的責任。其后,地方各級政府出臺了生態環境責任追究制度。事實上,追究環境行政決策責任的前提是決策出現失誤,但是關于環境行政決策失誤的表現往往是根據環境質量惡化,出現環境群體性事件,或利用職權阻礙環境監管及執法。這從某種程度來說都是環境行政決策失誤導致的后果,是事后追責,無法彌補環境損害所造成的損失。由于環境問題的特殊性,筆者認為,界定環境行政決策是否失誤通常存在以下難點:
⒈環境決策對象的動態變化導致了行政決策失誤判斷的不確定性。環境行政決策的客體是環境,由于不同時期的不同環境問題以及不同的價值取舍,決策者關于決策判斷正確與否難以立刻得出結論。即便是同樣的問題,在不同的決策者面前,受不同因素的影響,正確與否都很難做出判斷。
例如:在黃河流域城市中打造城市水景,使城市面貌煥然一新,招商引資速度加快,居民生活環境大為改善,項目也都強調“河道整治”“防洪”“保護濕地”等,但水災卻在暗流涌動。2003年,黃河流域出現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水荒,入海水量每天只有幾立方米。2005年,河套灌區又發生了嚴重的旱災,黃河內蒙古流段出現斷流現象。2007年4月14日,中國科學院的《長江保護與發展報告2007》顯示,長江情況一直處于不斷惡化狀態。[17]由此看來,地方政府名曰生態建設,實為政績驅動。
再如:因焚燒垃圾引發的環境群體性事件,導致垃圾焚燒項目成為眾矢之的,但垃圾焚燒發電是一種較為先進的垃圾處理方式,已經得到了很多國家的推廣和使用。日本東京的垃圾處理廠就建在城市中心,德國為了處理每年將近1800萬噸的垃圾,也建造了68個垃圾焚燒廠。[18]而北京、廣州、杭州卻先后出現了群眾集體反對建設垃圾焚燒廠的事件。2015年度的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特等獎由中國石化獲得,其研究的項目是高效環保芳烴成套技術開發及應用。PX就是芳烴衍生的品種之一,并且占30%的比例。但PX項目在我國大連、昆明、彭州、廈門、寧波、鎮海等地都受到了相關群眾的集體反對。客觀事實是PX國內產能嚴重不足,需要進口。由此看來,與環境相關的決策在這些背景和綜合因素作用下,正確與否不能簡單而論。
⒉社會公益與公眾環境權利存在矛盾,決策失誤界定標準難以量化統一。環境行政決策會涉及到政府、企業、公眾,而每個主體都有自己追求的利益目標。地方政府追求社會秩序及任期內的政績,企業追求經濟效益,公眾追求生活品質及生存環境安全。當其目標不能實現時,都會認為自己是受害者,沒有得到公平的保護。環境具有公共產品外部性特征,往往是項目本身帶來的經濟效益為所有社會成員享有,但是項目的負面效應——環境損害卻要項目周圍的公眾承擔。按照美國學者龐德的觀點,可以總結為公共利益、社會利益、個人利益。
從政府角度看,其引進的PX項目如果不能按期建成項目基地或開工,該項目就將成為政府的“包袱”,不僅影響當地政府收入,還可能間接地影響公共設施建設及就業等,最終導致相關群眾利益受損,政府公信力下降。從企業角度看,大型的石化項目投資都在十億甚至百億元,利潤可想而知,比利潤更重要的是,如果能夠上馬PX項目,我國會降低PX的對外依賴,保障經濟安全。從公眾的角度看,項目一旦建成,輻射、噪聲、空氣污染程度都是未知的。在這些項目中,企業和政府獲得了可觀收益,相關群眾卻要承擔不可確定的環境風險,這種失衡是每次群體性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天生”的利益矛盾加上人類認知水平的局限,必然會給環境行政決策失誤的判斷帶來不確定性。
五、環境行政決策失誤界定的標準
在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中,關于政府責任的規定已大幅度增加,該法明確要求,地方政府對生產經營者、企事業單位的環境行為實施監督管理,采取獎勵的方式,鼓勵那些對保護、改善環境方面有突出貢獻的單位或者個人;地方政府要推動公眾參與事項,鼓勵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社會組織、環境保護志愿者開展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和環境保護知識的宣傳,營造保護環境的良好風氣。在這些規定中,政府責任體現在對環境的監管、改善環境等具體行政執行上,對行政行為決策責任較少提及。對此,我們必須在眾多的利益取舍中選擇最佳的價值取向,在不確定的環境損害選擇面前,選擇最為理性的決策。筆者認為,要讓責任追究落到實處,還要細化判斷行政決策失誤的標準:
⒈實質標準。第一,過錯標準。環境行政決策關系到當下及以后的環境問題,又帶有不確定性,現實中的決策主體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不能做出完全理性的環境行政決策,總在追求某些方面的效益最大化。決策主體在搜集大量相關信息后,可能發現決策即將影響當地的經濟效益。而經濟效益顯現結果比較快,較能體現自己的政績;環境效益顯現結果比較慢,在任期內可能不會出現結果,決策主體要完成自利的目標,就有可能出現行政決策失誤。此外,由于科學認知水平有限,或者行政決策還是集體討論研究決定,人人有責也就變成了人人無責,從而導致環境行政決策失誤。故意是主觀上明顯或濫用權力行為導致的決策失誤,過失是主觀麻痹大意或認知不足造成的決策失誤。兩者都是環境決策失誤,都要承擔環境行政決策失誤責任,因此,在進行環境行政決策失誤界定時,只有對其進行區分,才能保證權責一致,懲罰公正,才能使決策主體以高度的責任心開展行政決策活動。第二,合理標準。環境資源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只談環保不談經濟發展也是因噎廢食。例如:煤炭、石油、天然氣都是不可再生資源,在開采或使用過程中會損害環境或者傷害到相關群眾的利益,但人們的生活離不開這些資源,相關群眾也比較認可這種使用方式,同時,一些替代性能源如風能、電能、潮汐能和太陽能等也在逐步推廣和使用。然而,這些比較傳統的環境問題并沒有引起相關群眾的利益失衡感,原因在于:除了已經形成的傳統思維外,還存在一些經濟補償因素。政府在項目利用上權衡多種因素后,認為利大于弊,造成的環境損害較小,取得經濟效益或社會效益較大,對相應的受害者進行適當的經濟補償,這樣的環境行政決策也是合理的。目前,我國煤炭、森林等已經有了相關的補償規定,生態環境資源作為一種公共資源,不是企業生產加工出來的,企業損耗了社會公共環境資源,就應當給予受害者補償,補償對象包括相關群眾或資源的所有者,補償可以用于生態環境污染治理。但在企業單純造成的環境污染中,是否應該給予受害者相應的補償,目前還只停留在企業環境責任保險上。因此,政府在進行環境行政決策時,應該與相關群眾進行協商,對其產生的環境損害給予適當的經濟補償,以保證環境資源的妥善使用。第三,社會公益標準。在環境問題面前,因利益主體多元化,利益取向不盡相同,要找到他們之間的利益平衡點是比較困難的。環境行政決策的主體往往是政府,其代表公權力,如果公權力不受監督和控制,就會侵害公眾的權利。從這個角度上說,公眾屬于弱勢群體,在決策過程中,往往缺少參與權和知情權。因此,決策主體應當對弱勢群體給予特別保護,在行政決策過程中不僅要關注其他利益主體的利益訴求,也要傾聽這些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并且與其進行協調、溝通,最終滿足其利益訴求。
⒉程序標準。美國學者舒伯特認為,在行政理性主義中,社會公共利益應該存在于適當的決策程序中,行政決策程序是能夠保證價值中立的一個技術環節。也就是公共利益存在于決策程序的理性中,決策主體才會自覺地執行公共的意志。[19]換言之,決策失誤的判斷標準還在于程序上是否正確。第一,公眾知情標準。比如很多地方的垃圾焚燒項目,初衷是解決垃圾處理問題,政府在向公眾告知這一項目時,大多是告知公眾城市已經被垃圾包圍,垃圾焚燒是破解垃圾圍城困境的唯一出路,世界上最先進的方法是焚燒垃圾。這些內容只是公眾想要了解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公眾還需要知道這種焚燒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對于可能產生的環境污染問題,政府或者企業如何避免或解決;如果產生損害,政府如何補償。而有選擇的告知不僅導致了公眾對項目存在的風險缺乏充分的了解,也為決策失誤埋下了隱患。在政府不充分告知的情況下,公眾為實現利益目標就可能采取極端的方式。第二,公眾參與決策標準。公眾參與是實現公眾民主權利的重要渠道之一,參與決策的程度與規模是衡量一個國家是“人治”還是法治的重要標準。[20]但由于不同的社會公眾代表不同的利益群體,片面地注重民主可能會影響決策效率,片面地注重決策效率又會侵犯公眾的民主權利,因而在環境行政決策失誤界定上要充分考慮兩者之間的平衡。在決策中充分發揚民主,既是獲取群眾支持的基礎,也是減少行政決策失誤的關鍵。環境行政決策的相關群眾因不同的行業背景、不同的認知水平、不同的利益取向,可能會導致行政決策長時間地懸而未決,進而引起決策失誤。在環境群體性事件中,比如廈門的PX項目和杭州余杭的垃圾廠項目,相關群眾的訴求是“項目可以建,但不可以建在我家附近”,這是由于相關群眾對于項目的環境影響沒有得到正確的信息,又受到網絡傳播的影響,導致群體性事件一觸即發,政府最終只能選擇停止項目。換言之,由于侵害了公眾的環境權,環境行政決策必然以失敗而告終。第三,專家評估標準。行政決策可能存在風險,當出現決策失誤時,項目本身的風險可能會成為“擋箭牌”。因此,在認定是否存在失誤時,要注意區分是決策帶來的失誤還是項目自身風險的不可操控。對于存在較大爭議的事項或者可能產生較大影響的項目,應該在項目決策之前設計應急預案或者其他的替代方案。另外,我國《行政強制法》對行政強制措施的設立建立了后評估制度,即在行政強制實施一段時間后,應對其科學性、合理性、群眾滿意度作出評價。對此,在行政決策中也可以設立后評估機制,如在政府內部設立評估機構或者中介評估機構,對已經開始的環境行政決策進行分析評估,及時發現決策失誤并評估損失大小,盡可能地減少損失或及時停止項目。所以,在環境行政決策失誤的認定上,既要充分考慮公眾的參與權,也要考慮專家的權威論證,尤其是體制外的專家,因為這些專家能夠獨立出具專業意見。只有將專家出具的意見及時向公眾進行反饋,才能增強環境行政決策的準確性。
我國正在建設責任政府,啟動政府環境問責制,對環境行政決策失誤界定是其承擔責任的起點。具體而言,應不斷完善環境行政決策相關法律,注重決策的社會評價,在界定環境行政決策是否失誤時,充分考慮界定的實質標準和程序標準,因為實質標準能夠保證決策價值取向的公平,程序標準能夠保證決策的合法、合理。只有通過這些標準的復合使用,才能判斷環境行政決策的失誤與否及其失誤程度并承擔相應的責任。
【參考文獻】
[1]汪勁.環境法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283.
[2]朱廣忠.公共決策失誤責任論析[J].理論探討,2004,(06):56-61.
[3]黃凱騰,王鴻詩.論政府決策失誤防范機制構建[J].遼寧行政學院學報,2007,(02):35-41.
[4]環境保護部和國土資源部聯合發布了《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EB/OL].http://www.water8848.com/news,2015-04-20.
[5]環保部發布《2013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告》[EB/OL].http://www.china5e.com/news/news-871778-1.html,2015-05-12.
[6]全國29城飲用水質抽檢報告:14城水質存不合格項[EB/OL].http://news.163.com/15/0201/20,2015-05-12.
[7]環境保護部發布2014年重點區域和74個城市空氣質量狀況[EB/OL].http://news.sina.com.cn/c,2015-05-12.
[8]張富有.地方政府應對環境群體性事件機制研究[D].云南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12.
[9]聶帥均.構建重大行政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的困境與路徑選擇[J].行政與法,2015,(04):26-32.
[10]潘井亞.公共決策失誤的責任追究制度探析[D].南京農業大學碩士論文,2008.
[11]黃京平,蔣熙輝.決策失誤構成犯罪嗎?[N].北京日報,2001-01-22.
[12][13]于祖饒.建立決策追究制度好[N].北京日報,1999-01-03.
[14]張峰.政府決策失誤與責任研究——以人造景觀“三峽集錦”決策失誤為個案[J].理論導刊,2007,(05):52-58.
[15]馬波.論科學發展觀視野下環境行政決策之因應[J].中共桂林市委黨校學報,2009,(02):31-37.
[16]方林.論現代公共政策的價值沖突[J].中國行政管理,1998,(12):32-38.
[17]城市“圈水工程”背后的巨大隱患[EB/OL].http://news.sina.com.cn/s,2015-12-29.
[18]網民就垃圾焚燒廠事件呼吁政府信息公開[EB/OL].http://news.china.com.cn,2015-12-29.
[19]GLENDON A S.The public interest in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theorem,theosophy,or theory?[J].the American political review,1957(51):347-348.
[20](美)薩繆爾·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華夏出版社,1988.67.
(責任編輯:高 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