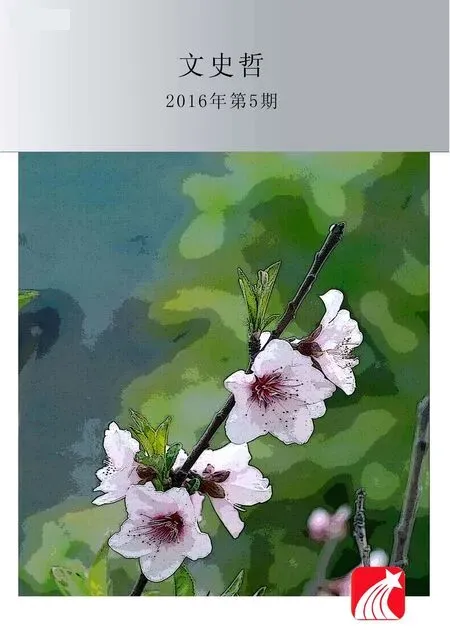中國是如何成為專制國家的?
白彤東
?
中國是如何成為專制國家的?
白彤東
傳統中國專制說之所以流行,蓋因西方普遍流行“東方主義”態度并對中國缺乏理解,而通過日本,該觀念成為迫切尋求救亡之道的中國學人的主流觀點。然而,上述觀察無法解釋為何在歐洲對中國充滿好感的時代,孟德斯鳩提出了中國專制說。因此,欲反駁傳統中國專制說,必須對始作俑者孟德斯鳩的中國專制說,進行批判性考察。實際上,中國專制說誤解了傳統中國政治,而近代中國基于這種誤解的各種錯誤行動,恰恰可能為傳統中國政治崩潰后中國走向專制埋下了伏筆。此極具反諷意味地命中了孟德斯鳩關于專制的理解。
中國專制說;封建制;君主制;極權;有效制衡;孟德斯鳩
一、中國專制說的源與流
最近一百多年的中國,人們先是對傳統喪失信心,進而激烈地反對自己的傳統。從器物層面對傳統中國的懷疑,導致了洋務運動。洋務運動五十年后,中國卻被日本打敗,中國士人遂漸漸形成了一個共識,即中國傳統政治也是有問題的,是壞的。很快,這種“壞政治”就獲得了一個新名字:“專制”。在新文化運動中,“專制”不僅指代中國傳統政治,還進而涵蓋整個中國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①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83頁。。也就是說,只有更新中國的文化,中國才能從根源上告別舊“專制”,真正在制度上擁抱“現代”與“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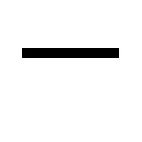
孟德斯鳩及其《論法的精神》,是將中國正面形象轉換為專制形象的始作俑者,或者至少是最重要的一個早期推手*侯旭東指出,孟德斯鳩是“西方思想家中第一個將中國劃入‘專制政體’的”(侯旭東:《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但黃敏蘭引述許明龍的研究指出(黃敏蘭:《質疑“中國古代專制說”依據何在?——與侯旭東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在孟德斯鳩之前,有法國人西魯哀特指出“中國皇帝擁有專制權力”,但與此同時他“對中國的政治體制和以儒家學說為主題的中國人的道德觀念備加贊賞”。這比孟德斯鳩的中國論述正面得多。更重要的是,后來的啟蒙思想家和其他哲學家對中國印象的轉變,更可能是追隨孟德斯鳩的結果(程艾蘭:《法國漢學與哲學》,《文匯報》2015年3月27日,第24版)。黃敏蘭文章中提到的對中國持負面印象和說法的其他西方思想家,皆出于孟德斯鳩之后。。從此之后,西方對中國政體的主流印象,變得極為負面。如所周知,近一百五十年來,中國學習西方(包括學習西方偏見),常常假道日本*宋洪兵:《二十世紀中國學界對“專制”概念的理解與法家思想研究》,《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與此相關,侯旭東指出,日本學人在翻譯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時,用“專制”譯“despotism”,此為將中國政體稱為“專制”的直接源頭*侯旭東:《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梁啟超在1899年已注意到這種翻譯,而通過《論法的精神》的日譯中版本(僅前四章),上述提法開始在中文世界出現*侯旭東:《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1903年,孫中山也開始用“專制”而非泛泛的“腐敗統治”,來指稱中國政體*侯旭東:《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這種認知甚至成為一些清朝官員的共識*侯旭東:《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作為訂正,萬昌華指出,嚴復在1895年已有中國傳統政治乃專制的說法*萬昌華:《一場偏離了基點的“知識考古”》,《史學月刊》2009年第9期。。不過,作為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的譯者,嚴復的這種說法,應該也是受了孟德斯鳩的影響。但值得一提的是,嚴復和梁啟超起初用“專制”翻譯的是“monarchy(君主制)”這個詞,當時多數人實際上是將君主制與專制混為一談的*宋洪兵:《二十世紀中國學界對“專制”概念的理解與法家思想研究》,《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而孟德斯鳩是區分君主制和專制的,所以在譯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的時候,嚴復才開始區分君主制與專制*宋洪兵:《二十世紀中國學界對“專制”概念的理解與法家思想研究》,《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
總之,孟德斯鳩及后來西方人對中國政體的認識,通過日本以及嚴復等人的直接推動,傳入了中國。但是,侯旭東指出,中國專制說并非科學研究的結果。法國啟蒙哲學家對于中國只有道聽途說,而大肆貶低中國的黑格爾,乃至對如何理解中國構成深遠影響的韋伯,同樣也是如此*侯旭東:《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確實,在孟德斯鳩時代的歐洲,中國是歐洲人最了解的異邦之一。但是,隨著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活動被天主教當局禁止,歐洲長期不再輸入來自中國的知識;最終,印度取代了中國,成為歐洲人更關注的異邦*參見程艾蘭:《法國漢學與哲學》,《文匯報》2015年3月27日,第24版。。鑒于此,筆者認為,用“東方主義”外加“無知”解釋“中國專制”說在近現代西方之流行是成立的。而且,這種說法,迎合了軍國主義日本取代中國成為東亞領袖的需要,此可進一步解釋歷史上的日本對于傳播甚至發揚這種有時近乎種族主義的學說所起的作用。
諷刺的是,這種說法傳入中國之后,迅速成為中國學人和政客的共識。據侯旭東考察,民國歷史教科書均采用中國傳統政治乃專制之說,相關作者大多受過五四運動的民主思潮洗禮。在那時,堅決反對這一說法的,只有錢穆。侯旭東認為,中國人這么快、這么廣地接受中國專制說,明顯不可能是學術研究的結果,乃是基于傳統中國史家的成王敗寇思維,在中國被西方乃至日本擊敗的現實下,所采取的立場*侯旭東:《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甘懷真認為,清末不論改革派還是革命派都希望改變中國政治,而中國專制說迎合了他們的需要,但這種說法并無學術基礎*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第382-384頁。。侯旭東更指出,按錢穆的說法,將傳統中國政治當成專制,是“自鄙”;而按照侯旭東自己的說法,中國專制說本來是西方為了證明自己的優越、為了正當化自己的殖民活動而對東方的惡意貶低,中國人接受這樣的說法則是“自我東方化”*侯旭東:《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黃敏蘭在其反駁侯旭東的文章中指出,當代西方對中國傳統政治有了越來越多的正面、持平之論,此顯非出于西方中心論立場*黃敏蘭:《質疑“中國古代專制說”依據何在?——與侯旭東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但是,這種聲音即使在當代西方也并非主流*這種聲音的出現,除了學術研究的深入之外,還與中國重新崛起有關。但與此同時,中國這種非西方式政體國家的崛起,也加劇了一些西方人對中國的敵意,并加劇了西方對中國、包括傳統中國的偏見。由無知與東方主義造成的對傳統中國的偏見,在西方,恐怕很長時間內還會是主流。。而與黃敏蘭所試圖反駁的侯旭東的論證更相關的是,從19世紀到當代中國開始重新崛起之前,“中國”在現代西方確實代表著專制、落后、停滯和黑暗。例如,程艾蘭指出,“黑格爾的法國弟子維克多·庫贊……提出了一個我們至今還難以擺脫的二元對立:‘地中海地區和希臘是自由和運動的土壤,而印中世界(即印度和中國)的高地是停滯和專制的領地’”*程艾蘭:《法國漢學與哲學》,《文匯報》2015年3月27日,第24版。。
又如,英國哲學家密爾認為,“不滿足”是人類進步的動力,而“知足常樂”其實往往是無法遂欲之人對其嫉妒心的一種掩飾。接著,他一本正經地認為,這樣的嫉妒心,在包括中國、印度在內的東方人那里是最厲害的,其次是在包括西班牙人和法國人在內的南歐人那里,而在“自助的和奮斗的盎格魯—薩克遜人”那里自然是最輕的*Mill, John Stuart ,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New York: The Liberal Arts Press, 1958), 50.。這種“知足常樂”的、自由思考與創造力被壓制的民眾,恰恰為專制君主(despot)所喜愛,是專制制度的必然結果*Mill, John Stuart,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37-39, 52.。我想,當代中國讀者應該非常熟悉這類說法,因為它們仍是中國反傳統者用以自鄙的慣常說法。
“東方主義+無知”雖然可解釋中國專制說在西方的流行,但卻難以解釋它在始作俑者孟德斯鳩那里的產生。孟德斯鳩時代的歐洲,對中國充滿好感,上述“東方主義”態度很難加在孟德斯鳩身上。黃敏蘭在批駁侯旭東時指出,孟德斯鳩的專制說并非專門針對中國,而是同時指向歐洲所有的專制政體*黃敏蘭:《質疑“中國古代專制說”依據何在?——與侯旭東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并且,孟德斯鳩對中國也不是一味貶低*但黃敏蘭稱孟德斯鳩對中國是“褒多于貶”(黃敏蘭:《質疑“中國古代專制說”依據何在?——與侯旭東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恐怕就太隨意了。。當然,孟德斯鳩對中國的了解,確實是間接地通過其他人,而非親自學習中文,直接研究中國的歷史與政治。但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孟德斯鳩時代的歐洲對中國充滿興趣,其對中國的了解甚至要多于后兩個世紀的歐洲對中國的了解。孟德斯鳩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貴族,曾當選為波爾多學院乃至法蘭西學院的院士,對許多異域之事都很感興趣。除了從當時社會上(尤其是通過耶穌會士)獲得關于中國的知識外,孟德斯鳩還和一個中國來訪者有過非常廣泛的關于中國的交流*Anne Cohler, “Introduction,”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Anne M. Cohler, Basia Carolyn Miller, and Harold Samuel Stone eds. and tr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xiv.。因此,較之當時其他歐洲思想家(包括主流“中國迷”),以及后來兩個世紀的歐洲思想家,孟德斯鳩對中國的了解要更深入一些。于是,我們就面臨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孟德斯鳩對中國有如此負面的描述和評價?這是本文下節所要討論的重點。
二、孟德斯鳩的中國專制說
在《論法的精神》第二卷第一章,孟德斯鳩將所有政體分成三類:共和制(republican)、君主制(monarchical)、專制(despotic)。孟德斯鳩對三種政體的本質進行了界定,并認為哪怕受教育程度最少的人也會持有這些界定。其中,共和政體是人民擁有主權的政體。在共和政體里面,如果是全體人民擁有主權,那就是民主政體;如果是部分人擁有主權,那就是貴族政體(aristocracy)。君主和專制政體,都是一個人統治的政體。它們的區別在于,前者通過確定的法律來統治,后者則是“一個人自己,在沒有法律和規則的情況下,從他自己的意志和隨意的念頭里面引出所有的事情”*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10. 這種政體劃分是相對明晰的。王紹光批評孟德斯鳩的劃分混亂(王紹光:《政體與政道:中西政治分析的異同》,王紹光主編:《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第80-81頁),恐怕是因為他對孟德斯鳩的劃分沒有充分理解。當然,我們下面會看到,“專制”本身確實是一個易致混淆的概念。然而,這是現實本身的復雜性所致,并非孟德斯鳩的概念劃分有問題。。
在接下來的討論*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18-19.中,孟德斯鳩進一步指出,君主制中的法律掌管者需是君主自己的政務咨詢會(council)之外的政治實體,否則法律就沒有獨立地位,就無法約束君主。并且,除了法律約束之外,君主的權力還要通過貴族來制衡。孟德斯鳩甚至指出,貴族制衡是君主制的本質。此外,他還提到了教士階層和獨立城鎮對君主的約束*孟德斯鳩這里講的制衡與調節的力量,與當時法國政體中的軍事貴族、議會貴族、教士階層相呼應(Anne Cohler, “Introduction,”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xxii)。伏爾泰因此攻擊孟德斯鳩在這里無非是在為他所出身的那個階級(孟德斯鳩是法國貴族)進行辯護。參見Mark Hulliung的評論,收于Steven Cahn, Classics on Modern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22。王紹光也提出了類似的影射,參見王紹光:《政體與政道:中西政治分析的異同》,王紹光主編:《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第84頁。但是,對于貴族的作用,孟德斯鳩并非一味持正面觀點。例如,他指出,與中世紀的法國類似,波蘭和匈牙利的封建貴族勢力并沒有起到中介調節的作用;在西班牙,教士與貴族控制國家,占有土地,輕視商業,通過宗教教條阻礙經濟,這使得西班牙無法發展出一套工作倫理。參見Mark Hulliung的評論,收于Steven Cahn, Classics on Modern Political Theory, 322。總之,指責孟德斯鳩的立場受他本人出身背景影響,這種誅心之論本身似乎并不完全成立,而更重要的是,它似乎并不能對孟德斯鳩論證的正當性構成直接挑戰。。當這些制衡都不存在時,君主制就蛻變成了專制。
因此,孟德斯鳩區分專制與非專制政體(他有時稱其為溫和或有節制[moderate]的政府*例如,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28.)的關鍵,在于是否存在有效的制衡。但很有意思的是,孟德斯鳩接著上面的討論指出,專制中沒有獨立的法律制衡,而宗教和習俗就起到了替代性的制衡作用*Ibid., 19.。如果是這樣,那么專制與節制政府的差別何在呢?
所以,正如孟德斯鳩專家Anne Cohler所指出的,孟德斯鳩可能恰恰是要指出,“節制與專制是幾乎可以在任何政府里面都能找到的特征——[它們只是在]分量上不同罷了”*Anne Cohler, “Introduction”,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xxvii.。這在深受孟德斯鳩影響的托克維爾的論述里也有體現。據Cohler的理解,在《舊制度與法國革命》一書中,托克維爾指出,法國絕對(專制)君主之下的官僚沖動對君主的絕對性有所制衡,而在《論美國的民主》里面,他又指出了這種民主的專制與暴政傾向*Ibid., xxvii-xxviii.。實際上,孟德斯鳩本人就曾明確指出,英國革命的共和政體去除了以前君主制里面的各種制衡因素,如果它無法保證自由的話,英國人“將會是地球上最被奴役的人”*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19.。王紹光認為,以上情況說明孟德斯鳩的政體劃分充滿混亂*王紹光:《政體與政道:中西政治分析的異同》,王紹光主編:《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第80-81頁。。但我想指出的是,這種劃分之所以看似混亂,也許是因為我們先在地認定了民主與專制是對立的政體。但從孟德斯鳩角度看,這種認定恰恰是錯的。沒有制衡的民主,也是專制*王紹光本人其實也在挑戰民主與專制截然對立的觀點,但他可能沒意識到,孟德斯鳩正是這種挑戰的先驅。。
在討論了不同政體的本質與結構、運作的動力(他稱為“原則”,principle*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22.)及其他法律、規則之后,孟德斯鳩又探討了導致不同政體蛻變的因素。他指出,有一些因素能非常有效地保護這些政體的原則,并宣稱讀者只有讀過這些討論之后才會真正理解他*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123.,這些討論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他在這里所講的因素,是國家的大小。他認為,共和政體必須是小國,君主制國家需中等大小,而大國只能是專制或暴政(tyranny)。
順便一提,在《論法的精神》里面,孟德斯鳩還列舉了影響政體的其他因素,例如氣候與地理因素(《論法的精神》第三部分,第十四至十九卷)*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231-307.。這些理論現在看來雖近乎荒誕,但試圖提出不同因素借以理解政治的努力,卻是值得肯定的。并且,他未曾說氣候決定政體,因此并未陷入王紹光所批評的“氣候決定論”*王紹光:《政體與政道:中西政治分析的異同》,王紹光主編:《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第81頁。。王紹光批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充滿混亂,根本原因可能在于:孟德斯鳩并非王紹光所指責的政體決定論者,而是認為,政治的好壞,必須把許多具體因素考慮進來。在這一點上,孟德斯鳩恰恰與近現代西方主流思想界過度看重政體有所不同,而這種考慮情境因素、非簡單貼“民主”或“專制”標簽的做法,恰恰是王紹光的文章所意圖辯護的。
根據孟德斯鳩對專制的定義,以及他對中國的了解,我們不難明白,為什么他會認為中國是專制政體。傳統中國最終似乎由一個人統治。而同為一個人統治,君主制與專制的區別在于有無貴族的制衡。中國自秦以降,就不復存在具有自治權力的、在主流政治架構中占據地位的血統意義上的貴族。中國也不存在孟德斯鳩提到的其他兩種制衡力量:教士與獨立城鎮。并且,中國還是一個大國。因此,中國似乎只能是個專制國家。
不過,孟德斯鳩也因此遇到了麻煩,因為他的中國專制說與當時流行的中國形象(一個世俗的、道德的、開明的君主制國家)不符*孟德斯鳩明確承認主流中國形象的正面性(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126-127)。。對此,他先是指出,另有其他人提供了更符合他的理論的中國形象,一個充滿欺詐、暴虐、殘忍的國家。其次,他認為,那些對中國進行正面報道的教士可能心存偏見。因為天主教內部是等級制的,所以教士對中國的等級制度會有所偏好。中國由一個君主專制,這樣,傳教士只須說服君主,“得君行道”,即可以讓中國人都皈依天主教。孟德斯鳩認為,這是他們盛贊中國制度的原因。此外,孟德斯鳩承認,中國政府可能沒有一般專制政府那么腐敗,但這可能是一些特殊因素所致。首先,在世界上所有國家當中,中國女人有著最高的生育率,中國的人口因而不像在一般專制與暴政政體下那么少。中國女人的子宮永遠勝于暴君的屠刀。其次,中國依賴稻米生產,而稻米生產不穩定。這樣,壞的統治者會因稻米生產不穩定造成的混亂被迅速替代,而不像一般的專制國家,同一個暴君可以長時間虐待其人民*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127-128.。
最后幾個近乎荒誕的論述告訴我們,孟德斯鳩做了多么絕望的努力,以便削中國之實適他的理論之履。不過,除了理論上的自我辯護之外,孟德斯鳩貶低中國,可能還有另一個更深刻的動機。與其他法國啟蒙思想家不同,孟德斯鳩為歐洲找到了一個更好的典范,即在英國剛剛萌芽的基于制衡的憲政體系(特別參考他在《論法的精神》的第十一卷第六章的描述)*Ibid., 156-166.。甚至可以說,他是這套發展中的英國政治體系最好的早期理論總結者與發揚者,要比早于他的英國本土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在理論上更好地總結和完善化了英國的憲政體系。對于英國的認同,強化了他對中國的不認同,并促成了他心目中的負面中國形象。此后,歐洲乃至中國人自己關于傳統中國的負面印象,恐怕也與這種觀念,即英國或其他西方國家為世界提供了最好的政治模式的信念相關。此雖非直接出于西人傲慢與偏見的“東方主義”,或中國人自鄙的“自我東方主義”,但其背后的邏輯——“某一種西方是好的,因此其他各方都是壞的”——卻與“東方主義”實相呼應。
三、專制、極權、封建
傳統中國專制說肇始于孟德斯鳩,了解其對中國的描述之荒誕,也許會促使一些持中國專制說的人反思,甚至放棄這種說法。但是,對于多數持中國專制說的人來說,這恐怕不會產生什么實質影響。他們會說,英國的憲政制度就是好,所以,說傳統中國制度壞并沒有錯。更重要的是,孟德斯鳩之所以提出上面的荒誕觀點,是因為他要為傳統中國進行有限的辯護,并回應當時流行的中國正面形象對他的中國專制說的挑戰。當今主流反傳統者,則通常認為傳統中國是一個醬缸,其中并沒有什么正面的東西,因此也就回避了對孟德斯鳩糟糕解釋的需要。因此,要想從根本上駁倒傳統中國專制說,我們就不得不直面如下問題:傳統中國究竟是否專制?
在回應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需先澄清關于“專制”的幾個常見誤解與混淆。首先,“專制”尤其是其英語原詞“despotism”,如今常與“暴政(tyranny)”等詞混用。在日常語言中,它的含義則更加泛泛,可以指任何殘暴、嚴苛的人物、行為等。而在英語里面,最適合表達這種意思的詞匯是“autocracy(獨裁)”,“absolutism(專制主義)”亦相對適合*侯旭東援引北成的研究指出,專制用來翻譯“absolutism”并不好(侯旭東:《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但是,從孟德斯鳩對“專制”的定義看,absolutism(原意指君權的絕對性)確實與專制是一回事。。現在,“專制(despotism)”被當成絕對的貶義詞,乃是壞的人物與制度的代表。但是,相對另一些可能性,專制可能是個較好的制度。存在著比專制更壞的可能性,例如:所有人與所有人為敵的叢林政治,或者,像孟德斯鳩所理解的波蘭和匈牙利那樣,貴族專制其領地,而非君主專制整個國家*參見Mark Hulliung的評論,收于Steven Cahn, Classics on Modern Political Theory, 322。。針對后一種可能性,孟德斯鳩特別指出,專制統治者所威脅的對象,首先并主要是那些高級官員和重要人物*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28-29, 95. 閻步克也指出,專制政體不一定是最壞的,參見閻步克:《政體類型學視角中的“中國專制主義”問題》,《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較之更壞的可能性,在這種專制當中,人民反而可以得到喘息。
關于專制概念,政治理論研究一般傾向于從制度角度來理解它。因此,關于中國傳統政治是否專制問題,我們要考察的是其制度,而非某些特定的人物和事件。作為反例,針對錢穆為中國傳統政治所作的辯護,黃敏蘭提出這樣一些反駁:某朝某代某個君主或大臣如何濫用權力。幾千年的傳統中國政治,包括了太多的政治人物。并且,不同朝代的政治制度,甚至一個朝代內部不同時段的政治制度,相互之間都有很多不同。通過搜羅某某君主不受約束或罔顧制度約束行使權力的事例,論證中國傳統政治是專制,只能說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運用這種路數,我們甚至可以得出美國政治也是專制的結論,因為自美國立國以來,關于美國總統或者某些政要濫權乃至專制甚至暴政的指責,從未間斷過。不從制度上考察專制,我們也可能犯相反的錯誤。正如甘懷真所指出的:“今天對于皇帝制度是否為專制(絕對)的研究,必須從制度層面談,因為就個人的行為層面而言,沒有任何人的權力可能是絕對的。”*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第390頁。這一點,對于本文下面要講到的極權政體及其獨裁者,恐怕也是適用的。即使極權政體下的獨裁者如希特勒,其權力同樣難免受到其他人的限制。如果從個人而非制度層面考察,我們恐怕就要得出納粹德國不是專制或極權政體的荒誕結論。
所以,中國(或任何一個政治實體)是否專制,需要從制度層面進行考察。如果傳統中國曾經有過不同的制度,那么,我們就要考察其主流*比如,黃敏蘭在其支持傳統中國專制說的文章里,征引田余慶的研究指出,東晉門閥政治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治。但她接著斷言,這是皇權政治的變態(她認定皇權政治是專制政治),是短暫的。參見黃敏蘭:《質疑“中國古代專制說”依據何在?——與侯旭東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關于后一點,我們稍后再討論。。如果很難說哪個朝代或者哪種傾向是主流,那么,我們就應該專論某個朝代或某個時段的中國是否專制,而非以偏概全,一棒子打死。后者是持中國專制說之人常犯的錯誤之一。
明確了上述“制度”意識之后,我們還是要回到那個根本問題,即何為專制。“專制”這個詞在漢語中經常被用于各種不同的情境,此一事實意味著它在使用上的混亂*例如,侯旭東在《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一文中提到,在1949年以前的教科書里,“專制”一詞被加在不同時代的不同政治實體頭上。又如,宋洪兵指出,嚴復、梁啟超以及當時的很多人都混淆了“君主制”與“專制”(《二十世紀中國學界對“專制”概念的理解與法家思想研究》,《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這里,我們不妨采用一個修正版的孟德斯鳩定義,即專制即一個人或一個政治實體在一個政治系統內部享有不受制度限制的權力。不過,我們要把一般所說的“專制”,與20世紀才出現的作為專制之極端的“極權政體”區分開來。簡單分析“極權政體”的英文“totalitarianism”可知,它是一種“全面(total)控制”,即對該政治系統內部所有人的所有生活方面進行控制。英國政治史家芬納(S. E. Finer)即是如此定義極權統治,并將之與一般意義上的專制相區分的。他指出,極權主義或極權主義專制是“在所有時間,對所有人口,就所有事務,統治者都擁有不受約束,任意而為的自由”,而“這種政體的物質前提直到當前的世紀才出現”*[英]芬納:《統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權和帝國——從蘇美爾到羅馬》,馬百亮、王震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56頁。。納粹德國是極權政體的代表。極權控制的一大特征就是,意圖且確實能夠相對有效地控制人的思想。
不區分極權與專制,我們就會經常做出錯誤的歷史投射,借批古代來消解今人塊壘。我們一提秦始皇焚書坑儒,就想到納粹燒書與殺戮猶太人。但是,前者只針對精英,而且也并非以全民思想改造為目標。后者針對大眾,并意圖控制他們的思想。這并不是說韓非子或秦始皇等不想做后者所做的事情,而是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這是可能的。但不管是他們不想做還是沒有條件和能力做,我們都不應該用20世紀的極權去想象前工業化時代的專制。反過來,我們也不能僅僅因為前工業化的政體不是極權,就說它(們)不是專制。芬納明確指出了這一點*[英]芬納:《統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權和帝國——從蘇美爾到羅馬》,第56頁。。閻步克在其討論中國專制主義的文章里,也引述并認同芬納這個觀點*閻步克:《政體類型學視角中的“中國專制主義”問題》,《北京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
另一個常見的混淆就是混同專制與封建,這一混淆常被“封建專制”的提法所強化*筆者在一篇通俗文章里,已經處理了這個問題,參見白彤東:《直面傳統,去“封建專制”之污名》,《南方周末》2014年2月28日。。這個詞常常泛指中國傳統政治,或者稍微精確一點,用來指秦以后的制度。按照侯旭東的考察,日本疑為“封建專制”說的源頭*侯旭東:《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第13頁。。馮天瑜也指出,所謂陳獨秀是“封建專制”說在中國的始作俑者,乃是一個在學術上明顯站不住腳的觀點:該說在當時幾乎無人認同,后來卻變成中國人的歷史共識,而其學說來源其實是日本*馮天瑜:《“封建”考論(修訂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192-215頁。。到了1939年,毛澤東也開始用“封建專制”指稱秦以降的中國傳統政治*侯旭東:《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第24頁。,這種說法隨著1949年革命的勝利,最終成為中國大陸關于中國歷史的標準說法。當然,在臺灣、香港等地區,這種說法也很常見,但似乎沒有大陸用得那么廣泛。
這種說法,在歷史和概念上,均站不住腳。歷史上,中國西周制度最接近歐洲意義上的封建制,盡管二者存在很多重要不同。秦以后中國實行的是反封建或非封建的郡縣制。概念上,很多學人已經指出,古典封建制度恰恰不是專制的,或者常常不是專制的。
例如,意大利政治思想家拉吉羅指出:“‘在法國,自由是古典的,專制才是現代的。’斯塔爾夫人的這句話,頗道出了歷史的事實。自由與現代君主制下的專制相比,確實更為古老,因為它植根于封建社會。”*[意]圭多·德·拉吉羅:《歐洲自由主義史》,楊軍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頁。英國思想家阿克頓同樣引述斯塔爾夫人的這句話,指出:“根據歐洲大陸最著名的女作家的一句名言——自由是古老的,專制才是新的。證實這一名言的正確性,已是最近之史學家的榮耀。希臘英雄時代證實了它,在條頓人的歐洲則表現得更加明顯。”*[英]阿克頓:《自由的歷史》,王天成等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頁。臺灣學者甘懷真也明確指出,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君主,與后來的絕對(專制)君主不同*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第385頁。。
雖然孟德斯鳩不同意這樣的截然區分*參見Mark Hulliung的評論,收于Steven Cahn, Classics on Modern Political Theory, 322。,但是這一區分確實可以在孟德斯鳩理論中找到某種支持。在西方中世紀乃至近代早期的封建政體以及中國西周的封建政體中,當上一級貴族(乃至一國之君主)和下一級貴族形成權力上的相互制約關系時,自由就產生了,這樣的政體因而就不是專制政體(當然,孟德斯鳩會補充說,即使存在封建貴族,但相互之間若形不成制衡,則封建君主制度也可以是專制)。其實,在陳獨秀、郭沫若等人罔顧中國歷史、扭曲“封建”一詞在中西方的通常用法之前,一些中國學人也意識到,西周君主制并非專制,而封建貴族的消亡,才為后來的君主專制奠定了基礎*參見閻步克所引梁啟超的說法(《政體類型學視角中的“中國專制主義”問題》,《北京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
就本文主題而言,不區分封建與專制,我們可能犯下“關公戰秦瓊”的錯誤。例如,黃敏蘭在其綜述中國專制說爭論的文章中,雖然也引了前述“自由是古代的,專制是現代的”說法,但其對于“封建”一詞的使用卻是混亂的:一會兒是我們上面所說的歷史和理論上的正確用法,一會兒又滑到經陳獨秀、郭沫若扭曲之后的用法*黃敏蘭:《質疑“中國古代專制說”依據何在?——與侯旭東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在其更早的反駁侯旭東的文章中,黃敏蘭長篇大論地談到歐洲君主與中國的皇帝不同,即前者不具有絕對權力。但是,她所謂的歐洲君主,都是歐洲封建時代的君主。而按照上述歷史與概念的分疏,如果要進行中西比較,那么,歐洲封建時代應和中國西周時代相應,歐洲后封建時代的君主則相應于中國秦以后的皇帝*順便指出一點:按照這種制度比較,筆者近年來提出的一個看似極端的說法,即周秦之變乃是一種現代化,其實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實。。
四、中國是否專制?
在厘清專制及其相關概念之后,我們回到問題的核心,即中國是否專制。這里所謂“專制”,采取上一節給出的修正版的孟德斯鳩定義。這個定義的關鍵在于,對統治者權力的制度性限制。而考察的對象,應該是秦以降的兩千年傳統政治,而不是西周的政治,因為如上一節所述,西周的封建貴族政治并非專制,這是任何明白專制的含義并了解西周制度的人都會得出的明顯結論。
論到中國秦以降的傳統政治,宋洪兵指出,嚴復和梁啟超都反對中國專制說。梁啟超尤其指出:“是故中國之君權,非無限也,欲有限而不知所以為限之道也。”*宋洪兵:《二十世紀中國學界對“專制”概念的理解與法家思想研究》,《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但這種說法是模糊的,因為限制之制度的存在乃至有效與否,是區分專制與節制政體的核心,主觀的期望不能算數。黃敏蘭也在文章中指出,雖然費孝通和吳晗持中國專制說,但費孝通承認,中國皇帝的權力是受限制的。吳晗則反駁說:“雖然在理論上、在制度上,曾經有過一套以鞏固皇權為目的的約束辦法,但是,都沒有絕對的約束力量。”*黃敏蘭:《質疑“中國古代專制說”依據何在?——與侯旭東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不過,黃敏蘭所引的吳晗這段話,實際上反駁了中國專制說,因為吳晗在這里承認存在著對皇權的制度性限制。同時,吳晗這里犯了一個理論上的錯誤:他給“非專制”加了一個過高的要求,即對皇權的絕對限制。
據侯旭東考察,在西方,利瑪竇、維科、伏爾泰、魁奈等都對中國專制說持保留態度。利瑪竇認為,中國在一定程度上是貴族政體,其中,皇帝的權力是受到限制的*侯旭東:《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魁奈雖然用“專制”稱呼中國政體,但是侯旭東指出,魁奈的“專制”其實更接近“君主制”的意思。特別地,魁奈認為,中國制度中有“明智和確定不移的”法律,皇帝只是執行者,必須遵守這些法律*侯旭東:《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按照我們修正過的孟德斯鳩定義,這樣的制度,在法律的獨立性有制度保障的前提下,肯定不是專制。其實,即便孟德斯鳩也指出了中國政體與典型的專制政體的許多不同*對此,王紹光收集了很多相關說法,參見王紹光:《政體與政道:中西政治分析的異同》,王紹光主編:《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第83-84頁。。
那么,傳統中國政體里面,到底存不存在有效的、制度性制衡?如前所述,在孟德斯鳩看來,這種制衡,來自貴族等因素(當然,如前所述,有貴族不一定有制衡)。“廢封建,立郡縣”之后的中國,總的來說并不存在歐洲中世紀以及近代早期的血緣性的、在其屬地內有很大自治權的封建貴族。就此而言,似乎自然可以說,秦以后的傳統中國是專制的*按照黃敏蘭的考察,梁啟超就認為因為中國沒有貴族政治,所以中國是專制的。參見黃敏蘭:《質疑“中國古代專制說”依據何在?——與侯旭東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宋洪兵對梁啟超的看法與此不同,參見宋洪兵:《二十世紀中國學界對“專制”概念的理解與法家思想研究》,《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但上述黃氏說法本身,無論是不是梁啟超的看法(或只是善變的梁啟超在某一階段的看法),其預設卻符合孟德斯鳩對專制的理解。而這個說法的問題之一在于,梁啟超(或者黃敏蘭所呈現的梁啟超)似乎忘了,歐洲非專制的貴族政體,在中國西周早就存在過。有意思的是,閻步克引用梁啟超的說法意在展示,梁啟超的意思其實是:西周是貴族政體,中國因而也曾有過非專制的階段。參見閻步克:《政體類型學視角中的“中國專制主義”問題》,《北京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筆者非梁啟超專家,茲將不同說法列在這里,供有興趣的讀者進一步探究。。而在后封建時代,按孟德斯鳩的理解,英國發展出通過權力分立進行制衡的憲政體系。不過,在孟德斯鳩所討論的英國政體里面,貴族依然存在。與此相應,孟德斯鳩自然而然地認為,傳統中國沒有這種權力分立的憲政體系。但是,孟德斯鳩并非政體決定論者,他(正確或錯誤地)注意到了傳統中國制衡專制的一些因素,因此在對中國政體進行判定時,他還用了一些含混的說法。其實,是否存在制衡雖然似乎是專制與節制的區分之所在,但在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孟德斯鳩自己也認為,專制制度里宗教和習俗也有制衡作用*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19.。區別僅僅在于份量不同*Anne Cohler, “Introduction,”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xxvii.。閻步克也指出,“‘無限權力’并不是說君主權力不受限制,只是說限制的大小有別,權力的集中化程度有別”*閻步克:《政體類型學視角中的“中國專制主義”問題》,《北京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也就是說,區別僅在于在從純粹節制到純粹專制這個光譜上的相對位置。
不過,閻步克還進一步指出:“‘中國專制主義’概念的反對者,至今沒能提供這種譜系化的比較。”*閻步克:《政體類型學視角中的“中國專制主義”問題》,《北京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但問題是,堅持傳統中國專制說的人,他們給出譜系化的比較了嗎?并且,他們的比較是否是針對制度,又能否兼顧中國秦以降兩千年各朝代甚至朝代內部明顯不同的制度呢?從我們前面考察過的那些文章看來,持中國專制說的人恐怕并未達到這些要求。下面,我們就從“份量”上、從在“光譜”上的相對位置的角度,考察一下傳統中國專制說是否成立。
我們首先回到孟德斯鳩。雖然他承認中國傳統政治里面存在制衡因素,但是他堅持給中國傳統政治貼上“專制”的標簽。究其原因,大概是他覺得這些制衡因素至少是無法與運行良好的封建貴族君主制中的制衡因素相提并論,更無法與當時英國形成的制度相比。站在孟德斯鳩角度看,這個結論確實是有道理的。專制中的制衡因素是宗教與習俗。在西方啟蒙運動者看來,中國是世俗國家,并不存在宗教(歐洲意義上的)。因此,制衡的因素就只剩下習俗,而習俗看起來確實不像強有力的制衡因素。
但是,正如錢穆先生所指出的:“貴族世襲的封建制度,早已在戰國、秦、漢間徹底打破。然而東漢以來的士族門第,他們在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地位,幾乎是變相的封建了。”*錢穆:《國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1996年,第296頁。前面提到,黃敏蘭援引田余慶的研究,亦認為東晉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治,但她辯駁說這是傳統中國政治的變態。參見黃敏蘭:《質疑“中國古代專制說”依據何在?——與侯旭東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但如果錢穆先生的講法正確,則這個“變態”的持續時間還是挺久的。如果我們接受錢穆(以及田余慶)先生的判斷,并且,如果我們承認封建制與節制政權相關聯,且承認運行良好的封建制是節制政體的話,那么,秦以后士族門第興盛的時代,就不應該被歸為專制。
那么,在士族門第不占主流的時代呢?前面提到的,受到孟德斯鳩影響的托克維爾就曾指出,法國絕對(專制)君主之下的官僚沖動對絕對君權有所制衡*Anne Cohler, “Introduction,”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xxvii-xxviii.。也就是說,官僚是替代貴族的一個可能選項。而孟德斯鳩本人可能沒有看到這一點。這種制度,其實是現代國家的一個重要標志與普世特征;而理性官僚制在秦帝國已經引入,并且成為兩千年中國傳統政治無法放棄的制度。此為筆者近年提倡“秦以降的中國已經是現代國家”一說的主要依據之一。與此相對,歐洲的理性官僚制,是在現代早期才開始成長起來。在孟德斯鳩時代的法國,這種制度剛剛萌芽。因此,孟德斯鳩既不了解這樣的體系,也不理解中國的官僚體系及其可能的制衡作用,乃是很正常的。實際上,當談到包括中國在內的專制國家時,孟德斯鳩常用的詞匯,往往是特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詞匯(例如,參見《論法的精神》第二卷第五章)*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20.。
在反駁錢穆的“有相權即非專制”的說法時,閻步克指出,“孟德斯鳩已指出,‘宰相’的存在恰好是專制政權的特征”*閻步克:《政體類型學視角中的“中國專制主義”問題》,《北京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他沒有指出孟德斯鳩這種說法的出處。我想,他所指的應該是我在前一段中給出的文獻。但是,孟德斯鳩在那里的用的詞是“vizir”,這個詞是用來指稱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中的大臣的。孟德斯鳩給出了他自己對這種大臣的解釋*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20.。他指出,專制者自然是“懶惰、無知、充滿欲望的”,因此他就必須把對公共事務的管理“外包”出去。但這又不能外包給太多人,因為這樣會產生爭吵,君主將不得不進行裁斷。因此,他就把所有事情委托給“vizir”,而這個被委托者不過是“第一奴隸”而已。
但是,余英時則認為,“君權是絕對的(absolute)、最后的(ultimate);相權是孽生的(derivative),它直接來自皇帝”*轉引自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第386頁。順便一提:余英時持此種論調,究竟在何種意義上可被稱為錢穆的弟子?。閻步克也認為,文官制的“發達反而是專制的條件”*閻步克:《政體類型學視角中的“中國專制主義”問題》,《北京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這里的關鍵問題是,傳統中國的官僚系統是不是孽生的,是不是專制君主的執行者乃至打手?我們需要意識到,“官僚”這個詞有很大的誤導性。官僚確實具有一定的被動執行者形象。但對于官僚的這種理解,直接與前面提到的托克維爾的理解相沖突。并且,這種被動執行者形象,恐怕更符合韓非子所描述的“北面委質,無有二心”、“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韓非子·有度》*本文所引《韓非子》據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的臣下的特征。如果我們承認儒家對傳統中國有重要影響的話,那么,傳統中國官僚更準確的提法應該是“士大夫”。相關制度規定(注意,這里談的是制度性保證),這些士大夫官僚的教育與選拔以儒家經典作為依據;這些經典所內含的及其被解釋出來的天道觀、道統觀,使得士大夫具有獨立于皇帝的意志,而這種獨立意志又通過制度得以伸張。這種獨立而非孽生的士大夫官僚體系,完全有可能對皇權起到制衡作用。
除了士權(包括相權)對皇權的制衡外,傳統中國還有很多其他源自儒家的制約皇權的制度。例如:皇帝死后的萬世名聲由儒家通過謚號來控制;皇太子由儒家教育;除了秦制之外,傳統中國的大部分時期,縣以下由士人與鄉紳自治;等等。當然,我們可以繼續爭論這些制度是否有效制衡了皇權。然而,正如孟德斯鳩所認識到的那樣,封建貴族政體也不能保證不專制。中國的士大夫郡縣政體(尤其考慮它在兩千年中的不同形態),可能也無法提供這種保證。但分析至此,我們至少可以承認,這里的譜系差別并非黑與白的截然反差!
此外,上面的論述其實還存在一個問題:它似乎把皇權與專制君主等同起來。但是,錢穆早就有中國政權乃一種信托政權之說*侯旭東:《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甘懷真進一步發揮了其中的含義*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第387-390頁。。他首先指出,今天中國史研究的一個危機,就是用西方歷史的概念框架來套中國。其中,與本文相關的是,在專制問題的討論上,把西方的主權觀念及與此相關的家長制,套在了傳統中國皇權與家長制上。在西方,作為主權者的君主或家長,擁有國與家內部的所有權力。甘懷真轉引的法國專制君主路易十五(也是孟德斯鳩在世時的國王之一)的話,能夠很好地說明這一點:“主權只存在我的人身,法庭的存在與權威只源于我一個人……立法權也完全屬于我一個人……所有公共秩序也來自我,因為我是它的最高捍衛者。”*轉引自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第390頁。如此絕對的君權,如果不加限制,當然就是專制。但是,在儒學作為官方主流意識形態的傳統中國,其君主和家長,只不過是(國人或家人)公產的管理者。在這個框架下,君主、家長、臣民、家人各有其分,“皇帝沒有權利決定別人的分,因為這些分在皇權出現前即已存在了”*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第389頁。。
甘懷真在這篇文章中,把傳統中國的安分、合禮與西方的守法觀念進行了區分。其實,這種“分”、這種“禮”,與“法”是相關的。至少在有些朝代,合禮也即守祖宗之法,非個體君主所能改變*例如,參見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朝政治述略(修訂版)》(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的細致考察。。
前面提到,完全“孽生”于君主的官僚,更接近韓非子所代表的法家理想。韓非子欲使臣下進入“無為”、“聽令”乃至“竦懼乎下”的狀態(《韓非子·主道》),此常被視為韓非子支持君主肆意妄為的專制暴政的證據。但值得注意的是,韓非子同樣要求君主“虛靜以待令”(《韓非子·主道》)。君主所待的,是“道”的命令。臣下不敢違法,是因為君主手握二柄。君主不敢違道,是因為政治之道以國家興亡為二柄控制著君主。按照韓非子的看法,臣下守法、君主守道,都有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自利性作為根據。近一百多年來,亦有評論者強調:法家主張的是法治,而非專制*宋洪兵:《二十世紀中國學界對“專制”概念的理解與法家思想研究》,《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當然,正如本文第二節所展示的,對孟德斯鳩來講,節制政權的關鍵在于法律有獨立性,并且還要有獨立的政治實體(比如貴族)來制衡君主。但是,我們同樣應該注意到,在韓非子看來,君主與凡人一樣具有根深蒂固的自利性,此會成為他守道、守法的根本動力,因此會保證法律的“一”與“固”。而且,我們還可以反問:歐洲的封建君主政體,以及近代早期涌現的絕對君主政體(專制政體),其中是否都有韓非子式“君主守道”的說法?如果有,并且如果其中還存在著孟德斯鳩所說的維護法律的獨立機構以及制衡君主的貴族實體,那么,其實際效果是否真的就比韓非子的理想政體或是秦制要好?畢竟孟德斯鳩認為,除了這些制度性因素外,還有很多其他因素會讓一個節制政權蛻變成一個專制政權。前面提到,節制與專制是一種譜系性的差別,而非黑白分明的差別。
除了與運轉良好的封建政體進行比較之外,專制與否的另外一個標桿,是筆者前面所猜測的孟德斯鳩改變歐洲的中國印象的誘因,即被孟德斯鳩理想化了的英國式憲政政體。在孟德斯鳩對英國憲政政體的討論中(《論法的精神》第十一卷第六章)*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156-166.,我們看到,在這種理想的節制政體中仍然存在著封建貴族。因此,上述很多比較,也可以轉化為與英國憲政的比較。一般來講,只要我們承認傳統中國存在制度性的制衡,那么,傳統中國制度,尤其是那些基于儒家的制度(其中吸收了法家“因道全法”(《韓非子·大體》的法治精神),就與西方憲政有了可比性。限于辯護性目標,本文對此就不再進一步展開了。簡單來說,雖然筆者不同意一些當代儒者所謂儒家或傳統中國一直存在憲政的說法,但是筆者同樣不同意一些反對者把傳統中國等同于專制,并因此將之與憲政對立起來的說法。傳統中國試圖對權力進行制度性制衡,在這一點上是可與西方憲政相比擬的,甚至我們可以說,它有憲政因素。或者,我們也許應該放棄憲政專制這個對子,承認憲政之外還有其他節制政體。
五、結語:反對傳統中國專制說的意義
本文并非簡單地斷言傳統中國政體不是專制,而是說,兩千年傳統政治從理論到實踐都是多元的光譜性存在。在此光譜中,某些時段的中國傳統政體,可能比歐洲的所謂節制政體更不專制。缺乏對“專制”的深入理解,缺乏對傳統中國之復雜性的認知,用“專制”標簽把傳統中國一棒子打死,這在理論上是幼稚、有害的,在實踐上是危險的。其理論上的害處是:在“傳統中國=專制”、“專制=壞制度”的前提下,得出“傳統中國政治一片黑暗”的結論,從而使得我們無法正視傳統中國的政治理論與實踐資源,無法公允地評價中國政治的得失(乃至認為只有失沒有得),更談不上從其得失中吸取正面的經驗和反面的教訓。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在20世紀30年代,主流思潮強烈地否定傳統中國政治,錢穆想開一門中國政治制度史的課,但性本謙和的歷史學系主任反對,其理由大致是:“中國秦以下政治,只是君主專制。今改民國,以前政治制度可勿再究”。錢穆“屢爭”才開出這門課,但開始居然沒有學生正式選課*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169-170頁。對于傳統中國政治的這種否定,在今天依然是主流。例如,政治理論學者唐世平最近一篇廣為傳播的文章,就號召大家少沉迷中國歷史,多了解世界文明,因為“中國歷史,特別是公元1840年前的歷史,其實是非常乏味的”。參見唐世平:《多了解一點世界》,《南風窗》2015年第3期。。
傳統中國專制說在理論與實踐上的實際危害就是,誤解了傳統中國的問題,為近一百五十多年來的“有病亂投醫”種下了禍根。我們已經看到,孟德斯鳩的中國專制說存在很多問題。實際上,我們是在西方以及日本的侵略下進退失據,出于一種弱者或失敗者心態全盤接受了這種有問題的觀點,甚至發展出“封建專制”這種言辭不通的說法。如果真正理解孟德斯鳩,我們應該知道:反封建,容易走向專制;而要制衡專制,封建恰恰是很好的手段。由此來看,中國百年來“反封建專制”不果,也就沒有什么稀奇的了。
以儒家為背景的整套政治制度與社會組織,可能恰恰是中國很早地進入后封建社會后(比歐洲早了兩千年)借以制衡專制的方式。至于這種制衡是否有效,我們需要對傳統中國進行節制專制的光譜分析,這是一個可以爭論的問題。即使傳統中國實際上更偏向光譜的專制一側,我們也不應該去批儒家,因為儒家式制度與組織恰恰旨在制衡權力。但新文化與“五四”運動,恰恰以“孔家店”作為主要攻擊對象,廢除科舉(1905)則是這種攻擊在制度上的一個重要開端。當這些制衡性制度與組織被打擊殆盡的時候,中國社會就只剩下原子化的個人,而在個性解放的旗號下,作為專制制度的極端形態的極權政治,便很容易不受制約地誕生*黑格爾對中國充滿偏見,但是他所謂“中國人既然是一律平等,又沒有任何自由,所以政府的形式必然是專制主義”(轉引自侯旭東:《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既是對孟德斯鳩思想的繼承,亦很好地(具有諷刺性地)描述了后“五四”的中國。。這恰恰是孟德斯鳩的理論預言。可惜的是,我們只學習了孟德斯鳩問題重重的傳統中國專制說,卻未能深入了解他對專制政體本身的正確分析。簡言之,把傳統中國錯誤地當做專制國家全盤否定,反而會因消解了制衡因素而導致真正的專制。
上述觀點不可避免地會對其他學者相關論斷形成挑戰。例如,閻步克指出:“如果承認‘中國專制主義’的話,還能帶來這樣一個學術便利:有利于對當代中國的若干重大政治現象提供解釋。清王朝瓦解僅40年,一個全新的中央集權體制即得重建。毛澤東掌握了巨大的個人權力,甚至出現了個人崇拜與‘文革’悲劇。這僅僅是外源因素造成的嗎?”*閻步克:《政體類型學視角中的“中國專制主義”問題》,《北京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
但如果本文的解釋是正確的,那么,“文革”的悲劇確實不僅僅是外源因素造成的,新文化與五四運動以來國人對傳統中國的錯誤理解,特別是“中國專制”說廣泛流行是其重要內因(當然,這不是說新文化與五四運動反傳統必然會導致“文革”悲劇)。而且,“文革”的一個重要攻擊對象,恰恰是兩千年來作為中國傳統政治之核心的理性官僚系統,它的崩潰反過來加重了“文革”的惡果。此外,如果用清代的專制解釋“文革”的專制,那么,如何解釋世界上其他深受中國傳統影響的國家或地區能夠相對順利地轉型?這些國家或地區并沒有直接經歷新文化和“五四”洗禮,其領袖要比中國大陸的領袖更擁護傳統,就此而言用清代專制解釋“文革”專制乃是成問題的。
與閻步克從批判傳統中國專制角度進行“文革”批判相反,本文屢次提到的王紹光的文章則通過批判“傳統中國專制”說進而批判“(傳統與當代)中國專制”說。筆者雖然同意他對中國專制說的一些分析,但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觀點。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不同在于,雖然本文反對傳統中國專制說,但筆者同時認為,“文革”時的中國,確實出現了專制乃至極權的現象。而傳統中國專制說,是要為此負責的。
在周秦之變中,中國可能已經早于西方兩千年,提前進入了后封建社會。當然,這種早熟不能保證中國一直領先。西方在公元1500年左右邁向后封建社會,其中一些制度嘗試,中國歷史上已經出現過。其真正的創新,是在英國發展出來的憲政*因此,與啟蒙時代的其他思想家不同,孟德斯鳩選擇英國而非中國作為理想目標,這一點是有道理的。他的錯誤在于,為了爭奪話語權,去貶低中國。更大的錯誤則是,中國的學人與政客,吸取了他的錯誤,卻拒絕了他的正確方面。,以及此后的工業革命。相應地,傳統中國則需要從早熟版的后封建社會,向另一種版本的后封建社會過渡。簡單地用“中國專制”論,從理論和實踐上否定傳統中國政治,等于直接割斷了這種過渡的線索。早熟版的后封建中國社會中包含許多好的東西,如以科舉為基礎的理性官僚制、鄉紳自治等制度與實踐,以及為接引工業化社會而有必要進一步加強的“書同文,車同軌”、“編戶齊民”等傳統做法。這些好的東西,有源自儒家的,也有源自法家的。我們錯誤地去學習法國、日本等從封建社會進入后封建社會的方法,在割斷中國固有線索的同時,卻并沒有順利地學到我們應該去學習的東西。這可能是百年來中國問題的最終根源。
簡而言之,改正我們的錯誤,應該從質疑“傳統中國專制”說開始,應該從與新文化與五四運動告別開始。
[責任編輯李梅鄒曉東]
白彤東,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上海 200433)。
本文系上海高校特聘教授(東方學者)崗位計劃、上海哲學與社會科學規劃一般課題“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現代意義”暨教育部基地課題“古希臘羅馬政治倫理研究”(12JJD72001)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