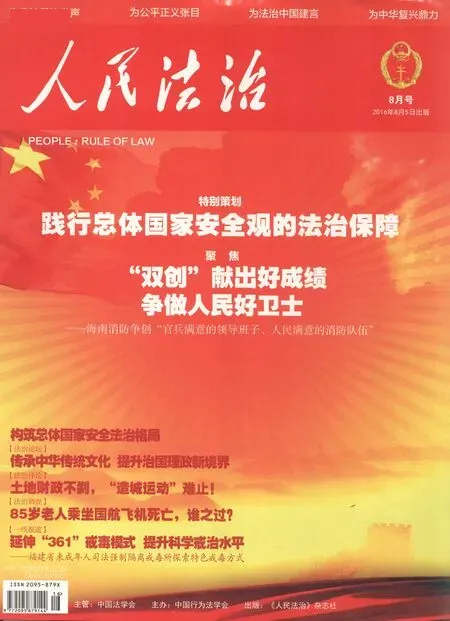新疆生產(chǎn)建設兵團對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作用
文/陳欣新
新疆生產(chǎn)建設兵團對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作用
文/陳欣新
新的《國家安全法》明確規(guī)定,文化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安全問題在本質上是實踐提出的問題,而不是單純的理論問題,并具有復雜性、隱蔽性和長期性。就新疆地區(qū)而言,今后相當長時間內(nèi),在文化安全領域必須同時面對來自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裂勢力以及恐怖主義的外來威脅。兵團文化是在克服自然界惡劣條件和應對各種復雜形勢的環(huán)境中,在與外國強權威脅和三種勢力破壞進行長期艱巨的斗爭中,逐步積累形成的,是我國歷史上“屯墾戍邊、保家衛(wèi)國”文化的新發(fā)展,是中華文化的寶貴財富,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的《國家安全法》從總體國家安全觀出發(fā),將國家文化安全列為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安全法》第三條明確規(guī)定,“國家安全工作以文化安全為保障”。文化安全在本質上是實踐提出的問題,而不是單純的理論問題。文化安全問題具有復雜性、隱蔽性和長期性,從確保國家文化安全,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先進文化提供可靠的文化環(huán)境的角度,加強對文化安全戰(zhàn)略問題的研究,應該成為必須強調的一個長期而又緊迫、艱巨的任務。
我國面臨的文化安全威脅
新的《國家安全法》著力維護各領域國家安全,構建國家安全體系,走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而文化安全領域突出體現(xiàn)了中國特色的國家安全觀。首先,中國特色的國家文化安全要求意識形態(tài)安全,即“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fā)展道路,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其次,國家文化安全要求文化產(chǎn)業(yè)安全,即文化產(chǎn)業(yè)具有強大的競爭力、文化市場健康有序、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再次,國家文化安全要求文化事業(yè)得到大發(fā)展大繁榮,即中華文化具有強大的創(chuàng)造力和生命力。第四,國家文化安全要求中華文化富有包容性,能夠吸收和借鑒人類文明在文化領域的先進成果,能夠勇于丟棄舊有糟粕,實現(xiàn)自我完善和進步。總結人類歷史經(jīng)驗,文化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水平尤其是文化創(chuàng)造活力,從根本上決定了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的程度,而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從根本上決定了文化安全的水平。當然,文化安全為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提供秩序保障,并具有反作用。
1.文化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威脅
世界范圍內(nèi)不同文化類型之間長期的相互交流、碰撞及融合,形成了充滿活力的國際多元文化發(fā)展圖景,為中國面向現(xiàn)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發(fā)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和環(huán)境。但是,在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交流的過程中,也有一些奉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國家為了維護其在經(jīng)濟和政治上的利益,不斷利用其國力優(yōu)勢,推行“文化殖民”政策,形成了日益嚴重的“文化帝國主義”傾向。這些文化殖民者以損害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qū)本土文化為手段,強力傳播本國的文化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圖謀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新的方式延續(xù)和強化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對全世界的操控。作為發(fā)展中國家的中國,由于在文化、意識形態(tài)、社會制度、國家利益等諸多方面與某些發(fā)達國家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分歧,自然而然地成為某些推行文化霸權主義國家進行文化滲透和文化顛覆的主要目標之一。這就決定了中國未來相當長時間內(nèi)必然面臨來自外部的嚴峻的文化安全挑戰(zhàn)。
2.境外敵對勢力利用一切手段進行全方位的文化滲透
當一個國家的文化在全球范圍內(nèi)成為主流文化,其價值觀支配了國際政治秩序,它就必然在國際社會中居于領導地位。因此,對發(fā)展中國家特別是另類意識形態(tài)的發(fā)展中國家進行文化滲透就成為發(fā)達國家最有力的進攻方式。目前,西方部分發(fā)達國家利用一切手段大力宣揚西方推行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以近乎強制的方式加強對發(fā)展中國家的文化滲透和文化輸出。
在理論層面,反華勢力推行以“西方中心主義”為基礎的各種人文、哲學社會科學理論,宣揚西方的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例如,將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稱之為“狹隘的民族主義”;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價值,稱之為“極權主義”;用西方的價值觀念和多重判斷標準,否定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根據(jù)中國國情現(xiàn)實地推進中國的人權、自由、民主、平等的努力。搞亂民眾的思想,破壞中國人民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消解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在具體方法上,反華勢力除了繼續(xù)進行意識形態(tài)攻擊,以及通過廣播、電視、電影、報紙、雜志等文化產(chǎn)品的輸出,公開或隱蔽地推銷其社會政治理論、價值觀念、意識形態(tài)和生活方式外,還利用其網(wǎng)絡優(yōu)勢,通過網(wǎng)絡這只無形的手,實施信息壟斷,以網(wǎng)絡所特有的穿透力突破傳統(tǒng)的國家概念和框架,潛移默化地改變著人們傳統(tǒng)的語言交流規(guī)則和行為方式。而中國作為相對被動地接受信息的國家,在對抗西方文化的滲透、防范信息霸權方面顯得力不從心,在一些領域甚至出現(xiàn)了嚴重的“集體失語”現(xiàn)象。
一方面,文化涉及到一個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它包括“價值、規(guī)則、體制和在一個既定社會中歷代人形成的思維模式”。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凝聚和激勵全國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消解民族文化,必將化解中華民族的內(nèi)在凝聚力,造成中國深層次的“文化弱勢”,削弱中國的綜合國力。
另一方面,西方生活方式的滲透和理論上的話語霸權,將使中國主流文化價值體系失去在社會生活中的主導地位。如果一個國家失去了這種共同的、穩(wěn)定的基本價值觀念,或者是分裂為許多不同的相互沖突的價值觀念,或者是遭到外來文化的入侵在短時間內(nèi)失去了自己的主導地位,那么社會中具有不同基本價值需要、運用完全不同的話語體系的各利益集團就必然沿著不同價值觀念的邊界進一步發(fā)生深刻的、乃至不可彌合的分裂,進而引發(fā)整個社會的大分裂、大動蕩。與此相關,諸多社會組織,包括國家和執(zhí)政黨的價值基礎也一并遭到懷疑,由于失去文化價值的支撐而必然產(chǎn)生的“合法性危機”將導致國家意志、價值觀念、國民心理上的全面崩潰。在組織內(nèi)部,組織的規(guī)則失去應有的約束力,組織內(nèi)部出現(xiàn)一種離心現(xiàn)象,整個社會將陷入一種嚴重的無序化狀態(tài)。與此同時,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價值基礎也會被動搖,引發(fā)諸多社會、心理問題。
就新疆地區(qū)而言,除了來自西方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因素的文化滲透外,還有宗教極端勢力假借被歪曲的伊斯蘭教義和被扭曲了的阿拉伯文化而進行的文化滲透,這一文化滲透主要針對受教育程度低的少數(shù)民族人群,在南疆地區(qū)的威脅尤甚,并且具有通過新疆地區(qū)向內(nèi)地發(fā)展的潛在威脅,更有極端勢力利用恐怖主義手段推行其分裂國家破壞民族團結的主張,是今后相當長時間內(nèi)我國文化安全領域必須面對的同時涉及宗教和民族事務的主要威脅之一。為此,《國家安全法》第二十八條規(guī)定,“國家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加強防范和處置恐怖主義的能力建設,依法開展情報、調查、防范、處置以及資金監(jiān)管等工作,依法取締恐怖活動組織和嚴厲懲治暴力恐怖活動”。
新疆生產(chǎn)建設兵團在維護國家文化安全方面的功能
兵團文化是幾代兵團人秉承井岡山精神、南泥灣精神,在近60年的歲月里,在克服自然界惡劣條件和應對各種復雜形勢的環(huán)境中,在與外國強權威脅和三種勢力破壞進行長期艱巨的斗爭中,逐步積累形成的,是我國歷史上“屯墾戍邊、保家衛(wèi)國”文化的新發(fā)展,是中華文化的寶貴財富,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兵團要在新的歷史時期更好地發(fā)揮“建設大軍、中流砥柱、銅墻鐵壁”作用,需要不斷加強對兵團文化的提煉、傳播和推廣,以引領新疆地方先進文化的發(fā)展方向,為兵團繼續(xù)創(chuàng)造輝煌提供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精神支持。
1.成為探索、支撐和發(fā)展新疆特色的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的擎天柱
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是中國共產(chǎn)黨在總結中國歷史上邊疆治理的經(jīng)驗教訓并揚棄參考蘇聯(lián)治理少數(shù)民族區(qū)域做法的基礎上,根據(jù)建國初期的中國國情所創(chuàng)建的治理少數(shù)民族聚居地方的制度。經(jīng)過60多年的實踐,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已經(jīng)成為國家治理少數(shù)民族聚居的邊疆地方和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憲法制度。有鑒于此,《國家安全法》第二十六條規(guī)定,“國家堅持和完善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鞏固和發(fā)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加強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防范、制止和依法懲治民族分裂活動,維護國家統(tǒng)一、民族團結和社會和諧,實現(xiàn)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fā)展”。
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的核心思想是:“生活在民族區(qū)域自治地方的各民族和睦相處、均衡參與自治事務”,盡管某些民族區(qū)域自治地方在名稱上冠以“某某族自治”的字樣,法律也規(guī)定由各該少數(shù)民族的成員擔任地方行政首長,容易使人望文生義地認為,該地方就是某個或某幾個少數(shù)民族行使自治權進行治理,但是,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的本質是“多民族共和自治”而不是“個別民族壟斷自治”。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是我國多層級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的典型,也很好地體現(xiàn)了“多民族分級共治”的特點。兵團自創(chuàng)建以來,對新疆的發(fā)展和穩(wěn)定起到了重要的支柱作用,未來應在探索、支撐和發(fā)展新疆特色的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的制度創(chuàng)新過程中,發(fā)揮積極的作用。從制度設計上看,兵團在地域建制上屬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但是,在組織建制上接受中央和自治區(qū)的雙重領導。這正是新疆特色的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在制度設計上區(qū)別于其他省級民族區(qū)域自治地方的一大重要特點。從制度功能上看,不論兵團的創(chuàng)建還是復建,都兼具“邊疆治理”和“地方發(fā)展”的雙重目的,但是,這兩種功能的地位和性質不同。就國家對兵團的功能要求而言,邊疆治理是全局性、基礎性功能,地方發(fā)展是局部性、附屬性功能,因此,任何時候,兵團都必須堅持“地方發(fā)展服從、服務于邊疆治理”這個全局性、根本性、戰(zhàn)略性目標,這與某些特定時空條件下,中央要求兵團將具體工作重點放在地方發(fā)展的戰(zhàn)術性安排上不存在矛盾沖突,而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因此,從功能上講,在邊疆治理方面,兵團承擔中央管治權延伸的職責;在民族區(qū)域自治方面,兵團是參與新疆民族區(qū)域自治的主體之一;在地方治理方面,兵團是新疆內(nèi)部部分次級地方的治理主體。全面準確地認識兵團在國家邊疆治理、新疆民族區(qū)域自治及地方治理三個層次上的不同功能至為重要。
2.在新疆發(fā)展、弘揚中華各民族多元一體的文化價值
費孝通先生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提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觀點。這一觀點在文化安全領域也具有極高的理論價值。中華文化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各組成部分原有文化經(jīng)過幾千年的相互碰撞、吸收、融合,逐漸發(fā)展形成的“多元一體”的有機體。而兵團文化正是新疆地區(qū)最典型地體現(xiàn)上述特點的代表。在兵團管轄的地區(qū),就文化的地域性而言,中國東西南北中的地方文化均在兵團有所體現(xiàn)。并經(jīng)過近60年的融合形成了聚五湖四海文化于一身的獨特性格。就文化的民族性而言,兵團文化以漢族文化為主體,兼具維吾爾、哈薩克、蒙古等幾十個邊疆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組分。就文化的職業(yè)性而言,兵團文化以軍旅文化為基礎,兼有城市市民文化和農(nóng)村村民文化的形態(tài)。特別是在兵團近60年的發(fā)展歷程中,各種形態(tài)、不同起源的區(qū)域和民族文化在這個特殊的社會群體中不斷交流、磨合,形成了以漢文化為主體,兼具多民族、多地域色彩的一種特殊文化形態(tài)。兵團組建之初就認真貫徹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在極端艱苦創(chuàng)業(yè)的條件下出色完成了新疆許多骨干工程的建設任務,為新疆的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奠定了基礎。在實現(xiàn)自身發(fā)展的同時,兵團還在努力發(fā)揮示范和輻射作用。60年來,兵團人和新疆各族人民和睦相處,其無私奉獻的境界也集結為兵團精神并傳承下來,邊塞文化與中原文化交匯,少數(shù)民族文化與漢民族文化融合,軍旅文化和地方文化共存,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兵團軍墾文化。
歷史地看,兵團所處的地域屬于古代西域,是一個多種宗教文化集聚的地方。從那些作為文物的洞窟以及文化成果中可以看到,新疆既有佛教,又有伊斯蘭教,甚至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多種宗教和文化長期并存。所以,新疆兵團不僅多民族的人生活在一起,各個宗教也都融合在一起,如果沒有高度的包容性,是不可想象的。新疆的文化,也是歷史的沉淀,其豐富性無與倫比。居民構成的多樣性、地域色彩的豐富性、各種宗教的包容性、各族文化的兼容性,造就了新疆兵團成為難得的文化富礦,也是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充分體現(xiàn)。
3.引領新疆先進文化的發(fā)展方向
中國歷史上的“屯墾戍邊文化”,一直是同時期少數(shù)民族聚居邊疆地區(qū)“地方先進文化”的代表,屯墾戍邊的將士往往是隱形文化融合和文化同化的重要主體。由于復雜的歷史原因,少數(shù)民族聚居的邊疆地區(qū)無論在生產(chǎn)力發(fā)展水平、社會發(fā)展水平還是文化發(fā)展水平上,與內(nèi)地都存在巨大的差距。漢族執(zhí)政的中央王朝對少數(shù)民族聚居的邊疆地區(qū)往往采取羈縻模式進行治理,不采取強制性漢化措施,而是通過實施“屯墾戍邊”、鼓勵民間交往等方式,隱形帶動邊疆地區(qū)的文化融合和社會進步。相比之下,由少數(shù)民族執(zhí)政的中央王朝或對峙割據(jù)型政權,為了提升自身發(fā)展,往往采取更為主動的“胡漢分治”及“推進漢化”的戰(zhàn)略措施。
《國家安全法》第二十三條規(guī)定,“國家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防范和抵制不良文化的影響,掌握意識形態(tài)領域主導權,增強文化整體實力和競爭力”。以“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艱苦創(chuàng)業(yè)、開拓進取”為主要內(nèi)涵的兵團精神是兵團文化的核心。這種精神與黨的十八大提出并倡導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yè)、誠信、友善”24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符合,既有其特殊的含義,又傳承了中華文化的精髓。兵團文化體現(xiàn)并維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具有為屯墾戍邊事業(yè)提供強大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增進民族團結,保持社會穩(wěn)定,維護祖國統(tǒng)一的功能。兵團軍墾文化繼承了中國歷史上“屯墾戍邊”文化的優(yōu)秀傳統(tǒng),不僅肩負著傳承中華文化、傳播主流文化、發(fā)展民族文化、創(chuàng)建特色文化、服務屯墾戍邊、造福職工群眾的職責,更肩負著文化戍邊的歷史使命。中央對兵團的定位是“既要當好生產(chǎn)隊、戰(zhàn)斗隊,又要當好工作隊、宣傳隊”,這就要求兵團必須更好地發(fā)揮推動改革發(fā)展,促進社會進步的建設大軍作用;增進民族團結,確保社會穩(wěn)定的中流砥柱作用;鞏固西北邊防,維護祖國統(tǒng)一的銅墻鐵壁作用。“三大作用”的實現(xiàn),需要通過對兵團軍墾文化建設的不斷推進,使兵團上下形成統(tǒng)一的思想文化基礎。
先進性是兵團文化的本質特征。首先,兵團文化的發(fā)展是軍旅文化。人民軍隊是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武裝力量。兵團屯墾戍邊事業(yè)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fā)展觀。其次,科技教育是推動社會進步也是推動文化進步的重要力量。兵團探索創(chuàng)建新疆的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工商建設企業(yè),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為新疆各族人民起到了示范作用。新技術和發(fā)明創(chuàng)造提高了兵團和新疆的生產(chǎn)力水平,影響并改變著新疆各族人民的生產(chǎn)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以及風俗習慣。兵團在新疆較早地建立完整的教育體系,確保兵團有一支高素質的職工隊伍。兵團人來自全國各地,在綠洲內(nèi)部無時不發(fā)生著文化的交流與碰撞,實現(xiàn)著文化的揚棄與創(chuàng)新。
4.樹立民族團結、和睦相處、開放包容的文化范例
兵團軍墾文化是在繼承中國兩千多年的屯墾戍邊思想并在不斷實踐中逐步形成的新的文化形態(tài),不僅是對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和發(fā)展,也融合了當?shù)氐拿褡逦幕屯鈦砦幕哂袕姶蟮陌菪浴H诤闲允潜鴪F文化的形態(tài)特征。首先,兵團文化是歷史文化與時代精神的融合,它既繼承發(fā)揚了中華民族優(yōu)秀的文化傳統(tǒng),又具有鮮明的社會主義時代特征。其次,兵團文化是全國各地域文化的大融合。兵團人來自五湖四海,他們帶著滿腔的熱情、操著不同的方音來到兵團這塊熱土,在國家、民族精神的感召下自愿扎根邊疆,承擔起屯墾戍邊的歷史使命與責任,帶來了內(nèi)地先進的生產(chǎn)技術和生產(chǎn)經(jīng)驗,帶來了內(nèi)地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風俗文化背景下的生活方式,帶來了具有內(nèi)地文化特色的精神文化產(chǎn)品,更好地滿足了邊疆各族群眾的精神文化需要,推動邊疆形成了開放和融合的文化。促進了東西部文化的交流。
再次,兵團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融合。某一文化的先進程度取決于其對外交往和善于辯證地吸收其他文化的優(yōu)秀成果的程度。文化來源的多元化造就了兵團文化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兵團人是一個以漢民族為主體,包括維吾爾、哈薩克、蒙古、回等少數(shù)民族在內(nèi)的多民族的社會群體。兵團文化包含著各民族的優(yōu)秀文化元素,使兵團文化能借助于地緣優(yōu)勢,融西北游牧文化、中原農(nóng)耕文化、現(xiàn)代城市文化、軍旅文化于一體,形成以軍墾文化為核心,聚合不同地域和民族文化的優(yōu)點于一體的交融型文化,具有極強開放性、包容性、創(chuàng)造性的特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一批又一批各地大中專院校畢業(yè)生加入兵團,投身邊疆建設,兵團文化的多元化、交融化特色日益凸顯。
5.探索和實施新時期中華文化“和平西進”戰(zhàn)略
在長達幾千年的歷史上,以漢文化為主體的中華文化因其具有在特定時空條件下的相對先進性,而具有極強的文化擴張力和同化力,但是,這種文化擴張和同化是以強大內(nèi)功自然延伸以及繼受者自愿接受為前提的,不是憑借武力和強權實現(xiàn)的,這與當前文化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存在根本性區(qū)別。中華文化“西進”在歷史上具有重要的文化戰(zhàn)略和國防戰(zhàn)略意義,許多朝代尤其是漢族王朝中央政權的領導者也十分重視通過中華文化西進實現(xiàn)維護國防、民族和睦融合、多元文化的一體化、以文化認同和文化同化促進國家認同和鞏固統(tǒng)一。清中期以后,中華文化的西進因落后的專制制度造成國力的衰弱而受到嚴重阻滯。相反,帝國主義和分裂勢力(后來是三股勢力)卻借機在近200年的時間內(nèi),實施“文化東進”,通過文化殖民和文化異化,企圖破壞中華文化的一體性,撕裂、切斷中華民族不同民族組分之間的文化紐帶。為了遏制當前三股勢力假借極端伊斯蘭宗教教義和故意扭曲的外來文化,推行文化滲透,進而分裂國家和中華民族的圖謀,《國家安全法》第二十七條明確規(guī)定,“國家依法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宗教活動,堅持宗教獨立自主自辦的原則,防范、制止和依法懲治利用宗教名義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違法犯罪活動,反對境外勢力干涉境內(nèi)宗教事務,維護正常宗教活動秩序”。歷史和現(xiàn)實的經(jīng)驗教訓提示我們,單靠防衛(wèi)性文化安全戰(zhàn)略難以改變在文化領域被動挨打的局面,必須采取積極主動的文化安全戰(zhàn)略,這就是總結歷史上中華文化西進的經(jīng)驗教訓,結合當前乃至今后相當長時間內(nèi)的國情和國際形勢尤其是周邊區(qū)情,形成新時期中華文化“和平西進”的戰(zhàn)略部署并切實實施。
6.探索在新疆實現(xiàn)伊斯蘭教本地化
在新疆實現(xiàn)伊斯蘭宗教及相關文化本地化,應成為確保新疆長治久安的重要戰(zhàn)略措施。實際上,就歷史經(jīng)驗而言,佛教實現(xiàn)漢化和回族實現(xiàn)伊斯蘭教本地化就是成功的先例,伊斯蘭教本地化在世界上也是有先例的。就世界范圍而言,最大的伊斯蘭教國家是印度尼西亞,印度尼西亞90%以上的人口信奉伊斯蘭教。但是,在印度尼西亞信奉伊斯蘭教的公民與信奉其他宗教或不信教的公民在風俗習慣上形成了相互尊重、相互影響的局面。這一事實表明,即使在伊斯蘭教處于國教地位的國家,伊斯蘭教教義也可以容忍非伊斯蘭教民眾的文化、生活方式和宗教習俗存在。目前,三種勢力采取歪曲伊斯蘭教教義和扭曲中東文化主要是阿拉伯文化的方式向新疆等地信奉伊斯蘭教的民眾實行文化滲透和文化異化,企圖利用極端宗教原教旨主義和外來文化達到割裂中華民族、割裂中華文化的目的,進而破壞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破解這一難題的辦法就是逐步實現(xiàn)伊斯蘭教本地化,伊斯蘭教本地化不僅可以確保包括維吾爾族在內(nèi)的新疆信奉伊斯蘭教的少數(shù)民族民眾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落實,也可以使新疆長期形成的本地文化與外來伊斯蘭教文化有機地結合起來,還有利于多種文化的融合以及伊斯蘭教自身的發(fā)展與完善。對于國家安全而言,伊斯蘭教本地化可以從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tài)領域實現(xiàn)中國的國家主流意識形態(tài)與少數(shù)民族文化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生活方式之間的協(xié)調,從根本上避免不可調和的沖突。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